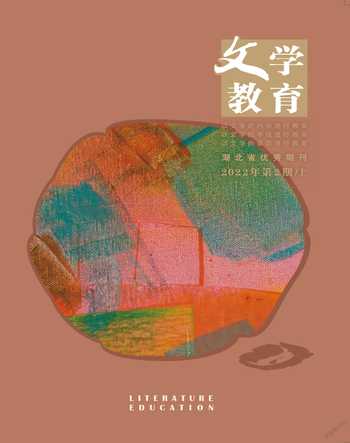余華《文城》浪漫敘事中的人性思考
王鄴彤
內容摘要:余華長篇小說作品《文城》在敘事風格上顯現出其一貫打破傳統現實主義的特點,“文城”作為虛構的“余華世界”具有濃烈的浪漫主義色彩,“補篇”的存在是余華浪漫敘事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余華在《文城》中對具有復雜性和難以解決的人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討論角度和看法,這一鑲嵌在傳奇浪漫敘事中的人性思考也是他為讀者留下的永恒命題。
關鍵詞:《文城》 余華 浪漫風格 敘事 人性
余華《文城》講述了突然出現的小美成為林祥福的妻子,為林祥福生下女兒后離開,林祥福帶著女兒踏上去“文城”尋找小美之路,卻沒能找到文城,便和女兒落腳溪鎮等待小美歸來……這部作品展示了余華后期創作的混雜性,即雖然保留著他的歷史感和現實感,打破現實主義描寫方式,關心著普世的人性問題,卻在文體上保留著現代性,敘事中彰顯著浪漫主義風格。在都市生活繁榮發展的今天和現代化語境下,這部飽受爭議的長篇新作或許能用它自己的世界和傳奇故事帶給我們對于更普遍問題的思考。
一.多角度的浪漫敘事
浪漫主義注重創作上的自由、表達內心感受和傳達強烈的情感、展現自然風景與風物。愛情主題是浪漫主義作品常見的主題。《文城》作為一部傳奇性的小說作品,在敘事進程中不乏“浪漫”因素的存在,余華通過使用敘事策略,使整個愛情故事具有了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普通的愛情故事成為了時代縮影下傳奇般的存在,余華為現代讀者創造了獨特的世界,它是一個普通卻永遠無法被主人公找到的江南水鄉,也是一片只有作者與讀者能夠探尋到的浪漫土地。
余華的現實描寫突破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方式,用一種“虛偽的形式”去探求表面下的真相,他說:“當我發現以往那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職能導致表面的真實以后,我就必須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尋找的結果使我不再忠誠所描繪事物的形態,我開始使用一種虛偽的形勢。這種形式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實。”①這段話標志著八十年代余華對敘事的創新,也開辟了一條滿足內心表達自由的新道路,盡管過去多年,余華的創作走到了晚期的階段,讀者依然能在《文城》中發現這種不符合現實秩序和邏輯的“余華世界”,這種超越現實的敘事為這部作品帶來了浪漫與充滿想象的豐富色彩。
浪漫色彩也在林祥福一直尋找的江南水鄉文城中彌漫開來。江南水鄉是余華出生成長的地方,“江南文化的一個突出內涵就是其抒情性”②,余華的創作一直有一種“回到南方”的特點,小說《文城》核心故事的發生地“文城”或說“溪鎮”,就是一個地道的江南水鄉。對林祥福來說,在多年尋找文城無果之后,這座叫做“文城”的江南小鎮變成了他對小美的感情寄托。而對溪鎮來說,這數年的歷史發展和時代變化中又刻著深重的現實印記,其中不乏對戰亂時代風景與風物的描寫,這些看似是鋪敘,用來渲染氣氛的內容是連接殘酷現實和人之情義的橋梁,這使江南水鄉和其中的人物充滿浪漫主義的強烈情感。林祥福被殺害后由田氏兄弟拉著棺材回故鄉,“曾經是稻谷、棉花、油菜花茂盛生長的田地,如今雜草叢生一片荒蕪;曾經是清澈見底的河水,如今混沌之后散出陣陣腥臭”,這一對比鮮明的風景描寫照應著林祥福的慘死,更為戰爭下溪鎮的灰暗現實籠罩上一種了無生機的窒息之感。小說的標題叫做“文城”,文城的神秘性和林祥福寄托與此的深沉感情都具有浪漫主義的氣息。從補篇可知,林祥福在尋找時已經離開溪鎮前往文城,但他始終覺得溪鎮更像文城,哪怕尋找無果,他還是認定文城就是溪鎮,從此在溪鎮等待小美。林祥福帶著女兒留在溪鎮為這一漫長的愛情故事和凄美結局做了鋪墊,同時也奠定了小說的浪漫基調。
補篇的存在成為完成浪漫敘事的關鍵。在正篇中,小美從天而降又突然消失,其背景身世是缺失的,而讀者也更多關注作品“講了什么”,而對“為何不講什么缺乏探究心理”。余華在《文城》的第一部分中對小美的敘事空白或許就是一種有意為之的敘事策略。“作為敘事交流的重要手段,敘事空白乃是敘事話語中的沉默和空白,是缺席”③,這種空白成為連接作者創作意圖和讀者主觀接受之間的橋梁,讀者或許自發為小美的離開找到了基于自己經驗判斷的原因,以此滿足自己對這一故事情節的期待。然而實際上,當故事走向尾聲,讀者內心深處依舊對主人公小美有著好奇和困惑,如果故事到這里就戛然停止,那么小美和林祥福的愛情故事也只是林祥福一生故事中的一個重要插曲,兩個人的愛情故事自然也說不上浪漫,而補篇作為小美的“個人傳記”,不僅補足了第一部分中的敘事空白,解答了讀者的困惑,更讓小美和林祥福的愛情故事實現了亂世中愛情的悲劇性和傳奇性。同時真相的揭示讓整個故事情節更加具有連貫性和完整性。在小美去世十七年后,林祥福才來到埋葬小美的地方,然而這時候林祥福也已經離世,“小美的名字在墓碑右側,林祥福躺在棺材左側,兩人左右相隔,咫尺之間。”這是小美離開后兩人第一次距離如此之近,但卻無法見面,真相也將永遠被掩埋,文城依舊無處可尋,在溪鎮的半生也未能等到愛人,兩人各有各艱辛的人生與不如意,只有之后兩人終于見面的這天,“西山沉浸在安逸里,茂盛的樹木覆蓋了起伏的山峰,沿著山坡下來時錯落有致,叢林竹林置身其間,在樹木綿延的綠色里伸出了它們的翠綠色。青草生長在田埂與水溝之間,聆聽清澈溪水的流淌。鳥兒立在枝上的鳴叫和飛來飛去的鳴叫,是在講述這里的清閑。”與兩人顛沛流離與被命運支配的一生相比,在生命逝去后來到彼此身邊,在與時代形成強烈反差的安逸閑適的自然環境中完成“相見”,無疑完成了對兩人愛情故事的浪漫敘事。
余華在第一部分中對小美生平敘事的缺席存在是一種策略性敘事空白的體現,這種空白突顯了補篇的重要意義,使結尾成為整個故事的高潮,達到了實現浪漫敘事“隱而愈顯”的驚人效果。余華突破現實主義傳統敘事特點的再次呈現在他的作品中,讀者在敘事空白存在的過程中不得不和全知敘事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一處理方式讓敘事的接收者獲得了和林祥福一樣真切的感受和情感體驗,實現了浪漫敘事對濃烈情感的表達。這種策略性敘事空白“有意不讓讀者迅速弄清所有事件,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有效地控制了讀者的情緒,更好地將讀者的闡述引導到作者希望的軌道上來,以實現作者的敘事意圖”④,余華因此實現了他浪漫敘事的意圖。
二.人性底線與情感限度的思考
余華在《文城》中不僅繼續突破現實主義的浪漫敘事,更保持了他一貫在作品中所關注的歷史與現實中的人性問題。林祥福和小美的浪漫故事其實是一場時代與命運支配下的殘酷悲劇。正是戰亂社會環境中這樣的傳奇經歷和具有浪漫色彩的故事,使作品對人性極限的反映和思考顯得更具張力,《文城》在這一問題上的探討可以分為兩個不同方面。首先是困難境遇中人對于善惡人性的自我選擇與底線思考,其次是作者對愛情主題的關注,即小美與阿強、小美與林祥福的愛情與婚姻,他們的愛情是被封建傳統歷史、個人性格與選擇以及時代命運捆綁的愛情,這樣的愛情必然是難以正常生長和生根發芽的,其必然引發思考的是——在這種“一妻二夫”的復雜感情中,人的情感限度及其具有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當父母身處其中,子女又將承擔何種命運?
雖然林祥福和小美是故事的主線,但小說同時展現了動亂年代江南小鎮的人物群像,其中有代表著終極仁義又勇敢有謀略的商會主席顧益民、認為想要在亂世中生存下去就只能當壞人做壞事的土匪水上漂和尚等人、為了保護良家婦女不受侵犯不得不被送出去犧牲和受傷的妓女們……亂世中普通人所表現出來的真善美和仁義是作者堅持表現的善良主題,而在自身難保時善與惡如何判斷和自恃則是人性最真實的反映。布萊希特早在其戲劇《四川好人》中就提出了苦難生活中“誰是好人”和“如何讓好人有一個好結局”的問題,他在收場白中無奈又不乏希望地感嘆道“事情既然如此,解決辦法會是怎樣,我們未能找到解決辦法,金錢也枉然。應該是另外一個人,或者是另外一個世界?……我們已無能為力,這不是裝模作樣……人世間一定有一個美好結局,一定,一定,一定!”⑤在筆者看來,余華在《文城》中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并保留了樂觀的希望。其中他塑造的土匪“和尚”這一角色,讓人看到了苦難生活中善與好人的希望。“和尚”雖然是土匪的一份子,但他內心保持著善良和憐憫的人性,和殘忍至極的水上漂等土匪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世道的不太平讓這些善良之人很難有立身之本,人們只好用傷害他人的方式來保全自己。傷害別人盡管不是“善”的選擇,也并不符合傳統意義上的倫理道德,但這種保全自己去“作惡”的“善”的人性底線應該在哪里?人在向善的路上遇到了威脅自己生存的外在障礙應該何去何從?這些依然是沒辦法做出評判標準的重要倫理問題,這一人性問題的矛盾性也成了永恒的話題。布萊希特讓沈黛(隋達)在劇中道出這種無解的困惑:“做好人又要生存,它像閃電一般將我劈成兩半。我不知道,對人對己也好,怎能兩周全。”⑥余華也讓“和尚”在小說中說道:“身處這亂世若想種田過日子,必遭土匪劫殺;若做上土匪,不搶劫又活不下去。”“和尚”一直走在向善的路上,最后和尚和張一斧同歸于盡,完成了他能做的所有善事,這是“和尚”的選擇,也是作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和尚”雖然不是主角,但卻是人物群體中一個重要的角色,他身上所肩負的對于人性問題的探討以及他最終對于善惡的選擇,是作者想要傳遞給我們的重要信息。
傳統中國文學作品中對于以男性為中心的愛情問題的思考不在少數,而《文城》則探討了以女性為中心的“一妻兩夫”的情感和道德問題。小美原是貧苦家庭的孩子,因為原生家庭沒辦法同時養活幾個孩子只好送小美去做童養媳,而當時的阿強家作為經濟實力雄厚的家庭自然成為“小美們”的家長向往的親家。如果說小美不得不被送到阿強家做童養媳說艱難時世的逼迫,那么她在阿強家受到的婆婆抹殺小女孩天性的殘忍行為則是封建傳統的思想為她套住的枷鎖,到此為止她的顛沛流離和坎坷的人生命運是那個窮人沒有生存辦法的時代和封建社會造成的。但從她離開溪鎮,她和阿強的命運更多的就是自己選擇的結果。兩人在逃離的路上難以維持生計之時,小美多次積極地想用自己的手藝去養活自己,而阿強則陷入悲觀和不想付出現實行動的猶豫與怯懦中,小美在好壞的境況中都堅定地追隨阿強,而阿強卻為了能生存下去愿意讓小美和一個陌生男人生活在一起。薩特的存在主義指出,每個人都有進行自我選擇的行動自由,但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應該為他人承擔起自我選擇帶來的結果和責任。而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也包括忠誠、誠信、仁愛等內容。面對兩個不同的男人和生存困境,小美做出基于情感和道德上的選擇,以此來緩解自己內心對帶走林祥福的孩子、偷走林祥福的金條產生的內疚和罪惡感。若時間與歷史都停留在此,這場關于情感與道德極限的問題看似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但時間終究還是成為檢驗并擊破這一情感道德沖突的罪魁禍首,由此也再次向人們宣告,人類情感的極限潛藏在欺騙隱瞞背后,其所具有的人類未知的可能性也不應該被視為擺脫困境的救命稻草。
多年后,當林祥福帶著林百家來到溪鎮,看似早已經成為歷史的“一妻兩夫”的問題再次成為小美家庭的危機以及內心煎熬的苦難。這一問題無疑在感情上還是道德倫理上都難以實現某種盡善盡美和平衡,哪怕是封建社會和戰亂世道導致的命運所趨的結果也無法讓人接受。這種兩難境地存在于小美、阿強和林祥福三人之間,也同時影響了兩代人的情感糾葛與其后代自我身份的缺失。長大之后的林百家雖然離開了戰亂的溪鎮,但從小到大母親的缺失將成為她整個人生中揮之不去的傷痛。與余華其他作品中的母親形象來進行對照,余華依舊在這部小說中去尋找母親的存在,盡管這位母親只能作為缺席的存在,但余華通過母親的缺席傳達出來的是他對時代與人性的思考,“母親沒有錯,錯的是那個對婦女極為苛刻的社會,她們道德刻碑不只是自身的可悲,而是社會的可悲”⑦,作為母親身份的小美是時代的產物,也是這個時代中突破人情感限度的產物。婚姻、愛情與代際情感的悲劇結局更是必然性的。試看,林百家在已經和顧家訂立婚約之后又把自己全部熱烈的情感都留給了陳耀武,這似曾相識的婚姻與愛情糾葛或將再度成為一種兩難的選擇……
丁帆教授對《文城》的評價是“如詩如歌、如泣如訴的浪漫史詩”⑧,確實,《文城》保持著余華一直以來突破傳統現實主義敘事的方式,使用“敘事空白”的策略使真實的讀者跟隨著隱含讀者的腳步進入作者已經鋪墊好的情緒,人物與情節在第一部分中都為讀者保留了大量的空白,因此補篇帶來的傳奇性與浪漫性才能在結尾部分達到高潮,而那不可忽視的江南文學特有的抒情性和浪漫性也在小說對于環境鋪敘的細節描寫之處得到體現。更為重要的是,浪漫敘事的背后對人性的思考是深刻的,余華將生存困境中人性的復雜與自我選擇的悖論完全展現給讀者,并用故事的悲劇性與人物形象的塑造給出了他的答案,而未完開放的故事結局則需要身為讀者的我們做出屬于每個人的選擇。
參考文獻
[1]余華.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
[2]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N],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3]韓松剛.回到南方——余華小說論[J].當代作家評論,2019(03):132-138。
[4]涂根年.敘事空白及其意義生成[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6): 62-66。
[5]涂根年.策略性敘事空白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15(03):109-114。
[6] (德)貝托爾特·布萊希特著,丁揚忠譯.四川好人[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7]蘆海英.論母愛缺失對作家創作的影響——以王朔和余華為例[J].青海社會科學,2019(03):175-179。
[8]丁帆.如詩如歌 如泣如訴的浪漫史詩——余華長篇小說《文城》讀札[J].小說評論,2021(02):4-14。
注 釋
①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160頁。
②韓松剛:《回到南方——余華小說論》,《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3期。
③涂根年:《敘事空白及其意義生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④涂根年:《策略性敘事空白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
⑤[德]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四川好人》,丁揚忠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
⑥同上。
⑦蘆海英:《論母愛缺失對作家創作的影響——以王朔和余華為例》,《青海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⑧丁帆:《如詩如歌 如泣如訴的浪漫史詩——余華長篇小說<文城>讀札》,《小說評論》,2021年第2期。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