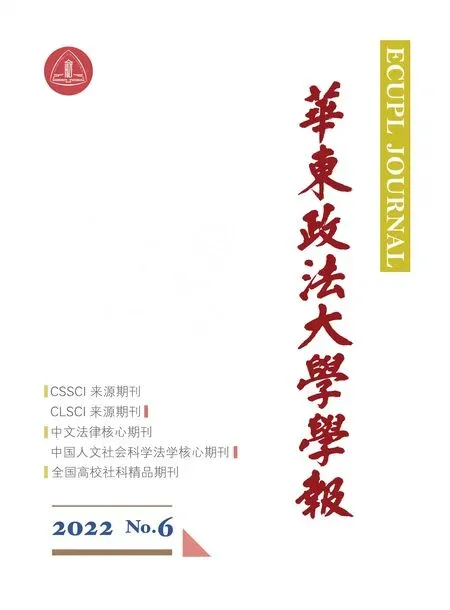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中的疑難爭議問題
李奮飛
目 次
一、“合規不起訴”的適用對象問題
二、企業犯罪分離追訴的可行性問題
三、檢察建議模式的實踐性質問題
四、合規考察和第三方監督評估的關系問題
五、合規整改驗收的決策主體問題
六、有效合規與不起訴決定的關系問題
七、第三方監督評估的工作屬性問題
八、合規犯罪預防功能的絕對化問題
九、結語
“21世紀的大趨勢不是對公司罰款和定罪,而是檢察官改變公司的治理方式。如今,檢察官正嘗試重塑公司,協助建立發現和預防雇員犯罪機制。更廣泛地說,培養內部的道德和誠信文化。”〔1〕[美]布蘭登?L.加勒特:《美國檢察官辦理涉企案件的啟示》,劉俊杰、王亦澤等譯,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頁。自2020年3月起,在服務“六穩六保”、優化營商環境、加強民營企業司法保護的背景下,我國開啟了一場由檢察機關主導的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探索以更為謙抑和輕緩的方式辦理涉企犯罪案件,嘗試將合規作為從寬的理性依據。這場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署啟動,現已推向全國的改革最為原始的效仿對象和靈感來源是域外的“審前轉處”程序。〔2〕自2007年的美國金融危機時期,司法制度的設計者們開始認識到,企業定罪會帶來巨大的負效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其前車之鑒就是2002年的安達信案件。參見陶朗逍:《美國企業犯罪的審前轉處協議研究》,載《財經法學》2020年第2期,第140-141頁。可以說,正是在借鑒域外審前轉處程序運轉經驗的基礎上,我國檢察機關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種通過釋放現有檢察權能所蘊含的從寬處理空間尤其是相對不起訴來處理涉企犯罪案件的新思路。此項改革不僅在穩定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檢察機關參與社會綜合治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開拓了實踐路徑。至2022年4月,此項改革試驗已在全國范圍內推開。
兩年多來,各地檢察機關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推進和指導下,將“嚴管”和“厚愛”相結合,積極延伸檢察職能,大膽探索實踐,辦理了一大批企業合規案件。截至2022年8月底,全國檢察機關累計辦理涉案企業合規案件3218件,其中適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2217件,對整改合規的830家企業、1382人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3〕參見蔣安杰:《樹高千尺總有根——新時代刑事司法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路》,載《法治日報》2022年9月28日,第9版。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辦案經驗。也正是得益于實踐經驗的逐步積累,一些改革初期呈現的難題和爭議已經基本解決,〔4〕參見陳瑞華:《企業合規不起訴改革的八大爭議問題》,載《中國法律評論》2021年第4期,第1-29頁。包括“合規不起訴”能否適用于“企業家”犯罪案件、中小微企業如何開展合規整改、如何建設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等,檢察機關和社會各界已經形成了初步共識。
但是,隨著改革試驗的深入推進,一些更深層次的難題爭議也凸顯出來。例如,具體哪些“企業家”犯罪案件可以適用“合規不起訴”;再如,在辦理企業合規案件時,檢察機關應當如何在檢察建議模式和合規考察模式兩種辦案模式間做出合理選擇;又如,應當如何在檢察機關和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間配置合規監管權,等等。筆者以近期實踐調研積累的信息和經驗為基礎,總結了改革現階段的疑難爭議問題,實際上也是需要避免的認識誤區。這些疑難爭議問題的解決,是繼續深化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探索形成刑事立法修改方案的必要前提。〔5〕參見李奮飛:《“單位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立法建議條文設計與論證》,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2年第2期,第17-34頁。
一、“合規不起訴”的適用對象問題
“合規不起訴”的適用對象包含涉罪企業和涉罪“企業家”,這是改革現階段的基本共識。但是,對于兩個對象的具體指代、涵蓋范圍、概念限度等,尚缺乏清晰規定,這使得實踐中產生了一些分歧和爭議,也導致了一些認識上的誤區。
(一)涉罪企業的概念范圍
合規是專屬于企業的詞匯,是指企業為防范外部的法律風險而建立的內部管理體系。但是,“企業”并非既定法律概念,究竟哪些市場主體屬于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所涵蓋的對象,仍存在不同觀點。在雷某某涉嫌非法采礦一案的專家研討過程中,筆者發現,分歧的核心在于,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市場主體是否屬于此項改革的適用對象。在該案中,涉案的主體是一家登記為個體工商戶的采石場,不具有民商事法律意義上的法人資格。筆者之所以認為該主體屬于涉案“企業”,主要是因為我國刑事法律和涉案企業合規改革都沒有以法人資格限定市場主體范圍。“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是我國《刑法》第30條針對單位犯罪作出的規定。其中沒有涉及法人資格的問題,而企業通常包含合伙企業、獨資企業兩種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市場主體,許多人合性較強的律所、會計師事務所也都包括在內。
實踐中,只要市場主體依法成立,有獨立于自然人的名義和財產,能夠獨立承擔刑罰,就能夠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我國《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第3條明確規定改革的適用對象包括:“公司、企業等市場主體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涉及的經濟犯罪、職務犯罪等案件”,這也將不具有法人資格企業、個體工商戶等市場主體包含在內。因此,“合規不起訴”對象所包含的“涉罪企業”,應當能夠涵蓋非法人市場主體,但也需要檢察機關在個案中作出具體裁量,并審慎決定是否將其納入合規考察程序。畢竟,合規改造涉及如何將合規機制融入現有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因此,對于那些個人與企業意志、行為、財產嚴重混同,沒有獨立管理結構的市場主體,可以將企業視作自然人的“犯罪工具”,按照自然人犯罪案件處理,不宜將該“犯罪工具”納入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驗的對象。
(二)涉罪“企業家”的概念范圍
“企業家”不是既定法律概念,社會各界較為一致地將其理解為負責企業經營和管理活動的自然人,包括企業實際控制人、董事長、總經理等。但實踐中,這些人所涉及的犯罪案件類型較為多樣,具體哪些可以納入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驗,也是爭議較大的問題。有觀點認為,所有“企業家”犯罪案件都可以作為企業合規案件辦理;也有觀點認為,僅少數“企業家”犯罪案件能符合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適用條件。在企業涉嫌輕微單位犯罪的案件中,企業及“企業家”(作為單位犯罪的責任人)以企業合規整改換取檢察機關的相對不起訴決定,不存在障礙。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兩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來看,已經呈現出了既放過企業又放過個人的“雙不起訴”現象。〔6〕參見李玉華:《企業合規本土化中的“雙不起訴”》,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22年第1期,第25頁。
但是,在“企業家”涉嫌個人犯罪的案件中,企業并不涉罪、而僅僅涉案,此時,企業進行合規整改是否能夠成為對“企業家”個人不起訴等從寬處理的理由,爭議較大。〔7〕有學者指出,“企業合規,本質上是企業自身具有獨立意思的體現,是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出現犯罪行為時,讓企業全身而退、免受處罰的理由,而不是讓其中的自然人免責的理由”。參見黎宏:《企業合規不起訴:誤解及糾正》,載《中國法律評論》2021年第3期,第184頁。最高人民檢察院等9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明確將可以納入改革范圍的“企業家”犯罪案件,限定為“公司、企業實際控制人、經營管理人員、關鍵技術人員等實施的與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犯罪案件”,但尚未對“與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限定條件作出具體的解釋和說明。實踐中,已出現“企業家”在涉嫌危險駕駛、職務侵占等純正自然人犯罪的案件中,也申請啟動合規考察的情況。此時,檢察機關就面臨著案件是否符合改革試點范圍的判斷難題。
對此,需結合我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基本精神,對“與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這一條件作出合理解釋。一般認為,此項改革之所以將“企業家”個人犯罪案件也納入范圍,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企業家”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實施犯罪行為,有為企業集體利益考慮的一面,也與早期市場監管不力的歷史原因有關,有情有可原之處;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受限于國家監管資源和企業管理能力,我國企業特別是不少民營企業,在早期發展階段就缺乏必要的規范,治理結構普遍存在著先天的缺陷。甚至,不少中小微企業存在著法人與法定代表人或實際控制人“人格混同”的問題,使得企業經營的人身依附性較強。因此,“企業家”在被起訴定罪后,企業往往也難逃經營嚴重受損甚至走向破產倒閉的命運。正所謂如不保護“企業家”,就保護不了企業。而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的命運又可能會與不少人(有的案件可能達到數萬人)的就業密切相關,與一些(有時可能達到數十個)關聯企業的生存相關,與地區發展和稅收相關,甚至與行業經濟和國家命運相關。〔8〕參見李奮飛主編:《企業合規通識讀本》,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8頁。因此,基于避免造成員工失業、地區經濟受損等社會公共利益的考慮,檢察機關與其“一訴了之”,將定罪后果經由市場和經濟鏈條傳導給更多無辜者,不如以保住“企業家”的方式激勵相關企業建立合規管理制度,彌補企業治理缺陷,消除企業經營和管理模式中的“犯罪因子”,以促進企業依法依規經營,從根本上降低再犯風險。
筆者認為,在改革精神的指引下,“與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企業家”犯罪案件應當具備兩個條件。第一,“企業家”為企業利益而實施犯罪行為。“企業家”從事挪用公款、職務侵占、違規發放貸款等個人犯罪行為,其目的一般只為個人利益,涉案企業不會直接或間接獲利,甚至可能成為案件的被害人。此時,要求企業為“罪魁禍首”的個人“出罪”而花費成本,開展合規整改,于情理明顯不符。第二,“企業家”的犯罪行為需與企業的管理制度漏洞有關。企業開展合規整改的前提,是企業確實存在合規管理漏洞,“企業家”能夠順利實施犯罪行為,也與這種漏洞存在著因果聯系。依據企業合規理論,合規能成為“出罪”等從寬的理由,是因為其修正了企業的治理結構,降低了企業及相關自然人的再犯風險,提前實現了犯罪預防,使刑罰不再具有落實的必要性。但是,在那些“企業家”犯罪與企業管理制度沒有明確因果聯系的案件中,合規無法預防該類犯罪,“企業家”刑罰有落實的必要性,因此,不宜作為企業合規案件辦理。
在夏某某涉嫌操縱證券市場罪一案的專家研討過程中,筆者之所以建議檢察機關將該案作為企業合規案件辦理,是因為發布股權變動消息是上市公司的法定職責,夏某某作為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實控人(其持股16%,是第一大股東,第二大股東僅持股2%)、核心專利持有人,其違法行為與公司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暴露了公司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合規漏洞。因此,將其作為合規案件辦理,無論是采取合規考察模式,還是采取檢察建議模式,都有助于通過保住實控人而維護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同時有助于督促企業修補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管理漏洞,符合最高人民檢察院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規定的精神。該案與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第三批典型案例中的“王某某泄露內幕信息、金某某內幕交易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該案中,涉案公司是一家年產值超20億元的汽車電子制造企業,該公司高管王某某因法律意識淡薄,將工作中獲知的項目信息泄露給第三人,涉及一起泄露內幕信息案件。2021年8月,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受理了該案,經該公司提交合規整改申請,啟動合規考察和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在驗收合規整改合格后,對兩名被告提出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半,適用緩刑,并處罰金的量刑建議。最終,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檢察機關開展的合規工作有利于促進企業合法守規經營,優化營商環境,可在量刑時酌情考慮,采納了該量刑建議。
二、企業犯罪分離追訴的可行性問題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引發了我國關于單位犯罪刑事責任制度的反思,〔9〕有學者認為,“雙罰制可能人為制造出數量眾多的企業犯罪,不利于企業犯罪的預防”。參見歐陽本祺:《我國建立企業犯罪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探討》,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年第3期,第66頁。其中單位與責任人的罪責關系問題特別引人注目。在英美法系國家,企業與自然人的刑事責任自產生之時起即為分離狀態,企業和直接構成犯罪的自然人是同一個罪名的平行犯罪主體,二者分別承擔刑罰:自然人并非作為企業犯罪的責任人而承擔責任,而是構成獨立犯罪,承擔獨立刑罰。所以,當企業通過合規實現“出罪”時,仍依據該罪名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責任不存在任何障礙。〔10〕參見李奮飛:《“單位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立法建議條文設計與論證》,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2年第2期,第37頁。而在我國,如涉罪企業通過合規整改實現“出罪”,檢察機關是否仍需繼續追究責任人的刑事責任,尚缺乏明確規定。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企業合規典型案例中,“雙不起訴”的做法較為常見,〔11〕對此做法,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在企業合規改革中,一些地方將涉罪企業與涉罪的企業成員捆綁在一起,涉罪的企業成員也一并納入合規考察的范圍予以不起訴,這并不妥當。”參見孫國祥:《單位犯罪的刑事政策轉型與企業合規改革》,載《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21年第6期,第37頁。但也出現了企業與“企業家”分離追訴的司法探索。例如,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人民檢察院行刑銜接工作典型案例中,“上海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就采取了“放過企業、嚴懲責任人”的做法。該案中,涉案兩公司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而涉嫌單位犯罪,后通過合規考察,獲得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對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姜某,檢察機關另案處理,提起公訴。
根源于對單位犯罪構成形態的認識誤區,實踐中,不少人對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中單位和責任人分離追訴的做法并不認同,認為應當依據我國單位犯罪雙罰制的規定,認定單位犯罪具有牽連形態,單位構成犯罪是追究內部成員刑事責任的依據和前提,因此,司法機關需將單位犯罪和單位成員同案捆綁處理。〔12〕參見李勇:《涉案企業合規中單位與責任人的二元化模式》,載《中國檢察官》2022年第12期,第32頁。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雙罰制之下,企業和其員工之間處于‘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連帶關系。這種關系的直接結果是,對單位員工的業務違法行為只有兩種選擇: 或者作為單位犯罪,被‘雙罰’;或者作為個人犯罪,被‘單罰’。絕無可能構成單位犯罪,但只處罰其員工‘個人’,單位不擔責的選項。”〔13〕參見黎宏:《企業合規不起訴改革的實體法障礙及其消除》,載《中國法學》2022年第3期,第263頁。
但是,隨著域外企業犯罪暫緩起訴制度的擴張,以及國內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發展,企業犯罪治理遵循“放過企業、嚴懲責任人”原則的必要性逐漸清晰化,即需要將企業內部違反合規文化的“毒瘤”剔除,不僅檢察機關應當對涉罪責任人依法追訴,企業也需要依據內部規章制度作出降薪、開除、決定永不錄用等制裁決定,這樣穿透企業負責的管理結構,將刑事責任和違規責任落實到個人,能夠更好地發揮制裁措施的威懾功能。〔14〕See Nick Werle, “Prosecuting Corporate Crime When Firms Are Too Big to Jail: Investigation, Deterrence, and Judicial Review”, 128 The Yale Law Journal 1366, 1366 (2019).對此,我國早有學者提出,《刑法》規定的單位犯罪實則為聚合形態,而非牽連形態,即單位犯罪是兩類犯罪的聚合體:一類是客觀實在的作為單位成員的自然人犯罪,另一類是擬制的單位犯罪,二者是獨立的兩類犯罪行為。〔15〕參見葉良芳:《論單位犯罪的形態結構——兼論單位與單位成員責任分離論》,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6期,第101頁。這為二者的分案處理和分離追訴提供了理論基礎。
在法學理論方面,單位犯罪的聚合形態能夠破解單位和責任人“雙向牽連”的“反責任主義”困境:一方面,單位作為擬制的犯罪主體,受到責任人行為的牽連而承擔刑事責任;另一方面,主管人員、法定代表人等責任人又因單位成立而被歸罪。這兩種情形都違反了刑法的罪責自負原則,易導致單位犯罪處罰范圍的不當擴張。
在司法實踐方面,我國單位犯罪的分案處理、分離追訴的做法也已被司法解釋確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340條規定:“對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案件,人民檢察院只作為自然人犯罪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對犯罪單位追加起訴。人民檢察院仍以自然人犯罪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審理,按照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并援引刑法分則關于追究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的條款。”基于此,檢察機關本就享有裁量決定是否追加單位被告人的權力,本就可以通過不追加企業為被告人而達到“放過企業、嚴懲責任人”的效果。這也佐證了我國單位犯罪為聚合形態的基本事實,即單位犯罪成立不以單位被追究刑事責任為前提。實踐中,也有大量分離追訴的企業犯罪案件,即檢察機關經過非正式的公共利益權衡,拒絕追加企業為被告人,而“企業家”仍被作為單位犯罪責任人定罪和處罰。
在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推進過程中,檢察機關將涉罪企業作為“合規不起訴”的對象,但對涉罪“企業家”仍繼續追訴,既不存在理論障礙,又符合我國的司法傳統。而且,相較于傳統司法中一些檢察機關通過不追加被告人而直接放過企業的做法,以“合規”為由對涉罪企業進行事后考察出罪,能補足罰金刑再犯預防功能的不足,因而更具有正當性和可行性。畢竟,對合規整改合格的企業雖不再予以定罪處罰,但并非“一放了之”。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企業不僅為合規計劃建設投入大量經濟成本,還在治理結構、商業模式、組織人事等方面完成‘斷尾求生’式的自我改造,合規整改這種非刑罰制裁方式較之罰金刑更具嚴厲性”。〔16〕參見劉艷紅:《企業合規不起訴改革的刑法教義學根基》,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2年第1期,第107頁。
三、檢察建議模式的實踐性質問題
試點檢察機關在將企業合規納入辦理“涉企犯罪案件”的過程之中,大體形成了檢察建議模式和合規考察模式(也稱附條件不起訴模式)兩種基本辦案形態。〔17〕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合規激勵模式》,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6期,第226頁;李奮飛:《涉案企業合規刑行銜接的初步研究》,載《政法論壇》2022年第1期,第104頁。在第一期試點中,檢察建議模式為主要的辦案形態。在最高人民檢察院2021年6月3日公布的第一批(共4起)企業合規典型案例中,有3起采取了檢察建議模式。其通常做法是,檢察機關在對涉罪企業或者負有責任的自然人作出酌定不起訴的同時,向涉案企業提出建立合規管理體系的檢察建議,一般也不為企業設置確定的考察期。〔18〕參見劉譯礬:《論企業合規檢察建議激勵機制的強化》,載《江淮論壇》2021年第6期,第134頁。檢察建議雖具有制發時間、對象較為靈活的獨特優勢,〔19〕參見李奮飛:《論企業合規檢察建議》,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1年第1期,第97頁。但卻存在著約束力不足、專業性不夠等內在局限性;而合規考察模式則可以彌補檢察建議模式的這一不足,因而成了第二期試點的主要辦案形態。在最高人民檢察院2021年年底公布的第二批(共6起)企業合規典型案例中,全部采取的是附條件不起訴模式。其通常做法是,檢察機關為那些被納入考察對象的企業設立一定的考察期,并根據其在考察期內的合規整改情況,再作出是否對涉罪企業或涉罪“企業家”起訴的決定。
但是,筆者在最近調研的過程中發現,有的檢察院認為,企業合規案件的辦理模式只有合規考察模式一種,這顯然降低了改革工作的靈活度。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辦案數據和典型案例來看,檢察建議模式在第一期試點工作中的適用比例較高,而合規考察模式在第二期試點工作中的適用比例迅速提升。這種趨勢導致有人誤以為,檢察建議模式不再屬于企業合規案件的辦案模式,檢察機關應當首先以合規考察模式辦理案件。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第二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張家港S公司、雎某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中,張家港市檢察院聯合公安機關對只有3名員工的S公司也啟動了合規監督考察程序,并為其確定了6個月的整改考察期。
實際上,兩種辦案模式雖各有利弊,但都屬于合規改革的辦案模式,應當區別地適用于不同類型的企業合規案件。在有關大型企業涉嫌的重大犯罪案件中,由于企業的“犯罪基因”掩藏于復雜的治理結構當中,開展合規整改的難度較大,這時選擇有司法強制力支撐的合規考察模式,更具有必要性;在那些中小微企業涉嫌輕微犯罪的案件中,企業的治理結構較為簡單,所涉犯罪類型也較為單一,企業合規整改的難度不高,通常沒有必要對其開展耗時費力的合規考察。檢察機關在作出不起訴決定后,制發合規檢察建議,一般就足以督促企業實現有效合規整改。如若擔心檢察建議的強制力不足,檢察機關也可以考慮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向涉案企業提出合規檢察建議,或向行政機關制發檢察意見,建議行政機關繼續監督企業完善合規建設。畢竟,行政機關通常更為熟悉監管法規且本身就對涉案單位行為規制負有責任。此外,對于那些拒不整改的企業,檢察機關還可以通過提起公益訴訟的方式,對其予以制裁。
而且,檢察建議模式獨具中國特色,不應當被排除在涉案企業合規案件的辦案模式之外。尤其是,就學理而言,對于那些不構成犯罪的企業,檢察機關適用柔性的合規檢察建議,更有助于充分尊重合法企業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有學者認為,“如果企業的實際控制人、經營管理人員、關鍵技術人員等實施了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犯罪行為,說明企業在內部管理與風險控制方面存在問題。因此,即使涉案企業沒有受到追訴,要求其接受合規考察也完全符合涉案企業合規的制度目的。”〔20〕參見周振杰:《涉案企業合規刑法立法建議與論證》,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2年第3期,第37頁。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待商榷。合規考察不僅具有保護功能,也具有懲罰功能(因此其才能有效地替代刑罰)。這種懲罰功能體現在,企業一旦被納入合規考察,就需要承擔諸如積極配合、退繳違規違法所得,補繳稅款和滯納金并繳納相關罰款、提交合規計劃、接受合規監管等義務,其最終所付出的經濟代價可能比起訴定罪后被判處的罰金還要多,因而才能夠實現懲罰涉罪企業、形成威懾作用的目的。〔21〕參見李奮飛:《論企業合規考察的適用條件》,載《法學論壇》2021年第6期,第34頁。而且,在企業不涉罪的情況下,如果檢察機關對其啟動合規考察,并為其設置一定的考察期,那么,考察不合格又會產生何種法律后果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適用柔性的檢察建議模式可能更為妥當。即使啟動合規考察,也應當以企業自愿申請為前提。例如,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第二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隨州市Z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責任事故案”中,曾都區檢察院經審查認為,康某某等人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屬于企業人員在生產經營履職過程中的過失犯罪,同時反映出涉案企業存在安全生產管理制度不健全、操作規程執行不到位等問題。征詢Z公司意見后,Z公司提交了開展企業合規的申請書、書面合規承諾以及企業經營狀況、納稅就業、社會貢獻度等證明材料,檢察機關經過審查,對Z公司作出了合規考察的決定。
四、合規考察和第三方監督評估的關系問題
“合規體系建設是專業性較強的公司治理問題”,而受限于專業知識、辦案經驗、司法資源等現實情況,檢察官要在所有案件中親自監督和指導企業實現有效合規整改,可以說是無法完成的任務。在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推進過程中,我國檢察機關對企業合規監管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形成了兩種主要的合規監管方式:一種是檢察機關自行監管,即由檢察官在合規考察期內調查、評估、監督和考察企業的合規整改活動;另一種是第三方監管,即由合規專家、律師、相關監管官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組成的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由其彌補檢察機關合規專業能力的不足,代行部分合規監管職能,對涉案企業的合規整改活動進行調查、評估、監督和考察,相關結論和建議可以作為檢察機關“依法作出批準或者不批準逮捕、起訴或者不起訴以及是否變更強制措施等決定,提出量刑建議或者檢察建議、檢察意見的重要參考”。
相較而言,由檢察官自行監管的便宜度較高,且因介入的主體較少而更為經濟、節約,但其通常欠缺有關公司治理、合規管理以及企業犯罪學等方面的知識,也缺乏督導企業開展合規整改的經驗和技能,〔22〕參見陳瑞華:《合規監管人的角色定位——以有效刑事合規整改為視角的分析》,載《比較法研究》2022年第3期,第34頁。而第三方監管的專業度較高,但第三方專家的選任、管理、履職等需要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
隨著我國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迅速發展,加上我國《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規定的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適用案件范圍,與我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適用案件范圍相一致,一些人開始將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等同于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建設,或者將其中的合規考察活動等同于第三方監督評估活動,主張在所有企業合規案件中廣泛地適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即,“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無論是中小微企業還是上市公司,只要涉案企業認罪認罰,能夠正常生產經營、承諾建立或者完善企業合規制度、具備啟動第三方機制的基本條件,自愿適用的,都可以適用第三方機制。”〔23〕封莉:《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全面推開 適時推動完善立法》,載《中國經營報》2022年4月11日,第4版。
我們認為,為避免合規監管資源的浪費,應將合規考察條件與適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條件作出區分。即,不是所有符合啟動合規考察條件的案件,都同時符合啟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條件。在那些企業規模較小、涉嫌罪名較為常見、犯罪情節較為輕微、合規整改難度不大的案件中,即使啟動合規考察程序,通常也沒有必要啟用高消耗的第三方監管,否則就有“殺雞用牛刀”的嫌疑。在美國檢察官與企業達成的暫緩起訴和不起訴協議中,也僅有四分之一要求聘請合規監管員,其中涉及證券欺詐或違反《反海外腐敗法》的案件最為普遍。〔24〕[美]布蘭登? L. 加勒特:《美國檢察官辦理涉企案件的啟示》,劉俊杰、王亦澤等譯,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215頁。未來,應當明確第三方監管的啟動原則,即只有在充分考量合規整改難度、合規監管難度等因素后,認為確有必要的情況下才予以啟動,尤其是在企業僅涉案而不涉罪的案件中盡量避免適用,在小微企業涉嫌常見犯罪的案件中審慎適用,〔25〕參見李奮飛:《完善第三方機制促進企業合規發展》,載《法治日報》2022年6月29日,第5版。并進一步區分“范式合規”與“簡式合規”,鼓勵檢察機關采用自行監管方式辦理簡單案件。目前,已有試點檢察院認識到,應當審慎適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例如,在江蘇F公司、嚴某某、王某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案中,考慮到涉案企業為僅有39名員工的小微企業,江寧區檢察院決定開展“簡式”合規,不啟動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而是由檢察院自行履行合規監管職能,以便降低合規成本、減輕企業經濟負擔。
五、合規整改驗收的決策主體問題
“合規計劃的有效性評估充滿挑戰”,〔26〕[美]菲利普?韋勒:《有效的合規計劃與企業刑事訴訟》,萬方譯,載《財經法學》2018年第3期,第142頁。因此,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順利推進離不開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良好運行,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涉案企業有效合規整改的基本保證。2022年4月,全國工商聯、最高人民檢察院等9部門聯合發布了《涉案企業合規建設、評估和審查辦法(試行)》(以下簡稱《審查辦法》),明確了第三方機制管委會和人民檢察院審查第三方組織合規監管工作的方法,也規定了對第三方組織及成員違規行為的基本處理流程,為第三方組織評估企業合規管理體系有效性提供了初步標準,也為檢察機關、第三方機制管委會評價第三方組織履職情況提供了初步依據。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我國第三方監督評估活動開啟標準化和規范化進程的重要標志。
但是,隨著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廣泛適用,有人誤以為,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是涉案企業合規整改的唯一驗收主體,檢察機關應當尊重其驗收結論,沒有責任就合規整改的有效性進行獨立評估和驗收。這種觀點沒有認識到第三方監督評估活動的司法輔助屬性,易降低合規整改驗收的準確性,難以有效預防“紙面合規”。
在我國,合規剛剛引入刑事司法,學校課程、職業培訓等都尚未注重培育合規專業人才,許多被納入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候選名錄庫的律師、會計師、行政機關人員等,也是初學者,缺乏合規實踐經驗,對于企業如何開展有效合規整改,缺乏充分認識。在此背景下,如果檢察機關僅僅依靠社會力量驗收合規整改,將“紙面合規”錯認為“有效合規”的風險較高。因此,檢察機關作為辦案機關,即使在有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參與的情況下,也應對涉案企業的合規整改承擔主導責任,其不僅有權監督企業的合規整改工作,還可以對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的履職情況進行監督。即,對于涉案企業是否通過合規整改,最終要由檢察機關作出決定。根據《指導意見》的規定,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的合規整改驗收結論只是“人民檢察院依法處理案件的重要參考”。該規定與域外的通行做法相一致,都是將最終決策權交給檢察機關,將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對合規整改效果的驗收結論視為如“專家鑒定意見”一般的參考性意見,而不是唯一的依據,避免造成社會人員左右司法決策的結果。
作為合規整改驗收的決策主體,檢察機關有權獨立審查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的驗收結論,并可以依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聽證工作規定》開驗收聽證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和相關行業專家等參加,也可以邀請第三方組成人員到會發表意見,以對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的工作情況進行審查。〔27〕未來,在明確合規驗收應當召開聽證會的基礎上,應當對聽證會的具體程序進行統一規范。需要明確參與聽證會人員的數量、身份、組成方式等,確定聽證會的發言順序,規范聽證會的表意和決策方式。有效的聽證會應當主要圍繞兩個文件展開:一是企業方提交的合規整改報告;二是合規監管人提交的合規評估和驗收報告。長期來看,也可以推動合規聽證員的專業化,引入更有經驗的合規專家參與,提升合規驗收結果的公信力。有些試點地方還規定,檢察機關可以對涉罪企業進行回訪檢查,如發現涉罪企業合規整改仍不夠徹底,工作制度仍可能為犯罪提供便利條件,實現合規目的仍有困難,或者再次發生違法犯罪等情況的,經檢察機關審查確認,還可以撤銷原合格評定。〔28〕參見《深圳市檢察機關企業合規工作實施辦法(試行)》。
六、有效合規與不起訴決定的關系問題
對于涉案企業而言,其開展合規整改的主要目標還是換取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而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驗推行以來,除了少數提出寬緩量刑建議和合規考察不合格的案件,絕大多數被作為企業合規案件辦理的涉罪企業和“企業家”也都獲得了不起訴處理。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合規典型案例“深圳X公司走私普通貨物案”為例。在該案中,第三方工作組通過查閱資料、現場檢查、聽取匯報、針對性提問、調查問卷等方式,進行考察評估并形成考察意見。工作組經考察認為,X集團的合規整改取得了明顯效果,制定了可行的合規管理規范,在合規組織體系、制度體系、運行機制、合規文化建設等方面搭建起了基本有效的合規管理體系,彌補了企業違法違規行為的管理漏洞,從而能夠有效防范企業再次發生相同或者類似的違法犯罪。檢察機關因此對X公司及涉案人員作出了相對不起訴處理。
正因如此,有觀點認為,只要企業開展了合規整改,彌補了企業管理上的制度漏洞,且合規整改的結果被驗收為合格,檢察機關就必須作出不起訴決定。這種觀點過分關注了改革的合規整改面向,而忽略了檢察機關裁量決定訴與不訴過程的復雜性。畢竟,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署啟動的,尚未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授權,檢察機關通常只能在現行刑事訴訟法律的框架和范圍內,將一些犯罪情節輕微、符合相對不起訴適用范圍的涉企刑事案件作為試驗對象。在不起訴裁量權缺乏明確標準和指引的情況下,究竟需要納入何種考量因素,對一些輕微案件(包括但不限于“涉企刑事案件”)予以“出罪”處理,實際上屬于檢察機關裁量的范疇。通過將企業合規因素納入起訴裁量,檢察機關可以激勵和督促涉案企業在考察期內進行有針對性的合規整改。對于合規計劃無效、合規整改不合格的企業,檢察機關當然可以在考察期屆滿時提起公訴。例如,在隨州市L公司、夏某某非法占用農用地案中,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在經過近兩個月的合規考察后,出具了考察報告,認為:雖然經過法律政策講解,L公司認識到其占用農地行為不符合土地管理法,但仍然認為自身受當地鎮政府邀請投資建設沒有過錯,導致現場整改不主動;多名股東對夏某某的整改處理意見提出異議,但并未得到尊重,夏某某的個人意見最終仍代表公司意見,《企業合規計劃》中規定的完善內部決策程序、法務審核程序,加強與政府相關監管部門的協調配合等整改措施落實不到位,其申請適用企業合規程序的主要目的是想通過相關單位的協調,幫助其補辦土地使用手續,企圖將其非法占地行為合法化。在考察期到期時,該公司既未辦理用地合法手續,也未拆除違建的廠房,其違法占用農用地一直處于持續狀態。綜合認定合規考察結果為“不合格”。結合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的考察結果,隨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于2021年8月3日經討論決定,依法對L公司提起公訴,同時向隨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發出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
不過,即使企業落實了有效合規整改,也只是檢察機關行使起訴裁量權時的考量因素之一。除此之外,檢察機關還需要將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辦理涉企刑事案件的新要求,〔29〕參見李玉萍:《論公訴裁量中的公共利益衡量》,載《政法論叢》2005年第1期,第92頁。并結合企業的犯罪性質、配合調查、“法益修復”的情況等因素,作出綜合性的司法決策。考慮到企業所涉嫌的犯罪絕大多數是“行政犯”,道德可責性較低,而且,“相較于嚴格懲罰整個企業集體,公眾更加愿意看到企業對社會的規范化、可持續服務”,〔30〕陳學權、陶朗逍:《企業犯罪司法輕緩化背景下我國刑事司法之應對》,載《政法論叢》2021年第2期,第124頁。因此,對于合規整改合格的企業,檢察機關應盡可能對其予以“出罪”處理,以激勵更多的(涉案)企業能夠“加入到合規管理體系建設中來”。
當然,筆者在近期調研中發現,有的涉罪企業雖然完成了合格的合規整改,但在考察期內對認罪認罰反悔,或者拒絕充分修復受損法益,甚至涉嫌其他違法犯罪。此時,若檢察機關僅以合規整改的有效性決定是否追訴,不符合我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價值目標。對于那些付出了合規整改努力,但沒有達到有效合規標準的企業,以及那些存在其他因素導致合規考察不合格的企業,檢察機關可以依法提起公訴,也可以同時提出從寬處罰的量刑建議。
值得肯定的是,在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驗過程中,合規考察程序的啟動并非檢察機關“單向性的法律適用活動”,〔31〕參見時延安:《單位刑事案件的附條件不起訴與企業治理理論探討》,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年第3期,第57頁。而是在涉罪企業、個人認罪認罰的前提下,通過與涉案企業、犯罪嫌疑人的溝通、協商和對話,就涉案企業配合調查、采取補救措施、進行合規整改、接受合規監管等事項上達成合意,從而將涉案企業納入合規考察的軌道。未來,我國在建立企業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之后,可以在立法中將此改革經驗固定下來,即由檢察機關和涉罪企業在合規考察程序啟動后,通過平等協商并在“附條件不起訴決定書”中明確考察條件,諸如承認涉案事實、在合規考察期內進行有效合規整改、配合(執)司法、賠償損失、繳納罰款等,并明確檢察機關對符合條件的企業決定不起訴,對違反條件的企業提起公訴,以增加制度運行結果的確定性,實現合規從寬激勵的穩定預期。〔32〕參見孫國祥:《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與刑法修正》,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2年第3期,第50頁。
七、第三方監督評估的工作屬性問題
無論是《指導意見》,還是《審查辦法》,都未對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的薪酬問題予以明確。在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前期探索過程中,一些地方檢察機關在聯合相關部門制作的規范性文件中明確了合規監督考察費用的承擔問題。例如,湖北省黃石市人民檢察院聯合黃石市司法局制發的《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管人選任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合規監管考察費用由涉案企業承擔,并設置了“企業合規監管保障金”,由市司法局統一管理、專款專用,用于支付第三方監管人及合規考察驗收小組專家費用。《深圳市檢察機關企業合規工作實施辦法(試行)》第17條也明確規定:“第三方監控人進行監督考察所需費用以考察所發生的實際費用為準,由涉案企業承擔。”
但是,也有不少檢察機關至今仍將第三方監督評估工作視作公益性活動,不向第三方監管人支付費用,或者僅要求涉案企業支付微薄勞務。應當承認,此舉在改革試驗階段確實有其現實合理性。畢竟,所謂的“合規不起訴”就其性質而言就是相對不起訴。甚至,有些試點檢察機關所制定的改革實施方案,就直接冠以“企業犯罪相對不起訴適用機制”。也就是說,即使在此項改革推行以前,檢察機關原本也可以對其直接裁量“出罪”。因此,有學者也指出,“試點單位將該類企業納入合規考察,以涉案企業承諾并履行合規計劃、修復受損法益等事由為根據,不起訴企業是出于促進涉案企業改善內部控制機制從而預防犯罪的政策考慮。由于合規考察具有準刑罰性質,因此,對本可以通過相對不起訴程序獲得寬大處理的輕罪范圍內企業啟用合規考察,不要求其承擔制裁成本(監管費用)具有一定合理性。”〔33〕參見李本燦、王嘉鑫:《論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管人啟用機制》,載《江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第123頁。
不過,從長遠來看,容易導致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中的專業人才流失,降低合規整改的質量。筆者在調研中發現,一些有能力、有經驗的律師已經不再有改革初期的熱情,對作為第三方監管人參與辦理企業合規案件的興趣并不高,而是更愿意擔任企業的“合規顧問”,以獲取更高額的專業報酬。
在域外,擔任合規監管人的專家資質較高、人員較為固定,其薪酬標準較高。例如,依據美國檢察機關公布的《合規監管人名錄》,愛立信案的合規監管人曾經擔任西門子、福樂斯多、蘭萬靈等多家著名跨國企業的首席合規官,沃爾瑪案的合規監管人是前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其在2010年就曾經擔任戴姆勒案的合規監管人。〔34〕See DOJ, List of Independent Compliance Monitors for Active Fraud Section Monitorships.依據媒體公布的信息,在為期18個月的合規監管工作中,合規監管人的費用總價甚至可能高達數千萬美元。〔35〕See Veronica Root, “The Monitor- ‘Client’ Relationship”, 100 Va. L. Rev. 523, 580 (2014).域外采取高額收費方式,是因為其法律服務市場本身專業費用標準較高,且大型企業的合規監管難度較大,需要以經濟利益保障合規監管人的獨立性,使其無需為后續的小額商業賄賂而改變監管立場。雖然這種收費標準并不一定適合我國國情,〔36〕畢竟,絕大多數被納入試驗對象的企業都是存在經濟困難的“中小微企業”,沒有支付高額監管費用的能力,且其短期合規監管活動本身也并不復雜。但是其也為合規監管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借鑒思路。
我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應當為第三方監管人確定合理的薪酬標準,以不低于市場服務的價格吸引人才涌入。雖然律師、注冊會計師、稅務師等社會專業人員被選為合規監管候選人,納入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專家名錄庫,能夠為其帶來聲譽收益,并可以間接地為其帶來商業利益。但是,一方面,各區、縣、市等已發布較多份合規監管人候選名單,甚至有大量律師事務所、社會組織被整體納入,〔37〕有學者建議,第三方監管人應由個人擔任,由獨立專家領銜組建監管人團隊,而不應由機構擔任。參見陳瑞華:《企業合規不起訴改革的八大爭議問題》,載《中國法律評論》2021年第4期,第28頁。這導致合規專家聲譽的商業價值急速下降;另一方面,律師、注冊會計師、稅務師(注冊稅務師)等中介組織人員一旦被選任為第三方組織組成人員,不僅在履行第三方監督評估職責期間內無法接受可能有利益關系的業務,而且在履行第三方監督評估職責結束后一年以內,其以及其所在中介組織也不得接受涉案企業、個人或者其他有利益關系的單位、人員的業務。也就是說,目前擔任第三方監管人不僅較為費時費力(特別是在那些涉案企業規模較大、治理結構較為復雜的案件中),潛在收益也不高,而且還可能失去未來一年內的諸多商業機會,不支付報酬或僅支付微薄報酬,已無法產生足夠的激勵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要保障第三方監管人的積極性,保障合規整改的質量和成效,就需要改變工作的法律援助屬性或公益屬性,及時引入市場化的薪酬支付機制,尤其是在企業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確立在《刑事訴訟法》中之后,應明確規定由涉案企業按照市場價格支付合規監管費用。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管委會和辦案檢察院的雙重監管下,已經無需過分警惕第三方監管人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問題,企業以高額薪酬賄賂第三方監管人的風險也大大降低,只需解決合規專家參與第三方組織的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只有確定恰當的薪酬標準和支付路徑,才能保障第三方組織吸納真正懂合規的專業人才,并確保其盡職盡責提供合規監管服務,避免合規監管流于形式,進而防止企業利益因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運行而遭受損害。我們建議,由第三方機制委員會確立統一的合規監管費用標準,由其向企業統一收取,形成支付隔離,以避免腐敗。〔38〕參見陳瑞華、李奮飛:《“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二人談(下)——推動企業合規改革,探索本土化的有效合規標準》,載《民主與法制》2022年第38期,第42頁。
八、合規犯罪預防功能的絕對化問題
在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推行以前,不起訴權就存在不敢用、不愿用、不會用等現象。〔39〕參見童建明:《論不起訴權的合理適用》,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年第4期,第23頁。此項改革推行后,各試點地區的企業合規案件辦理量存在很大差異。甚至,有些試點檢察機關僅僅制發了規范性文件,幾乎沒有辦理“合規不起訴”案件。筆者通過近期的調研發現,一些檢察機關“不敢”“不愿”啟動“合規不起訴”的原因主要在于,擔心涉罪企業通過合規考察后,企業或責任人仍會再犯,導致案件成為“錯案”。這種觀點對合規的犯罪預防功能存在絕對化的認識誤區,錯誤地以“結果中心主義”的立場判斷企業合規整改的有效性和企業合規案件辦理的適當性。
刑罰理論的共識是,沒有哪一種刑罰或措施能夠完全預防所有罪犯再犯,其只能通過懲罰、矯正、失能等手段盡量降低再犯可能性。〔40〕See Albert Alschuler, “The Changing Purposes of Criminal Punishment: A Retrospective on the Last Century and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Next”, 70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1 (2003).企業合規整改亦然。與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不同,企業是一種法律擬制主體,其行為需要通過自然人代理實施,但企業無法完全控制其代理員工的行為,即使企業建立最完善的合規管理制度,也可能有員工實施犯罪。〔41〕See Maurice E. Stucke, “In Search of Eあective Ethics & Compliance Program”, 39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769, 799(2014).從考察結果的視角出發,要求企業建立能實現完全犯罪預防的管理制度,嚴密管控和預防其代理人的所有行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和現實可行性。因此,在評價企業合規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以及在評價企業合規案件的辦理效果時,不能將涉罪企業是否發生再犯作為唯一衡量標準。需要從“結果中心主義”走向“過程中心主義”,客觀地理解合規有限的犯罪預防效果。
在合規整改方面,只要涉案企業盡到了合理努力,建立了符合合規管理體系特征的制度,為該制度的運行投入了充分的資源,并確認該制度在實踐中實現了降低犯罪發生概率的效果,那么,就應當認定該合規整改為有效合規整改。即使合規考察期內有再犯事件發生,也不應該直接認定該合規整改為無效合規整改,應進行嵌入場景的具體分析,區分案件情況。對于那些違法違規事件是偶發的、難防控的情況,可以通過延長合規考察期、完善合規整改方案等方式,繼續推動企業提升犯罪預防效果。對于那些違法違規事件是企業合規整改過程努力不足所導致的情況,才能確認合規整改的無效性,再據此對涉罪企業提起公訴。在案件評價方面,只要檢察機關及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按照辦案流程和合規考察流程履行職責,在履職過程中盡到了合理注意義務,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42〕參見朱孝清:《錯案責任追究的是致錯的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再論錯案責任》,載《人民檢察》2015年第21期,第5頁。那么,即使企業或者責任人在合規考察結束后再次涉嫌違法犯罪行為,也不應當認定該案為“錯案”,更不能對承辦檢察官進行追責。
在域外,企業在合規整改后再涉嫌犯罪的案例不少。例如,捷邁邦美是美國一家醫療器械制造公司,該公司于2012年因賄賂海外醫療人員而違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與檢察機關達成第一個暫緩起訴協議,繳納近2000萬美元罰款,在合規監管人的監督下,進行為期18個月的合規整改。在監管期內,該公司發現其巴西分支機構仍有賄賂行為,于是向合規監管人和美國檢察機關自行披露,最終合規監管期被延長至2016年。但在合規驗收合格后,該公司于2017年又因為海外賄賂和賬目問題而再次違反《反海外腐敗法》,與美國檢察機關達成第二個暫緩起訴協議,又繳納近2000萬美元罰款,進入為期三年的新合規監管期。〔43〕See Zimmer Biomet Holdings, Inc. DPA with U. S. DOJ.
再如,著名的摩根大通集團在2016年因賄賂外國官員而違反《反海外腐敗法》,與美國檢察機關達成不起訴協議,支付超過7000萬美元的罰款,進行為期三年的反腐敗合規整改,最終于2019年解除監管。但是,摩根大通集團又于2020年因市場操縱行為而涉嫌欺詐類犯罪,再與美國檢察機關達成暫緩起訴協議,約定支付9.2億美元的罰款,進入為期三年的新合規監管期。〔44〕See J. P. Morgan Chase & Co. DPA with U. S. DOJ.
可見,對許多大型企業而言,復雜的經營領域、大量的員工數量、多重的管理結構導致企業管理的難度較高,違法犯罪的風險點較多,合規犯罪預防功能的有限性更為明顯。此時,若檢察機關采取“結果中心主義”的嚴格態度,將加劇大型企業的生存困境,同時降低企業開展合規整改工作的積極性。因此,域外檢察機關對企業合規整改后的再犯處理,采取了較為包容的司法態度。
在此項改革試驗過程中,涉嫌犯罪的企業在被納入合規考察后,要進行有效的合規整改,除需要采取諸如停止犯罪行為、采取補救措施、處理責任人、堵塞和修復企業經營管理上導致犯罪發生的制度漏洞和缺陷等“去犯罪化合規”整改措施以外,在必要時還需要根據第三方監督評估組織的要求,針對相關的犯罪行為實施專項合規計劃(即進行“體系化合規”)。〔45〕有學者認為,專項合規計劃的適用是例外而非原則。參見李本燦:《企業合規程序激勵的中國模式》,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2年第4期,第149頁。這意味著,在有限的考察期內,企業一般只能建立一種專項合規管理制度,而無法做到建立一個“大而全”或者“畢其功于一役”的合規管理體系,〔46〕參見陳瑞華:《企業有效合規整改的基本思路》,載《政法論壇》2022年第1期,第99頁。其只能降低相同或類似犯罪行為的發生概率,既無法完全預防再犯,也無法預防企業構成其他類型的犯罪。因此,檢察機關應當客觀看待企業或者關聯人員于合規考察合格后再涉嫌違法犯罪的情況,對完善企業合規建設采取逐步推進的“過程中心主義”方式,避免因對合規功能的刻板認識而阻礙改革的廣泛推進。
九、結語
我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繼續深化改革,除了需要在避免上述八大認識誤區的前提下,辦理更多的企業合規案件,保障涉案企業進行有效的合規整改,使其能夠真正發揮超越刑罰的實質制裁和犯罪治理效果,還需要盡快形成公、檢、法三機關協作推動企業合規改革的實施辦法,明確合規從寬制度體系的內涵,確定合規從寬制度的適用范圍,制定合規整改的監督和評估標準,等等。只有這樣,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才能獲得更為充分的正當性,并凝聚更多的社會共識,也才有望通過《刑法》《刑事訴訟法》的及時修改,將司法推動企業合規建設的制度創新和成功做法加以固定和確認,以促進中國特色的企業行為規制制度的發展完善,助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就此項改革對刑事訴訟理論的影響而言,我們認為,“涉企犯罪案件”中逐漸形成的“附條件不起訴”辦案樣態,意味著一種以教育矯治和預防犯罪為價值追求的新型司法模式,已在中國刑事訴訟中初步形成。這種新型的司法模式,或可稱為“診療性司法”,以區別于傳統的單純注重查明案件事實、實現合法合理處理結果(起訴或者不起訴)的公訴模式(或可稱為“查處性司法”)。
作為協商性刑事司法理念的最新發展,“診療性司法”的本質特征就是,通過釋放現有檢察權能所蘊含的裁量“出罪”空間,激勵涉案企業針對犯罪暴露出來的特定合規風險,“進行有針對性的制度糾錯和管理修復”,乃至建立專項合規計劃,以達到有效預防相同或類似犯罪再次發生的效果。因此,“診療性司法”雖脫胎于“協商性司法”(又稱“合作性司法”),但卻有別于“協商性司法”,也不同于“恢復性司法”,更與“對抗性司法”有著明顯的區別。“協商性司法”的本質特征是,被追訴人在承認犯罪的前提下,與控訴方就某些事項達成合意。〔47〕參見王新清:《合意式刑事訴訟論》,載《法學研究》2020年第6期,第150頁。“恢復性司法”則重在吸納特定案件的利害關系人參與司法過程,并強調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對話、協商,“以求共同地確定和承認犯罪所引發的損害、由該損害所引發的需要以及由此所產生的責任,進而最終實現對損害的最大補救這一目標”。〔48〕[美]霍華德?澤爾:《恢復性司法》,載荻小華、李志剛編著:《刑事司法的前沿問題——恢復性司法研究》,群眾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頁。至于“對抗性司法”,則是一種控辯雙方圍繞各自(不同)的訴訟立場,通過法律賦予的手段進行平等對抗,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緊張(競技)關系的刑事訴訟模式。〔49〕參見李奮飛:《論控辯關系的三種樣態》,載《中外法學》2018年第3期,第727頁。而近年來方興未艾的附條件“出罪”改革實踐所孕育的“診療性司法”,則重在激勵、監督和教育涉案企業在考察期內調整內部治理結構,改造商業模式,去除犯罪基因,堵塞管理漏洞,消除制度隱患,以有效防止再次發生相同或者類似的犯罪行為。未來,還可以針對特別犯罪類型,如“醉駕”案件,借鑒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基本經驗,以醫學治療、戒酒課程、社區服務等行為矯正措施替代刑罰,建立“矯正不訴”“矯正輕緩量刑”等程序路徑,探索在保障刑罰威懾力的同時,防止因過度入罪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不過,論題所限,只能期待未來在獲取更多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對這種新的司法模式進行系統論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