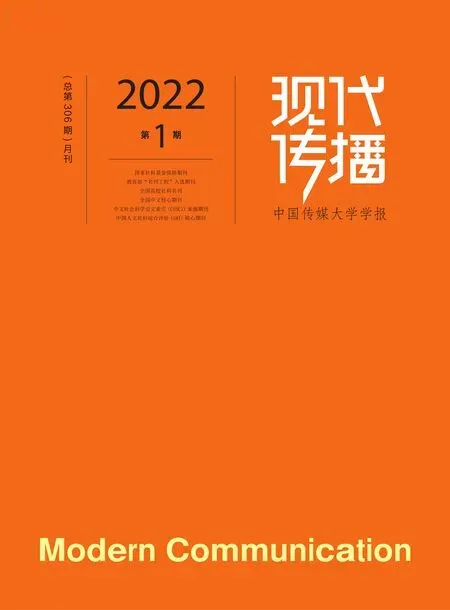身體、遮蔽與新中區:對AI合成主播技術具身的反思*
鄔建中
一、問題的提出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AI”)對媒介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認知科學與人工智能在播音主持方向的代表應用之一,AI合成主播在一定層面上反映了從“離身性”(disembodied)向“具身性”(embodied)的發展。而技術具身理論(embodied theory)來源于對身體理論的源頭異議和思考。①首先,離身理論作為第一代認知理論,認為認知與身體是分離的,心智可以獨立于身體而存在。具身理論則認為心智是基于身體而存在的,在任何時候,它都占有一個特殊的空間,且面臨一個具體的方向。②而對技術身體的反思可追溯到蘇格拉底的“理解你自已”。從費希特到謝林再到黑格爾,無論是“自我”,還是“絕對精神”,都讓自我與現實的差別相對越來越遠,現象和本質的二元對立越來越突出。直到胡塞爾強調 “回到事物本身”,關注先于理論存在的體驗,標志了向現象學的轉向。唐·伊德繼承了現象學的傳統,以“后現象學”的角度專注于“事實”和“事實本身”,力求將現象和本質合二為一。唐·伊德對技術建構的身體體驗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身體始終在場,是物質、文化、技術的此在世界。他綜合了前人的理論,提出了技術身體即身體的存在,從而形成了三個身體的理論③:其中,“身體1”即物質層面的身體;“身體2”即社會與文化層面的身體;而在“身體1”與“身體2”的相互交織與展現中,技術層面的身體即“身體3”便隨即產生了。他認為技術身體是通過技術對特定事物進行體驗,身體與技術便關聯在一起,是在與技術的關系中通過技術或者技術化人工物為中介建立起來的身體3。在此意義上,物質身體成為他對胡塞爾、梅洛·龐蒂為代表的傳統現象學的描述,而文化身體代表他對福柯反現象學的批判。那么,在新的媒介技術環境下,如何理解AI合成主播的技術具身?其技術身體是否帶來了肉身器官的異化與延展?遮蔽與去蔽?“新中區”的AI 合成主播給我們的傳播場景帶來了什么變化?未來會出現怎樣的發展可能?
二、AI合成主播技術具身的蜂窩模型
(一)三個身體與“新中區”
按唐·伊德的相關理論,AI合成主播分成物質身體、文化身體和技術身體。每個身體又在技術的遮蔽、去蔽及雙重遮蔽下,形成了戈夫曼所述的前臺和后臺。在此基礎上,AI合成主播不斷適應技術具身下傳播場景新的融合與裂變,在梅洛維茨所說的中區行為基礎上,成為了“新中區”。所謂中區行為,梅羅維茨認為是“以后區和前區觀念為基礎,在混合場景中出現的新行為。也就是說,觀眾同時看到了部分傳統上的后臺和前臺區域,為了適應新場景,有能力的演員會調整他或她的社會角色,以期與觀眾獲得的新信息保持一致”④。而“新中區”即AI合成主播通過技術具身適應AI技術發展過程中前臺與后臺邊界的模糊,通過跨平臺數據的挖掘、分析,進行傳播場景的融合與重構、技術的去蔽與遮蔽,以模塊化的方式形成更有價值的傳播場景,以適應新的場景,迎合受眾不同的需求,創造更多的可能,成為新的社會角色,同時還產生了肉身器官的異化和延展,讓單一器官能夠變通服務于多器官場景,單一身體能夠服務于多身體場景,為人工智能媒體具身發展提供新的方向和參考。我們可以憑借Peter Morville提出的蜂窩模型⑤,對AI合成主播的技術具身做如下分析,如圖1所示。

圖1 AI合成主播技術具身的蜂窩模型
(二)AI合成主播技術具身的蜂窩模型
首先是物質身體,麥克盧漢認為:“人在正常使用技術的情況下,總是永遠不斷受到技術的修改。反過來,人又不斷尋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術,人仿佛成為了機器世界的生殖器官。”⑥AI合成主播以人類主播的肉身主體為后臺,以肉體與意識的生理共生為基礎,但其肉身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還受到人體記憶力、耐力等因素的限制。而在技術的推動下,AI合成主播與真實主體雖然于具身性在場中分離,但其依然具有衣著、語言、表情等。成為反映世界的數字化身和增強現實技術的生理學實體。⑦在鏡像世界(Mirror world)中,生成數字孿生(Digital Twin),人們可以像在現實世界中一樣進行操作與體驗。⑧且不同于人類主播肉身,其物質身體在技術的幫助下表現為多時空泛在。
其次是文化身體,AI合成主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以去蔽為榮的賽博文化的化身,所謂賽博文化即推崇一個并行于實體空間的虛擬世界,以網絡替身實現向外延展,追求非常規塑造的自由,樂于揭露傳播背后的傳播、真相背后的真相,并形成各種“圈子”,以擺脫身體極其嚴厲權力控制的文化。⑨AI合成主播順應了新媒介環境下,受眾獲取信息手段多樣化的趨勢,在以去蔽為榮的賽博文化基礎上,形成了前臺的文化身體。但實際上,AI合成主播的傳播行為一般都由其后臺的傳播目的決定,這些傳播目的不一定為受眾所知,在一定程度上,AI合成主播的傳播行為是精英階層或社會控制者出于自身利益,對受眾的勸服行為。它服從于階級社會中慣于遮蔽的社會文化。盡管媒介時常提供無比正確的表象,但恰恰是這一點掩蓋了構成正確性的本質的東西。海德格爾曾認為:“現代技術的本質還長期遮蔽著自身;即使電動機已被發明,電子技術已經步入正軌,以及原子技術業已運行。”在某種程度上,AI合成主播的技術具身遮蔽著存在;同時,技術具身也遮蔽著自身的本質。在此意義上,AI合成主播形成了新媒介環境下,以“去蔽”為名的更深層次“遮蔽”,即雙重遮蔽。這才是其位于后臺的文化身體本質。
最后是技術身體,從現象學和人類學的視域出發,技術身體不僅有其當代表現,更有其古代譜系。巫術就是原始人某種意義上的“技術身體”。身體與技術之間因而是源始共生的關系。身體不但是一切技術產生之所,而且也是人類再現或虛擬客觀實在的天然手段。位于前臺的AI合成主播盡可能地讓受眾相信它富有等同于人類的親和力,是掌握了播音主持技術與技巧的人類主播肉身。而在后臺則從傳播目的出發,利用基于算法的AI傳播技術,建立起技術身體與物質身體的交織模型,讓新聞主播發生了從真實到虛擬、從可視到可感、從單一到多向的轉變,這是在特定場景中與觀眾進行多方位、多層次互動的媒介技術形式。在此背景下,戈夫曼提出的前臺、后臺的邊界日趨模糊,各種場景不斷融合和裂變,出現了梅羅維茨所主張的“中區”。而AI人工合成主播作為以物質身體為基礎,與文化身體交織的“技術身體”,可視為進化的 “新中區”代表。下面,我們將對AI合成主播的技術具身進行具體討論。
三、對AI合成主播技術具身的反思
(一)AI合成主播泛在而統一的技術具身
我們首先需要討論的是AI合成主播的技術具身如何存在。在利用蜂窩模型對AI合成主播進行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發現AI合成主播的三個身體是交織而統一的,是泛在而統一的技術具身。
首先,在傳統信息時代,人們利用身體使用媒介,對外部世界進行探索、認識和反思,尋找事物背后的因果關系,總結規律,再在此基礎上作出反應。而在人工智能時代,包括AI合成主播在內的各種傳播工具充斥著人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出現信息冗余與過載。人們必須在技術幫助下,通過技術具身,直觀、迅速,甚至實時地發現事物間有價值的相關性,并實時地作出反應,才能適應當前時代的發展。具體到AI合成主播,就是在云計算和AI智能終端的幫助下,以技術身體直接接受外界刺激,并實時進行AI分析、合成相關節目,及時播報,完成AI合成主播作為媒介的職能。同時,麥克盧漢還曾說過,媒介即訊息。而在人工智能時代,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媒介即數據。首先,所有的媒介信息由數據構成并表現,媒介的各種音視頻、文字等內容,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同一種形態:數據。其次,每個媒介實質上只是一個數據入口,媒介通過云端后臺,在算法支配下對數據進行分析,作出反應,媒介已在一定意義上退化為數據鏈中的一個節點。最后,不同媒介在數據層面同質化,并通過比特幣等量化、物化。因此,世界一定程度上已在數據層面形成身體與技術的融合,技術身體泛在而統一。
其次,麥克盧漢還說過,媒介是人體的延伸,一切技術都是肉體和神經系統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既然媒介即數據,那么也可推論出,數據是人體的延伸。這是因為AI合成主播可被看作是人聽覺、視覺的延伸,而人體的各種器官是相關的,受肉身的神經系統和大腦等支配并相互影響。而各種媒介作為人體的延伸,它們實質上也是相關的、相互影響的。因此,在媒介即數據的前提下,數據間的相關與人體感官間的相關是統一的,感官即數據。世界的各種事物之間,世界和人體之間也存在類似身體感官的各種聯系。從這點看來,世界不過是一個大的身體,而身體就是一處微觀的世界,也即黑格爾提出的無機物的有機化。AI合成主播的技術具身因此泛在而統一。
最后,我們認識到的世界是我們身體的各種感官綜合感覺到的世界。人和世界中一切事物的交流都必須由肉身的各種器官,通過聽覺、視覺等身體體驗而進行。這正如恩斯特·卡普在《技術哲學綱要》中所說:“在工具與器官之間所呈現的那種內在關系,更多地是一種無意識的發現——就是人通過工具不斷地創造自己,因為其效用和力量日益增長的器官是控制的因素,所以一種工具的合適形式只能起源于那種器官。”這個過程具體到AI合成主播,是通過深度學習、語音識別、AI合成等技術,通過視聽甚至觸覺如力回饋等多種方式,以類似生物神經反應的形式傳遞給受眾的,是受人的感官影響的。“我看——通過視覺人工物——世界、視覺技術首先處于看的意向性之中,在這種使用情境中,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將技術融入到我的經驗中,我是借助這些技術來感知的,并且由此轉化了我的知覺和身體的感覺”目前媒介的發展方向是通過智能手表、谷歌眼鏡等穿戴式設備,以模擬人的自然生理方式進行交互,并憑借移動智能終端的互聯與泛在,實現AI合成主播技術具身的泛在與統一。AI合成主播在一定程度上只不過是人類身體各種器官功能的融合與外化。各種媒介如世界之間的事物一樣天生是有聯系的、關聯的。各種媒介組合而成的系統在世界中像一個虛擬的人體,在互相影響中、在人的需要中進化。其可分為三個由小到大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媒介系統自身的進化;第二個層次是媒介在世界中起到類似人體的神經系統的信息溝通作用。媒介的進化包含于身體的進化之中,就像細胞與器官一樣相互聯系、自我生長;第三個層次是現在的所有媒介革命,AI合成技術、物聯網、虛擬現實等不過是在一定層面上強化這種類人體間的聯結。“技術就像是我們的假體,其使得我們能夠在今天的信息世界中遨游。”AI合成主播借助語音識別、深度學習等新技術,成為了基于圖像視覺的虛擬泛在。它也可能自我進化,但如同水中倒影,風一吹過即會變形一樣,AI合成主播仍泛在而統一地存在于技術身體之中。
(二)作為雙重遮蔽的技術具身
梅羅維茨認為:混合場景的新界定有時會產生那么多的含義,我們常常注意不到原來的場景已不復存在,代之而出現的是第三個場景。然而在新場景中常會發生許多行為,這些行為在原來的兩個不同場景中都不可能發生。如前所述,AI合成主播等新技術引發了原有場景的融合與裂變,創造了新的場景,而場景融合的狀態有著必然的“文化邏輯”,受制于技術具身的雙重遮蔽。
一方面,技術的發展讓場景越來越透明,AI合成主播以技術具身實現多時空泛在。利用人的形象,創立了更具交互性、親和力的社會角色,讓我們對現實世界有了更多的把握,更多的去蔽。受眾在一定程度上相信AI合成主播能更快更好地播出新聞節目,揭示事件“真相”,從而以技術實現去蔽來對抗權力控制。“技術不僅是手段。技術是一種去蔽方式。它是去蔽的領域,也就是真理。”例如在某時某處被某種技術遮蔽的知識,可能在深層被卷起,與其他知識之間發生非線性相關,把被遮蔽的各種可能性在歷史、當下甚至未來一一去蔽,呈現在主體面前。
另一方面,在技術的去蔽中,存在受制于技術,而以存在者的方式顯現。不管受眾使用哪一種技術,技術都會對受眾灌輸某種標準化的思想。因此,技術的去蔽同時也是對存在的遮蔽。技術的去蔽是一種挑戰性的,其前提與基礎就是“設定”(stellen)。所謂設定就是從某一方面去看待某物、取用某物。現代技術設定自然、挑戰自然,將事物變成為持存物(bestand)。事物作為存在者在表象中成為對象,世界則被把握為圖像。因此,技術的去蔽不是本真的。海德格爾把技術的這種挑戰性要求稱為座架(gestell),并把它與技術本質相關聯,他說:“現代技術之本質居于座架之中。”座架構成了技術的本質,技術由此關聯世界。AI合成主播在去蔽過程中通過大數據及算法技術的結合,能根據受眾的精確需要和愛好、弱點,對各種場景進行廣泛的聯系和融合,適應新場景的變化,達到其后臺的傳播目的,從而受制于座架之中,形成了新的遮蔽。海德格爾認為:座架在賦予人一種技術的解蔽方式的同時,又遮蔽它自己以及其他的解蔽方式,即座架與存在者對抗并控制存在者,使自身不再顯露,同時也遮蔽解蔽自身和真理。也就是技術的本質在座架中,“我們全部的理解方式都發生于構架的背景中與技術的立場上,我們不能逃脫或站到這種構架之外。”在此意義上,AI合成主播形成了以“去蔽”為名的更深層次“遮蔽”,即雙重遮蔽。
最后,技術的發展也讓我們的肉身器官在對技術的使用中,存在器官功能的轉換與異化。比如光纖中傳輸的光線本來是看的范疇,但我們用它來傳輸高保真音響的聲音信號,讓視覺變為了聽覺。在地質勘測中,我們無法看到深處地底的情況,但是我們用人造可控爆炸,用聽到的回響探索地殼深處的構造。我們用射電望遠鏡監聽來自宇宙深處的電磁脈沖聲音,同時發現了光譜和星球內部結構的關系,學會了用光譜分析星球的組成。在這一切行為中,肉身器官的原有功能被技術遮蔽,聽覺不再為聽,視覺不再為看,但又在另一維度去蔽,通過聽到而看到,通過看到而聽到,從而實現了技術身體的去蔽與遮蔽。但其遮蔽與去蔽同時也是相對的,因為作為技術具身的身體本身也受制于人的情感,人的情感是不可捉摸的,有時會突然變化,存在例外的、“測不準”的情況。而宇宙中也存著不可捉摸的變化,蟲洞、黑洞等“例外”的存在讓時空成為相對的概念。在此意義上,AI合成主播技術具身的去蔽與遮蔽受制于座架,以肉身為限實現無限,是統一而相對的。
(三)發展為“新中區”的技術具身
在遮蔽與去蔽、泛在而統一的技術具身基礎上,AI合成主播發展為了新的媒介技術環境中的“新中區”,為人工智能媒體具身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參考。
AI合成主播是一種媒介領域的視聽呈現,可以看成是一種數字化的表演。因此,我們在三個身體的理論基礎上,可以引入戈夫曼的擬劇理論。他認為社會是一個舞臺,人生是一場表演,表演又分為前臺和后臺,前臺是讓觀眾看到的,被社會規范接受的符號表達。有一整套模式化的期待。“成功的前臺表演需要在劇組和受眾之間達成某種共識,即視前臺為唯一的現實,否則表演將難以為繼。而后臺表演者隱藏的是不想為人所知或不被人接受的形象或內容。同時,在前臺與后臺之間還存在保護性通道,表演者會采取掩飾、隱藏和偽裝的行為,使自我呈現與角色期待保持一致。”每個AI合成主播,如新華社的“小小浩”都是一個場景,因為“電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過內容來影響我們,而是通過改變社會生活的‘場景地理’來產生影響。”它在前臺以類似真人的親和力讓技術身體拉近與受眾的距離。而后臺則根據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針對每個受眾的喜好和弱點制定精確的傳播策略,無隙不入,甚至可以根據每個人的獨特需要和追星行為,在后臺合成以其“愛豆”為基礎的AI主播,創造新的場景,增強傳播效果。同時,“電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間和社會場景的傳統關系,電子媒介創造了新的場景,破除了舊的場景”。在新的媒介環境下,人們獲取信息的手段越來越多,大數據、算法、人工智能更是給了人們分析信息背后的信息的更多可能。因此,戈夫曼提出的前臺后臺的邊界日趨模糊,各種場景不斷融合和裂變,出現了梅羅維茨所主張的“中區”。而AI人工合成主播作為以物質身體為基礎,與文化身體交織的“技術身體”,可被視為進化的“中區”代表。
所謂中區,按照梅羅維茨的定義,是在技術發展的背景下,各種舊的傳播場景不斷融合與裂變,新的傳播場景不斷出現背景下出現的新現象。 “中區行為可以指任何兩個或多個以往不同場景的融合所產生的行為。”中區的演員需盡可能地適應觀眾的在場,但仍將能隱藏的都藏起來。“電子媒介是社會場景的融合與分離所引發社會變化的一種模擬。新媒介傾向于分隔現存的社會信息系統,允許個人形成更深的后臺和更前的前臺和行為風格,而新媒介具有的融合現存的信息系統趨勢,導致了側臺或中區行為。”在人工智能時代,人們接受的信息碎片化、多變化、擴展化,傳播場景不斷融合、裂變,多個場景的相關性與復雜性不斷增加,需要與之適應的中區。而AI合成主播在大數據、算法技術的支持下,能夠針對不斷融合與裂變的場景進行精準傳播。在此意義上的AI合成主播將不再是一個單純進行視聽服務的“技術身體”,而是對各種傳播場景進行融合和增殖的平臺化“新中區”,讓AI合成主播通過深度學習達到類似真人主播的個性化、差異化水平,并基于平臺的用戶大數據挖掘,通過技術后臺的自適應生產,形成適應觀眾個性化需要的“一對一”播音主持藝術風格,開發“長尾市場”,形成AI技術支持下的具身化市場增量。在此背景下,AI合成主播通過“數字孿生”的數字身體,在數據收集的基礎上進行播出只是前臺表象。更重要的是憑借后臺的AI算法及傳播技術,在對受眾數據進行分析、重組的基礎上進行中區化的“場景融合”,從而進行基于客戶關系管理(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的“精確場景傳播”。而所謂客戶關系管理(CRM)可以被描繪為吸引、保留、開發客戶的過程。AI合成主播在新的媒介環境下實現的場景融合,本質是數據化的受眾需求融合,這種互補性融合不應僅局限于傳播內容或傳播場景的功能融合,更重要的是讓基于雙向數字網絡流動的數據為基于場景的“受眾融合”提供幫助,從而實現基于跨平臺的客戶關系管理(CRM),讓媒體能通過AI合成主播,最大化利用現有的受眾資源,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建立新場景來挖掘、引導、創造受眾的需求,為受眾提供差異化的、持續性的傳播場景體驗。未來影響類似AI合成主播智能媒體發展的,將是它能否在合法的基礎上掌握更多、更準確的受眾數據,在此基礎上進行傳播場景的融合與重構,進行多次開發,以模塊化的方式重新組裝,在此基礎上進行 “一次生產,多次加工,多元輸出,廣泛相關,多重服務”,形成更有價值的傳播場景,適應受眾的多層次、個性化需求。
因此,在泛在而統一的基礎上,順應新技術條件下傳播場景的裂變和融合,以梅羅維茨的中區作為定位,AI合成主播成了新的傳播場景融合“新中區”,成為了新的社會角色。它一方面迎合場景需要,在前臺進行相應的傳播行為,同時另一方面通過后臺的AI智能傳播技術,產生場景的融合、裂變和增殖。如對場景1融合裂變出場景n+1,甚至場景n+2、n+3…n+n。新場景之間、新舊場景之間又會不斷地融合裂變,不斷拓展場景的多樣化和可能,同時對原始場景產生多維度回饋。其相關流程如圖2,較粗的線條表現裂變、增殖。

圖2 AI合成主播作為中區的技術具身流程示意圖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流程可能會融合、重合、裂變與反復。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時代》中認為:媒介的新時代不是從一種存在狀態過渡到另一狀態,并非彼此置換而是相互補充,并非按順序發生而是同時存在。而AI合成主播作為“新中區”,以大數據作為生產資料,以算法作為生產力,以互聯網作為生產關系,以擬人化的數字孿生,增加了傳播力和傳播效果,為以AI合成主播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媒體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參考。
注釋:
① 於春:《傳播中的離身與具身:人工智能新聞主播的認知交互》,《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5期,第35頁。
② 唐芳貴:《具身道德的心理機制及其干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頁。
③ 楊慶峰:《物質身體、文化身體與技術身體》,《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第14頁。
⑤ 蔣立兵、萬力勇、陳佑清:《面向用戶體驗的微課設計框架構建與應用》,《電化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3頁。
⑦ 陶飛、劉蔚然等:《數字孿生及其應用探索》,《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2018年第1期,第2頁。
⑧ 譚雪芳:《圖形化身、數字孿生與具身性在場:身體—技術關系模式下的傳播新視野》,《現代傳播》,2019年第8期,第64頁。
⑨ 杜丹、江玉琴:《中國賽博朋克文化表征及話語建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