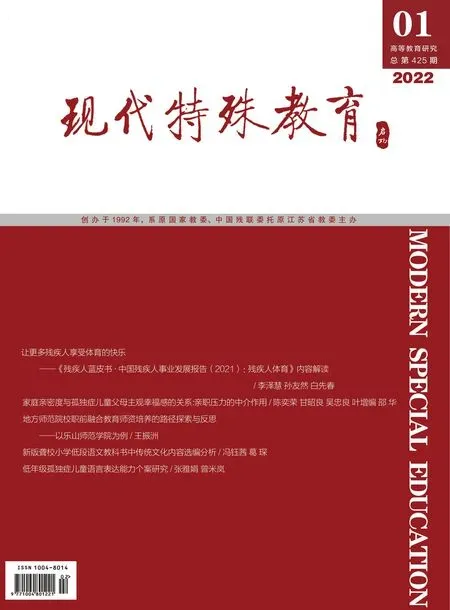全景式的歷史回顧 基礎性的教育研究
——《民國特殊教育研究》書評
馬建強
(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 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 南京 210038)
人是萬物靈長,人也是萬物尺度。自從地球有了人類,就有了殘疾人。殘疾人的出現,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必然現象,也是正常現象。關于殘疾人,從概念到定義,從現象到本質,從產生原因到殘疾分類,從對殘疾人的認識到與殘疾人的相處方式,等等,在人類自身的不同發展時期都有著不同的歷史呈現與現實表達。在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甚至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條件下,對殘疾人的認識也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因而,殘疾人問題是人類社會固有的問題、同生共存的問題、不斷發展變化的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出發,人類既存在殘疾人,與之同時就客觀存在殘疾人教育——無論是原始社會階段的群居公育,還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階段的寬疾、養疾。殘疾人在家庭里,有自然發生的家庭教育;殘疾人在社會中,有或隱或顯的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之外,也客觀存在相對專業化和職業化的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生存、生計教育,甚至也出現過史料多次記載過的機構化和形式化的“學校教育”。比如商周時期出現的專門對盲人進行音樂培訓的機構“瞽宗”等。進入近代以后,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進步,科學技術水平特別是醫學的迅速發展,催生了制度化的殘疾人學校教育。自18世紀起,近代教育學意義上的盲人學校、聾啞人學校首先肇啟于西歐,繼而推展到歐洲、美洲,19世紀中后期傳入亞洲,相繼在中國、日本等地出現。其中,創辦于1835年的澳門女塾被史學界認定為近代中國盲教育的濫觴。創辦于1874年的瞽叟通文館和創辦于1887年的登州啟喑學館,分別為現北京市盲校、山東煙臺特教中心的前身。他們歷經了晚清、民國、新中國,盡管幾經易名易址,但薪盡火傳,弦歌不輟,歷百年而維新,被史學界公認為中國的第一所盲校和第一所聾校。人生五官而有五覺,失去視覺、聽覺即為盲人、聾人。不管是盲人還是聾人,都能與明眼人、健聽人一起進入學校接受正規化、制度化、形式化的教育,這無疑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巨大突破與重要標志。我國的特殊教育,上溯商周,近接晚清,歷經民國,進入新中國開辟新天地,既彰顯了華夏文明“仁愛濟世”的歷史傳統與“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更體現了中華民族“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與“平等、參與、共享”的制度優勢。殘疾人,特別是在認識感知世界、接受文化知識教育方面存在諸多局限與缺陷乃至困難的視障者、聽障者、智障者,讓他們和普通人(或稱“正常人”“健全人”,即非視障者、聽障者、智障者等)一起平等接受教育,共同參與社會生活,一起分享文明成果,一起促進自身發展,一起創造美好生活,這是國家、社會、時代的歷史使命與偉大責任。
教育史是人類認識自身、了解自身、發展自身、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歷史。而特殊教育史,因為教育理念、教育對象、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教育內容、課程內容、組織形式、管理方法,包括社會觀念、經濟水平等要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長期以來一直是被忽視的,不僅歷史學界、教育學界,就是特殊教育界,也少人問津,成果更是屈指可數。客觀來說,在黨的十九大提出“辦好特殊教育”的歷史背景下,這一現狀與全社會關注與重視特殊教育、學術界支持特殊教育學的學科發展、特殊教育界加快特殊教育內涵建設和高質量發展之間,是有一定的差距的。2021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宗順教授所著《民國特殊教育研究》,可謂是近年來特殊教育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是特殊教育學界的一大突出貢獻。該書體幅宏大,圖文兼具,稱得上是“全景式的歷史回顧,基礎性的教育研究”。
一、全景式的歷史回顧
《民國特殊教育研究》以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歷史為主軸,以盲人教育和聾啞教育發展為線索,在梳理兩大類特殊教育機構發展歷史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民國時期的特殊教育在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發展。“全景式的歷史回顧”是該書的最大特色。從1912年到1949年,作者聚焦民國時期中國大陸、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所有特殊教育學校,并將這些學校按創辦主體分為兩大類,一是外國人創辦,二是國人自辦(內含三種:公辦、私辦公助、私辦);按教育對象分為兩大類,一是盲教育,二是聾啞教育。所謂全景式,就是作者最大程度地做到沒有遺漏。從史料中披沙揀金,在考證中條分縷析,提供了不同特殊教育學校的所有創辦、轉辦、續辦、停辦、復辦等信息,并具表呈現,可謂理清盤活了特教的“民國家底”。這一方面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教育史史學功底,更體現了作者“化壓力為動力”、孜孜以求、精耕細作背后對特殊教育史研究的使命感、責任感與人文情懷。
二、基礎性的教育研究
教育史研究,史料是基礎。特殊教育的史料收集,難上加難。但教育史研究關鍵還是要通過史料,完整客觀地呈現民國特殊教育發展的歷史,準確把握其歷史脈絡和精髓,以史為鑒,助推當代特殊教育朝向更高水平發展的需要,展現中國社會文明歷程乃至世界文明進步歷程的題中應有之義。本書在設計研究思路方面頗多亮點。特殊教育史研究,既是教育學學科建設方面的基礎性研究,也是特殊教育理論研究與實踐指導乃至特殊教育事業發展的基礎性研究。因此,它的作用、價值、意義,往往是長期、隱性而多元的。特殊教育,因愛而有教、教之須有方。相比普通教育,它更加需要寬廣博大的愛心、不計收獲的恒心、執著深切的細心、一人一策的專心。學習、了解特殊教育的歷史,可以促進全社會正確認識殘疾人、理性對待殘疾人、服務保障殘疾人,可以推動各行各業的人加深對特教工作者的理解、尊重、信任、支持、幫助,可以增強特教從業人員的職業歸屬感、專業認同感、行業榮譽感、事業使命感。中國有著可歌可泣的特殊教育歷史,更不能沒有可信可傳的特殊教育歷史研究。眾所周知,整個民國時期內憂外患、政府無能、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民不聊生,特別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而導致國土淪喪、家國破碎,從晚清踉蹌蹣跚而來的民國特殊教育,歷經外國人創辦到中國人自辦,從慈善救濟為主到養教工結合到正規化制度化辦學,從少人問津到慘淡經營到逃亡辦學,總體呈現出的是缺乏明確的國家意志、沒有基本的辦學保障、缺少自覺的辦學理念、少有穩定的師資隊伍等特點。這一切更體現在后人從事特殊教育史研究時的史料匱乏,零星散見的信息矛盾、錯誤、存疑之處比比皆是。這對以可信史實為基本要求的教育史研究,可謂障礙重重、困難多多。朱宗順教授“數年磨一劍”,對民國特殊教育進行全景式歷史回顧,繼而就民國特殊教育在學制演化、華洋轉型、思想發展、特征分析、歷史分期、課程剖析、人物研究、文化積淀、盲文手語等方面,進行了科學、謹慎、深入的研究與探討,為我們提供了史料系統、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嚴謹可信的教育史研究成果。這些成果,雖然還有可以繼續深入研究的空間,也有可以進行商榷的地方,但本書在特殊教育專史與斷代史研究方面,無疑可以稱得上極富歷史價值與現實作用的基礎性重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