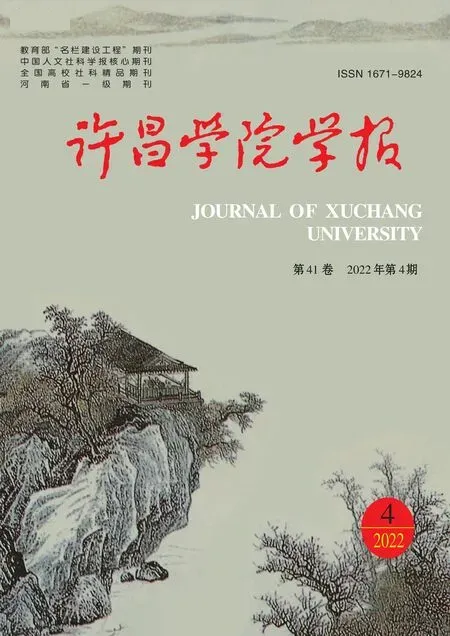“激進派”與“溫和派”的碰撞:“趙湯之爭”的思想緣起
劉 向 輝
(許昌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許昌 461000)
1976年《女勇士》(TheWomanWarrior:MemoirsofaGirlhoodAmongGhosts)出版引發的以趙健秀(Frank Chin)為首的陣營與以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為首的陣營之間的論爭(以下簡稱“趙湯之爭”)是美國亞裔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事件,也被不少學者稱為“關公大戰花木蘭”(1)多位學者使用類似說法指代“趙湯之爭”,美國華裔學者尹曉煌2000年在著作《19世紀50年代以來的美國華裔文學》(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該書2006年在中國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譯為《美國華裔文學史》,譯者為徐穎果)第234頁使用了“Kwan Kung versus Fa Mulan:The War of Words between Chin and Kingston”來稱謂“趙湯之爭”,徐穎果在此書的中文版中使用了“‘關公’大戰‘花木蘭’”這一譯法;中國大陸學者張龍海2004年使用“關公戰木蘭”指代“趙湯之爭”,詳見其論文《關公戰木蘭——透視美國華裔作家趙建秀和湯亭亭之間的文化論戰》(《外國文學研究》2004年第5期)。。縱向來看,“趙湯之爭”始于《女勇士》1976年以自傳形式出版,升級于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以趙健秀發表的論文《中國最暢銷的書》(“The Most Popular Book in China”,1984)、《這不是自傳》(“This Is Not An Autobiography”,1985),收錄在《大唉咿!美國華裔和美國日裔文學選集》(TheBigAiiieeeee!AnAnthologyofChineseAmericanandJapaneseAmericanLiterature,1991)的開篇長文《真假美國亞裔作家你們一起來》(“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湯亭亭發表的論文《美國評論家的文化誤讀》(“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1982),具有戲仿趙健秀意味的小說《孫行者》(TripmasterMonkey:HisFakeBook,1989),1991年被授予布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名譽博士學位之后湯亭亭接受唐娜·佩里(Donna Perry)的訪談等為主要標志。20世紀90年代初期之后伴隨著美國亞裔文學的蓬勃發展,“趙湯之爭”雖然趨于緩和,但時至今日并未徹底結束,依然是學界關注的話題。幾十年來國內外學界對“趙湯之爭”做出了數量不菲的回應或解讀。不過這些研究主要探討20世紀80年代以來處于升級階段的“趙湯之爭”,對20世紀70年代這一醞釀生發階段關注不足,尤其忽視了對“趙湯之爭”思想緣起的探討,從而影響了對“趙湯之爭”的全面認識。本文在闡釋“趙湯之爭”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著力梳理分析“趙湯之爭”的思想緣起。
一、學界對“趙湯之爭”的關注狀況
金惠經(Elaine H.Kim)是較早對“趙湯之爭”進行關注的代表性學者。在1982年出版的著作《美國亞裔文學:作品及社會背景介紹》(AsianAmericanLiterature:AnIntroductiontotheWritingsandTheirSocialContext)中,她強調了趙健秀和陳耀光(Jeffery Paul Chan)對湯亭亭的指控,即《女勇士》是湯亭亭利用“女性主義熱潮”(“feminist fade”)“撈金”(“cash in”)的表現,并指出這種指控正是男性評論家反女性偏見(anti-female biases)的體現[1]198-199。1990年,她在論文《“如此對立之物”:美國亞裔文學中的男性與女性》(“‘Such Opposite Creatures’:Men and Women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中延續了女性主義立場,指出趙健秀等美國亞裔男性對湯亭亭的持續聲討是為了迫使女權主義從屬于民族主義。盡管金惠經對湯亭亭具有一定的偏袒意識,但她最終還是基于現實狀況對趙健秀批判《女勇士》的行為進行了肯定:“趙健秀擔心之事實際已經發生:《女勇士》的白人讀者的確從中找到了強化美國亞裔刻板形象的方法。”[2]75-80在金惠經之后,學界對“趙湯之爭”的關注度不斷攀升,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女權主義批評熱潮,代表性人物有張敬玨(King-Kok Cheung)、黃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馬勝美(Sheng-mei Ma)等。在她們看來,趙健秀等是以大男子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疊加的身份對湯亭亭進行攻擊,而湯亭亭的文學創作是為亞裔女性乃至所有女性賦權發聲,她們也因此通過嚴厲斥責趙健秀來聲援湯亭亭。
與上述女性批評家不同,一些男性批評家對“趙湯之爭”的關注沒有單純局限于性別層面,而是以更開闊的視野看待它。根據里德(Ishmael Reed)1995年在文章《圣迭戈爭論》(“The Battle of San Diego”)中的論述,來自南加州大學的學者李磊偉(2)里德在原文中把李磊偉的名字和其當時所在的學校分別錯寫為“David Lee”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正確的寫法應分別為“David Leiwei Li”和“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994年在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年會專題論壇“第三世界罷工25年之后的美國亞裔文學”(Asian-American Literature Twenty-Five Years After the Third World Strike)的發言中指出,作為一場族裔性別戰爭(ethnic gender war),“趙湯之爭”對峙雙方甚至不是民族主義者與女權主義者,而是讀者群體較小的作家與讀者群體較大的作家。這種讀者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白人女權主義者的籠絡(co-optation)造成的,因為白人女權主義者把美國亞裔作品帶入學術界。不過里德并不認同李磊偉把趙健秀等視為讀者群體較小的作家,他認為李磊偉忽視了趙健秀等在20世紀70年代編輯出版的第三卷《菜鳥讀物》(YardbirdReader)和《唉咿!美國亞裔作家選集》(Aiiieeeee!AnAnthologyofAsian-AmericanWriters)等開創性作品,呼呼少數族裔共同體必須超越性別之爭。在里德看來,女權主義者在這次美國亞裔專題論壇上對趙健秀的責罵攻擊只是對暗地里為政治正確搜尋證據者的一種迎合,而在公開辯論場合她們會樂于接受趙健秀的觀點[3]18-19。尹曉煌(Xiao-huang Yin)2000年在著作《19世紀50年代以來的美國華裔文學》中雖然把“趙湯之爭”稱為“關公大戰花木蘭”式的“舌戰”(War of Words),闡明了二者在創作思想等方面的差異,指出雙方論戰削弱了美國華裔作家作為共同體代言人的力量,但認為它也是美國華裔文學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反映了多元化的美國華裔感性,證明美國華裔文學已經成為美國華裔經歷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4]246。
進入21世紀以來,“趙湯之爭”雖然并沒有進一步升級,但學界的關注卻依然在增加,其中中國學界的關注就是一個代表,代表性論文有趙文書的《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的錯置——華裔美國文學中的男性沙文主義解析》(2002)、張龍海的《關公戰木蘭——透視美國華裔作家趙建秀和湯亭亭之間的文化論戰》(2004)。正當中國學界熱議“趙湯之爭”時,多年關注趙健秀的學者徐穎果2004年在《中華讀書報》第3期刊發了《“我不是為滅絕中國文化而寫作的”——美籍華裔作家趙健秀訪談錄》。她指出“近年來”的“趙湯之爭”在美國的華裔文學及其研究中是個重要話題,因為它涉及華裔文學書寫的一系列重要主題,其實質是關于華裔應該如何看待中國文化的問題[5]3。這篇訪談為當時中國處于上升勢頭的“趙湯之爭”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然而也遭到了激烈回應。美國華裔學者林澗(Jennie Wang)2005年3月3日在《文學報》上以《何謂趙湯之爭?趙湯不爭;趙湯休爭!》的文章對徐穎果的訪談進行了回應,其目的是及時制止“趙湯之爭”在中國學界引發的“誤導輿論”,避免造成兩性敵對的現象和國內學術界的不幸。林澗以絕對的態度否認“趙湯之爭”的存在,并以鮮明的“褒湯(亭亭)貶趙(健秀)”姿態斥責趙健秀,認為趙健秀不擇手段地打擊湯亭亭,并以打擊湯亭亭,批評女性文學、女性作家而出名,是華人文學、華裔文學走向世界,進入西方文壇主流社會的一塊討厭的絆腳石,也為西方主流社會讀者與批評家提供了現成的笑料和抵制的理由[6]3。
林澗犀利的呼吁式批判最終沒有達到“不爭”或“休爭”的效果,在其之后有不少中國學者繼續關注“趙湯之爭”,而且有學者對林澗的觀點進行了直接回應。2012年肖畫在文章《重讀美國華裔文學中的“趙湯之爭”》中指出,林澗針對“趙湯之爭”表現出明顯的“揚湯抑趙”傾向,她所謂的“湯亭亭從來沒有也不屑于和趙健秀爭論”等種種說法值得商榷,并從“故事新編”“自傳寫作”和“性別爭論”三個角度重新探討了“趙湯之爭”[7]69-75。2015年陳永在文章《“趙湯之爭”的表演性與任璧蓮對“亞裔感性”的消解》中指出,“趙湯之爭”折射出趙健秀對如何構建“亞裔感性”的不斷深入思考和此理念的斯皮瓦克式“策略性本質主義”實質,雙方在事實上形成了共謀關系,因而是文化表演,但它以奇特的方式促進了美國亞裔文學的長足發展[8]124。2017年劉會鳳在文章《從“趙湯之爭”看趙健秀的華裔文學創作觀》中主要從關注趙健秀的角度分析了曠日持久的“趙湯之爭”,她認為“趙湯之爭”是圍繞華裔文學如何真實再現美國華裔社會生存狀況展開的激烈爭論,而趙健秀是這場持久論戰的頑強守護者。趙健秀的主要觀點是批評以湯亭亭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自傳體的方式呈現被改編之后的偽中國文化[9]129-130。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趙湯之爭”的態度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抑或中立,基本點出了其焦點問題:自傳體裁問題、中國文化改寫問題、性別爭論問題。這些討論主要圍繞20世紀80年代以后進入升級階段的“趙湯之爭”,關注的基本是處在顯性層面的矛盾沖突,而對“趙湯之爭”的內在誘因關注不夠,進而易把“趙湯之爭”塑造成一個1976年后突然或偶然發生的孤立事件。事實并非如此,“趙湯之爭”的爆發有著深刻的社會思想基礎,絕非不少學者所言的趙健秀對湯亭亭的個人攻擊行為,而是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美國亞裔文學內部不同思想碰撞的必然結果。
二、“趙湯之爭”的思想緣起
1976年《女勇士》以自傳形式出版是趙健秀公開批判湯亭亭的導火索,因為1975年趙健秀在受克諾夫(Knopf)出版社之邀審校《女勇士》樣稿時曾專門致信湯亭亭:
黃種人自傳是一種白人種族主義形式……是對我們創作的侮辱,把我們塑造成怪胎和供養在白人動物園里的人類學研究對象,而非擁有完整復雜世界的人類……(建議湯亭亭)放棄自傳而以小說形式出版。作為小說的話,我可以喜歡你的作品,而不用必須喜歡或認同其中的敘述者或任何人物角色,也可認同你創作的微妙之處以及心照不宣的疏漏(knowing lapses),但我不能把其賦予自傳作家。[10]51
結局是湯亭亭沒有聽從趙健秀的建議以小說體裁出版《女勇士》,而是繼續以自傳體裁出版,進而直接引發了趙健秀的譴責。其實湯亭亭對以何種體裁形式出版《女勇士》沒有表示太多關注,因此也沒有在回信中直接回應趙健秀的建議,當然她也沒有足夠的權力決定以何種體裁形式出版。最終決定圖書體裁形式的是出版商,而出版商考慮的首要因素自然是市場和利潤。針對《女勇士》被劃分為非虛構類別這一問題,克諾夫出版社的編輯艾略特(Charlies Eliot)曾經解釋說:“小說很難賣,而《女勇士》作為非虛構自傳暢銷的機會更大。”[10]51湯亭亭對趙健秀建議的不置可否以及出版社基于市場銷售的體裁劃分看似為純粹的圖書出版之舉,實則背后隱藏著一種文化治理思想,即美國主流社會文化對美國亞裔文化的操控與塑形,這才是趙健秀激烈反對的根本所在。
李磊偉指出,圖書編輯對體裁類別的劃分實際上控制著作品的被體驗過程,體裁問題不僅涉及經濟利益,而且涉及政治利益,而趙健秀一直最為關注的就是政治利益。對趙健秀來說,美國亞裔文學自傳的出版史就是美國白人出版商操控壓制“黃種人藝術”(“yellow art”)的歷史[10]51。趙健秀對自傳體裁以及美國出版行業的批判由來已久,早在1972年他在與陳耀光合發的文章《種族主義之愛》(“Racist Love”)中就對美國出版業和自傳進行了嚴厲譴責。他們指出,美國的出版體制是導致少數族裔自我輕視錯覺的手段之一,過去只有五個美國出生的華裔出版過具有一點嚴肅意味的文學作品,即出版自傳《虎父虎子》(FatherandGloriousDescendant,1943)的劉裔昌(Pardee Lowe)、出版自傳《華女阿五》(FifthChineseDaughter,1950)的黃玉雪(Jade Snow Wong)、出版四部小說和詩歌的張粲芳(Diana Chang)、出版小說《大明所建之屋》(TheHousethatTaiMingBuilt,1963)的李金蘭(Virginia Lee)、出版半自傳《金山》(MountainofGold,1967)的宋李瑞芳(Betty Lee Sung),其中劉裔昌、黃玉雪、李金蘭和宋李瑞芳這四位作家都證實了美國華裔為大眾所熟悉的刻板形象[11]67-68。在這四位作家的作品中,有三部都是自傳或半自傳,可見趙健秀對自傳體裁的反對絕非空穴來風。針對趙健秀厭惡自傳的原因張敬玨進行了專門分析,她認為根源在于美國亞裔自傳與市場關系的矛盾歷史,即早期美國亞裔作家為了使作品出版基本采用自傳體裁,這也是美國亞裔生命書寫英語作品數量居于多數的原因,但這些作品容易被解讀為民族志,進而成為滿足主流讀者凝視和東方主義期待的工具[12]35。因此可以說趙健秀對《女勇士》以及湯亭亭的攻擊并非偶然性的個人恩怨,其要旨是對操控美國華裔自傳出版的美國白人主流社會進行批判。
從趙健秀對李金蘭小說的批判可以看出,趙健秀的目的并非純粹批判自傳體裁,而是批判任何強化美國亞裔刻板形象的文學體裁,只不過自傳在早期出版的美國亞裔文學作品中占據的數量更多、更具代表性而已。許芥昱(Kai-yu Hsu)和帕魯賓斯卡斯(Helen Palubinskas)在《美國亞裔作家》(Asian-AmericanAuthors,1972)中指出,雖然自傳本身沒有問題,但《虎父虎子》《華女阿五》這兩部自傳以及李金蘭的半自傳《大明所建之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白人社會期待的華裔刻板化形象[13]10,即與趙健秀和陳耀光的觀點形成了共鳴。李金蘭的《大明所建之屋》不管是被趙健秀等界定為小說,還是被許芥昱等界定為半自傳,都擺脫不了被詬病的結局,因為它是美國亞裔刻板形象的塑造者和驗證者。趙健秀與許芥昱共同的根本目標不是批判自傳體裁,而是批判以上述自傳為代表的塑造或強化亞裔刻板形象的作品。就此而言,趙健秀批判湯亭亭的《女勇士》并不只是因為其自傳體裁,更重要的是因為《女勇士》以自傳體裁出版帶來的負面效果——對美國華裔刻板形象的強化。
趙健秀對湯亭亭的批判自然更不是因為嫉妒或擔心湯亭亭的名望蓋過他。首先,趙健秀在湯亭亭因出版《女勇士》成名之前早已因創作《雞籠里的中國佬》(TheChickencoopChinaman)等作品而聲名鵲起,這也正是克諾夫出版社主動邀請趙健秀審校《女勇士》樣稿的主要原因。其次,趙健秀的確具有強烈的好斗性,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他就與華裔作家李金蘭針對身份問題展開了激烈論爭,并對劉裔昌、黃玉雪以及黎錦揚(C.Y.Lee)的自傳或小說進行批駁,同時向哈斯勒姆(Gerald W.Haslam)、比克曼(Alan Beekman)等白人批評家“宣戰”,痛擊他們的種族主義思想。即使趙健秀對湯亭亭的批判被定性為個人攻擊,湯亭亭也只是趙健秀眾多攻擊對象中的一個,只不過這一攻擊因《女勇士》后來影響巨大而變得更為矚目而已。趙健秀四處樹敵的做法固然值得商榷,但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抵制白人種族主義來構建具有主體地位的美國亞裔身份。因此,“趙湯之爭”爆發的內因不是趙健秀針對湯亭亭《女勇士》發泄私憤,而是其反對白人至上主義、構建美國亞裔身份思想的外化與延續。
知悉趙健秀的思想初衷之后,學界可以進一步探究“趙湯之爭”爆發的必然性。從本質上看,“趙湯之爭”是美國亞裔內部兩種不同文學思想長期交鋒碰撞的必然結果。趙健秀代表的是相對激進的思想,即主張通過痛擊白人至上主義思想來構建鮮明的美國亞裔身份;湯亭亭代表的是相對溫和的思想,即主張通過中西文化的有機調和來構建具有包容性的美國亞裔身份。這兩種思想的碰撞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趙李之爭”中就有充分體現。1970年趙健秀訪談李金蘭時問她的身份是什么,而李金蘭對身份問題根本不在意,直言她沒有類似困擾,只是偶爾會想到身份問題,即對身為中國人、美國人、美國華裔(Chinese-American)或華裔美國人(American-Chinese)的問題不是特別關注[13]1-2,因為她已經習慣了趙健秀所言的白人主流社會強加給亞裔的刻板形象,而且認為這種刻板形象適用于包括黑人、華人在內的所有少數族裔,她也不會因此感覺受到冒犯[14]ⅹⅹⅸ。趙健秀完全不同意李金蘭的觀點,他要打破白人主流社會一貫強加給亞裔的刻板形象。在趙健秀眼中,李金蘭是一個被白人主流社會徹底洗腦的受害者,她對中國歷史、美國華裔歷史、中國藝術、中國戲劇的認知完全源于白人視角[14]ⅹⅹⅲ。李金蘭以白人視角為基礎的創作只能強化由來已久的亞裔刻板形象,而這正是她與趙健秀產生矛盾的思想基礎。
正是緣于一直以來對美國白人主流社會操控美國亞裔社會的不滿,趙健秀不僅在自身創作中不遺余力地打破白人強加給美國亞裔的刻板形象,而且極力反對塑造或強化亞裔刻板形象的作品。與李金蘭的作品相比,湯亭亭的《女勇士》在美國亞裔運動、女權主義思潮高漲等多重事件疊加的影響下,引發了空前的關注。當然,《女勇士》也借助其廣泛的銷量在讀者群體,尤其是白人讀者群眾中再次印證了美國亞裔的刻板形象,而造成這種結局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女勇士》的自傳體裁,因為它使很多讀者相信《女勇士》中經湯亭亭藝術加工的中國文化就是真實的中國文化。作為一名以批判亞裔刻板形象為己任的斗士,趙健秀自然要對作為自傳的《女勇士》進行譴責,況且他在該書出版之前已經“好言相勸”湯亭亭不要以自傳體裁出版。巧合或者具有偶然性的是,湯亭亭的《女勇士》成為《虎父虎子》《華女阿五》《大明所建之屋》之后美國亞裔文學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自傳或半自傳作品,湯亭亭也成為與黃玉雪、李金蘭等類似的強化或驗證美國亞裔刻板形象的作家。因此,趙健秀對湯亭亭的批判不是一時興起,也不是完全針對個人,而是其反抗白人種族主義思想的延續。
三、結語
作為美國亞裔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趙湯之爭”的確引發了學界大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美國亞裔文學的存在感和關注度,體現了趙湯二人“殊途同歸”的結果,但也反映出美國亞裔文化共同體內部不甚和諧的一面。學界之所以過多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進入升級階段的“趙湯之爭”,主要在于它觸及了自傳體裁、中國文化改寫、性別之爭這三個在美國華裔文學研究領域乃至整個美國亞裔文學研究領域中都備受關注的議題。但也正是因為過于關注“趙湯之爭”中的熱點問題,學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趙湯之爭”思想緣起的探究。“趙湯之爭”的直接誘因固然是《女勇士》以自傳體裁出版,固然存在一定的個人恩怨色彩,但其本質是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美國亞裔意識覺醒的表現,其發生確切地說是美國亞裔內部兩種文學創作思想碰撞的必然結果,即以趙健秀為代表的激進派思想與以湯亭亭為代表的溫和派思想碰撞的外在形式。兩種思想的對立并置一方面說明20世紀70年代美國亞裔文學的確步入了較為成熟的階段,體現了美國亞裔文學創作的多元性與豐富性;另一方面說明美國亞裔族群內部開始認真思考關乎美國亞裔文化共同體構建的身份問題,而這正是美國亞裔運動深入推進的表現。宏觀而言,“趙湯之爭”是通過“和而不同”的形式為亞裔聯合發聲,使其在美國政治領域和主流社會達到最大的影響力和輻射度[15]總序4,進而推動美國亞裔文化共同體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