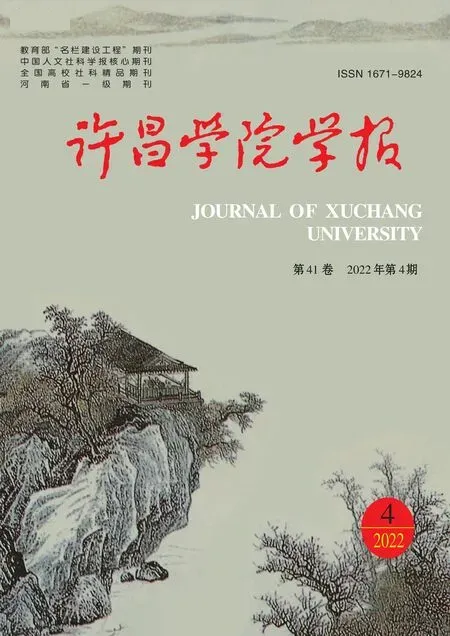《秦王破陣樂》在古代日本的傳播及其變革
王 文 清
(中央民族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北京 100081)
作為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之一,《秦王破陣樂》曾經(jīng)在東亞文化發(fā)展史上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然而,截至目前,國(guó)內(nèi)有關(guān)《秦王破陣樂》的研究多著眼于其創(chuàng)作來源、歷史變遷以及樂曲本身,較少論及對(duì)外傳播的具體情況(1)目前學(xué)術(shù)界有關(guān)《秦王破陣樂》創(chuàng)作來源與歷史變遷的研究居多,歷時(shí)性研究如歐陽(yáng)予倩:《唐代舞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王克芬:《中國(guó)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87年版;楊憲益:《秦王〈破陣樂〉的來源》,《尋根》2000年第1期;柏紅秀:《唐代宮廷音樂文藝研究》,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王怡康:《唐〈破陣樂〉考釋》,河南大學(xué)2009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另有程雅娟:《“軍權(quán)”與“戲飾”之融合——〈信西古樂圖〉中的唐代武舞服飾研究》,《裝飾》2011年第10期,從服飾構(gòu)成角度分析《秦王破陣樂》的舞蹈服飾;李丹婕:《〈秦王破陣樂〉的誕生及其歷史語(yǔ)境》,《中華文史論叢》2016年第3期,結(jié)合《秦王破陣樂》的由來、特色與功能,考察其誕生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環(huán)境。而有關(guān)《秦王破陣樂》對(duì)外傳播史少有專門研究,但在部分古代樂舞交流史的研究專著中有所提及,如金秋:《古絲綢之路樂舞文化交流史》,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年版;王克芬、江東:《日本史籍中的唐樂舞考辨》,上海音樂出版社2013年版。。本文將視角擴(kuò)展至古代日本,從唐代樂舞文化傳播的角度考察《秦王破陣樂》在古代日本的傳播情況,初步展示古代日本對(duì)唐代《秦王破陣樂》的接納及產(chǎn)生的衍變,以期對(duì)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和古代日本樂舞文化發(fā)展史的研究有所貢獻(xiàn)。
一、《秦王破陣樂》的初創(chuàng)
有關(guān)《秦王破陣樂》產(chǎn)生的時(shí)間,通常認(rèn)為在武德三年(610)左右秦王破劉武周時(shí),地點(diǎn)在破劉武周所在地河?xùn)|(今山西)。談及《秦王破陣樂》的最初創(chuàng)作者,雖有爭(zhēng)論,但學(xué)界通常圍繞“軍中將士”和“民間百姓”這兩個(gè)行為主體展開論述。在筆者看來,對(duì)于此類具有政治內(nèi)涵的創(chuàng)作作品而言,不同階層的創(chuàng)作者代表著不同的政治態(tài)度和政治認(rèn)同。就此曲而言,若由將士自發(fā)創(chuàng)作,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將士的忠心、軍心的穩(wěn)固、士氣之盛;若是百姓自發(fā)創(chuàng)作并傳唱于坊間,便可體現(xiàn)百姓當(dāng)時(shí)的精神狀態(tài)以及對(duì)政治形勢(shì)的態(tài)度。因而筆者現(xiàn)以此曲創(chuàng)作者身份為劃分,做一分析。
持“軍中將士論”者認(rèn)為此曲最初流傳于軍隊(duì)中,是軍中將士為太宗所作。如學(xué)者王安潮認(rèn)為,這部作品是為表現(xiàn)李世民于武德三年在山西謝州、并州一帶大敗叛軍劉武周,軍中士兵中相頌秦王軍功之歌,這是“破陣”之樂的源頭[1]。持此觀點(diǎn)者所據(jù)史料是最早記錄《秦王破陣樂》的《隋唐嘉話》:“太宗之平劉武周,河?xùn)|士庶歌舞于道,軍人相與為《秦王破陣樂》曲,后編樂府云。”[2]18另《新唐書·禮樂十一》中載:“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3]467-468若論其創(chuàng)作的“靈感來源”,可見《音樂百科辭典》中《秦王破陣樂》的條釋:“《破陣樂》原是隋代(581—618)軍歌。唐武德庚辰年(620),秦王李世民(627—649在位)擊敗叛將劉武周,將士們把新詞填入《破陣樂》舊曲,以歌頌秦王功德,在慶功之際唱出,名《秦王破陣樂》。”[4]487即《秦王破陣樂》最早源于隋代軍歌,是在隋舊曲《破陣樂》基礎(chǔ)上填詞改編而成的。
持“民間百姓論”者則認(rèn)為《秦王破陣樂》為唐代民間所創(chuàng)的歌謠,是百姓歌頌唐太宗豐功偉業(yè)而傳唱的。這種觀點(diǎn)所據(jù)史料如《唐會(huì)要·中·破陣樂》:“貞觀元年正月三日,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之曲。太宗謂近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民間遂有此歌。’”[5]612《舊唐書·音樂志二》曰:“太宗為秦王之時(shí),征伐四方,人間歌謠《秦王破陣樂》之曲。”[6]715以及《通典·樂六》載:“太宗為秦王時(shí),征伐四方,人(民)間歌謠有《秦王破陣樂》之曲。”[7]3718據(jù)此推斷《秦王破陣樂》最早為百姓所作的民間歌謠。
除以上兩種傳統(tǒng)說法外,楊憲益先生的“外來傳播論”給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他在著作《譯余偶拾》中提出《秦王破陣樂》很有可能從突厥傳入中國(guó),其源頭是古羅馬的武舞——“突羅戲”。他認(rèn)為,因古代稱羅馬為“大秦”,所以“秦王”非唐太宗而是羅馬皇帝,而“破陣”是“突羅戲”別稱“霹靂戲”的音譯;又因古代我國(guó)與東羅馬存在文化交流,而突厥又是重要媒介,所以羅馬武舞很有可能經(jīng)突厥傳入中國(guó)[8]19。
就上述觀點(diǎn)而言,第三種說法雖新穎,但僅是簡(jiǎn)單論證了其可能性,史料依據(jù)太少,只能說是一種猜測(cè)。在筆者看來,據(jù)《唐會(huì)要·中·破陣樂》中太宗對(duì)近臣所說的一席話,“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民間遂有此歌”,可推斷出唐太宗在武德元年(618)掛帥出征到武德九年(626)登基稱帝這段時(shí)間內(nèi),此曲已在民間創(chuàng)作傳唱。另?yè)?jù)《新唐書·禮樂十一》記載:“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隋唐嘉話》也稱:“太宗之平劉武周,河?xùn)|士庶歌舞于道,軍人相與為《秦王破陣樂曲》,后編樂府云。”可知在武德三年左右秦王攻破劉武周平定北方后,軍隊(duì)中已存在此曲。若論此曲最早的創(chuàng)作者是民間百姓還是軍中將士,現(xiàn)有史料還不能確定。但據(jù)現(xiàn)有材料可以推測(cè),在武德三年至武德九年這段時(shí)期,已存在此類時(shí)事政治題材的樂曲創(chuàng)作,并且這些樂曲是由百姓和軍士創(chuàng)作的主題一致的不同樂曲。
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秦王破陣樂》并非一種樂舞,僅僅是民謠形式,而最初的這種只歌不舞的《秦王破陣樂》也非唐太宗本人所創(chuàng)[9]4。據(jù)《唐會(huì)要》記載:“貞觀元年正月三日,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之曲。”可知,貞觀元年(627)唐太宗即位后此曲便在宮廷首次演出。既然這時(shí)《秦王破陣樂》已成為在宮廷展演的侍宴樂曲,必然不可能僅是簡(jiǎn)單民謠,而是由宮廷樂工加工而成的內(nèi)容更加豐富、規(guī)模更大的《秦王破陣樂》。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展演的《秦王破陣樂》還沒有舞的部分。在唐太宗結(jié)合戰(zhàn)爭(zhēng)形勢(shì)繪制《破陣樂舞圖》之后,《秦王破陣樂》才加入了舞的部分[9]5。可見唐太宗對(duì)這一歌功頌德的武舞極為重視,《秦王破陣樂》也從此逐漸具備了唐代大曲的規(guī)模。
二、唐樂東傳與日本對(duì)《秦王破陣樂》的接納
早在日本飛鳥時(shí)代,以天皇為中心的國(guó)家政權(quán)剛剛建立,政權(quán)不穩(wěn),文化發(fā)展處于起步階段。而這一時(shí)期的中國(guó)隋朝結(jié)束了長(zhǎng)期的南北分裂,其強(qiáng)大的國(guó)勢(shì)引起日本統(tǒng)治者關(guān)注。圣德太子確立文化立國(guó)政策,并恢復(fù)了與中國(guó)的交流,以攝取新文化。到了奈良時(shí)代,日本更是大量吸收并模仿中國(guó)唐代文化,自630年舒明天皇第一次派遣遣唐使,至895年的二百六十余年間,日本朝廷曾計(jì)劃向中國(guó)派出20次遣唐使,其中成行的有13次。可見中日交流之頻繁。雖然遣唐使在不同時(shí)期有不同的組成,但都是經(jīng)過日本朝廷嚴(yán)格篩選的學(xué)問淵博或有一技之長(zhǎng)之人,其中便有專業(yè)的樂師和舞者。此外還有漂洋過海的商人和前往日本的中國(guó)人,他們都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此過程中,高度繁榮、形式豐富的唐代樂舞隨之東傳,在日本的藝術(shù)土壤上生根發(fā)芽,其中便有被稱為唐初第一部大曲的《秦王破陣樂》。
據(jù)筆者研究,在大多數(shù)有關(guān)《秦王破陣樂》的研究專著或論文中,談及《秦王破陣樂》傳入日本者,多引《大日本史》對(duì)《皇帝破陣樂》的記載,認(rèn)為《秦王破陣樂》是文武天皇時(shí),由遣唐使者粟田真人傳入的[10]10。如《山西音樂史》:“《秦王破陣樂》在當(dāng)時(shí)名氣很大……武則天時(shí)期日本遣唐使節(jié)粟田正人將其帶回了日本。《秦王破陣樂》傳入日本后,被譯為《皇帝破陣樂》。”[11]138若論此觀點(diǎn)是否成立,我們就先要討論《大日本史》所載的《皇帝破陣樂》和唐代歌頌唐太宗的《秦王破陣樂》是否為同一樂舞。
持兩者所指為一論者,主要有以下兩種邏輯:其一,認(rèn)為《秦王破陣樂》傳入日本后,被譯為《皇帝破陣樂》;其二,認(rèn)為《秦王破陣樂》和《皇帝破陣樂》所指相同,因傳入時(shí)唐太宗為秦王,故稱《秦王破陣樂》,后來太宗即皇帝位,改稱《皇帝破陣樂》[12]154。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兩者所指并不為一。如王克芬認(rèn)為《皇帝破陣樂》與唐代歌頌唐太宗的《破陣樂》非同一樂舞,應(yīng)為唐燕樂中“立部伎”八部之一的《安樂》,而《信西古樂圖》所錄的另一個(gè)《破陣樂》,即《散手破陣樂》也似為《安樂》[13]343-344。
據(jù)筆者搜集到的史料,日本方面有關(guān)《皇帝破陣樂》和《秦王破陣樂》的直接文字記載可見《大日本史·禮樂志》和《樂曲考》。另在《信西古樂圖》和《舞樂圖》中大量保存著先后傳入日本的唐樂舞圖文資料,從中可見《皇帝破陣樂》和《秦王破陣樂》的部分舞蹈形態(tài)。綜合分析后,筆者認(rèn)為前一種觀點(diǎn)尚且存疑,后一種觀點(diǎn)更有說服力,有以下三個(gè)理由:首先,就翻譯本身而言,《秦王破陣樂》中的“秦王”和《皇帝破陣樂》中的“皇帝”的日語(yǔ)發(fā)音并不相近反而差別很大,且寫法上也有很大差別,很難想象是翻譯本身的原因使同一樂舞產(chǎn)生不同名稱。其次,當(dāng)時(shí)遣唐使帶回日本的唐樂小調(diào)有48種,其中有歸入壹越調(diào)曲的《皇帝破陣樂》和歸入乞食調(diào)曲的《秦王破陣樂》(2)田邊尚雄:《東洋音樂史》,植村幸生校注,日本平凡社2015年版,轉(zhuǎn)引自金秋:《古絲綢之路樂舞文化交流史》,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頁(yè)。。最后,日本《樂曲考》載:“(皇帝破陣樂)此曲或言唐太宗所作,又言唐玄宗所作,不確切。其名亦稱《武德太平樂》,又稱《安樂太平樂》,在唐朝不聞此名。”[14]25在《大日本史·禮樂志》中有關(guān)《皇帝破陣樂》的記載為:“皇帝破陣樂……后周宇文邕平齊所作,即唐立部伎也,新樂,大曲,有舞,文武帝時(shí)遣唐使粟田真人道麻呂傳之。”[10]10可見《皇帝破陣樂》是后周武帝宇文邕平齊所作的樂舞,在中國(guó)古籍中稱作《安樂》,又稱《城舞》,而并非唐太宗所作的《秦王破陣樂》。實(shí)際上,在《大日本史·禮樂志》中載有三種“破陣樂”,即《皇帝破陣樂》《散手破陣樂》和《秦王破陣樂》。日本《舞樂圖》中的《皇帝破陣樂》和《信西古樂圖》中的《皇帝破陣樂》所繪舞者并非“披甲持戟”,與《舊唐書》所記《秦王破陣樂》的演出服飾不同,且“拔劍而舞”的動(dòng)作也與歌頌太宗的《秦王破陣樂》不符。而《舞樂圖》中的《散手破陣樂》舞者服飾姿態(tài)頗具“胡風(fēng)”,確實(shí)更似《安樂》。
綜上,日本典籍中所載的《皇帝破陣樂》和《秦王破陣樂》雖同為日本文武天皇時(shí),由遣唐使者粟田真人(粟田道)傳入的,但兩者實(shí)則非同一樂舞,且唐代典籍中并無《皇帝破陣樂》這一樂舞名稱,而是傳入日本后出現(xiàn)的稱謂,與中國(guó)古代典籍中的《安樂》《城舞》相對(duì)應(yīng)。日本《樂曲考》所載《皇帝破陣樂》這一名稱應(yīng)是沿用了日語(yǔ)的稱呼,至于部分中國(guó)研究者認(rèn)為《皇帝破陣樂》和歌頌唐太宗的《秦王破陣樂》為同一樂舞,應(yīng)是混淆兩者所致。
日本人從飛鳥時(shí)代晚期至平安時(shí)代初期曾大量引入中國(guó)唐樂,但也并非全盤照搬,而是在主觀上有選擇性地接納,如唐代用于帝王朝賀、祭祀天地等大典的儀式音樂——雅樂便不在其中。究其原因,一如他們認(rèn)為中國(guó)雅樂并不是一種令人愉快的音樂;二如雅樂規(guī)模太大,難以引進(jìn)。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國(guó)王權(quán)性質(zhì)的不同。日本和中國(guó)王權(quán)的由來、正統(tǒng)性的說明方法有很大的區(qū)別:中國(guó)的皇帝權(quán)力來源于天的受命和委托,自詡為天子。因此,就有必要祭奠天地,祭奠自己權(quán)力的根源——天地、四季、各種自然現(xiàn)象,祈求宇宙的和諧和地上世界的安定。而日本天皇由天孫降臨來說明權(quán)力的正統(tǒng)性。因?yàn)榕c天神有直接的血統(tǒng)聯(lián)系是前提,所以天地祭祀是無用的,以天地祭祀為中心的禮樂制度并不為日本所接受。可以說日本學(xué)習(xí)吸納唐朝的雅樂是沒有必要的。因此,日本古代宮廷接受的是禮儀、祭祀結(jié)束后用于筵席的燕樂和散樂[15]。唐《秦王破陣樂》等大曲及宮廷燕樂傳入日本后,常在其宮廷宴會(huì)和宗教等重要儀式活動(dòng)中時(shí)有上演,可見日本積極接納大曲及宮廷燕樂亦用于其禮儀服務(wù)。
三、《秦王破陣樂》在日本的衍變
唐代“安史之亂”后盛唐氣象不在,對(duì)日本的吸引力銳減,而日本自平安朝開始政治社會(huì)發(fā)展趨于穩(wěn)定,在新王朝的統(tǒng)治下日本民族意識(shí)逐漸覺醒,不再如之前那樣遣使學(xué)習(xí)中國(guó)文化,中日之間官方的樂舞文化交流也漸趨停滯。不同于奈良時(shí)代的“唐風(fēng)熱”,進(jìn)入平安時(shí)代后日本“國(guó)風(fēng)化”漸盛。從仁明天皇開始到平安中期(10世紀(jì)中葉)的樂制改革,根據(jù)日本人的審美意識(shí)并結(jié)合日本固有的樂舞,將外來的樂舞改造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樂舞,推進(jìn)了唐樂日本化的進(jìn)程。
日本著名音樂家田邊尚雄認(rèn)為,“從中國(guó)傳入的隋唐音樂,多少按照日本的風(fēng)格改變了形式,縮小了規(guī)模,稱為雅樂,以后世世代代在宮廷中相傳至今”(3)田邊尚雄:《中國(guó)音樂在日本》,載《光明日?qǐng)?bào)》1956年10月12日,轉(zhuǎn)引自金秋:《古絲綢之路樂舞文化交流史》,第217頁(yè)。。中國(guó)學(xué)者金秋曾簡(jiǎn)要?dú)w納了《秦王破陣樂》東傳日本后發(fā)生的幾個(gè)變化:第一是演員人數(shù)銳減為4-6人;第二是舞樂調(diào)式由“大食調(diào)”變?yōu)椤耙荚秸{(diào)”;第三是演化出了“六策上將樂”“齊王破陣樂”“大定太平樂”等別名;第四是舞容改變;第五是舞者加上了面具[16]229。除了上述幾點(diǎn)外,對(duì)比日本《樂曲考》對(duì)《秦王破陣樂》演出盛況的記載,可見傳入日本后的《秦王破陣樂》在表演形式上也發(fā)生了變化。日本《樂曲考》載,《秦王破陣樂》詞曲表演時(shí)舞者128人,全部披甲持戟進(jìn)行舞蹈,隊(duì)伍隨著音樂節(jié)奏共變化三次,每次換成四種陣勢(shì),舞者持戟來往疾呼擊刺[17]2-3。但傳入日本后,《秦王破陣樂》人數(shù)銳減為4-6人,且舞容后來被吸收進(jìn)了《太平樂》之中。由于演出人員及規(guī)模的限制,“左圓右方”的舞蹈隊(duì)形和“先偏后伍”(古陣法: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的隊(duì)形變化也是無法實(shí)現(xiàn)的,也很難有如唐《秦王破陣樂》“觀者見其抑揚(yáng)蹈厲,莫不扼腕踴躍,凜然震竦”般震撼人心的演出效果。由此可知,日本的樂舞雖直接學(xué)習(xí)唐舞,但因地狹人稀、空間限制和人才缺乏,即使在日本宮廷也很難達(dá)到和中國(guó)唐朝一樣的陣勢(shì)規(guī)模,而形成一種“縮小版”的樂舞。除此之外在中日文化交流之前日本已形成了自身民族性格和歷史文化背景,受到日本人審美心理和對(duì)異文化接受程度的影響,必然會(huì)在學(xué)習(xí)外來文化的基礎(chǔ)上選擇性吸收并有所加工再創(chuàng)造,使之符合日本民族的審美,并與其文化符號(hào)體系相適應(yīng)。再者,作為一種身體文化,舞蹈表演是歷史文化的藝術(shù)加工的同時(shí)也是舞者情感的藝術(shù)表達(dá),很難始終保持一種固定的范式,因而勢(shì)必會(huì)隨著時(shí)間的流動(dòng)以及主體客體的變化而產(chǎn)生一定的衍變。
四、結(jié)語(yǔ)
在日本飛鳥時(shí)代后期便有了早期唐樂舞的東傳,到了奈良時(shí)代日本大量學(xué)習(xí)吸收以唐樂為主的外來樂舞,至平安時(shí)代在消化吸收外來樂舞的同時(shí)進(jìn)行本土化的加工創(chuàng)造,孕育了日本的樂舞文化。可以說,在古代日本樂舞是在直接借鑒唐樂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發(fā)展的,并在接納的基礎(chǔ)上發(fā)生了些許變化。唐《秦王破陣樂》在日本的傳播及衍變不僅是唐樂高度繁榮的體現(xiàn),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gè)縮影,其傳入日本后有了多種別稱,且規(guī)模縮小、人數(shù)減少、隊(duì)形簡(jiǎn)化,形成了“縮小版”的《秦王破陣樂》,而其舞容的變化則體現(xiàn)出日本的審美選擇和本土創(chuàng)造。
(指導(dǎo)老師:周海建,中央民族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guó)文化史和中外關(guān)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