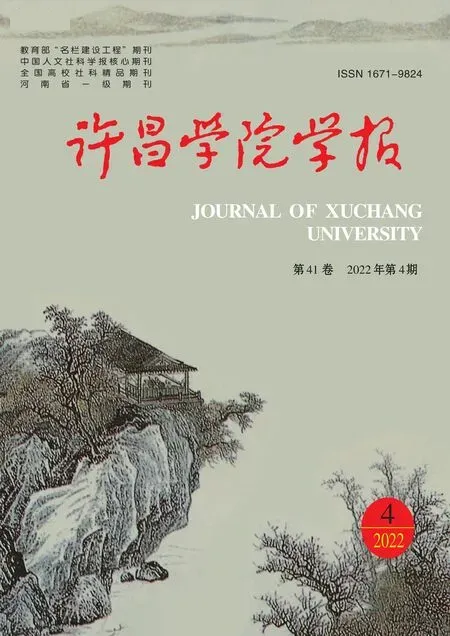鐘嶸為何置惠休于下品
倪 緣
(安徽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安徽 蕪湖 241002)
《詩品》研究者眾,但對“齊惠休上人”條的研究卻甚少,可能是現(xiàn)存文獻(xiàn)較少的原因。然惠休卻是《詩品》研究乃至齊梁文學(xué)研究極為重要的一環(huán)。《詩品》中提及惠休者共有四處:中品“宋光祿大夫顏延之”條:“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cuò)彩鏤金。’顏終身病之。”[1]351下品“齊惠休上人”條:“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1]560下品“齊黃門謝超宗……齊秀才顧則心”條:“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dòng)俗。’”[1]575下品“晉參軍毛伯成……齊朝請?jiān)S瑤之”條:“湯休謂遠(yuǎn)云:‘吾詩可為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為庶兄。’”[1]585
在劉宋詩壇上,惠休與鮑照齊名,但為何鐘嶸將鮑照置于中品,而反常地將惠休置于下品呢?以鐘嶸對惠休的評語來看,詩情淫靡似乎是其詩被置于下品的原因。但問題在于,同樣是抒發(fā)閨怨,為何秦嘉、江淹等人的品第卻高于惠休呢?
一、問題的提出
惠休在當(dāng)時(shí)影響頗大。作為詩僧,他與當(dāng)時(shí)文人有著廣泛的交游。《宋書·徐湛之傳》記:“時(shí)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艷,湛之與之甚厚。”[2]1847除徐湛之外,鮑照、吳邁遠(yuǎn)和謝超宗等人也與惠休有所來往,如鮑照詩集中存《秋日示休上人》《答休上人》等,而惠休也現(xiàn)存《贈(zèng)鮑侍郎》詩一首。《南齊書》記:“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咸亦標(biāo)世。”[3]908鐘嶸在《詩品》中亦言:“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dòng)俗。”[1]575可見在劉宋詩壇上,惠休與鮑照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影響幾乎是并立的。
唐釋懷信《釋門自鏡錄》載:“慧休,字茂遠(yuǎn),俗姓湯,住長干寺。流宕倜儻,嗜酒好色,輕釋侶,慕俗意。秉筆造牘,文辭斐然,非直黑衣吞音,亦是世上杜口。于是名譽(yù)頓上,才鋒挺出。清艷之美,有逾古歌,流轉(zhuǎn)入東,皆良詠紙貴,賞嘆絕倫。自以微賤,不欲罷道。當(dāng)時(shí)有清賢勝流,皆共賞愛之。至宋世祖孝武,始敕令還俗,補(bǔ)揚(yáng)州文學(xué)從事。意氣既高,甚有慚愧。會(huì)出補(bǔ)勾容令,不得意而卒。”[4]809通過這段記載可知,惠休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極受歡迎,一時(shí)造成“洛陽紙貴”的現(xiàn)象。江淹也曾擬五言詩《休上人怨別》,模仿惠休的五言詩創(chuàng)作,而同為其擬詩對象的還有曹植、阮籍、謝靈運(yùn)等文壇翹楚。可見,在江淹看來,惠休也可稱為創(chuàng)作怨別詩的代表。
朱右道:“予嘗觀晉唐來高僧,以詩名者概不少也。若支遁之沖淡,惠休之高明,貫休、齊己之清麗,靈徹、皎然之潔峻,道標(biāo)、無本之超絕,惠勤、道潛之滋腴,雖造詣不同,要適于情性,寓意深遠(yuǎn),至于今傳誦不衰。”[5]73-74惠休對后世詩人也有很大的影響,如李白“君同鮑明遠(yuǎn),邀彼休上人。鼓琴亂白雪,秋變江上春”[6]1823、白居易“道林談?wù)摶菪菰姡坏饺颂毂阕鲙煛盵6]4875、杜甫“隱居欲就廬山遠(yuǎn),麗藻初逢休上人”[6]2563等。王樹平、包得義認(rèn)為惠休與鮑照的交往在唐代甚至具有重要的文化符號意義[7]。
那么,為何鐘嶸要將惠休詩放在下品呢?鐘嶸云:“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1]560以現(xiàn)在的觀點(diǎn)來看,惠休之詩并不如鮑照,鐘嶸也確實(shí)可評惠休詩于下品,但問題在于鐘嶸對惠休的評語并不能完全解釋將后者置于下品的原因。
首先,鐘嶸認(rèn)為惠休詩歌情感淫靡。但在當(dāng)時(shí)這樣的詩人并不少,江淹、鮑照等都創(chuàng)作過這類詩歌,如江淹《征怨詩》《詠美人春游時(shí)》、鮑照《代白頭吟》《幽蘭五首》等。而江、鮑二人卻被列入中品,鐘嶸評鮑照詩道:“其源出于二張。善制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俶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jié)強(qiáng)于謝混,驅(qū)邁疾于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凐當(dāng)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diào)。”[1]381鐘嶸甚至未提及鮑照愛情閨怨類五言詩。而鐘嶸對于江淹的評價(jià)亦是如此。
惠休詩現(xiàn)存十一首:《怨詩行》、《秋思引》、《江南思》、《楊花曲》三首、《白纻歌》三首、《楚明妃曲》、《贈(zèng)鮑侍郎》。存五言詩五首,其《怨詩行》:“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滿,斷絕孤妾腸。悲風(fēng)蕩帷帳,瑤翠坐自傷。妾心依天末,思與浮云長。嘯歌視秋草,幽葉豈再揚(yáng)。暮蘭不待歲,離華能幾芳。愿作張女引,流悲繞君堂。君堂嚴(yán)且秘,絕調(diào)徒飛揚(yáng)。”[8]1243此詩源于曹植《七哀詩》,感情悲愴婉轉(zhuǎn),抒發(fā)了深閨少婦對遠(yuǎn)方丈夫的思念以及美女遲暮的悲傷。《楊花曲》其三:“深堤下生草,高城上入云。春人心生思,思心長為君。”[8]1244這首詩也表達(dá)了戀人相思之情。倘若鐘嶸認(rèn)為閨怨詩詩格較低,則不應(yīng)將秦嘉夫妻詩列入中品。可見,至少在詩歌情感表達(dá)方面,鐘嶸因惠休詩“淫靡”而置其于下品實(shí)難讓人信服。
其次,鐘嶸認(rèn)為將惠休、鮑照相提并論是因?yàn)轭佈又刀术U照而故意為之。這一觀點(diǎn)源于羊曜璠,其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1]560。羊曜璠是謝靈運(yùn)的好友,《宋書·謝靈運(yùn)傳》:“靈運(yùn)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huì),共為山澤之游,時(shí)人謂之四友。”[2]1774羊曜璠認(rèn)為顏延之心胸狹窄,妒忌鮑照的文采,因此將鮑照與惠休并立。但羊曜璠的話有兩個(gè)理解方向:一、惠休詩確不如鮑照詩;二、借此貶低顏延之的人格。
先從第一個(gè)角度來看。顏延之與惠休曾有過爭執(zhí),惠休評謝靈運(yùn)與顏延之詩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cuò)彩鏤金。”[1]351顏延之因此“終生病之”[1]351。而顏延之亦作惠休詩評:“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dāng)誤后生。’”[9]881倘若說惠休對顏延之詩的批評尚是從辭采出發(fā),那么顏延之評惠休詩則近乎毫無道理的攻擊。“委巷中歌謠”在顏延之這樣的上層文人眼中乃是俗體,詩格卑下,“作家一旦使用這種俗體進(jìn)行創(chuàng)作,那么他在這種藝術(shù)形式上的一切文學(xué)表現(xiàn),無論水平多高,也還是一種低俗的表現(xiàn),逃脫不了被歧視的命運(yùn)”[10]。鮑照對顏詩的評價(jià)與惠休語極為相似:“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yùn)優(yōu)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fā)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9]881因此,面對二人負(fù)面的評價(jià),顏延之極有可能因詩體的格調(diào)將鮑照與惠休并列,而此非關(guān)乎詩歌藝術(shù)水平的高下。再從第二個(gè)角度來看。顏延之曾與謝靈運(yùn)爭名,作為后者的好友,羊曜璠的立場顯然站在謝靈運(yùn)這邊。因此,羊曜璠所言的真實(shí)性是值得懷疑的,并不能直接證明鮑照詩優(yōu)于惠休詩。
最后,雖然在《詩品》中并未言惠休詩歌辭采方面的問題,但《宋書》記惠休“辭采綺艷”[2]1847,那么,鐘嶸是不是因此置其于下品?答案是否定的。上品之班婕妤、張協(xié),中品之張華等皆有綺麗之評,下品“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條亦言:“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1]524顯然,鐘嶸沒有將辭采綺麗作為詩歌品評等級的標(biāo)準(zhǔn)。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不論是從詩歌情感,還是從詩歌形式等方面,鐘嶸在討論惠休詩時(shí)都未能給出充足的理由將后者置于下品。
二、酒肉與入仕:惠休的身份特征
要解決這一問題,則不得不先了解惠休的特殊身份。自曇標(biāo)道人謀反之后,孝武帝意識(shí)到佛門中未必都是潛心學(xué)佛者,于是詔令:“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jì)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奸心頻發(fā),兇狀屢聞,敗亂風(fēng)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違犯,嚴(yán)加誅坐。”[2]2386-2387而惠休也在沙汰之列。釋神清《北山錄》云:“惠休為文,名冠上才。嗜酒色,無儀法(蜀僧可朋亦然,死于逆旅,而尸棄郊野)。孝武以其污沙門行,詔勒還俗,補(bǔ)揚(yáng)州文學(xué)從事,患不得志,終于句容令焉。”[11]629惠休雖為僧人,卻“嗜酒好色”[4]809,完全不守沙門戒律。但惠休被勒令還俗后,孝武帝因其文采斐然而引其入仕途,任揚(yáng)州文學(xué)從事。可見,惠休有兩重身份特征——嗜酒好色與入仕。
佛教有著嚴(yán)格的戒律。戒學(xué)被看作佛教戒定慧三學(xué)之首,戒律文獻(xiàn)也被看成三藏之一。《四十二章經(jīng)》言:“弟子去離吾數(shù)千里,意念吾戒必得道。在吾左側(cè)意在邪終不得道。”[12]724可以說,戒律的遵守與否直接關(guān)系著僧人能否實(shí)現(xiàn)解脫。雖然佛教在傳入中國后不斷轉(zhuǎn)向,但始終都保持著對戒律原則的重視。佛陀耶舍譯《四分比丘尼戒本》言:“善護(hù)于口言,自凈其志意,身莫作諸惡,此三業(yè)道凈,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13]1040只有在身、口、意三個(gè)方面止惡行善,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僧人首先就要受戒持戒,而戒有兩種,分為出世戒與世間戒。在實(shí)踐中,僧人所持的出世戒往往比世間戒嚴(yán)格得多,其基本的止持戒律有十: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對于飲酒,佛教戒律中亦有限制,如《十誦律》:“佛種種因緣訶責(zé)飲酒已,語諸比丘。……‘若比丘飲酒者,波逸提。’酒者有二種:谷酒、木酒。……若比丘取嘗,咽者亦名為飲,是謂飲酒波逸提。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14]121佛教認(rèn)為凡違反戒律飲酒且屢教不改者,不能得道。
盡管在佛教中戒律這般重要,惠休卻“嗜酒好色”。會(huì)不會(huì)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未有戒律經(jīng)文傳譯過來而致惠休對此不知情呢?據(jù)文獻(xiàn)記載,律學(xué)五論之一的《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在劉宋時(shí)期的元嘉十二年已由僧伽跋摩譯出。《高僧傳》卷三《宋建康龍光寺佛馱什傳》也記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什執(zhí)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yán)共執(zhí)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于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并行于世。”[15]96可見,至南朝已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的戒律文獻(xiàn)流傳了。
即使惠休并未接觸過這類經(jīng)論,但其對劉宋僧侶因違戒而受到處罰的事跡也應(yīng)有所耳聞。孝武帝時(shí)期,周郎進(jìn)言:“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復(fù)假精醫(yī)術(shù),托雜卜數(shù),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托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fèi)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nèi)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yán)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余則隨其蓺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jīng)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2]2100此足見當(dāng)時(shí)佛教廣泛存在各類違戒事件,嚴(yán)重者甚至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惠休活躍于僧團(tuán)和文人之間,對此肯定是知悉的。
同時(shí),惠休詩的題材主要集中在閨情方面。閨怨詩,多以情貫穿,纏綿悱惻,表現(xiàn)男女之間濃烈的愛意,往往具有強(qiáng)烈的藝術(shù)感染力。毫無疑問,創(chuàng)作這樣的作品與惠休的僧人身份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沖突。《四十二章經(jīng)》云:“佛言:人為道去情欲,當(dāng)如草見火,火來已卻。道人見愛欲,必當(dāng)遠(yuǎn)之。”[12]723佛教將男女之愛乃至由其產(chǎn)生的欲望稱為“染污愛”,而“染污愛”又會(huì)引發(fā)惡行,致人犯下惡果,造下惡業(yè)。《別譯雜阿含經(jīng)》云:“欲愛染著能生惱亂,于現(xiàn)在世,增長惡法,憂悲苦惱,由之而生;未來世中,亦復(fù)如是。”[16]392但惠休不僅沒有因創(chuàng)作閨怨詩而獲罪,反而憑此出仕。
從《北山錄》的記載來看,惠休任過揚(yáng)州文學(xué)從事與宛朐令兩個(gè)職務(wù)。作為州郡官員,文學(xué)從事主要從事文化教育,一般由明經(jīng)者擔(dān)任。劉宋孫法宗“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2]2252,因此被辟為揚(yáng)州文學(xué)從事。雷仲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yuǎn),篤志好學(xué),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wù)”[2]2292-2293,也被辟為江州從事。朱百年“頗能言理,時(shí)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2]2292-2293,揚(yáng)州亦辟其為從事。《隋書·經(jīng)籍志》記梁揚(yáng)州文學(xué)從事太史叔明撰《孝經(jīng)義》一卷[17]934。與這些人相比,惠休顯然并不具備任文學(xué)從事的基本條件。且據(jù)所見史料,惠休出生素族,無顯貴家族所依傍。因此,詩歌才華成為惠休得以入仕的原因,也為惠休貼上了不同于其他僧人的標(biāo)簽。
三、詩情與政治的交織:惠休被置下品的原因
鐘嶸評詩方法之一是知人論世,如《詩品》“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于《楚辭》。文多凄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1]106鐘嶸將李陵的詩歌與其“頹喪”的人生經(jīng)歷相結(jié)合,由此得出“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的結(jié)論。而鐘嶸對惠休“上人”的稱呼表明鐘嶸對其經(jīng)歷有基本了解。《釋氏要覽·稱謂》云:“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18]34在當(dāng)時(shí),文人對惠休亦稱“上人”,如鮑照《秋日示休上人》《答休上人》。鐘嶸面對惠休兩段截然不同的經(jīng)歷,依舊選擇以僧人的身份稱呼惠休。
鐘嶸既然注意到惠休的僧人身份,那么在品評惠休詩歌時(shí)自然會(huì)用以參考。與惠休同條的康寶月、帛道猷現(xiàn)存詩較少,康寶月存有《估客樂》二首,文辭清麗,帛道猷存《陵峰采藥觸興為詩》,描寫景色,清新自然。而其他佛教僧人所寫詩歌,如支遁《四月八日贊佛詩》《詠八日詩三首》等、慧遠(yuǎn)《廬山東陵雜詩》,皆充滿佛理而別有隱逸之氣,這與惠休詩風(fēng)形成鮮明的對比。對鐘嶸而言,優(yōu)秀的詩歌情感表達(dá)皆由直尋:“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tái)多悲風(fēng)’,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shí);‘明月照積雪’,詎出經(jīng)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bǔ)假,皆由直尋。”[1]220在這一理論指導(dǎo)下,山林僧人的詩歌似不應(yīng)該有閨怨之情。惠休詩歌毫無疑問與這一觀念相左。因此,惠休詩自屬下品,完全不能與鮑照相比。值得注意的是,鐘嶸在評惠休詩時(shí)言其“情過其才”[1]560,這里的“情”是指本不應(yīng)該屬于僧人的俗情,而所謂的“才”更沒有超過“情”。然而,惠休卻恰恰憑借詩才擔(dān)任官員。考慮到鐘嶸的政治經(jīng)歷,則不得不再從政治角度來尋找其將惠休置于下品的答案。
鐘嶸出身世家,但官位卑末,他曾上書梁武帝云:“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dāng)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yīng)在綏撫,正宜嚴(yán)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19]694鐘嶸認(rèn)為官員的任免應(yīng)該與其家族次第緊密關(guān)聯(lián),不應(yīng)當(dāng)以軍功等條件為任官標(biāo)準(zhǔn)。從鐘嶸上書梁武帝可以看出,他依然保留著強(qiáng)烈的門閥意識(shí)。梁武帝雖重視門閥,并修訂譜牒,“‘……竊以晉籍所余,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9]1462,但是他并非要重用倚靠門閥貴族,而是要溯流正本,嚴(yán)辨清濁以拉攏高族對他的支持。實(shí)際上,當(dāng)時(shí)具有實(shí)權(quán)的職位無一不是寒門把控。如《通鑒》一四五記:“霄城文侯范云卒。云盡心事上,知無不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dāng)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wèi)將軍周舍同參國政。……舍豫機(jī)密二十余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20]4529-4530此中所提及的士人,皆出身寒士。所謂“寒士”,非底層人民,而是士族中的中下層。
《魏書·蕭衍傳》:“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國家強(qiáng)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風(fēng)旨,莫敢正言。”[21]2184-2185《隋書·五行志》亦云:“時(shí)帝自以為聰明博達(dá),惡人勝己。”[17]659一方面,蕭衍自恃甚重,另一方面,鐘嶸家族在齊梁時(shí)代已經(jīng)式微。因此,鐘嶸只能忍耐內(nèi)心的矛盾,迎合皇帝。如在《詩品序》中,鐘嶸極為夸張地稱贊了梁武帝的才華:“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學(xué)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為稱首。況八纮既奄,風(fēng)靡云蒸,抱玉者聯(lián)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于胸中。諒非農(nóng)歌轅議,敢致流別。”[1]83
正如上文所言,湯惠休本是下層素族,入沙門期間行事頗為浪蕩,目無佛法,創(chuàng)作淫辭,如此違背佛家戒律的僧人卻因孝武帝賞識(shí)其才華而入仕。鐘嶸并非認(rèn)為有才的素族不能入仕,也沒有將政治勢力納入評詩的標(biāo)準(zhǔn),但問題在于惠休“情過其才”。在鐘嶸看來,惠休沒有多少詩才,不應(yīng)有的俗情卻充斥在字里行間。相比之下,惠休的人生經(jīng)歷無疑構(gòu)成了對鐘嶸遭遇的某種譏諷。因此,鐘嶸在評價(jià)惠休時(shí)或許不自覺地?fù)竭M(jìn)了個(gè)人政治情感的因素,而不是僅從詩學(xué)層面對惠休詩歌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斷。
鄔國平《梁武帝與鐘嶸〈詩品〉》詳細(xì)地談?wù)摿肆何涞蹖︾妿V《詩品》寫作的影響[22]。梁武帝在《述三教詩》中寫道:“少時(shí)學(xué)周孔,弱冠窮六經(jīng)。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中復(fù)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shù)鏤金版,真言隱上清。……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不毀惟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zhí)著性易驚。窮源無二圣,測善非三英。”[23]352雖然在詩中,梁武帝直陳自己的信仰變化,并主張將三教調(diào)劑合一,但實(shí)際上,梁武帝更偏愛佛教:“至天監(jiān)十年四月五日。(郝)騫等達(dá)于楊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掛是弓刀槊等,并作蓮華塔頭,帝由此菜蔬斷欲。”[24]389天監(jiān)元年,梁武帝派郝騫等人迎佛像。天監(jiān)十年,梁武帝與諸官徒行以迎佛像還。再如,天監(jiān)六年,范縝寫作《神滅論》,梁武帝集結(jié)諸臣對此文進(jìn)行反駁。梁武帝親自主持這些聲勢浩大的崇佛運(yùn)動(dòng),以致社會(huì)中無處不彌漫著佛香。在梁武帝崇信佛教的背景下,將負(fù)有詩名的僧人惠休放置在下品似乎有些冒險(xiǎn)。
事實(shí)上,梁武帝在崇佛的同時(shí)也對佛教進(jìn)行了規(guī)約,其中一項(xiàng)重大舉措就是倡導(dǎo)僧尼食素。在梁武帝的推動(dòng)下,中國佛教戒律開始變革,其根本目的是確保眾生佛教信仰的堅(jiān)定性和佛教團(tuán)體的純潔性。在梁代僧官體系中還增加了白衣僧正的職位,所謂白衣僧正,是指俗人管理佛門事務(wù),梁武帝甚至想要自己擔(dān)任此職務(wù)。《續(xù)高僧傳》言:“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dòng)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dá)僧正,憲綱無施于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敕主書遍令,許者署名。”[25]170-171因此,即便是梁武帝,也會(huì)厭惡惠休的所作所為,并不會(huì)因其有僧人身份而網(wǎng)開一面。更何況,南朝佛教徒魚龍混雜,甚至有人有過反叛的行為,如宋僧人曇標(biāo)與羌人高阇謀反,梁沙門僧強(qiáng)起義。在這種背景下,惠休違戒的行徑實(shí)際上成了對統(tǒng)治階級挑戰(zhàn)的象征。鐘嶸將惠休詩置于下品恰恰符合梁武帝規(guī)范僧團(tuán)的政策,并不會(huì)招致蕭衍的反感。
四、結(jié)語
在南北朝時(shí)期,惠休與鮑照齊名,然鐘嶸卻一反眾說將鮑照置于中品,將惠休置于下品,僅從鐘嶸所給的評價(jià)與解釋來看實(shí)難令人信服。鐘嶸論惠休樂府閨怨詩“淫靡”,可同寫閨怨詩的其他詩人卻鮮見被置下品。惠休雖為僧人,但其行事乖張,經(jīng)常違反佛教戒律,以致宋武帝強(qiáng)行使其還俗,后因宋武帝欣賞其才華而得以入官。鐘嶸將惠休置于下品,從詩學(xué)層面而言,在于惠休詩歌所抒發(fā)的感情并非直尋。同時(shí)在鐘嶸看來,惠休淺薄的詩才并不足以支撐他出仕。在詩情與政治兩種因素的影響下,鐘嶸將惠休放置在下品。或者此舉未為允當(dāng),但也不得不強(qiáng)調(diào)這是由于惠休身份、經(jīng)歷特殊,且并非意味著鐘嶸將詩人的出身作為評詩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