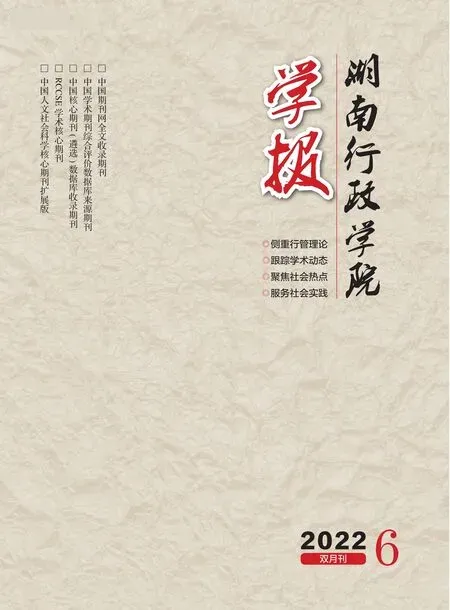數字技術支撐社會治理的邏輯機理、潛在風險及紓解路徑
李玉軒,周建鵬
(1.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閔行 200241;2.河西學院經濟管理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我國“十四五”規劃提出了建設數字中國的發展戰略,新技術革命的時代潮流和現實需要再一次催生了社會治理方式的變革。新興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場域的廣泛應用,為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數據驅動-技術嵌入-協同賦能”的運作邏輯。同時,數字化變遷也引發出不同層次的治理問題,“技術鴻溝”“信息繭房”“信息孤島”等風險因素愈加復雜。基于此,在新時期迎接數字時代,加快數字化發展,需要進一步激活數字要素,發揮數字技術潛能,深刻認識和警惕在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中的數字風險和負面效應,避免數字技術的“工具異化”,共創社會公共價值,破解制約數字治理效能提升的藩籬,為推進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一、數字技術支撐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邏輯機理
(一)數據驅動:數字經濟下數字治理的生成邏輯
21世紀以來數字化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人類社會已進入工業革命4.0時代。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使得各類經濟新形態快速成長起來,全球經濟從工業經濟進入了數字經濟時代。在這種數字技術驅動社會大變革的趨勢下,各類新潮數字技術紛紛涌現,覆蓋經濟產業、社會活動、政府治理等諸多領域,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變革,并引起一系列社會變遷和社會治理轉型。基于大數據的數字技術,引發經濟社會活動中各類資源、要素、內容的升級轉化[1],數據成為了最有價值的生產資料和要素。在此情境下,大數據作為一種有效治理資源,提供了全面升級社會治理能力的契機,驅動治理體系、治理結構、治理績效、治理形態的革新。
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號召最大限度激發科學技術生產力。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國家和地方先后出臺一系列大數據戰略發展規劃,北京、上海、廣東、貴州等地相繼成立一批大數據管理機構,開發政務數據平臺。新興數字技術應用逐漸發揮基礎性支撐作用,擴展至整個社會治理體系,包括政府部門、企業、社會組織在內的治理主體數字化建設水平得以顯著提升,極大地強化了國家和社會的宏觀數據治理能力。隨著數據量指數級增長,大數據驅動下的社會治理變革實質上是治理模式的更迭,大數據的“多維度”與社會治理的“多主體”、大數據的“全樣本”與社會治理的“科學性”、大數據的“去中心化”與社會治理的“整體性”等屬性相契合,兩者互動交融,有了高度的目標一致性,拓展了政府、社會與公眾之間的溝通渠道,大量數據成為國家和政府了解現實社會、制定公共政策的信息來源。大數據驅動的社會治理趨于高效化、精準化、多元化,成為了我國社會治理場域的時代特點和發展趨勢。
(二)技術嵌入:數字生態下平臺治理的連接邏輯
新發展理念下的數字生態包含了數字理念、數字技術、數字治理、數字安全、數字發展等主要內容,其中數字技術的創新和迭代,內嵌于推進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系統性進程中[2]。營造良好的數字生態環境,有助于發揮和拓展數字技術的創新活力和發展空間,進一步創新優化治理格局。而數字技術嵌入社會治理場域的主要途徑之一就是聚合社會資源,發揮技術優勢,構建一體化服務的平臺治理網絡。
在大數據技術加持下,各類平臺架構成為數字生態中的核心部件,平臺治理作為一項新的數字化治理模式,成為了技術治理在數字時代的新產物。日益勃興的互聯網平臺企業依托掌握的海量數據、先進技術和信息渠道,形成了影響經濟社會的作用機制和話語優勢。基于數字技術的互聯網平臺具有數字化、互動性、感知性、跨界性等屬性特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等多元行動者均可參與治理過程。在各地興起的“一網通管”“跨省通辦”等“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顯現出數據平臺集約化、高效化的治理優勢。數字時代下平臺治理基于獲取全面、可讀取、可計算的海量數據支持,打通部門行業之間的信息盲點,將實時數據與歷史大數據進行云上分析和挖掘,精確匹配社會資源,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數字技術為平臺治理開拓了新的場域空間,技術的嵌入為數字化轉型實現了治理流程再造,豐富拓展了數字技術在數字政府、數字鄉村、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想象空間和發展路徑。
(三)協同賦能:數字革命下政府治理的運行邏輯
隨著數字技術與政府治理的互動融合,現代政府在大數據時代下的職能結構、運行機制、價值理念等領域都面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考驗。數字政府治理形態在治理理念、治理技術、治理主體、治理對象、治理過程等維度,需要進行全面變革。2022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以數字化改革促進制度創新,實現政府治理方式變革和治理能力提升。鑒于此,深入推動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已成為新時代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數字技術推動政府管理和服務模式創新,平臺支撐和技術應用在其中起了關鍵的基礎性作用。數字化技術的嵌入賦予了政府治理結構扁平化、協作性、整體性的運行形態,在治理過程中實現多主體的“跨界”協作,央地政府之間的跨級合作,政府部門不同系統的跨部門合作,增進了“政府-市場-企業-社會-公眾”五維立體協同,打破了傳統科層制縱向控制的行政壁壘,促進跨部門數據共享與業務協同,提高治理精準程度和公共服務供給,協同提升社會治理效能。例如浙江、上海等地借助全面數字化轉型戰略機遇,以“放管服”為抓手,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堅持全方位賦能,打造升級“一網通辦”在線政務服務平臺,統籌推進城市經濟、生活、治理全面數字化轉型。
二、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中的潛在風險與問題剖析
(一)數據依賴:治理機制下的“技術鴻溝”
新興數字技術的全球化擴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生產力增長、提供就業機會和改善公共服務等“數字紅利”,人們愈發依賴數字技術產品,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有意或無意“接入”數字生活。作為社會治理體系中的科技支撐以及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實踐工具[3],數字技術的進步與社會互動的實際需求或適應、或脫節,存在著結構性差異。一方面,數字技術已成為提升治理效能的創新工具,提供了數據的開放、共享和應用,促進了治理理念、模式的轉變,增進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和價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過度信賴數字技術,過度收集數據信息不僅威脅著個人信息和隱私安全,而且把數據分析結果作為判斷是非、實施政策的依據,恐將為社會治理帶來數字威權的治理風險。數字技術異化產生的“數字利維坦”傾向,直接揭示了技術力量嵌入社會治理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風險。進言之,數字技術推動著社會資源和公共利益的再分配,不僅社會成員的力量對比發生轉變,而且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再次重塑。因人們掌握數字技術能力和程度的不對等、不協調,事實上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技術鴻溝”。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社會階層之間的差異,可能進一步激化身份焦慮、貧富差距等社會矛盾,在社會心理、網絡空間、弱勢群體等領域引發社會分裂,國家的政治安全和社會秩序規范也面臨新的考驗。
(二)數據陷阱:社會交往下的“信息繭房”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數字化網絡環境下社交媒體迅猛發展,互聯網平臺為吸引社會注意力以實現流量的資本變現,不斷升級優化人工智能、算法技術,抓取個體信息和行為偏好進行個性化傳播,使得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信息傳播交流從信息匱乏向信息過量轉變,從“同質化”向“個性化”轉變。由于自身信息需求的偏倚,人們容易陷入以自我為中心的相對封閉和窄化的擬態環境,導致“信息繭房”現象的出現。這種以點擊率、瀏覽量、關注度為特征的分眾化、精準化的傳播策略,會限制人們接觸信息內容的多樣性,有損開放性視野和有序的公共領域,存在擴散社會不確定因素、破壞社會治理秩序的風險。[4]在此背景下數字化轉型帶來的社會治理顯然面臨新的挑戰。其一,“信息繭房”中的社會成員在社交平臺、網絡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中獲取符合個人喜好的、封閉有限的碎片化信息,進一步導致人們觀點和立場的固化;其二,“信息繭房”深刻影響信息接收者與傳播者之間的互動。各類信息交互平臺隱藏的權威效應暗示借助網絡輿論不斷擴散,引發不同觀念、立場之間群體的對抗與博弈,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造成沖擊;其三,“信息繭房”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社會鴻溝,造成個人認知的片面,侵占其它社群的網絡空間,破壞網絡社會共同體意識的治理生態。
(三)數據壁壘:公共服務下的“信息孤島”
在社會治理場域中數字政府治理強調以需求為導向,依托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創新社會公共服務,為滿足社會公眾需求提供多元化的數字產品服務。而數字技術產業的飛速發展和政務活動的多樣性導致了數字政府治理的復雜性,對政府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要求和標準更加苛刻和多元。各級政府機構雖然掌握大量信息資源,但是受局域網、區域性等客觀因素的影響,加之部門利益存在沖突,同時缺失共享機制和技術標準,我國數字政府建設還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數據壁壘,“信息孤島”的現象還很突出。其現實表征具體體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受我國社會治理條塊關系的影響,各級政府社會公共服務出現“縱強橫弱”現象,縱向有著很強的系統性和嚴密性,但橫向互聯互通、信息共享還存在著斷點和難點;二是我國相當多基層政府遠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數字治理模式,網站媒體更多是信息展示的窗口,貼近公眾社會生活、優化營商環境、服務企業發展的意識和效果還存在差距;三是數字化轉型仍側重于管理、著眼于控制,建設和開發政務數據平臺是一時之景,存在重復建設和數據“打架”。四是在城鄉建設、社會治理、社區服務等方面,以用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缺失,用戶訪問、獲取信息、在線辦事和公眾參與的功能性服務體驗不盡人意。打通數據壁壘并非一朝一夕,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還需要更高效的政策供給,以完善數據共享通道、推動解決數據要素合理流動的堵點、難點和痛點,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人民群眾的真實問題,充分釋放數字化紅利。
三、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創新的整體性治理路徑
推動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時代重任。建設數字中國迫切需要社會治理體系進一步轉型升級。現階段國家和社會場域中數字技術、數字社會、數字經濟、數字政府的實踐與革新,進一步推動了數字治理理論和實踐的成熟和完善。數字化時代,新興數字技術支撐和賦能社會治理現代化創新,在客觀上貼合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展邏輯,朝向基礎性、系統性、綜合性方向演進。數字化轉型意義重大,有必要從整體性、協同性和全局性的角度深入探究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創新。
(一)主體層面:營造數字治理共同體
作為與數字時代相適應的治理模式,數字治理并非簡單的技術嵌入,而是意味著多元合作治理行動的開始。營造數字治理共同體的實踐基礎在于政府、市場、企業、社會組織、公眾等多元主體的互動,主張多元參與者的整體性聯動,尋求破解社會治理問題的整體性方案。從治理目標看,現代社會治理致力于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設數字治理共同體有助于提升治理主體的地位,落實治理主體責任。從行政權力看,數字治理共同體超脫于單純行政權力主導,轉向激發公眾參與治理的活力和信心,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體現出人民群眾的意志。從社會資本看,數字治理共同體有助于強化資源的有效配置,防止數字資本的無序擴張,抵御未知的技術風險和安全隱患。隨著數字技術持續嵌入和融進社會治理,數字技術與社會治理共同體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為營造數字治理共同體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現實可行性。其一,數字技術面向社會群體進行“技術賦能”與“技術賦權”,前者強調新技術的賦能作用,后者則是賦權社會主體以提升其參與治理的能力,兩者共同重塑了社會治理參與主體的角色和價值。其二,實現數字治理權責邊界的重新配置和清晰化,鞏固了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相互融通依存的關系,多元主體以責任分擔與風險共擔為準則,更加負責有效地參與社會治理過程。其三,以共同體形式尋求具有共識性的治理方案,調和多元主體間不同利益訴求、社會資源、活動策略和遠景目標上的差異,提升共同體的內部協作能力。其四,形成數字社會治理紅利“人人共享”機制,打造開放式合作共享模式,激勵共同體成員參與的積極性。
(二)價值層面:共創社會公共價值
數字經濟時代,為了回應社會公眾多樣化需求,需要從社會公共價值創造的視角審視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作為社會治理愿景的關鍵目標,公共價值的實現日益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倡導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公共價值,目的在于更好地促進數字創新與公共治理的有效融合,在公共服務供給領域拓展公共價值。數字化創新的價值生成路徑遵循的是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公共服務,提供具有創新性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提高治理效能,增進民生福祉。首先,政府作為以服務為導向的公共價值生產者,回應數字時代的新型公共需求是數字政府的首要職責[5]。數字技術驅動政府治理形態的結構性重組與功能性轉變,打破以往傳統的治理邊界,實現社會公共服務的“網上辦、掌上辦、指尖辦、碼上辦”,精簡流程服務公眾的“一網通辦”“最多跑一次”改革構建了新型的社會互動關系,打通了聯系和服務社會公眾“最后一公里”,共同促進了社會公共價值的增益和提高。其次,社會治理以協同共治為原則,以滿足人民群眾需求和提升其獲得感、幸福感為價值導向。數字社會盡管引起了社會形態演變和結構分化,但在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中也實現了對公共價值的整合與重塑。最后,數字技術為公眾提供了高效便捷以及個性化的公共服務,增強了服務滿意度,公眾對數字技術促進社會和諧善治給予了高度信賴和積極回應。“互聯網+”的一站式數字信息網絡或服務平臺,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重心的下移,更好地加強了政民互動、保障了公眾權益、增進了社會信任。
(三)制度層面:統籌頂層設計改革
我國積極回應經濟社會全面數字化轉型的時代要求,持續加快推進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和智慧社會的建設。為了系統推進數字治理,需要做好頂層設計,謀劃數字治理的長遠發展。在戰略舉措上,國家出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和《“十四五”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發展規劃》,積極主導或參與國際數字領域的標準和規則的制定,盡早解決“卡脖子”問題,掌握和贏得數字技術領域更大的主動權和自主權。在治理體制上,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數字治理領域的法律法規,引導規范國家和社會數字化轉型朝著健康和諧有序方向發展。《國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先后出臺,鋪就了數字治理的制度基石,但還需積累經驗、彌補缺陷,進一步探索國家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標準規范、行業自律等制度的完善。在機構設置上,需要建立一個獨立完整的國家大數據管理機構以進行統籌管理[6]。這一機構由立法機關授權成立,作為行政體系的一部分,接受法律監督和政治監督,維護國家安全、政治安全和數據安全,確保國家和公眾利益不受侵犯。在治理模式上,深入推進政府治理流程再造,構建政府精準治理、社會整體聯動、數據扁平高效的治理結構,提升政府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治理能力,助推形成適應數字時代發展的治理體系。
(四)機制層面:賦能數字治理創新
數字技術已經成為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驅動力,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變革了國家和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為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科技支撐。為了激活和釋放數字技術賦能治理現代化的驅動力,需要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發力。在宏觀上,需著眼于建立完善數據驅動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規劃,完善“政企產學研”多主體協同參與機制,實現跨部門之間聯動協調,建立數據交換、信息共享機制,進行重大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研發攻關,有效推動數字化技術賦能社會治理創新。在微觀上,需要加強以下三個方面的機制建設。一是加強公共數據開放共享。擴大公共基礎信息數據的安全有序開放,將公共數據服務納入公共服務體系,推進數據信息跨層級、跨地區、跨部門融合匯聚和深度應用,提升公共數據共享交換平臺的運用效能。二是推動政務信息化共建共用。深化基礎數據庫應用,系統整合政務信息,健全政務信息化項目清單,在法治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公共安全、市場監管、環境保護等領域布局重大信息系統,統籌推進數字基礎設施、技術平臺、數據中心、應用服務系統建設,構建共建共用的一體化大平臺體系。三是提高數字化政務服務效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服務宗旨,以數字化轉型為契機,以數字技術融合應用為抓手,加快政務服務科學化、協同化、智能化建設,不斷完善以數據賦能、協同治理、智慧決策、優質服務為主要特征的政務服務體系,不斷提升政務服務供給能力和水平。
四、結語與展望
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創新驅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為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基礎條件,也為國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時代命題。提升數字社會治理能力既是對數字技術全面融入社會實踐新趨勢的適應,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應有之義,更是建設數字中國的必然要求。在數字時代,關于社會治理數字化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不斷走向縱深,破解阻礙社會治理現代化發展的瓶頸與挑戰勢在必行。數字技術帶來深層次變革,催動著數字政府與數字治理在多學科領域交叉融合,這要求我們思考如何把握機遇做好前瞻布局,不斷豐富治理手段以妥善應對挑戰,加快完善數字技術賦能治理現代化的體制機制。面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要贏得數字競爭,還需抓好國家戰略布局、做好全局性謀劃,為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提供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