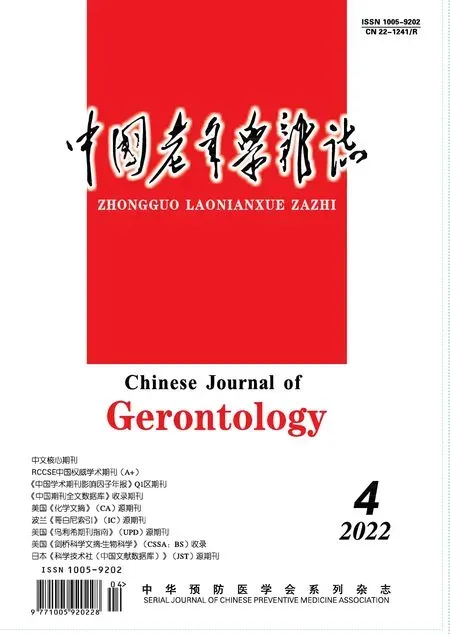老年Graves病合并甲狀腺功能亢進性心臟病患者肝功能與心功能的相關性
徐怡 彭松夏 秦麗 孫殿靜 耿建林 劉晴晴 孫霞
(衡水市人民醫院內分泌科,河北 衡水 053000)
Graves病是一種臨床常見的器官特異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又稱為毒性彌漫性甲狀腺腫,人群發病率為(20~30)/1 000 000〔1〕,女性患者多于男性,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2〕。Graves病是引起甲狀腺功能亢進(甲亢)的最常見原因,占全部甲亢病因的80%〔3〕,甲亢性心臟病(HHD)、甲狀腺危象、粒細胞缺乏癥合并感染、多器官衰竭、腦梗死、腸系膜動脈栓塞伴腸壞死、感染性休克等均可導致Graves病患者死亡,其中,HHD是主要致死原因〔4〕。雖然Graves病的高發年齡是30~60歲,但Graves病患者的HHD發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增高,高齡、病程長、Graves病均為HHD發病的危險因素〔5〕,老年Graves病患者是HHD發病的高危人群,做好HHD的預防、診斷和治療工作是改善老年Graves病患者預后的重要環節之一。甲亢性肝損傷也是Graves病相關性甲亢的重要并發癥之一〔6〕,盡管Graves病患者肝功能損害與HHD可能具有相似的病理機制,但其是否與HHD的發生、發展及患者的心功能損害具有相關性,這仍然是一項廣受爭議的課題。本文針對老年Graves病合并HHD患者肝功能與心功能的相關性進行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收集2017年1月至2020年10月衡水市人民醫院收治的60例老年Graves病合并HHD患者為A組,同期60例單純老年Graves病患者為B組,同期60名老年健康體檢者為對照組。3組均簽署知情同意書自愿參與本研究,研究方案符合《赫爾辛基宣言》的要求。
1.1.1納入標準 3組年齡均大于60歲,Graves病的診斷依據歐洲甲狀腺協會(ETA)制訂的《Graves病相關甲狀腺亢進管理指南》〔7〕,具體診斷標準為:患者具有甲亢的臨床癥狀和體征,可伴有眼球突出、浸潤性眼征、頸前黏液性水腫等,多數病例甲狀腺觸診和B超檢查可見甲狀腺彌漫性腫大,實驗室檢查結果顯示甲狀腺激素水平升高、促甲狀腺激素(TSH)水平降低,可伴有促甲狀腺激素受體抗體、甲狀腺刺激抗體陽性。HHD的診斷依據美國紐約心臟病協會(NYHA)制訂的HHD診斷標準〔8〕,具體診斷標準為:在確診甲亢基礎上同時伴有1項或以上的心律失常或心臟器質病變,除外其他病因所致心臟疾病,經針對甲亢正規治療后心臟癥狀消失或明顯減輕。對照組均經臨床檢查排除甲狀腺疾病,所有研究對象臨床資料完整,A組和B組均為初診初治病例,入院均接受常規檢查。
1.1.2排除標準 合并心腦血管意外、原發性肝腎功能不全、原發性心律失常或心臟器質性病變、惡性腫瘤、惡性貧血、嚴重急慢性感染、具有心臟手術史的患者;入院時合并Graves病外自身免疫疾病;入院前已接受抗心臟病治療的患者。
1.2觀察指標 3組年齡、性別構成、合并基礎疾病等一般資料及甲狀腺功能、肝功能指標。甲狀腺功能指標包括血清總三碘甲狀腺原氨酸(TT3)、總甲狀腺素(TT4)、游離三碘甲狀腺原氨酸(FT3)、游離甲狀腺素(FT4)和TSH,肝功能指標包括血清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γ-谷酰胺轉肽酶(γ-GT)、總膽紅素(TBIL)、堿性磷酸酶(ALP)。心功能指標包括血清乳酸脫氫酶(LDH)、α-羥丁酸脫氫酶(α-HBD)、肌酸激酶(CK)同工酶(MB)及CK,同時對A組心功能進行評價。
1.3統計方法 采用SPSS18.0軟件,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法),兩兩比較采用最小顯著差異法(LSD法),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相關性采用Pearson直線相關分析和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
2 結 果
2.13組一般資料、甲狀腺功能、肝功能指標的比較 3組年齡、性別構成、合并基礎疾病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甲狀腺功能、肝功能指標均有統計學差異(P<0.05),其中,A組或B組血清TT3、TT4、FT3、FT4及肝功能指標水平均顯著高于對照組,而血清TSH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A組血清FT4水平和肝功能指標水平均顯著高于B組(P<0.05)。A組與B組血清TT3、TT4、FT3、TSH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3組心肌酶指標的比較 3組血清LDH、α-HBD、CK-MB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A組上述指標顯著高于B組或對照組(P<0.05),而B組與對照組上述指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3組血清CK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老年Graves病合并HHD患者肝功能與心功能的相關性 A組心功能Ⅱ級33例(55%)、Ⅲ級18例(30%)、Ⅳ級9例(15%)。剔除B組和對照組數據后,A組肝功能指標與血清LDH、α-HBD、CK-MB水平及心功能分級呈正相關(P<0.05),與血清CK水平不相關(P>0.05)。見表3。

表3 老年Graves病合并HHD患者肝功能與心功能的相關性(r/P值)
3 討 論
HHD在甲亢患者中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和一定的致死率,相關統計數據顯示,甲亢患者中的HHD發病率為10%~15%〔9〕,以心房顫動為主要表現,可出現心腔擴大、瓣膜關閉不全、室間隔或左室壁增厚、節段性運動障礙、收縮功能減弱等心臟結構和功能異常,可合并肺動脈高壓,嚴重者可導致心力衰竭〔10〕。而在老年HHD患者中,甲亢癥狀不典型病例占比較高,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存在心力衰竭的表現,因此,對于具有原因不明的心律失常、心臟擴大、心力衰竭等表現的老年患者,應盡早檢查其甲狀腺功能,減少HHD的誤診和漏診。一般來說,在甲亢得到控制后,HHD患者心臟病變可得到明顯改善甚至消失,故早期的學術觀點〔11〕認為,HHD的發生源于過量表達的甲狀腺激素對心臟的直接毒性,其主要機制包括:①高水平甲狀腺激素導致心率增快、房室傳導時間和心房不應期縮短,從而引發心動房顫等心律失常;②高水平甲狀腺激素導致心肌收縮力和心臟循環血量上升,從而增了心臟容量負荷,導致以左室增厚和擴大為主要特征的心臟擴大;③高水平甲狀腺激素導致心肌代謝過度消耗、心排出量增加,引起高排出量心力衰竭。學者們發現,HHD的發生和進展并不與甲狀腺激素水平完全正相關〔12〕,即使是甲狀腺激素的微小變化也會導致相應的心臟反應,HHD會發生在一些亞臨床型甲亢患者,當血清FT3和FT4水平正常但TSH受抑制時,患者即可表現為心臟損害,甚至部分患者以HHD為首發癥狀〔13〕,而且不同特征甲亢患者HHD發病風險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影響因素〔14〕,這些提示HHD病理機制可能不局限于甲狀腺激素對心臟的直接作用。因此,尋找甲狀腺激素外的新型指標用于HHD病情評價和預后預測具有重要臨床意義。
本研究提示,老年Graves病合并HHD患者肝功能狀態可能與心功能密切相關,其肝功能指標可用于評價疾病程度。從本質上說,Graves病是以甲狀腺為特異性損害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甲狀腺濾泡上皮細胞增生、甲狀腺激素表達上調等甲亢表現是其主要臨床特征,但Graves病合并HHD可進一步導致多器官功能損害,其中肝功能障礙比較常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其發病率為20%~40%〔15〕,有的報道稱其發病率可高達80%〔16〕。甲亢合并肝損害的類型比較多樣,包括了甲亢性肝損害、抗甲狀腺藥物相關肝臟不良反應、甲亢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病、甲亢合并病毒性肝炎等,對于初發Graves病來說,當出現肝臟形態結構改變和肝功能異常時即可診斷為甲亢性肝損害,如未能及時干預治療,肝損害可從輕度肝功能不全進展至中心性肝缺血〔17〕。而Graves病合并HHD患者肝損害與心功能相關,其主要機制可能是:Graves病肝功能損害與患者機體的體液和細胞免疫功能有關,與無肝損害患者相比較,Graves病合并肝損害患者表現為更加嚴重的自身免疫過激狀態,其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紊亂程度和血清免疫球蛋白、甲狀腺自身抗體、免疫復合物、補體水平較高〔18〕,患者機體存在白細胞介素-23/輔助性T細胞17軸、腫瘤壞死因子-α蛋白等炎癥通路的紊亂〔19〕,而這些自身免疫炎癥損害可能通過誘導心肌肥大、心肌細胞結構改變、心肌間質纖維化、心房和肺靜脈交感神經增生等機制促進Graves病患者HHD發生和進展〔20〕。但是,其確切機制仍需要進一步的基礎醫學研究予以證實。
綜上,合并HHD的老年Graves病患者表現為更加嚴重的肝功能損害,其肝功能指標與心功能損害程度具有相關性,臨床醫生應對此類患者的肝功能狀態給予高度關注,從而對患者的疾病程度進行全面評價和預測、及時采取治療干預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