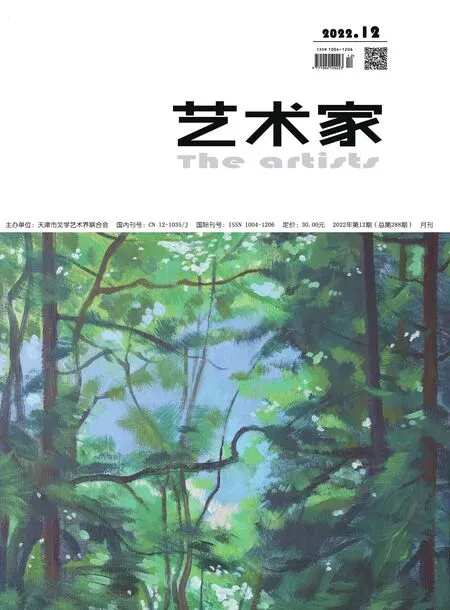救亡與審美的融通
——倪貽德戰時現代藝術觀的轉型
□石凱雪
倪貽德是20 世紀中國現代藝術的重要傳播者和實踐者,在藝術理論和繪畫實踐的探索均代表了20 世紀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前沿。民族危亡時刻,崇尚個性獨創的現代藝術遇到社會變革時它是以何種形式存在?現代洋畫家又如何平衡創作獨立與抗戰宣傳?從倪貽德的藝術軌跡中可窺得一斑。倪氏在不同社會環境下對現代藝術都有深刻的洞見,他用自己獨到的藝術思考與創作努力將審美與救亡融合,在保留了藝術家相對的自由度的同時,又積極與社會主流對話,創作出一系列抗戰主題的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品。本文通過對倪貽德于抗戰前后的理論文章和繪畫作品的梳理,力求對倪貽德先生現代藝術價值觀的轉變進行探究。
一、抗戰前
(一)創造社時期——個性自由的文學書寫
倪貽德出生于1901 年,18 歲考入上海圖畫美術院,思想上受崇尚個性、提倡創造的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繪畫上師從第一代留法畫家李超士和校長劉海粟,繪畫理論受到呂澂的啟發。1922 年畢業并留校任教于上海美專,同時加入東方藝術研究會。這時期倪氏多熱心于寫作,他模仿郁達夫筆法寫了一篇私情性小說,得到創作社的郭沫若、郁達夫和成仿吾的賞識,隨后加入了高度禮贊“個體的我”的創作社。創作社時期是倪氏文學創作的高峰期,他在創作社發表文章20 多篇,如《玄武湖之秋》《秦淮暮雨》《迷惘》等均毫不掩飾地表露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也獲得了文藝界的關注。重視個人情感的私情文學寫作經驗也使他在接受現代個人主義,以個體為中心的現代文藝價值觀時毫無心理障礙。1924 年,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創作社的幾位成員來到文化氛圍較自由的上海,成立了幻州社,倪貽德也加入了幻州社。在此期間倪貽德拋棄了針對私人情感的文學寫作,將寫作熱情轉移到對現代美術的批評,并于1927 年出版美術評論集《藝術漫談》。其中,《論裸體藝術》將當時國人對裸體模特寫生的態度分為三類:一是絕對反對的老觀念代表者;二是裸體藝術只是為風俗故事畫所做的練習;三是借裸體畫之名取媚無知青年獲利。三種人皆未了解裸體藝術的真義,倪氏認為新時代的新道德是以強烈的自我表現為主體,裸體藝術非但不與新道德沖突,反而更能取同一精神在創造的大路上前進。倪氏通過對裸體藝術從希臘時代到現代藝術的分析,對披著一身華美外衣內心腐敗的舊道德之人進行了批判。1926 年,北伐戰爭開始,不久,倪貽德便失去了在學校的教職,隨后跟隨田漢加入了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宣傳工作,不到四個月這個文藝部門就因革命局勢解散。在這段短暫的從軍經歷期間,倪貽德提出了“社會革命”與“內心革命”的論題,中心觀點是在社會革命的同時,藝術家仍需致力于人類的內心革命,保持對藝術自由表現的熱忱。
(二)留日時期——現代藝術觀的確立
倪貽德于1927 年9 月受到創造社成員成仿吾的資助到日本進行左翼理論的學習。在日期間,倪貽德在參加左翼理論學習的同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的“中國留日社會科學研究所”。1928 年,倪貽德又與友人王道源共同建立“中華留日美術研究會”,初衷是團結留日藝術家,相互交游進而為回國推進現代藝術做準備,但后來其被改名為“青年藝術家聯盟”,改名之后其將重心轉移到左翼戲劇運動,這與倪貽德與王道源的初心相差甚遠。
在日的倪貽德在藝術理論學習上受到日本美術理論家前田寬治《繪畫論——新寫實主義的要訣》與日本美術批評家外山卯三郎的物心結合的寫實性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塞尚以來關注繪畫形式的構成為核心的新寫實觀念。1930 年,倪貽德發表《新寫實的要點》,首次對新寫實主義進行了闡釋:“一切繪畫的要點有三:一,須有質感;二,須有量感;三,須有實在感。所謂質感者,便是舍去了依物的說明而表現的方法,而捕捉那根據物質的觸覺感。所謂量感,是并非依賴幾何學的澂透視學所得到的空間感和立體感,當線方面和色面一致的時候所現出來的。以上兩種條件具備了,最后便得到全體的統一感而表現出實在的感覺。”這同樣可以看出倪氏對畫面形式要素和創作者的自主性表達的強調與重視。倪貽德對繪畫本體的關照,以造型傳遞情感的追求使他的作品始終有一種淳樸且真誠的力量。
二、抗戰時期
(一)決瀾社時期——掀起現代主義浪潮
1932 年決瀾社正式成立,決瀾社同人認為藝術家的主體性與國家利益并不沖突,藝術家對主體性的追尋反映了藝術家服務國家的特殊能動性:國家必須努力建設,而建設必須有創造獨立的精神。因此,決瀾社成員對同期的客觀再現式的學院派寫實繪畫和與矯飾的月份牌繪畫極為反感,他們大多數崇尚表達個性自由及內心情感的西方現代藝術。在決瀾社宣言中,“激情”“自由”“新”“天才”等關鍵詞表達出他們對現代藝術狂飆般的熱情。盡管決瀾社成員的作品往往有著明顯的借鑒西方現代藝術的痕跡,但其對現代藝術精神堅定的信念和理想激起了現代藝術的浪潮。
決瀾社時期,倪貽德更堅定了對自由創作的追求,這段時期也是倪氏藝術思想逐漸成熟的時期。在決瀾社時期,倪貽德以《藝術旬刊》為主要陣地宣揚他的現代主義時代精神。在《現代繪畫精神論》中,倪氏提到19 世紀的繪畫,是被動地模仿眼睛看到的物象,模擬物象表面的瑣碎的細節,缺少主動的精神,因而沒有把握住繪畫的本質,是自然主義的被動模仿。而20 世紀的繪畫,是抓住對象的本質的特點,過濾掉可有可無的細節,使畫面物象單純化,更融入主觀情感加以強化、夸張,甚至對一些表象進行調整,是自我的繪畫的精神的表現,這才是真正的寫實性。在這個時期,倪貽德在創作和理論上均堅守著人本主義、自由創作的價值觀,試圖擺脫社會環境的制約,努力維護藝術的獨特性和純粹性。然而,中國的社會現實環境并沒有給現代藝術發展的空間,國難當頭,時局動亂時刻,緊跟社會革命宣傳步伐的普羅派、新興的木刻以及漫畫的崛起,使重視心靈表現的現代藝術處于尷尬之地。1935 年10 月,決瀾社在舉辦了第四次展覽之后解散。隨后在1936 年出版的《藝苑交游記》中,倪貽德記錄了一些青年藝術家的交游,談到現代主義風格的藝術作品在內容上脫離了社會大眾,審美上也并未得到大眾的認可。這樣的論述表明倪氏對現代藝術的處境有清晰的認知,同時他意識到為藝術而藝術的道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難以走通的,也預示了抗戰爆發后他對現代繪畫的新思考和新轉向。
(二)抗戰時期——現代藝術觀與壁畫的結合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倪貽德有機會到政治部第三廳的美術科擔任代理科長(原本是擬由徐悲鴻擔任)。戰時的美術科匯集了美術界各個畫種的年輕畫家,如擅長場景人物描寫的王示廓、周令釗、李可染等。在眾多畫種中木刻版畫與漫畫因其創作成本低廉、利于抗戰宣傳成為戰時畫壇的中心力量。根據倪氏自述和史料記載,作為美術科代理科長的倪貽德并沒有實際的話語權,既是崇尚現代主義價值觀的洋畫家,又是革命宣傳組織的一分子的他顯然是需要對兩種身份進行平衡的。重返軍營的倪貽德在這次經歷中對藝術與社會的聯系以及藝術用于抗戰宣傳的態度有所轉變,相較于北伐戰爭時期對“內心革命”的強調,此時的倪貽德已然無法過濾掉對現實的關注。隨后,倪氏在遍布街頭的壁畫上找到了可以平衡現代繪畫與抗戰宣傳的落腳點。1938 年武漢黃鶴樓大壁畫創作的開展成為倪貽德欲重建洋畫話語權的良機,從一開始倪貽德就十分重視此次創作,但倪氏和其小組的創作草案未能通過,最終采用受擔任美術科科長田漢指導的小組的方案。不久倪貽德因“躲避空襲”被革職。
1938 年9 月,倪貽德動身去香港,并在香港得到了繪制壁畫的機會。香港玲英中學的《抗戰》《建國》這兩幅壁畫均由倪貽德個人完成,可以說在三廳美術科的經歷并沒有影響倪貽德的壁畫創作風格,但內容上與武漢黃鶴樓大壁畫有相似之處。《抗戰》在語言風格上延續了其戰前的現代主義繪畫風格并大膽借鑒了日本、法國藝術家的風格元素,畫面風格有生硬的拼湊感,這也正是他在表達抗戰壁畫主題任務的同時又在努力探尋繪畫的個性和獨創性的首次實踐。在之后的《建國》壁畫中繪畫語言與表達主題融合得更自然與成熟。兩幅壁畫的完成體現出現代藝術在戰爭時期的獨特內涵,也給了倪貽德本人繼續探索現代藝術與抗戰主題相結合的信心。
1939 年,倪貽德在發表的文章《從戰時繪畫說到新寫實主義》中對“新寫實主義”進行了新的闡 釋:“從內容方面來說,新寫實主義所采取的不是理想的、幻想的、夸大的題材,而是實實在在現實生活的表現……”戰時版新寫實主義相較于寫實主義對內容的要求更寬泛,革命生活場景、抗戰宣傳等都可以畫,但要區別于戰爭初期內容重于技巧、感情大于理智的戰爭宣傳的繪畫作品,真實地表現社會斗爭,傳遞民族精神,鼓舞人民繼續艱苦奮斗。
(三)孤島畫室與重慶聯展——現代主義的新藝術形態
1939 年9 月,倪貽德返回上海,任教于上海美專,1940 年開辦尼特畫室,為青年藝術家提供了學習和交流的場所。重返上海的倪貽德在這段時期積極鼓勵青年藝術家對現代繪畫技巧與精神的研究學習,在1941 年舉辦的“現代繪畫展覽會”展示了上海青年藝術家的作品,倪氏也有一幅作品《大漢》參展,畫面整體上看是現代主義風格,同時注重民族精神的表達,以新寫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為出發點表達抗戰母題中的民族精神。盡管在內容表達上有隱晦的特點,但可以看出他對戰爭主題與現代繪畫的結合越來越成熟,形成一種反映民族精神的新藝術形態。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倪貽德前往重慶,其間還舉辦了個人展。倪貽德在重慶時期遇到在戰爭時期同樣堅守著融合中西,探索新藝術的藝術家,如林風眠、趙無極、丁衍鏞等。1945 年,倪貽德受邀參加“現代繪畫聯展”與“第一屆獨立美展”,兩次展覽重新引發了關于現代藝術的爭論。“并不是依樣葫蘆的西洋畫,也不是僅得了西洋美術皮毛的折衷畫,是東西美術接觸后所孕育而成的一種新的藝術”,這是當時批評家對倪貽德等藝術家在戰時繪畫創作的評價,可以說,以倪貽德為代表的現代主義畫家在經歷了抗戰民族意識形態的影響后,并未放棄對現代主義美術的探索,反而在特殊的時代環境下取得了新的發展。
可以說,抗戰時期是倪貽德藝術思想的轉折點,他不再單純地探索純藝術的世界,對社會現實的關照,救亡與審美的融通,都體現了一位現代藝術家在努力與社會和人民對話。最可貴的是,在思想上,倪貽德始終堅守著表達個人精神與情感的現代藝術價值觀,即便在戰爭時期依然保留了作為藝術家的自由度,以現代主義的繪畫方法描繪抗戰救國的內容,其在危難時刻的反應與思考與武漢“美術工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繪畫內容上,倪貽德在表現戰時人民的真實生活時,借鑒西方戰時繪畫的經驗,以一種個性化的方式表達自己理解的民族精神。在藝術理論上,倪貽德淡化了對繪畫本體和自我表現的強調,增加了對繪畫內容與表達主題的關注,以積極的態度介入社會,鼓舞人民。
倪貽德整個藝術生涯與社會變革緊密相連,他的藝術思想是中國早期現代藝術家的典型代表。橫亙其一生的現代藝術價值觀在抗戰前后雖有不同的側重點,其實是體現了倪氏在不同時期對現代藝術本質的把握程度。從抗戰前對現代繪畫純造型元素的強調到抗戰時期表現于社會人民的現實生活的題材內容;從抗戰前致力于“為藝術而藝術”的現代主義繪畫的傳播和實踐到抗戰時期將現代繪畫精神與民族精神相融合,用現代主義風格的繪畫表達抗戰主題,都可以看出身在民族危亡時刻的倪貽德努力平衡自己的藝術家和國民身份。倪貽德在抗戰勝利后在油畫民族化、素描教學改革等方面都發表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藝術本體、人格獨立和個性化表現始終是倪貽德最關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至今仍是藝術家的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