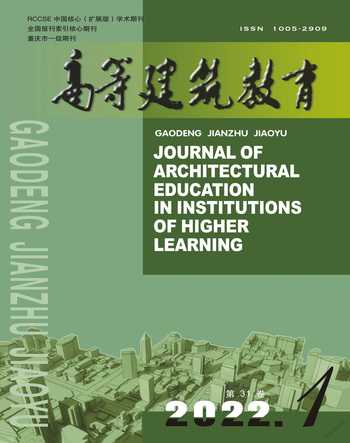土木工程專業課課堂教學中的“三結合”
陳建兵 李素貞

摘要:針對工科類專業本科教學中的若干共性問題,結合錢學森現代科學技術體系觀,在專業課教學中注重共性與具體、科學與常識、定性與定量“三結合”,即科學共性基礎與具體問題相結合、科學原理與生產生活經驗常識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基本理念,以土木工程專業荷載與結構設計原則課程教學為例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土木工程;專業課;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技術科學
中圖分類號:G642.3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5-2909(2022)01-0123-07
本科生課堂教學是本科教育的核心環節。多年以來,教育主管部門、高等院校和高校教師對本科生課程教學給予了高度重視,開展了大量教學研究工作。工科類專業的本科課程設置主要包括基礎課(公共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對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的教學研究較為深入系統,而對專業課的教學研究則相對薄弱。由于專業課種類繁多,又各具特點,對專業課課堂教學的共性問題研討尚顯薄弱。事實上,在整個本科教學體系之中,專業課程占總課程門數的60%以上,而課時則占總學時的40%,甚至50%以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工科類專業的本科專業課課堂教學共性問題的教學研討寥寥無幾。因此,以土木工程專業課課堂教學實踐為基礎,提出共性與具體、科學與常識、定性與定量“三結合”的教學理念,即在課堂教學中注重科學共性基礎與具體問題相結合、科學原理與生產生活經驗常識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
一、工科類專業本科生課程體系設置與錢學森現代科學技術體系觀
在工科本科生課程體系中,主要包括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對土木工程本科生而言,基礎課包括高等數學、普通物理學等課程,這些課程也是絕大部分工科專業學生要學習的課程。土木工程專業基礎課包括理論力學、材料力學、結構力學等課程,有些也是機械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港口、水利和海洋工程等多個學科的專業基礎課。專業課則包括荷載與結構設計、鋼結構、鋼筋混凝土結構等課程。從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到專業課,專門化程度上升、參與學習的人數逐步由整個工科到部分工科專業再縮小為土木工程專業。從專業及學習的人數來看,從下到上呈金字塔形(圖1)。從基礎課到專業課的知識實用性上升,但與此同時其適用范圍減小、邏輯性減弱。錢學森先生將現代科學技術體系劃分為11個門類,同時,在每個門類中又分為基礎科學、技術科學與工程技術3個層次[1]。不難看到,工科類專業的大學本科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的設置,與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技術3個層次的劃分具有內在一致性。
從經驗性知識到應用技術、技術科學與基礎科學的過程是從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提升和飛躍的過程[2]。與實踐經驗性知識相比,專業課知識具有一定的科學基礎與邏輯體系,但與專業基礎課和基礎課相比,專業課知識經驗性相對較強,邏輯性相對較弱。學生在大學一、二年級基本學完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建立起對現代科學邏輯嚴密性、定量精確性和體系完整性的印象,開始接觸專業課后,有邏輯體系不再、精確性“瞬間崩塌”、內容“零碎雜糅”之感,而且,似乎感覺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所學知識在專業課中的應用很少。這一強烈的反差,是造成不少本科生感覺專業課學習難以深入,對專業課學習興趣下降的重要原因。
基礎課知識是經簡化、提煉和抽象后積淀下來的邏輯嚴密的科學知識。例如,一般工科本科生在高等數學中學習的知識體系,在150年前已經基本成型,即使線性代數與概率論中的知識,也已經有80年以上的歷史[3]。數學家希爾伯特指出,經過邏輯梳理的知識體系和理論工具,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變得更為抽象,但本質上更簡單、更強大[4-5]。邏輯體系不具跳躍性,一步一個階梯,因此,學習具有邏輯體系的知識在本質上更為容易。這可能是為什么近代以來的學校教育,無論在小學、中學和大學,都以邏輯化的知識教育為第一要務的根本原因。反之,在本科專業課中學習的知識,則往往歷史相對較短,且由于實際問題的復雜性而難以對每個環節進行邏輯嚴密的科學處理,在本科課程中通常僅給出最終的簡化結果。工程實際問題總體上較零碎,跳躍性較大,邏輯體系不嚴整。事實上,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不斷從實踐經驗性知識中提取科學認識,夯實科學基礎,對應用技術、技術科學乃至基礎科學進行更新和完善[1,6],這是一個不斷發展、永無止境的動態過程。專業課相當于“技術科學”與“應用技術”的銜接,或“應用技術”為主,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專業課的相關知識得到更新和完善,與基礎課相比,其邏輯性相對較弱的基本格局也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得到根本改變。
二、本科生專業課程課堂教學的“三結合”
在本科生專業課的課堂教學中應體現共性與具體、科學與常識、定性與定量三結合的教學理念,即科學共性基礎與具體問題相結合、科學原理與生產生活經驗常識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使學生既能把握總體的邏輯體系、掌握知識要點,又能逐步學習和領會對工程實際應用和決策來說至關重要的一些基本原則。
(一)科學共性基礎與具體問題相結合
現代工程技術雖然難免具有經驗性知識與成分,有時甚至比重還較大,但是,科學共性原理在工程分析、設計與決策中占有基礎性地位[6],則是現代工程技術與以經驗為主的古代工程技術的根本性差別。因此,結合專業課中的具體知識點強調科學共性基礎與具體問題相結合的重要性,由此建立專業課不同知識點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至關重要。
以土木工程專業課荷載與可靠性設計原則為例,在風荷載和地震作用兩部分,分別介紹風的基本知識和地震基本知識,其中風的分級表和地震烈度表是重要的基本知識。事實上,人們對具體現象進行科學認識的第一步,即從感性認識邁向理性認識的第一步,往往是對紛繁蕪雜的經驗知識進行初步整理,給出合理的分類,因此,在講課中,應強調科學分類這一科學認識過程的統一性。例如,對于風級,無論是唐代科學家李淳風將風的等級根據樹木響應的情況分為“動葉、鳴條、搖枝、墮葉、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飛砂石、拔大樹和根”等八級風力標準[7],還是“蒲氏風級”中以“靜、煙直上” ,即“大漠孤煙直”景象為特征的“靜風”,或以“漁船滿帆時傾于一方” ,即“風正一帆懸”的“和風”,以及“微枝折毀”的“大風”和“陸上少見,見時可使樹木拔起或建筑物摧毀”的“狂風”等12級標準[8],在早期無法進行定量觀測的情況下,都是以人們可見可感的海洋或陸地地面物征象作為科學劃分的第一標準。類似地,在中國地震烈度表中,對于6度以下的情況,也主要以諸如“驚慌失措,倉皇逃出”等人的感受和“不穩定物翻倒”等物理現象區分。從這里,不難看到古今中外的科學家在風級和地震烈度研究科學方法上的共同之處。事實上,跨出從經驗到科學認識的這一步,即科學分類,雖然難免具有經驗性和模糊性,但卻意味著人們開始對基本現象進行系統化梳理與邏輯歸類[2],因而開始觸及科學的脈搏,乃是真正科學研究,即理性認識的開始。
又如,在介紹動水壓力和風壓力的過程中,都需要用到伯努利公式,即對于層流中的一根流線,其“動”壓強和“靜”壓強之和為常數。這一原理,從本質上解釋了動水壓力與水的密度成正比、與流速平方成正比,風壓力與空氣密度成正比、與風速(氣流速度)平方成正比這兩個事實在科學原理上的統一性。盡管在教材中[8],這一基本原理的推導是在風壓部分(在水壓力之后)進行的,但在講到動水壓力時可進行一個更為簡潔的推導。事實上,只需要兩個關鍵公式就可以解決問題:考察一維穩定層流的流線所在的微小直線流管(不是水管的管道),記橫軸方向空間坐標為x,以向右為正,微團長度為dx。設截面積為A,流體微團的速度為v。顯然,速度v和流體壓強p本質上是x和t的函數。對于穩定層流,在給定空間點的“視”速度不隨時間變化,即
v(x,t)/t=0
與此同時,該流體微團左側的壓力為p(x,t)A,右側的壓力為p(x+dx,t)A。因此,根據牛頓第二定律,有
ρAdxdv(x,t)/dt=[p(x,t)-p(x+dx,t)]A
式中,dv(x,t)/dt為流體微團的加速度,是一個全微分。這是第一個關鍵公式。從中消去A,并對右側利用一階Taylor展開,可得
ρdv(x,t)/dt+p/x=0
對于流體微團來說,其所在位置也與時間有關,即x/t=v,因此,根據全微分及鏈式法則,
dv(x,t)/dt=v(x,t)/t+vv/x
由于v(x,t)/t=0,根據牛頓第二定律所得的上述方程進一步簡化為
ρvv/x+p/x=0
這是第二個關鍵公式。由此積分即可得到ρv2/2+p=C,C為積分常數。此即著名的伯努利公式[9],這一公式對層流流體(無論氣體還是液體)均成立。在這一推導過程中,同時復習了高等數學中的全微分概念、Taylor展開和鏈式法則,從而認識到基礎課所學知識(科學共性基礎)是如何融會貫通地應用到具體工程問題中的。通過這一概念,避免了歐拉描述、拉格朗日描述、當地速度、對流影響等本科生不易理解的概念。
與此相反,雖然同為流體,但在風對結構的作用與波浪對結構作用的計算中,基本公式卻不同。在風對結構的作用中,順風向風壓是CDρav2/2,其原理來自伯努利公式,CD是一個比例系數,ρa是空氣密度。而在波浪對小直徑圓柱形物體的計算中,則可采用Morison公式
C′DDρwv|v|/2+C′accρwπD2v/4
其中,D是圓柱體直徑,C′D,C′acc為通過實驗確定的系數,ρw為水的密度。該式中第一項是黏性作用項(與速度有關),第二項是與慣性力有關的項,ρwπD2/4是單位長度圓柱體大小的水的質量,而v則是加速度。在此,聽課學生常產生的第一個問題是:同是流體,為何基本公式有別?實際上,不難發現兩式中關于黏性作用項的本質是相同的,而風壓計算中缺少慣性項,因為空氣密度很小,第二項與第一項相比可以忽略不計,二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這正是同一科學原理在不同問題中根據具體因素變化而導致的結果。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會存在慣性項?盡管可以解釋為該部分圓柱體對流體慣性效應的阻擋,但通過浮力原理加以解釋更見統一性,該項是由被圓柱體排開水體的“橫向浮力”導致的(當然需要乘以一個系數C′acc)。事實上,阿基米德浮力定律指出,浮力是被物體排開體積的液體的重力。重力是由豎直向下的重力加速度而產生的,類似地,Morison公式中的慣性項是由水平向的加速度而產生的,可以理解為與加速度共線的“橫向”浮力效應。由此,將流體的動態作用力與靜態浮力在某種意義上“統一”。
科學共性原理的統一性往往體現為科學規律(如物理或力學規律)及其數學公式表達的一致性。不少學生對數學公式表現出某種天然的畏懼。在具體講課過程中,讓學生意識到數學公式是表達科學規律的精確語言和強大工具,從而消除學生的畏懼感,增強基于科學共性原理、利用這一工具精確表達和解決具體工程問題的信心。
(二)科學原理與生產生活經驗常識相結合
在專業課中,來自生產生活經驗常識的知識較多。拘泥于生產生活經驗常識可能導致創造性的禁錮,甚至錯誤的直覺判斷。然而,科學原理與生產生活經驗常識并非總是相悖的,相反,在大部分情況下具有一致性。事實上,科學原理與生產生活經驗常識是對立統一的。人們根據生產經驗常識而對問題產生誤判的情況,一般是對基本條件的認識不清晰或對存在復雜非線性耦合效應的系統進行“線性外推”的結果[10]。例如,亞里士多德沒有認識到對輕質物體(如羽毛)來說空氣作用力不可忽略,因而得出了錯誤的落體運動規律。與基礎課教學相比,在專業課課堂教學中,科學原理與生產生活經驗常識的結合尤為重要,可幫助學生逐步建立工程直覺。
例如,在課程中,涉及樓面活荷載的取值。在規范中給出的樓面活荷載取值,是通過經驗或實際數據、采用概率統計并加以適當工程判斷的結果[11]。在這里,符合客觀實際與概率統計分析是處理這一問題的科學原則。對于活荷載的處理,有兩個要點:第一,從歷史上看,在不同時期修訂的規范中活荷載取值一般是增大的。以橋梁為例,近30年,車流密度增大,因而活荷載必然增大,這一經驗常識就是前述荷載設計取值增大的基本背景。第二,活荷載的取值依據與使用情況及物理背景有關。例如,對于普通住房的樓面活荷載,我國現行規范的取值為2.0 kN/m2。這一數值對于一般的學生來說沒有直觀概念。事實上,在一個房間的樓面上若每平方米上站3個人,每人平均體重70 kg,則其重力密度約2.0 kN/m2。上述人員布局情況雖然稍顯極端,但在家庭聚會時可能局部樓面會接近這一極端狀態,考慮到設計荷載取值一般偏大,作為設計取值標準是具有合理性的。將上述設計取值與日常經驗常識結合,有助于逐步建立工程直覺。
又如,在側壓力和地震作用部分,都涉及波動,需要介紹一些波的基本性質。但由于課時有限,不可能通過詳細的波動方程推導介紹這些基本概念。因此,結合生產生活常識直觀地說明有關概念,是學生比較容易接受的方式。首先,波動分為體波和面波,即在物體內部傳播的波和僅在表面附近存在和傳播的波。例如,海洋表面上可能驚濤駭浪,而一定深度以下則十分平靜。不僅是水面,地球表面也存在類似情形。體波又分為縱波和橫波。固體中可以傳播縱波和橫波,但靜止流體,不能承受剪應力,橫波是剪切波,不能在流體中傳播。固體中的波傳播速度比流體中的波速大。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古法以牛革為矢服,臥則以為枕。取其中虛,附地枕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就是利用了這一性質。波速又和很多因素有關,不僅在不同介質中不同,在同一介質中不同類型波的波速也不同,而且可能與波長等有關。例如,在平靜的湖面上丟入一個石頭產生的漣漪,一秒鐘只傳播數米;但1960年智利大地震引起的海嘯,以每小時800 km(約220 m/s)的速度,橫穿太平洋,24 h后襲擊了日本海岸。可見水波波速可以從每秒幾米到每秒200多米,不僅與介質的性質有關,還與波長(或頻率)有關,即存在散射現象。波浪還有淺水波和深水波的差別。淺水波的波速與水深有關,淺水波的波速為gh[12],其中,g為重力加速度,h為水深。中國古話說,“長江后浪推前浪”,正是因為波峰處的水深較大,波峰前行快于波谷,因此波浪總是向前彎折乃至破碎。明乎此,再來欣賞日本著名的浮世繪《富岳三十六景》的《神奈川沖浪里》,當有更深刻的體會。
通過上述生產生活經驗中關于波動現象的常識與物理規律加以解釋,有助于學生對相關知識的深入理解。
(三)定性與定量相結合
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是基于科學基礎、解決具體復雜工程問題的不二法門[10,13]。現代計算機技術與裝備的發展,為定量計算與分析提供了強大的工具。然而,定量計算的基礎是正確的科學理論與合理的工程模型。對定量計算結果的判斷與檢驗,隨著現代分析工具和方法的發展而愈益重要[14]。在專業課的課程教學中,關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例子俯拾皆是。
例如,前述列舉的淺水波與深水波的概念,關于“深”“淺”,是定性的區別,這是由于淺水波與深水波有一系列性質上的差別。然而,何為“深”,何為“淺”?并非簡單地根據絕對水深而論。根據波動理論,當水深小于波長的1/2時,為淺水波,否則為深水波。因此,以大海之深,可有淺水波,以池塘之淺,可載深水波。由此可見,“深、淺”水波的分類依據是水深與波長之比。類似地,對小圓柱物體,可以采用Morison公式計算波浪作用力。當物體的尺度較大時,可以采用直墻上的波浪作用方法計算。介于其間的第二類問題,則需要根據繞射理論具體分析。大體上說,海上的燈塔一般屬于第一類,海邊的防波堤一般屬于第三類,而大型浮體,如大型貨船或航母,則可能屬于第二類。對于不同的分類,需要分別采用不同的定量方法分析。然而,這3種定性分類本身,并非簡單地以人的感覺為依據,而是通過波長與物體尺度之比這一定量指標來劃分,即波長與物體線度之比小于0.2、介于0.2~1.0和大于1.0時,分別為上述三類。因此,從科學上看,并非肉眼直觀所見的水中之墻都是“直墻”,而是從定量上滿足波長與長度之比大于1的構筑物方為波浪力計算中定義的科學意義上的“直墻”。
又如,在波浪力計算中,有一個高度差定義為“波浪中線(平分波高的中線)與計算水平面(即平均水平面或靜水面)之差”。如何理解二者之差?涉及線性波與非線性波的定性差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一般由此產生的波是微小的波,類似于對稱波紋(正弦形狀),基本是上下對稱的,這時波浪中線與計算水平面是重合的,二者之差為零。“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這時的波浪,已經接近或發生破碎,其形狀波峰尖、波谷緩,正如在海邊沙灘常見的波浪那樣。這時的波浪為非線性波浪,顯然,此時計算水平面較波浪中線要低。由此可見,在分析中考慮波浪中線與計算水平面之差,在某種程度上考慮了非線性波浪影響。線性波浪與非線性波浪是定性不同的兩種情況,如何區分?可以用波陡,也就是浪高與波長之比來定量劃分。對于深水波,當波陡大于5%時,一般非線性效應開始變得顯著,而波陡達到10%時波浪開始破碎。
在土的側壓力計算中,根據擋土墻是否移動及如何移動,有靜止土壓力、主動土壓力、被動土壓力之別。一般學生容易記反主動土壓力與被動土壓力的定性特性。實際上,可以直觀理解為“主動土”壓力和“被動土”壓力。“主動土”壓力是指土“主動地”發生變形并產生對擋土墻的壓力,這是由于擋土墻具有離土體而去的位移。“被動土”壓力是由于擋土墻要向土體方向移動,因而土體“被動地”受到外來的壓力。如此一來,就容易理解“主動土”壓力一定小于靜止土壓力,而“被動土”壓力一定大于靜止土壓力。在這一定性認識的基礎上,采用Rankine土壓力理論,結合Mohr應力圓上土應力狀態點的移動,很容易根據圖解進一步計算出“主動土”壓力和“被動土”壓力大小。
在工程實踐中,根據工程經驗給出某些物理或力學量的數量級估計是非常重要的[13]。例如,在總高632 m的上海中心大廈開始規劃之初,基本方案尚未確定,只有總尺寸、總高度和總層數的基本設想,判斷地基是否能承載,需要多少根樁,就需要估計總重量。在重力荷載一節中,給出了混凝土結構折算到每層單位面積重量的基本數值[5],對鋼筋混凝土結構,折算的每層單位面積平均重量為4.95~7.43 kN/m2。混凝土的容重約為24 kN/m3,將包括樓板、墻、柱等混凝土總重量平鋪折算為混凝土樓板時,其等效厚度約為0.2~0.3 m。對于上海中心大廈,按照130層估算,其總折算等效厚度為26~39 m。對于上海中心大廈這樣的超高層建筑,一般設計安全性要求較高、用材較多,且層數越多,中下部柱和墻的截面積相對樓板面積比例越大,因而折算重量越大,底部折算重量可以考慮1.5~2.0的放大因子。以平均每層面積70 m×70 m估計,130層總重量為46~92萬t,中值約為69萬t。這一估計值與實際重量74.8萬t在同一數量級上[15]。可見,即使根據工程經驗進行粗略的定量估計,在設計中特別是規劃階段,也對工程決策起到重要作用。
三、結語
工科類本科專業課程教學起著連接大學基礎教育與工程實踐教育的橋梁作用,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因此,文章梳理了工科類專業的本科課程體系與錢學森現代科學技術體系觀之間的對應關系,論述了專業課程教學的邏輯地位,在本科專業課程教學中應體現科學共性基礎與具體問題相結合、科學原理與生產生活常識經驗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教學理念,并通過具體教學實踐進行了闡述。共性與具體、科學與常識、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三項基本原則,不僅是處理工程技術問題的重要方法,也是哲學基本原理在本科生專業課中的具體體現。在教學過程中,上述三個方面不是完全分開的,在一個具體問題中可能同時體現了其中的兩個甚至三個方面。
參考文獻:
[1]顧孟潮.錢學森論建筑科學[M].2版.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4.
[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M.克萊因.古今數學思想[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4] 希爾伯特.數學問題[M].李文林,袁向東,譯.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14.
[5]陳建兵.研究生課程中教師應起到怎樣的作用?[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4):116-120.
[6]錢學森.工程和工程科學[M].力學進展,2009,39(6):643-649.
[7]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8]李國強,黃宏偉,吳迅,等.工程結構荷載與可靠度設計原理[M].4版,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6.
[9]歐特爾.普朗特爾流體力學基礎[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10]錢學森,于景元,戴汝為.一個科學新領域——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及其方法論[J].自然雜志,1990,13(1):3-10.
[11]洪華生,鄧漢忠.工程中的概率概念[M].陳建兵,彭勇波,劉威,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7.
[12]王振東,武際可.力學詩趣[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
[13]趙凱華.定性與半定量物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4]王大鈞,王其申,何北昌.結構力學中的定性理論:解的定性性質與存在性[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15]丁潔民,巢斯,趙昕,等.上海中心大廈結構分析中若干關鍵問題[J].建筑結構學報,2010,31(6):122-131.
Abstract: For some issues of common interest in specialty course teaching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ed in engineering, Tsien’s thought on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is adopted, and the viewpoint of “three-incorporation” in teaching, i.e., the incorporation of scientific common basis and special engineering problems, the incorporation of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experiences or commonsense in daily life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qualitative concepts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is proposed. The idea is illustrated by taking the teaching of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of loads and structural design principles as an example.
Key words: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ty course;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technological science
(責任編輯 周 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