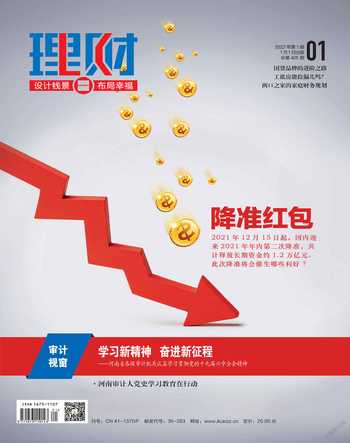壽險業急需生前遺囑金箍
陳輝
當前壽險業存在的問題
近日,銀保監會印發了《關于進一步豐富人身保險產品供給的指導意見》,雖然只有12條意見,但卻回答了“人身保險業務發展到底怎么了” 這一問題。當前宏觀經濟延續穩中有進的基本態勢,但壽險業歷史上積累的一些風險和矛盾正在水落石出,對壽險業形勢要客觀認識、理性看待,對存在問題要開準藥方,及時解決。結合2021年中國壽險業的發展狀況,當前壽險業需要思考并解決的十大問題是:
問題1:中國壽險業保費增速全面放緩,現金流風險與日俱增。
問題2:中國壽險業資金運用穿透后所指向的房地產,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正在強化,要警惕償付能力監管的失效。
問題3:中國壽險業資金運用收益開始下行,利差率風險正在醞釀發酵。
問題4:中國壽險業的資本喜好度在下降,未來凈資產增長速度將放緩,抗風險能力值得關注。
問題5:中國壽險業盈利能力(ROE)雖然領跑其他金融業,但如果拆開來看卻令人擔憂。
問題6:中國壽險業盈利主力是個人代理人業務,隨著知識經濟智能進化時代的到來,消費者開始覺醒,個人代理人業務的利潤正在被蠶食。
問題7:中國壽險業的半壁江山是銀行保險業務,隨著消費者開始適應銀行互聯網業務,銀行保險成為明日黃花。
問題8:中國壽險業的后起之秀是互聯網保險業務,隨著人身保險互聯網新規的施行,互聯網保險將會大幅縮水。
問題9:中國壽險業真正的未來在養老保險或養老金融,雖然過去20年徘徊不前,但能不能找到方向就在當前。
問題10:中國保險業因疫情放大了其價值,但是未知的風險也在放大。
上述十大問題正是壽險業安全問題的風險源頭:最大的不確定性(金融危機)、最大的風險源(投資業務)、重大的危險源(承保業務)和重大的隱患源(保險機構)。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局面?主要是因為我們缺少對金融(保險)的認知和敬畏感,我們經歷了P2P的瘋狂,但是部分壽險機構有過之而無不及,真乃“無知者無畏”,歸根結底,都夢想“大而不倒”。
為什么“大而不倒”?又該如何破解?也許除了公司治理、市場行為、償付能力監管之外,還需要一個金箍——“生前遺囑”。
金融業的“生前遺囑”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多家世界知名大型金融機構倒閉。痛定思痛,為防范危機,“生前遺囑”機制應運而生。
所謂“生前遺囑”,包含恢復計劃(RCP)和處置計劃(RSP)兩部分,即要求金融機構擬訂并向監管機構提交,當其陷入實質性財務困境或經營失敗時快速有序的處置方案,以促使機構恢復日常經營能力,或者實現部分業務功能分拆或機構整體有序關閉的制度安排。
2021年12月1日《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監管規定(試行)》正式施行,制定恢復和處置計劃正式成為19家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規定動作”。加上之前文件明確的“調整后表內外資產達到3000億元人民幣及以上的存款類金融機構”以及設立時須提交恢復和處置計劃的民營銀行,我國將有數十家銀行面臨集團層面恢復和處置計劃的制定任務,中國銀行業開始步入“生前遺囑”時代。
壽險業的“生前遺囑”
《銀行保險機構恢復和處置計劃實施暫行辦法》第四條規定:“表內總資產達到2000億元人民幣及以上的保險(控股)集團和保險公司均應當制定恢復和處置計劃。”該辦法主要還是針對“大而不能倒”的保險機構,但“小而容易倒”也是當前中國壽險業的“痛點”。
2014年年初,原中國銀監會要求5家試點民營銀行設立“生前遺囑”;2017年年初,原中國保監會擬在3家相互制保險機構試點“生前遺囑”,可惜沒有最終落地。
回顧中國近20年壽險公司的成立過程,基本上每家機構都少不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的支持函”成了壽險公司成立的必要條件。這些“支持函”所隱含的就是一種承諾,給予保險監管部門的承諾,給予社會大眾的承諾,所以地方政府發出的“支持函”成了道義上的“生前遺囑”。
從恒大最新的處置方案來看,地方政府正在履行“生前遺囑”,主要是為了避免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因為“大而不能倒”,更因為地方政府歷史上的各種“支持函、承諾函”已經成為道義上的“生前遺囑”。
對于壽險業來說,各地政府出具的“支持函”雖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生前遺囑”,但卻是道義、民心上的“生前遺囑”,這些都會記入保險業的歷史。
根據《保險保障基金管理辦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規定,壽險公司也存在被依法撤銷或者依法實施破產的可能,在此情況下個人保單持有人的救助金額不會超過保單利益的90%。所以,保險監管部門保護消費者權益不能變成口號,也不能變成承諾,只能進一步約束保險公司股東的行為,要求所有股東簽署“生前遺囑”。
從法律性質上來看,壽險機構和民營銀行承擔的責任基本一樣,所以需要借鑒民營銀行的“生前遺囑”來重新確定壽險業的生前遺囑規則。《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監管規定(試行)》《銀行保險機構恢復和處置計劃實施暫行辦法》雖然做了一些規定,但無法約束當前部分壽險機構存在的問題。
《關于進一步豐富人身保險產品供給的指導意見》第一條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需要落到實處,除了產品設計之外,關鍵在于產品的安全。一旦產品發生問題,要解決“如何追索、向誰追索”的問題。
雖然理論界對是否應設立“生前遺囑”議論紛紛,有“支持論”和“反對論”,但是當前部分壽險機構暴露的問題正是因“大股東貪婪、小股東不作為”“董事會一言堂、監事會不作為”“執行董事操縱、獨立董事不作為”造成的,所以必須通過“生前遺囑”來約束股東的行為,必須通過“過錯推定、連帶賠償責任機制”來約束董事、監事和高管的行為。
所謂治標先治本,最近幾年保險業的“穿透式監管”解決了部分機構的股東關聯性問題,還需要“生前遺囑”來進一步放大股東的連帶賠償責任。如此,我們才能暢想未來10年、20年中國壽險業的變革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