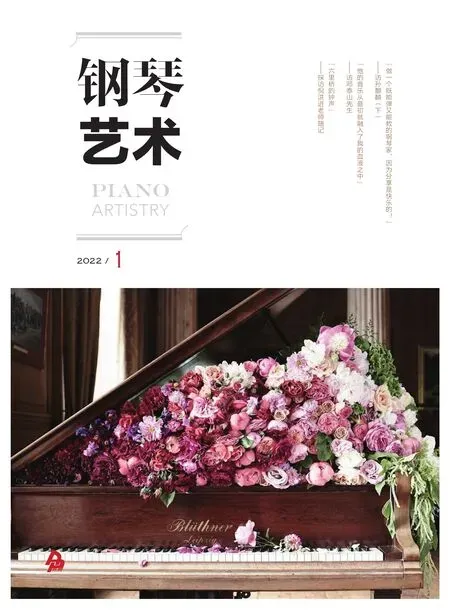『他的音樂從最初就融入了我的血液之中』
——訪鄧泰山先生
訪談?wù)? 郭 煦

本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以下簡稱“肖賽”),加拿大華裔選手劉曉禹以其精湛的琴藝和出色的發(fā)揮征服了廣大觀眾和評委,一舉奪得冠軍,而他的老師鄧泰山教授(同時也是我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的老師)又是當年第一位獲得肖賽冠軍的亞洲人,人們不禁對這對冠軍師徒充滿好奇,更想聽聽這位傳奇鋼琴家(同時又是本屆肖賽的評委)如何評價本屆比賽及對肖邦作品的獨到見解。為此,我專門和鄧泰山教授相約做了本次采訪。
Q:您作為肖賽的評委之一,我們想了解一下,對于評委來說,什么樣的演奏是評委希望看到的?
A:這有關(guān)評委的喜好和品位。其實我不太確定其他評委是以什么方式去評判的,我只知道我自己的評判標準。肖賽美好也獨特的地方,就是我們最終能夠看到所有評委的分數(shù)和投票情況。而每一位評委之間的喜好其實有非常大差異,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這也是我們?yōu)槭裁葱枰粋€如此龐大的評審團,最終從這些“瘋狂”的評判當中得出一個平均分。
我的評審標準隨著輪次不同而變化。當然,我認為像任何一個鋼琴比賽一樣,我們要選擇的是非常高水平的演奏家,與此同時,肖賽非常重要的一點,也是它的特殊性,就是完全只演奏肖邦一人的作品。如果細致地從每一輪講的話,第一輪的評審更像是對一個選手綜合實力和第一印象的評判。以多年作為肖賽評委的經(jīng)驗來看,這一屆選手總體水平最高。例如,在上一屆的第一輪當中,只要選手的總體演奏沒有瑕疵,比如,技巧上完美、夜曲具有歌唱性、大曲子有結(jié)構(gòu),那進入下一輪就不是件難事。但是這種情況在這一屆當中就變得很困難,我們在第一輪就可以看到很多選手的演奏無論從作品的完整性,還是音樂風格的把握各個方面都在非常準確的方向上,但是卻沒有進入第二輪。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彈得不好,只是因為參賽選手整體的水平非常高。所以,在參與這一屆評審時,我對于選手在每一輪演奏的要求就會更加嚴格。第二輪的曲目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波蘭舞曲和圓舞曲等舞蹈體裁形式,這對于肖邦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第二輪,我們的要求就已經(jīng)具體在更細致的曲目類別中了。第三輪的奏鳴曲和瑪祖卡就更具有挑戰(zhàn)性了。所以我認為如果想要在這一屆比賽中勝出,需要非常完美的、符合肖邦總體風格品位的成熟的演繹。



Q:您覺得現(xiàn)在的肖賽相比您1980年獲獎時的那屆有什么區(qū)別?
A:跟我那屆比較而言,現(xiàn)如今肖賽選手們的演奏風格更加多種多樣,各富特點。尤其是這一屆比賽,選手之間的演奏風格差異非常大。之前,我們總是對如何詮釋肖邦有著一些刻板觀念或印象—應(yīng)該這樣演繹肖邦,不應(yīng)該那樣演繹肖邦,所以這一屆選手們千差萬別的演繹從某種角度來說讓評委感到了些許困惑,也解釋了為什么評委之間的投票和分數(shù)有那么大的差異。相比現(xiàn)如今的趨勢,在我那屆比賽時,甚至是更早的時候,評委的審美和態(tài)度也許會更加保守,現(xiàn)在評委們的觀念更加開放,也更具有包容性。
為什么評審會出現(xiàn)這樣一個新的趨勢呢?我認為其中一個因素是現(xiàn)代發(fā)達的科技和網(wǎng)絡(luò),把全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讓所有的信息得以共享,而在這之前,還是有“一堵墻”阻隔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共享。在我那個時代,想要了解西方國家的文化與藝術(shù),獲取一些西方古典音樂的相關(guān)知識與信息是非常困難的。如今,我們只需要簡單地點擊鼠標,就可以獲取一切訊息,這堵墻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甚至是之前比較閉塞的國家,例如日本,總是被人評價為“地理上和文化上都與世隔絕的島國”,而在今天,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日本選手的變化,他們的演奏更加國際化,更具有個性。這其實很有意思,就是我們所謂的當今社會更加民主的發(fā)展趨勢,讓我們作為音樂家也更具有包容性。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評委會的組成也發(fā)生了變化。在我那個時期,肖賽的評委非常多,大概24位,而且大多數(shù)由“老師”組成,這種情況在2005至2010年左右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肖賽主辦方由最初波蘭非政府組織“肖邦社”,變成了2001年起建立的“國立肖邦研究院”,由此,很多東西都發(fā)生了改變。例如,評委的組成更趨向于邀請往屆肖賽的獲獎?wù)撸蚴悄切┰趪H舞臺上以詮釋肖邦著稱的鋼琴演奏家,評委的數(shù)量也減少到16至17位左右。
這些原因累積起來,解釋了為什么之前波格雷里奇事件造成了如此大的轟動—那時候人們第一次聽到如此有個性的肖邦,大家無法接受,但是放在今天的比賽中,這樣有個性的演奏是很常見的。
Q:這一屆肖賽比較特殊,由于疫情推遲了一年。您覺得這是否與這屆選手總體較高的演奏水平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
A:對于選手來說,因為疫情推遲一年的比賽帶來最直接的積極影響就是每個人都額外多了一年的準備時間,所以總體的平均水平是很高的,可能因為疫情期間大家都只能待在家里練琴吧。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會選擇比預定人數(shù)稍微多一點的選手參賽,比如原定正賽應(yīng)該只有80人,但是我們選擇了87人,因為有點擔心一些選手由于疫情原因可能面臨出行、簽證、隔離,甚至生病的情況導致無法參加比賽。但是結(jié)果卻很神奇,這87人全部到場了!這也許是另一個這屆肖賽競爭更加激烈的原因吧,人數(shù)更多了!當然這只是一句玩笑話。
Q:作為第一位在歷史上獲得肖賽冠軍的亞洲人,您向我們展現(xiàn)了最好的肖邦詮釋,這意味著彈好肖邦不僅是波蘭人或者歐洲人,更可以是亞洲人。您覺得肖邦及他的作品與我們亞洲人之間有什么共性或連接?
A:第一,肖邦的音樂更多的是對一種情緒的宣泄與表達,我們亞洲人對于情緒和意境的感知更加敏感—當然不是說西方人不敏感,只不過在我看來歐洲人的情感與理性所占比可能相對來講更平均一些。在藝術(shù)上面,亞洲人更加偏向“寫意”,這可能使得肖邦的音樂更加容易且更加迅速地走進我們的內(nèi)心,我們發(fā)自內(nèi)心地喜歡并且著迷于這樣的音樂,因為它觸動人心;而西方國家的人的審美有時更趨向于欣賞由理性及頭腦出發(fā)的、用邏輯思維構(gòu)建的藝術(shù)。
第二,肖邦的音樂是充滿詩意的。我們觀察中國和越南的語言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都有一個共性,就是非常“旋律化”,不是橫平豎直的。中文有四種聲調(diào),越南有六種聲調(diào),從這可以看出我們對旋律和音調(diào)是多么的敏感!當然肖邦的作品當中還有和聲等很多其他要素,但是其詩意的旋律是最能夠直接打動人心的,這也使他的音樂可以距離我們更近,與亞洲人的情感建立如此緊密的聯(lián)系。
第三,可能與體格也有關(guān)系。肖邦本身相對來說是比較瘦弱小巧的,不屬于大塊頭體型,也不是高個子的人。有一次我在西班牙一個博物館看到他的一件絲綢制的衣服,發(fā)現(xiàn)居然如此小巧,跟咱們的高度差不多。如果我們更加具體的從鋼琴演奏的角度講,也許可以跟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做一個對比。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大多由成千上萬個細密的音符構(gòu)成, 彈奏他的作品需要一雙大手,并且演奏者要能夠發(fā)出龐大且渾厚的聲音;而肖邦的音樂相比之下就顯得比較輕盈,對于我們亞洲人來講,身體上也更加容易適應(yīng),更加容易擁有一個良好的控制力。
綜上所述,敏銳的感知力、詩意與成熟的情感、小巧的身材,還有旋律的美、音色的美、樂句的美、歌唱性、抒情性等,這些都是肖邦與其音樂的特征,都將肖邦與我們亞洲人連接在一起。
Q:確實是的。那從您自身的角度來講,您覺得肖邦對于您個人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A:對我自己來講,肖邦的音樂給我的人生帶來極其重要的影響。我幼年時,成長在越南的戰(zhàn)亂之中。那個時候我沒有辦法接觸到任何其他的作曲家,但是我卻擁有所有肖邦作品的樂譜。1970年那屆肖賽,也就是奧爾森(Garrick Ohlsson)和內(nèi)田光子(Mitsuko Uchida)參加的那屆,我的母親作為客座嘉賓被邀請到比賽現(xiàn)場。她飛去華沙觀看了整場比賽,重要的是,她帶回了全套肖邦作品的樂譜與錄音唱片,并給我們講述了好多關(guān)于肖賽的故事。當時我12歲,除去肖邦的音樂,我沒有接觸過任何其他作曲家的音樂—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等,所以我每天從早到晚就是聽肖邦的作品,我為之著迷!你知道我人生當中聽的第一首肖邦作品的錄音是什么嗎?是阿格里奇在1965年比賽現(xiàn)場的演奏,她彈了《e小調(diào)協(xié)奏曲》《諧謔曲第三號》《瑪祖卡》,等等。你可以想象這對于一個第一次聽到“真正的音樂”的孩子來講具有怎樣的意義,在此之前,我對于什么是“真正的音樂”是沒有概念的。
另外我母親最喜歡的作曲家也是肖邦。戰(zhàn)亂時期我們住在山上,每到晚上萬籟俱寂的時候,我的母親會坐在鋼琴前,彈奏一些像瑪祖卡、夜曲這樣的作品。這個場景對我來說如此感人—尤其在那時所處的環(huán)境下,我們從白天的勞作中回來,肖邦詩意的旋律突然流淌在如此寧靜的山中夜晚。所以,我們之前講述的肖邦音樂的“美”,在這個時刻都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此外,唱片對我的影響也非常大。1960年,紀念肖邦150周年誕辰時,波蘭發(fā)行了由波蘭鋼琴家錄制的全套肖邦專輯,我仍然記得那套厚厚的唱片,車爾尼-斯婕萬斯卡(Halina Czerny-Stefanska)、斯門江卡(Regina Smendzianka)、艾凱爾(Jan Ekier),等等。也許,在最開始學習肖邦的時候就接觸到這些比較“正宗”、傳統(tǒng)的熏陶,與完全站在個人的角度去接觸肖邦音樂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是有一定區(qū)別的。
所以他的音樂從最初就融入了我的血液之中,之后我又為自己開辟了充滿幻想的旅途。
Q:我還記得您推薦我去聽很多肖邦音樂的專輯錄音,并且您說過,如果想要提升演奏肖邦音樂的品位,例如,如何彈好一首瑪祖卡,要首先彈奏大量的瑪祖卡。另外我注意到,在課堂中,您多次提到“即興”“情緒”“特殊性”“氣氛”等詞匯。您覺得在演奏時我們最應(yīng)該注意的是什么?有沒有什么關(guān)于肖邦演奏的“規(guī)則”?
A:是的,那些詞語不光針對肖邦的音樂,它們適用于所有作曲家的作品。設(shè)想當我們?nèi)ヒ粋€劇院時,無論是戲劇、芭蕾、還是歌劇。大幕拉開的那刻,我們不光是聽到了音樂,我們還可以看到舞臺的場景布置—有時候在城堡、有時候在河邊、有時候在森林、有時候在舞會……包括燈光的設(shè)計,有時明有時暗,浪漫氛圍下可能會有月光的襯托,當表現(xiàn)悲劇色彩時色調(diào)可能較重較冷較暗,甚至一些燈光也可以表現(xiàn)神秘的氛圍,等等。但是,所有這些我們看到的,都是劇院為觀眾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些布景已經(jīng)為之后即將發(fā)生的故事情節(jié),出現(xiàn)的人物性格,整體氛圍等進行了鋪墊。當我們演奏音樂時也是一樣的,要為觀眾營造樂曲本身的一種特殊氛圍,以此來襯托出樂曲想要表達的情感和性格。
“即興”這個詞其實更針對肖邦,因為肖邦本身不光是作曲家,也是鋼琴家,并且他的演奏經(jīng)常用到“即興”這個技巧。所以掌握“即興感”和“彈性節(jié)奏”是演奏肖邦最重要的兩個要素,也是肖邦有別于其他作曲家的特質(zhì)。我觀察到,在肖賽的歷史中,一些特定國家或地區(qū)的人更容易取得成績—比如,拉丁裔人、法國人、意大利人、東歐人、甚至南美洲人,他們的情感更加外放,精神意識可能相對更加自由,那他們可能就會更加接近肖邦的音樂情感。但是偏重理性的德國人和英國人,就很少在肖賽中取得成績。甚至在肖邦還活著的時候,他很難贏得德國觀眾的喜愛,對于他音樂中的“即興”和“彈性節(jié)奏”所產(chǎn)生的自由的感覺,當時的德國聽眾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理解接受。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講,這兩個國家的演奏者更容易在類似于“柴科夫斯基大賽”(以下簡稱“柴賽”)這類的比賽中獲獎,柴賽歷史上來自英國的獲獎?wù)邤?shù)不勝數(shù),例如,1962年的冠軍奧格登(John Ogdon)、1970年的冠軍里爾(John Lill)、1982年的多諾霍(Peter Donohoe)和1986年的冠軍道格拉斯(Barry Douglas)等,所以其實是依照不同比賽的具體需求。一些比賽也許比較看重具有宏觀構(gòu)思、結(jié)構(gòu)框架清晰條理的演奏。我曾經(jīng)在莫斯科學習過,可以體會得到他們有多么地熱愛“理性”的演奏。但在肖邦的音樂中,首當其沖的應(yīng)該是他的情感,當然這絕不表示我們要用“愚蠢”、盲目的直覺去演奏,我們?nèi)匀灰兄腔鄣匮葑啵徊贿^“邏輯”在這里不是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素。
Q:說到不同演奏者的個性差異,我從觀眾的評論當中觀察到,一個具有強烈個性的演奏者總是能讓其每一次演奏為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對于肖賽,大家都演奏肖邦的作品,我們應(yīng)該如何去平衡作曲家的本意與演奏者的個性?
A:其實不同作曲家情況各不相同。一些作曲家的作品允許詮釋者有更多自由空間發(fā)揮自己個性,比如,貝多芬的作品雖然看起來要用一種很嚴謹?shù)膽B(tài)度去彈,但是他的作品最主要的宗旨是去傳達一種理念、一種思想—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演奏貝多芬,只要你想要傳達的理念是具有說服力的。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可以聽到那么多對于貝多芬的不同演繹。但前提是你必須要有一個主旨、一個信念,因為貝多芬的音樂所強調(diào)的就是一個人的思想與信念,單靠直覺和第六感是不可能演奏貝多芬的。
而有幾位作曲家在這方面給演奏者的空間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莫扎特和肖邦。也許是我個人太保守,當一個人用太標新立異或者太個性化的方式去演奏莫扎特的時候,我是很難消化的。肖邦可能相較于莫扎特來說空間稍微大一些。也就是說,我們當然可以在演奏肖邦時擁有自己的個性,但是重要的是這個比例占多少。如果你偏離軌道太多,人們就很難接受。



Q:在這屆肖賽中,您的學生劉曉禹、白立君,包括上一屆的陸逸軒、劉珒、楊藝可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這么多學生在世界最頂尖的鋼琴賽事中創(chuàng)造佳績,這在我看來是一位老師在教學上創(chuàng)造的奇跡,能否請您分享一下您的教學秘訣?


A:沒有魔法,沒有秘訣!首先,我覺得彈好鋼琴非常重要的一點當然是要有天分,很幸運我擁有非常有天分的學生。其次就是這個世界上并沒有奇跡,比賽要做到十分充分的準備。在比賽中我經(jīng)常見到很多十分有天分的學生,由于各種原因,沒有在賽前進行充分的備賽。所以,面對比賽要非常認真、細致、充分地進行準備,讓整套參賽曲目保持最好的狀態(tài)。我的學生中,包括上一屆的劉珒和陸逸軒,在華沙肖賽之前已經(jīng)在很多比賽中得到了訓練。比如,美國邁阿密的肖賽、韓國的肖賽、中國佛山的肖賽,這一屆的白立君也是在兩年前就參加過北京的肖賽……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有點類似于奧林匹克,不是說有一天想贏比賽了,我們就可以馬上做好,必須要經(jīng)過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訓練。尤其對于這一屆肖賽來說,因為疫情原因,產(chǎn)生了很多的不便,我們的課都變成了線上課。但是白立君和劉曉禹很幸運,可以接受線下課。劉曉禹定居在蒙特利爾,而白立君的父母則每周都會從多倫多開車來陪他上課。線下課和線上課還是有差別的。因為像參加肖賽的這些選手,都已經(jīng)是具有極高音樂水平的鋼琴家,每位演奏家之間的差別其實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們要確保在比賽的時候保持最佳的狀態(tài)。為此,在9月份(2021年)時,我還在家中為學生舉辦了小型模擬比賽,我們稱之為“肖邦奧林匹克訓練營”。學生們都來到蒙特利爾,張凱閩也從中國臺灣飛過來。每周,我們進行一輪比賽的完整預演,我們甚至還抽簽決定演奏的先后順序。他們在肖賽的時候發(fā)揮得比在我家的時候要好,在蒙特利爾我還不能說完全發(fā)揮得很好。總而言之,任何事情我們想要取得成功都要經(jīng)過腳踏實地的訓練。另外我還建議我的學生們到華沙之后先去拜訪存放肖邦心臟的教堂去表達敬意,然后再到舞臺上去盡情展現(xiàn)音樂。
Q:準備如此重大的比賽,時間是一個很關(guān)鍵的因素,因為龐大的曲目量包含了如此多的不同風格的肖邦樂曲。您認為什么樣的狀態(tài)或能力是參加大比賽的人最應(yīng)當擁有的?
A:關(guān)于準備大比賽,曲目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決定要參賽之前就已經(jīng)擁有了豐富的曲目量,是最好的一件事。這也是為什么很多時候我在為一些鋼琴家寫參加大比賽的推薦信時,比賽方會問到:這位選手是否具備成為一個事業(yè)極其成功的演奏家的條件—他是否隨時可以準備好開啟繁忙的演出日程;他能不能夠勝任跟樂團的巡回演出;有沒有足夠的與樂隊合作的協(xié)奏曲曲目量,等等。所以,這不是簡單的參加比賽這一件事,而是需要為一切的可能性做好準備。當你有足夠的曲目積累時,在比賽準備過程當中的熱身與經(jīng)驗也就更加充足。如果你還記得,早在六七月份的時候,我們就已經(jīng)開始為肖賽的正賽進行曲目練習的規(guī)劃安排—從協(xié)奏曲開始,一輪一輪倒著進行。有些選手可能比較謙虛或沒有自信,覺得我肯定進不了決賽,所以就不去重視協(xié)奏曲,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借口—只要一個人決定要參加比賽,那他就要準備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