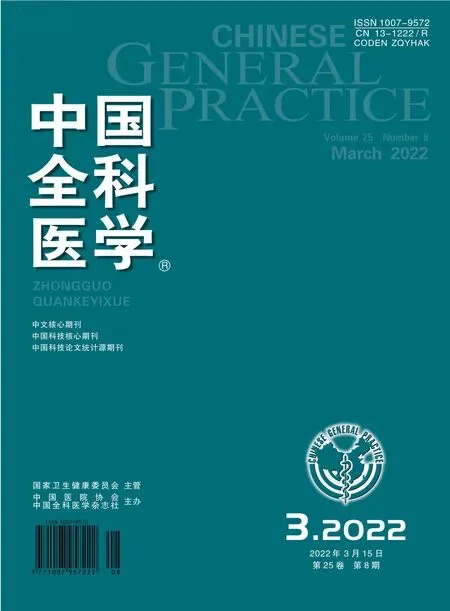腸道菌群及免疫調節與兒童哮喘關系的研究進展
崔天怡,劉佳蕊,呂彬,高秀梅,趙鑫*
支氣管哮喘(以下簡稱哮喘)在全球范圍發病率較高,且通常情況下,哮喘患者常從幼兒期開始出現癥狀[1]。兒童哮喘伴隨反復發作的喘息、咳嗽、氣促、胸悶等臨床表現,以慢性氣道炎癥和氣道高反應性為主要特征[2]。哮喘與免疫調節密切相關,個體易感性、病毒感染、過敏原暴露等因素導致免疫失衡引發哮喘[3],而且免疫細胞在哮喘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兒童哮喘具有多種不同的臨床和病理生理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哮喘患兒的腸道微生物組成與健康兒童相比有顯著差異。臨床研究表明,3 月齡哮喘患兒的糞便樣本中毛螺菌屬(Lachnospira)、韋榮氏菌屬(Veillonella)、糞桿菌屬(Faecalibacterium)和羅斯氏菌屬(Roseburia)的相對豐度顯著降低,并伴有乙酸鹽合成減少和腸肝代謝產物失調[4]。另一項隊列研究證實,糞便樣本中鏈球菌(Streptococcus)和擬桿菌(Bacteroides)的相對豐度增加,且雙歧桿菌(Bifidobacterium)和瘤胃球菌(Ruminococcus)相對豐度降低的3 月齡兒童,在其5 歲時患特應性喘息的風險更高[5]。腸道中雙歧桿菌、阿克曼菌屬(Akkermansia)和糞桿菌屬相對豐度較低,且念珠菌(Candida)和紅酵母(Rhodotorula)相對豐度較高的兒童發生特應性哮喘的風險升高[6]。在生命早期,免疫系統的成熟與微生物群的形成同時發生。由于腸道微生物對于調節免疫細胞功能和抵抗致病菌有重要影響,因此嬰幼兒期的腸道微生物定植與失調同包括哮喘在內的眾多呼吸系統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此外,腸道菌群失調誘發腸道損傷及黏膜免疫功能失調,加速了哮喘的發生與發展。因此,本文概述了哮喘兒童的腸道菌群特征和基于“腸-肺軸”的免疫調節機制,并探討菌群精準化治療哮喘在未來的應用前景。
1 哮喘中的免疫調節依賴于腸道菌群
多項臨床和基礎研究已證實了腸上皮細胞和腸固有免疫細胞通過吸收內皮細胞的信號,形成局部細胞因子微環境,從而導致遠端呼吸道免疫反應的改變[7-11]。兒童哮喘涉及先天和獲得性免疫反應,以下將具體闡述腸道菌群對兒童免疫系統的影響及其與兒童哮喘的關系(圖1)。

圖1 腸道微生物參與調節哮喘的免疫反應Figure 1 Gut microbiota regulate the immune response in asthma
1.1 腸道菌群調節T 淋巴細胞群 T 淋巴細胞包括輔助型T淋巴細胞(Th 細胞)和調節性T 淋巴細胞(Treg 細胞),具有調節機體免疫活動、維持對自身抗原的耐受性以及阻礙自身免疫性疾病發生發展的功效[12]。過敏性哮喘的慢性炎癥多由常見的、非致病性的過敏原產生的Th2 型免疫反應增強所致[12-13],且免疫球蛋白E(IgE)水平升高[13-14]。Th2 細胞產生的細胞因子白介素4(IL-4)、白介素5(IL-5)、白介素9(IL-9)等通過刺激B 淋巴細胞產生嗜酸粒細胞和IgE 抗體,進而促進肥大細胞釋放組胺、5-羥色胺和白三烯,造成支氣管收縮及過敏反應[15]。Th1 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白介素2(IL-2)、干擾素γ(IFN-γ)、腫瘤壞死因子β(TNF-β)等促進巨噬細胞介導的免疫應答過程[16]。研究表明,Th1/Th2 平衡及Treg 細胞的免疫功能受腸道微生物的調節,如腸道分節絲狀菌(segmented filamentous bacteria,SFB)直接刺激Th17 分化[17]、梭狀芽孢桿菌(Clostridium spp.)參與誘導Treg 產生[18]、擬桿菌參與調節Th1/Th2 平衡[19]。因此,從腸道菌群入手對T淋巴細胞的免疫反應調節有助于緩解哮喘。
1.2 腸道菌群調節氣道上皮細胞和樹突狀細胞(DCs) 氣道上皮細胞在協調先天和獲得性免疫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而先天免疫和獲得性免疫參與了哮喘的發展[20]。上皮細胞調控免疫球蛋白A(IgA)抗體、防御素和溶菌酶的局部免疫活性,這些免疫活性也受白介素33(IL-33)、白介素25(IL-25)和胸腺基質淋巴生成素(TSLP)的調節,后者刺激Th2 型炎癥并促進哮喘發生。另一項相關研究證實了抗TSLP 抗體能夠抑制由上皮細胞驅動的Th2 炎性反應,該抗體可使過敏原誘導的支氣管收縮減少,并降低呼出氣一氧化氮(NO)水平和痰中嗜酸粒細胞的數量,上皮細胞還產生其他調節細胞因子,如白介素10(IL-10)和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21]。腸道菌群通過代謝L-酪氨酸使甲酚硫酸鹽(PCS)水平升高,該作用促進了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和Toll 樣受體4(TLR4)信號解偶聯,從而減少了氣道上皮細胞CC 族趨化因子(CCL20)的產生,保護宿主抵抗過敏性氣道炎癥[22]。該研究提示腸道菌群代謝產物可作用于遠端氣道上皮細胞從而減少過敏性哮喘反應。
DCs 是先天免疫和獲得性免疫之間的重要紐帶,其影響過敏性哮喘的發展。DCs 呈現給免疫系統的微生物片段可以促進許多調節和適應性反應,包括Th1、Th2 和Th17 細胞通路[23-24]。最近的研究證實了肺DCs 在哮喘中的作用,DCs 可以激活幾種免疫細胞類型,如T 淋巴細胞和固有淋巴樣細胞(ILCs),這些細胞能夠提供針對共生菌的環境信號[25]。
1.3 “腸-肺軸”免疫細胞遷移依賴于微生物群 “腸-肺軸”的通訊機制也涉及免疫細胞,如2 型固有淋巴樣細胞(ILC2)、3 型固有淋巴樣細胞(ILC3)和Th17 細胞,通過血液循環從腸道直接遷移到呼吸道,參與哮喘的發病過程[26]。研究表明,通過給一只小鼠腹腔注射細胞因子IL-25,激活其腸道的炎癥性ILC2,將ILC2 移植至正常小鼠體內可觀察到ILC2 細胞向肺部遷移[26-27],但若是小鼠在注射IL-25 后服用抗生素并感染巴西擬青霉(Penicillium),則遷移現象并不明顯[27],該實驗證實了免疫細胞遷移可以依賴于微生物群。免疫細胞在腸道和肺部之間的轉移可能會增強宿主抵抗感染的能力,例如,腸道DCs 調控表達白介素22(IL-22)的ILC3 遷移到肺部并介導對炎癥的保護,該過程需要依賴于腸道共生菌的參與[28]。然而,這樣的串擾也可能在疾病中發生,因為SFB特異性Th17 細胞帶有雙重T 淋巴細胞抗原受體,一個是SFB特異性的,另一個是自身抗原特異性的,其遷移到呼吸道并且會促進肺部病理性損傷加重[29]。
2 腸道菌群代謝物參與免疫調節機制
2.1 脂多糖或肽聚糖 具有表達模式識別受體(如Toll 受體或核苷酸結合結構域、富含亮氨酸重復的受體)的宿主細胞——可溶性腸道微生物代謝物肽聚糖或脂多糖(LPS),經循環運輸是腸道微生物和呼吸系統溝通的主要方式。經抗生素干預的小鼠直腸內注射LPS,可恢復其對流感病毒肺部感染的免疫反應能力[30]。LPS 失活小鼠在塵螨中產生Th2 細胞反應的能力降低,這表明具備生物活性的LPS 對哮喘具有預防作用[31]。不過,當研究人員給耗盡腸道微生物群的小鼠腸內注射LPS 時,這種預防作用就消失了[31]。這些實驗反映了腸道微生物衍生的LPS 影響呼吸道對過敏原反應的能力。
2.2 短鏈脂肪酸 經微生物群代謝產生的短鏈脂肪酸(SCFAs),包括丁酸、丙酸和醋酸,釋放至腸腔后,會在腸道形成局部免疫反應[32-33]。臨床研究表明,1 歲時糞便中丁酸酯和丙酸酯含量較高的兒童患過敏性哮喘的概率顯著降低,并且在其成長到3~6 歲時患哮喘的可能性較小[34]。不同于胃腸道的SCFAs 經門靜脈輸送到肝臟進行代謝,未代謝的SCFAs 進入外周循環和身體遠端部位會影響免疫細胞的發育。研究證實,口服丙酸可以通過削弱對DCs 的招募,從而抑制Th2 細胞功能,進而減輕小鼠過敏性氣道炎癥[35]。在經萬古霉素干預的口服丁酸鹽、丙酸鹽和醋酸混合物的小鼠中,也被證實DCs 功能減弱與肺部過敏反應相關[36]。在哮喘的小鼠模型中,喂食小鼠醋酸有利于Treg 細胞的分化[37]。另外,有研究結果提示SCFAs 可減輕雞卵白蛋白(OVA)和屋塵螨(HDM)誘導的氣道炎癥模型的炎性反應[36]。此外,在妊娠和斷奶期間小鼠口服SCFAs 可以保護后代免受過敏引起的肺部炎癥,尤其是服用丁酸酯后,可有效誘導后代肺部的Treg 細胞增加[34]。
最新的證據表明“肺-腸軸”是雙向的[38],例如LPS刺激小鼠肺臟可以導致腸道細菌數量顯著增加[39],并且細菌性肺炎會導致腸道損傷[40]并減少腸上皮細胞增殖。此外,來自腸道細菌的SCFAs 通過與G 蛋白受體結合或通過羥甲基戊二酰輔酶A(HMGCoA)還原酶抑制甲羥戊酸途徑來抑制先天免疫應答,發揮對肺部炎性反應的抑制作用[41]。其他已知具有免疫調節作用的腸道微生物代謝物,包括膽汁酸、吲哚衍生物(膳食色氨酸代謝產物)、煙堿、多胺(l-精氨酸代謝產物)、尿素A、丙酮酸和乳酸,在維持腸道內穩態中均有重要作用[42-45]。然而,這些腸道微生物代謝物是否影響呼吸系統健康仍有待確定。
3 益生菌改善哮喘的前景分析
應用益生菌對呼吸系統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已有文獻報道[46-47]。使用益生菌或益生元防治兒童哮喘已開展了多項隨機對照試驗(RCT)。2020 年一項薈萃分析顯示,應用益生菌可以顯著降低特應性哮喘嬰兒的喘息發生率[48]。此外,應用雙歧桿菌和乳酸乳球菌(Lactococcus lactis)能夠誘導產生IL-10,并參與抑制Th2 細胞因子IL-5 和白介素13(IL-13)的表達[49-51],這些免疫細胞因子的改變有助于預防或治療過敏性哮喘。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在產前或產后使用乳桿菌(Lactobacillus)和雙歧桿菌對兒童哮喘發生率無顯著影響[49,52-62]。動物研究中,口服鼠李糖乳桿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63-64]、羅伊氏乳桿菌(Lactobacillusreuteri)[65]、副干酪乳桿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66]和雙歧桿菌[63]已被證實能夠減輕哮喘小鼠的肺部損傷,其主要機制是通過促進Treg 細胞和Th1 細胞的活性,從而發揮保護性免疫作用[63,67]。在OVA 誘導的小鼠哮喘模型中,益生菌降低了血清中特異性IgE 水平,減少了支氣管肺泡灌洗液和血清中炎性Th2 細胞數量[68]。使用乳酸乳球菌NZ9000 減少了OVA誘導的哮喘大鼠支氣管肺泡腔中嗜酸粒細胞的浸潤,并降低了肺組織中IL-4 和IL-5 的表達以及血清中特異性IgE 的水平[69]。此外,益生菌對呼吸道病毒感染的保護作用在大量動物模型中已被證實,其主要機制是通過誘導相關抗體的產生[70]、提高自然殺傷細胞的活性[71]、分泌Ⅰ型干擾素和INF-γ[71-72],以及誘導生成具有抗炎作用的細胞因子如IL-10[73],發揮免疫調節作用。盡管諸多研究證明了,腸道菌群在調節免疫反應和預防過敏性哮喘方面具有較大潛力,但應用益生菌進行哮喘治療的可行性以及有效性仍需深入探索。
4 展望
近20 年的研究使人們對腸道微生物在肺部疾病中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認識,并明確了兒童哮喘發生發展與腸道微生物的密切關系,例如毛螺菌、瘤胃球菌、韋榮氏菌、糞桿菌和羅斯氏菌、雙歧桿菌、阿克曼菌和糞桿菌在兒童腸道內豐度相對較低,且念珠菌和紅酵母相對豐度較高時兒童特應性哮喘風險升高[4,6]。腸道菌群結構特征的改變將導致包括LPS、短鏈脂肪酸、氨基酸和膽汁酸在內的腸道細菌代謝產物含量變化,而這些代謝產物均已被證實能夠作為內源性小分子參與哮喘疾病的發生,主要調控機制涉及了Th1/Th2 平衡、肺部免疫因子釋放以及調節型T 淋巴細胞肺部遷移。但目前仍未開發出具體的預防和治療策略,提示仍需通過更為深入的研究來發掘兒童哮喘和腸道微生物的深層聯系。此外,腸道微生物的代謝物在兒童過敏性哮喘中的應用也值得研究和探討。雖然使用益生菌具有防治過敏性哮喘的巨大潛力,但只有明確哮喘發生時腸道菌群的具體變化和調控機制,以及益生菌菌株和益生元類型,才能夠合理的使用益生菌對抗哮喘導致的特定菌群失調。
作者貢獻:崔天怡進行文章構思與設計,文獻查詢,論文撰寫;劉佳蕊、呂彬進行了論文的修訂,英文摘要的修訂;高秀梅進行了文章質量控制;趙鑫負責文章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