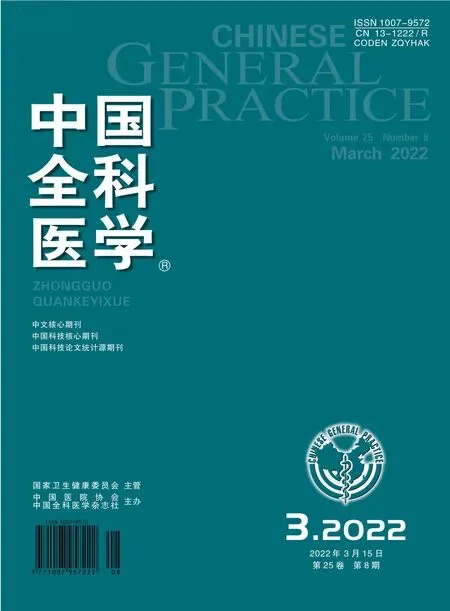兒童康復相關發育性疾病的命名現狀與建議
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康復學組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及醫療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既往嚴重威脅兒童健康的感染性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顯著降低,新生兒死亡率也顯著下降,我國人口疾病譜已發生很大變化,高危兒、發育遲緩、全面性發育遲緩(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GDD)、語言障礙、智力障礙、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等疾病也逐漸成為影響我國人口質量的重大致殘性疾病。科學和精準的診斷是早期、有效康復干預治療該類疾病的前提。目前國內對這些疾病的診斷和命名暫無統一標準,異質性也較大,導致兒童家長對疾病的理解有一定困難,未能正確認識疾病和介入干預,臨床專業人員也很難進行同質化交流。兒童早期是神經細胞發揮可塑性和代償潛能的最佳時期,也是生長發育的關鍵時期,兒童早期的發展直接影響成人時期的生命健康狀況,為了規范我國兒童康復相關發育性疾病的診斷和命名,中華醫學會兒科學分會康復學組組織相關專家多次討論,并結合我國目前實際情況制定如下建議。
1 高危兒
高危兒主要是指早產兒、有特殊保健需求或需要某種形式的支持性技術的嬰兒、因為家庭問題而處于危險之中的嬰兒、預期會早亡的嬰兒[1]。而我國兒童康復領域中的高危兒,目前主要特指腦性癱瘓(簡稱腦癱)高危兒(infant at high risk of cerebral palsy,IHRCP)和孤獨癥譜系障礙高危兒(infant at high risk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IHRASD)。
1.1 IHRCP IHRCP是臨床懷疑腦癱但不能確診時,在確診前使用的過渡性診斷,其中診斷為IHRCP 必須存在運動障礙,并且符合至少一項附加標準,即顱腦磁共振成像異常或腦癱風險臨床病史[2-4]。IHRCP 常用于1 歲以內具有異常表現的嬰幼兒,他們尚不足以診斷為腦癱,但有較大概率發展為腦癱,經過早期干預或可能改變其預后。在糾正胎齡5 個月之前,最能預測腦癱風險的工具是磁共振成像(靈敏度為86%~89%)、全身運動質量評估(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general movements,GMs)(靈敏度為98%)和Hammersmith 嬰兒神經系統檢查(靈敏度為90%)。在糾正胎齡5 個月后,最能預測風險的工具是磁共振成像(靈敏度為86%~89%)(在安全可行的情況下)、Hammersmith 嬰兒神經系統檢查(靈敏度為90%)和幼兒發育評估(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of young children,DAYC)(83% C 指數)[4]。
1.2 IHRASD IHRASD 是指存在一定交流障礙、語言發育遲緩或障礙、興趣狹窄、刻板行為等臨床表現,不能用發育遲緩或其他精神疾病解釋,達不到ASD 的診斷標準,但極有可能發展為ASD[3,5-6]。目前ICD-11、DSM-5 尚未收錄此診斷。這類兒童大多在母孕期、圍生期及嬰幼兒時期暴露過高危因素,包括孤獨癥家族史、胎次、母親情緒、產程、窒息、養育環境等。該類兒童早期表現出ASD 的特征性表現,如眼神交流少、對聲音或表情反應差、行為刻板、興趣狹窄、缺乏共同注意等,但又未達到ASD 的診斷標準。目前ASD 全球患病率呈上升趨勢,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3 歲以下是IHRASD 的康復黃金期,一旦診斷為IHRASD 需立即進行早期干預,早期干預可阻止IHRASD 向ASD 發展或減輕ASD 的嚴重程度[7-8]。
美國兒科協會認為對18~24 月齡的兒童進行篩查可有助于早期發現、早期干預IHRASD[9],常用的一級早期篩查工具有改良的嬰幼兒孤獨癥量 表(Modified 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M-CHAT)、量化的嬰幼兒孤獨癥量表(Quantitative 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Q-CHAT)、 嬰 幼兒溝通及象征性行為發展量表(Communication and Symbolic Behavior Scales,CSBS)等,二級篩查工具有幼兒期孤獨癥篩查工具(Screening tool for Autism in Toddlers,STAT)等[10-11]。
專家建議:(1)對于具有腦癱高危因素,1 歲前存在一定程度的運動功能障礙和姿勢異常,但目前還不足以診斷為腦癱,而又有發展為腦癱潛在風險的嬰幼兒可將其診斷為IHRCP。嬰幼兒時期是神經發育的關鍵時期,也是發揮大腦可塑性的最佳時期,因此部分患兒經早期康復干預后可追趕上正常兒童的發育水平,也有部分患兒發展為腦癱、全面性發育遲緩或智力障礙。家長和醫生對這類兒童應予以重視,及早對該類患兒進行康復干預,最大限度地減輕其功能障礙[12]。(2)對于有/沒有孕期、圍生期、新生兒期及嬰幼兒期高危因素,有/沒有家長自閉癥指數偏高,有/沒有養育照護問題,主要表現為社會交往障礙和行為問題(刻板行為、興趣狹窄、缺乏共同關注)但達不到DSM-5 中ASD 診斷標準的兒童,可將其診斷為孤獨癥譜系障礙高危兒。3 歲以下是IHRASD 的康復黃金期,一旦診斷為IHRASD應該立即進行早期干預。此診斷既能夠引起家長的高度重視,使患兒及時得到康復干預,改善其臨床癥狀和遠期結局,同時此診斷可以給醫生、家長及兒童一定的時間進行追蹤隨訪并進一步精準診斷,而非一錘定音,將該類兒童標簽化,引起家庭的恐慌。
2 發育遲緩
發育遲緩(developmental delay)是兒童廣泛發育遲緩表型的一種描述,必須使用與發育落后相關的因素來加以說明,其本身并不是一種診斷,而是臨床上使用的一個分類、說明性術語[13]。ICD-11 中對發育遲緩的描述是指粗大運動、精細運動和社交等的標志性發育指標/里程碑未達到預期正常生理發育水平。發育遲緩還包括在排除厭食癥、限制性食物攝入障礙和重癥疾病等的情況下,體質量或體質量增長率明顯低于其他同年齡和同性別兒童的體格發育延遲[3,14]。發育遲緩可以表現為特定的某一能區,如運動發育遲緩、語言發育遲緩、認知發育遲緩及社交、情感和行為發育遲緩;也可以是累及多個能區,如GDD。發育遲緩的病因是多因素的,絕大多數發育遲緩的病因是特發性的。已知的病因包括遺傳、環境和/或社會心理因素。發育遲緩應與發育障礙(developmental disorders)相互鑒別,發育障礙是一組范圍較大的綜合征,其典型的發育順序或模式因發育的延遲和/或發育過程的偏差而中斷,盡管有早期篩查策略,但仍有大量存在發育障礙的兒童未被診斷和治療[13]。對發育遲緩進行有效的早期識別和及時的早期干預可以積極地改變孩子的長期軌跡[15-16]。建議在所有健康兒童就診時進行監測,并在9 個月、18 個月和24 或30 個月時使用標準化發育篩查工具篩查發育遲緩[17-18]。目前推薦使用父母對孩子發展狀況的評價(Parents' 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al Status,PEDS)和年齡與發育進程問卷(Ages and Stages Questionnaire,ASQ)進行早期篩查[19-20]。
專家建議:發育遲緩(developmental delay)與發育障礙(developmental disorders)簡稱都是“DD”,但兩者含義不同,臨床上為了防止混淆,不建議使用“DD”這一縮寫。發育遲緩是指與正常發育的兒童相比,他們在一個或多個領域達到里程碑或獲得技能的時間明顯延遲。發育遲緩描述了兒童發育過程異常這一癥狀,是一種過渡性命名。發育遲緩患兒通過早期干預可能發育為正常兒童,也可能轉歸為智力障礙或發育障礙。兒童的發育具有個體性和不均衡性,對存在發育遲緩的患兒,需要針對性早期干預及動態評估,以改善其預后。
3 GDD
GDD 影響1%~3%的5 歲以下兒童[21]。GDD 的診斷標準為:大運動或精細運動、語言、認知、社交和社會適應能力等至少兩個發育能區的顯著延遲(低于標準測試的平均值至少2 個標準差);年齡<5 歲;同時必須滿足以下3 個條件:(1)智力功能缺陷,如推理、解決問題、計劃、抽象思維、判斷、學術學習和經驗學習功能缺陷,并且被臨床評估和個性化、標準化的智力測試所證實;(2)適應功能缺陷導致無法達到個人獨立、社會責任的發展和社會文化標準。如果沒有持續的支持,適應性缺陷會限制日常生活中一項或多項活動的功能,如交流、社會參與和獨立生活等,涉及多個生活環境,如家庭、學校、工作和社區;(3)在發育期間出現智力和適應性缺陷[22]。
GDD 與ICD-11 疾病編碼分類中的暫時性智力發育障礙診斷內容基本相符,但暫時性智力發育障礙的診斷年齡為4 歲以下,并且需要增加個體因感覺或軀體障礙(如失明、學語前聾)和運動障礙等影響智力功能和社會適應性行為的有效評估[14]。
專家建議:GDD 專用于5 歲以下兒童,適用于在智力功能的若干方面無法達到預期的發育標志的患兒,并且適用于無法接受系統性智力功能評估,包括因年齡太小而無法參與標準化測試的兒童[23]。因此,對于符合診斷標準的兒童,建議年齡<5 歲時統一使用GDD 的診斷標準,≥5 歲統一使用智力障礙的診斷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GDD 兒童會發展為智力障礙,因此需要對GDD 患兒進行動態隨訪。
4 語言障礙
語言障礙(Language disorder)在DSM-5 中的描述主要包括:(1)對語言的綜合理解或運用中存在困難,包括詞匯量減少、句式結構局限和論述缺陷;(2)語言能力明顯低于同齡正常兒童,導致有效的交流、社交參與、學業或工作等方面出現障礙;(3)癥狀發生在發育早期;(4)需排除聽覺或者其他感覺損傷、運動功能失調或其他軀體疾病或神經疾病,也不能用智力障礙或全面性發育遲緩來解釋[23]。ICD-11 將ICD-10 中的“特定性言語和語言發育障礙”修訂為“發育性言語或語言障礙”,是ICD-11 中神經發育障礙的一種重要類型。發育性言語或語言障礙的特點是難以理解或使用言語和語言,超出了相應年齡和智力功能水平的正常變化范圍,不能歸因于社會或文化因素,也不能通過解剖學或神經系統異常來解釋,并且發生在兒童發育階段[14,24]。
專家建議:語言障礙不僅對兒童的語言理解及語言表達能力造成嚴重影響,嚴重者還會危害兒童的認知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及神經心理發育等[24]。語言障礙的診斷應基于對個體病史、不同環境中(家庭、學校或社會)直接的臨床觀察和可用于協助診斷的語言能力標準化分數等方面的綜合考慮。由于大部分家長對兒童語言障礙缺乏足夠的敏感性,對兒童的語言表達能力也缺乏足夠的重視,造成了部分兒童的語言障礙未能得到及時發現和早期干預。
5 智力障礙
DSM-5 將DSM-4 中的精神發育遲滯(mental retardation,MR)改為智力障礙,并定義為:在發育階段發生的障礙,包括智力和適應功能缺陷,表現在概念、社交實用的領域中[23]。診斷需同時符合以下3 項標準:(1)功能缺陷發生在發育階段;(2)總體智能缺陷:包括推理、解決問題、計劃、抽象思維、判斷、學業和經驗學習等方面的缺陷,并由臨床評估及個體化、標準化的智力測試確認。智能缺陷通常對應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低于平均值2個標準差;(3)適應功能缺陷:是指適應功能未能達到保持個人的獨立性、完成社會責任所需的發育水平和社會文化標準,并需要持續的支持。在沒有持續支持的情況下,適應缺陷將導致患兒一項或多項日常生活能力(如交流、社會參與和獨立生活)受限,且發生在多個環境中,如家庭、學校、工作和社區。根據疾病的嚴重程度,分別診斷為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GDD、未特指的智力障礙[23]。
ICD-11 將ICD-10 的智力發育遲緩重新命名為智力發展障礙,智力發展障礙的定義仍然是基于智力功能和適應性行為方面的重大限制,理想的是通過標準化、適當規范和個別實施的措施來確定[25]。由于許多地區缺乏適合當地的標準化措施或相關專業人員來實施這些措施,并且確定治療計劃至關重要,因此國際疾病分類ICD-11 還提供了一套全面的行為指標表[26]。智力功能和適應性行為功能領域(概念上的、社會上的、實踐上的)分別根據3 個年齡組(幼兒期、兒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期)和4 個嚴重程度(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進行分類。行為指標描述了這些類別中可觀察到的技能和能力,預計將提高主要特征描述的可靠性,并改善與智力發展障礙相關的公共衛生數據[14]。
專家建議:對智力障礙的診斷應基于病史、臨床表現、臨床評估及標準化的智力和適應功能測評,智力障礙一般起病于發育階段,起病年齡和典型特征基于大腦功能失調的病因和嚴重程度,嚴重智力障礙個體可在2 歲以前識別出運動、語言和社交等方面的發育指標延遲,而輕度智力障礙的個體直到學齡期、學習困難變得明顯時才能被識別。ICD-11 的診斷多為描述性,更傾向于診斷指南,DSM-5 診斷均是分條目列出的,可操作性比較強,更傾向于診斷標準。不論是ICD-11 還是DSM-5,都不能僅僅以智商分數來下診斷,還需要結合其適應能力進行綜合判斷,建議今后不再使用精神發育遲滯這個診斷。
6 ASD
ASD 是一組以社會交往、交流障礙和興趣或活動范圍狹窄及重復刻板行為核心特征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27]。DSM-5 中,ASD 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其中包括典型的孤獨癥障礙、Rett's 綜合征、阿斯伯格綜合征、童年瓦解性障礙和未區分的廣泛性發育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PDD-NOS)。DSM-5 以社會交往、交流障礙和興趣或活動范圍狹窄及重復刻板行為這兩個核心特征為ASD 的診斷標準[23]。在ICD-10 中,PDD-NOS 包括孤獨癥、阿斯伯格綜合征、雷特綜合征、童年瓦解性障礙、未特指的PDD-NOS 等。但在ICD-11 中,這些疾病已不再被認為是獨立的疾病實體,而是一類譜系障礙,即ASD,是單一類別的疾病,其特征是社會交流缺陷和行為、興趣或活動受限、重復和僵化模式[14,24]。ICD-11 和DSM-5 將ASD 的核心癥狀分為兩大領域,即社交互動與交流能力的持續性缺陷和受限的、重復的行為模式、興趣或活動。ASD 的診斷性量表包括兒童孤獨癥評定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CARS)、孤獨癥診斷訪談量表修訂版(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ADI-R)、孤獨癥診斷觀察量表(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ADOS)等[28-29]。
專家建議:ASD 的基本特征是交互性社交交流和社交互動的持續損害和受限的、重復的行為、興趣或活動模式,這些癥狀從兒童早期出現,并限制和損害了日常功能。對ASD 的診斷需要遵從DSM-5 的診斷標準,結合詳細的病史記錄、診斷性的評估結果及臨床中功能性損害的狀況等進行綜合分析。因很大一部分患者就診時主訴為語言發育落后或倒退,所以應注意ASD 與語言遲緩或障礙之間的鑒別,并關注患者社交行為與智力發育水平的不平衡性、家庭養育環境和方式,動態觀察患者在不同環境和條件下的行為表現[30-31]。
7 發育性協調障礙(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DCD)
DCD 是指由于運動功能發育障礙影響日常生活和學習的一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32]。DCD 的發生主要是由于大腦皮質、基底核、頂葉等部位對運動的處理過程出現障礙引起運動模式的改變,使大腦發出的運動信號不能準確達到肢體,導致運動協調出現障礙,最終影響日常生活和學習工作。DSM-5 對DCD 的定義是:(1)協調運動技能的獲得和使用顯著低于基于個體的生理年齡和技能的學習及使用機會的預期水平。其困難表現為動作笨拙(例如,跌倒或碰撞到物體)以及運動技能的緩慢和不精確(例如,抓一個物體、用剪刀或刀叉、寫字、騎自行車或參加體育運動);(2)前述的運動技能缺陷顯著、持續地干擾了與生理年齡相應的日常生活活動(如自我照顧和自我維護),以及影響學業/學習成績,就業前教育和職業活動,休閑、玩耍;(3)癥狀發生于發育早期;(4)運動技能的缺陷不能用智力障礙(智力發育障礙)或視覺損害來解釋,也并非是某種神經疾病影響了運動功能(如腦癱、肌營養不良、退行性疾病)[23]。
專家建議:診斷DCD 需要臨床上對病史、體格檢查、影像學檢查和標準化測評進行個體化的綜合評估。診斷該類患兒,首先要排除其他疾病導致的運動協調能力障礙,如腦癱、肌營養不良和神經肌肉病等。其次,根據病史了解是否存在導致發育性運動協調障礙的高危因素,這需要結合影像學檢查和康復評估才能明確。康復評估包括兒童標準運動協調能力評估測試(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MABC)和發育性協調障礙問卷(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Disorder Questionnaire,DCDQ)等[33]。由于早產兒的DCD 發病率較高,因此應密切關注該類兒童,預防DCD 的發生發展。
8 小結
兒童康復相關發育性疾病的命名現狀與建議以兒童年齡為基礎,以臨床核心癥狀和病種傾向為主要依據來進行劃分,如1 歲前以運動落后、姿勢異常和肌張力異常等為核心癥狀可診斷為IHRCP;3 歲以前以社會交往、行為異常和語言落后為核心癥狀的可診斷為IHRASD,以區別于單純的語言發育遲緩;3 歲以后符合ASD 診斷標準的可診斷為ASD;5 歲以前以單一能區落后為主要表現可診斷為該能區特定性發育遲緩,而多能區均表現出落后則可診斷為GDD;5 歲以后可根據核心癥狀診斷為智力障礙等。但不排除符合相關疾病診斷標準的非年齡劃分的早期和超早期診斷。此外,對兒童康復中相關發育性疾病的診斷通常需要一個團隊進行長期動態隨訪,包括基層兒童保健人員、兒童康復專家、發育行為兒科專家、兒科神經、精神病學專家等。對發育相關性疾病的規范診斷是為了突出核心問題,為兒童的早期轉介及康復干預做指引,而非添加“標簽”。一個完整準確的疾病診斷命名應基于患兒的臨床癥狀、年齡、病史、體格檢查以及輔助檢查等,同時還應結合患兒家庭成員的心理狀況及文化程度、家庭養育照護環境和社會環境,盡可能做到全面、客觀和準確。
制定專家組成員(按單位首字筆畫排序):
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徐開壽,唐紅梅,李金玲);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杜青);天津市兒童醫院(趙澎);長春市兒童醫院(吳秀麗);寧波市康復醫院(謝鴻翔);西安交通大學附屬兒童醫院,西安市兒童醫院(陳艷妮);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武漢兒童醫院(林俊);成都市第一人民醫院(孔勉);蘇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顧琴);沈陽市兒童醫院(商淑云);昆明市兒童醫院,昆明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劉蕓,馬靜,何雪梅);鄭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朱登納);鄭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河南省兒童醫院(尚清);青島大學附屬青島市婦女兒童醫院(候梅);青海省婦女兒童醫院(金紅芳);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肖農);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呂忠禮);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張躍);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李海峰);深圳市兒童醫院(曹建國);銀川市第一人民醫院(郝會芳);湖南省兒童醫院(胡繼紅);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李同歡)。
本共識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