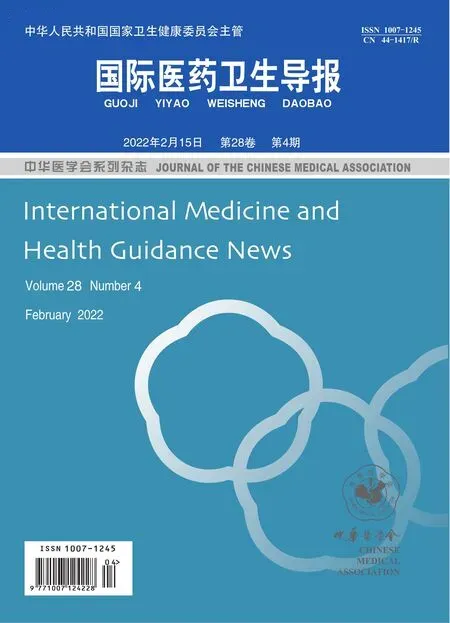棍針治療頸源性眩暈的臨床觀察
黃詩 雷智 周雙武 李華峰 梁文 譚永振
1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中醫科,廣州 510260;2廣州醫科大學第二臨床學院,廣州 511436
頸源性眩暈屬于臨床一類常見病,能為椎動脈、本體感覺與交感神經等多類因素引發,近年來患病人數不斷增多,且發病呈現年輕化趨勢。眩暈是疾病的主要表現,以晨起發病較為多見,眩暈能呈現慢性持續性,也能表現為發作性劇烈眩暈,患者可伴隨精神萎靡、耳鳴耳聾、惡心嘔吐、乏力嗜睡以及視力下降等癥狀,嚴重影響其日常工作及生活[1]。西醫多采取藥物或者手術治療,其中藥物治療雖能改善患者癥狀,但存在一定不良反應;手術可徹底消除癥狀,但較多老年患者的耐受性較差,且術后易復發。祖國傳統醫學認為,疾病多是風寒濕邪入侵頸椎內部,使局部經絡閉塞進而發病[2]。棍針、小針刀作為2類中醫特色治療方法,可舒筋通絡,促使氣血流通,進而發揮良好療效。本文對2019年3月至2021年7月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收治的頸源性眩暈患者320例開展研究,分析不同中醫療法對該類患者的療效,現報道如下。
資料與方法
1、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3月至2021年7月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收治的頸源性眩暈患者320例為研究對象,依據隨機數字表法將其分為兩組,各160例。對照組男89例、女71例,年齡為45~68(53.25±6.78)歲,病程為1~15(10.14±3.28)年。觀察組男92例、女68例,年齡為46~70(53.40±6.20)歲,病程為1~16(10.20±2.35)年。均自愿參與此次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診斷標準:依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3]有關標準開展診斷。(1)存在眩暈,伴隨惡心或嘔吐,頭部疼痛,心悸,視物模糊;(2)或伴隨頭位性猝倒,于短時間中能自主站立行走;(3)頸部活動受限,存在酸脹疼痛感,頭頸活動時癥狀能加重;(4)存在風寒、外傷或慢性勞損史;(5)X線、CT、椎動脈造影等檢查均有類似本病的異常表現。兩組頸源性眩暈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2、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均與疾病的診斷標準相符;(2)年齡≥18歲。排除標準:(1)非頸源性眩暈者;(2)存在重度腦血管病、急性傳染病或者惡性腫瘤者;(3)過敏體質者;(4)處在妊娠或者哺乳階段女性。
3、方法
(1)對照組開展小針刀治療,操作方法如下:指導患者采用俯臥位,于其胸部墊上一個軟枕,盡量使頭部維持屈曲位,充分暴露出頸枕部,采取風池穴和上下大約2.0 cm位置的壓痛點(上點為枕骨粗隆中心旁開大約3.5 cm位置,下點為C1椎體的橫突尖部)、C2椎體的棘突尖當作定位點,常規開展消毒鋪巾處理,使針刀和頸椎軸線之間呈25°~30°平角進針直至骨面,縱向開展2~3次疏通,橫向開展2~3刀剝離,進行1~2刀切割,單次需治療2~3個治療點,做好消毒紗布或者創可貼貼敷后,局部進行2~3 min按壓,同時頭前屈輕輕加壓開展牽引,治療結束。間隔3~5 d開展1次治療,2~3次為1個療程,共治療1個療程。注意針刀治療過程中于針刀至枕骨骨面和橫突骨面之后,需要控制好操作深度和角度,防止刺進寰枕關節腔和橫突以下,對神經血管、延腦和脊髓產生損傷,危及患者生命。(2)觀察組開展棍針治療,操作方法如下:消毒后采取棍針的粗錐端對重點穴位開展小步式推撥,從輕至重,找準病筋,采取棍針于痛點重推重撥,經過的穴位依次是兩側攢竹穴、魚腰穴、頭維穴、太陽穴、率谷穴以及風池穴;印堂穴、神庭穴、前頂穴、百會穴以及腦戶穴。由眉毛起往前發際方向開展推撥,由前額正中往兩側發際撥行,從前發際往后枕部撥行,各部位操作5 min,將未產生血痕為度。間隔3 d開展1次治療,共治療3次。
4、觀察指標
(1)眩暈改善程度。分別在兩組結束治療后開展眩暈改善程度評定,將眩暈癥狀積分下降>70%為顯效;將眩暈癥狀積分下降50%~70%為好轉;將眩暈癥狀積分下降不足50%或者增加為無效[4]。統計兩組顯效及好轉比例即為總有效率。(2)疼痛。分別在治療前和結束治療后經視覺模擬評分量表(VAS)對兩組頸肩部和頭部疼痛程度開展評估,得分范圍為0~10分,由患者自主評定,最終得分越高,即疼痛越明顯[5]。(3)上肢麻木程度。分別在治療前和結束治療后對兩組單側或雙側上肢麻木程度開展評分,采取目測比類法開展評定,用一條長度10 cm帶刻度直線,兩端依次代表無麻木、劇烈麻木,患者于其中劃線表示麻木程度,結合所劃刻度換算成0~10分,分數越高,即麻木癥狀越嚴重。
5、統計學方法
經SPSS23.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計數資料以例(%)表示,行χ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行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行配對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臨床療效比較
對照組的眩暈改善有效率為98.13%(157/160),高于觀察組80.63%(129/16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5.800,P<0.05),詳見表1。

表1 兩組頸源性眩暈患者臨床療效比較[例(%)]
2、治療前后頸肩部及頭部VAS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頸源性眩暈患者頸肩部及頭部VA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治療后,兩組的頸肩部及頭部VAS評分均較治療前降低,且觀察組頸肩部及頭部疼痛評分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詳見表2。
表2 兩組頸源性眩暈患者治療前后頸肩部及頭部VAS評分比較(分,±s)

表2 兩組頸源性眩暈患者治療前后頸肩部及頭部VAS評分比較(分,±s)
注:對照組開展小針刀治療,觀察組開展棍針治療;VAS為視覺模擬評分量表
組別觀察組對照組t值P值例數160 160頸肩部治療前6.40±1.52 6.35±1.58 0.288 0.773治療后1.48±0.38 2.98±0.40 34.390<0.001 t值39.075 26.151 P值<0.001<0.001頭部治療前2.68±0.90 2.70±0.85 0.204 0.838治療后0.82±0.20 1.58±0.22 32.333<0.001 t值25.519 16.135 P值<0.001<0.001
3、治療前后上肢麻木評分比較
兩組頸源性眩暈患者治療前后上肢麻木評分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治療后,兩組上肢麻木評分較治療前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詳見表3。
表3 兩組頸源性眩暈患者治療前后上肢麻木評分比較(分,±s)

表3 兩組頸源性眩暈患者治療前后上肢麻木評分比較(分,±s)
注:對照組開展小針刀治療,觀察組開展棍針治療
組別觀察組對照組t值P值例數160 160治療前5.40±1.35 5.32±1.48 0.505 0.614治療后1.90±0.58 1.94±0.52 0.650 0.516 t值30.131 27.254 P值<0.001<0.001
討 論
頸源性眩暈即頸源性因素導致的眩暈綜合征,癥狀復雜且復發率較高,會對患者日常工作和生活產生嚴重影響。中醫學上將該病劃分到眩暈的范疇,認為疾病是風、痰、虛等因素引發,多屬虛實夾雜,于外邪入侵后,邪入空竅,侵犯腦絡,導致肝膽失調和肝氣上逆,或因氣血虧虛、腦海空虛等使得精血不能上承腦竅,最終引發眩暈。再加上姿勢不良和外傷等使得頸部肌肉群勞損進而導致痙攣水腫和脈絡瘀阻。內外因素一同作用導致頸椎生理失去平衡,使得筋失其和、骨失其位,患者最終因血瘀氣滯、筋脈痹阻、氣機升降失常產生疾病[6]。
任耀龍和黃景峰[7]發現,小針刀加推拿對頸源性眩暈有著理想療效,能減輕患者的疼痛感,改善其頸部血流動力學。蘇瑟琴等[8]發現,予以頸源性眩暈者針刺結合棍針治療能夠改善血流動力學指標,緩解眩暈癥狀。但當前有關小針刀、棍針對頸源性眩暈的療效對比研究較少。本次研究的創新之處在于對比兩類療法對頸源性眩暈的療效,結果顯示,治療后對照組的眩暈改善有效率比觀察組高,觀察組頸肩部及頭部疼痛評分比對照組低,兩組上肢麻木評分改善幅度相當,這說明棍針治療對頸肩部疼痛和頭痛癥狀的改善效果更佳,小針刀治療對于眩暈癥狀的改善效果更佳,2種療法均能改善上肢麻木癥狀。經小針刀治療能使頸椎的生物力學重新恢復到平衡狀態,經小針刀松解局部組織,能使組織張力下降,進而恢復頸部組織力學平衡,促進頸部的血液循環,改善腦部血運,進而緩解患者的眩暈癥狀[9-10]。棍針治療采取牛角加工而成小棍的粗錐端對局部開展推撥,能調節機體的抗病能力,改善施術部位的血液循環,加快局部的新陳代謝,起到醒腦開竅、活血行氣和舒筋通絡效果,減輕患者頸肩部和頭部疼痛感[11]。
綜上所述,就頸源性眩暈患者而言,采取棍針治療對頸肩部疼痛和頭痛癥狀有著良好療效,小針刀治療對于眩暈癥狀有著良好療效,2種療法均能改善上肢麻木癥狀,臨床可結合實際情況合理選擇相應的治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