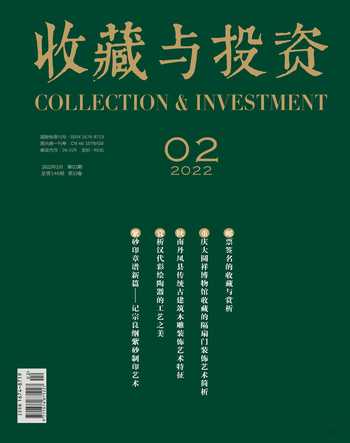沈銓鶴題材繪畫研究
摘要:清代花鳥畫家沈銓,歷康雍乾三朝,遠師宋明院體畫,近取明清諸家所長,兼具時代特色。沈銓以畫翎毛、花卉見長,對清代畫壇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他的花鳥畫作品中,尤以鶴題材繪畫最為畫史推崇。鶴是具有祥瑞、長壽等美好寓意的祥禽,多見于繪畫。本文首先對鶴文化進行溯源,其次對沈銓鶴題材繪畫的象征寓意等方面展開研究,揭示沈銓鶴題材繪畫的內涵與影響。
關鍵詞:沈銓;鶴繪畫;象征寓意;南蘋畫派
一、沈銓鶴題材繪畫源流
(一)沈銓生平及師承畫風
清代畫家沈銓,字南蘋,號衡之,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今浙江德清人。畫史對于沈銓卒年說法不一,一說1752年,另說1750年。沈銓自幼家貧,隨父親學習紙扎,20歲左右拜師胡湄,專事繪藝,并以此為生。胡湄是著名收藏家項元汴的外孫,項元汴家藏頗豐,胡湄有條件接觸并臨摹歷代諸家真跡。通過不斷地臨摹古人作品,胡湄所繪制的花鳥不僅能得古人畫作之形,更能傳古人畫作之神,可謂形神兼備、栩栩如生,時稱“仙筆”。沈銓與諸家畫風均不同,但又博采眾家之長,將花鳥與山水結為一體,意境幽遠。沈銓作品包羅萬象,師古不泥,得古人之神韻而又自成面目。《清史稿》記載沈銓“工寫花鳥,專精設色,妍麗絕人”。沈銓一生繪制作品多為工筆,被召入宮后大量繪制設色艷麗、比例嚴謹的院體工筆花鳥畫,其中尤以鶴題材居多,一方面是為了迎合皇家審美,延續宮廷畫風;另一方面,乾隆皇帝也將繪畫作為籠絡人心的工具,傳達長治久安,臣民順服的心愿。
(二)沈銓鶴題材繪畫的源流
沈銓既跟隨胡湄學習繪畫,又繼承明代院體畫家呂紀的繪畫風格。今故宮博物院藏《松梅雙鶴》款識云:“乾隆己卯秋,衡齋沈銓法呂指揮筆,時年七十有八。”呂紀(1429—1505年)是明代宮廷院體畫家,深得明孝宗賞識。他曾臨摹唐宋以來的名畫名作,練就了扎實的技法,其繪畫作品被后世譽為“妙品”。呂紀擅繪翎毛,其傳世畫作《梅鶴圖》《瑞鶴圖》等皆有法有度、妍麗厚重、生動傳神。
沈銓在描繪鶴時,不單單描繪“鶴”這一個體,而是通過配景來襯托鶴,渲染整幅作品的意境,而這些配景又采用多種繪畫手法。沈銓作于乾隆己卯年(1759年)的《松梅雙鶴》中,雙鶴的配景有蒼松、古梅、百兩金和山石。沈銓采用兩種風格描繪四種不同的配景:百兩金采用沒骨畫法;蒼松、古梅和山石則是學習南宋院體花鳥山水畫,繼承南宋院體繪畫的寧靜淡雅。沈銓的鶴題材作品集眾家之長于一身。
二、沈銓鶴題材繪畫文化與藝術分析
(一)鶴原型與鶴文化考述
鶴在中國文化中備受推崇,無論是帝王貴族還是平民百姓,都將鶴視為一種祥瑞。從最早的巖畫到后來的青銅器,再到雕塑、國畫和文學作品,鶴都被賦予了吉祥、長壽、堅貞的美好寓意。鶴體態優美、身姿優雅、超逸出塵,無論是翔鶴、鳴鶴還是舞鶴,都給人以美的視覺感受。故而從古至今,鶴自然而然地成為藝術家、文學家的描繪對象。
鶴的壽命比一般的禽類要長,普遍在50~60年。鶴的飛行速度較快,且飛得較高,在禽類中罕見。因此古人抓住鶴長壽、高飛兩大特征,賦予了鶴神話色彩,認為鶴是長壽永生的象征。
鶴的叫聲高亢嘹亮,可以傳到數里以外。《詩經·小雅·鶴鳴》:“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后人取鶴鳴之意,將在野高士稱為鶴鳴之士。《后漢書·楊賜傳》載:“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征鶴鳴之士。”告誡統治者遠離奸佞滑巧之臣,招募德才兼備之士。鶴由于品質、性格與中國古人的精神追求極為相似,故而深受各個階層的喜愛,為文人所推崇。
鶴的精神品格被不斷地放大,寓意不再僅限于長壽升仙,文人士大夫階層和統治階層更欣賞鶴的高逸瀟灑、忠貞高潔,甚至開始養鶴。宋人林逋于杭州西湖孤山隱居養鶴,終身不娶,以梅花為妻,白鶴為子,過著如白鶴般與世無爭、恬靜自然的生活。
在清代的帝王中,乾隆皇帝最愛鶴。乾隆所作的第一首詩,便是《戲題鶴來軒》。一個擁有廣袤國土的封建帝王,自然不會像文人隱士那樣通過鶴來抒發、排遣內心的苦悶憂郁,而是用鶴宣揚、表現他的“治吏觀”和“治世觀”。清代官吏等級森嚴,通過官員官服前的“補子”來確定官位高低。清代一品文官的補子就是鶴,將鶴作為一品大員的官服補子形象,充分表現了乾隆皇帝的“治吏觀”和“治世觀”:乾隆皇帝希望自己的臣下像鶴一樣,對統治者和國家做到忠心耿耿,肝腦涂地。在自然界中,鶴一生只有一個伴侶,一旦選定配偶,便終身相隨,從一而終。鶴的這一品質完全符合儒家“事君以忠”的主張。另外,清代的滿族統治者為了加強對漢人的統治,更強調忠貞侍主的精神。此外,由于鶴具有長壽、吉祥、安定的美好寓意,康雍乾三朝又是清朝的鼎盛時期,統治者更希望用鶴來表達對國家長治久安、百姓安居樂業、江山永固的美好意愿,同時希望自己也能像鶴一樣長壽。
在以上的演變過程中,鶴形象逐漸由構圖元素變成了畫面的主要表現對象,并和其他圖像配合出現。常與鶴配合出現的有仙桃、松樹、梅花、鹿、龜、靈芝、海波、仙山和祥云等形象。這些生物和景物的組合,使鶴的寓意愈發豐富,也使藝術作品的表現力更強。
(二)沈銓鶴題材繪畫的意義與內涵
這些組合在歷史演進中逐漸約定俗成,廣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故而沈銓在繪畫中大量運用鶴與其他花卉、走獸、翎毛組合的創作方法,來表現吉祥寓意這一主題。
沈銓生于清代最為繁盛的“康乾盛世”,清代帝王藝術修養普遍較高,對書畫喜愛有加,其中不乏“丹青圣手”,尤以乾隆皇帝為最。后來沈銓被召入宮,長期供職于宮廷,成為御用畫家,其大量的鶴題材繪畫也創作于此時。
乾隆皇帝并非只停留于富貴堂皇、奢華威儀、萬壽無疆等普遍的帝王審美特征上,他也具有傳統中國文人恬淡雅致的審美觀念,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雙重審美,沈銓在畫中將二者巧妙結合。作于乾隆己卯年(1759年)的《松梅雙鶴》即為這類作品的代表。
《松梅雙鶴》現藏于故宮博物院。據款識可知,《松梅雙鶴》作于沈銓78歲時。整幅作品以兩只丹頂鶴為主體;蒼松、古梅、修竹和百兩金為襯托,點綴山石、溪流,這些被賦予象征之意且符號化的景物,共同組合成這幅作品。
1759年的乾隆平定了準噶爾、大小和卓叛亂,清代中國的疆域臻于極盛。沈銓在《松梅雙鶴》中用鶴表達吉祥寓意,迎合乾隆在大亂平定后希望國家長治久安、臣民忠順的想法。畫中的松、竹、梅,則迎合乾隆皇帝的文人審美。沈銓敏銳地捕捉了乾隆的心思,巧妙地將乾隆喜愛之物融入畫中,將畫面從客觀反映景物的層面提升到極富寓意的高度。
也正是由于不斷地“揣摩圣意”,沈銓的此類作品流露出極大的功利性,創作趨于程式化,作品題材較為單一且刻板、僵化。其原因有二,一是沈銓出身貧寒,未受過良好的教育,國畫的內涵又往往與畫家的自身修養密不可分。古籍畫論未見沈銓留下的一詩一文,他在畫面上的落款也常為窮款或短題,僅見幾幅書法作品也都是大眾化內容。文學修養的缺失使沈銓的畫作出現了技法精深而內涵淺薄的問題。沈銓供職宮廷并為皇帝作畫,森嚴的等級制度、作畫時誠惶誠恐的心理,往往使他不敢越出固有的作畫法度。沈銓為了迎合皇帝,其畫面中僅出現幾種設色艷麗寓意美好的圖像,雖然在構圖上有疏密之分,設色上有濃淡之別,配景上有品類之別,但整體風格大同小異,未出現明顯變化。如作于乾隆戊寅春(1758年)的《鶴壽圖》和無年款的《雙鶴圖》,風格和構圖都極為接近,只是在配景上有所區別,前者畫面上方繪壽桃,后者在同樣位置只是將壽桃改為花卉,甚至兩幅作品中鶴的狀態都極為相似,有程式化創作的嫌疑。在講求內涵的文人畫盛行時代,這類作品自然被主流畫壇排除在外。二是鶴作為一種候鳥,主要生活在我國東北一帶。在我國古代,鶴并不作為一種可銷售的禽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很難見到。沈銓生活在江南,不在鶴的遷徙路徑上。中國古代的工筆花鳥常用粉本作底稿,鶴在粉本和畫譜中的姿態也只有幾種,沈銓鶴題材繪畫又大量“師法某人”“仿某人筆”,導致其鶴題材繪畫出現了大量雷同,也是環境的局限所致。
三、結論
沈銓從民間進入宮廷,得益于他精深的繪畫技法和自身的努力不懈。沈銓在畫面中把平常的景物上升到了具有祥瑞意義的高度,也將儒家思想所體現的政治意味融入畫面中。沈銓供職宮廷后,在作畫時巧妙地迎合皇帝的心思,為鶴題材的繪畫賦予了多種象征意義,用作品來博得皇家的喜愛。但宮廷森嚴的等級也使沈銓在作畫時過于小心謹慎,不敢隨意創作,導致了沈銓的鶴題材繪畫缺乏更深層次的內涵。沈銓出身于社會底層,作為平民畫家被召入宮,并未在宮中擔任確職。雖然他技法水平高超,深得皇帝賞識,但出身低微、無官無職卻使沈銓難以嶄露頭角,這或許是沈銓很長一段時間湮沒無名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者簡介
廖澤禛,1998年9月生,男,漢族,陜西西安人,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美術學理論專業2021級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美術史。
參考文獻
[1](清)愛新覺羅·弘歷.乾隆御制詩文全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2]周積寅,(日)近藤秀實.沈銓研究[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7.
[3]李曉玲.清代文官補子紋樣的演變[J].藝術設計研究,2015(4):43-51.
[4]劉贏.論道教文化中的鶴崇拜現象[J].安徽文學,2015(1):6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