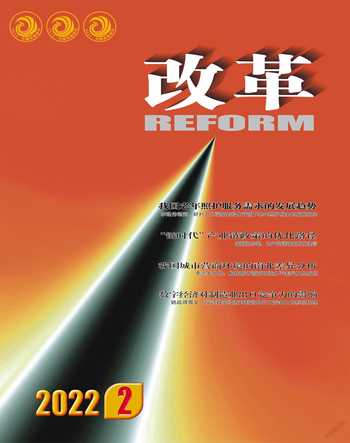財政壓力、支出結構與公共服務質量
詹新宇 王蓉蓉












摘? ?要: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以滿足轄區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財稅體制改革給地方政府帶來的財政壓力,會對其公共服務供給行為產生影響。在測度中國229個地級市公共服務質量與財政壓力的基礎上,構建系統GMM模型,實證分析地方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結果發現:地方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產生了非線性影響,當地方政府承壓超過一定限度時,財政壓力將顯著降低轄區公共服務質量;實證結果因地區、城市規模不同而呈現異質性;不同種類公共服務間的質量差異,源于財政壓力環境下地方政府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的行為。為此,應將財政壓力控制在適度范圍內,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努力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質量相對均衡。
關鍵詞:地方財政壓力;公共服務質量;財政支出結構;系統GMM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543(2022)02-0111-16
地方政府財政壓力通常是指地方政府因財政收入不足而難以滿足財政支出需求所產生的壓力。自2018年中國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以來,一系列舉措不斷“加碼”并密集實施,地方財政壓力驟然增加。2020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和潛在經濟增速下降的雙重沖擊,各種實質性減稅降費政策持續實施,這給地方財政平衡帶來了新的負擔。應對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和財政支出需求剛性增加,必須切實提高財政支出績效,這是財政政策提質增效的根本出路。
公共服務質量與地方財政支出能力及其績效密切相關。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以滿足轄區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財政壓力的增加,對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行為產生的影響如何,是否會累及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這是本文重點關注的問題。本文建立系統GMM模型,考察了2004年以來中國229個地級市財政壓力的公共服務質量效應,并探討了其影響機制。
一、相關文獻綜述
目前鮮有學者將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結合起來探討,但對政府在經濟發展領域的干預、財政收支行為與效率等方面的研究較為豐富,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其在公共服務供給上的行為傾向,即地方政府是否將更多精力放在引導經濟發展以增加財政收入或將更多財力投入非民生性支出領域而懈怠了公共服務的供給責任等。這對本文研究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與本文相關的研究可歸納為以下方面:
一是財政壓力方面的研究。財政壓力沖擊下的地方政府傾向于利用財政“收”與“支”兩個抓手來實現“減壓”。其一,在分稅制改革和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背景下,中國地方政府為履行事權和支出責任,會主動革故鼎新,其收入征收等行為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減少了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為避免或緩解“入不敷出”的狀況,地方政府會選擇加大非所得稅稅收收入的征稅力度,以彌補資金缺口[1],并且根據受沖擊程度選擇加強對制造行業的增值稅征管力度[2]。另外,方紅軍和張軍認為,新財政集權理論揭示了地方政府所承擔的財政壓力引致其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行為傾向,地方政府通過大力發展制造業謀求持久穩定的增值稅等直接收益和土地出讓收入等間接收益[3]。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還通過舉借債務、加大稅收征管力度等方式獲取財政收入,緩沖財政壓力的激增。其二,在支出方面,地方政府也在積極探索路徑。在支出結構上,財政壓力的沖擊使得地方政府產生增加基建支出水平的行為傾向。隨著政府間事權的下移,政府為履行事權而大幅增加的支出,會通過犧牲其他支出甚至是民生性支出的增長為代價,財政支出結構受到的影響也難以短期消除。進一步來說,財政體制改革的急促性將使得公共服務領域的問題惡化[4]。在支出效率上,所得稅改革帶來的財政壓力倒逼地方提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即政府支出效率得以顯著提高[5]。
二是公共服務質量方面的研究。涉及“公共服務質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公共服務質量水平的測度、公共服務質量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等實證性研究,以及基于國外經驗得出公共服務質量系統概念的理論性研究成果等。在公共服務質量或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測度方面,學者們采用不同的方法構建公共服務質量評價或供給效率體系,其中包括熵值法[6]、主成分分析方法[7]和DEA模型[8]等。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城市公共服務質量吸引著人口向城市流動[9],且長期流動的勞動力更傾向于選擇公共服務質量更優的地區[10]。Tiebout的用腳投票理論[11]認為,人們會趨向選擇最符合自己公共產品偏好的地域居住,因此公共服務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了公共服務質量對居民的重要性。部分研究國外公共服務供給和質量管理經驗的學者認為,國外政府在改革中逐漸找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注重疏通供給需求表達通道,不斷優化公共服務質量評價方法,在公共服務改革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12-13]。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既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現實需要,又是落實中國“加力提效”的積極財政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14]。
三是財稅體制改革、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供給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現有文獻就財政支出對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影響已進行較多探討,如王哲等認為,地方政府供給的公共服務與其用于公共服務的財政支出水平存在高度相關關系,而地區間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也離不開地方財政相對支出水平、民生性支出效率以及地方財政支出偏好和結構的作用[15-16]。地方財政壓力更多體現的是財權與事權變化對支出端與收入端的影響,其與公共服務供給的影響關系鏈條要長于財政支出對公共服務的影響,且更能反映地方政府在被動“加壓”和主動“釋壓”情況下自發產生的行為傾向。雖然鮮有文獻直接研究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但已有部分研究聚焦于財稅體制改革、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供給的影響關系上。如傅勇認為,在財政分權體制下,基礎教育質量和城市公用設施這類非經濟性公共物品質量顯著降低[17]。雖然財政分權帶給了地方政府供給公共物品上靈活調整的可能,但面對財政壓力,地方政府更偏向于基礎設施建設,加之公共部門的尋租行為等影響,公共部門供給公共物品的效率進一步偏離。儲德銀和韓一多的研究給出了不一樣的結論,他們發現中國的分權水平對義務教育供給效率呈現非線性影響,認為目前中國的分權水平比最優的分權水平要低,可以通過激勵性的財稅政策使得地方政府不斷釋放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動力[18]。另外,也有學者認為,財政壓力在公共服務領域產生的效應,伴隨著財稅體制改革而得到“催化”。余靖雯等以農業稅的取消為準實驗,研究發現,縣級公共教育供給受到財政壓力帶來的顯著負向影響,且隨著時間的延伸有更突出的長期效果[19]。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重點支出領域將不再要求與生產水平和財政收支掛鉤,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便少了一層約束,但地方政府存在易忽視基本公共服務的傾向,地方財政壓力的增加,會使地方政府顯著減少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
綜合以上文獻可知,地方政府在財政壓力上升時的行為傾向是復雜的,不同的選擇會對公共服務質量產生不同的影響。目前,盡管有學者關注到了財政壓力對財政支出效率、公共教育服務和公共醫療服務供給水平的影響,但對公共服務質量的研究多集中在人口流動與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關系和國外公共服務質量管理的經驗總結上,對財政壓力的公共服務質量效應的研究較少。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地方政府的行為傾向
新財政集權理論為研究財政壓力下地方政府的行為傾向提供了一種解釋路徑,但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具有特殊性,因而應將財政壓力引起的激勵效應和財政分權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職能的履行結合起來,進而分析地方政府在保障公共服務質量方面作出的選擇。
地方政府在面對財政壓力的激增時會傾向于干預經濟發展和調整地區產業結構。在政治晉升和自身財政壓力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地方政府偏向于引進產能過剩企業、房地產企業等來提高稅收水平[20],甚至會放寬環境規制以吸引工業污染企業[21]。地方政府也可能傾向于采用稅式支出的方式扶持相關產業,以達到獨享稅源的目的,這一點在已有研究中得到印證,如在所得稅分享改革之后,交通運輸業、建筑業及房地產等產業的產值得到迅速增長[22]。但是,地方政府在為支持經濟增長而“貢獻”出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稅式支出的過程中,實際上在收緊的財政預算內,留給民生性支出的空間也受到了擠壓,繼而公共服務的供給乃至公共服務質量的保障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圍繞地方政府職能和公共物品供給形成的第一代財政分權理論認為:最優分權程度實際上是異質性和規模經濟相權衡的結果,欲使公共物品供給水平達到最優,需保證公共物品供給差異化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供給公共物品帶來的外部性的邊際成本。公共物品能使私人資本回報率得到提高,進而增加稅基,財政壓力下的激勵效應促進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重視起公共服務質量的保障,由此可見,財政壓力可能正向促進公共服務質量提升[23]。但結合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外學者對Tiebout模型假設前提、分權成本的重新審視以及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地方政府面對財政壓力,更多的是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24],以及招商引資提高稅基增長的可能性,而不是努力增加公共物品數量、保障公共服務質量,按此邏輯,財政壓力有可能累及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發現,地方財政壓力既可能促進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又可能累及公共服務質量,而且這兩種作用是相互交織的,它們之間的關系很可能是非線性的。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H1:若其他條件不變,地方財政壓力與轄區公共服務質量之間呈非線性關系,且這種非線性關系很可能是倒U型的。
(二)地方政府的支出行為
地方政府的赤字程度反映了其所背負的財政壓力,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債券、增加非稅收收入來彌補。若將地方政府在t期需要支付的債務的還本付息額作為該地區財政壓力的體現,則可以得到以下等式[22]:
其中,Bt和Bt+1分別表示第t期和新發行的政府債券,Tt為轉移支付,Rt是非稅收入,Gt是財政支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財政壓力的提升會使得地方政府傾向于壓縮財政支出,進而影響公共服務質量的保障。總的來說,中央事權的下放和財稅體制改革約束了地方的財政收支,受財政壓力沖擊的地方政府不得不過起“緊日子”,調整財政支出規模和支出結構,若其中與公共服務質量密切相關的民生性支出被“犧牲”,公共服務質量必將受到影響。
進一步來說,從地方政府執行事權角度來看,中央硬性的事權完成指標如果涉及公共服務的某一領域,地方政府的相關支出規模就會迅速擴張[25]。在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和質量保障方面的事權和支出責任較大。分稅制改革后,人們普遍認為事權和財權不相匹配使得地方政府難以充分保障公共服務的供給,但也有學者認為,地方政府的財力足以支撐中央政府下放的事權,造成公共服務質量低下的原因主要源于財政支出結構的不合理[2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H2:財政壓力下地方政府傾向于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影響轄區公共服務質量。當中央對地方政府某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提出硬性要求時,易造成不同類型的公共服務之間出現質量異質性。
三、模型、變量與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構建
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干預經濟與產業結構、利用財政“收”與“支”兩個抓手等方式,一定程度上遏制財政壓力的進一步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解決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滿足公共需求,是財政活動的主要內容,那么與日俱增的地方財政壓力會累及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嗎?
目前鮮有直接探究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效應的研究成果,圍繞相關話題,學術界觀點莫衷一是。有的學者認為,地方財政壓力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公共資金使用效率的提高,這就意味著地方政府對財政的管控能力得以提升,進而有利于當地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提供[5]。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中國地方政府有明顯的重視基本建設、易忽視基本服務的特點,地方財政壓力的增加,會使地方政府在上下級政府權責不對等的情況下顯著減少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27]。
由此可見,地方財政壓力和公共服務質量并非單純的正向或者負向的線性關系,而很可能是非線性關系。為探究地方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本文擬建立面板固定效應模型。由于靜態面板模型在內生性問題與遺漏變量方面存在不足,考慮到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的質量很有可能受到上期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本文在模型中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建立以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
其中,QPSit、QPSit-1為被解釋變量公共服務質量及其滯后一期,地方政府財政壓力FPit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Xit是各種控制變量,θi、μt分別代表地區固定效應和時間趨勢項。
(二)變量說明
1.公共服務質量
公共服務質量綜合考量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數量的充足性、分配的均衡性、居民享有的普惠性,涉及教育、醫療、環境等多個方面,因此公共服務質量指標是綜合了多個因素的結果。
在量化方法上,主成分分析法既可以獲得構成公共服務質量各個維度的量化結果,又能充分反映構成公共服務質量各維度的基礎指標對總指數的貢獻[28]。目前,已有部分學者用主成分分析法來研究公共服務相關領域的問題。夏怡然和陸銘用基礎教育和醫療服務主成分得分值來表示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29]。
本文共選取了13個基礎指標,分別構成了教育、醫療、環境、文化和交通五個一級指標。各基礎指標都屬于正指標,但由于在量綱、量級上存在差異,需要對原始值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用于主成分分析的輸入變量為原始指標均值化后的協方差矩陣[30],這可以有效減少主成分對較大量級指標的過分偏重帶來的影響。各一級指標由二級指標通過主成分分析法確定的權重合成,再將形成的五個一級指標同樣合成總指數,得到2004—2015年各地級市公共服務質量指標的測度值①(見表1)。
按地區劃分的公共服務質量指標值,呈現東高西低的特點。東部地區公共服務質量均值達到2.629,而西部地區平均水平為2.157(見圖1,下頁)。總體上,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內的城市間地方政府供給公共服務質量水平較為平均,差異相比東部地區城市間要小。
從各年的分區域公共服務質量指標均值來看,2006—2015年,各地區的公共服務質量都有逐漸提升的趨勢,東部和中部地區公共服務質量優于西部和東北地區,在2009年之前東北地區的公共服務質量要優于西部地區,但在2009年之后,東北地區的公共服務質量被西部地區趕超。
2.地方財政壓力
地方財政壓力相關實證分析的首要之務是指標的測算。除一般公共預算外,其他預算體系的收支項目,以及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舉借地方債等方式獲得的收入等都將影響財政壓力水平。結合實證需求,本文用兩種主流方法測算財政壓力。
1949年以來,中國預算管理體制總體可以分為“統收統支”、“分灶吃飯”和“分稅制”三個階段,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在推進財稅體制改革中不斷調整。在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中,中央政府為增強宏觀調控能力,在公共財力的劃分中有所側重,保證了中央財政的主導地位,這次“財權上移、事權下移”的改革,賦予了中國式分權體制“非對稱性”特征。儲德銀、遲淑嫻指出,在財稅體制改革下,縱向財政平衡程度會隨著政策沖擊發生改變[31],因此縱向財政失衡度的變化趨勢從宏觀層面上反映了中國式分權下地方財政收支失衡帶來的地方財政壓力的變化情況。
在分稅制改革平穩推進和順利實行企業新財務制度的背景下,國務院于2002年1月1日起實施了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對所得稅收入實行了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享,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進一步縮小。陳思霞等[22]、徐超等[32]認為,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前后企業所得稅相對規模的差額可以匹配為地方財政壓力。所得稅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源泉,所得稅損失率度量下的地方財政壓力比縱向失衡度的口徑要窄。以政策沖擊下的所得稅損失率來度量地方財政壓力,不僅能夠捕捉改革給地方政府帶來的財政壓力變化情況,而且有利于克服由宏觀數據構建指標帶來的內生性問題。
因此,本文在以縱向財政失衡度①為主要解釋變量進行基準回歸的基礎上,也將用所得稅損失率②所測度的財政壓力進行穩定性檢驗。
3.其他控制變量
本文選取了產業結構、人口因素、經濟發展與地方政府方面的控制變量。將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Second)以及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Third)作為控制地方產業結構的變量。人口因素的控制變量選取了人口數量(POP)、人口密度(Den)與人力資本(HR),人口數量用各市年末人口的對數來衡量,人力資本(HR)用各地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占年末總人口的比重來刻畫。經濟發展方面,借鑒徐超等的方法用各地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比重來表示[5]固定資產投資(Invest);取人均GDP的自然對數用來反映當地的經濟實力,本文用PGDP表示。最后,用地方財政自給率(FSSR)和政府參與度(GOV)作為地方政府方面的控制變量,用地級市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除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得到地方財政自給率;用各地區財政支出與GDP的比值來表示政府參與度。
(三)數據說明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樣本區間取為2004—2015年;本文剔除了直轄市和樣本區間內數據缺失在3年以上的地級市,并剔除了明顯不合邏輯關系的樣本值,剩下的229個地級市構成了非平衡面板數據①。本文對229個地級市2004—2015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源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統計數據應用支持系統的地級市數據、EPS數據平臺中的中國城市數據庫和中國區域經濟數據庫。主要變量的統計特征描述如表2所示。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本文在確定對229個地級市的非平衡面板數據模型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的基礎上,檢驗所有年度虛擬變量的聯合顯著性和個體虛擬變量的顯著性水平,結果拒絕“無時間固定效應”和“所有個體虛擬變量系數都為0”的原假設。因此,在模型中,對時間效應與個體效應同時加以控制。
表3(下頁)列(1)—(5)中加入公共服務質量指標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后,均通過了過度識別檢驗,且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模型中加入了財政壓力的一次項和平方項以探究公共服務質量和財政壓力的內在關系。為進一步驗證加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合理性,本文進行了“從小到大”的模型設定方法,但被解釋變量滯后二期到滯后四期加入模型后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因而本文將繼續采用設定系統GMM模型中因變量最大滯后階數為一階的模型進行回歸分析②。
在表3的列(1)—(5)中,財政壓力的一次項和平方項的系數顯示,財政壓力和公共服務質量呈現倒U型關系,說明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政支出具有剛性。中央政府在教育、環保、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對地方政府下達的要求等,使得地方政府在趨緊的財政壓力下也沒有放松保障公共服務質量,但總體上財政壓力帶來的公共服務質量提升效應是遞減的,且這種邊際影響在財政壓力超過時,發生了由正轉負的變化。以列(4)為例,兩者關系轉折在財政壓力值為0.653的點,各地政府財政壓力均值為0.658,說明超半數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較大,對該地公共服務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
在含平方項模型中分別加入地方政府行為、產業結構、人口因素和經濟發展的控制變量,回歸結果顯示,地方財政壓力和公共服務質量始終顯著存在倒U型關系,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除逐步增加控制變量外,本文還在表3列(1)、列(4)的基礎上,通過變換時間固定效應、加入對時間—個體交互項的控制得到列(2)和列(5)的結果,即地方財政壓力和公共服務質量的倒U型關系始終顯著,進一步驗證了基準模型的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從回歸結果來看,首先,在產業結構方面,回歸結果中第三產業占比顯著提高了公共服務質量。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產業發展可以為當地的消費和生產注入活力,為地方政府提供收入來源。第三產業對地區建設和環境要求較高,促使地方政府不斷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其次,整個社會上固定資產投資(Invest),尤其是對第三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會涉及教育、文化、醫療、社會福利業、交通運輸、房地產業、環境、水利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等領域,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密切相關,實際上模型中固定資產投資(Invest)的回歸系數也印證了其對公共服務質量有提升效應。另外,人均GDP反映了一個城市的經濟實力,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的政府往往有能力保障公共服務供給,如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其公共服務質量也相應地更優,這和圖1、表3中展示的結果一致。最后,政府參與度(GOV)體現了各地區政府財政支出活動對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程度,在表3中,政府參與度(GOV)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若政府的各項財政支出結構合理、使用效率優良,在社會性支出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公共服務質量也應隨著財政支出占國民經濟比重的增加而得以提升。
(二)穩健性檢驗
雖然系統GMM能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但利用縱向財政失衡度來測度地方財政壓力進行回歸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為避免測量誤差給基準模型分析帶來的影響,本文采用所得稅損失率作為地方財政壓力的代理變量。所得稅損失率由于使用了外生所得稅,本質上是一個強度DID模型,它有效規避了內生性問題。此外,為探究地方財政壓力對不同種類公共服務質量產生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性,進一步佐證模型的穩健性,本文將公共服務質量這一綜合性指標拆分為教育、醫療、環境、交通和文化五個方面的公共服務質量指標,對地方財政壓力進行回歸。
1.變更主要解釋變量的度量方式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地方政府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參考詹新宇和苗真子的方法,以所得稅損失率(FP_int)作為主要解釋變量[24]。由于2002年開始實施所得稅分享改革,中央與地方政府采用五五分成的方式對增量的收入進行劃分,2003年地方政府對增量收入的分成占比進一步縮減為四成,地方政府財政壓力持續激增,這種外生性財稅改革政策沖擊為構建財政壓力指標提供了機會,它本質上是一個強度DID模型,有效規避了內生性問題。同時,考慮到2013年“營改增”改革會對地方財政壓力帶來新的影響,因此本文用2004—2012數據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4(下頁)所示。公共服務質量的滯后一期在列(1)—(5)中均在1%水平下顯著,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本期公共服務質量的高低。所得稅損失率(FP_int)在模型中平方項系數均為負,一次項系數均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列(1)未加入控制變量,列(2)—(5)逐步加入了地方政府相關的控制變量以及產業結構、人口因素、經濟發展水平等與地方財政壓力、公共服務質量相關的控制變量,兩者的倒U型關系依舊顯著,說明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在表5的回歸模型中,公共服務質量即使在分指標后,系統GMM估計結果顯示在1%的水平下公共服務質量的滯后一期依舊顯著為正,證明了使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穩定性。
由表5可知,教育、醫療、文化、環境、交通等公共服務質量與財政壓力回歸的結果和基準回歸基本一致,均呈現倒U型關系。通過財政壓力一次項和平方項的估計結果計算得到,教育、醫療、文化、環境和交通公共服務質量拐點對應的財政壓力值分別為0.746、0.024、0.367、0.752和0.309,結合財政壓力的均值0.658可知,教育和環境公共服務質量與財政壓力的回歸模型的拐點位于財政壓力均值的右側,其他的則位于左側。總的來說,除教育、環境類公共服務外,絕大多數城市的醫療、文化和交通公共服務質量在樣本期內都表現出受較高財政壓力帶來的負向影響。也就是說,隨著財政壓力的進一步攀升,與發展當地經濟相比,醫療、文化和交通公共服務質量可能會被“犧牲”。由此可見,分公共服務種類回歸結果的差異,可能源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導向:中央給地方政府下達的國家性財政教育經費占比目標以及環境相關的政策文件,要求地方政府重視教育和環境質量。
五、進一步分析
(一)地區異質性分析
中國的國土面積廣闊,地區間資源種類數量、人口特點、經濟發展程度、政府行為與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特點相異。僅對全國的樣本進行回歸,無法觀測到地區差異帶來的結果是否會有差異,因而本文通過異質性分析來探究財政壓力的公共服務質量效應是否會因為地區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表現。
根據表6的回歸結果和表7中各地區回歸函數中財政壓力的拐點和均值可以看出,東部和東北地區的各市財政壓力均值位于拐點的左側,對于這兩個地區來說,適度的財政壓力可以提升當地的公共服務質量水平。在樣本期內,東部和東北地區多數城市都處于回歸曲線的左側,在倒U型回歸曲線中,表現出了公共服務質量隨著財政壓力的增加而提升的趨勢,這主要受益于財政壓力的適度,東部和東北地區絕大部分城市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普遍低于其他地區,尤其是東部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各產業發展成熟,人才的持續流入和資本的扎實積累,給當地政府帶來了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財政收入的充足保證了政府在民生領域的支出“不掉鏈子”,在同等財政壓力條件下,東部城市不需要迫切扭曲財政支出結構,尚有能力穩步提升公共服務質量。
中部地區雖然回歸系數不顯著,但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城市有著相似點:兩個地區絕大多數樣本點都分布在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有著負向影響的部分;二者的區別是,西部地區更多城市要略高于中部地區城市的財政壓力。中國日益重視區域協調發展和公共服務供給,雖然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制度縮小了西部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財力差距,但配套的轉移支付制度和稅收返還政策,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西部地區地方政府資金不足、稅基小的劣勢,地方政府難以統籌兼顧,只能將有限的財政資金優先用在基礎設施等生產性支出領域,而教育、醫療和環保等民生領域的支出明顯不足,從而累及了該地區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
(二)城市規模異質性分析
中國城市間勞動人口和居住人口規模也存在明顯差異,公共服務的供給和質量水平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城市人口規模這一特征。為探究不同規模城市下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本文計算出樣本城市2004—2015年城區常住人口的均值,對照國務院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將人口數100萬以下、100萬至300萬、300萬至500萬、500萬至1000萬分別設為四組:中小城市、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進行回歸分析①。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不同人口規模分類下城市的財政壓力和公共服務質量的關系與基準回歸基本一致,體現了本文模型的穩定性。從城市規模由大至小的財政壓力來看,測算出的均值分別是0.443、0.619、0.718、0.720,即規模越小的城市,地方政府會面對越大的財政壓力(見表8,下頁)。此外,從除特大城市的其他城市規模回歸模型中財政壓力的平方項和一次項系數可以發現,城市規模越小,公共服務質量受地方財政壓力的影響程度越大。城市優良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往往是吸引人口流入的關鍵因素,勞動力與人才涌入支撐了城市的經濟發展。對于城市規模較小的地方政府來說,常常陷入由于財政壓力趨高,被迫只顧經濟建設而忽視保障公共服務質量的怪圈中,從而易造成人口與人才流失、經濟難以提振的困境。
(三)影響機制分析
地方政府財政壓力趨增,加劇了政府間財政競爭,最終導致地方財政支出結構的扭曲。地方政府在不同時間對公共服務投入的資金結構存在的差異,會直接作用于公共服務領域的人員、公共物品等資源數量與質量,使得公共服務質量發生改變。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對公共服務質量產生影響的內在邏輯,可以用各領域公共服務財政投入占比作為橋梁,揭示財政壓力和公共服務質量之間的作用關系①。
POE、POM和POA分別是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和農林水利事務支出,用它們各自占一般預算支出的比重來測度,在一定程度上,上述三個指標反映了該地區對各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情況[33]。從表9(下頁)中我們發現,隨著財政壓力的增大,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和農林水利事務支出均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特點。這是地方政府權衡自身財政壓力與事權支出責任后的結果: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完成教育、環保、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的事務,且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政支出具有剛性的特征,地方政府面對逐增的財政壓力,需通過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減少非急需和非剛性支出,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的公共服務。但地方政府承壓能力是有限的,財政壓力帶來的教育、醫療衛生和農林水利事務支出的提升效應是遞減的,甚至在拐點之后,發生了由正到負的轉變。
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政投入直接影響了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公共服務領域財政占比的提高有助于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財政壓力和公共服務質量之間的影響機制。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伴隨著稅制改革的推進,政府財政壓力受到政策沖擊而不斷發生變化。地方政府在權衡事權與支出責任的需要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而公共服務質量又與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行為息息相關。當下,隨著“減稅降費”政策的持續推進和民生性財政支出需求的剛性增長,地方政府面臨著日益趨緊的壓力考驗,此時地方政府易以經濟發展為首要任務,而忽視轄區公共服務質量的保障。本文通過研究地方財政壓力的公共服務質量效應,揭示地方政府的行為傾向,警示地方政府在“釋壓”的過程中也不能忽視與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質量問題。
本文測度了中國229個地級市的公共服務質量和財政壓力,建立系統GMM模型,實證分析了地方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地方財政壓力與公共服務質量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一定范圍內的財政壓力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從而提升轄區公共服務質量,但當地方政府承壓超過一定限度時,財政壓力則將顯著降低公共服務質量。將財政壓力指標替換成更外生的所得稅損失率,將被解釋變量細分為教育、醫療、環境、文化和交通五種公共服務質量,回歸結果依然穩健,但相較于教育、環境類公共服務,絕大多數城市的醫療、文化和交通公共服務質量在樣本期內更多表現出受到財政壓力的負向影響。此外,異質性分析發現,倒U型關系在西部和中部地區絕大部分樣本城市處于財政壓力惡化地區公共服務質量的階段,而東部區公共服務質量尚能穩步發展;人口規模越小,城市公共服務質量受地方財政壓力的影響程度越大。機制分析發現,地方財政壓力是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從而影響轄區公共服務供給質量的。
通過研究,可得到如下啟示:一是以適度的地方財政壓力穩步提升地方公共服務質量。中央在進行財稅體制改革以及下放財政事權給地方政府的同時,需權衡地方政府承受的財政壓力。在地方政府承壓適度的情況下,合理分配各級政府的公共事務,關注其對公共服務領域和地方政府行為的深遠影響。二是注重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避免壓縮民生性支出。公共服務質量問題主要源于財政支出結構的不合理,政府為履行事權而急劇增加的支出,將通過犧牲其他支出特別是民生性支出為代價,由此給財政支出結構帶來的負面影響難以在短期內消除。因此,政府需要保障民生性支出的充足性,重視民生財政支出彌補機制的建立。三是尋求地區間公共服務質量的相對均衡,在發揮財政的支持作用時要因地制宜。中部與西部地區財政壓力均值已過倒U型曲線的拐點,超負荷的財政壓力阻礙著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因此,可以綜合各地財政支出結構的合理性和地方財政壓力情況進行政府間轉移支付,以均衡提升各地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
參考文獻
[1]張原,吳斌珍.財政分權及財政壓力沖擊下的地方政府收支行為[J].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9(11):940-952.
[2]CHEN S X. The effect of a fiscal squeeze on tax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7, 147: 62-76.
[3]方紅生,張軍.財政集權的激勵效應再評估:攫取之手還是援助之手?[J].管理世界,2014(2):21-31.
[4]席鵬輝,梁若冰,謝貞發.稅收分成調整、財政壓力與工業污染[J].世界經濟,2017(10):170-192.
[5]徐超,龐雨蒙,劉迪.地方財政壓力與政府支出效率——基于所得稅分享改革的準自然實驗分析[J].經濟研究,2020(6):138-154.
[6]史衛東,趙林.山東省基本公共服務質量測度及空間格局特征[J].經濟地理,2015(6):32-37.
[7]李冬.京津冀地區公共服務質量評價[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8(2):52-57.
[8]趙晏,邢占軍,李廣.政府公共服務質量的評價指標測度[J].重慶社會科學,2011(10):113-120.
[9]陳詩一,張軍.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國社會科學,2008(4):65-78.
[10] 侯慧麗.城市公共服務的供給差異及其對人口流動的影響[J].中國人口科學,2016(1):118-125.
[11] 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416-424.
[12] 陳曉光.財政壓力、稅收征管與地區不平等[J].中國社會科學,2016(4):53-70.
[13] 謝星全.基本公共服務質量:一個系統的概念與分析框架[J].中國行政管理,2017(3):68-72.
[14] 林閩鋼,楊鈺.公共服務質量評價:國外經驗與中國改革取向[J].宏觀質量研究,2016(3):90-98.
[15] 王哲,周麟,彭芃.財政支出、標尺比較與公共服務滿意度:基于縣級醫療數據的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8(3):49-54.
[16] 陳秋紅.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改善:基于農民需求的視角[J].改革,2019(6):92-101.
[17] 傅勇.財政分權、政府治理與非經濟性公共物品供給[J].經濟研究,2010(8):4-15.
[18] 儲德銀,韓一多,張同斌,等.中國式分權與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線性抑或倒“U”[J].經濟學(季刊),2018(3):1259-1288.
[19] 余靖雯,陳曉光,龔六堂.財政壓力如何影響了縣級政府公共服務供給?[J].金融研究,2018(1):18-35.
[20] DU J, LU Y, TAO Z. Government expropriation and Chinese-style firm diversification[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5, 43(01): 155-169.
[21] 席鵬輝,梁若冰,謝貞發.稅收分成調整、財政壓力與工業污染[J].世界經濟,2017(10):170-192.
[22] 陳思霞,許文立,張領祎.財政壓力與地方經濟增長——來自中國所得稅分享改革的政策實驗[J].財貿經濟,2017(4):37-53.
[23] OATES W E. Toward a second-generation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J].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005, 12(4): 349-373.
[24] 詹新宇,苗真子.地方財政壓力的經濟發展質量效應——來自中國282個地級市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財政研究,2019(6):57-71.
[25] 席鵬輝,黃曉虹.財政壓力與地方政府行為——基于教育事權改革的準自然實驗[J].財貿經濟,2020(7):36-50.
[26] 平新喬,白潔.中國財政分權與地方公共品的供給[J].財貿經濟,2006(2):49-55.
[27] 李永友,張子楠.轉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會性公共品供給激勵嗎?[J].經濟研究,2017(1):119-133.
[28] 詹新宇,崔培培.中國省際經濟增長質量的測度與評價——基于“五大發展理念”的實證分析[J].財政研究,2016(8):40-53.
[29] 夏怡然,陸銘.城市間的“孟母三遷”——公共服務影響勞動力流向的經驗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30] 鈔小靜,任保平.資源環境約束下的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4):102-107.
[31] 儲德銀,遲淑嫻.轉移支付降低了中國式財政縱向失衡嗎[J].財貿經濟,2018(9):23-38.
[32] 徐超,龐雨蒙,劉迪.地方財政壓力與政府支出效率——基于所得稅分享改革的準自然實驗分析[J].經濟研究,2020(6):138-154.
[33] 周黎安,陳祎.縣級財政負擔與地方公共服務:農村稅費改革的影響[J].經濟學(季刊),2015(2):417-434.
Financial Pressure, Expenditure 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Quality: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e Panel Data of 229 Cities in China
ZHAN Xin-yu? ?WANG Rong-rong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duty of local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public services to meet the needs of residents in the district. The financial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and tax system to local government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behavior.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public service quality and financial pressure in 229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the GMM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local financial pressure on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financial pressure has a nonlinear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under pressure beyond a certain limit, the financial pressure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ublic service quality in the jurisdic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heterogeneity due to the different size of the region and the city; the difference of quality among different kinds of public services stems from th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under the financial pressure.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rol the financial pressure in a moderate range,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and strive to achieve a relatively balanced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among regions.
Key words: local financial pressure; public service quality; financi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system GMM model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政府間財政關系與經濟增長目標管理研究”(20FJYB014)。
作者簡介:詹新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王蓉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研究生。
3522500338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