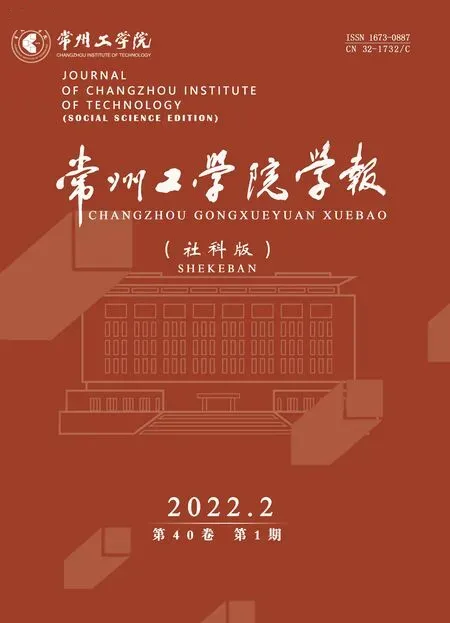康熙《無錫縣志》中運(yùn)河詩歌的整理與研究
曲金燕,賈愚
(1.無錫學(xué)院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江蘇 無錫 214105;2.南京信息工程大學(xué)商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49)
無錫是一座因運(yùn)河而生的江南名城,根據(jù)南宋《咸淳毗陵志》和元王仁輔《無錫志》的記載,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商末奔吳的泰伯率領(lǐng)百姓開鑿的泰伯瀆是最早的人工運(yùn)河,傅崇蘭在《運(yùn)河史話》中說:“因?yàn)檫\(yùn)河暢通,無錫得益于運(yùn)河航運(yùn)。在明代,無錫與九江、蕪湖、長沙成為我國四大米市。明清時(shí)期的無錫城內(nèi)手工業(yè)、商業(yè)、文化都很發(fā)達(dá)。”①大運(yùn)河對無錫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體現(xiàn)在地方典籍的整理上,無錫縣志中記載了大量與運(yùn)河相關(guān)的地理、漕運(yùn)、水利、詩文、古跡、冢墓、物產(chǎn)等文獻(xiàn)資料,對此,我們嘗試從康熙《無錫縣志》所收運(yùn)河詩歌入手,研究無錫古運(yùn)河流經(jīng)區(qū)域的自然風(fēng)貌、人文景觀及其蘊(yùn)含的文人情致和文化內(nèi)涵,進(jìn)而挖掘無錫地區(qū)的運(yùn)河文化資源,探索大運(yùn)河的精神底蘊(yùn),為“講好運(yùn)河故事”、打造運(yùn)河城市品牌、傳承運(yùn)河文化提供文獻(xiàn)依據(jù)。
史家言“郡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無錫先后修志13部,散佚4部。元代一修,明代有景泰(散佚)、弘治、萬歷3志,清修康熙、嘉慶、道光、光緒《無錫縣志》各1部,乾隆《無錫縣志》2部。其中康熙《無錫縣志》屬方志中的上乘之作,被后世奉為圭臬,《續(xù)修四庫全書提要》評:“因秦、嚴(yán)并名流,精史法,故其書完美。所為凡例,尤多名論,誠佳構(gòu)也。”編纂者為秦松齡、嚴(yán)繩孫,二人皆為無錫本地人,對地方故事了如指掌,且均參與編修《明史》,有史學(xué)功底和文學(xué)素養(yǎng)。在“詩文”類的編排上,康熙《無錫縣志》沒有像萬歷志那樣,將詩文“或散于山水事跡”中,而是按照“敘次則分代分體”進(jìn)行編排,打破了以往“以詩證地”“以詩證史”的史家局限,完全遵從文學(xué)家的編排規(guī)范。康熙《無錫縣志》中一共收錄了36位作家的39首運(yùn)河詩歌。我們擬從康熙《無錫縣志》運(yùn)河詩歌的輿地風(fēng)貌、作者及創(chuàng)作背景、主題呈現(xiàn)、史料價(jià)值等4個(gè)方面進(jìn)行探討。
一、康熙《無錫縣志》運(yùn)河詩歌的輿地風(fēng)貌
無錫最著名的山是惠山,最主要的河是運(yùn)河。“運(yùn)河自武進(jìn)五牧入無錫境,迤邐東南行四十五里,抵縣城,又四十五里至望亭。”②大運(yùn)河自西北而入,東南而出,主流經(jīng)五牧、黃埠墩、芙蓉湖、望亭,分流西行為梁溪,南行東分為泰伯瀆。康熙《無錫縣志》中所錄相關(guān)詩歌見表1。

表1 康熙《無錫縣志》中的運(yùn)河詩歌
康熙《無錫縣志》中所錄運(yùn)河詩歌,唐代7首、宋代6首、元代13首、明代10首、清代3首(康熙《無錫縣志》成書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故清代只有3首)。唐宋數(shù)量較少,因?yàn)闊o錫是在中唐以后才得到初步開發(fā),在這一過程中,大運(yùn)河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全漢昇在《唐宋帝國與運(yùn)河》一書中說,唐憲宗時(shí)代“一方面由于運(yùn)河的暢通無阻,他方面由于江南諸道地方財(cái)政的整頓,運(yùn)河對于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經(jīng)濟(jì)重心的南方的聯(lián)系,又由過去的松懈變?yōu)槊芮小雹邸T院螅筮\(yùn)河截彎取直,實(shí)現(xiàn)了真正意義上的溝通南北,很多文人沿運(yùn)河南下,其中包括康熙、乾隆二帝,他們鐘情于景色宜人的江南風(fēng)光,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康熙《無錫縣志》中運(yùn)河詩歌涉及以下運(yùn)河區(qū)域:
黃埠墩,位于運(yùn)河中流,是進(jìn)出無錫的必經(jīng)之路,南宋愛國將領(lǐng)文天祥曾兩次途經(jīng)此處,第一次是1259年,“己未歲,余攜弟璧赴廷對,嘗從大江入里河,趨京口”④。第二次是南宋德祐年間,元軍主帥伯顏扣押文天祥,將其幽禁在墩上過夜,文天祥寫下了《過無錫》。沿運(yùn)河南下,黃埠墩是無錫的第一“門面”,對它的印象就是對這座城市的印象。相傳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南巡時(shí),百姓在黃埠墩結(jié)三層燈樓迎駕,“立木水中,使廣可隱墩,綴以雜絳,高四五丈,于是龍舟往返皆駐蹕焉”⑤。風(fēng)水搖蕩、恍若蜃樓的絕美景觀引得皇帝大為贊賞。舊時(shí),黃埠墩還是登游惠山的唯一水路,明代談修《惠山古今考》記載:“從舟者有出北水關(guān),過長安橋,由芙蓉湖抵黃埠墩,墩有閣,可登山間之臺殿……”⑥明代,黃埠墩是離錫的水路出口,華察有《秋夜送戶部家叔登黃埠》詩。
芙蓉湖,又名無錫湖,曾是古運(yùn)河北塘水域最寬闊的一段,今已不存。“堙芙蓉湖為田始于宋,成于明”⑦,圍湖屯田始于北宋,此前芙蓉湖碧波萬頃,十分宏闊,《寰宇記》記載“上湖一名芙蓉湖,亦謂之無錫湖,占晉陵、江陰、無錫三界限”,《吳地記》中言“無錫湖,萬五千三百頃,為晉陵上湖”,陸羽《惠山寺記》中言“其湖南控長江,東洞江陰,北掩晉陵,蒼蒼渺渺……”,李紳有《卻望芙蓉湖五首》,宋胡宿作《芙蓉湖泛舟》。
梁溪,本是自然河道,為梁時(shí)重浚,“宋嘉佑中,開運(yùn)河,通梁溪,取太湖水”,因此將其視為運(yùn)河支流亦不為過。梁溪凝結(jié)著無錫人的故鄉(xiāng)情懷,被視為“母親河”,“俗云:州人不能遠(yuǎn)出,出輒懷歸,以此溪水有回性”⑧。在外為官的抗金名將李綱,自號“梁溪先生”,以明不忘家鄉(xiāng)之志。梁溪還是一處幽隱勝地,《錫金識小錄》載:“梁溪以梁鴻曾隱此故名,亦稱梁鴻溪。”康熙《無錫縣志》共錄7首梁溪詩,整體風(fēng)格沖融淡易,簡雅深秀。
元代華锳在梁溪邊建華君別墅,“在無錫西門,惠山橫陳,悉露其深秀,凡山之霏煙、泄云、雨紓、晴晦、朝暉、夜光吐護(hù)閃映”⑨,別墅地處山水要會,能總攬惠山勝貌,是觀賞惠山的絕佳勝地,后華锳見“吳中碩儒”鄭元祐題“溪山勝概”舊藏,大喜,以四字命其樓,自此溪山勝概樓名聲大噪,倪瓚、陳汝言、陳顯曾皆有題詩,鄭元祐作《溪山勝概樓記》,元后樓不見所錄。
泰伯瀆,系泰伯所開,據(jù)地方文獻(xiàn)記載,泰伯為了發(fā)展吳地農(nóng)業(yè),率領(lǐng)百姓開鑿了一條以梅里為中心,東到漕湖,西到今無錫南門外的人工運(yùn)河,長87里,寬12丈。泰伯是無錫的開拓者,也是吳文化的奠基人。無錫共有3處祭奠泰伯的古跡景觀:梅里的泰伯墓、婁巷廟、惠山至德祠。《論語·泰伯篇第八》:“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讓天下,民無得而稱焉。”泰伯的禮讓精神備受世人景仰,歷代都有頌揚(yáng)的詩篇,康熙《無錫縣志》存6篇。
望亭,大運(yùn)河邊的驛站,位于蘇州、無錫之間。《吳郡圖經(jīng)續(xù)記·卷下》:“望亭,在吳縣西境。吳先主所立,謂之御亭。隋開元九年置為驛,唐常州刺史李襲譽(yù)改今名。劉禹錫詩云:‘懷人吳御亭。’”六朝庾肩吾有詩《亂后行經(jīng)吳御亭》。五代前有望亭堰,北宋初年廢,后復(fù)置,神宗熙寧元年(1068)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jiān)護(hù)使臣并以‘管干河塘’系銜”,清代設(shè)望亭巡檢司,“望亭巡檢司在縣南五十里望亭鎮(zhèn)”。康熙《無錫縣志》中收望亭詩6首。新安驛,南門外水馬站,宋元時(shí)設(shè),明初乃廢,“錫山驛在南門外,宋以來有太平、南門、北門三驛,元置洛社、新安水馬站各一所,明初站廢,置錫山驛于今地”⑩。元顧瑛有《晚泊新安有懷九成》,于立、剡邵、沈明遠(yuǎn)各有和作。
二、康熙《無錫縣志》運(yùn)河詩歌作者及創(chuàng)作背景
康熙《無錫縣志》運(yùn)河詩歌作者一共36人,他們有的是自幼就生長于運(yùn)河畔的無錫籍人,有的是或流寓此地、或游歷此地的外地文人。
(一)本土詩人
1.唐代
李紳(772—846),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身材矮小精干,性格精明強(qiáng)悍,于詩最有名,時(shí)號“短李”,《新唐書》《唐才子傳》有傳。按今人眼光來看,李紳是無錫歷史上成功推廣家鄉(xiāng)文化的第一人,他進(jìn)京城做官,不忘帶上特產(chǎn)惠泉水,贈予權(quán)相李德裕,深得上司喜歡。李德裕不僅作《惠泉》詩以示贊譽(yù),還千里置驛,利用大運(yùn)河傳輸運(yùn)送,如此勞民傷財(cái)?shù)呐e動引起了時(shí)人的不滿,皮日休作詩“丞相常思煮茗時(shí),郡侯催發(fā)只嫌遲。吳關(guān)去國三千里,莫笑楊妃愛荔枝”諷刺。
2.元代

3.明代
華察(1497—1574),字子潛,號鴻山。民間故事《三笑姻緣》中華太師的人物原型,出自江南望族華氏,東晉華孝子后裔,《明史》有傳。《秋夜送戶部家叔登黃埠》作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華察辭官歸隱里居時(shí)期。八月十六日,華察與老友施漸共登黃埠墩送族叔華舜欽。華舜欽,華啟直父,別號余溪,嘉靖二十年(1541)進(jìn)士,任瑞州知府,施漸《武陵詩選》卷一《癸丑八月十六日夜同華秋官昆仲登黃埠南樓送乃武戶曹余溪》同記此事。
王立道(1510—1547),字懋中,嘉靖十四年(1535)進(jìn)士,官翰林院編修。“有羸疾,僦居僻遠(yuǎn)下樓,讀書為詩文,博瞻婉切,于諸閣老無屏人之謁,寡交游。”由于年歲不永,又罕有交游,關(guān)于他的資料甚為寥落,有《具茨集》5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jià)其詩“雖微嫌婉弱,而沖容淡宕,不為奇顯之語,猶有中唐錢、劉之遺”,由《泛梁溪》可窺一斑。
秦植(1540—1605),原名秦鳳竹,字子培,號濟(jì)弘,出自錫山秦氏家族第九世,著有《清湖集》抄本3卷,現(xiàn)藏?zé)o錫圖書館。《錫山秦氏詩鈔》收錄其詩81首,《梁溪詩鈔》收其詩2首。
4.清代
劉雷恒(1623—?),字震修,號易臺。康熙《無錫縣志·貢生》:“劉雷恒,康熙二十年,本府訓(xùn)導(dǎo)。”著有《震修詩文稿》,與顧貞觀等結(jié)成云門詩社。作《太伯墓》詩。
(二)外地文人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望亭驛酬別周判官》作于寶歷二年(826)白居易從蘇州至洛陽途中。周判官,即周元范,白居易為蘇杭二州刺史時(shí),周元范為從事,二人經(jīng)常宴集酬和,白居易有詩作《歲假內(nèi)命酒贈周判官蕭協(xié)律》《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日漸長贈周殷二判官》《九日思杭州舊游寄周判官及諸客》《三月二十八日贈周判官》。
羅隱(833—910),原名橫,字昭諫,浙江富陽人。羅隱前半生,十次不中第,常年流落長安,游走于家鄉(xiāng)與京城之間,大半生顛沛流離。《唐才子傳》稱羅隱“恃才忽睨,眾頗憎忌。自以為當(dāng)?shù)么笥茫坏诼渎洌瑐魇持T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其詩文以諷刺為主,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魯迅在他的《小品文的危機(jī)》中說:“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fàn)幒蛻嵓ぶ劇!彪m然是論羅隱小品,但他的詩篇,大抵也是這一風(fēng)格。康熙《無錫縣志》所載《夜泊毗陵無錫縣有寄》是詩人回鄉(xiāng)稍作休整后又返長安途中,經(jīng)由無錫運(yùn)河時(shí)所作,末句“他日親朋應(yīng)大笑,始知書劍是無端”出自《史記·項(xiàng)羽本紀(jì)》:“項(xiàng)籍少時(shí),學(xué)書不成,去學(xué)劍,又不成。項(xiàng)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xué),學(xué)萬人敵。’”表面看起來是詩人屢戰(zhàn)屢敗后的頓悟,實(shí)際是故作曠達(dá)的自我安慰。
皮日休(838—883)、陸龜蒙(?—881)是中晚唐著名詩人,人稱“皮陸”,康熙《無錫縣志·流寓》:“錢氏卒,日休嘗寓無錫,與陸龜蒙魏璞泛舟芙蓉湖,共為煙水之游。”二人義結(jié)金蘭,日相唱和,皮日休有《泰伯廟》,陸龜蒙和之。
范仲淹(989—1502),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蘇州,北宋政治家、文學(xué)家。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奉命移知蘇州治理水患,在處理政務(wù)之余,他游覽了不少以前沒有到過的地方,創(chuàng)作了《蘇州十詠》,其一是《泰伯祠》,這本是蘇州的泰伯廟,但被《無錫縣志》收錄其中,因是同一泰伯,所以也在研究范圍之列。
三、康熙《無錫縣志》運(yùn)河詩歌的主題呈現(xiàn)
(一)懷古——邇來父子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
《史記·吳太伯世家第一》記載:“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fā),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太伯。”自孔子以來,禮贊泰伯都是頌揚(yáng)他“讓賢”、謙讓的懿德,詩人所處時(shí)代不同,抒發(fā)情感的側(cè)重點(diǎn)也有所不同。
越是朝代之末,越需要泰伯精神。中晚唐時(shí)期,經(jīng)過“安史之亂”這場浩劫,唐朝從如日中天的盛世一轉(zhuǎn)而為夕陽衰草的末世,從中唐到晚唐,大唐的氣數(shù)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農(nóng)民起義此起彼伏。詩人是時(shí)代最敏銳的“感應(yīng)器”,他們早就嗅到了王朝日趨沒落的衰朽氣息,知識分子中的有識之士企圖力挽狂瀾,卻又報(bào)國無門,徘徊于仕途之外,曾是寒門子弟唯一的進(jìn)身途徑——科舉考試,此時(shí)把持在極少數(shù)權(quán)貴手中,那些有理想、有抱負(fù)的文人士子空有一身才華而無用武之地,比如:有“十上不第”之稱的羅隱,一共參加了10次進(jìn)士考試,均鎩羽而歸;被魯迅譽(yù)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的皮日休,以末榜及第,終未授予正式的官職;與皮日休齊名的陸龜蒙,舉進(jìn)士不第,歸隱鄉(xiāng)里,務(wù)農(nóng)為業(yè)。
皮、陸二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懷古詩,他們以歷史古跡為憑借,抒發(fā)胸中不平之氣,以澆心頭塊壘。二人將目光投向了泰伯,皮日休寫了《泰伯廟》,陸龜蒙和以《和襲美泰伯廟》,襲美,皮日休的字,這兩首是詠懷泰伯最早的詩歌,也是成就最高的詩歌。皮詩中的“當(dāng)時(shí)盡解稱高義,誰敢教他莽卓聞”肯定了泰伯的高義之舉,陸作和詩“邇來父子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抨擊了近世“壞人倫”“禮樂崩”的社會亂象,鞭撻了人與人之間冷漠殘酷的搶奪爭戰(zhàn),二人以普通文人的身份,喊出了絕大多數(shù)人內(nèi)心深處的正義呼聲,他們渴望泰伯“謙讓”至德精神的再現(xiàn),以實(shí)現(xiàn)四海晏清、百姓安居樂業(yè)的社會理想。
海內(nèi)承平時(shí)期,泰伯之至德精神有規(guī)范道德秩序、教化社會風(fēng)俗的作用。謙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對個(gè)人而言,它是孔子所說的“五德”之一,對社會而言,謙讓有利于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康熙《無錫縣志》存兩首北宋詠泰伯詩歌,一首是范仲淹的《泰伯祠》,另一首是蔣堂的《泰伯廟》。二人為同時(shí)代人,同朝為官,他們都從統(tǒng)治者角度談到了泰伯精神的道德教化作用。范詩言“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蔣詩言“隱德昭來世,遺祀傳斯民”。泰伯信仰官方化日益明顯,泰伯精神也越來越儒化了。
明末清初是歷史上又一個(gè)社會秩序遭到嚴(yán)重破壞的動蕩時(shí)期,顧炎武曾說:“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江南地區(qū)是受到重創(chuàng)區(qū)域,泰伯廟經(jīng)久失修,清初人張夏寫道:“葉積空階稀客到,塵封坐帳有墻遮。”(《至德廟》)由于許久未有人來,臺階上堆滿了落葉,簾帳早已塵封,破敗的景象讓人唏噓不已。同時(shí)代人劉雷恒在《太伯墓》中感嘆“玉魚金碗思悠悠,誰重皇山土一抔”。皇山,即泰伯所葬之地,此句表達(dá)了詩人對泰伯墓遭冷遇的遺憾和不滿。這種情況并未持續(xù)太久,滿族統(tǒng)治者一旦坐穩(wěn)了天下,立刻意識到“以漢制漢”的重要性,康熙南巡至蘇州,御書“至德無名”于泰伯廟中,將泰伯“讓賢”的精神象征重新恢復(fù)并推向高潮。
(二)游賞——水寬山遠(yuǎn)煙嵐回,柳岸縈回在碧流
無錫自古為山水勝地,風(fēng)景秀美,甲冠江南,康熙《無錫縣志》中收錄的芙蓉湖詩、梁溪詩頗具代表性。
芙蓉湖,其名即充滿詩情畫意,本是運(yùn)河自西北入無錫后最寬闊的水域,陸羽《惠山寺記》載“故惠山有望湖閣,蓋自山下百余里,目極荷花不斷,以為江南煙水之盛”。后因宋代塞湖屯田,日益縮小,今已沒,只剩“江湖傳說”,芙蓉湖的觀賞價(jià)值遠(yuǎn)大于交通價(jià)值,康熙《無錫縣志》中存詩3首:唐代李紳的《卻望芙蓉湖五首》、宋代胡宿的《芙蓉湖泛舟》、清代何之杰的《錫山竹枝詞》。李紳所見芙蓉湖為全貌,何之杰所見只是驚鴻掠影。李紳的《卻望芙蓉湖五首》展現(xiàn)了“蒼蒼渺渺”的芙蓉湖之舊日風(fēng)采:
水寬山遠(yuǎn)煙嵐回,柳岸縈回在碧流。清晝不風(fēng)鳧雁少,卻疑初夢鏡湖秋。
丹橘村邊獨(dú)火微,碧流明處雁初飛。蕭條落葉垂楊岸,隔水寥寥聞?chuàng)v衣。
逐波云影參差遠(yuǎn),背日嵐光隱見深。猶似望中連海樹,月生湖上是山陰。
舊山認(rèn)得煙嵐近,湖水平鋪碧岫間。喜見云泉還悵望,自慚山叟不歸山。
翠崖幽谷分明處,倦鳥歸云在眼前。惆悵白頭為四老,遠(yuǎn)隨塵土去伊川。
李紳對家鄉(xiāng)有著十分深厚的情感,《慧山寺家山記》中載:“心寧色養(yǎng),家寓是縣,因肄業(yè)于慧山,始年十五六。”他常親切地稱惠山為“家山”“舊山”。步入仕途后,李伸的宦海生涯并不平靜,周旋于紛亂復(fù)雜的“牛李黨爭”,他身心俱疲,如今再次回到當(dāng)年苦讀之地,置身“水寬山遠(yuǎn)”“柳岸縈回”如仙境般的芙蓉湖畔,眼前開闊宏大的豁朗氣象讓人心生歸隱之意,他不禁感嘆“喜見云泉還悵望,自慚山叟不歸山”,表達(dá)了對遠(yuǎn)離塵世的安寧生活的渴望與向往之情。
梁溪是運(yùn)河西行的一個(gè)分支,古代設(shè)有控制蓄泄的水利工程將軍堰,《風(fēng)土記》載:“唐景龍中置,宋嘉祐中開運(yùn)河通梁溪以引湖水,堰遂廢。”對于無錫人而言,梁溪是故鄉(xiāng)的代稱,明李湛“錫山八景”之一“梁溪曉月”,將月景拈出,可謂抓住了梁溪神韻。康熙《無錫縣志》中共載6首梁溪詩歌,元代2首,明代4首,元代的梁溪詩充滿了“仙道”氣息,明代梁溪詩則有濃濃的市井味,體現(xiàn)了梁溪意象由“雅”向“俗”的漸變。

和元代相比,明代的江南是熱鬧的,發(fā)達(dá)的水上交通網(wǎng)絡(luò)、豐富的產(chǎn)業(yè)狀態(tài)、渠道多樣的謀生方式,成為太湖地區(qū)最鮮明的標(biāo)識。梁溪褪去了不食人間煙火的仙道之氣,逐漸變成供人觀賞、消費(fèi)的旅游場所,兩首“梁溪詩”即透露了這方面的信息,屠隆的《與王彥貽鄒彥吉泛梁溪登惠山》寫與友人先泛舟梁溪,再登覽惠山,這無疑是當(dāng)時(shí)最時(shí)興的一條“黃金旅游路線”,梁溪周圍的很多人家都在做游覽生意,“家家游舫依山轉(zhuǎn),面面通波抱郭平”寫出了游舫、游人之多。另一首秦植的《梁溪詞》則描繪了伴隨旅游而興起的餐飲業(yè):“堤上重重沽酒樓,湖邊日日木闌舟。”梁溪場景是江南地區(qū)旅游業(yè)的縮影,為我們研究城市文化、運(yùn)河旅游文化提供了鮮活的資料。
(三)羈旅——月色滄波共渺茫,驛亭雜坐看湖光
大運(yùn)河畔靜靜佇立的驛站,像歷盡滄桑的老人,默默注視著眼前流淌而過的運(yùn)河,它見證了歷史的風(fēng)云變幻,見證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無錫有一個(gè)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詩詞中的驛站——望亭驛。望亭的歷史十分悠久,早在南北朝時(shí)期,庾肩吾就寫過一首《亂后經(jīng)行吳御亭》,以波瀾壯闊的史家筆法描寫了“侯景之亂”后江南的慘象。
望亭驛由于遭遇歷年戰(zhàn)火,幾經(jīng)焚毀、遷移,它的主要功能是官方招待所,為過往官員、使者提供膳食和住宿。作為旅途中轉(zhuǎn)和暫時(shí)落腳的地方,望亭驛在詩人眼中是充滿感傷的,它承載了人生無常、相離相別、聚散不定的羈旅之愁。嚴(yán)羽在《滄浪詩話·詩評》中說:“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fā)人意。”羈旅詩不僅反映了詩人的行旅蹤跡,也是人生際遇、思想軌跡的真實(shí)寫照。例如許渾《宿松江驛卻寄蘇州一二同志》:
候館人稀也自長,姑蘇城遠(yuǎn)樹蒼蒼。江湖水落高樓回,河漢秋歸廣簟涼。
月轉(zhuǎn)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葉濕螢光。西園詩侶應(yīng)多思,莫醉笙歌掩畫堂。
候館人稀,遠(yuǎn)樹蒼蒼,在月朗星稀的秋夜,詩人駐足眺望,遠(yuǎn)處高樓掩映于暮靄之中,蒼穹寥廓,河漢悲涼,獨(dú)自在郊外的古驛,秋夜顯得格外的漫長。看著月下徘徊的鵲影、低飛的流螢,詩人思緒翩躚,想到剛剛作別的蘇州友人,他發(fā)自肺腑地真情相勸:“西園詩侶應(yīng)多思,莫醉笙歌掩畫堂。”許渾曾在入仕的道路上蹣跚蹭蹬20多年,深知落第失意的痛苦,故以詩相贈,勉勵(lì)詩侶不要耽于歌舞而荒蕪了學(xué)業(yè),體現(xiàn)了詩人對朋友的良苦用心。
許渾去世400多年后,在同一個(gè)望亭,同樣的秋夜,出現(xiàn)了另外一個(gè)望月感懷的詩人——元代的張翥,與許渾關(guān)注人間情誼不同,張翥的羈旅之愁表現(xiàn)為或隱或仕、或進(jìn)或退的糾結(jié)與矛盾,他將對人生的思索聚焦于浩瀚的夜空和蒼茫的宇宙。如其《中秋望亭驛對月》:
月色滄波共渺茫,驛亭雜坐看湖光。仙家刻玉青蟾兔,帝子吹笙白鳳凰。
蘆葉好風(fēng)生晚思,桂花清露濕空涼。回槎使者秋懷闊,倒瀉銀河入酒殤。
中秋本是家人團(tuán)聚、盡享天倫的日子,身在旅驛的詩人卻沒有因孤寂而思親念友,自憐自艾,反而十分享受獨(dú)處的時(shí)光,皎潔的月光下遙望夜空,詩人展開了豐富的想象,用恣肆的手筆勾勒了一幅雄渾大氣的月宮仙境,“青蟾兔”“白鳳凰”“回槎使者”“銀河倒瀉”交錯(cuò)變幻,紛至沓來,沉浸在幽邃的夜空,詩人暫時(shí)忘卻了人間的哀傷。張翥身處元代末世,盡管身居官位卻不受重視,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矛盾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蠶食著他經(jīng)世致用的抱負(fù),他既找不到出路,也看不到前景,中秋夜于古驛對月懷想,苦悶又彷徨。
四、康熙《無錫縣志》運(yùn)河詩歌的史料價(jià)值
彰顯地方文化、提升地方景觀的文化魅力是歷代方志編纂者共同遵循的原則。基于這一原則,地方志在選錄詩歌時(shí),多以題詠當(dāng)?shù)仫L(fēng)物的詩作為主,但是這并沒有掩蓋這類詩歌的史料價(jià)值以及它們的寫實(shí)性,經(jīng)過藝術(shù)處理的歷史事件能更鮮活、生動地還原歷史,歷史本事已經(jīng)褪去,但是痕跡永存世間。
文天祥的《吊五牧》創(chuàng)作于元朝初年,記錄的是元軍大兵南下橫掃江南的一次戰(zhàn)役。五牧位于錫西洛社重鎮(zhèn)西沿大運(yùn)河9里處,自古以來就是水陸交通要道。詩前有一段遠(yuǎn)長于詩歌的小序:
予初以朝廷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救常州,以其為淮將,必經(jīng)歷老成,遂遣朱華將二千人從之。張全無統(tǒng)御之才,自為畦町,十月二十六日,提淮軍自往橫林設(shè)伏,虞橋北兵至,麻士龍死之,張全不救,走回五牧,五牧乃朱華所駐,如掘溝塹設(shè)鹿角,張全皆不許,……嗚呼!天哉!予初欲先斬張全,然后取一時(shí)敗將,并從軍法,以張全乃朝廷所遣,請于都督乃宥,張全使自贖,予遂不及行法,后詣余杭,發(fā)京師,取曾全以殉眾,而噬臍多矣!過五牧吊戰(zhàn)場,為之流涕不可御。
小序中交代了五牧之戰(zhàn)的具體經(jīng)過,張全的懦弱無能、將士的出生入死、戰(zhàn)爭的殘酷慘烈鮮活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詩文如下:“首赴勤王役,功成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淚成川。我做招魂想,誰為掩骼緣。中興需再舉,寄語謂重泉。”面對慘死的戰(zhàn)士,文天祥痛哭流涕,怎奈朝廷孱弱腐敗,江山氣數(shù)已盡,除了傷心、哀慟又能如何?整首詩生動、完整地還原了當(dāng)時(shí)的戰(zhàn)爭場景,運(yùn)河邊血流成河,尸骨遍野,英雄仰天長嘯,哀嘆頓足。
對于這次戰(zhàn)役,《宋史》記載:“癸亥,張全、尹玉、麻士龍?jiān)V荩魁垜?zhàn)虞橋死,全奔五牧。朱煥至廬州,貴不內(nèi)。煥歸,復(fù)以為淮東制置副使。陳合坐匿廖瑩中家資,奪執(zhí)政恩數(shù)。甲子,尹玉戰(zhàn)五牧,死之,張全不戰(zhàn)遁。”同書《文天祥傳》記載:“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zhàn)死,朱華以廣軍戰(zhàn)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zhàn),比旦皆沒。”兩則關(guān)于“五牧之戰(zhàn)”的史料皆寥寥數(shù)語,極易淹沒于浩瀚的歷史長河之中,《吊五牧》則將其深深地印入了讀者的腦海。
李嘉祐的《自蘇臺至望亭悵然有作》是描寫亂后景象的詩歌,所涉事件是中唐時(shí)期李光弼平“袁晁之亂”,“野堂自發(fā)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yuǎn)岫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dú)傷春”。舊苑長洲,塵虜未息,從蘇州到望亭一帶烽戍連年,滿目瘡痍。《三體唐詩》卷四高士奇輯注:“嘉祐此詩,蓋作于劉展、張景超亂浙西、平盧軍大掠之后,即寶應(yīng)二年(763)。”關(guān)于這次戰(zhàn)爭,《舊唐書·代宗紀(jì)》記載:寶應(yīng)二年三月,“丁未,袁傪破袁晁之眾于浙東”,“(四月)庚辰,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奏生擒袁晁,浙東州縣盡平”。同書《王棲曜傳》記載:“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臺州,連結(jié)郡縣,積眾二十萬,盡有浙東之地。御史中丞袁傪東討,奏棲曜與李長為偏將,聯(lián)日十余戰(zhàn),生擒袁晁收,復(fù)郡邑十六。”如果不是李嘉祐詩歌,后人可能很難了解這種正史記載不夠翔實(shí)的歷史事件。
此外,康熙《無錫縣志》還收錄了一些有關(guān)治河工程的詩歌,可與史料互為參證。張商英《留題惠山寺》,詩前小序?yàn)椤霸好瑑烧氵\(yùn)判曾孝蘊(yùn)作常潤京口、奔牛二閘成,集英殿修撰發(fā)運(yùn)使被旨相視,遂至惠山寺,留題以記行役”。
詩歌前幾句云:“咸陽獲重之明年,五月端午予泛船。二閘新成洞常潤,組練直貫吳松川。淮南柁師初入浙,借問邑里猶茫然。”詩歌詳述了張商英奉命視察京口、奔牛二閘的時(shí)間、路線、途行狀況。查《宋史·河渠志》,京口、瓜州、奔牛諸閘始建于元祐四年(1089),元符二年(1099)閏九月畢工,“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奔牛澳閘畢工。先是,兩浙轉(zhuǎn)運(yùn)判官曾孝蘊(yùn)獻(xiàn)澳閘利害,因命孝蘊(yùn)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啟閉日限之法”。詩歌中信手拈來的一筆,為歷史提供了可靠的佐證。
康熙《無錫縣志》中收錄的運(yùn)河詩歌以運(yùn)河區(qū)域?yàn)闀鴮懕尘埃尸F(xiàn)了豐富的主題,蘊(yùn)含了深厚的文化,是我們了解無錫運(yùn)河文化的一扇窗口,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有助于發(fā)掘無錫古運(yùn)河文化資源,提升城市形象魅力,為大運(yùn)河的文旅開發(fā)提供文獻(xiàn)依據(jù)。
注釋:
①傅崇蘭:《運(yùn)河史話》,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1年,第141頁。
③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yùn)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年,第77頁。
④劉文源:《文天祥詩集校箋》,中華書局,2017年,第616頁。
⑥談修:《惠山古今考》,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28頁。
⑦黃卬:《錫金識小錄》,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據(jù)乾隆十七年修光緒二十二年刊本影印,1983年,第1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