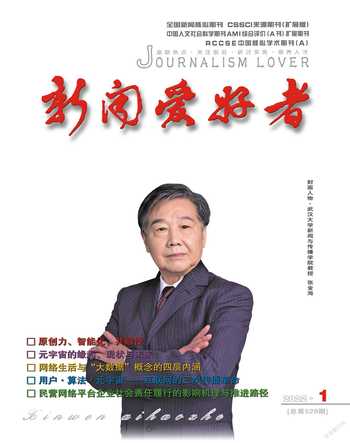新時期中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創作方法
關玲 翟元堃
【摘要】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自中國電視劇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并且始終是中國主流影視作品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年來,出現了大量經典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對建構國家形象、培養人民的愛國情感起到了重要作用。2021年時逢建黨百年,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贏得了廣泛熱議和好評,獲得了豆瓣9.3分的超高評分,是一部難得的藝術佳作,為后續該類題材作品的創作提供了啟示與范本。
【關鍵詞】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方法論
2021年6月,第27屆白玉蘭電視節在上海落下帷幕。時逢建黨百年之際,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獲得了最佳導演、原創編劇和最佳男主角三項大獎,再次引發了人們對于新時期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方法的討論。
《覺醒年代》講述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及廣大人民群眾在思想覺醒過程中遇到的矛盾、沖突、困境、抉擇和犧牲,對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如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帶來的風云巨變進行了深刻呈現,以此來證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勝出的必然性,藝術地再現了百年前中國一批有志青年追求真理的激情澎湃的光輝歲月。憑借其在人物塑造、視聽語言等方面的精細塑造與精良制作,贏得了口碑與收視率的雙豐收,它的成功標示著黨的十八大以來電視行業積極踐行黨的文藝工作方針的成果,為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創作提供了新范本。
一、藝術審美形式與主流話語表達的統一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同時包含了重大革命歷史、重要歷史人物等多個要素,因此在創作上比起其他類型的主旋律電視劇會多一些困難,藝術審美形式的可突破空間受到的限制也較多。藝術性過于濃厚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主流話語,而意識形態性過于濃厚又會讓作品充滿說教色彩。同時,隨著近年來題材空間的逐漸飽和,創作慣性的漸漸形成,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數量和質量都有下滑趨勢,除了少數優秀作品之外,題材重復、人物臉譜化、主題概念化、橋段僵化、修辭造作、戲劇性設計庸俗等現象比較突出。[1]講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影視作品有許多,《覺醒年代》通過運用各類藝術創新,講述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中國第一代先進知識分子以及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年等進步青年的覺醒和探索救國救民路線的過程,系統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邏輯以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必然性,塑造了雖身處晦暗不明的時代卻仍舊充滿激情的新文化知識分子群體,以極高的藝術水準完成了對建黨百年的獻禮,并且也獲得了廣大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的好評,做到了藝術審美形式與主流話語表達的統一。
在藝術審美形式方面,《覺醒年代》運用了許多隱喻鏡頭來提升作品的藝術性與可解讀性。比如毛澤東出場的畫面,天上下著大雨,毛澤東懷里抱著新一期《青年雜志》在人群中穿梭奔跑,在這樣混亂的環境中,毛澤東的出場帶有一種“他從風雨中走來”的意味。另外,螞蟻也是劇中一個重要的隱喻符號。第一次出現是在陳延年吃飯時,發現碗里有一只螞蟻,陳延年選擇將它放生,代表著陳延年心懷慈悲。第二次是在陳獨秀演講時,螞蟻順著陳獨秀面前的麥克風桿向上爬,意味著人民開始有了話語權。第三次出現在李大釗身邊,無論李大釗是什么樣的姿勢,螞蟻始終向著光往上爬,代表著人民的覺醒。這些象征符號和隱喻手法的運用,不僅增加了這部劇的藝術深度,也讓觀眾多了許多解讀與討論的空間,提升了觀眾的觀劇熱情。
同時,《覺醒年代》通過對題材和視角的突破重新建構了主流話語的表達方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在題材選擇、視角選擇以及人物設定上逐漸形成了較為固化的模式,比如題材在建國、建軍、建黨、重要戰爭等范圍內,人物設定為偉人、元帥、將軍等。這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是觀眾非常熟悉的,按部就班進行創作雖然比較安全,不會出錯,但也很難產生更多亮點和共鳴,久而久之,使得這類題材的作品逐漸往“命題作文”的方向靠攏,失去了對觀眾的吸引力。
《覺醒年代》另辟蹊徑,選擇從思想和文化層面入手去重新講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歷史,把思想與文化進行可視化呈現其實并非易事,但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2]在這一點上,主創團隊選擇了用新舊兩派思想爭論的方式來展現不同的思想觀、文化觀以及不同派別對于中國出路的探討,營造出了“百家爭鳴”的氛圍。觀眾在這種思想爭論的氛圍中,對中國共產黨是怎么來的、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歷史先輩們是在什么樣的環境下又經歷了怎樣的抉擇之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問題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和更深入的理解,這就自然而然地將文化演進的過程由器物層面、制度層面轉移到了思想層面。
二、寫實與寫意的統一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通常建立在真實的人物原型與歷史背景之上,于是如何平衡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的關系便成了這類電視劇要面臨的重要問題。作為建黨100周年的獻禮劇,《覺醒年代》在還原歷史事件和視聽語言的詩意化呈現等方面,均進行了很好的處理。
《覺醒年代》對劇中涉及的歷史場景進行了盡可能的真實還原。主創們在前期做了大量功課,小到一個開關、紐扣樣式,大到1∶1.2還原北大紅樓,整部劇共置340多個主要場景,甚至一道看似不起眼的車轍,是劇組用了38輛8噸以上的車,來回壓了3天,才壓出了劇中最后呈現出的效果。這些都展現出了主創們嚴謹的創作理念和真誠的創作態度,雖然這些服、化、道的細節并不承載真正的敘事功能,但卻能讓觀眾對當時的歷史與社會環境有了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增強了這部劇本身的歷史質感,從而獲得一種沉浸式觀劇體驗。
與此同時,《覺醒年代》中也用了大量詩意的內容,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中納入了“詩性內核”。比如“程門立雪”“三顧茅廬”“高山流水遇知音”等中國傳統文學典故融入其中,這些內容都是觀眾日常熟知的,觀眾很容易理解。陳獨秀在獄中唱《定風波》也表現了中國文人的風骨與氣節,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與中國傳統文學有著天然的契合感,二者結合能夠極大提升作品的詩意內涵。在人物動作的塑造上,魯迅寫完《狂人日記》之后躺在地上丟下筆的樣子、李大釗演講《庶民的勝利》時激情四射的樣子,都使得作品增加了許多浪漫色彩。同時,劇中配樂和畫面的運用也提升了作品的意境,使作品有了虛實相生的感覺,做到了影像構成和美學表達寫實與寫意的統一。
三、人物塑造立體化
從古羅馬時代賀拉斯的“定型說”,到恩格斯主張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的統一、人物的典型與個性的統一,人物的典型化和個性化問題一直是古今中外學者們探討的重要內容,在塑造人物形象時,《覺醒年代》拋棄了以往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慣用的“高大全”臉譜化的表現方式,而是將歷史人物的典型性與個性化進行了統一,并且與時代環境相結合,突出人物作為歷史推動者的一面。除塑造人物的典型性外,《覺醒年代》還善于從細節入手,展現人物日常生活的一面。比如陳獨秀與陳延年、陳喬年之間的矛盾,胡適的風流韻事,李大釗與家人相處之間的溫情都有所體現。甚至總是有兩個仆人跟著的守舊派代表辜鴻銘,也通過設置中國文化講座、參與與英國大使談判等情節彰顯出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愛國情懷以及對蔡元培知恩圖報的性格特點。總導演張永新在給《人民日報》的撰文中寫道:“《覺醒年代》要將劇中所涉及的歷史人物,從書本中的一個個名字還原為有血有肉的個體。”這些生活化的、有煙火氣的細節讓人物變得飽滿、立體、真實、接地氣,更能引發觀眾的共情。
“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3],這些深得民心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都是將歷史、思想和文化蘊藏在劇中角色的思想變化和行動變化上,通過塑造出一大批具體可感的人物形象,讓觀眾能夠對人物命運產生共情,進而移情到家國情懷上。比如劇中對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塑造,這些人不僅是劇中主角,也是當時那個時代的主角,描寫好他們的命運及思想轉變過程,也就相當于描寫好了中國歷史的命運及轉變過程。同時,一部優秀的作品中,配角也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覺醒年代》中蔡元培、辜鴻銘、陳延年、陳喬年等人,其實代表著當時中國社會中形形色色和他們有相同想法的大眾。整部劇其實并沒有刻意設置戲劇沖突,所有的沖突均來自人物之間情感、思想、道路的沖突,這就讓觀眾在看劇的時候,不自覺地與劇中人物共情,擔心他們的命運,與他們一起痛苦、一起憤怒、一起興奮、一起選擇,在與人物的共情中感受到或崢嶸或動亂的歲月。當然,人物的塑造也離不開服、化、道的支持,主創團隊對這些歷史人物形象進行了細致的考究,最后呈現出的人物形象盡量逼真地還原出了人物的本來形象,讓不少觀眾大呼“感覺歷史課本里的人物活了”。
縱觀近些年收獲了不少好評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無一例外都是立足現實本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原則,因而收獲了巨大的成功。馬克思主義理論把人民看作歷史主體,是歷史發展的真正承擔者,這使馬克思主義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理論有了本質的區別。[4]電視劇是人的電視劇,以人民為中心的藝術觀和創作觀共同塑造了新時期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熠熠生輝的“人民美學”,那些曾經活躍在教科書上的人名和歷史事件,通過這部電視劇被生動地展現出來,這也是這部劇被大眾津津樂道的地方之一。可以說,人物鮮活了,歷史才是鮮活的。
四、表達方式年輕化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曾經被認為“不接地氣”和“高高掛起”的一個最主要原因就在于沒有充分考慮到年輕人的訴求。但實際上,年輕群體對于優質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作品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他們希望能夠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歷史和表達愛國情感,因此這類題材的作品采用一種年輕化的表達方式,追求與年輕觀眾審美需求的深度共鳴就顯得格外重要。這里的“年輕化”表達方式,除了在情節構造、人物設置等藝術創作層面,還需要在精神層面打造出一個能與年輕觀眾進行精神對話的更高層次的藝術空間。
《覺醒年代》中,首先在人物設置方面,在尊重歷史和人物原型的基礎上,創作團隊將每一個人都塑造得非常立體,通過臺詞、動作的設置,使人物一方面是“歷史書上救中國的關鍵人物”,另一方面也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比如魯迅在教育部門口舉著“不干了”的牌子示威、陳獨秀看到《狂人日記》后難掩激動的心情喊出的“我要狠狠地親吻他”、蔡元培北大就職演講中的“救救孩子”等,這些內容不僅讓人物變得豐滿立體,也給了年輕觀眾許多二次創作的空間。一些年輕觀眾將劇中有趣的片段制作成表情包或短視頻,在社交平臺和視頻網站上傳播,無形中也擴大了作品的傳播范圍,增加了作品的影響力。
其次,在整部劇的線索設置方面,《覺醒年代》聚焦國家和民族的成長發展史,力求表現出在發展過程中一些比較重要的轉折點。其中,陳獨秀與陳延年、陳喬年這兩代人進行艱苦卓絕的探索救國道路的歷程,在一定程度上將青年成長與國家發展統一了起來,于是觀眾可以透過陳延年、陳喬年的成長歷程看到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歷程,打破了因年齡和時間帶來的共情阻礙。延年、喬年兩兄弟最后奔赴刑場時堅定的腳步,讓許多年輕觀眾為之落淚,展現出個體命運和家國命運的統一,使年輕觀眾在與角色共情的同時,內心的愛國情懷和使命感也會被喚起。許多觀眾看完劇后自發到陳延年、陳喬年的墓碑前獻花和手寫信,表達對他們的祭奠、緬懷和敬仰,也表達了當代青年對祖國的熱愛。導演張永新接受采訪時說“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覺醒年代》最好的續集”,可以說這是一部思想深度、歷史深度和藝術深度融為一體的優秀劇目。
五、結語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屬于中國電視劇類型中經久不衰的題材類型,但在創作上的局限往往較其他類型電視劇相對較多。但《覺醒年代》通過題材、視角、人物塑造等方面的突破與創新,在制作上展現出了較高的藝術水準,并且做到了藝術審美形式與主流話語表達、寫實與寫意、個體與群體、過去與現在的統一,非常符合當下中國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的收視訴求和審美需求,給觀眾帶來了情感與認知上的多重審美體驗,讓觀眾能夠連接當下與過去,形成跨時空的精神對話空間。同時,《覺醒年代》通過塑造一系列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通過他們的言行及思想碰撞,回答了“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問題,提升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的認同感、責任感與歸屬感,也為后續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創作提供了良好范本。
參考文獻:
[1]尹鴻,楊慧.歷史與美學的統一:重大歷史題材創作方法論探索——以《覺醒年代》為例[J].中國電視,2021(6):6-12.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4]徐迎新.建構人民美學的三個維度[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31-34.
[關玲為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院長、藝術學部副學部長、博士生導師;翟元堃為中國傳媒大學(電視策劃方向)碩士生]
編校:張紅玲
3686501908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