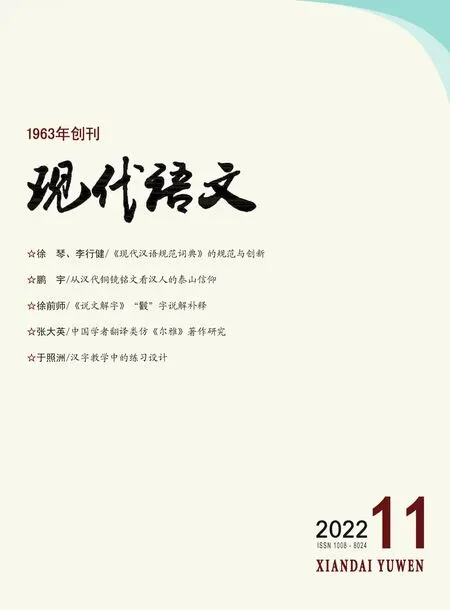“壸彝”考釋
劉艷紅,袁鑫懿
(東華理工大學 文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問題的提出
在北宋著名散文家曾鞏的作品中,共有60篇墓志,有25 篇是關于女性的,其中有3 篇墓志銘出現了“壸彝”或“壸有彝則”。例如:
(1)銘曰:性有能否,行有失得。一當于理,士有不克。淑哉夫人,秉是壸彝。周旋大小,無過無虧。(《永安縣君李氏墓志銘》)[1](P615)
(2)銘曰:允淑夫人,秉是壸彝。有韡車服,維寵嘉之。葬有卜壤,其吉在斯。推求美實,視此銘辭。(《雙君夫人邢氏墓志銘》)[1](P618)
(3)乃為其辭曰:女德在幽,而始人倫。詩有顯揚,以立生民。尚類于古,淑為夫人。壸有彝則,仔肩以身。(《夫人曾氏墓志銘》)[1](P631)
“壸彝”是古代典籍中的常用詞語,在女性的墓志中尤為常見,通常用于歌頌女性的高尚品德。《漢語大詞典》對“壸彝”的解釋是:“婦女的楷模、儀范。”那么,“壸彝”為何會產生“婦女的楷模”之義呢?我們認為,這與“壸”“彝”兩字的語義密切相關。本文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綜合性的大型古籍數據庫——中國基本古籍庫中的相關文獻,分別對“壸”“彝”的詞義進行考釋,并探析“壸彝”表“婦女的楷模”義的歷史邏輯和內在理據。
二、“壸”字考釋
值得注意的是,“壸”與“昆”的關系也十分密切。在上古語音系統中,“壸”為溪母,“昆”為見母,二字讀音相近。同時,“昆”的古音亦在文部,與“閫、困”的區別只在聲母的送氣不送氣之分。“昆”的金文字形為“”,“眾”的甲骨文字形為“”,二字的古文字形體皆像眾人在太陽底下從事勞動。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昆”是由“眾”分化而來的。我們認為,從字形上看,“昆”更像是人或物對“日”的“比附、依賴”。《說文解字·比部》:“比,密也。二人為從,反從為比。凡比之屬皆從比。”[4](P166)《周易·比卦·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5](P211)人類依賴太陽而生存、活動,就如同“昆仲”之間的互相比附、依賴。同時,由于月亮依賴太陽而發出光芒,因此,古人往往認為月亮是太陽的分化物。在眾多民族的神話傳說中,常常將“月”視為是女性、陰性。溫哥華島上的阿特人崇拜日神、月神,他們認為太陽為夫,月亮為妻。在阿爾奎色人的觀念中,月亮是太陽的妻子。在非洲大陸,上贊貝茲的至上神是太陽神納亞姆比,他的妻子是月神拿西勒勒。古埃及神話中的俄西里斯和伊西斯既是太陽和月亮,也是丈夫和妻子。壯族人也認為太陽、月亮、星星是一家,太陽是父親,月亮是母親,星星是孩子[6](P213)。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也把月亮看成是陰性的。唐代李淳風《乙巳占》卷二云:“夫月者,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7](P39)宋代陳師道《后山談叢》卷五云:“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8](P31)月亮不僅被視為陰性,而且與女性的信水有著密切關系。古人發現月亮的變化周期是二十八天,女性的信水也是二十八天一個周期,于是人們便將月亮與信水聯系起來,稱之為“月信”“月經”。由此可見,“昆”字是兼具了“日”“月”屬性的。正是因為它詮釋了古人“日月一體”的觀念,所以與“昆”相關的“昆侖”也具備了這兩種屬性:它既是日神黃帝的住所,同時又是月神西王母的住處,何新稱之為“天堂與地獄之山”[9](P118)。
“昆侖”同女性一樣,具有“陰”之屬性。《山海經·西山經》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這里的“下都”,即為“幽都”,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陰曹地府。天神陸吾的形貌是“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他與西王母一樣都具有虎之特征。《山海經·西山經》云:“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司天之厲及五殘。”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云:“厲及五殘,皆星名也……《月令》云:‘季春之月,命國儺。’鄭玄注:‘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是大陵主厲鬼,昴為西方宿,故西王母司之也。五殘者,《史記·天官書》云:‘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正義》云:‘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之分野。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七丈。見則五分毀敗之征,大臣誅亡之象。’西王母主刑殺,故又司此也。”[10](P146)可以看出,陸吾與西王母都是掌管人們生命及刑殺的“司命之神”。因此,他們的居住地“昆侖”便成為了鬼魂所在的“下都/幽都”,從而具備了“陰”之屬性。
“昆侖”還兼具“黑”義,而“黑”在古代的傳統觀念中也屬于“陰”。清代王筠《侍行記》卷五云:“考昆侖者當衡以理,勿求諸語。上古地名多用方言,昆侖乃胡人語,譯其聲無定字。或稱昆凌(東方朔《十洲記》)、混淪(鄭康成《周禮注》)、祈淪(王嘉《拾遺記》),要之為胡語‘喀喇’之轉音,猶言黑也。”[11](P22)程發韌在《昆侖之謎讀后感》一文中指出,“昆侖”一詞出于西戎,有“崇高”與“玄黑”二義。昆侖之發音為K、L,由喀喇(kara)一音之轉,或作哈拉,蕃語黑也。凡崇高之山,自遠而望,必呈青蔥之色。即有萬年積雪,其低壑部分,青蔥之色,仍能浮出空際。今新疆境內,以喀喇名者不可指數。如喀喇昆侖(大山)、喀喇哈斯(墨玉)、喀喇庫里(玄湖)其最著者。因而有“黑”義之物,被命名為“昆侖”[12](P536)。《舊唐書·南蠻傳》:“自林邑以南,皆卷發黑身,通號為‘昆侖’。”[13](P738)據唐代杜寶《大業拾遺錄》記載,隋煬帝大業四年將茄子改為昆侖紫瓜[14](P102)。可以看出,古代“昆侖”一詞確實是可以表示“黑”義的,這也再次證明了“昆”具有“陰”之屬性,而在古人觀念中,“陰”又是女子的顯著特征,因此,“昆”字與女子關系匪淺。與“昆”音近之“壸”,自然也會與“女子”產生一定的關聯。
那么,“壸”字又怎么發展出了“身份尊貴、地位崇高的女性”義的呢?下面,我們就對“壸”的初文進行深入探討。陳獨秀認為,“壸”的初文為“亞”。他解釋說:“(壸)”下之“”,即金文“亞”形;“囗”為宮垣,其中,空白處為宮中通道,四隅則宮中室,猶甲骨文“(宮)”字之“”部件。“(壸)”上部之“”,蓋象巷間止扉木橛,《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郭注:“,長杙,即長橛也。”故“壸”或作“閫”(《史記·馮唐傳》)。“(壸)”之從“”,猶“閫”之從“困”。《說文》:“橛,一曰門梱也。”《荀子》井里之厥,《晏子》作井里之困。困字,囗象墻垣,木即謂止扉之橛。因此,“亞”即“壸”之初形[15](P867)。朱芳圃指出:“原始社會有祀火之俗,于室之中央砌一形之塘,燃火其中,晝夜不息,視為神圣之所,無敢跨越。現今西南兄弟諸族,遺俗尚存,可資參證。故‘亞’為殷代宗彝中習見之圖銘,蓋所以象征祖先之神所依憑也。”[15](P868)
何新則認為,“亞”字古音近“宇”,就是“宇宙”之“宇”的本字。《爾雅·釋詁》:“宇,大也。”《淮南子·齊俗訓》:“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解字·宀部》:“宇,屋邊也。從宀于聲。《易》曰:‘上棟下宇。’”《詩經·豳風·七月》:“八月在宇。”陸德明釋文:“屋四垂為宇。”何新援引很多例證,力圖來證明“亞”的本字為“宇”[9](P12)。我們認為,“亞”字的本形,有可能是來源象征太陽的十字。正是因為太陽光芒四射,遍布于宇宙之間,所以才延伸出“宇宙”之義。從這一意義上說,“亞”字亦是古人太陽崇拜的反映。由于太陽給人類帶來光明和溫暖望,因此,世界很多民族都產生了太陽崇拜意識,并對太陽加以祭祀,在甲骨文中就有關于祭日的記載:
(4)貞燎于東母三牛。(《甲骨文合集》14339)
(5)燎于東母……暇三泵三。(《甲骨文合集》14341)
(6)乙巳卜,王賓日,弗賓日。(《甲骨文合集》32181)
(7)乙酉卜,佑出日、入日。(《懷特氏等所藏甲骨集》1569)
據考證,例(4)、例(5)中的“東母”,應為生十日的羲和,亦即太陽神,因此,“燎于東母”就是以火祭日。郭沫若認為,古人對日神有朝迎夕送的祭拜儀式,卜辭中的“賓日”“出日”等,正是對這種儀禮的歷史記錄[16](P492)。先秦時期在統祭天上諸神時,太陽神占據主神的地位。《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鄭玄注:“大,猶遍也。天之神,日為尊。”孔穎達疏:“而天之諸神,唯日為尊,故此祭者,日為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17](P53)可見,太陽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如上所述,“亞”無論是象征祖先之神所依憑,還是古人太陽崇拜的反映,都在古人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也由此而具有了“尊貴”之義。高田忠周曾指出:“亞字符當從工作為正,變作,亦作,又省作耳。工象天地人。二者,天地也。丨者,人也,工亦用為人形,……以工為人者,蓋尊貴之也。”[15](P866)就此而言,作為“亞”的后出字,“壸”能夠表示“尊貴”義,自在情理之中。
綜合以上分析,“閫”“困”“昆”皆可表“女性/陰性”義,與之音近義通的“壸”字,也與女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同時,“壸”的初文“亞”具有“尊貴”義,“壸”自然也可以表示“尊貴”義。兩者的疊加,就使得“壸”字發展出“身份尊貴的女性”這一詞義。
三、“彝”字考釋
關于“彝”字的發展流變與構字理據,馬薇庼曾有精到的分析:“彝,契文作,金文作。象雞形,縛其兩翼。為喙,為米,雞之所食,為足,蓋活雞也,從,捧雞以祭也,故契文彝之本義為祭享,引申之凡祭享之器皆稱為彝。”[15](P1269)
問題是,古代先民為什么要以雞來祭祀呢?郭沫若解釋說:“用雞的痕跡在彝字中可看出,彝字在古金文及卜辭均作二手奉雞的形式。雞在六畜中應是最先為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彝字竟為雞所專用,也就是最初用的犧牲是雞的表現。”[18](P179)古人認為雄雞守夜不失時、天明早報曉,《說文解字·隹部》:“雞,知時畜也。”[4](P71)《風俗通義》卷八引《青史子書》:“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19](P128)因為雞與太陽升起的東方相對應,所以被古人認為具有喚起太陽的能力。《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引郭璞《玄中記》云:“東南有桃都山,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太陽一旦升起,鬼祟就會退去,因此,雞又被賦予了避禍就吉的神力。《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八《神異經》云:“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黃父,又名食邪。以鬼為飯,以霧為漿也。”[20](P217)由于雞與專捉惡鬼的神人相伴,于是便成為鎮服鬼魅的神物。南朝齊梁時期陶弘景《真誥》云:“學道山中,宜養白雞白犬,可以避邪。”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在記載正月初一的民間風俗時說:“帖畫雞于戶上,懸葦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21](P15)近年在出土文物中也發現,漢代以來的墓葬中有隨葬木雞和陪葬雞形枕頭的習俗。由于雞秉持了文、武、勇、仁、信五種美德,具有溝通人神、鎮服鬼魅的神奇功能,寄寓著人們趨吉避兇、祈求平安吉祥的美好愿望,因此,它不僅成為光明神圣、尊貴祥瑞的象征,也成為古代祭祀時的重要祭品。與雞崇拜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彝”字,由此而產生出“尊貴”“崇高”之義,亦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劉節認為,“彝”為氏族圖騰,最初的彝是拿實物來做的,所以甲骨文里是從兩手執玄鳥形[15](P1266)。《詩經·商頌·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是殷商時期的圖騰,被認為是商部族的先妣。先民們將玄鳥視為生育之神,在春天玄鳥飛來之時,要舉行祈子活動。《禮記·月令》:“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鄭玄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17](P325)《說文解字·乚部》:“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從孚從乚。乚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故乳從乚。請子必以乚至之日者,乚,春風來,秋風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4](P247)南宋羅愿《爾雅翼·釋鳥·燕》云:“(燕)以春風來,秋風去,開生之候。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以請子。契因是而生,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22](P376)由于玄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按照巫術中的感應律,可以借助玄鳥的神力來驅除邪祟,保佑平安,于是玄鳥便成為氏族所崇拜的圖騰。因此,依據劉節的觀點,“彝”作為氏族圖騰,自然會產生出“尊尚、崇尚”義。
《說文解字·糸部》:“彝,宗廟常器也。”段玉裁注:“彝本常器,故引申為彝常。《大雅》:‘民之秉彝。’傳曰:‘彝,常也。’”[2](P209)我們認為,這里的“常”可以理解為“尚”的假借字。俞樾《群經平議·毛詩四》“曰商是常”條云:“古常、尚通用。”[23](P190)“尚”字的本義為煙氣自窗戶上騰,由此可以引申出“高出”義,由“高出”義又可引申出“崇高”“尊尚”義。如前所述,無論是按照郭沫若的觀點,還是按照劉節的觀點,“彝”都有和先民的圖騰崇拜密切相關,并在古代祭祀時承擔著重要功能。因此,“彝”自然也成為祭祀時所崇尚的器物,由此可以引申出“尊尚、崇尚”義,在這一基礎上,又引申出“儀式、模范”義。
綜上所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基本古籍庫中的相關文獻,分別對“壸”“彝”的詞義進行了考釋,并探析了“壸彝”表“婦女的楷模”義的歷史邏輯和內在理據。研究顯示,“壸”與“閫”“困”“昆”音近義通,均與女性/陰性存在著密切聯系;同時,“壸”與“亞”實為一字,“壸”的初文“亞”具有“尊貴”義,“壸”自然也可以表示“尊貴”義。兩者的疊加,就使得“壸”字發展出“身份尊貴的女性”這一詞義。“彝”則和先民的圖騰崇拜密切相關,在古代祭祀時承擔著重要功能,由此引申出“尊尚、崇尚”義,又由“尊尚、崇尚”義引申出“儀式、模范”義。由兩字組成的“壸彝”一詞,便衍生出“婦女的楷模、儀范”義。在曾鞏的三篇女性墓志銘中,不僅記載了李氏“周旋大小,無過無虧”、邢氏“經理其家,使無內憂”、曾氏“孝友慈順”“仔肩以身”的模范事跡,更通過“壸彝”這一詞語贊美了墓主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風范,表達了作者對這些女性的欽佩之情、推崇之義,希望當時及后世女性能向這些墓主學習,將她們的行為與品德奉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