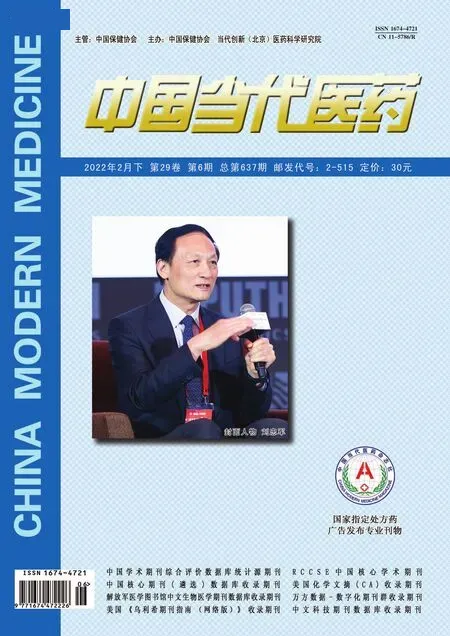化療引起骨髓抑制的肺癌患者的化療前常規檢查分析
賴富治 杜玉霞 周志斌
1.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服務中心,福建泉州 362000;2.福建省呼吸醫學中心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福建泉州 362000;3.福建省石獅市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福建石獅 362700
肺癌是全球癌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預后不良,目前位于我國惡性腫瘤發病率之首,5年生存率僅為16.8%[1-2]。近年來,隨著針對肺癌驅動突變基因的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的進展,肺癌的治療取得了飛速發展。但化療仍然是肺癌中晚期患者的主要治療手段之一,尤其是對一些不具備靶向或免疫治療條件的人群。對于化療預期收益的評估,有助于優化化療方案,骨髓抑制是化療的主要副作用,化療引起骨髓抑制(chemotherapy-induced myelosuppression,CIM)的后果包括貧血、血小板(platelt,PLT)和中性粒細胞(neutrophils,NEUT)減少癥,所有這些都會導致嚴重的并發癥,并限制患者按時和按標準治療劑量接受化療的能力。從而降低治療效果。一項調查研究顯示79%的患者因化療相關骨髓抑制接受治療,64%的患者改變化療劑量[3]。化療毒性的有效管理可能會導致住院時間縮短,對化療骨髓抑制的預測可能為臨床提供制定干預策略的機會,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或消除化療的預期副作用。然而,目前缺乏可靠的預估CIM 的指標。化療前常規檢查是化療前的常規步驟,容易獲得,探討其與CIM 的關系,具有操作的簡便性及可及性。本研究收集患者化療前常規檢查,研究相關指標與CIM的關系,為化療前藥物方案的選擇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選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呼吸科收治的76 例配對成功的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按照化療后有無骨髓抑制分為試驗組(38 例,CIM 患者)和對照組(38 例,非CIM患者)。試驗組若出現多次化療骨髓抑制,收集首次骨髓抑制的臨床資料。試驗組與對照組按照腫瘤病理類型、分期、性別、化療方案、化療周期1∶1 配對而成。兩組患者中男性均為33 例,女性均為5 例;小細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均為13 例,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均為25 例,其中腺癌均為13 例,鱗癌均為12 例。試驗組中,平均年齡(59.95±9.18)歲;體力狀態評分(1.24±0.59)分。對照組中,平均年齡(61.45±6.96)歲;體力狀態評分(1.26±0.50)分。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納入標準:①肺癌診斷、分期明確,肺癌診斷分期采用第7 版TNM 分級標準[1];②無合并其他腫瘤或既往有其他腫瘤病史;排除標準:①首次化療不在福建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呼吸科實施;②住院資料不完整;③無合適匹配條件的患者。
1.2 方法
38 對配對成功的肺癌患者,35 對接受聯合鉑類的兩藥化療,3 對接受非鉑類單藥化療方案,化療2周期后進行療效評價。化療方案中,培美曲塞、伊立替康、多西他賽、依托泊苷、長春瑞濱和吉西他濱聯合鉑類化療各12、8、7、4、2 和2 對。培美曲塞、伊立替康、多西他賽單藥化療各1 對。
1.3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1.3.1 觀察指標 ①收集兩組患者化療前的一般檢查結果,包括:脈搏(pulse P)、平均動脈壓(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體表面積(body surface area,BSA)。②常規檢驗,包括:血常規指標、生化指標、血腫瘤標志物;血常規指標包括:白細胞(white blood cell,WBC)、NEUT、血紅蛋白(hemoglobin,HGB)濃度、PLT;生化指標包括:白蛋白(albumin,ALB)、堿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乳酸脫氫酶(lactic dehydrogenase,LDH)、肌酐清除率(creatinine clearance,Ccr);腫瘤標志物包括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神經氨酸烯醇化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細胞角蛋白19 片段抗原21-1(cytokeratin 19 fragment antigen 21-1,Cyfra21-1)、腫瘤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
1.3.2 評價標準 ①按照WHO 化療毒性評定標準將骨髓抑制分為0~Ⅳ級[4]。其中WBC 以4.0、3.0、2.0、1.0(×109/L)為界值,HGB 以110、95、80、65(g/L)為界值,PLT 以100、75、50、25(×109/L)為界值。②化療第3周期開始前,應用RECIST 對已完成的2 周期化療療效進行評價,療效分為完全緩解(complete response,CR)、部分緩解(partial response,PR)、穩定(stable disease,SD)及進展(progressive disease,PD)。CR:所有目標病癥消失,無新病灶,腫瘤標記下降至正常;PR:所有基線目標病灶最長徑總和減少≥30%;SD: 所有基線目標病灶最長徑總和縮小但未達PR,或增大未達PD;PD:已記錄到的最小目標病灶最長徑總和增大≥20%,或出現新病灶[5]。為進一步量化兩組之間的療效差異,將療效為完全緩解、部分緩解、穩定及進展的患者分別按3、2、1、0 分進行評分。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用獨立樣本t 檢驗,組內比較用配對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化療前一般檢查的比較
兩組患者的P、MAP、BSA 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兩組患者化療前一般檢查指標的比較(±s)

表1 兩組患者化療前一般檢查指標的比較(±s)
注 1 mmHg=0.133 kPa;P:脈搏;MAP:平均動脈壓;BSA:體表面積
images/BZ_65_1275_2574_2268_2629.png試驗組對照組t 值P 值83.4±12.0 81.1±19.1 1.031 0.309 117.0±18.3 113.6±13.9 0.837 0.408 1.63±0.12 1.58±0.13 1.622 0.113
2.2 兩組患者化療前常規檢驗結果的比較
試驗組的WBC、ALP、NSE 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血常規指標、生化指標、腫瘤標志物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兩組患者化療前常規檢驗指標的比較(±s)
注 WBC:白細胞;NEUT:中性粒細胞;HGB:血紅蛋白;PLT:血小板;ALB:白蛋白;ALP:堿性磷酸酶;LDH:乳酸脫氫酶;Ccr:肌酐清除率;CEA:癌胚抗原;NSE:神經氨酸烯醇化酶;CA199:腫瘤抗原199;Cyfra21-1:細胞角蛋白19 片段抗原21-1;非正態分布數據均經變量轉換后進行比較
組別 WBC(×109/L)NEUT(×109/L)HGB(g/L)PLT(×109/L)ALB(g/L)ALP(U/L)LDH(U/L)Ccr(ml/min)CEA(ng/ml)NSE(ng/ml)CA199(kU/L)Cyfra21-1(ng/ml)試驗組對照組t 值P 值7.10±2.83 8.32±3.13 2.062 0.046 4.52±2.53 5.49±3.00 1.814 0.078 126.6±17.0 127.6±15.2 0.288 0.775 257.8±86.2 306.8±118.7 1.897 0.066 38.6±5.3 38.2±5.1 0.363 0.718 78.2±18.3 107.9±70.4 2.614 0.013 197.7±82.6 256.3±193.9 1.530 0.135 87.1±33.9 91.5±20.4 0.714 0.480 28.7±70.4 38.2±77.4 0.553 0.584 25.2±25.6 58.9±81.6 2.819 0.008 54.7±27.4 85.9±211.2 0.691 0.494 8.54±12.6 14.6±18.4 1.624 0.113
2.3 兩組患者化療后2 周期療效的比較
38 對患者中,15 對患者的2 周期化療后療效無法比較,其中因合并癥或并發癥導致病情加重中止化療6 例;個人原因拒絕再次化療或拒絕復診5 例;Ⅳ級骨髓抑制中止化療4 例; 其余23 對患者均于化療第3 周期完成全身系統檢查,評估2 周期化療后腫瘤治療療效。23 對患者試驗組2 周期療效評分為(1.39±0.66)分,高于對照組的(0.96±0.24)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865,P<0.05)。
3 討論
CIM 是肺癌化療常見副作用。化療前血WBC 水平是CIM 的影響因素。骨髓轉移患者腫瘤細胞進入骨髓造血系統,可加速造血細胞的死亡,對于化療前即存在WBC 或PLT 降低的患者,化療后更易發生骨髓抑制。本研究結果顯示,試驗組患者化療前WBC 水平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血WBC 水平是肺癌患者出現CIM 的影響因素之一。但兩者之間的NEUT、HGB 及PLT 并沒有明顯差異。ALP 廣泛存在于人體組織,研究顯示ALP 為NSCLC患者發生骨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骨髓轉移的患者ALP 水平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并且NSCLC 患者的血漿游離DNA 片段與ALP 呈正相關性[6-8]。而本研究顯示試驗組的ALP 水平低于對照組,說明ALP 水平較高的患者對化療藥可能具有較好的耐受性。
既往研究顯示,治療前NSE 可作為治療反應的敏感指標,對治療有反應的患者的治療前NSE 水平低[9]。同樣的,在接受化療的SCLC 患者中,NSE 水平升高的患者的完全緩解率顯著低于NSE 正常水平的患者。NSE 水平升高的患者對預后產生不利影響,血清NSE 水平正常且體力狀態評分良好的患者預后良好,而血清NSE 升高的患者骨轉移更多、生存期更短[10-12]。此外,與正常NSE 水平的患者相比,NSE 升高患者腦轉移的風險增加,是總體生存率的獨立預后因素[13-14]。國內亦有研究報道NSE≥15 ng/ml 是影響NSCLC 患者手術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15]。與既往的研究類似,本研究同樣觀察到血NSE 水平較低的CIM 組2周期化療后的療效好于非CIM 組患者。除NSE 外,也有報道Cyfra 21-1、胃泌素前體釋放肽的水平亦與不良預后相關[12,16-17],但是本研究并未發現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Cyfra 21-1 的差異。Netterberg 等[18]發現同一化療方案中,更高絕對計量的標準化療藥物與提高生存率的趨勢相關,低毒性可能與低暴露相關,因此效果欠佳。肺癌患者尤其是SCLC,血NSE 水平高,可能提示更高的腫瘤負荷,常規化療劑量存在劑量相對不足的可能。
較多的研究顯示CIM 患者具有比非CIM 患者更好的療效[18-19]。Cameron 等[19]研究顯示與沒有NEUT 減少癥的患者相比,NEUT 減少患者的生存率更高,并且其對結局的影響大于年齡或藥物劑量強度,本研究結果亦顯示,試驗組2 周期化療后療效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并非骨髓抑制越嚴重,治療預后越好,因為藥物本身的超敏反應及對機體本身的過度傷害可能抵消化療帶來的益處。研究顯示局限期的SCLC 患者化療后出現0~2 級骨髓抑制的患者總生存期明顯優于3~4 級的患者[10]。因此,適當的骨髓抑制可能與更好的治療效果相關。
綜上所述,肺癌患者較低的血WBC、ALP、NSE 水平更易出現CIM,而CIM 則與短期較好的臨床療效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