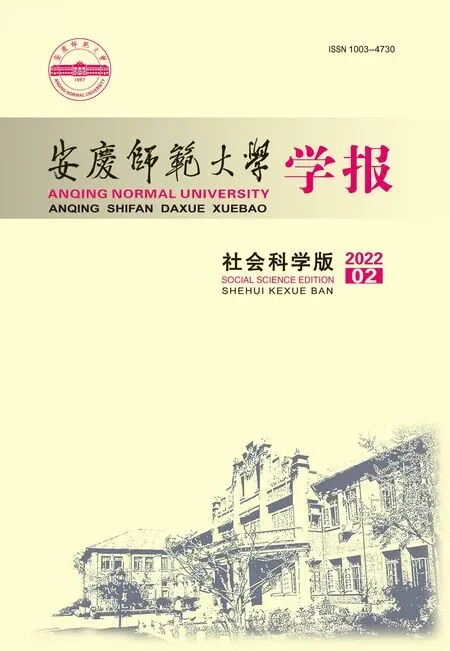“十召堅辭一羽毛”:方以智“十辭疏”考論
鄭晨晨
(安慶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安徽 安慶 246011)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號曼公,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面對易代之際的亂世紛爭,在以身殉國未果的情況下,他毅然逃禪,成為明遺民中的代表人物。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方以智的生平事跡一直備受關注,但學界所論多是關于他的逃禪和死節,其南明永歷年間長達四年之久的辭官行為,則并未引起足夠重視。
實際上,方以智的辭官發生在亡國和逃禪之間,是其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對其自身,乃至整個永歷朝所造成的影響都不容忽視①亡國作為最慘烈的時代背景,深刻影響著方以智其后的舉動,自然也包括辭官行為,而逃禪在某種意義上則可以看作是方以智辭官選擇的接續。若能清楚揭示出方以智辭官的緣由,那么諸多與此有關的行為也將得到更合理的解釋。。其時,南明朝廷偏居一隅,政權更替不斷,內憂外患不絕。當權者們卻深陷權力的爭斗,無意為復國而戰。南明的形勢岌岌可危,帝國的大廈搖搖欲墜。危難之際,永歷帝數次以內閣大學士之職征召方以智,方以智卻堅辭任命,于輾轉流離中留下了扣人心弦的“十辭疏”②關于“十辭疏”,學界尚沒有專門的研究成果,僅陳璐的碩士論文《方以智散文研究》(閩南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論文,第90-95頁)中有所論及,作者雖對方以智辭官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但并未展開深入探究。。在這十封辭疏中,方以智對辭官一事作了詳盡的解釋,其中不僅涉及到其本人四年間的遭際,對南明的時局也多有論及。因此,我們得以返回現場,對方以智的心路歷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歷史線索,展開更為深入的探析。
一、“十辭疏”的篇目界定
“十辭疏”是永歷元年(1647)至永歷四年(1650)間,方以智為辭永歷帝內閣之召所作的十篇文章。當時,南明永歷帝初立,方以智代言頒布,后任宮詹。因與司禮監秉筆太監王坤不和,放舟而去。豈料,元年二月初五,永歷帝復以東閣大學士之任召之,方以智力辭不就,故作“十辭疏”。其所作諸篇雖名為“十辭疏”,其中明確題為辭疏的,卻僅有《四辭請罪疏》《六辭入直疏》《七辭疏》《八辭疏》《九辭疏》《十辭疏》六篇。經筆者推論,余下四篇應為《答吳年伯書》《夫夷山寄諸朝貴書》《夫夷山再辭疏》和《請修史疏》。
首先,從時間上看。《四辭請罪疏》和《六辭入直疏》的創作時間均十分明確,分別作于戊子(1648)八月和己丑(1649)九月。據此,前三封辭疏必然作于永歷二年(1648)八月之前。《四辭請罪疏》中又提到“臣自元年三月再疏陳辭”[1]588,說明上一封辭疏應當作于永歷元年三月,意即前三封辭疏均作于永歷元年,且永歷帝初次下詔是在元年二月,如此便進一步將范圍縮小到永歷元年二月至三月間。符合這一條件的有《答吳年伯書》(作于二月)、《夫夷山寄諸朝貴書》(作于三月)。五辭疏則應作于永歷二年八月至永歷三年(1649)九月之間。符合這一條件的有《請修史疏》(作于永歷二年十二月)和《寄朝中諸公書》(作于永歷三年春)。其次,就內容而言。在明確題為辭疏的六篇中,《四辭請罪疏》銜接了前三封辭疏與之后的數篇辭疏,內容顯得尤為重要。疏中,方以智首先詳細描寫了元年三月至今的經歷,來解釋何以對永歷帝之召未有應答。并隨即就此自陳其罪:
一年以來,臣凡八奉溫綸,三蒙特使,而臣曾不能一有應答,此則臣之罪也!權奸亂政,臣每畏忌其鋒,不能抗疏劾爭,此則臣之罪也。丑■憑陵,臣僅萬苦伏匿,自保短發,不能起義嬰城,與蕭曠等罵賊而死,此則臣之罪也[1]590。
永歷元年至二年間,永歷帝數次專派特使,以內閣之職召方以智入朝。方以智本人亦在《九辭疏》中寫道:“從來朝廷召用新卜,不過降麻,敦起耆舊老成,方遣專使。”[1]598永歷帝的厚遇由此可見,但方以智始終沒有給出肯定的答復。君有詔而臣不應,這在當時堪稱逆罪。因此,方以智必然要對辭官之事有所交代,這也是他會以較大篇幅記錄行程的原因。只是,此處所列的后兩條卻讓人有些難以理解。權奸當朝,方以智以未能彈劾力爭為己罪;賊軍頻至,他又以未能誓死與之抗爭為己罪。既是對自己的無所作為感到愧疚,當此內憂外患之際,則更應入朝為官、施展抱負。然而,方以智似乎并沒有發憤圖強的打算,反倒以此“三罪”為辭,試圖婉拒永歷帝的征召。可見,不論內中有何曲折,方以智的最終目的都是在于辭官。
其實,在辭疏的開頭,方以智就已明確提出“乞賜處分事”[1]588,文末又再次“伏乞明賜處分,以肅綱紀”[1]590,足以看出他的決心。至于辭官的原因,從文中來看,應是對自己的“才之不堪”[1]590有所顧慮。且疏中有“閣臣”明旨,說明永歷帝征召的職位便是內閣大學士。也就是說,《四辭請罪疏》是永歷二年八月方以智為推辭內閣之任所作的辭疏,辭官的原因是自覺才能不堪。
此后的幾封辭疏中,方以智均表達了不愿出任內閣之職的想法。《六辭入直疏》中明確寫道:“伏乞皇上收回閣銜,免其入直。”[1]594《七辭疏》亦稱:“實無分毫之功、尺寸之才,何敢叨冒宰相,以誤國欺君?”[1]595《八辭疏》以為:“疏散之才,實不足以濟國匡時。”[1]597《九辭疏》則認為:“臣之不可為宰相,非獨臣自知之審也,人皆知之。”[1]598《十辭疏》堅稱:“才卑庸劣,叨留史官,已為過分,何敢冒忝揆地,誤國茍榮?”[1]600方以智固辭的態度十分明確。由此可見,“十辭疏”的主旨便是固辭內閣大學士之職,且這一主旨在十封辭疏中貫穿始終。
既然要達到辭官的目的,那么方以智所作辭疏中必然有明確推辭的言語,且相鄰辭疏之間應有一定的連續性。《答吳年伯書》開篇即提到:“不謂復濫及此,捧綸讀諭,病人驚懼失魄矣。”[1]511此當是方以智首次奉詔。《夫夷山寄諸朝貴書》中稱“得吳年伯書,始知不免”[1]512,并以“三不能”“三可笑”“三不便”為由推辭。以此推測,吳炳的來信即是就內閣之召規勸方以智,故而才有后文的“求以原官”[1]513,可惜此文今已不見。另外,《十辭疏》寫道:“臣第三辭疏,引鄭綮之辭。”[1]599《夫夷山再辭疏》中恰有“唐鄭綮之歇后之誚”[1]588云云,且辭疏中亦有“若非常之任,則臣萬萬不敢冒受,以誤國家”[1]588的說法。因此,《答吳年伯書》《夫夷山寄諸朝貴書》《夫夷山再辭疏》三篇應屬辭疏無疑。
至于《請修史疏》和《寄朝中諸公書》,前者明顯是為辭官而作,后者則僅是就時政發表看法、提出建議。《請修史疏》的開頭,方以智就謄抄永歷帝的詔書,以示對圣恩的感激。雖有表達出為史官的意愿,但他的最終目的仍是推辭閣職。正如文中所述:“倘蒙天恩,罷其入職,但守翰院,老為史官。”[1]591也就是說,史官之職只是方以智的以退為進。此外,《六辭入直疏》中也提到了《史學自當盡職》一疏[1]592,即《請修史疏》,表明兩封辭疏是前后接續,并有所關聯的。綜合來看,五辭疏當是《請修史疏》。
綜上,筆者以為,就現存材料來看,方以智的“十辭疏”應是《答吳年伯書》《夫夷山寄諸朝貴書》《夫夷山再辭疏》《四辭請罪疏》《請修史疏》《六辭入直疏》《七辭疏》《八辭疏》《九辭疏》《十辭疏》這十篇文章。在這十封辭疏中,方以智明確表達了不愿出仕內閣之職的意愿,并羅列了各種理由來說明辭官的合理性。在南明王朝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情形下,方以智的濟世之志本可有機會得以實踐,他卻堅定地數辭征召,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二、“十辭疏”中的辭官緣由
“十辭疏”中,方以智堅定地表明了不愿出任閣職的態度,但畢竟是呈給永歷帝的辭疏,應當要有合理的解釋。因此,在十封辭疏中,方以智均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論述,并給出了辭官的幾個理由。
(一)身患痼疾之限
方以智在“十辭疏”中反復強調了自己身體狀況的惡劣。《答吳年伯書》中,他一開始就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病人,稱“捧綸讀諭,病人驚懼失魄矣”[1]511。此外,他還自陳病史:“自木石海濱,冤憤入骨,沉病一年,有感即發。”[1]511-512不僅如此,已然危重的病情尚有進一步加重的趨勢。“近日嘔血之后,益覺虛仆,目昏氣逆,頭大如箕,顧影殘生,無復人理。”[1]512《夫夷山寄諸朝貴書》中,他又將病情列為難當重任的“一不能”,寫道:“病且一年,今桂林復發之后,僅存人形耳。近日目昏不見,加以氣逆,一有所思,則暈大如斗,何以勝勞乎?一不能也。”[1]513次月,方以智作《夫夷山再辭疏》,更是自稱“年來憂憤,遂得痼疾,人且憐之為廢人矣”[1]588。《四辭請罪疏》中也不乏對身體狀況的描寫,如“冒病投小艇”[1]588“孤身強病”“稿身骨立”[1]589,都在無意間透露了積病未愈的情況。《請修史疏》亦稱“疾病連年,慮入骨髓,近者粗能拜起,而腠理已殘”[1]591,且特意強調“此詔使臣之所親見也”[1]591。《六辭入直疏》則進一步說明了“積病以閑可養,狂直以冷可免”[1]593的動機。《九辭疏》也提到“病骨支離,毫無資藉”[1]599。《十辭疏》中,方以智則再次于請罪后表明自己已是“木石殘喘”,不僅“舊疾時發”,且“膏肓之癥,增發無次”[1]600。并第一次明確辯解,“非直以病為辭”[1]600。顯然,方以智的病貫穿“十辭疏”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影響因素。時年方以智36 歲,在他早期和同期的作品中均有諸多關于疾病的記載。據筆者統計,此前,方以智所患的疾病主要包括消渴、癰疽、水腫、眼疾等①方以智的詩文中多有關于所患疾病直接的記載。消渴病:《病中作萬索詩書此》有“消渴**行”(《方以智全書:第九冊》,黃山書社,2018年版,第108頁);《又用前韻》有“醉飽反令消渴甚”(同上,第137頁);《秦淮漫興十首·其七》有“消渴傷心學酒徒”(同上,第198頁)。癰疽:《懷龔孝升蘄令·其三》有“中年恐病疽”(同上,第93頁);《又與農父、克咸夜談作》有“腹心此日患癰疽”(同上,第164頁)。水腫:《聞事有感》有“腰肢患疾偏生腫,手足皆疲更剝膚”(同上,第138頁)。眼疾:《過梧州卡》有“病眼耐摩挲”(《方以智全書:第十冊》,黃山書社,2018 年版,第257 頁);《病目》有“欲除文字障,左目竟無光”(同上);《書周思皇紙》有“止匡廬,養翳目”(同上,第29頁)。按,筆者以為,方以智所患的主要疾病是消渴,類似于現代醫學中的糖尿病。。這些疾病深深困擾著方以智,在他的詩中時常能見到諸如“今歲妨多病”(《乙亥元日侍大母仲姑坐志感》)[1]83、“寒暑常有疾”(《自簡少年所作率爾放歌》)[1]48、“一病嘗旬月”(《出入愁十首·其十》)[1]95的記載。疾病對方以智的人生產生了重大影響,以至于他的結局都曾被認為是“疽發背而死”。
“十辭疏”中,方以智所提到的疾病主要包括虛勞和心悸②虛勞:《答吳年伯書》載有“近日嘔血之后,益覺虛仆,目昏氣逆,頭大如箕,顧影殘生,無復人理。”心悸:《夫夷山寄諸朝貴書》載有“即得怔忡驚悸、嘔血頭暈之癥。”虛勞是現代醫學的慢性消耗性和功能衰退性疾病,心悸則包括各種原因導致的心律失常。。同一時期所作的《九龍盆飯僧題辭》中,也有“理疴蓮潭剎中,日與芐苓伍”[1]514之句,芐即地黃,苓即茯苓,二者很可能是方以智用以調治身體的藥物。其永歷三年所作的《祭姚默先文》中,亦有“入山病矣”[1]553的記載。此外,他還在此時期所作的數篇文章中自稱“病夫”。不難想見,疾病確實對方以智造成了較大的困擾。而且吳炳和方以智原本都是追隨永歷帝的,后因方以智“倉促載病”[1]605,才追駕不及,這也就意味著疾病已經影響到了他的行程。因此,“十辭疏”中所描述的病情是有其合理性的,只是癥狀是否像方以智所陳述的那般嚴重,卻要另當別論了。
辭官期間,方以智幾經輾轉,四處逃亡,如果他的身體狀況確如描述的那般惡劣,恐怕很難承受長途奔勞。且從方以智之后的行蹤中也不難看出,他憑借著堅定的信念和強烈的使命感,一直頑強地與疾病作斗爭。即使身患多種疾病,他依然筆耕不輟,并積極參與反清復明斗爭。可見,痼疾纏身固然對方以智的抉擇產生了一些影響,但并不是其辭官的決定性因素。亂世之時,士人們常以疾病為喻,表達對家國天下的憂患之情。方以智很有可能也只是以夸大的疾病癥狀,來表明其憂國日久、心系天下的情懷。
(二)性情狂直之慮
病情之外,方以智也多次論及自身性格上的缺陷。在《答吳年伯書》中,他自稱“賤性狂直,外放內狹,與人齟齬,動而得禍”[1]512。《夫夷山寄諸朝貴書》中他則將“賤性狂直”列為“二不能”,并補充以“見人之不善,則若不能容。今日之勢,能一刻與人處乎”[1]513。此外,“三不便”也是“賤性外和內方”[1]513。性情方面,方以智還始終以“狂”自認①“狂生”稱謂在方以智早年的詩作中也經常出現,但當時所謂的“狂”,與其說是一種精神狀態,倒不如說是由現實遭遇而產生的一種宣泄行為。與年少時的慷慨悲歌不同,此時,方以智再次以“狂”自認,面臨的境遇比數年前更加嚴峻。亂世中,死生只在一瞬間,如果連自身都難以保全,更遑論為國效力了。因此,在宣泄之外,方以智的這種行為可能也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夫夷山再辭疏》稱:“臣秉性疏直,動即多忤,半生消骯臟于詩酒,人目之為狂生。”[1]588《九辭疏》亦有:“臣不惟半世疏狂,無益世事,兼且天性直率,動與物忤,覯閔受忌,無禍不歷,以言仕宦,竟屬廢人。”[1]598《十辭疏》也稱:“臣性疏易,少頗不羈。”[1]599
不難看出,性情狂直也是方以智辭官的原因之一。他在早年即意識到:“智性疏散,不知事事,言語過失,多不能免。”(《膝寓信筆》)[2]方以智自知性情疏散,很容易有所過失而得罪于人。當前的局勢之危急,更讓他很難不有所顧忌。顯然,性情狂直也是方以智的托辭,其最終目的是為了避禍。至于何以需要避禍,細讀之下,便可在自稱“狂直”之余窺見禍事的源頭,即與朝臣的政見不合。《夫夷山寄諸朝貴書》中的“一不便”和“二不便”正展現了這種政見不合:
弟議廢三衙門,以六曹帶之,分班直中書,又欲廢巡方、廢監司,今可行乎?一不便也。愚議不必每事差朝臣,今諸公乞差者差矣,朝堂幾空,得無怪乎?二不便也[1]513。
議廢之事不可行,議行之事不可用,方以智為官的意愿難免會有所消減。況且,這兩條僅是針對朝廷的行政制度而言,便已無法實行,那么,在根本性問題上的分歧之大就更加可以想見了。亂世之中本就難以自保,若再與當權者有所抵牾,自身的安全將更加難以得到保障。更何況,方以智之所以辭去宮詹之職,正是因為王坤的弄權。
此外,方以智的被舉薦亦不排除與黨爭有所關聯。雖無確切史料記載,但由吳炳之寄書可知,他在此事中應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鑒于吳炳是由瞿式耜推薦入閣,且方以智與作為父執的瞿式耜往來密切,瞿式耜亦有規勸方以智的舉動,或可推斷三人間存在著某種更為隱秘的聯系。瞿式耜《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中曾稱:
上質地甚好,真是可以為堯、舜,而所苦自幼失學,全未讀書。今須博學詞臣,大開經筵,終日講學究,而內去其口銜無憲、擅作威福者,毋使煬灶;再得一二有擔當力量閣臣,每事主持;不為群奸所煽,將來猶可想望太平[3]258。
在瞿式耜看來,南明太平中興的關鍵之一就是為永歷帝尋覓良師。此前他對方以智的稱呼便是“詞林方以智”,可能正是將輔佐永歷帝的希望寄托在了方以智的身上,畢竟方以智在崇禎朝就曾擔任過定王講官。而且,瞿式耜對當時的內閣構成頗為不滿,其《戊子九月又書寄》中稱:“朝中宰相則江西王化澄、浙江嚴起恒、吾鄉朱天麟。朱天麟吾所薦者,而不合時,合時者惟嚴一人,以善媚人逢時也。”[3]266嚴起恒與當時的錦衣衛文安侯馬吉翔勾結,相為表里,幾乎壟斷了軍國大事的決定權。方以智對此事也是了然于心,因此才會自稱已“局外久矣”,似是有意地與南明朝廷脫離,并試圖從黨爭的政治漩渦中脫身。
不僅如此,入閣后的方以智還會成為清廷的重點關注對象,甚至牽連其家人、朋友,給他們帶去巨大的災難。明遺民若被清廷追捕,往往牽連甚廣。方以智的好友陳子龍便身遭此禍,清廷對涉嫌窩藏陳子龍者大肆追捕,受牽連者多達五十余人。方以智的《靈前告哀文》亦證明了這一點,文中稱:“家鄉傳聞,遂令大人有子相南海之嫌,迫令索歸,受盡委迮,洗橐幸免。”[4]35這也就意味著,僅是征召之旨已經給方家造成了不小的麻煩。方氏家族歷來以孝著稱,方以智本就因不能侍奉老父膝下而心懷愧疚,自稱“為子者竟未能盡一日菽水之職”[4]34,必然不愿再因入閣而牽連老父②“十辭疏”以外,方以智也曾透露出辭官的原因,即為白發老父故。他在《辛卯梧州自祭文》(《方以智全書:第十冊》,第4頁)中稱:“流離嶺表,十召堅隱,不肯一日班行,為白發也。”《象環寤記》(《方以智全書:第一冊》,第393頁)亦稱:“然中丞公白發在堂,眥為之枯,十年轉側苗峒,不敢一日班行,正以此故。”他的好友錢澄之也在《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田間文集》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379頁)中寫道:“屢詔不起,無他,為有老親在故鄉也。”忠臣與孝子的沖突古已有之,方以智的父親方孔炤也確實因擔心他的安危,多次勸其歸隱山林。另據《祭直之弟文》(《方以智全書:第十冊》,第9頁)記載,流亡期間,家人在與方以智的通信中“獨嘉”其之不仕,以為“將謂擇禍,猶可免累”。可見,家人對方以智的辭官是知情且十分支持的。這應當與方孔炤晚明時期的遭遇有一定的關系。。
總結而論,方以智自認性情狂直,故與朝局格格不入。此種情況下,不僅無法為國效力,甚至難以保全自身。他在辭疏中就曾提到,“今且出而死”[1]512“今出則速死”[1]513。意即借性情狂直之由,行全身遠害之實。方以智雖不懼為國獻身,卻并不期望以此種方式遭禍。因此,更準確地說,他是看清了南明朝廷的腐敗和政治的昏暗,不愿與之同流合污,更不愿為黨錮之爭作出無謂的犧牲①蔣國保《方以智哲學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頁)以為,方以智“雖然祟尚東林精神、積極主盟復社,但他思想上卻認為黨爭是為了各自的私利”。宋豪飛《明末桐城方以智與阮大鋮兩大家族交往考述》(《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8期,第78頁)也認為,方以智與阮大鋮的矛盾“早已不再是單純的個人恩怨,而是閹黨勢力與復社清流之間的不可調和的黨爭延續和矛盾的逐步激化的反映”。。因而將過失攬到自己身上,以性情狂直之慮為辭。
(三)才能不堪之憂
“十辭疏”中,方以智還反復提到自己的才能不堪。他在《夫夷山再辭疏》中稱“馬齒未及四十,歷官不滿兩年”[1]588“不敢以后進淺俸,逾越老成”[1]588,故無法承擔“中興恢復之相”[1]588的重任。《四辭請罪疏》中寫道:“至于臣才之不堪,則臣前三疏,哀辭懇切,已瀆圣聽矣。”[1]590《七辭疏》以為“無分毫之功、尺寸之才”[1]595。《八辭疏》則自稱“不足以濟國匡時”[1]597。《九辭疏》指出:“臣之不可為宰相,非獨臣自知之審也,人皆知之。”[1]598《十辭疏》亦稱:“本為才卑庸劣,叨留史官,已為過分,何敢冒忝揆地,誤國茍榮?”[1]600
可以看出,才能不堪之憂也是方以智辭官的重要原因。在方以智看來,為相之人必須聲望極高,能使天下信服。“朝廷用一人,必先養其資望,足以服天下;練其才具,足以理庶務”(《夫夷山再辭疏》)[1]588;“朝廷用一相,必其心有以自信,又必養其望,使天下皆信,然后參贊佐理,內外咸服”(《九辭疏》)[1]598。粗略來看,方以智所慮確是事實。相較而言,他年紀尚輕,為官時間尚短,并不是宰相的最佳人選。而據《小靦紀年》記載:“明征前禮部尚書文安之、前大學士王錫袞入閣,道阻不至,乃以前朝翰林學士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5]似有退而求其次之嫌。況且,在前輩重臣面前,不論是主觀還是客觀上,方以智都不可能坦然受命。
不過,永歷帝的數次下詔必然是有其考慮的,正如詔書中所稱:“卿天人實學,忠孝世傳;鼎鉉弘謨,人倫師表。……實望卿居端揆之任,理機務之繁,樹表于朝廷,則四方豪俊,知所歸依;發策于疆場,則遠邇群英,共奪撻伐。”[1]595顯然,永歷帝十分看重方以智,尤其是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據《明季南略》記載,當時南明群臣粉飾太平,如醉如夢,“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三人”[6]421,方以智便是其中之一。且直到《青原志略》中,尚有人認為其“當見宰相身,可使邦國活”[7]。因此,方以智的才能顯然是得到時人認可的。若非如此,吳炳也不會致書方以智,力勸其出山輔政。此外,瞿式耜也有《庚寅八月,方密之相國四十初度,敬賦二律申頌,促其入朝以慰圣眷》詩,稱“為君置酒兼成頌,須及鑾輿早出關”“為語謝公高臥久,承恩四載急從王”[3]232。錢澄之亦以“興朝大政需公出,早辦收京并馬歸”(《昭江壽曼公四十》)[8]相勸。余如劉湘客、丁時魁、金堡等,均曾力勸方以智入朝。他們的敦促,應當都是出于對方以智的認可。
同時,方以智對自己的能力也是有信心的。他的詩中就曾有“生小逢亂離,長大學軍務”[1]46之說,《方以智先生年譜》也稱其“專心于致用之學,并學習兵事”[9]63-64。身處“天下多事時”[1]52,方以智密切關注時局,常針對重大事件擬策。因建議始終未被采納,他不禁發出“我獨困蓬蔚,被褐行且遲”(《吳門遇臥子作兼寄舒章》)[1]52、“被褐困草莽,所望無一遂”(《舟次三山,阻風不進,欲投梁父,遂徒步至蕪陰,夜雨雪。翌日,冒寒至其設,見其兒女想與,感慨賦此三章》)[1]54的感慨。甚至在寫就《夫夷山再辭疏》后,他還呈上過《芻蕘妄言》,條分縷析,積極獻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由此可見,方以智并無才能不堪的擔憂,反而是多次獻策不被采納,讓他在焦慮之余,漸生隱退之心。
因此,當南明王朝出現中興轉機之時,在“彈冠者遍地……一時人情咸以出仕為榮,不仕為辱”[6]250的情況下,方以智堅隱不出,并再上《四辭請罪疏》。所慮之事仍是:奸臣當道,卻無力抗爭;國難深重,卻不能為國獻身。盡管如此,他還是以“才之不堪”為由,婉拒了永歷帝的再次征召。不可否認,在動蕩的時局面前,方以智或許確實有過才能不堪、難以勝任的擔憂,但他的濟世之心可昭日月,面對殘破的南明王朝不可能無動于衷。據此推測,方以智反復強調自身的才能不堪,應當都只是謙辭而已。并且,在自謙之外很難不感受到他的無奈和失望。即使是在危急的局勢下,才能不堪也尚可補救,而南明王朝日益顯現的頹勢已然無法挽回。
(四)不入班行之誓
方以智的“自矢不加官”之說也多次出現在“十辭疏”中。《答吳年伯書》中稱“未嘗一日列班行”,因“向在端州會議,原自矢不加官”[1]512。《夫夷山寄諸朝貴書》也提到,“當端州會議,自矢不加官”,因此“自圣人登極以來,未嘗一日立朝,一事與聞”[1]513。《夫夷山再辭疏》亦稱:“一則自矢不加官。”[1]587同一時期所作《贈詔使》詩中,也有“辭官因血誓,憂國仗天心”[4]222之句。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他更是反復強調“始終未嘗一日立班行”(《與程金一》)[1]526、“智未嘗一日立班行”(《寄張爾公書》)[1]530、“自登極三年中,一日未立班行”(《與金道隱給諫》)[1]551。
據此可知,方以智似乎曾有過“不入班行”的誓言,只是未見相關資料。但結合上下文不難發現,除了反復說明“自矢不加官”,方以智還一直在強調一個時間節點,即“端州會議”時。《九辭疏》中亦論及了這一問題:“即自皇上監國時,臣議開創之政,一切與人不合,得罪首輔,從此暌違。”[1]598也就是說,方以智的不入班行是以端州為始的。那么端州所議究竟是何政策,才會導致方以智“自矢不加官”呢?這從他的《芻蕘妄言》中可以見出端倪。《芻蕘妄言》第一條就是關于制度的更改:“端州之始議曰:‘以行在為大營盤,天子如總督,群臣如偏裨,不設百官,不用部覆,君臣同心,文武戮力,魚水之深,義猶朋友。’”[1]601這里所說的始議,應當是指永歷帝登基時與群臣議定的行政制度。其主旨是不設置官職,減少繁雜的程序,君臣同心,以最直截了當的方式復興明朝基業。
“本龍來自糖人國!”休息足夠,糖龍的身體也恢復到原來的硬度,它坐起來昂著腦袋,龍須也顯得格外飄逸。糖龍因為由糖制成,遇水遇熱身體便會融化,一疲勞身體就會變軟。不過,這糖龍的性格倒是像龍一樣高傲呢。
如此,前文所議“二不便”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它們針對的其實是永歷帝登基之初所設立的制度。因為種種原因,這種制度并未得以實行。方以智的不入班行,也不是真的拒不為官,而是對“不設百官”這一政策的堅守,因此,他不僅在“十辭疏”中,也在寫給朋友的信件中,頻頻強調不入班行。端州所議還提到要“文武戮力”,方以智就曾致信時任督師的何騰蛟說:“為今之勢,各督各鎮,戮力同心,天子為神祖之胤,中原有不歸命者乎?”(《寄閣部云從何公》)[1]524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在武力為先的時代背景下,南明朝廷多由武將擁立、操縱。“自弘光朝廷以來雖然任命了閣部、總督、巡撫之類的高級官員,大抵僅擁虛名,實權分別掌握在盤踞各地的軍閥手里。”[10]623-624軍閥們則“因襲了過去朝廷上黨爭故套,一切以個人和小集團的利害為轉移,國家大局被置于腦后”[10]401,永歷朝更是如此①詳情參見顧誠《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頁)“永歷朝廷的內部黨爭”一章。。永歷帝不僅放任武將的跋扈,還試圖通過任命官職來籠絡人心。
由此,我們得以追溯到方以智辭官的源頭。面對復雜多變的時局,方以智始終堅守初心。但是,他的進言并未被永歷帝采納,且又因此得罪了當時的權臣。進言未被采納意味著他的理念沒有得到認可,得罪權臣則意味著他的理念在未來也不太可能付諸實踐。方叔文就曾針對這一點發表看法:“公非偷安忘事也明矣。徒因開創建議時,即與首輔相忤,且僉任盈廷,魁柄陵替,一二正人君子,幾無立足之地,不惟恢復無望,即欲少申正氣,暫守偏隅,亦不可得,故公十疏哀辭,豈得以哉?”[9]141方以智的無奈被充分地解讀出來。因此,不入班行之誓歸根到底也是方以智的托辭,他是想借此來提醒永歷帝,同時表明與當事的不合,以及遠離朝堂的愿望。
至此,方以智的辭官疑云得以揭曉,十辭閣職無疑是其人生的重大抉擇,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更可謂影響深遠。綜合來看,身患痼疾確實限制了方以智的部分行動,性情狂直也著實容易招致禍端,才能不堪或許確是他的擔憂之處,但其辭官的最主要原因應是礙于不入班行之誓。而在不入班行的背后,則隱含著方以智對永歷朝廷的心灰意冷。甚至可以說,方以智的這種失望是從崇禎朝就開始累積的。初入朝堂,方以智便感受到了理想與現實巨大的沖突;亡國后,他更是不得不直面信念的崩塌。“十辭疏”中亦存在著由矛盾到無奈,再由無奈到失望的態度轉變。方以智一度積極救國,忍死以苦守志節,只是在認清現實后,他才最終對南明朝廷徹底失望。
此后,方以智清楚地意識到,即使是出任內閣之職,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朝局。南明閣臣已然權力不足,無法真正地參與國家政治,發揮應有的上傳下達作用②顧誠《南明史》(同上,第602頁)中對瞿式耜的慷慨就義進行了分析,認為他“在可以轉移的時候不肯轉移,寧可束手待斃”,原因之一就是“對南明前途已經失去了信心”。瞿式耜本人亦在家書中寫道:“只是目前局面,凡勛鎮之強梁跋扈者,則奉之惟恐不及,而留守、閣臣與地方撫、按,直視為可有可無。”(《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頁)瞿式耜當時已身處內閣,可以說是永歷朝的政治中心,但他仍然無力改變南明的局勢,足以看出閣臣之職已今非昔比。。由此亦可見出,方以智作“十辭疏”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辭官,更意在表達對南明政局的不滿和怒其不爭的無奈。從半壁江山到殘疆剩土,南明王朝敗給了清軍,更加敗給了內耗。正是因為看清了這一點,方以智才失望地走上了另一條反清復明的道路。其后的逃禪雖是無奈之舉,卻也從側面說明,方以智已不再寄希望于南明朝廷,而是試圖以民間的抗爭力量實踐復國大業。憑借著自己的號召力,方以智嘗試喚醒遺民們對故國的情感,戮力同心,共圖恢復大計。反觀南明朝廷,則依舊沉浸在內部斗爭中,漸失民心。終于,在1650 年底,桂林被攻破,永歷帝再次踏上逃亡之路,永歷朝廷已然形同瓦解。
三、“十辭疏”在遺民研究中的價值
“十辭疏”作于南明永歷元年(1647)至永歷四年(1650),此時南明王朝經歷了三個統治政權,仍在苦苦支撐。放眼而觀,遺民群體無疑是這一時代舞臺上最閃亮的主角。作為遺民代表人物,方以智的經歷和創作鮮明地反應出這一時期遺民的生存狀況和心理狀態,為遺民群體及其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就“十辭疏”而言,它不僅展現出遺民生存狀況的惡劣,而且凸顯出遺民心理狀態的復雜,最重要的是,還呈現出遺民文學的真性情。
(一)展現遺民生存困境
從“十辭疏”中不難看出,不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方以智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遭受著沉重的折磨。
此外,方以智還面臨著心理上的折磨。身處惡劣的環境,在輾轉流離、為國憂思的同時,他還遭遇著道德倫理層面的苛責。因為拒絕入仕南明,他已然引起不少非議,此后的逃禪則更有甚之。全祖望在為《周囊云文集》所作的序中就曾寫道:“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為君子所譏。”[11]1211雖沒有直接點明是哪些人,但在他的作品中尚有跡可循。其《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有云:“公(黃宗羲)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為之反復言其不可。蓋公于異端之學,雖其有托而逃者,尤不肯少寬焉。”[11]219黃宗羲對“有托而逃”者嚴苛的道德審視,可見一斑。其《亭林先生神道表》記載:“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為助,答曰:‘愿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11]231顧炎武亦將逃之世外視為最下之選擇。
可見,即使是在遺民間,也橫亙著巨大的道德鴻溝,亦足以見出遺民們所處境地的艱難。“在這種責以死節方是完人的極端化倫理氛圍中,易代士人——尤其是聲高譽隆者——難免會陷入生隱與死殉二難抉擇的政治倫理困境,遺民群體選擇了生隱或斗爭,這并不能消彌殉節者所帶給他們的政治倫理焦慮。”[12]這就意味著聲名越大的遺民,所受的世俗之累也越重。方以智即深為聲名所累,這一點也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了他的多病上。
雖是以病為辭,但方以智的病是真實存在的,且這些疾病均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①前文已論及方以智所患疾病,主要包括消渴、虛勞和心悸。消渴可能的病因應是情志失調和先天不足。這在方以智的六叔方文的《疽嘆》(《方嵞山詩集》黃山書社2009年版,第88頁)一詩中可以得到部分的驗證。詩中細致地描寫了兩年內兩次病疽的經過,并分析得出了病因病機:“二疽但屬厥陰經,肝火郁抑氣血停。內淫發于懷抱間,坐臥行立各不寧”。明確了“肝火郁抑”是導致兩次病疽的原因,肝火郁抑即屬于情志失調的表現。考慮到方文和方以智的叔侄關系,尚不排除遺傳,即先天不足的可能性。虛勞則常由先天不足、情緒失調及久病失養、病后失治等引起,故消渴很有可能進展為虛勞,且情緒失調會導致病情加重。心悸病情較輕者為驚悸,病情較重者為怔忡。大凡驚悸發病,多與情志有關;怔忡則多由久病體虛所致,亦與情志有密切的聯系。。也就是說,他所患疾病的發生、發展大多與情志失調有關。在描述病情時,他也將病因歸結為“年來憂憤”[1]511“冤憤入骨”[1]511,雖然只是簡單地提及,其背后的含義卻頗值得深究。此外,方以智的病疽①潘務正《“疽發背而死”與中國史學傳統》(《文史哲》,2016年第6期,第141頁)中指出,“明清之際‘疽發背而死’是載集中遺民的一種比較普遍的死亡方式,與屈原自沉汨羅江、文天祥英勇就義有異曲同工之妙”。疽發背傳達了遺民的心曲,體現了他們的民族氣節和憂患意識。以及癥狀上的嘔血和頭暈等,均極具沖擊性,亦蘊含著強烈的情緒情感色彩,幾乎可以看作是一種對黑暗現實活生生的、最慘烈的反抗。遺民們的生存困境亦由此展現得淋漓盡致。
(二)揭示遺民心理沖突
“十辭疏”同樣揭示出遺民們最激烈的心理沖突。他們既對南明王朝保持絕對的忠誠,又因朝政的腐敗而對其失望至極。
方以智對南明王朝即懷著復雜的情感。一方面,他自幼受到忠孝思想的影響,對皇室正統忠心耿耿。馬其昶《方密之先生傳》有云:“自先生曾祖明善為純儒。其后廷尉、中丞,篤守前矩。”[13]方氏家族世受國恩,與大明王朝有著盤根錯節的聯系。且方以智“因午會之說而對時代充滿樂觀”[14],亦對抱負的實現充滿希望。崇禎甲申年(1644),方以智就曾上《請纓疏》,謂“誓暴此骨,愿就河北行伍,父子枕戈,以報國恩事”[1]376。可以看出,方以智起初是熱心用世的,其從政的意愿強烈,十分渴望能有一番作為。
另一方面,方以智對南明朝廷是失望的。出于士的責任感,他一直關心時局、針砭時弊,積極為朝政、軍事出謀劃策。然而,令其大失所望的是,南明朝廷的狀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至永歷朝,“閹人用事,內批、廷杖等舊習,寖寖復行之”[15],已然看不到恢復政治清明的希望。統治階級最在意的始終是權力的爭斗,權臣秉政,忠良下野,內憂外患也阻擋不住他們的自相殘殺。“大廈忽如此,一木何以支!”[4]235趙園即認為:“明清之際的遺民如方以智、熊開元,各有其復雜的世俗經歷,其逃禪固然因抵抗的失敗,也應緣于對政治的深刻失望。”[16]正是對方以智心態確當的總結。
值得注意的是,方以智的辭官長達四年之久,也就意味著永歷帝求賢四年。其中或有戰時通訊不便的因素影響,但永歷帝的誠意和決心仍可見一斑。受此殊榮,本應感激涕零,并以實際行動回報②錢澄之在《昭江壽曼公四十》(《藏山閣集》黃山書社2014年版,第309頁)中即寫道:“主恩十召君應起,莫戀滄江負白麻”。,方以智卻還是堅定地拒絕了永歷帝的征召。其實,方以智也不是沒有矛盾和糾結過。他曾問語錢澄之說:“吾歸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親,其緇乎?”(《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17]流離嶺表之時,他亦“長期徘徊在事君與事親、出仕與隱遁之間”[18]。雖然南明朝廷混亂的現狀,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方以智入世從政的積極性,他卻并未完全置身事外,“十辭疏”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他為此而做出的一種努力和嘗試。
永歷帝的內閣之召,本沒有什么問題。只是方以智清楚地知道,這并不是解決南明王朝所面臨困境的辦法③彼時,方以智的好友陳子龍、孫臨皆曾以文人之身領軍,意圖舉兵恢復。對于他們的從戎,方以智應當是十分羨慕的。他在《哭陳臥子》(《方以智全書:第十冊》,第200頁)詩序中即寫道:“聞臥子死難,得死所矣。”且方以智一直都有從軍的志向,或許在他看來,相較于入朝為官,這種在戰場上與敵人正面交鋒的暴力手段成效更加明顯。。如果不對朝中的諸多問題加以重視和解決,僅憑一己之力是無法扭轉頹勢和敗局的,南明朝廷也就永遠不可能實現真正的中興。方以智之所以在“十辭疏”中將心力交瘁的狀態展現出來,不僅是為了表達不滿和怨憤,還期望能以此達到勸諫的效果。換言之,他是通過“書寫不幸與痛苦來發揮干預政治、批判社會現實的作用”[19]。借此,歷史的細節在文學作品中清晰地顯現出來,這種看似私人化的情緒情感,其實已經超越了個人的得失,像這樣因為黨爭、私怨而被誣陷、排擠的,又豈止方以智一人!《又寄爾公書》中,他就曾感慨道:“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欲盡殺天下善人名士,何獨于智?”[1]529在政治分歧所造就的亂局中,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永歷帝原本期望方以智能夠成為入世為政的典范,他的推辭卻把自己推到了對立面,反而成為辭官的典范。因此,即使言辭再委婉,方以智本人也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壓力。出于挽救南明的目的,卻做出了辭官的舉動,兩相違背之下,方以智的心路歷程必然是不平靜,甚至波瀾起伏的。明亡以后,這種矛盾性導致遺民心理一直處于拉鋸狀態。因此,每個遺民的選擇都難免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有鑒于此,遺民作為群體的復雜性尚能加以探討,但從個體角度出發則很難加以詮釋。方以智的“十辭疏”恰好為此提供了個案,他將自己在面對出處問題時的矛盾和糾結展現出來,使后人得以窺見遺民心理的細微之處,對遺民心理的理解更加深刻,這十封辭疏也因此呈現出重大的現實價值。
(三)抒發遺民真性情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十辭疏”中呈現出了遺民文學中的真性情。方以智雖數次以身患痼疾、性情狂直、才能不堪、不入班行等理由推辭,且流露出難掩的怨憤之情,可這十封辭疏讀來卻讓人感受到難得的真誠。由此,亦可以見出其以真為美的審美追求。
性情之說由來已久,在文學史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李瑄以為,“明遺民真正將‘性情’作為論詩的根本立足點,它決定了作詩的宗旨、詩歌的命題立意和評價標準”[20]482。潘承玉亦認為,“南明遺民詩人普遍強調詩歌抒寫真性情”[21]。他們的觀點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南明詩歌發展中的突出現象。明遺民群體中,有些人持溫柔敦厚的詩教觀,有些則強調發憤以抒情,但他們都十分看重性情背后的真,強調抒寫真性情,即以“真”為美。“真正的性情,負載著詩人的理性深度與感性熱情,顯示出生命的力度”[20]485,于明遺民來說尤其如是。
這一點在文章中亦有所體現,“十辭疏”便是其中的典型。這十封辭疏不僅凝聚著方以智明亡以來真實的生命體驗,亦蘊含著其真實的情感抒發。魏藻德曾謂方以智“傷父功之不成”[1]365所作的《激楚》,仍是“發情止義,而體歸于不怨矣”[1]366。到了“十辭疏”中,他的怨也算是有所顯露。疏中所述看似是為避免被卷入政治漩渦而論,卻也難免蘊含著一絲怨憤的意味。永歷二年中元節,方以智曾作《屈子論》憑吊屈原,通篇所論固然皆是先賢之事、生死之論,可“孤臣孽子,何代無之”[1]534的感慨,還是瞬間將人拉回同為亂世的當下,也就很難不將二人聯系起來,忠臣的無奈和失望因此實現了互通。司馬遷以為:“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22]方以智亦當如是。
但是,流亡的困頓、疾病的困擾和被污蔑的困境都沒有能夠阻止方以智,他將憂國的情懷和憂憤的情感訴諸文字之間,試圖通過文學書寫達到干預現實政治的目的。其中的擔憂是真,怨憤亦是真,“十辭疏”也因此顯得愈發真誠。易代之際,時局混亂,人心動蕩。方以智于此時堅辭永歷帝征召,此種決定不可謂不艱難,他本人卻指出:“士不幸生亂世,既已幸全于當時,而猶不得全于后世之說。”[1]429對于輿論,方以智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的抉擇都是出于本心,而不是為了一時的褒譽或身后之名。因此,以“易代”為契機,他對明王朝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省。他的《滿江紅》寫道:“爛破乾坤,知消受、新詩不起。正熱鬧,黃金世界,紅妝傀儡。”[4]305《滿庭芳》亦有“錦繡園林,芙蓉筵席,從來狼藉東風”[4]305之句。詞中不僅揭露了南明王朝的腐朽破敗,還對朝廷一直以來的粉飾太平予以抨擊。即便是在中興有望之際,表面上的太平也根本無法掩蓋南明深層的危機。
這一時期,方以智的創作多是感于時事而作。他將對社會和政治的悲憤情緒爆發于文學創作之中,并為諸多遺民作傳。正如他本人所說,“性情之發,發于不及知”(《周遠害詩引》)[4]72。“十辭疏”因是呈給永歷帝的疏奏,其中忌諱頗多,言辭也應當盡量委婉,但方以智并未磨滅真實的性情。“聞足以戒,激怒亦中和也;孤孽哀鳴,怨興亦溫厚也”(《正葉序》)[4]51。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方以智以為怨怒亦中和、亦溫厚,縱然發不及知,卻也著意為之。因此,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治信念的坍塌與維護傳統文化的悲劇性沖突”[23],方以智卻也達成了創作實踐與“以和為美”審美追求的高度一致。
早年,陳子龍曾因方以智的詩歌過于悲涼,勸誡以“悲歌已甚,不祥”[1]410。方以智回應稱:“余亦素慷慨欲言天下事而不敢,但能悲歌……然非無病而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1]312然而,在國變之后,連陳子龍也“不再斤斤于風貌是否合乎漢魏盛唐,詩學重心轉為強調詩的情感宣泄與道德規范功能”[20]472。這種轉變既是創作的需要,也是時局的需要。同方以智一樣,遺民們的人生與文學緊密相連,不論是內心的矛盾掙扎,抑或是怨憤不滿,均可訴諸文學創作。
文學是遺民群體抒發的重要手段,他們期望通過文學創作對社會現實加以干預,繼而實現經世的理想。文學也是他們的情感寄托,用以表白忠節,發出對國家和個人命運的反思。因此,解讀“十辭疏”,必將有助于補充和完善南明時期文學的發展脈絡,明確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經歷過禾黍之悲,遺民文人筆下的情感抒發已然變得越發豐富、真實,他們詩文創作中所流露出的情感,一改晚明文學的頹廢、矯情,形成了南明遺民文學“真性情”的品質,也因此呈現出獨特的真實、真切的文學價值。
四、余 論
南明永歷朝,方以智的數次上辭疏并不是個例。瞿式耜亦有《力辭勛爵疏》《辭督師敕命疏》和《堅辭勛封疏》。當時,瞿式耜已身任東閣大學士,永歷帝進之以臨桂世伯,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他亦堅辭不就。永歷四年,瞿式耜再上《引咎乞罷疏》,自列七罪,以病請辭①參見《瞿式耜年譜》(齊魯書社1987年版),以上諸篇皆收入《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理想的高昂和行動的無力,往往使得南明遺民們始終身處矛盾狀態。瞿式耜就曾在家書中表明:“與之同流合污既不能,終日爭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猶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戊子九月又書寄》)[3]265這與方以智“不入班行”的顧慮亦有著相通之處。針對這一現象,或可繼續展開群體性的研究,充分挖掘遺民的一致性和差異性。
此外,“十辭疏”中的疾病書寫也需要予以充分關注。以病為辭在辭官中本是最常見的現象,方以智的書寫卻明顯展現出其本人對醫學的熟識。亂世與疾病有著天然的聯系,不僅因為亂世容易導致疾病的發生,也因為古人習慣于以疾病來比喻國家和社會的弊病。方以智身處亂世,他的創作中會出現大量的醫學元素自然可以理解。只是,這固然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但與方氏家族及其本人醫學儲備的關聯則更加緊密。同時,作為一名思想家,方以智十分重視融會貫通,他的文學與醫學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碰撞。因此,關注到其文學與醫學之間的聯系,或可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讀方以智其人及其文學理論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