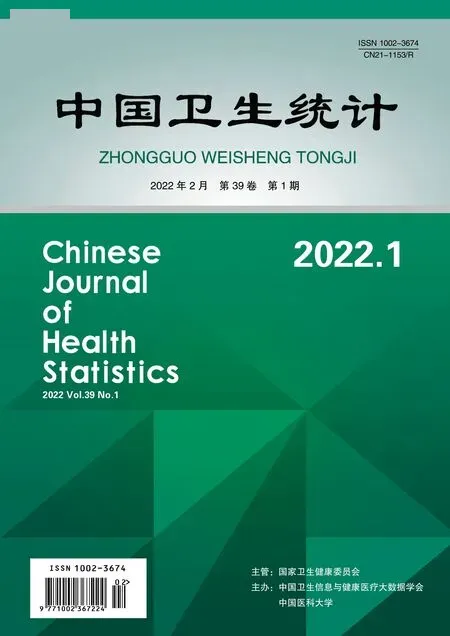基于模糊斷點回歸的退休對老年男性醫療服務利用影響研究*
曾雁冰 羅 貝 方 亞Δ
【提 要】 目的 了解退休對老年人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方法 基于模糊斷點回歸模型,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2013年、2015年數據,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退休對門診服務、住院服務、自我治療以及醫療服務滿意度的影響,并分析退休對老年人的健康、健康行為、收入和時間成本的影響機制。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2044個男性老年人樣本,退休率在60歲出現了明顯跳躍。門診服務利用方面,退休減少了14%的門診放棄率,看醫生的次數每月增加0.3次以上,門診就診率提高14%,門診自付費用占總費用的比重增加42.3%。住院服務利用方面,退休使得放棄住院率增加13.4%。自我治療方面,退休后男性老年人自我治療總費用和自付費用顯著增加。醫療服務滿意度方面,退休后的老年人降低了對本地醫療服務的質量、成本和方便程度的滿意度。從影響機制上看,退休后個體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自評健康均呈下降趨勢,其中退休后其認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生活滿意度明顯下降,患慢性病病種數量增加9.8%、患抑郁的風險增加9.1%、自評健康下降49.8%。退休后社交參與率和吸煙概率顯著上升。退休后隨著時間成本變化私營部門員工門診放棄率、住院放棄率相較于公共部門顯著下降。結論 退休后男性老年人醫療服務利用呈上升趨勢。退休通過對健康和健康行為產生負面影響,降低就醫時間成本來促使個體提升醫療服務利用。相關部門應采取措施提高就醫服務的便捷性、可及性以及滿意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并關注勞動者和退休人員身心健康,保障不同部門職工休息休假的權利,加強健康教育以促進健康行為,為推動健康老齡化、保障老年人醫療服務利用提供重要基礎。
現今,中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劇,60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從2008年的12%增加到2019年的18.1%[1],進入快速老齡化階段。而中國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女性則為50歲或55歲,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低的國家之一。退休人數的增加給公共財政支出造成極大負擔。針對這一現狀,我國目前實行漸進式的延遲退休政策以調整制度撫養比,預計2045年退休年齡將延遲至65歲。然而目前關于延遲退休這一政策仍存在諸多爭議,本研究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分析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并從退休后老年人的健康、健康行為、收入和時間成本變化探索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機制,為決策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1.數據來源
本研究資料來自“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3年和2015年的調查數據,納入擁有城鎮戶口的50~70歲男性非自雇者,并排除一生從未工作過和目前既沒有工作也沒有辦理退休手續的個體。最終納入2044個樣本。
2.變量及其描述
本文的分組變量為退休,定義為個體辦理了正常退休手續(排除內退和退職),并且不再從事任何有薪工作[2]。結果變量為醫療服務利用狀況,主要從門診、住院、體檢、自我治療、醫療服務利用滿意度進行測量。年齡設為驅動變量。控制變量選取受教育程度、性別、同伴侶居住情況。
此次研究探討退休對男性老年人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機制,選取健康、健康行為、收入、時間成本作為影響機制變量。考慮到不同部門員工請假以及退休前后就醫時間成本不同,本文從職業部門性質和延遲就醫兩個方面測評退休是否通過影響就醫時間成本進而影響醫療服務利用。具體變量及描述見表1。

續表1
3.實證模型
我國的退休年齡存在戶口、性別和職業上的差異。男性勞動者法定退休年齡是 60 歲,女性干部為55歲,其他女性勞動者為 50 歲。此外,個體退休與否也與其社會經濟狀況、個人偏好等有關,故采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估計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極易導致內生性問題。斷點回歸設計是內部有效性較強的準自然實驗,可有效避免內生性問題,近年來在經濟學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3]。其基本思路為斷點附近樣本近似,退休作為分組變量具有隨機性,個體醫療服務利用的差異主要歸因于是否退休,通過估計局部平均處理效應可分析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
斷點回歸分為精確斷點回歸和模糊斷點回歸。前者特征為斷點處個體得到處理的概率從0跳躍為1,后者概率則從(a)跳躍為(b),其中0<(a 圖1 法定退休年齡對退休的影響 在較小退休年齡區間能更好控制年齡效應[4],本研究進一步將樣本年齡限制在50~70歲。模型如下: H1=β0+β1Ri+β2(xi-zi)+β3(xi-zi)+Zi+εi (1) Ri=α0+α1Di+α2Di(xi-zi)+α3Di(xi-zi)2+δi (2) Hi為醫療衛生服務利用,Ri為是否退休,Zi為控制變量,xi為年齡,zi是斷點年齡60歲,Di為年齡斷點虛擬變量。β1解釋了年齡斷點附近醫療服務利用的局部平均處理效應(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LATE),利用2SLS可得。 為保證斷點結果穩健性,本文進行了年齡連續性檢驗[4-5]制變量連續性檢驗和安慰劑檢驗。 1.醫療服務利用現狀 樣本平均年齡為65.7歲,其中75.05%處于退休狀態,約45.94%任職于公共部門。門診服務利用方面,79.87%的個體在調查前一個月未使用過門診服務。其中,8.43%存在生病但未就診情況。門診自付比為71%。住院服務利用方面,5.82%的個體放棄接受住院治療。自我治療方面,自付比例高達90%。體檢服務利用方面,約63.94%的個體過去兩年有參加常規體檢,其中74.13%體檢項目超過7項。醫療服務利用滿意度方面,僅有約33.06%的患者表示滿意當地醫療服務的質量、成本和方便程度。 2.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 應用模型(2)進行第一階段回歸,分析法定退休年齡對退休的影響。結果顯示,年齡斷點虛擬變量(Di)對退休的影響在 1% 的水平上顯著,意味著政策規定的退休年齡是影響退休的重要條件,達到國家法定退休年齡后退休概率高出33%。 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情況如表2所示,根據K-P rk LM統計量、K-P wald F統計量以及相關研究[6-8],年齡斷點虛擬變量通過工具變量檢驗,可用作退休的工具變量。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門診服務利用方面,退休能使門診放棄率減少14%,看醫生次數每月增加0.3次以上,門診就診率提高14%,門診自付費用占總費用的比重增加42.3%。住院方面,退休增加了放棄住院的概率(+13.4%)。自我治療方面,退休后男性老年人的自我治療總費用和自付費用顯著增加(+83.5%、+42.1%),自付費用比例有小幅減少(-2.9%)。體檢方面,退休對男性老年人是否體檢以及體檢項目未產生顯著影響。醫療服務滿意度方面,退休后男性老年人降低對本地醫療服務的質量、成本和方便程度的滿意度(-27.1%)。 表2 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 3.影響機制分析 進一步從退休對老年人的健康、健康行為、收入和時間成本的影響,分析退休對老年人醫療服務利用影響機制。 (1)健康 本文利用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基于模糊斷點回歸模型(2)從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與個體自評健康三個方面分析退休對健康的影響。 由表3可見,生理健康層面,退休后老年人的認知功能顯著下降,個體患慢性病病種數量增加了9.8%,對日常生活能力的影響不顯著。心理健康層面,退休增加了男性老年人患抑郁的風險,生活滿意度下降45.9%。自評健康層面,男性老年人在退休后自評健康下降49.8%。 表3 退休對健康的影響 (2)健康行為 健康行為層面,退休后老年人社交參與率提升了14.6%,吸煙概率增加了9.8%(表4)。 表4 退休對健康行為的影響 (3)收入 本文研究發現,退休后男性老年人收入顯著增加30.1%。 (4)時間成本 在不同性質部門中,私營部門男性員工退休后看醫生次數每月增加約0.4次,增加幅度高于公共部門男性員工。且其門診就診率相較公共部門男性員工,增加了20.9%。自我治療方面,私營部門男性員工退休后自我治療總費用和自付費用大幅增加(231%,176%),而公共部門男性員工則相反,自我治療總費用和自付費用均有減少(-43.9%,-95.8%)。退休后私營部門男性員工住院放棄率增加幅度(6.7%)小于公共部門(10.9%)。 考慮到退休后老年人閑暇時間較多,可能存在延遲就診情況,本文剔除斷點年齡前后一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醫療服務各項指標并未發生顯著變化。 4.穩健性檢驗 年齡連續性檢驗中,根據年齡變量的直方圖(圖2)和McCrary檢驗結果(圖3),驅動變量在60歲斷點附近沒有跳躍,故個體未操控年齡,滿足年齡連續性假設。控制變量連續性檢驗和安慰劑檢驗回歸結果顯示,退休前后,性別、受教育程度和同伴侶居住情況均未產生顯著變化,未受到退休的影響,研究滿足控制變量連續性假設。安慰劑檢驗中,在新的年齡斷點(56歲和64歲)退休不對醫療服務利用產生顯著影響,在新的年齡區間,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影響方向沒有發生變化,回歸結果在不同年齡區間具有穩健性。限于篇幅限制,檢驗結果未匯報。 圖2 年齡直方圖 圖3 年齡連續性McCrary檢驗 1.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 門診方面,退休對門診就診率有著有利影響,可以減少男性老年人退休后的門診放棄率,增加看醫生的次數。與此同時,門診自付費用占總費用的比重亦有所增加,這與以往研究結論相似,可能與健康狀況的下降有關[2]。 住院服務利用方面,退休增加了男性老年人放棄住院的概率,約68%因為病情不嚴重而選擇放棄。僅有3.88%的男性因為費用問題放棄住院治療。這表明費用問題并不是男性老年人是否住院的關鍵影響因素。有學者從中觀系統(家庭環境)角度出發,亦發現住院情況不受家庭收入的影響[9]。 自我治療方面,退休后男性老年人的自我治療總費用和自付費用顯著增加。樣本中74%的個體患有慢性病,且退休后患慢性病病種的數量有所上升。有研究發現,醫療消費的支出彈性與戶主年齡呈正比[10],且現階段適度提高老年群體醫保待遇,不會帶來公共財政的過度增長[11]。故減少老年人看病負擔,解決費用問題在當下有著重要的民生意義。 醫療服務滿意度方面,退休后男性老年人對本地醫療服務的質量、成本和方便程度的滿意度降低。退休后老年人對醫療服務利用的需求增加,與此同時,醫療支出的個人自付部分以及自我治療費用亦有所上升,醫療支出的顯著增加是影響醫療服務滿意度的關鍵因素[12]。 2.退休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機制 健康方面,退休后男性老年人的認知功能、生活滿意度、自評健康有所下降,患抑郁的風險和慢性病患病數量明顯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患有慢性病病種數量的增加不能完全歸因于退休。可能在退休前就已患病,只是退休后才得到確診。退休對老年人的健康有著不利影響,尤其是心理健康,由此易導致醫療服務利用整體上升[13],這與以往研究結論相似[2]。 健康行為方面,本研究顯示退休后男性老年人社交參與率上升,也有其他研究顯示退休后,閑暇時間增多有利于增加社交參與率[14]。但仍有72.5%的個體在過去一個月沒有參與社交活動,社交參與率較低。有學者發現中國退休老人社交活躍程度(社交項數和社交頻率結合)普遍較低,且社交活躍度對老年健康的影響程度受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15]。退休后老年人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在較低的社交活躍度下,更容易感到空虛、寂寞[16],進而誘發抑郁。本研究也顯示退休后男性老年人抑郁風險增加,生活滿意度顯著下降,因此在增加社交參與率的同時,更應注重提升社交參與效果,提高老年人的社交活躍度。退休后飲酒情況有下降趨勢,雖然并不顯著,但可推測與退休后應酬減少有關[7]。此外,本文發現退休后吸煙概率有所上升,目前退休對吸煙率的影響沒有一致的結論,有學者指出,相比于靜坐型工作者,體力型工作者健康意識不強,且對吸煙危害認識不夠[17],在退休后可能由于閑暇時間增加、交友更廣泛以及生活壓力增加等原因而增加吸煙的頻率。 收入方面,經濟狀況是影響醫療服務利用的關鍵因素之一[18]。本文發現退休后男性老年人收入有上升趨勢。這與孫鵑娟學者的研究結果類似,城市老年人的年齡與其收入呈正向關系,年齡越大收入越高[19],可能與城市老年人收入來源的多樣化有關。 時間成本方面,患者就醫時間成本也會影響就醫決策[20]。本文從職業部門性質測評退休是否通過影響就醫時間成本進而影響醫療服務利用,結果顯示在不同性質部門中,私營部門的男性職工退休后相較公共部門職工,其就診次數、門診就診率、自我治療總費用和自付費用會增加,加大對醫療服務的利用。這與Caroli等人的發現一致,退休后對醫療服務的利用因工作性質的不同存在顯著差異[21]。目前國內公共部門有著較完善的職業福利制度,與私營部門相比,更能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在公共部門,職工休息休假權利更能得到保障,就醫機會和時間成本低于私營部門,在退休后并不會因為就醫時間成本的下降而大幅增加醫療服務利用。同時,本研究顯示退休后男性老年人不存在延遲就醫的行為,這與何慶紅等學者研究結果一致[20]。 退休會導致醫療服務利用的增加,延遲退休在短期內有利于減少醫療公共支出。但退休后男性老年人醫療服務利用短期內明顯增加,且有學者指出退休對生理健康的改善作用在退休5年后才顯現[22],這給我國醫療衛生系統增添了更多的壓力。故若單純依靠延遲退休以減少醫療公共支出,只是治標不治本。 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建議:第一,退休后男性老年人門診、住院服務利用明顯上升,醫院在保障老年人醫療服務利用、滿足就醫需求的同時,還需著力改善醫療服務的質量、成本和方便程度,以提升其滿意度;第二,退休后男性老年人門診自付比例、自我治療費用顯著增加。建議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制度,推進長期護理保險業務的開展,減少因“看病難”和 “看病貴”而放棄醫療消費的現象;第三,針對退休對男性老年人帶來的負向心理影響,社會和家庭要提供積極的心理干預,加強健康教育,開展年齡導向的公益活動,推動再就業,促進其心理健康,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第四,個體就診行為受時間成本影響較大,不同性質的職業部門就診情況不同,且普遍存在延遲就診現象。因此,保障職工休息休假的權利,強化個體健康意識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定期體檢,加強疾病預防,實現“早干預,早發現,早治療”,可推進健康退休,提升退休后的生活質量。長期而言,利于緩解我國醫療衛生支出壓力。
結 果





討 論
建 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