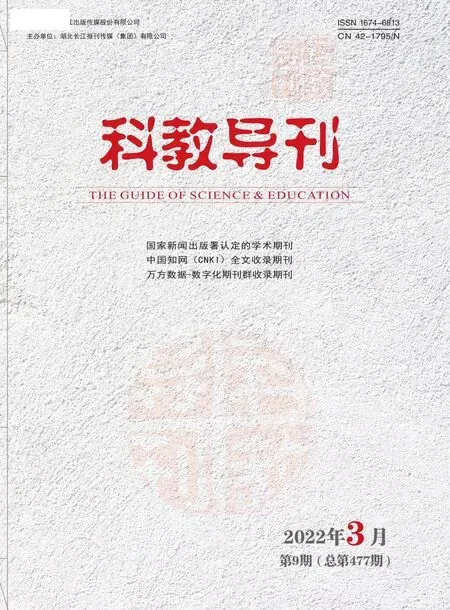高校非生態專業《生態學》教材拓展與教學方法探討
——以增加分子生態學內容為例
安 淵
(上海交通大學農業與生物學院,上海 200240)
近年來,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序推進,國家和社會對自然資源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日益關注和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寫進了黨章和憲法,成為黨和國家意志的體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已成為國家治理和行業管理的基本準則。在此背景下,高校有責任把生態理念和知識傳播給廣大學生,作為基礎課程將“生態學”納入非生態專業的必修課中,學習生態學知識,培養學生的生態思維和素養。
1 加強“生態學”在自然科學和管理科學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與生物科學、環境科學、資源科學、地理科學等自然科學緊密關聯,互有交叉,但又有明顯區別。生態學最明顯的特色在于將上述學科中相互關聯的生物和環境內容提煉出來,研究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關系。因此,生態學與眾多自然科學課程產生了交叉和關聯,如與植物學、動物學、微生物學、生理學、分子生物學、土壤學等;研究對象的層次更加廣泛,包括基因水平、物種個體和群體水平、區域和全球層面的生態系統和景觀水平;涉及植物、動物、微生物、大氣和土壤環境以及經濟、社會和人文等系統[1]。用共同屬性的環境因子將各學科之間的生物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反映出生態學的綜合性、宏觀性、戰略性和實用性的特點。通過“生態學”課程的學習,有助于學生建立不同學科之間的聯系,發揮“生態學”交叉學科的紐帶和橋梁作用。
隨著全球人口增加和工業化進程加速,人類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干擾程度越來越大、范圍越來越廣,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強度影響自然和環境,導致人與自然、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產生許多嚴重的生態和環境問題。生態學作為研究生物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必然成為認識和解決人與自然矛盾的基本理論,是人類與自然和諧共存、可持續發展應遵循的基本理論和指導思想,對我國構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促進社會和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特別是對解決當前全球面臨的六大環境和社會問題,包括能源短缺、資源枯竭、人口膨脹、糧食短缺、環境退化和生態平衡失調,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與此同時,現代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對生態學理論的系統性、先進性、創新性和適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動生態學的發展。
2 非生態專業《生態學》教材存在的問題
生態學關聯的學科多、綜合性強,而高等院校非生態學專業因受學分限制,不能像生態專業一樣設置多層次的生態學相關課程,多角度介紹生物與環境的關系,限制了學生對生態學知識的系統學習和綜合理解能力發展。因此,對非生態專業的《生態學》教材內容提出新要求,要區別于生態專業的《生態學》教材,把生態學領域最新的理論和技術與經典生態學知識結合起來,如把分子生態學、進化生態學等反映時代科學與技術進步的內容融入《生態學》教材,提升教材的先進性,讓非生態專業學生有機會從不同層面認識生物與環境的關系,多層面找準分析自然與環境問題的生態學理論“支點”,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對課程的重視度,更好地發揮《生態學》交叉學科的知識引領和整合作用,這是非生態專業《生態學》教材應具有的特點和內容拓展方向。
目前,國內《生態學》教材多達十幾種,如楊持主編《生態學》,李振基主編《生態學》、尚玉昌主編《普通生態學》等。這些教材共同包涵了經典生態學的內容:生物與環境、種群生態學、群落生態學和生態系統生態學,部分教材中增加了景觀生態學、恢復生態學等內容,但沒有一本《生態學》教材包含了“分子生態學”的內容。在生態專業,分子生態學作為專業課開設,學生可以從中系統學習生物在分子水平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與進化過程,而對非生態專業而言,由于《生態學》教材中不包含這部分內容,因此,學生沒有機會學習分子生態學知識。現代生態學已向微觀生態學和宏觀生態學領域發展,更多地利用DNA測序和微觀粒子等分子生物學技術研究生物的進化與適應,利用遙感和大數據等技術探索全球資源與生態環境變化。分子生物學是現代生物學發展的核心,是揭示生物個體和種群適應環境的最新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創新性成果不斷涌現。分子生物學為更準確、深入研究生物與環境的關系,詮釋傳統生態學理論和現象,豐富生態學內涵,并提供了堅實的分子機制和技術手段,為“分子生態學”的成熟和發展提供支撐。針對生態學涵蓋內容的多元化,以及新時代高等人才對生態學理論知識擴展和提升的需求,將“分子生態學”知識納入高等院校非生態專業的《生態學》教材十分必要,是完善新時代高校課程體系,培養“知識、能力、素質”三位一體高素質人才的需要。
3 非生態專業《生態學》教材增加分子生態學內容的建議
分子生態學是應用分子生物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生物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是宏觀與微觀的結合,關注生態過程和現象的分子作用規律,從分子水平解析環境變化引起的生物形態、遺傳、生理生殖、進化等各個水平上協調適應的分子機理,特別是宏觀生態學研究方法難以實現或宏觀生態學理論難以解析的生態現象,如微生物參與碳固定、甲烷代謝、碳降解等多個碳循環重要過程。傳統微生物碳循環研究多集中于微生物分離培養技術,無法覆蓋絕大部分未培養微生物,無法深入解析碳循環過程中微生物群落的結構、功能和相互作用關系的全貌。宏基因組學技術(如DNA分子指紋圖譜、高通量測序等)的出現克服了這些缺陷,實現了全面分析碳循環過程中微生物物種多樣性和功能多樣性的全貌特征和對碳循環過程的調控作用[2]。
分子生態學是基于基因表達、DNA標記(RFLP、RAPD、AFLP、SSR、SNP、RAD、MSAP、Hiseq等)、蛋白質標記(等位酶標記)和基因組測序等方法研究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內容包括群體保護遺傳學、生物地理與物種形成、親緣關系與種群遺傳分化、形態和生理分化的分子適應、生物共生與協同進化、轉基因生物釋放及其生態效應(即生物安全)以及分子生態學技術等。在瀕危物種保護和致瀕因素分析,環境變化與生物多樣性關系,物種起源與進化,生物與生物地化循環過程關系,親緣關系與種群遺傳分化、馴化與特征形成等研究方面顯示出其獨特的作用,形成了分子生態學固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3-5]。隨著DNA和蛋白檢測技術的不斷創新,生物個體適應、種群遺傳結構和多樣性差異會得到進一步闡明,將為生態學和分子生態學研究和理論創新注入強大動力,推動生態學快速發展。
分子生態學是高校生態學專業的必修課程,非生態專業基本不開設。“生態學”是非生態專業學生學習分子生態學知識的唯一途徑,但目前出版的《生態學》教材均未包含分子生態學內容,因此,在《生態學》教程中增加分子生態學章節十分必要,重點內容包括:分子生態學方法與原理、生物對環境因子的分子適應、種群分子標記生態學、宏基因組與生物進化等,6—8個學時較為適宜。
4 生態學教學的方法與目標
首先,非生態專業“生態學”課程教學面臨三個主要問題:(1)教學時數少,一般為32學時;(2)缺乏實驗教學環節,理論和實踐脫節;(3)教材建設缺乏針對性,生態專業和非生態專業教材共用。前兩個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而教材建設可以先行。根據非生態專業的課程設置特點,合理調整經典生態學內容,增加分子生態學等現代生態學內容,既講經典生態學,同時,啟發性地講授一些現代生態學知識(如分子生態學),開闊學生的視野、思路和知識面。
其次,按照本科專業特點,合理規劃《生態學》教材內容,授課過程的案例與生態學和社會關注的熱點緊密結合,進行啟發性教育。以學生為主體,講授知識的同時,引導和啟發學生關注自然資源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實際問題,理論聯系實際,用生態學理論和方法思考實際問題,例如“中度干擾假說”提出中等程度干擾有利于維持群落較高的物種多樣性。當前,國家對自然資源的保護與管理高度重視,實施了長江十年禁捕和海洋季節性休漁、對北方大面積草原實施生態補償,減輕草原放牧強度等措施。這些舉措是“中度干擾假說”理論的很好例證,在授課時可啟發性地引導學生思考自然資源管理與利用問題,思考“適度干擾或利用”的內涵及其適用的自然資源類型,樹立“適度干擾”是維持自然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理念。
第三,探索有效的教學方法。生態學具有多學科交叉的特點,非生態專業受到學時數和實驗課時數少的限制,以及關聯課程開課相對滯后的影響,實際授課時以生態學理論和原理講授為主,因此,生態學教學的手段和方法顯得尤為重要。靈活運用各種有效的教學方法如:講授法、研討式教學法、討論式教學法、Presentation教學法、合作學習、線上線下融合等,對提高教學效果十分有益[6-8]。此外,安排2-4學時的實景教學也十分必要,在講到種群和群落內容時,選擇校園或附近公園的典型復合種群植被,實地講解種群適應、群落組成、功能特征、動態變化等內容,增強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對生態理論應用的理解和思考,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創新性。
第四,增加學生反饋環節。在課程進度的不同階段,實時了解學生對生態學課程內容的理解和想法,鼓勵學生提出各自希望學習的生態學內容、感興趣的生態學問題等,諸如自然生態系統退化、生物多樣性維護與喪失、全球變暖、生物安全、糧食安全等,并在教學過程中針對性地將這些問題融入課堂,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學生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
第五,生態學是反映人與自然矛盾的基本理論,也適于分析人與社會的基本矛盾。在講授相關生態學知識的同時,引導和啟發學生利用生態學理論思考和認識人與社會,以及學生未來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種社會和心理問題。通過生態學理論學習,培養學生的生態思維邏輯,達到知識學習和能力培養的目標。
5 結語
“生態學”作為一門基礎性、交叉性的課程,被越來越多的非生態專業院系選擇開設,因此,針對性地調整《生態學》教材內容,增加現代生態學比例十分必要。通過拓展《生態學》教材內容,改進教學方法,一方面,保證非生態專業學生全面、系統學習生態學的基本概念、理論和方法,熟悉生物在分子、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和景觀等不同尺度的生態學規律,科學認識生物與環境的關系;另一方面,培養學生“生態”思維的習慣和方法,并以此分析人類面臨的各種環境問題,建立科學的生態文明與綠色環保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