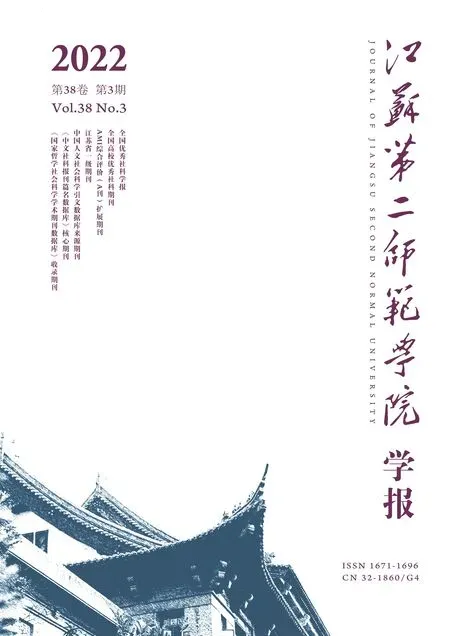語言活動和詞的用法: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疏論
張吉廷 朱進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江蘇南京 210016)
在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的目的、意義、真理性做詮釋時,西方學界維特根斯坦研究者之間存在著大量的激烈的爭論。首先,這種爭論體現在維氏前期《邏輯哲學論》與其后期《哲學研究》的關系上。“新維特根斯坦學派”對維氏做出嶄新的解讀,“他們始終認為,維氏的主要目的——用他本人在描述其后期哲學特征時所使用的一個詞說——是治療……維氏不是渴望提出形而上學理論,而倒是渴望幫助我們擺脫在做哲學時所糾纏于的混亂”[1]1。換言之,新維特根斯坦學派哲學家,皆將維氏理解為規避提出某種“實證的”形而上學計劃,進而將維氏理解為倡導作為“治療”形式的哲學。有的西方學者如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哲學系普羅普斯(Ian Proops)教授卻對這種新的解讀深不以為然,21世紀伊始他認為“這些新穎的解讀無需當作一回事,因為維氏后期的許多自我批評不能被解讀為針對與《邏輯哲學論》無關的內容”[2]。其次,要看到這樣的爭論幾乎貫穿于維氏哲學闡釋之始終。20世紀四五十年代,“第二波”維氏哲學闡釋期間就已出現了這樣的爭論,包括安斯康姆、斯梯尼、波爾等維特根斯坦學者對維氏的闡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三波”維氏哲學思想闡釋過程中涌現出的新維氏學者(例如卡維爾、皮徹、克里普克、羅蒂等維氏評論家)大體上認為《邏輯哲學論》預示著維氏后期包括《哲學研究》在內的著作。再次,在維氏哲學思想中,“規則”沒有被置于核心地位。不過,當代美國哲學家、邏輯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克里普克(Saul Kripke)卻把遵守規則的悖論當作維氏《哲學研究》的中心看待,并堅信該悖論是“哲學迄今所見到的最激進的最原始的懷疑問題”[3]60。與此同時,有些維氏闡釋者則認為,哲學只能描述日常語言而不能改變日常語言自身。我們認為,這種說法顯得有點因循守舊;如果這樣來解釋維氏訴諸日常語言的意義,那么看來好像有失偏頗,其實維氏的意思是單憑哲學根本無法改變語言自身。就日常語言的論述來說,維氏的論證是為日常信念辯護,反對與其論證相沖突的哲學見解。因此維氏眼里的哲學與常識之間本質上不存在什么相互沖突的因素,而且只因堅信人類知識是有條件而非絕對的所以才致使人們訴諸日常語言。本文嘗試在此爭論背景下從語言活動和詞的用法角度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的理路做出文本詮釋意義上的疏論。
一、形而上學:后期語言活動與早期邏輯
討論邏輯的《邏輯哲學論》和探究語言哲學的《哲學研究》二者既具有難以斷裂的深度關聯又做不到與形而上學一刀兩斷。當代哈佛大儒卡維爾曾對維特根斯坦的這兩本杰作之間的關系做了卡氏式的別具一格的論述。維氏《哲學研究》所揭橥的是他自己早期思想如何導錯了航向。奉獻一套嶄新思想理念的《哲學研究》呈現出對《邏輯哲學論》學說的揚棄式的否定而絕非徹底的顛覆。
我們認為,《哲學研究》屬后期維特根斯坦或維氏后期代表作亦為其扛鼎之作,它與前期維氏著作《邏輯哲學論》具有一種不應切割且難以斷裂的深度關聯。后者在內容上牽涉的是邏輯,在這里哲學變成了實行澄清的過程,但我們知道諸多事物的邏輯卻因言不達意或言不盡意而無法表達這些事物本身的內在邏輯;前者在維氏那里具備“風景速寫”[4]2畫冊之特質,其中被了解為一種活動的語言在這種活動中起到了工具的作用或扮演著工具的角色,在這里哲學研究展露為從形形色色方面探究一個相同的問題,這大有哲學上殊途同歸條條大路通羅馬的意味;公正地說,不管是在維氏后期著作《哲學研究》里還是在其前期著作《邏輯哲學論》中,也無論是討論邏輯還是探究語言哲學,要想完全撇開認識論或形而上學是根本做不到的。對于這種“不應切割的深度關聯”,我們嘗試做出以下幾點闡述:
第一,這里必然牽涉當代美國哲學家哈佛大學卡維爾(Stanley Cavell)教授的著名論述。20世紀70年代維特根斯坦哲學思想杰出運用者卡維爾在其《理性的主張》這本著作開篇就發問:“假如,不從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開端入手,因為哲學起點的聞名度在開始時和哲學如何收尾不相上下;假如,不從《哲學研究》開篇入手,因為它的開篇不能被混同于它所體露的哲學的開端,因為人們幾乎不能提供可以用來理解開篇的術語連同開篇本身;假如,我們從一開始就認可,無論如何拋掉開篇不談,這本著作的撰寫方式是與它論述的內容具有內在聯系的,這就意味著我們只有先理解具有某種方式的作品才能理解這種方式(我們稱之為方法);假如,我們不從依賴我們的歷史入手,因為幾乎能夠同時將這本書置于歷史和哲學的地位;假如,我們也不依賴從維特根斯坦的過去入手,從此以后我們很可能假定《哲學研究》的寫作源于《邏輯哲學論》遭受到的批評,這樣的假定與其說是錯誤的倒不如說是捕風捉影的,這既是因為知道什么構成對《邏輯哲學論》的批評當然意味著知道什么構成《邏輯哲學論》中的哲學,也是因為現時關鍵問題不只是明了《哲學研究》的撰寫怎么源于《邏輯哲學論》自身遭受到的批評,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從何入手且怎樣走近《哲學研究》這個文本呢?我們應該怎樣讓這本書教我們走近它或什么的呢?”[5]3
第二,這里的兩個發問,對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與《邏輯哲學論》這兩本著作之間的深層關聯,做出了卡維爾式的別具一格的論述,同時也讓人聯想到晚年卡氏在哲學回憶錄中的一處感悟:“能夠使余對先見之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吾人誨人不倦,學而不厭,學然后知不足;他者永遠擔心天下何人能識君,并老是向吾人傾訴衷腸。這乃是通向解讀維氏《哲學研究》開篇的一種路徑,也即余這些年以不同方式提出的解讀。”[6]122這堪稱是卡維爾式的解讀,也使人想到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在維氏《哲學研究》沒有正式出版之前,就已經悉心研讀了其中的一百多節。就《哲學研究》與《邏輯哲學論》之間的關系而言,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對自己在《邏輯哲學論》中持有的觀點是持否定態度的,不得不說的是,后者使維氏躋身20世紀領軍哲學家如杜威、海德格爾、羅蒂等人行列,但是此后他所形成的哲學見解與使他享譽世界的見解相去甚遠,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看到,他在《哲學研究》中所揭橥的是他早期思想怎樣導錯了方向。有的西方學者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皮徹(George Pitcher)就持有類似這樣的看法[7]。在我們看來,這并不意味著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思想徹底顛覆了前期哲學思想,換句話說,絕不意味著二者之間不存在什么承繼關系即后者實乃純粹是斷裂式的另起爐灶的哲學思想產物。
第三,說《哲學研究》試圖提出一套嶄新的思想理念,這一說法是符合維特根斯坦哲學思想實際狀況的而絕非是強加給他的,但同時應該看到的是《哲學研究》呈現出對《邏輯哲學論》學說的否定而絕非徹底的顛覆。正像有的西方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現代維特根斯坦學術研究中不斷談到,說后期《哲學研究》不代表與早期《邏輯哲學論》一刀兩斷,而二者曾經被認作是毫無關聯的:早期與后期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同等重要”[8]68,但是哲學界不少學者持有后一種看法并在維氏本人那里尋章摘句。我們贊成前一種看法,同時認為在《哲學研究》突顯的許多理路中,維氏在哲學性質為何這一問題上確實提出了別具一格的全新的理念。不得不說,在歐洲哲學史上,形而上學家不是將哲學當作邏輯看待就是當作皇冠科學看待,甚至就連早期維氏也抵擋不住這種看法的極大誘惑。不過,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去思考我們使自己陷于困惑狀態的緣由何在,結果發現了人的思想中具有一種根本的尋求同一性的天生傾向,發現同一性渴望的在于去彌合甚至忽略相關對象間的差異。我們認為,通過對哲學本性的分析,可了解維氏的方法在于使人打破借以看世界的眼罩之緣由,也在于論述語言使用中和世界中的差異性,這種論述既有別于黑格爾對同中之異的論述又有別于黑氏對異中之同的論述。
二、超越獨斷論、邁向日常語言與擁有卓殊的“書寫”形式
《邏輯哲學論》時期維特根斯坦哲學與獨斷論藕斷絲連或含有濃厚的獨斷論色彩,但向后期過渡之際已經完全跨越了獨斷論的藩籬。從邏輯領域邁向日常語言領域從而也就跨出了邏輯范圍。“新維特根斯坦主義”哲學家卡維爾對后期維氏風格上變化做了辯護:維氏的特殊“書寫”形式將“自白”“對話”揉為一體。哲學上的“治療”功用體現在本身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語言的活動中。
首先,作為前期維特根斯坦的杰作《邏輯哲學論》,其中最重要的真知灼見之一是哲學既然不作為一種學說那么哲學就不應該被加以獨斷論式地看待,而維氏后在20世紀30年代初卻坦承其早期哲學含有濃厚的獨斷論色彩。這就揭橥維氏早期哲學思想不可能與對終極實在的追尋毫無關聯,因為形而上學的根本旨趣在于對終極本體的追尋。在西方哲學史上,早在康德的“批判哲學”那里作為幻象的終極實在就已遭到無情的批判,同時康德對未來形而上學做出了論述;近代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布拉德雷,就形而上學的一些問題,譬如第一性質、第二性質、空間與時間、運動與變化、因果關系、自在之物、事物、思想與實在、謬誤、自然、惡、身體與靈魂、善、絕對及其現象、終極懷疑等等,做了淋漓盡致的“頭腦風暴”式的沉思;胡塞爾、皮爾士、羅素、馬利坦、塞拉斯有關形而上學著述是與認識論不可分割的。
與上述這些哲學家與形而上學的牽連一樣,要解釋早期維特根斯坦的獨斷論因素不大可能脫開維氏的后期思想。如同任何哲學的建立皆必然植根于一定的基礎那樣,令人眼花繚亂的《邏輯哲學論》這座哲學大廈奠基于的假定,在于邏輯分析之任務實即去尋找特定的基本命題。因此,如果說早期維氏還與獨斷論藕斷絲連余情未了的話,那么從早期維氏向晚期維氏過渡之際已經徹底地超越了獨斷論而且這種超越或摒棄勢必帶來一定的后果,換句話說,維氏那向極端的反獨斷論之過渡必然促使他所關注的焦點,乃是從邏輯領域邁向日常語言領域從而跨出邏輯范圍,實際上從強調對“家族相似”“語言游戲”做出界定而變成聚焦對它們做出實證的分析,這在風格上當屬從系統全面的哲學寫作變為格言警句式的寫作風格(其中維氏哲學出場風格因呈現為格言警句而飽受后世許多哲學家的詬病)。
其次,作為“新維特根斯坦主義”(或“新維特根斯坦”)巨擘,美國哲學家卡維爾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對后期維氏風格上的變化,表明自己獨到的見解或為維氏哲學上的“變法”做出了嘔心瀝血的令人信服的辯護。卡氏的這種辯護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維氏《哲學研究》乃至維氏整個后期哲學所呈現出的風格令許多讀者感到困惑不已,因為它看來好像算不上哲學的風格(或傳統的哲學風格或現代哲學意義上的風格),但是,卡氏旨在表明維氏的這種行文風格對于哲學并非面目全新的而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書寫”形式,因為這種形式將“自白”和“對話”這兩種風格糅合在一起[9];第二,在卡氏看來,論證的性質促使維氏不得不采用這種風格而非故作標新立異。我們認為,跟西方哲學史上康德、布拉德雷等哲學家一樣,維特根斯坦無論其前期哲學還是后期哲學都不可能與形而上學完全脫鉤,而維氏的《哲學研究》又確實可以歸入哲學的哲學和語言哲學之類;形而上學本身卻穩坐黑格爾所垂青的那座哲學廟宇,同時絕不會遇到黃昏而始終散射出玄學之芳香。
再次,從風格上觀之,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采用的格言警句式的表述方式,完全可以說是奇而不怪新而頗為有道。第一,必須指出的是,維氏的確意識到了自己“力主的研究方式”與“某些人的研究方式格格不入”[10]103,與某些人的研究方式不合軌轍,因為人們適應不了他的方法所要求的而根本上不同于科學上要求的“那種思考方式”,正如格雷林所說的那樣,“維氏后期著述風格上不具有系統性但絕不意味著內容上不具有系統性”[11]v-vi。第二,關鍵在于必須對維氏所說的與他說出所說的之方式做出毫不含糊的區分,因為維氏所言說的東西與他說出所言說的東西之方式這二者之間是不可畫等號的。作為一本遺著,維氏《哲學研究》所含有的一些新穎的思想,應當與他《邏輯哲學論》中那些舊思想加以比照而加以理解;他的新洞見可理解為重在揭橥哲學史上哲學的傳統思想方式之謬誤。第三,維氏《哲學研究》這一著作應該被設想為一部“治療”式的著作,將哲學本身設想為它應當成為的東西(或設想為“治療”);在維氏那里,“哲學處理問題就有如治病一般”[4]137。
此外,就哲學具有“治療”的功能而言,最根本的在于最好把語言視為一種活動,語言活動中“詞”是當作工具使用的,而詞(不作為事物的標簽)的用法是形形色色的,在用詞進行“游戲”(即“用詞行事”)過程中來理解詞,這其實表明可以說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因為,存在著“感覺”一詞的“語法”,以及像“痛苦”和“記憶”這些詞的語法,它們可被知曉相關“語言游戲”的人加以把握,與此同時,期待、意向、記憶皆由于使用語言而可能變為“生活方式”,其實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應該說,維氏奇特的、翻來覆去的方法,并沒有遮蔽其《哲學研究》這一著作里的理論論點——語言最好應該被理解成是一種活動,其中詞是被言說者作為工具來使用的,詞的用法是林林總總的和變化無常的,這就使得某些哲學問題的發生是由于對語言的誤解所造成的。
三、詞的用法:“語言游戲”與“意義”
語言是游戲(“語言游戲”或原始語言)和工具之隱喻。“語言游戲”揭橥的是語言實乃人類的植根于社會的“生活形式”(或“語言游戲”在于突顯語言的述說是一種活動或生活形式的構成部分)。詞的用法穿越錯綜復雜的相似關系的網絡。詞的意義在于語言中的使用。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的“語境原則”發展出“后弗雷格哲學”時代達米特(Michael Dummett)賦予語境原則。哲學家不應該再將詞當作可以用各種方式運用的工具看待,因為它具有鮮活的語境生命而絕非類似商品流通過程中一經鑄成的標簽式的硬幣。
第一,在解讀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時,最應該關注和探討的是它的內在理路。在維氏眼里,哲學研究不在于追求論題或理論(即不提出理論)亦非要去發現固定不變的意義或對象。“詞”是這種對象的永久的標簽,因此,要解決“當語言放假時”哲學問題如何發生這一問題,唯一的辦法乃是通過注意跟手頭問題牽涉的語言的用法。拿做詩人與做哲學家相比,詩人之為詩人是刻意為之,而哲學家之為哲學家卻是無心插柳。我們認為,在《哲學研究》這本著作里,維氏使用的是語言作為一種游戲和語言作為一種工具這兩個隱喻(亦即語言是游戲和工具之隱喻)。維氏在對用詞來稱謂對象的原始語言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主張可以把詞的整個過程當作兒童學習母語的種種游戲之一種看待,并且把這些游戲稱之為“語言游戲”,有時候把原始語言形容為“語言游戲”。這樣一來,維氏就把由語言和行動所組成的“整體”稱之為“語言游戲”。
第二,引入“語言游戲”這一關鍵性概念,維特根斯坦為的是論述數不勝數的形形色色的用途、用途的非確定性和用途“作為活動的一部分”。一方面,語言游戲和家族相似構成《哲學研究》中一條重要的哲學理路,但維氏從未對語言游戲做過明確的界定和詮釋,這是奇怪而不爭的事實。其一,他反復回到語言游戲這一概念且嘗試厘清他關于語言的大體思路。《哲學研究》第二節中論述了原始的語言游戲。在建造語言游戲過程中,建造者及其助手恰恰使用了四個術語——石塊、石柱、石板和石梁,被用來說明奧古斯丁語言圖像的部分內容可能是正確的。其二,語言游戲的一些特質可見于維氏列舉的若干例子和評注中,同時這些品質構成被用生活形式短語所描述的較為廣義上的語境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游戲”的選擇奠基于對語言與游戲的全盤類比。其三,這就決定了最初不能對“游戲”做出一錘定音式本質上的界定,所以維氏坦言未提出某種對于所有我們稱之為語言的東西為共同之物。在這里顯然是淋漓盡致地宣稱從根本上摒棄了日常生活意義上的“解釋”,同時絕不是指向哲學家“醉心于一般”的癥候,倒是應當借詞的用法穿越“一種錯綜復雜的互相重疊、交叉的相似關系的網絡”[4]48。因此完全可以說的是“游戲”形成一個家族,而且家族相似可用來展示描述同一概念的不同用法缺乏邊界和遠非具有確切性。
另一方面,與在近代德國哲學家弗雷格和羅素那里語言不是自給自足的抽象系統不同,從維特根斯坦意義上說的“語言游戲”恰恰要表述的是語言實乃人類的、植根于社會的實踐或“生活形式”,從這個角度來看,“語言游戲”一詞的用意在于突顯語言的述說是一種活動(或一種生活形式的組成部分)。這就可以用“下命令,服從命令”“報告一個事件”“演戲”“猜謎”“詛咒”等來表明語言游戲的多樣性。在考察語言游戲中發現,“我們看到一種錯綜復雜互相重疊、交叉的相似關系的網絡:有時是總體上的,有時是細節上的相似”[4]48。這種相似性的特點被他說成是“家族相似”。在各種各樣游戲構成了“家族”的同時,表達的各種用途也組成了“家族”。如此而來,就探討語言本質唯一有意義的方法而言,借助考察語言在各種方式中的使用情況這種做法最為合適。
第三,在詞的用法方面,除了“語言游戲”之外,《哲學研究》還有對人們使用的“意義”一詞的界定。“一個詞的意義是它在語言中的使用”[4]31。脫開運用中特定的語言環境,詞就會變成標本式的毫無生命力的標簽。首先,在這里人們使用的“意義”一詞可界定為“詞的意義”即為在語言中而非游離于語言之外的使用。這句話成了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口號,從而對這個口號的理解就成了對整個“哲學研究”的理解或做哲學過程的理解,“這個口號出現在對專名的探討中,強調吾人無法根據一個名稱的實指定義(the ostensive definability of a name)來斷定這個名稱的意義是它的承擔者。其次,雖然它的意義可做實指解釋,但它的意義仍然是它的使用,因為解釋一個名稱的意義乃是賦予它正確使用的規則。意義是否被吾人理解,這個問題的標準是后續的正確使用”[4]99。我們認為,在西方語言哲學史上,早在維特根斯坦之前,弗雷格就在《算術的基礎》中就提出了方法論意義上的“語境原則”,暗示僅僅在句子語境中詞語才表示特定的意思而在句子語境之外語詞無異于硬幣式的標簽,更重要的是,“后弗雷格哲學”時代英國當代哲學家達米特賦予語境原則標志著哲學的基礎性轉換(亦即“語言學轉向”)的主要意義。最后,在弗雷格那里“語言轉向”意味著若要分析思想的結構,那么唯一且必須做的就是對語言進行分析,這是因為語言是我們領會思想的主要手段、甚至成了唯一奏效的實用手段,而后期維氏嘗試用“語言游戲”這一概念來俘獲語境所擁有的敏感性。
第四,堅持“一個詞的意義是它在語言中的使用”,這就要求哲學家不復將詞當作對象的名稱看待,也就是說,不再將詞當作可以用各種方式運用的工具看待,這并不比要求哲學家習慣于以符號(指稱的方法)分析語言更容易。我們認為,在維特根斯坦把語言比喻為游戲時其在于突顯語言表達構成“生活形式”的內容;語詞的意義在于使用這一觀點直接反對的是,認為語詞的意義蘊于說話者心中或私人的感覺。然而,關于感覺的言談不是無意義的,因為“感覺”一詞不可能成為只對言說者有意義的一種私人語言的成分;《哲學研究》中論述的很多東西之所以有些哲學家完全無法接受,主要是因為這些哲學家形成了使語言出毛病的壞習慣。因此開明的“哲學家處理問題就猶如治病一般”[4]137。這一哲學治療后來成了新維特根斯坦派學者如卡維爾、普特南、麥克道威爾等人的主旨話題。
四、遵守規則的悖論與“逮蠅瓶中的蒼蠅”
在賦予詞意義時應該以對用途的描述替代闡釋性概括。遵守規則悖論使得維特根斯坦具有潛在的無法過濾掉的懷疑論色彩。維氏后期哲學里帶有一種神秘主義即某種哲學上的神秘境界。哲學對一切既不做說明亦不做推論。這種反理論的立場絕非顛覆了早期有關哲學的論述,因為《哲學研究》所揭橥的是哲學具有非獨斷性意義上的治療的性質。找不到一種哲學方法而確實又有諸多不同的“治療方法”。在辨析語言虛妄權力的同時,哲學家揭橥了無意義的哲學論證之陷阱,從而突顯哲學的目的在于指出“逮蠅瓶中的蒼蠅”出離的方向。
其一,上文已經考察了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中語言規則和“家族相似”與意義的用法方面的理路,我們現在再來梳理對規則的遵守和哲學的蘊意方面的理路。詞的意義在于使用這一基本陳述成為后期維氏思想最為典型的視角變化之基礎,這就是從作為表象的意義概念到一種看似用作哲學研究的關鍵觀點之變化。傳統的意義理論專涉某種與命題無關的、賦予命題以意義之物。“某物”常常不是被置于某個客觀的空間就是被置于心靈中作為精神表象。必須看到的是,在《哲學研究》之前,維氏就已經明確揭橥,我們如果指稱任何作為象征生命的東西,那么就必須說它是具有用途的;而《哲學研究》中表明,哲學家在研究“意義”時必須“看看”詞被賦予的各種不同用途,因此這個新的視角截然不同于“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4]47這也就意味著不要煞費苦心地冥思玄想而必須直面具體事件。因此,在賦予詞意義過程中但凡闡釋性概括皆應被對用途的描述取而代之,這恰恰構成了維氏后期哲學的主旋律。
其二,遵守規則是《哲學研究》中特別加以強調的內容。它成了何者應用于詞語全部用法問題探討的又一核心觀點。在這一問題方面維特根斯坦顯然超越了以往哲學的獨斷論立場。“現在,我們讓這學生從1 000以后接下去寫一個(比如+2)的數列。——而他寫下1 000,1 004,1 008,1 012。”[4]112在這個受到糾正的學生回答道,但是我要以同樣方式繼續做下去時,我們在做什么且這樣做又意味著什么呢?維氏對現時這一問題做了這樣的揭橥:我們怎么學習規則?怎樣遵守規則?它們在社會和公共場合被教之于人、被強使人們遵守嗎?《哲學研究》中這樣論述道:“這就是我們的悖論:沒有什么行為方式能夠由一條規則來決定,因為每一種行為方式都可以被搞得符合于規則。回答是:如果一切事物都能被搞得符合于規則,那么一切事物也就都能被搞得與規則相沖突。因而在這里既沒有什么符合也沒有沖突。”[4]121這里就悖論而言,引來后人大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闡釋。在對此做出懷疑論式詮釋的某些學者眼里,這個悖論竭力鼓吹的是一種懷疑論式的悖論而且解決辦法也是懷疑論式的。
我們認為,公允地說,在遵守規則悖論這個問題上還看不出維特根斯坦帶有明顯的懷疑論色彩,更重要的是,要從其整個前后期哲學貫通來看待這個問題,誠然他的后期哲學中潛在的懷疑論色彩是誰也過濾不掉的,不止于此,維氏后期哲學中還帶有一種神秘主義,換句話說,他達到了某種哲學上的神秘境界,如現代英國新黑格爾主義者芬德萊在20世紀70年代所說的那樣:“這種神秘主義至今依然無人提及但卻沒有理由懷疑它的存在。”[12]68誠然,維氏的意義哲學不可能使他去過多地談論神秘主義,但不應將他理解成是把形而上學家趕回柏拉圖洞穴的人,同時也不應把維氏理解成科學主義巨人和自然的語言行為的仲裁者。但美國后分析哲學家卡維爾的浪漫的懷疑論可以追溯到維氏這一時期的懷疑論。
其三,哲學對一切不做說明同時亦不作推論。大凡哲學家都依據自己的哲學對哲學意蘊做出一番獨具匠心的詮釋。在西方哲學史上,蘇格拉底認為,哲學世界是神生活的世界、真正神秘的世界,同時作為真正完善的人,癲狂的哲學家因通靈而向往神明的世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哲學不是一門生產科學,人們研究哲學緣起于驚詫,哲學智慧不是實用智慧,是非凡的、深奧的和神圣的但卻是無用的;在西塞羅眼里,哲學扮演生命的引路人、宇宙的探險家、罪惡的驅逐者的角色,而且賜予人類和平的生活和消除對死亡的恐懼;照黑格爾說,哲學實為思想對哲學所處時代的領悟;尼采主張,真正的哲學在于把握推理的限度。與西方哲學史上這些哲學家對哲學的看法不同,后期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里對哲學的性質做出了有別于傳統的新穎獨特的描述。如在《邏輯哲學論》中一樣,維氏依舊堅持認為哲學家沒有或不應當提供什么理論之類的東西。那么哲學到底是什么呢?“哲學只是把一切都擺在我們面前,既不做說明也不做推論。——因為一切都一覽無余,也就沒有什么需要說明”[4]76。我們認為,這種反理論立場是與早期維氏思想一脈相承的而絕非顛覆了早期有關哲學的論述,公正地說卻和他早期思想又是具有顯而易見的區分。原因在于,《哲學研究》所揭橥的是哲學具有治療的性質,而非具有獨斷論意義上的性質,搜集提示物,確切點說,為特定目的搜集提示物,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哲學家責無旁貸的工作。不同于柏拉圖認識論上的回憶說,維特根斯坦在其他地方講過,研究哲學歸根結底就是回憶,而且人們提醒自己事實上是在以這種方式使用詞語。
由于某些回憶和一系列事例,各種不同的問題才能夠得以順利地徹底解決。必須指出的是,《邏輯哲學論》時期維特根斯坦一直堅信,“解決哲學上的困難乃是消解哲學以往發現的全部有問題的話語領域”[8]63。哲學上這個話語領域既是極其抽象的也是純然思辨的,同時消解現有哲學問題的進路絕非是清一色而卻是有較大差異的。這就決定了《哲學研究》中找不到一種哲學方法,確實其中卻又存在著諸多方法(也即不同的“治療方法”)。通過分析語言虛妄的權力,哲學家揭橥無意義的哲學論證的陷阱,以前被視為哲學問題的東西,現在也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得以解決,這只不過表示哲學上的疑問“應當完全消失”,這里的“應當”類似于“批判哲學”中的倫理意義上的“應當”。所以說,哲學問題所擁有的形式乃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4]75。如此而來,哲學的目的旨在“給捕蠅瓶中的蒼蠅指明飛出去的途徑”[4]154-155。這可以說實即哲學家在哲學(在做哲學或從事哲學活動)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