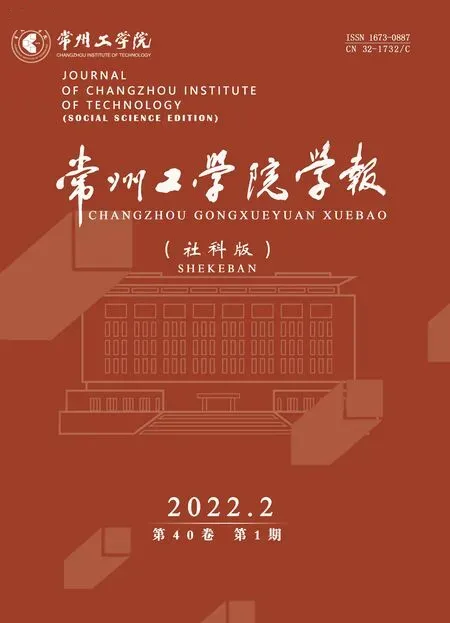論張愛玲與音樂藝術(shù)
周斌斌
(安徽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安徽 蕪湖 241000)
回顧張愛玲研究史,眾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張愛玲作品中獨特的、個人化的聽覺藝術(shù),并以此為切入點,分析張愛玲小說的寫作技巧與風(fēng)格特征。最早的研究者是傅雷,他從張愛玲的藝術(shù)修養(yǎng)角度探討了張愛玲小說的美感,傅雷之后的譚正璧承接傅雷的觀點,亦將張愛玲的藝術(shù)修養(yǎng)視作其文藝之美的母體。筆者試圖循此脈絡(luò),考察張愛玲的音樂素養(yǎng),并探求音樂藝術(shù)對張愛玲創(chuàng)作的影響。
一、張愛玲的音樂藝術(shù)素養(yǎng)
張愛玲學(xué)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音樂。在她上小學(xué)前就已經(jīng)接受過家庭教師的專業(yè)鋼琴教育,而她的音樂啟蒙,則時間更早。劉川鄂在《張愛玲傳》中評價張愛玲的音樂素養(yǎng)時說,她的音樂素養(yǎng)是第一流的[1]。這并非作者對傳主的吹捧與謬贊,而是基于她的家庭教育經(jīng)歷所得出的可靠結(jié)論。跳出張愛玲受教育的經(jīng)歷而單從作品來看,張愛玲音樂素養(yǎng)的形成又與她敏銳的感受力相關(guān)。或許,我們可以綜合這兩方面得出一個結(jié)論:張愛玲一流音樂素養(yǎng)的形成不僅依賴于她所受到的專業(yè)教育,還在于她是個音樂天才。
(一)來自家庭的音樂教育:從傳記作品看張愛玲的音樂素養(yǎng)
一般認為,張愛玲音樂素養(yǎng)的形成與其家庭密不可分。王一心在講張愛玲音樂素養(yǎng)時直言,以張愛玲那樣的出身,幾乎不可能不與音樂發(fā)生關(guān)系[2]。確實,張愛玲父親乃是清末重臣李鴻章的外孫,張愛玲的母親也門第相當(dāng),她乃清末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孫女。出身名門,依靠祖宗蔭庇,貴族化教育是應(yīng)有之義。
張愛玲真正的音樂教育開始于1928年。當(dāng)時張愛玲8歲,張父決意改過自新,把家從天津搬到上海的一處歐式洋房里,張母也因此回國。張母回國后經(jīng)常宴請朋友,宴飲豈能無絲竹,于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樣的畫面:張愛玲的姑姑彈著鋼琴,鋼琴上擺放著盛開的鮮花,張母則立在張愛玲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膀上,配合著鋼琴音吊嗓子,而小張愛玲則總在一旁靜靜欣賞。大人們這才注意到張愛玲有音樂天賦,張母從此對張愛玲在音樂方面悉心培養(yǎng)。張母把音樂才能當(dāng)作張愛玲“西式淑女訓(xùn)練”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教導(dǎo)張愛玲“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么愛惜你的琴”[3]169,她帶著張愛玲聽音樂會,給張愛玲請了一個白俄的琴先生。后來,即使張愛玲父母離婚了,張母也堅持插手張愛玲的教育,繼續(xù)對張愛玲進行音樂方面的培養(yǎng)。
音樂教育在張愛玲就讀圣瑪麗亞女校前半途而止,但正如劉鋒杰所說,張愛玲雖然沒有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yè),卻保持了對音樂的敏感,從而使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因為音樂的介入而有了獨特的魅力[4]。
(二)源自天分的音樂感受:從作品看張愛玲的音樂素養(yǎng)
張愛玲在她的散文中多次談起音樂藝術(shù),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談音樂的文章題目直接叫作《談音樂》,1944年發(fā)表在胡蘭成所辦的刊物《苦竹》上。在這篇文章里,張愛玲洋洋灑灑評價了各種東西方的樂器、各種雅俗的曲調(diào),表面上她是以比較手法表達自己在音樂方面的好惡,實際上在這種舉重若輕的姿態(tài)中,顯示了其不俗的感受力。她在比較古典音樂家的時候,說巴赫的音樂是“小木屋里,墻上的掛鐘滴答搖擺;從木碗里喝牛奶;女人牽著裙子請安;綠草原上有思想著的牛羊與沒有思想的白云彩;沉甸甸的喜悅大聲敲動像金色的結(jié)婚的鐘”[3]171。音響材料的非語義性決定了音樂藝術(shù)的非描寫性特征,因此音樂是以間接的、非視覺的、非具體的方式呈現(xiàn)的,這就使音樂藝術(shù)不可能像視覺藝術(shù)那樣去造型。在音樂藝術(shù)中塑造視覺表象,只能通過聽者自身對音響變化的感受加以聯(lián)想、想象,將感受到的音響運動具體化,甚至同某種視覺表象相聯(lián)系,這樣才能間接、曲折地構(gòu)想出音樂本身所不能提供的東西。從張愛玲對巴赫音樂的視覺性感受描述上,可見其有不凡的音樂感受力。
這種音樂感受力是一項據(jù)說只有12%的人才具有的色聽聯(lián)覺能力[5]。聯(lián)覺指的是當(dāng)一個感覺器官受到刺激時,另一個感覺器官產(chǎn)生了它所特有的感覺。色彩—音樂聯(lián)覺是一種較為常見的聯(lián)覺能力,指聽見聲音會產(chǎn)生色彩、形狀一類的視覺意象。1939年冬天,還在讀大一的張愛玲參加了《西風(fēng)》雜志的征文,寫了一篇《我的天才夢》。這篇文章算是年輕氣盛的張愛玲對文壇的一次自我宣講。她稱自己從小就被視為天才,除了發(fā)展自己的天才外沒有其他的生存目標(biāo)[3]2。她講的天才主要表現(xiàn)在文藝上。她說:“對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dāng)我彈奏鋼琴時,我想象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3]2人是以不同的感覺器官來接受外來刺激的,對于鋼琴樂的感受,人都是依賴于聽覺,在人腦中顯現(xiàn)的基本也都是聽覺意象。張愛玲把音符想象成跳舞的小人,除了是其獨特的聯(lián)覺力在發(fā)揮作用外,很難說沒有聯(lián)想活動的介入。音樂引發(fā)的色聽聯(lián)覺主要有4種形式:第一,局限于眼球后頭顱中的光幻覺;第二,在物體周圍,與物體不相混的底色;第三,投射于聲源方向空間的光幻覺;第四,非常光亮以至湮沒環(huán)境的視覺表現(xiàn)[5]。顯然,把音符想象成跳舞的小人是一種在聯(lián)覺基礎(chǔ)上引發(fā)的后續(xù)的聯(lián)想活動。人的觀念系統(tǒng)是高度聯(lián)系的,因此以一種感覺為基礎(chǔ)完全有可能觸發(fā)與這種感覺相關(guān)的經(jīng)驗或概念,至于聯(lián)想到什么這基于個人經(jīng)驗,與聽者自身的感情相關(guān)。聯(lián)覺和聯(lián)想活動的作用機制目前較為模糊,亦非本文所關(guān)注的,在筆者看來,張愛玲具有一種纖敏的音樂感受力,她能將抽象的音樂具象化,以獨有的感受描繪出音樂的某種境界,而這都得益于她天才般的音樂感受力。
二、音樂藝術(shù)對張愛玲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
韋勒克、沃倫的《文學(xué)理論》認為,各種藝術(shù)有相互影響的關(guān)系,但這關(guān)系并非這一個決定那一個,而是一種具有辯證關(guān)系的復(fù)雜結(jié)構(gòu),這種結(jié)構(gòu)通過一種藝術(shù)進入另一種藝術(shù)[6]。在筆者看來,音樂藝術(shù)進入張愛玲的小說文本,主要體現(xiàn)在3個方面:第一,音樂本身作為一種描寫對象,在小說里直接引入音樂內(nèi)容、音樂術(shù)語、音樂活動,通過音樂表現(xiàn)主題,塑造人物,組織情節(jié),樂聲、歌聲直接成為情節(jié)的一環(huán);第二,小說借鑒音樂的形式,主要在音樂的曲式結(jié)構(gòu)上;第三,通過一定的節(jié)奏、韻律,語句的長短錯落和句式的變換,達到文學(xué)語言的音樂性。
(一)音樂本身作為一種描寫對象
張愛玲的小說里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一些樂器、曲子、音樂活動,這些音樂本身的描寫揭示了人物性格,推動了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渲染了氣氛,與小說的文本表達相得益彰。
1.表現(xiàn)人物形象的音樂描寫
小說中與人物相關(guān)的音樂描寫,通常起到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這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通過音樂描寫襯托女性人物“知書達禮”的淑女形象。張愛玲深諳舊小說的人物塑造法,在塑造大家閨秀類的女性人物時,借由相關(guān)聯(lián)的音樂描寫展現(xiàn)人物內(nèi)在的品性。例如小說《花凋》在介紹主人公鄭川娥時,說她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夠開著無線電睡覺[7]。熱愛音樂的雅好,說明了該女子的才學(xué)與品位。音樂與柔弱女子的相伴,也襯出這位女子形象的嫵媚動人。而如此熱愛音樂的女子最終竟在花季的年齡珠沉玉隕,更增添了《花凋》主題的悲愴。另一種情況是借由音樂描寫表現(xiàn)男性人物自私虛偽的形象。在小說《花凋》里,鄭先生一家落魄不堪,卻擁有無線電和最新流行的唱片,這一細節(jié)描寫,有力諷刺了鄭先生貪圖享樂、奢靡腐敗的做派。
2.組織情節(jié)的音樂描寫
張愛玲在小說中經(jīng)常通過音樂展開故事情節(jié),構(gòu)思故事布局,把樂聲、樂器作為構(gòu)成情節(jié)發(fā)展的一環(huán)。張愛玲運用音樂藝術(shù)組織小說情節(jié)的做法,主要效法《紅樓夢》。《紅樓夢》里的音樂描寫,無一處不起作用,最通常的作用便是起到構(gòu)成情節(jié)發(fā)展的線索作用。張愛玲采用此種寫法,以樂聲、樂器組織情節(jié),層層深入,最終實現(xiàn)“曲終人散”的藝術(shù)效果。《沉香屑·第一爐香》是張愛玲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中篇小說,在這篇小說里,張愛玲著重描寫了一個現(xiàn)代知識青年女性沉淪的全部過程,而在這個過程里,音樂發(fā)揮了重要的鏈接作用。葛薇龍初來梁公館,她的本意是想清白地尋靠個機會。梁太太是個久經(jīng)風(fēng)月場的女人,在她眼中,收留人的標(biāo)準(zhǔn)只有一條,那就是能不能被她利用。所以,梁太太面試葛薇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會彈鋼琴么?如果葛薇龍不會,后面的沉淪也就不會發(fā)生。偏偏出身較好的葛薇龍會彈鋼琴。這時葛薇龍?zhí)ど狭顺翜S的第一步,留在梁府開始交際應(yīng)酬。住進梁府的第一晚,葛薇龍就被大廳宴席里的絲竹之聲迷了耳識,無線電樂聲令她心曠神怡,她微笑著入睡。這里,她滑向沉淪的第二步,沉醉地享受。葛薇龍第一次為梁太太工作是不知情的,她因為參加學(xué)校唱詩班才在無意中給梁太太弄來了大學(xué)生盧兆麟,但也在這次請客宴上,葛薇龍第一次當(dāng)眾彈唱《緬甸之夜》,開始留心為梁太太工作。另外也是這次請客,牽出了葛薇龍與喬琪喬糾纏不清的戀情。可以說音樂在此起到了重要的線索作用,層層推進了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
3.渲染環(huán)境的音樂描寫
音樂作為一種表現(xiàn)情感的藝術(shù),在小說里通常起著渲染氛圍、升華情感的作用。張愛玲的寫作有一個特點,喜歡將小說中的場景、氛圍具體化、感覺化,以實現(xiàn)人物與環(huán)境的和諧相融,這就好比一幅人物畫,總要以配合人物情緒的背景來表現(xiàn)整幅畫面的意境。張愛玲喜用音樂,尤其喜用高音表現(xiàn)歡快的環(huán)境氛圍。比如《沉香屑·第二爐香》,這篇小說采用降調(diào)的方式,小說開頭是一片濃厚的喜氣洋洋的氛圍,新郎羅杰安百登結(jié)婚當(dāng)天早上去新娘家的路上,他感到“那是個淡色的,高音的世界,到處是光與音樂”[8]55。這是一段虛寫,將主人公歡喜雀躍的感受世界泛寫為現(xiàn)實感官世界,將小說的氣氛推向高潮。接下來描寫婚禮,“風(fēng)琴上的音樂如同洪大的風(fēng),吹得燭火直向一邊飄”,高音的環(huán)境還在繼續(xù),只是稍有趨和。再接著,新郎和新娘離開教堂之后,耳邊沒有了教堂的音樂和喧囂的人聲,高音回落,完成了整個降調(diào)的過程,環(huán)境描寫開始趨于寫實,零度描寫周遭的環(huán)境氛圍。除了這篇小說,在《金鎖記》中也用“細細的音樂”描繪曹七巧被姜季澤告白時喜悅的氛圍,在《鴻鸞禧》中用“高升發(fā)揚的音樂”將婚禮的場面推向高潮。這些例子不勝枚舉。可見,音樂作為一種背景、引子,在張愛玲小說中雖然沒有占據(jù)過主要地位,但總是縈繞左右,無時或缺。
(二)音樂形式在小說中的嫁接
以音樂的思維方式結(jié)構(gòu)小說,參照音樂的曲式邏輯進行構(gòu)思,把音樂的形式嫁接到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這不僅豐富了小說的表現(xiàn)形式,還帶來了小說創(chuàng)作的革新。張愛玲借鑒音樂的曲式結(jié)構(gòu)革新小說的敘述方式,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主導(dǎo)動機的重復(fù),復(fù)調(diào)技巧的運用。
1.主導(dǎo)動機的重復(fù)
音樂是一種轉(zhuǎn)瞬即逝的時間藝術(shù),因此為了強調(diào)音樂印象,重復(fù)就成為音樂藝術(shù)重要的表現(xiàn)因素之一。在音樂作品里,用一個特定的、反復(fù)出現(xiàn)的旋律來表現(xiàn)某個角色的性格即為作品的主導(dǎo)動機[9]。主導(dǎo)動機除了能代表人物外,還能代表各種對象,如一種情緒、一種思想等。通過變奏,主導(dǎo)動機還能體現(xiàn)人物性格的變化、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因此音樂的主導(dǎo)動機被廣泛運用到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在意識流小說里,主導(dǎo)動機一般有兩種使用方式:一是杜夏丹式,只用兩三詞的短語;二是普魯斯特式,在小說開端使用主導(dǎo)動機暗示某個主題,然后在敘述過程中不斷地回到這個主題。張愛玲小說中的主導(dǎo)動機兩種兼有。第一類如小說《傾城之戀》,在這篇小說的戰(zhàn)爭敘述方面,張愛玲重復(fù)使用了“吱呦呃呃呃呃”這個摹聲詞。此摹聲詞主要模擬大炮射擊的聲音。張愛玲很少直接描寫殘酷的戰(zhàn)爭場面,如槍林彈雨等,而是通過一系列重復(fù)的摹聲詞象征殘酷的戰(zhàn)爭場面,每一次“吱呦呃呃呃呃”響起就是一次戰(zhàn)爭沖突的激烈爆發(fā),對于孤立無援的白流蘇就是危機感和荒蕪感的加重,表現(xiàn)了大時代下個人命運惘惘的威脅。此為第一種,用重復(fù)的短語表現(xiàn)一種場景、一種情緒的主導(dǎo)動機。第二種普魯斯特式的主導(dǎo)動機在《傾城之戀》中也表現(xiàn)明顯。《傾城之戀》開頭便是一段胡琴聲,胡琴咿咿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故事[8]160。胡琴是中國的傳統(tǒng)樂器,歐陽修《試院聞胡琴作》一詩說“胡琴本胡人樂,奚奴彈之雙淚落”。張愛玲在此以胡琴奏出這一段蒼涼故事,取的就是胡琴表現(xiàn)蒼涼的主題。胡琴聲的第二次出現(xiàn)發(fā)生在徐太太來之后,而這正是情節(jié)的一個轉(zhuǎn)折,也是人物思想性格產(chǎn)生變化的最初體現(xiàn)。如果說在這之前白流蘇還是一個囿于家庭的“受氣包”,那從這次談話之后,白流蘇已漸漸從自怨自艾中走出,將為自己的生存作一番拼斗。在這里,胡琴借助敘述的變奏,體現(xiàn)了人物思想性格的變化。故事結(jié)尾,白流蘇成功與富家子弟范柳原結(jié)婚了,這看似大歡喜的結(jié)局又響起了胡琴聲,同樣的胡琴咿咿呀呀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故事[8]201。相同胡琴聲的重復(fù)貫穿故事的首尾,既是重復(fù)的主導(dǎo)動機暗示主題的蒼涼,也在這主導(dǎo)動機的反復(fù)出現(xiàn)中導(dǎo)致結(jié)構(gòu)上的循環(huán)往復(fù)。傳統(tǒng)小說是時間性的線性結(jié)構(gòu),主導(dǎo)動機的反復(fù)使得小說脫離了線性的時空順序,什么是始、什么是終,都是流水般的不舍晝夜,循環(huán)的宿命感強化了哲學(xué)意義上的悲劇感。
2.復(fù)調(diào)技巧的運用
音樂的織體有4種,其中經(jīng)常運用到小說中的是復(fù)調(diào)藝術(shù)。復(fù)調(diào)在音樂旋律上的組合方法叫作對位法,意指兩條以上的旋律同時進行,相互交織,組成一個立體結(jié)構(gòu)。巴赫金最早進行復(fù)調(diào)概念的文學(xué)研究,認為復(fù)調(diào)小說的本質(zhì)特征是對話性,對話是復(fù)調(diào)得以形成的質(zhì)的規(guī)定性[10]。張愛玲的小說一般采用故事外敘述者的方式進行敘述,但《心經(jīng)》一篇,主要以人物對話展開故事敘述。《心經(jīng)》圍繞“戀父情結(jié)”主要有三重敘述視角,分別屬于女兒許小寒、父親許峰儀、母親許太太。三重視角圍繞“戀父”一事各有態(tài)度,分別發(fā)出了各自的敘述聲音。對于女兒許小寒來說,父親是她在這個世界上最愛的人,她對父親的聲音就是“我不過要你知道我的心”“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離開你的”[8]130。與此同時,許峰儀何曾不知女兒對自己異樣的感情,只是他不能接受這違背人倫的情感,所以他對許小寒的聲音只能是推拒的,“小寒,我們不能這樣下去了。我……我們得想個辦法,我打算把你送到你三舅母那兒去住些時”[8]131。面對這種難堪的愛,許小寒是進攻的話語姿勢,許峰儀對女兒的進攻始終是躲拒的,最后找了個和許小寒差不多模樣的段綾卿作為替代。而目睹這些的許太太無力改變也無心改變這種狀況,只能默默忍受及默默保護自己的女兒,面對小寒對自己的肆意嘲諷忍受不理,她對小寒的聲音一直是母親對女兒的關(guān)愛,“要緊的倒是你——你年紀輕著呢”,“現(xiàn)在我雖然遲了一步,有一分力,總得出一分力。你明天就動身,到你三舅母那兒去”[8]145。不同視角展開的人物對話消解了作者的情感態(tài)度,還主人公以話語權(quán),消解了人的社會道德屬性,還人以本能欲望的原始面貌。讀者在這篇小說里圍繞人性問題聽到了各種人物的聲音,眾聲喧嘩的背后是擁有獨立意識和完整價值的人發(fā)出的多重聲音的組合,這就是小說中的復(fù)調(diào)藝術(shù),所達到的功用也是鮮明的,能夠擺脫單調(diào)的敘述方式,呈現(xiàn)更為復(fù)雜的情感狀況,構(gòu)成一種有張力的敘述。
(三)小說語言的音樂性
歐根·希穆涅克在《美學(xué)與藝術(shù)總論》中講到,“文學(xué)語言,特別是詩的語言,都是與‘諧音’,即所謂‘音樂的’品質(zhì)密不可分”[11]。文學(xué)語言包含的音樂品質(zhì)表現(xiàn)在語音、音調(diào)、節(jié)奏這幾個方面。從語音上看,張愛玲小說里有大量疊音詞、雙聲詞、疊韻詞存在。以《第一爐香》為例,在透過葛薇龍的視角看梁府環(huán)境的這段描寫中,就使用了大量疊音詞,如“齊齊整整”“疏疏落落”等;雙聲詞有“住宅”“仿佛”等;疊韻詞有“闌干”“滿山”等。語音和諧,讀之朗朗上口。在音調(diào)和節(jié)奏方面,張愛玲小說里的例子也是俯拾即是。例如《第二爐香》寫羅杰與愫細結(jié)婚的場面:“現(xiàn)在,他前生所做的這個夢,向他緩緩地走過來了;裹著銀白的紗,云里霧里,向他走過來了。走過玫瑰色的窗子,她變了玫瑰色;走過藍色的窗子,她變了藍色;走過金黃色的窗,她和她的頭發(fā)燃燒起來了。”[8]64“走過……走過……”,這是排比的手法。此句以排比句式排列,句式整齊,每句的字數(shù)大致相同,節(jié)拍數(shù)均勻,節(jié)奏和諧。另外,該句還運用了雙聲詞、疊韻詞,音韻流動婉轉(zhuǎn),富有和諧的音樂美。除了語音、音調(diào)、節(jié)奏外,張愛玲還善用標(biāo)點,制造抑揚頓挫的音樂效果。如《金鎖記》中七巧對侄子春熹連聲責(zé)罵:“我把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我三茶六飯款待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什么地方虧待了你,你欺負我女兒?你那狼心狗肺,你道我揣摩不出么?”[8]240一連串感嘆號、問號的運用使得句式錯落有致,富有鏗鏘的節(jié)奏。
三、結(jié)語
早在1944年,胡蘭成就注意到讀張愛玲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鋼琴上行走,每一步都發(fā)出音樂[12]。時隔半個世紀,今天的學(xué)者劉鋒杰在評胡蘭成這段近似諂媚的文字時也同意他的表述,肯定這是張愛玲作品的真實寫照[13]。張愛玲作品的獨特價值正在于她用音樂來寫小說。小說與音樂的聯(lián)姻古已有之,張愛玲小說中顯性的音樂元素便是效法古典小說《紅樓夢》。所不同的是,張愛玲的文學(xué)音樂化形式指向的是蒼涼的情感意蘊層面。蒼涼既是張愛玲小說總的底色,也是其所造的音樂境界。胡琴之咿呀,遠處飄來的渺音,這些張愛玲常用的音樂意象就是蒼涼本體所顯之象,月映萬川,每一個音樂意象就是一曲敬慕的挽歌,萬川生輝,音樂意象的交相輝映共同抵達人生蒼涼的悲劇底蘊。此外,張愛玲小說的音樂化結(jié)構(gòu)延展了讀者的審美感受,讀者的期待視域在此受到阻隔,因為這并非讀者慣常見到的小說表達方式。所以,小說表達方式的陌生化使得讀者在細細品味中感受文字音韻之美,欣賞整體悲涼的音樂化情境。張愛玲小說的蒼涼是音樂化的蒼涼,是文本與讀者共同參與構(gòu)造的蒼涼,也從這個意義上說,張愛玲顯示了其獨特的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