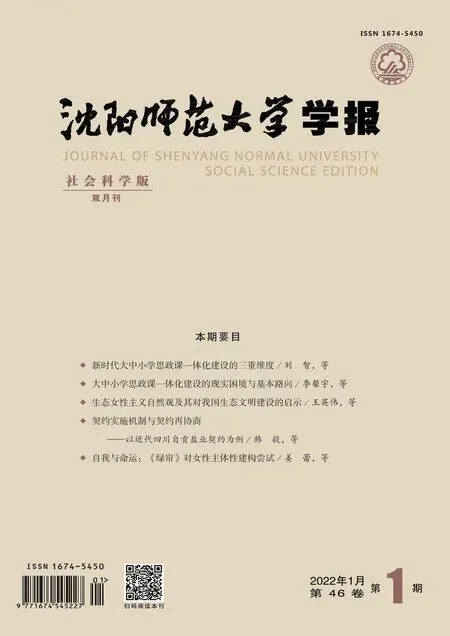契約實施機制與契約再協商
——以近代四川自貢鹽業契約為例
韓 毅,沈海泳,2
(1.遼寧大學 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110036;2.沈陽建筑大學 設計藝術學院,遼寧 沈陽110168)
一、引言
距今1.8億年前,四川地區形成了一個具有良好封閉條件的淺海盆地,在經歷數次海水淹沒后沉積下豐富的鹽類物質。因此,在這樣的地質條件下,四川盆地地下擁有區域分布廣闊、儲藏豐富的鹽鹵資源。四川井鹽,通過向地下鉆探幾百米到一千米不等的距離,汲取地下深處的鹽鹵資源。
自貢是我國著名的鹽都,在其檔案館中保存著自1732年(清雍正十年)到1949年之間有關于鹽業的歷史檔案3萬余件,其中鹽業契約檔案3 000余件。這些鹽業契約檔案涉及鑿井、買賣、租佃、合伙等方面,生動地再現了自貢當時歷史上有關于鹽業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美國學者曾小萍認為,四川自貢的鹽業生產是中國最早的私人高資本、高生產能力的工業企業,并且將自貢從事鹽業生產和投資的商人,稱作中國近代早期的企業家[1]1。四川自貢鹽業企業家通過契約的形式,創建了中國本土的契約股份制。鹽業契約將不同資金形式(土地、勞動力)、閑置的游資、外地人的資金,匯集到鹽井的開鑿上,有效地促進了中國最早的大規模股份制工業生產。本文通過深入挖掘鹽業契約的實施機制來分析自貢的企業家是如何通過親屬網絡、專門的中間人等形式將資金穩定地聯合起來,投入鹽井長時間進行開鑿與生產的。
對四川自貢鹽業契約實施機制和契約再協商的分析,研究清代四川自貢的鹽業企業家如何保障契約穩定實施與履約,對于當今企業融資、企業之間合同的簽訂和履約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不完全契約與自我實施機制
(一)不完全契約理論
理論上完全契約預先知道在執行契約時可能會遇到的各種情況,并且提供了強制性的自我實施機制。因此,完全契約在經濟學理論中都能得到執行。但是,現實世界中契約總是不完全的。根據本杰明·克萊因的論述,交易雙方無法就契約實施中遇到的所有情況,在簽約時做出詳細的契約條款加以規定[2]48-57。第一,現實世界中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使得人在處理紛繁復雜的信息時,其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交易雙方在締約時,簽訂的契約不可能是完全的。第二,在一份契約中,明確所有可能發生的偶然事件是不可能的。在復雜的、不可預測的世界里,交易雙方不可能為未來發生的各種情況制定出契約條款。第三,正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在變化多端的世界里,要制定完全詳盡的契約,代價是昂貴的,交易者更多使用的是不完全契約,這種契約通常并不仔細地考慮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與制定完備、詳盡的契約相比,這種不完全的、有缺陷的契約,成本中包含了能應對偶然情況附加條款而產生的交易成本。而完全契約中,包含有把各種不確定因素全部寫進契約的大量“筆墨”成本,還有承擔浪費在搜尋與談判上的成本,還要承擔大量的信息成本與估量成本。正是因為現實世界中的契約大多是不完全契約,當交易雙方遇到“特殊”情況,無法從契約條款中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契約的不完全性,給交易雙方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契約實施機制成為保障契約順利實施的關鍵。
(二)契約自我實施機制
契約的實施機制,是限制交易中的不誠實行為,保證契約得到履行的機制。契約的自我實施機制是通過對交易一方的違約行為施加一種私人懲罰來保證交易的正常進行[3]211。自我實施的私人懲罰涉及三種典型的懲罰方式。第一種是道德準則懲罰。因為交易中的欺騙行為進行自我道德譴責,從而引起消極的道德情感,這種懲罰需要建立在具有相同習俗的相同價值觀的參與人之間。第二種終止契約交易懲罰。在契約交易中,存在著因為終止交易關系引起的直接損失。1.契約中的押金。很多的契約中有押金的存在,一旦交易雙方中交納押金的一方違約,扣除押金是最直接的手段。例如,佃農耕種地主的土地,需要繳納一定的押金作為保證金,如果佃農不能及時繳納地租,地主將會扣除押金。“比日憑證,客家自備押租銅錢拾伍千文整”[4]272。2.契約交易中存在著專用性資產投入,當契約中的一方進行專用性投入時,就產生了“專用性準租”。資產的專用性,無論是地點的專用性還是用途的專用性,強調的是要素難以低成本地重新配置而處于一種易被要挾的境地所產生的收益。而無論是一般性的“準租金”還是由于資產專用性產生的“專用性準租”,它們都是可能被占用的[5]90。四川自貢鹽井開發中,投資者在地主的土地上開挖鹽井,在鹽井開鑿成功前都是一種專用性資本投入,因此地主要求投資者不斷進行專用性資產投入,在契約中規定不允許投資者暫停對井的挖掘,一旦停止挖掘,地主有權利收回鹽井的開采權和收益權。“自出佃以后,客人不得停工住銼;如有停工住銼,任主人將井接回,客人不得稱說用出銼井工本。”[6]314第三種是交易者的聲譽受損。交易一方違約的事情在市場中傳播后,使其聲譽受損。其他人不愿意與其交易,提高其在市場上的交易成本。欺騙者會發現未來在市場上,無人愿意與其簽署契約進行交易。聲譽損失,對于交易者來說是一種成本很高的懲罰。聲譽資本的數量越大,交易者就越依賴自我履行機制,從而在契約中明確規定的條款也就越少。中國鄉村人們生活在“差序格局”之中,具有相同血緣和地緣關系的人之間形成了緊密的網絡關系。即使在現代化的今天,鄉村的土地流轉契約很多都是選擇口頭的形式。有學者對17省1 962戶農戶調查發現,有86%的農戶在土地流轉時沒有簽訂書面契約而是采用口頭契約的形式,這些契約中87.6%的土地流轉發生在具有相同血緣或地緣關系之間[7]86。通過契約的自我實施機制,這些農村土地流轉契約大都得到了有效的執行。
三、鹽業契約第三方介入的實施機制
私人的聲譽機制是有限的,單純依靠市場化的力量通過契約自我實施機制來完成契約的履約是不現實的。從契約的結構上看,契約包含了契約規則、契約執行、契約懲罰等內容。契約第一方自我實施機制中,實際上是交易雙方共同監督了契約的實施。但是,當契約變得復雜、契約的不完全性增加、契約已經無法通過自我實施機制進行保障的時候,需要第三方私人實施機制介入。
(一)第三方私人介入契約
第三方私人介入契約,使得契約實施機制得到進一步完善。第三方私人實施制度不需要國家和法律的支持,它得以實施的主要條件是一種自我實施的集體主義懲罰機制和社區內較為充分的信息流通[8]76。清代宗族由于其宗族成員之間充分的信息流通優勢,使得宗族在契約的第三方私人實施機制中具有天然的優勢。清代鄉村的宗族社會包含了婚姻關系、血緣關系,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宗族的影響,無論是購買田產、子女教育還是賑濟救災。個人作為宗族中的個體,其交往范圍、生存價值、社會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宗族關系網絡之中[9]315。因此,宗族之中的契約,交易雙方一旦有人違約,其不誠信的行為將會在宗族內部得到快速的傳播。違約者相當于降低了其在宗族中的信用資質,當其尋找新的合作對象時,需要付出更高的擔保成本。因此,宗族成員之間的契約簽訂時,往往通過族人見證、公告、宴請、唱戲等諸多形式來向外界宣布契約真實有效。
宗族參與契約,除了對契約實施起到見證和監督作用,當簽約者違約時,宗族內部還可以通過族規對其進行非常嚴格的教育和懲罰。陳瑞認為,中國古代宗族內部,族長掌握著宗族內部事務的最高裁判權和控制權,是宗族裁判的最后執行人[10]56。宗族積極致力于安定和諧的理想社會秩序的構建。因此,族長常常被賦予調解平息紛爭、處理族內外糾紛、維護族內秩序穩定的重任。族長時常扮演族內外調解勸諭人的角色,成為宗族內部公正的化身。
根據清代乾隆《重修古歙東門許氏宗譜》記載:
凡我族人事之有不平,情或出于不得已,請眾于祠,備述顛末,自鼠牙雀角以至財產賬目,族長正副剖析是非,直為處分,各得其平。其或強欺弱,眾暴寡、富吞貧、恃尊凌卑、以少犯上、藐視族人而仇仇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族長正副而知此,愿秉是非之公[10]57。
當契約雙方處在同一個宗族內部時,宗族作為第三方實施機制可以有效地保障契約的順利實施,是契約的強力保障。
賣主當憑中證言明,原契失落,只有契尾,并無押借押當等情。日后倘有執契生事者,一力惟賣主及房族中證是問……。憑房族 王閣麟 王貴信[6]。
這份契約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土地持有的憑證“原契”部分丟失了,只有契尾。但憑借房族中證,證明該土地的所有權為賣主家族所有,并且得到了買主的認可,因此在契約中寫明,“日后倘有執契生事者,一力惟賣主及房族中證是問”。這份契約體現了宗族在土地管理上強大的公信力。
鹽業契約的第三方私人實施機制的演進,是一個由個人(族長)實施到行業組織(協會會長)實施、從兼職組織(宗族)到職業組織(行業協會組織)實施、從一事一議到制定具體的行業規范,不斷演化的過程。行業協會規范作為第三方契約實施機制擴大了保護契約的實施范圍。青木昌彥認為,隨著產權交易范圍不斷擴展,潛在交易者已無法事先識別其潛在交易伙伴,這時第三方就有必要代替直接的交易伙伴成為非人格化交易的治理手段[11]63-79。行業規范作為行業生產過程,交易雙方長期博弈形成的彼此都共同遵守的規則,在行業內部得到了從業人員的廣泛遵守。一方面,不遵守行業規則的人,其違約信息可以在行業從業者之間廣泛傳播,未來交易的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清代行業幫會訂立的行業規則具有非常嚴格的強制實施性。例如,童書業在《中國手工業發展史》中說:“幫,分有手工業行幫和商業行幫,都有相當嚴密的組織和幫規。幫,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行幫也作為迎神、祭祀、公益救濟事業的主體。此外,還有承應官府保證征役、征物的作用。幫會的會長,除了宗教事務外,主要就是查看有無外行人侵略本行的利益,和同行人中違反行業規定的行為,收取會費,如果會長辦事不力也要受到處罰。這些行業協會的規定都相當的嚴格。”[12]485
行業規范的存在,比較宗族而言擴大了第三方私人契約實施的范圍。以行業為實施的范圍,凡是從事該行業的人員簽訂的契約都是在該行業規范的框架內,并且按照規范的相關規定執行契約。在清代四川自貢,鹽業土地的擁有者和投資者通過契約來進行合資開鑿鹽井、開采井鹽資源的時候,都廣泛遵守當地的行業規范。清代同治朝《富順縣志》卷三十《井規·桐、龍、新、長四垱井規》記載:
其井作為三十股生意,照每月三十天分派。初立佃時,主、客議明客出押山銀或數十金,或百金;主人立出佃字約,客人立承佃字約,末書合同,主、客各執一紙。所佃井基,地主出井眼、天地二車、柜房、灶房、牛棚、鹽倉一切基址,每月得地脈日份或四、五、六、七天不等;客出銼井一切費用,每月得客日份二十二、三、四天不等。……其全井年限,方銼井時與見微功時,俱不起班;俟井見功,水足四口,大約八十擔,火足二十余口,始行分班起限,推煎或十二年、十六年、二十年,限滿全井交還地主——此客井情形也。
(二)第三方政府介入強制實施機制
市場交易范圍不斷擴大,超出宗族和行業范圍,需要帶有強制力和暴力手段的第三方來保護契約的實施,因此政府成為代替私人的第三方契約保障者。當國家最終掌握了強制性權力,可以沒收不履行裁決人的財產或將他們投入監獄時,懲罰犯規者的成本大為降低[11]。政府代替私人和行業組織保障契約的實施主要的優勢是政府執行契約和監督契約的職能具有規模效益。交易者實施的契約保護,往往需要高額的成本;由私人或者行業協會執行的契約保護也需要交易者交納一定數量的成本投入。相比之下,政府執行的契約保護是國家提供的保護性服務,因此對于個人而言成本比較低。
自貢地方審判廳民事簡易庭第一審判決:熊永鑒于戊子年承買張啟堂所有麗澤井半口鍋份之契約完全有效,并歸子孫永遠管業。民國十五年[6]621。政府成為第三方實施機制,使得契約的實施機制進入一個新階段。對于市場中的交易者而言,政府法院不是契約實施的最優選擇,往往是最后的選擇。因此,私人實施機制依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互聯網電子商務經濟大為發展的今天,我們越發地看見契約的第一方實施機制、第三方私人實施機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契約再協商與調整
契約調整與再協商作為一個概念是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艾倫·施瓦茨(Alan Schwartz)在《法律契約理論與不完全契約》中提出的一個關于法律如何解決契約糾紛的一種方式。再協商的經濟模型假定,任何一方可以無成本地執行原始契約的條款。因此,再協商是帕累托改進:一方將只建議比在契約下使其福利改善的變化,而另一方將只接受至少與其現在福利相同的變化。盡管無成本實施的假設條件太強,但如果接受調整請求的一方沒有因契約而投資,或如果它可以無成本地與另一方簽訂契約,再協商仍是帕累托改進的。在后者情況中,這一方通常是投資的。當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時,昂貴的實施成本意味著契約調整不一定是帕累托改進的;一方可能接受再協商的建議,但將使其比原來契約條件下的境況更壞[13]96-125。
(一)現實世界中契約再協商的成本
再協商經濟模型假定的無成本條件過于嚴格,在現實世界中很難得以實現。現實世界的契約再協商成本包括:契約再協商的事后成本和事前成本。
1.契約再協商的事后成本,指的是契約再協商過程本身產生的成本。交易雙方就新的契約內容進行談判,產生了相關的成本。而且,因為初始契約無法得到順利實施,對于雙方都會帶來一定的成本損失。為了減少因為契約無法實施而造成的損失,在當期簽訂契約的雙方在C1>C2時(C1為損失契約的成本,C2為契約再協商成本),都可以做出一定的讓步以使得契約得以調整。這其中協商的空間,專用性資產投入大的一方,作出讓步空間大;同時,另一方也會做出一定的妥協以減少自身的損失。
布斯倫克爾指出,傳統中國的農村里以調解方式解決糾紛得以實現的原因,在于中國人的價值觀所具有的功能。在中國,和諧具有極高的價值,對于原則的過分堅持往往被視為攪亂和諧行為而遭人厭棄。所以,對方已作出了讓步的姿態仍固執地主張自己權利的當事者,在這個社會里就會冒著與輿論為敵的危險。這種危險作為無言的壓力,迫使當事者放棄一部分權利向對手作出讓步,其結果促進了合意的形成[14]27-33。
湖北隨州乾隆六年,佃農朱又堂租種劉正坤“兩石田”,“說定每年八石租課”。后來朱又堂的妻子死了,勞動人手減少,種不得這些地,把一部分田退給了地主,只留一畝旱地繼續耕種。并且說定收了麥子,改為“四六分”,地主得四分,佃戶得六分(刑科題本,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刑部尚書來保題)[15]98-144。
該份契約的調節幅度是比較大的。第一個改動是,佃農耕種的數量發生了改動,由原來的“兩石田”更改為“只留一畝旱地”。第二個改動是,由原來的定額租制改為分成租制,“說定每年八石租課”改為“四六分,地主得四分,佃戶得六分”。這樣的契約改動對于地主而言,顯然是不利的,因為地主需要時間來尋找新的租佃者。但是,地主為了當時的成本損失最小化,于是簽訂了該份契約。這也為日后地主不斷要求增加租金埋下了隱患。契約的這種調節,在當期會因為失去契約造成的損失大而達成契約,交易雙方的暫時的利益平衡形成了契約調節,但是當下一租期來到的時候,契約雙方的利益無法平衡時,還可能發生契約的違約。
在T1期,地主與佃農簽訂了租佃契約,佃農無法繼續完成契約。佃農提出退還部分耕種土地面積給地主,調整契約內容。此時,對于佃農來說是最優選擇,失去整個契約是次優選擇。對于地主來說維持原有契約是最優選擇,在T1期如果沒有其他人能夠馬上接替原有的佃農繼續耕種土地,地主接受佃農提出的契約調整是理性選擇。現實世界中,契約的再協商造成多種成本。部分是事后成本,即契約協商過程造成的成本,如交易雙方之間就新的契約不停地進行談判。在T2期,地主和佃農再進行契約協商,地主希望彌補T1期造成的損失,因此需要增加租金數額,同時佃農的聲譽資本降低,這些都增加了契約協商的難度,造成了契約協商的成本。
2.契約協商事前成本,指當事人在契約簽訂前,就已經預料到了未來對于契約要進一步的磋商。當事人已經購得的房產或土地,出售者可能會找理由進行贖回,因此,當事人在交易時的預期會導致其購買后資產專用性投資不足。上海市檔案館中有一些關于清代房屋買賣的契約檔案,很好地說明了這種契約事前成本的存在。道光年間孫尚修等出賣祖上遺留房產的契約,再現了契約不斷找贖調整的過程。其契約經過了“賣契”“加契”“絕契”“嘆契”“裝修據”五張契約。時間跨度從道光二年十一月到道光三年三月之間。在原有的契約基礎上,不斷地簽訂新的契約來調整交易。可見,在完全購買整個房屋之前,交易者是不敢對其房產進行投入整修的,一旦進行修繕或是整修,原來的房屋主人很可能以此為要挾要求購買者提供更多的房屋購買款。
類似的找贖案例,在中國的其他地區也普遍存在。
立補字侄若裕先年退有大會一分,分數前契載明,今因歲暮荒歉,不得已前來向得畾玉叔手內補過銅錢叁佰五拾文正,其錢贖回會之日,一足算完,不致少欠,口恐無憑,立補字為照。
代筆弟 若 在見妻楊氏道光壬辰年十月廿八日若裕立[16]。
該份契約是在“前契”的基礎上增補調整的一份契約,其目的是賣主生活所迫無錢度日,通過對“活賣”的土地找補的方式,獲得了“銅錢叁佰五拾文正”,這種找補對于購買者而言無疑是一種損失,但是為了原有契約能夠繼續實施,不得不對賣主的要求作出一定的讓步。而且,看似是一種買賣契約,實則是如果出賣方有足夠的資金即可贖回“其錢贖回會之日,一足算完”。這種契約的協商造成了土地租佃者其后期的投資不足,因擔心地主將土地進行贖回,會減少對土地的深耕、修整等專用性資產投入。
同樣,在四川自貢的鹽業契約中,年限井是一種開發到規定年限歸還給地主的鹽井開發模式,當不斷需要投資者(井主)開挖深井的時候,發現其專用性資產的投資性逐漸降低。為了進一步鼓勵投資者(井主)加大投資,加快鹽井的挖掘,當地人通過“子孫井”即子孫永遠管業的方式來合資鑿井,改變了因為契約的事先成本導致的契約效率低下的問題。
(二)契約自動調節機制
根據契約規定的機制,當產量發生變化時,契約能自動調節。在不完全契約中設計一種機制,即根據每一年糧食的生產情況來協商糧食收成的浮動系數K。將浮動系數K與契約中的額定租金相乘,得出最后應該繳納的租金數量R=K·R額定。浮動系數K起到了自動調整契約的作用。
清代,在江蘇、浙江、廣東等南方省份有一種隨著收成分數浮動租額的定額租制。這種租佃制雖有一定的租額,卻要按照收成的分數作為系數乘以定額租來確定交租的具體數量。例如,有某一塊租佃田地,地主和佃農事先簽訂契約,規定了租金的數量。如果該年是十成收獲,則佃農就要按照確定的租額交租;如果該年是九成收獲,則佃農就可按照租額的九折交租。以此類推,八成收獲就按八折交租,七成收獲就按七折交租。
浮動額度的定額租契約,是一種可以自動調節的契約形式。當糧食產量受氣候原因產生變化時,契約交易雙方通過協商認定產量的成數,確定最終的租金。周遠廉等在《清代租佃制研究》中,列舉了根據收成的情況來決定浮動系數K的實際案例。乾隆朝年間,在廣東保昌縣,曾從方佃耕陳文華嘗田二畝二分,“每年租谷五石,議定按照收成分數交租”[15]。江蘇崇明縣,“各業主亦系按照豐歉交收,相安已久”。浙江吳興地方,“其賃田以耕之戶,向時人尚謹愿,除實租外,視豐歉為盈縮”,也都是按照收成分數交租的意思。
這種自動調整契約內容的浮動租額的定額租制,有效地調節了契約雙方之間的契約關系,即正常年份的時候交易雙方按照契約規定的租金額繳納;災害年景的時候,地主承擔部分風險和經濟損失。同時,這種浮動租額的定額租,降低了因為監督佃農勞動生產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定額租制,因為天氣、蟲災等一系列自然原因帶來的風險都將由佃農獨立承擔,而地主只需要按照規定的時間地點,獲得契約規定的定額租金或實物租。對于地主而言有效地節約了監督成本,但對于佃農而言,因為沒有足夠的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所以一旦出現大的災害,佃農往往是傾其所有也無法完成定額的租金。浮動額度的定額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方面的矛盾,降低了交易成本。根據R=K·R額定,地主和佃農只需要協商好浮動的收成系數即可。這相對于分成租的“臨田監分”,節省了人力和物力,最主要的是在分擔自然災害可能帶來風險的同時,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
現代社會中,肯德基連鎖店的房租合同中,在租金的確定上這樣規定:租金按每租賃年度凈營業額之百分比計算。例如:年凈營業額在700萬元(含700萬元)以下部分,按凈營業額之8%抽取租金,年凈營業額在700萬元以上至900萬元(含900萬元)之間,按凈營業額之9%抽取租金,年凈營業額超過900萬元以上部分按凈營業額之10%抽取租金。這是根據營業額來確定系數K,R=Ki·NSi(NS為Net Sale的縮寫)。
這種浮動定額租金契約,通過契約規定調整了交易雙方的收益比例,增加了契約實施的寬容度,使得契約更容易得到實施。
(三)第三方介入的契約再協商
1.政府官員調節。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江蘇省“忽因生蟲遇風,以致損傷田禾”。在原來實行定額租制的地方,佃農實在無力完成那種高額地租。在農民與佃農嚴重對峙,地主收不上租的情況下,江蘇巡撫陳弘謀從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采取“批檄各州縣官,凡報蟲傷者,務即履畝勘禾苗,在田勘明收成分數,傳諭業佃人等,按照所收分數完租;如因分數多少爭較者,即就田間所收各半均分,……如此均分,盡可相安。”照所收分數完租,指的是原來的定額租,要按照因災減產的成數,相應地降低定額地租的成數。就所收各半均分,指的是分成租制,是在連前一種辦法也行不通時,而拿出的最后一張王牌[13]。政府官員介入契約調整,帶有強制性質,提高了再協商的效率,有助于獲得交易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2.宗族內部調節契約。清代早期在四川自貢的許多鹽場,一些鹽業土地買賣契約主要是發生在宗族內部、地緣內部同鄉人之間。通過土地產權買賣,新的土地所有者在自己的土地上開鑿鹽井。當鹽業土地很難估計其價值時,很可能出現交易時價格被低估的現象。因此,當鹽井開鑿成功后,賣主或賣主的后代,通過收取掛紅錢的方式,追加土地出讓的價格。
第102號掛紅約[6]96
立收掛紅錢(井基原主借口鑿井成功,前來披紅慶賀,以索取金錢)人族孫明德,因乾隆丙戌年三方公議,將祖遺方家灣前抵壩上墻腳,后抵暢野公業墻腳,上抵張陜西店墻腳,下抵塘灣墻腳,三房杜賣與暢野公名下,明價實契,已經貳拾余年。今業內新開貢海、濴海二井,已見微水,明德請憑族人索取掛紅錢;眾勸暢野公,暢野公給明德錢貳拾千文。明德系大股子,今已收足,以后不得生端異說;如有異說,惟中人是問。恐口無憑,立此存據。
憑中 李復萬 李崇先
李芳時筆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族孫明德立
檔案中“暢野”為簡化后的稱呼,全名應該為李暢野,整個契約是發生在李氏宗族內部的關于土地的產權交易。李暢野在乾隆丙戌年(乾隆三十一年,1776年)購買了其族孫李明德和族侄李玉錄等人的地基。經過22年的準備和開鑿,到乾隆五十三年,開鑿的貢海井和濴海井已經見到微水,這是開鑿鹽井成功前的重要標志。因此,面對即將大量升值的土地,原土地所有者前來索取掛紅錢。從契約中能夠觀察到兩個細節。第一,三房是“杜賣”,即雙方立定是不可以贖回的契約。而且,契約中也寫明,原買賣契約是“明價實契”,說明契約是真實有效的。第二,原有的契約定立是發生在乾隆三十一年,距離這份掛紅契約發生的年代已經有22年之久。這兩點都造成了契約的當事人李暢野不愿意支付“掛紅錢”。因此,才有了“明德請憑族人索取掛紅錢”和“眾勸暢野公”。李明德和李玉錄等人知道在原有契約的規定范圍,靠自己的力量很難成功索取“掛紅錢”,于是就通過族人從中調解,勸李暢野支付他們出賣土地后的經濟補償。
本份契約履行靠的依然是宗族內部的再協商。“如有異說,惟中人是問”,中國古代契約中的“中人”更多的是擔任契約的見證人的角色,不承擔契約人之間的連帶賠償責任。但是在這份契約中,“中人”同時也是“族人”,正是在這些人的勸說之下,李暢野才給了原有契約人一定的經濟補償。要求中人提供連帶責任,這是這份契約的特殊之處也是這份契約的珍貴之處。可以說,通過該份契約,我們可以窺見在200多年前發生在四川自貢的李氏宗族內部一場關于鹽井開采成功后,而引起激烈爭論的內部協調會議。宗族中的權威者通過經濟的補償來調解宗族內部的危機,最終通過既得利益者李暢野的讓步,宗族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也使得原有的買賣契約得以順利地繼續執行。
在宗族內部范圍內進行契約調整與再協商,有效降低了契約實施帶來的交易成本,使得交易可以順利進行。因此,宗族成員往往希望在宗族內部尋找合作者。總體來說,晉商商號的發展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進行的互助合作。在家族企業內部,依靠血緣關系作為連接紐帶,由家族骨干成員控制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從而達到追求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目標[17]。
五、結論
新古典經濟學將契約的完全性做了假設,但在現實世界中人們很難就契約的各種情況事前通過談判作出最優的設計。現實世界的契約呈現出不完全性,契約的實施機制和契約的再協商是契約得以順利實施的關鍵。
契約的實施機制,限定了交易雙方的欺騙行為,保障契約的順利執行。契約再協商作為契約實施機制的重要補充,當契約執行過程遇到的情況大大超出預期時,交易雙方出于效率的考慮對初始契約進行再協商和調整,使得各方利益得到平衡,最大程度地執行契約。在四川自貢近代的鹽業契約中,其包含的執行時間經常是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這些契約在執行的過程中雖然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情況,但還是得以持續地執行了下去。既有多種契約實施機制的作用,也有契約再協商的調節作用。正是在這些機制的共同作用下,這些長期契約得以有效順利的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