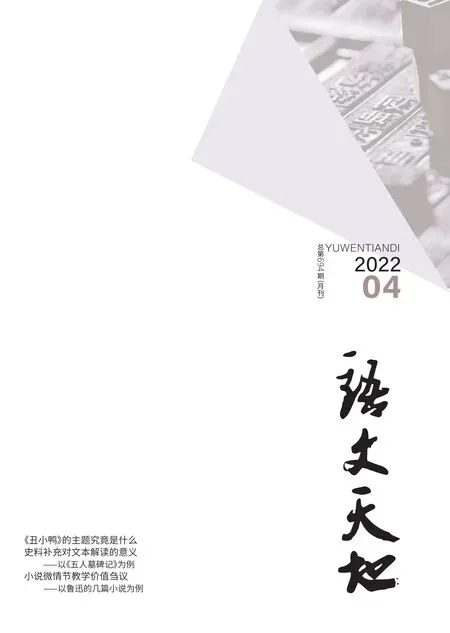雙向交疊繪風物,古今對接抒真情
——《念奴嬌·赤壁懷古》賞析
咸 娟
詞發展到宋代,經過很多大家的傾心耕作,日漸成為文學的正統樣式,而且占據宋代文學的制高點,成為表征宋代文學的符號。其中,蘇軾對詞的發展和走向成熟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雖然蘇軾也把詞作為抒發情感的媒介,但是由于其獨特的人生際遇和博大的胸襟,詞在他的筆端就具有了獨特的興味。從表現情感的方式看,婉約詞的陰柔纏綿和豪放詞的大氣磅礴,讓宋詞呈現出絢麗多姿的色彩。蘇軾對兩種風格的詞都有所操,而且都留下了很多經典。而《念奴嬌·赤壁懷古》作為豪放詞的代表,在詞林中稱得上是一朵奇葩。詞作書寫的方式和表情達意選取的視角,以及藝術技法的處理都烙上鮮明的蘇子印記。
《念奴嬌·赤壁懷古》是蘇軾經歷“烏臺詩案”劫難被貶到黃州之后以“戴罪之身”游覽黃州赤壁時所寫的一首豪放詞。為了排解心中的憤懣,蘇軾只能寄情山水。投身山水間,盡管個體生命面對茫茫宇宙恰似“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但是暫時從俗務中逃離也可以獲得暫時的釋懷。相較于“二賦”——前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在繪景抒情明志方面表現出獨特的風格。
一、虛構與真實映照,架構藝術時空
作家用文學描寫社會世情,反映人情世態的方式大致有兩種,紀實和虛構。雖然角度不同,但對世情和人生的觀照都是相似的。文學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外化,不同的生存境遇、不一樣的人生遭際造成作品文字的語質、語色不同。不論外顯的特質如何,“言為心聲”所表現出來的作者的性情是真實的。正值在仕途上大顯身手有所作為的年齡,被貶黃州對蘇軾的打擊是很大的。但是,在現實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他只能選擇方式排解內心苦悶的方式。黃州的赤壁本是造化所賜的自然風物。在蘇軾沒有造訪之前,它沒有真正意義上進入世人的視野。一旦進入蘇軾的眼中,成為他筆下描寫的對象,成為寄托情志的對象時,就具有豐富的生命氣息。從某種程度上說,與其是黃州山水滋養了蘇軾,不如說是蘇軾成就了赤壁的山水。
不過,從標題“赤壁懷古”可以看出,詞人面對眼前赤壁壯美的景色,情隨事遷,引發的是對古人古事的懷想。當然,懷古的目的還是言今言己。言及“赤壁”,人們自然而然會想到“火燒赤壁”的歷史事件。但是,從“有道是”三個字可以看出,眼前的“赤壁”并非是發生歷史大事件的地方。就是說,作者運用假托歷史故事和歷史人物的文學技法申說自己的內心感受。這種以虛寫實的寫法,在虛擬和真實之間架設藝術空間,由眼前的風物聯想到古代的戰爭和參與指揮這場戰爭的英雄人物,字里行間的因寄所托不言而喻。眼前的山水是真實的,赤壁是虛設發生歷史故事(此處不是火燒赤壁真正的發生地)的場所,兩者疊加在一起,亦真亦幻,增強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就像蘇軾的詞《江城子·記夢》一樣,把真實與夢境結合,以創設豐富的藝術時空。
二、歷史與現實對接,寄寓思想情致
“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情溢于海。”蘇軾面對“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雄渾壯闊的赤壁風景,心潮澎湃,情不能自已,這種情感的撞擊是復雜多元的。之所以引發如此大的情感沖動,源于詞人獨特的人生遭際;而情感表達的方式,不是采取直筆式的,而是將歷史與現實相對接,景與情相貫通。
站在赤壁山水前,目睹滾滾東去的大江水,再想想此時此地的自己,作者的心情是復雜的。生命個體在“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的時間流逝中漸漸老去——“早生華發”。盡管山水風物、清風明月是“大自然之無盡藏也”,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是生命之短暫,匆匆過客又能夠真正享受多少呢。而面對“如畫江山”,作者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多少豪杰”。此中的豪杰是歷史上建立豐功偉業,留得生前身后名的英雄人物。由此,作者把鏡頭由眼前向歷史縱深處延伸,聚焦到三國亂世,定格在眾人皆知的火燒赤壁的歷史事件。戰爭是殘酷的,生靈涂炭。但是,亂世出英豪,一場馳名古今的戰爭,成就了很多英雄。因為赤壁之戰,就有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因為赤壁之戰,成就了“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周公瑾。“小喬初嫁了”,以美人襯托英雄,英姿颯爽,建功立業。
歷史人物指點江山,成就功業,而自己呢?與周瑜相比,心懷鴻鵠之志的蘇軾不覺悲從中來。時間淘洗,英雄難在;時光飛逝,功業未就。時空轉換,再與英雄相比,失意的苦悶何以消解?蘇東坡曾說:“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韌不拔之志。”可是,現實的殘酷把他置于泥淖之中,僅憑自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從中脫身。憤懣失望要找尋一種消解的方式,這樣,“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當是無奈中的選擇。古人古事,從文字中走出來的是一位儒雅有為的英雄;赤壁山水間,站立的是一個心懷報國志,卻見棄于朝廷的失意之人。周瑜是成功者,蘇軾是失意者,二人對照,作者心中所思所感通過“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三個倒裝句生動地表現出來。
三、古人與今人互釋,營造藝術氛圍
歷史和現實是兩個層面的時空存在,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蘇軾很好地把兩者融合在一起。這種處理的方式,除了表情達意的需要,也有藝術氛圍營造的考量。在歷史的長河中,無數人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歷史,不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都能夠給現實中的人留下很多啟示——“以史為鑒,可以明興替;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而活在現實中的人,在繼往開來中也用自己的方式書寫新的歷史。古代的人與今天的人,雖然生活在不同的時空中,但是在精神情感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接續和相互闡釋的作用。當然,以古人映照今人,以古鑒今是主導。
在蘇軾的這首懷古詞中,同樣也采取古今互釋的技法布局構思。言周瑜之得志,實際是來襯托自己之失意;以古戰場血雨腥風的慘烈來映照失意者內心的苦悶。異質性的對比和同質性的映襯,兩相疊加,營造出陰郁的藝術氛圍。不過,從蘇東坡一生的遭際看,對修行者和樂天派的蘇子來說,人生的失意縱使把自己暫時投置到人生的低谷中,但是他對世界仍然懷著向善而樂觀的心態。在外放成為自己仕途常態的人生旅途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站立。這種樂觀曠達,在老之將至,“回首向來蕭瑟處”時,他用“身如不系之舟,心似已灰之木。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加以總結。用逆向思維看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使用的藝術技法,他寫古人周瑜,除了反襯自己眼前不得志的悲傷苦悶,還寄托著“只要自己不沉淪放棄,終將會取得像周瑜那樣的成就”之意。很顯然,對作者的這一層意蘊寄托應該品讀出來。
一首懷古詞,作者以二元對接的方式繪景寫情。在歷史與現實、古人和今人的對照互釋中,讀者不僅能夠讀出文字中濃濃的情思,更能夠感受到蘇子的心性人格。而二元對接的藝術架構,讓作品的藝術意境變得更加豐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