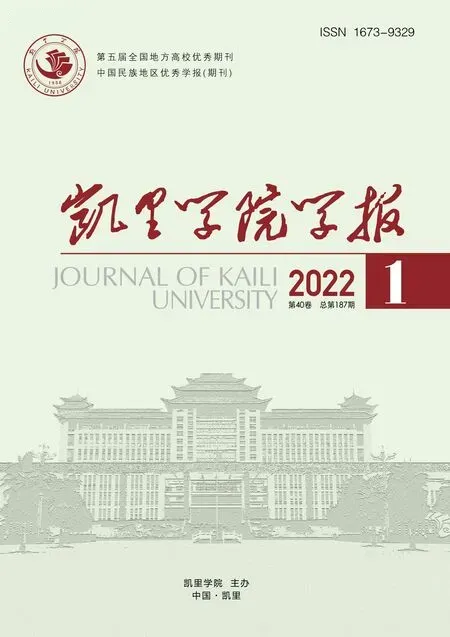生計與生態互構:基于國外關于牧區流動性的意義與關鍵問題的分析
趙國棟
(西藏民族大學,陜西咸陽 712082)
任何對牧區生態、生計、產業、社會方面的研究都無法完全繞過牧區中存在的流動性。從牧區的發展模式看流動性,爭論似乎集中于現代化的作用與傳統文化的作用之爭。這從Mark Moritz的總結中也可以發現,他指出,關于非洲牧區制度的未來和發展的爭論主要由兩種相互排斥的范式主導:流動性范式和現代化范式[1]。
流動性范式(Mobility paradigm)建立在“對牧區系統的理解”基礎之上。20 世紀90 年代進一步受到強調,該范式應當被視為一種新的牧區研究方法[2]。“希望確保適當的政策、法律機制和支持系統的存在,以允許畜牧主義向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的生計系統的自我進化是該范式的主要研究取向”[2]。流動性范式有兩個基本共識:(1)牧區、牧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2)牧民與牧群的流動是維持牧區平衡,尤其是牧業與生態環境之間平衡關系的關鍵。關于第一點,多數研究持肯定的態度。譬如Samuel D.Fuhlendorf 等人強調,牧場管理必須看到牧區作為一個復雜生態系統的地位,所以不能僅僅把放牧作為實現生產目標的工具[3]。關于第二點,Eyasu Elias指出,牧民們傳統的遷徙生活方式和對旱地資源管理的知識使他們一般能夠抵御干旱,并在其社區管理的牧場中維持著健康的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4]。為求得“自然進化的發展”,該范式在政策維度強調5個重點:(1)保護剩余的牧場不受外來的侵蝕;(2)支持地方牧區組織對牧區的管理;(3)支持牧民的流動性與靈活性;(4)改善市場基礎設施或其他結構,使牧民能夠通過減少和補充牲畜以更有效地應對干旱威脅;(5)關注可持續的生計[5]。總體而言,流動性范式的目標是支持畜牧系統以及其與自然的關系,而不是去人為干預或者改變它們。
現代化范式(Modernization paradigm)以非洲干旱、半干旱區域為例,強調隨著人口壓力的增加以及農業的擴張,發展大規模的畜牧系統并不明智,或者說失去了可發展的空間以及解決人口問題和發展問題的能力。牧民的出路在于加強混合養殖系統,并在其中完成牲畜生產[6]。整體上,該觀點并不否認畜牧系統與牧場的適應關系,也沒有拒絕流動性范式的理論框架[7]。但是他們關注的中心似乎更傾向于干旱、半干旱地區的整體發展,這樣一來,牧業與牧民則成為他們分析的一個組成部分。不過,傳統牧業系統的功能并沒有得到這一研究范式的充分認可[1]。由于這一傾向,研究者更關注農牧區域內的發展問題,而非純牧業區域,并強調把作物生產與畜牧的流動、生產相結合的重要性,推進以區域為單位的一體化生產與多樣化經營,尤其是在家庭生產經營上的多樣化[8]。“畜牧業生產系統的未來取決于與農業更緊密的一體化形式”[9]。
一、牧區與牧業的重要性
流動性的重要性發軔于牧區和牧業的重要性,相關研究對后者重要性的討論及相關觀點的形成主要依據的是對非洲牧區與畜牧業的分析。在此以三項研究為例進行簡要說明。
世界約25%的陸地面積供養著約2 000 萬戶牧民家庭,約1.8 億至2 億人口[10]。畜牧生產支撐著占世界近一半土地的農村人口的生計,并日益為城市人口作出貢獻[11]。A.Mottet等人強調,全球的牲畜飼養預計將在2005年至2050年間增長70%來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需求,同時畜牧業也將面對農業生態和氣候變化、市場全球化、人口遷移和政治不穩定等各種挑戰。這些將進一步增加擴大耕地面積和加劇畜群對自然資源的爭奪,導致耕地肥力下降和畜牧資源退化。因此,要進一步重視牧區和牧業發展,并做好相應規劃[11]。
A.A.Degen 從畜牧系統中綿羊奶與山羊奶的特征與作用角度出發,突出在牧區的干旱季節這些小反芻動物奶汁的重要意義。他認為,牧業的特殊意義由此得到顯現,即畜牧業中的動物能夠為畜牧社會提供奶、肉、羊毛、皮革和糞便,此外,還可以作為現金來源和運輸的馱畜,從而支撐廣大牧業社會人口并向外界提供畜牧產品[10]。
Peter Tyrrell等人以肯尼亞—坦桑尼亞邊界區域為例,強調在特定的保護區條件下,牧業與野生動物保護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保護區遠遠不能確保在全球范圍內維持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所需的空間。通過一項案例研究,他們認為:通過加強依賴于開放空間、流動性、社會網絡和公共資源的制度安排的畜牧活動,可以間接實現對大型開放景觀、生物多樣性以及野生動物和家畜共同的保護。所謂的“大型開放空間”(large open spaces)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保護方法,以應對出現的土地碎片化、異化和退化的威脅。該方法強調,基于牧區的重要性,應該強調將一項生態系統擴展至多維度的方法,以此來提升彈性和獲取新的經濟機會,達到有助于畜牧社區整體建設的目標[12]。
二、流動性的意義:六個重要維度
雖然本文主要關注牧業流動性意義與關鍵問題,對流動性的形成與發展不做討論,但仍要強調的一點是:流動性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并且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值得深入研究。本部分的重點在于從多維度討論流動性所具有的積極向度的影響,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和風險不做系統解讀。
(一)高原古路網的形成
關于橫跨亞洲綿延萬里的古代“絲綢之路”的形成與演變,還有許多未解之謎。處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區,崎嶇難行的交通條件都構成了重大的限制因素,但為什么它能夠被人們開辟出來并縱橫連貫于一體,這個問題顯得尤其重要。
Michael D.Frachetti 等人以“流動累積”(flow accumulation)模型計算了牧業社會的年度流動路線,其海拔范圍在750m 到4 000m 之間。他們發現,存在一個高分辨的流動網絡,并模擬出幾個世紀的季節性游牧牧民是如何在亞洲山區形成離散的連接路線的。然后,他們將已知的高海拔絲綢之路遺址的位置與這些優化的游牧流動的地理位置進行比較,發現在山區存在顯著的對應關系。所以,他們認為“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網絡起源于牧民之間數百年的相互作用,主要方式是在山區的高海拔和低海拔區域之間,隨著季節的變化牧民們遷徙牛群和羊群的不間斷的流動[13]。這一發現可能會促使考古學家為古代區域連通性的生成與演變尋求更為深入的解釋。
(二)牧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
Aime-Landry Dongmo 等人以非洲的富拉尼牧民為例,分析了他們面對種植面積擴大、草場短缺以及牛對作物的損害等問題,通過增加流動性進行的應對。他們強調,通過牧民們的類似于流動性的地方性知識,可以實現一種對牧民、牲畜與牧場之間的較好的協調,這對該區域的發展至關重要[14]。
關于流動性如何促進牧區經濟和牧業社會的發展,一項在埃塞俄比亞南部的博拉納牧區進行的調查做了深入的分析。該調查共選取了5個農民協會,20個村莊。調查發現,為了尋求牧場的良性發展以及增加畜牧業收入,他們采取了兩種傳統策略:焚燒和流動。焚燒從1975 年之后不再實行,只剩下流動。那里的流動性主要體現于兩個方面:居家為基礎的放牧(home based)和衛星式放牧(satellite herding),前者是在營地附近放牧擠奶的母牛、小牛和小于2 歲的幼獸,后者是到距營地更遠的牧場放牧公牛和超過2歲的未成年牲畜[15]。他們通過這樣的流動應對給牧業帶來巨大風險的干旱、飼料和水的短缺以及動物疾病侵襲等因素的影響。
當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時,流動性對牧區經濟社會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出來。在埃塞俄比亞南部和東部地區,放牧遷移是應對反復干旱和水資源短缺的最佳策略。Minyahel Tilahun 等人的研究發現,流動性是埃塞俄比亞東北部的阿法爾牧區牧民適應氣候變化影響的首選,如果沒有流動的支持,氣候變化會對牲畜資源和牧民的生計造成巨大的破壞[16]。
(三)有效應對氣候變化
有研究指出,雖然作為傳統的牧區管理策略,“牧群積累”可以一定程度上應對氣候變化,但它需要有足夠的畜群休養期[17]。以流動性應對氣候變化,尤其是干旱的威脅被認為是牧區應對策略的首選。這在對非洲牧區的研究中得到較好的體現[18]。
Anthony Egeru指出,氣候變化給東非的牧民帶來了巨大壓力,譬如導致出現“新的”牲畜和作物疾病,導致作物歉收和低產量,導致出現糧食短缺、水資源短缺和牧草供應差異等。牧民們有多種信息渠道來獲得氣候變化的信息,其中接受度最高和最可靠的渠道是社區會議,并以轉移放牧區和飲水區為主要手段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19]。Bilal Butt 等人強調,牲畜的流動是牧民應對牧場環境變化的最重要方式,其中一種策略就是在干旱時,將牲畜轉移到離牧草利用率低的地區更近的臨時營地。他們檢驗了肯尼亞境內的馬賽牧民沿保護區的北部邊界的牛群遷移假說以及季節性和牛群規模對牛群遷移參數的影響。結果顯示,流動可降低牧民及其牲畜在干旱期間所面臨的壓力[20]。
(四)促進牧場植被的恢復
在中國的某些半干旱區域,農業的擴張破壞了原有農牧發展的功能格局,引發了地下水位下降、植被退化、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態問題[21]。Richard Kock 等人指出,20 世紀非洲人口及動物數量的巨大變化導致了對動植物的空前破壞,這就需要重新審視相關政策和優先發展的事項[22]。整體而言,人口數量的增加以及牧場開發模式的變化一定程度上給牧場植被帶來了巨大挑戰。
形成和保持良好的牧區流動性則被視為一種恢復植被的有效途徑。Meredith Root-Bernstein等人研究指出,游牧和遷徙是古代人類為了適應大型食草動物的運動而開展的活動,而這些食草動物本身也會跟隨有利的環境條件遷移。于是,他們提出了一種“季節性遷移野化”(transhumant rewilding)的模式,以實現生態恢復和畜牧系統中糧食生產的可持續性[23]。這樣,特定的草場會隨著這種遷移而得到恢復涵養時機。
(五)有利于牧區土壤養分的均衡
牧區草場的土壤受放牧影響較大,流動性則降低了其中的負面影響。V.O.Snow 等人研究發現,畜牧系統有許多耕地系統不具備的特點,譬如:(1)牧場具有生物多樣性,植物物種之間的相互作用更大;(2)放牧動物和牧場之間具有復雜的相互作用,并受到環境、植物種類和動物行為的強烈影響,處理不好有導致惡性循環的風險;(3)動物在空間上會轉移大量的營養物質,可能會加劇土壤的變異[24]。
M.Okoti等人將放牧對土壤的影響進行了類型化,比較了主放牧區和畜群集散宿營區土壤微生物的大小和活性,結果表明:放牧動物的露營活動增加了營地土壤的肥力和生物活性,但損害了主要放牧區域的土壤屬性[25]。通過有效的季節性流動宿營以及放牧的牧場轉換,可以減少對放牧區域的持續影響。另一項關于肯尼亞北部圖爾卡納區(Turkana district)的研究也表明,由于牲畜被集中于該區域內的特定地區,流動性不足,所以土壤受到較大的侵蝕[26]。
(六)有利于協調人與野生動物的關系
對牧場進行科學的使用和管理通常被視作牧場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保障,不當的放牧則會對牧場產生破壞性影響。人與野生動物關系惡化是重要的一類影響,所以保持牧場的良性狀態對野生動物保護和牧業社會發展均具有重要性。
對此,Wilfred O.Odadi等人評估了肯尼亞北部的“計劃放牧”對當地的植被、野生動物和牲畜屬性的影響。結果發現:計劃放牧改善了植被條件和植被豐富度,并且提升了野生有蹄類動物的存在度和物種豐富度,促進了干旱期相對較差牛群的增重。這些結果表明了在公共牧區實施計劃放牧(有計劃的流動遷移)的積極效果[27]。Richard H.Lamprey 和Robin S.Reid 對肯尼亞西南部的牧業系統的研究發現,土地私有化導致了圍欄的增加,由此野生動物的活動被限制,來自旅游業的收入也受到影響。他們認為,除非在牧區土地管理上有所改變,維持牲畜和野生動物的自由流動,否則,這種獨特的畜牧——野生動物系統將很快消失[28]。
三、認識和處理好流動性的五個關鍵問題
(一)流動性不是萬能的,需要平衡好流動性與多樣化生計之間的關系
雖然流動性對牧區和牧業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并不是萬能的。這需要我們時刻警醒,隨著牧區人口增加(并不贊同于勞動力人口的增加)帶來的人口壓力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目標化訴求的增加,僅僅依靠流動性去實現顯得力不從心。此時,凸顯出流動性與多樣化生計相結合的重要性。
S.Joshi 等人對巴基斯坦北部干旱和半干旱的游牧地區的研究認為,為了應對當地氣候變化的影響,牧民們根據自身的實踐經驗和本地知識采取了一系列適應策略來應對這種變化,其中最主要的兩種就是遷移模式的改變和多樣化的生計[29]。
Douglas L.Johnson 指出,雖然牧民主要通過在牧區之間季節性輪換放牧以保護對他們至關重要的旱季草場資源,但是牧區的荒漠化卻在20 世紀發生了。他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包括農業向牧區的擴張壓力、重要旱季牧場的消失、牧民的定居化、戰爭和內部沖突的影響、牧區資源的國有化、傳統公有資源管理系統的崩潰,以及社會變革和經濟強化在內的眾多因素,使牧民通過流動性對草場進行管理和調控的系統崩潰了。他同時指出,通過對牧區實行全面的規劃,以牧民的生存智慧為基礎,把畜牧系統中的流動性與牧民生存所需要的多樣性(靈活的生計方式)相結合,強化并利用好牧民形成的共同財產體系,可以避免那些不利的因素,從而避免牧場的退化和荒漠化[30]。
(二)形成和維持良性流動性,要格外處理好流動與安居的關系
作為中國三大牧區管理政策之一的牧民定居政策雖然得到廣泛推行,但也受到了較多質疑,譬如認為定居破壞了牧民的本土知識,打破了原有的流動性,會給牧區生態與牧區產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對此,有研究者提出:在定居中應尊重牧民的意愿,尋求更多的創新之法[31]。筆者對西藏阿里地區普蘭縣牧區的調查發現,當地出現了流動性再造的效應,而其基礎就是安居房的建設和定居的出現,從而實現了牧區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保護與優化的有機結合。這一結論與包智明、石騰飛通過對內蒙古清水區的研究得出的“流動性的再造”結論相符[32]。這表明,流動性與牧民定居之間至少是可以相融的,而且可以產生更加優化的效果。
目前,在牧場的開發政策中,主張把流動性與定居相結合的取向已經獲得了多維度的研究支撐,譬如在研究牧民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生態與產業風險時,Michael Nkuba等人強調把本地知識預測(indigenous forecasts)和科學預測(scientific forecasts)相結合,推進支持流動與定居放牧的雙路徑方法(two-prong approach)[33]。
KAZATO Mari 研究了蒙古人在城市和牧區生活的時間分配,研究發現:在兒童處于學齡階段、城市地區有較高工資的工作機會以及由于自然災害家庭出現較大牲畜損失的時候,牧民更傾向于選擇在城鎮地區居住,而在其他時間,尤其是城鎮中難覓得較好工作機會時,人們更傾向于選擇在牧區生活。另外,職業技能、社會關系以及自然環境的變化會影響他們的選擇[34]。這至少表明,城鎮中的定居與牧業、流動性并不矛盾,它們之間存在協調發展的可能。
(三)擺脫純經濟計算思維,要認識到放牧流動性的文化意義
把漫山遍野的牛羊看作一種經濟上的潛在收入,這種做法無法真正衡量畜牧業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流動性的本質。筆者在西藏阿里調查時發現,在放牧著的羊群中,其中有1/4—1/2屬于放生羊,這些羊被牧民終生供養,羊死后也不會帶來任何經濟收入,而是被放置在大自然中,任其消失。市場化思維無法給出這種行為的真正含義。此時,放牧行為似乎更是一種文化的產物并代表著一種文化義務。
Misginaw Tamirat 等人對埃塞俄比亞哈迪亞(Hadiya)牧牛生產系統從生產和銷售兩個方面進行的分析肯定了筆者假設的文化說。他們的研究發現:盡管仍有經濟因素的影響,但當地牧民大量地飼養牛并非為了防范風險,而是作為一種文化義務存在,并由此獲得文化頭銜[35]。因此,在文化系統里,畜牧生產以及流動性的存在代表著一種存在感和歸屬感,并非經濟范疇可以完全涵蓋的。
從牧業活動形成的流動性的覆蓋范圍以及畜牧業所在的地理區域來說,它們的背后是一種更大范圍的文化圈子。A.A.Degen 強調,通常情況下,畜牧社會是在極端的自然環境中的特定區域內飼養牲畜,這些區域一般無法通過耕種實現對土地的利用以及對人口生存的支撐,而且這些地方多處于國家和地區的偏遠或邊緣地帶[10]。此時,牧業活動的存在就意味著當地在文化上的歸屬范疇。從政治層面而言,牧業以及它具有的流動性就代表著一種國土主權的含義。
(四)流動的安全性,關注流動過程中的風險
流動性可以降低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土壤異化風險、人與野生動物關系失調風險、草場破壞風險,但同時它也會帶來一定的風險,譬如加劇人與野生動物沖突的風險。Tesfaye Fentaw 和Jatni Duba評估了埃塞俄比亞奧羅米亞州亞貝羅保護區的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沖突,認為放牧地管理的失控、對當地社區的侵占、保護區附近和保護區內的聚居居住模式、缺乏邊界劃分和分區以及保護區內的產品需求不斷增加等因素是造成亞貝羅保護區人與野生動物沖突的主要原因[36]。
流動性引發與加重疾病傳播的風險要明顯高于引發人與動物沖突的風險。Samuel Bawa 等人認為,游牧人口感染一些疾病的風險要比一般人口高得多,而且游牧人口流動被證明是疾病傳播的溫床,包括脊髓灰質炎。他們通過對尼日利亞及周邊牧民的跨境研究,主張改善人口免疫力和疾病監測[37]。
另外,包蟲病是牧區的多發病。汪瑞鷗對馬爾康市農牧區居民包蟲病防治知識和行為的調查發現,當地的防治知識合格率有待提高;健康教育的重點是青年人群、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及養狗人群;需重點干預喝生水、拴養犬、犬驅蟲及犬糞掩埋等行為方式[38]。在流動發生時,由于牧民隨牲畜在不同牧場之間遷移,喝生水、接觸犬及其糞便,以及其他感染風險被進一步提升。
(五)流動的可持續性,關注勞動力的緊缺問題
牧區人口外流導致牧區內從事牧業的勞動力人口數量減少。一般來說,受過較好教育并且具有較高學歷或者較好技能的勞動力受到城市生活方式以及就業機會的吸引較大,他們很少會返回牧區從事畜牧業。隨著牧區教育水平的提升,如果沒有適當的舉措,這種現象可能還要持續甚至進一步發展。沒有足夠的從事畜牧業的勞動力,牧業中的流動性將難以有效維持。
Veena Bhasin認為,在拉達克,官員和政策制定者并不重視牧民的基本需求,牧區的傳統習慣和相關權利面臨著被剝奪的風險,保護野生動物的工作是以犧牲牧民的草料為代價的,牧民社區在政治上被邊緣化,所有這些為他們被強行逐出土地和限制他們的行動鋪平了道路。由此,牧民群體勞動力短缺等社會危機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39]。
Claire Manoli 等人強調,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干旱土地上牧民來說,家畜的積累是他們賴以生存的主要手段,另外的重要手段就是多樣化以及長距離流動,而二者都需要一種特定的家族組織才可以實現。他們共選取了508個家庭研究了這兩個主要手段的組合以分析牧民的生計安全問題。研究發現:至少40%的被調查居民點是小牧區家庭,由一到兩戶的小牧群(少于50頭牛和50頭羊)組成。畜群是維持生計的主要手段,但由于缺乏足夠的勞動力和其他資產,這些貧困家庭的處境十分危險[40]。
四、結語與討論
牧區的流動性是重要的,但流動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牧民的生計、牧場的生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它們是無法分開的。這是牧區、牧民所具有的流動性的本質屬性所在,本文將其稱之為一種“牧區的生計與生態互構模式”。但是這一屬性往往在政策制定中被忽視。ByJohn G.McPeak 強調,當代非洲牧民的作用被各類機構、外部觀察者和政策制定者低估甚至誤解。牧區的政策往往是在假設和原型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充分的經驗基礎[41]。
牧民的能動性與政府管理之間需要有效互動,否則將無益于牧區發展,也無益于流動性的良性作用發揮。對文獻的梳理表明,無論牧區生態與生計的良性變動還是消極變化都與二者有著密切的關系。Yang Wang 等人對西藏牧民受氣候和全球變化影響的應對進行了分析,他主張流動性范式允許牧場的靈活使用,但重建大規模的流動模式是困難的,政府需要制定靈活的政策,協調和規范不同區域之間的遷移路徑,為牧民遷移牲畜提供現代化、便利的交通設施[42]。
進一步而言,只依靠傳統流動性機制以及其他地方性知識并無法為解決牧區和牧業在不斷變動著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中出現的新問題提供全部答案,有時甚至顯得蒼白無力。所以,把以流動性為主的傳統地方性知識與政府的積極作為相結合是一種必由之路。A.Kassahun等人對埃塞俄比亞畜牧業生產系統的研究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環境的退化和對草場資源的管理不善,那里的土地干旱和草場退化情況越發嚴重;出現了貧窮和赤貧家庭,中層以下的財富等級消失了,即意味著貧困隨著時間的推移增加了;由于環境和牧場退化加劇以及缺乏減少或解決這些問題的國家政策,那些傳統的應對機制正在失效[43]。
如何將二者有機結合促進牧區生態與生計的共同發展,深入的研究尚顯不足,但一些研究已有所涉及。Trinity S.Senda等人對埃塞俄比亞南部畜牧業土地進行的研究表明,當土地保留區的政策嵌入到牧區的習慣結構中時,成功的機會就會相應提高。該研究主張:由于存在多種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在這些地區實施的土地政策需要多管齊下并提供多種支持機制[44]。Anthony Egeru在分析東非的牧民面臨氣候變化壓力時,主張實施綜合預警系統,并有效結合牧民的看法和做法,將二者結合促進對氣候變化的應對[19]。這些為我們進一步開展關于二者的實踐對話以及它們有機結合的方式等相關研究提供了一些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