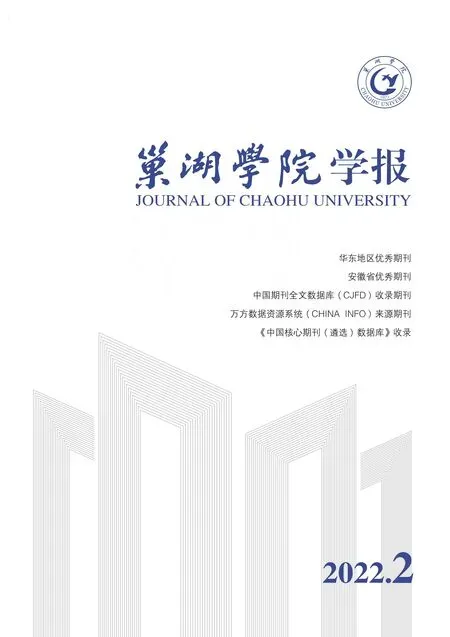跨媒介視域下藝術媒介之間的界限與相通
——以語詞和圖像為例
古 尚
(安徽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引言
“跨媒介”這一概念產生于二十世紀,但在古代東西方就已出現這種藝術現象,以及眾多古典文獻對這一現象的學理性描述。“詩舞樂一體”“詩畫同源”等包含跨媒介藝術思維的觀點在中國古典文論中隨處可見,正如《毛詩序》這樣描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詩歌、音樂和舞蹈采用不同的藝術媒介,但它們都是表達感情的藝術形式,所以在特定情況下可以相互融通。蘇軾認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亞里士多德從“摹仿”的角度指出詩歌與繪畫的同等地位,即它們都是對社會生活的摹仿,只是摹仿的媒介不同。賀拉斯也將詩歌與繪畫比作不可分割的“姊妹藝術”。應當指出的是,古代眾多學者雖然意識到這種跨媒介藝術現象,但沒有形成完善的跨媒介理論范式,也沒有從媒介的角度深究其中的原因,其學理性的認識較為淺薄。二十世紀以來,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媒介呈現出相互融合的現象,在跨媒介和跨學科的語境和藝術實踐下,對跨媒介藝術的理論研究呈現出二次增長的態勢。龍迪勇詳細探討了藝術中的跨媒介現象:“我們除了了解該作品本身的媒介特性之外,對于它‘跨’出自身媒介而追求的他種媒介的特性也必須有所了解;只有這樣,才能更好、更完整地欣賞其美學特色”[1]。周憲認為跨媒介性是藝術學理論研究的一種方法論,將藝術交互關系分為五種研究范式,即姊妹藝術研究、歷史考察模式、美學中的藝術類型學、美國比較文學的比較藝術或跨藝術研究以及最后的跨媒介研究。他還將藝術跨媒介性分為二分模態關系①單媒介的跨媒介性是在只存在一種單一媒介的藝術形式中模仿了其他藝術媒介的形態,如在元代文人畫中感受到的詩歌效果;多媒介的跨媒介性是指包含不止一種媒介的藝術形式中存在的跨媒介性,如電影、戲劇、舞蹈。,即單媒介作品的跨媒介性和多媒介作品的跨媒介性[2]。對于跨媒介性的模態關系,延斯·施洛特創造性地提出四分模態關系②綜合的跨媒介是指很多媒介融合為一種媒介的過程,好比電影藝術的媒介包含音樂、文學、繪畫等等的結合;形式的或超媒介的跨媒介性的含義是指這種模態表現為某些超媒介的特征,例如虛構性、節奏性、寫作策略、系列化等;轉化的跨媒介,也就是一種媒介以另一種媒介的形式來呈現,如法國系列短視頻《奇趣美術館》就是以短視頻的形式來介紹世界聞名的美術作品;而本體論的跨媒介性是認為無論每一種媒介的定義存在著怎樣的差異性,都存在著一種先天的媒介,也就是本體論的跨媒介性。,即綜合的跨媒介性、超媒介的跨媒介性、轉化的跨媒介性和本體論的跨媒介性[3]。拉耶夫斯基提出藝術跨媒介的三分模態關系③媒介轉換意義的跨媒介性是猶如文學改編的電影、音樂等現象;媒介融合意義上的跨媒介性是指電影、戲劇、圖畫書等含有多媒介的藝術形式;跨媒介意義上的跨媒介性則是一種藝術作品的創作含有對另一媒介的參考,如電影參考文學、音樂參考繪畫。,即媒介轉換意義的跨媒介性、媒介融合意義上的跨媒介性和跨媒介意義上的跨媒介性[4]。
在討論“跨媒介”這一概念之前,我們應有承認媒介特殊性的共識,即用以承載不同藝術形式的媒介材料有著自身獨特的表現方式和特殊的藝術效果,這是保持藝術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前提,但這并不代表它們是互相排斥或者存在不可滲透的隔閡,每一種表達媒介之間從來就沒有嚴格的界限。藝術的跨媒介性在于鼓勵各門類藝術的相互轉換與融通,超越自身媒介的表達限制,追求他種媒介的藝術效果。而筆者旨在以具體的語詞與圖像媒介為例,對不同藝術媒介之間的特殊性以及跨媒介性現象進行分析探討,這有利于打破傳統藝術學理論中因為對于藝術特殊性的重視而對藝術交互性的忽視,從而打通學科之間的壁壘,完善藝術學理論的嶄新建構,也為如今藝術理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語詞媒介與圖像媒介的界限
語詞與圖像是人類漫長歷史發展中具有表情達意功用的兩種基本媒介。語詞與圖像的關系源遠流長,它們不僅存在著一方向另一方藝術效果追求的渴望,甚至還包括兩者的配合與融合,同時相互對立和競爭的關系也包含其中,米歇爾將此稱之為一場“符號大戰”,而這場大戰雙方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它們自認為對人類文明、真理、精神最有影響力的符號媒介。語詞與圖像作為反映人類社會生活的媒介,既有著不同的特性,也包含相互模仿的現象,可以作為討論媒介特殊性與跨媒介性中最有代表性的兩種媒介。它們在理論研究范疇中既是指敘事中的不同表述方式,也是指作為承載信息內容的兩種符號在指代某物時的不同特征,其區分主要體現在敘事學和符號學中。
(一)語詞與圖像在敘事學中的差異
在人類還沒有發明文字之前,除了口語媒介,最重要的敘事媒介就是圖像,如果沒有相關圖像在遠古時期的創作,我們是無法對史前時期進行理解與認識的。對于圖像的記敘作用,魯迅這樣說道:“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洞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么悠閑,他畫一只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于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5]。而文字出現后,圖像對于敘事的主宰地位明顯受到了挑戰,甚至受到了文字的抑制,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在于文字與圖像在媒介特性中的區分。
語詞與圖像作為人類精神文明寫照的媒介,都承擔著敘事的責任,羅蘭·巴特認為用以承載敘事的媒介可以是一切物質材料,文字、口語、繪畫、聲音等媒介都是敘事的工具與手段。無法否認的是,文字與圖像仍然是敘事中的兩大主要媒介,但是自從文字產生之后,圖像在敘事中的主宰地位逐漸消落,文字在敘事中的天然優勢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肯定。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主要是這兩類藝術形式在敘事中所采用的不同媒介的特性導致的。萊辛將詩歌(文學)與繪畫分為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時間藝術適宜于敘述在時間中先后承續的情節,而空間藝術則適宜于描繪在空間中并列的物體。敘事的本質說得通俗一些其實就是講故事,而我們也無法反駁這是一件線性的時間性行為,而語詞不論是作用于視覺還是作用于聽覺,都必須在時間的流逝中完成,所以語詞作為一種時間性媒介且具備極佳的表情達意的功能,故在敘述故事時就變得無比輕松和自然,這與在空間中并列的靜態圖像媒介正好相反,空間性媒介只能創造出某一瞬間的靜態形象,無法像文字那般在時間的先后承續中去欣賞。他還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潘達洛斯把弓提起,調好弓弦,打開箭筒,挑選出一支沒有用過的裝好羽毛的箭,把它安在弦上,把弦帶箭拉緊,拉到弦貼近胸膛,弓嘩啦一聲彈回去,弦嗡了一聲箭就飛出去,很急速的飛向目標”[6]。潘達洛斯射箭的一連串動作是順著時間的順序一步步完成,所以這種持續的動作并不適合在空間藝術中表達,而是在時間藝術中去講述。由于圖像媒介材料的特性,它只能保持瞬間靜止的形態,我們無法了解在這一瞬間的前后情節究竟是怎樣的,當圖像作品呈現在我們面前時,它在敘事中是“失語”的,所以萊辛認為成功的繪畫應該描述出某一瞬間的頂點,即“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頃刻”,只有在這一頃刻,觀者才能最大程度地調動想象的自由性,填補原本在時間中失語的敘事關系,否則它就會淪為平淡和無趣。故在敘事的角度下,由于語詞媒介的特性,可以自然而然的在時間的先后承續中去講述一件事,而圖像作為一種空間性的媒介,只能在一定的空間中塑造在時間中凝結的形象,所以像繪畫、建筑、雕塑這種空間藝術在時間性的敘事活動中具有天然的劣勢。
(二)語詞與圖像在符號學中的差異
語詞媒介與圖像媒介不僅在敘事學中有著區分,在符號學的角度同樣存在不同,其中最根本的區分就是任意性和相似性的差別。索緒爾語言符號學中的“能指”與“所指”或許可以很好地解釋這種差異性。所謂“能指”是用以表示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語言符號,而語言符號所表示的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稱為“所指”,“所指”也就是“能指”中語言符號所要表達的意義,例如作為語言符號的“書籍”的詞語是“能指”,而作為具體對象的書籍是“書籍”這個語言符號的“所指”。文字作為一種抽象的符號其實就是皮爾斯所說的“象征”(一種任意的、約定俗成的符號),所以“能指”與“所指”的任意性就使語言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其指向作用相當準確。而米歇爾等將圖像定義為“某物的符號或象征,圖像與它所代表的東西在感官上具有相似性”[7]。也就是一副圖像的內容應該使觀者的感官認為與某物相似。但是圖像符號的意指作用并沒有語言符號那么精準,而是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我們可以將任意一個單詞或語句指代任意一件物品或者一個人,但是卻不能隨意的將一幅與某物相似的圖像準確地指代某物。例如有人說這幅圖像與太陽相似,又有人說它與向日葵相似,至于到底與什么相似,相似的程度有多少,一千個讀者自然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在符號學的角度,文字與圖像的差別就是任意、約定俗成的符號精準對應某個特定的具體事物與圖像符號所代表的東西具有相似性的差別,即任意性與相似性的差別。
二、跨媒介語境下的圖像與文字
每一種藝術形式都有其特定的表達媒介,它不僅是藝術外在呈現的物質載體,同樣也是構成藝術形式本身的符號體系,不同的表達媒介呈現出的美學效果和藝術意蘊也不盡相同。前文分析了圖像與文字在敘事學和符號學中的差異,更是證實了不同媒介在藝術表現中擁有不同的特性與優勢。不可否認,不同的藝術種類很大程度上受到它所使用和承載的表達媒介的限制,這是承認不同藝術形式具有差異性的基本前提。但是自二十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發展,在媒介融合的大環境下,跨媒介藝術逐漸成為藝術的主要形式,與這種藝術實踐相對應,跨媒介的藝術理論也應運而生。所以,一方面我們應對藝術媒介的特殊性與差異性有所認知;另一方面,打破學術之間的壁壘,以跨學科、跨媒介的視域重新看待傳統藝術理論和對于藝術媒介性的認知,也必須引起我們的關注。
(一)對于媒介多樣性以及跨媒介的理論認知
萊辛認為:“在空間中并列的符號就只宜于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空間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時間中先后承續的符號也就只宜于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時間中先后承續的事物”[6]。他的目的就是反對當時“詩畫相通”的主流美學觀點,指出混淆文本與形象之間界限的嚴重弊端,并提出“詩畫有別”的理論主張,也是從萊辛開始,詩畫正式劃分了邊界。藝術批評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說道:“在實踐中,這種美學鼓勵那些特殊的和一般的不誠實的藝術形式,它存在于這種企圖之中通過躲藏在另一種藝術的效果之中來逃避一種藝術的媒介問題;繪畫和雕塑在稍遜天賦的藝術家手中,不過成為文學的代筆和‘傀儡’。要還原一門藝術的身份就必須強調其媒介的不透明性”[8]。格林伯格是極力反對繪畫中含有文學的詩意的,他認為要追求一門藝術不可還原的本質,就應該摒棄其他藝術門類所帶來的藝術效果,避免其他表達媒介的參與,這種“不可還原的本質”是建立在媒介自身的特殊性與純粹性上的。按照萊辛和格林伯格的觀點,藝術中各個表達媒介之間可謂涇渭分明,壁壘森嚴,藝術變得越來越多元化,各個藝術門類之間產生一定的對抗性。我們相信,亞里士多德和萊辛以及格林伯格對已確立價值的媒介多樣性的研究具有根本的意義,也必須在基于他們觀點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展開對跨媒介藝術理論的研究。但是各門類藝術其實從一開始就沒有被明顯的區分過,它們非常容易就能夠相互融合。如果將身體作為一種鑒賞藝術的媒介,那么各個感官媒介都是密切相關的。錢鍾書認為:“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個官能的領域可以不分界限”[9]。正如米歇爾認為圖像與它所代表的東西在感官上具有相似性,其定義并不是僅視覺感官能夠滿足,其他非視覺感官也同樣滿足其圖像的基本定義,作用于視覺媒介的作品也同樣作用于聽覺和觸覺甚至嗅覺,當感官互相滲透或者融為一體時,我們就很容易在各門類藝術中找出共通性,不僅是文學與圖像,包括音樂、建筑,舞蹈等等藝術品類中,都能感受到這種藝術魅力。
“跨媒介”這一詞語最早可追溯至1812年柯勒律治在文學實踐中的運用,德國美學稱其為“出位之思”,即一種表達媒介在保持自身媒介特殊性所展現出的美學特色的同時,試圖跳出“本位”,不安分地追求另一種表達媒介的美學效果。另外,“跨媒介”并不是說轉變成為其他媒介,也并不是兩種或多種媒介的融合,這種情況并不在此次討論范圍內,而是一種表達媒介跨出自己的專業領域,追求另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的特征,其媒介本體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是在保持自身媒介特性的前提下,再“不知足”地去追求他種媒介的特有的藝術效果。中國書法作為我國獨有的一種造型藝術,其中就包含著對音樂藝術的跨媒介現象,不僅僅是承載語言內容的符號形式,更是一種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象征,是藝術家情感的表現,是像中國畫中“情景交融”的意境美。藝術家通過用筆的緩急、結構的疏密以及點墨的輕重來表達他對書法形象的感情以及意境的抒發,而這與音樂藝術的表達方式不謀而合,音樂就是用節奏、音調、旋律在時間的進程中表達藝術家豐滿的情感,所以我們能夠從書法藝術中感受到一種流動的音樂美,仿佛從書法形象里聽到自然界發出的美妙樂音。所以,書法作為造型藝術門類中的一員,其形式美是在空間中來概括的,而其中又蘊含著作為時間性特征的音樂美,兩者呈現出相通的現象,但是書法藝術的媒介并沒有轉換成音樂媒介,在同一種藝術形式中也沒有出現這兩種媒介的結合,而是書法藝術在保持自身媒介特征的同時,再來追求音樂美的藝術表現力。錢鍾書提到對藝術的跨媒介現象:“一切藝術,要用材料作為表現的媒介。材料固有的性質,一方面可資利用,給表現以便宜,而同時也發生障礙,予表現以限制。于是藝術家總想超過這種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縛,強使材料去表現它性質所不容許表現的境界”[10]。一件成功的藝術品之所以成功,也是因為它可以與其他門類的藝術相互轉換,而這種轉換恰恰具有某種不可思議的魅力。所以,在保持媒介自身“本位”特征的同時,通過對藝術自身界限的突破,并與各門類藝術之間的相互融通,從而獲得自身媒介所不具備的藝術力量,以新的眼光來重新創作和欣賞藝術,也正是出位之思的初衷所在。
(二)圖像向文字的跨媒介
藝術的跨媒介傾向主要體現在時間藝術與時間藝術之間(文學與音樂)、空間藝術與空間藝術之間(雕塑與繪畫)以及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之間(語詞與圖像),而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之間包含了最為重要的跨媒介藝術。首要探討空間藝術向時間藝術的跨媒介傾向。這種特殊的美學現象在中外藝術史中自古有之,唐宋時期在詩歌與繪畫之間的關系上就體現出跨媒介的思維傾向,蘇軾說:“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繪畫屬于造型藝術,是采用特定的物質媒介材料以美的規律和法則在一定的空間中塑造靜態的美術形象,不論是繪畫還是雕塑,由于其直觀和形象的媒介特性,一直以來都是作為再現藝術的典范,正如陸機所言:“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畫。”可中國的文人畫家偏不以畫寫實,而是借助繪畫表達自己豐富的思想感情,直抒胸臆,好比倪瓚所說:“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可見,繪畫作為一種再現寫實的藝術形式,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卻可以不受繪畫媒介特性的影響,反而去追求文學中詩意的效果,這本身就是一種藝術中的跨媒介。除此之外,繪畫作為一種靜態的空間藝術,也能夠表達出像詩歌一樣的表征時間性的藝術效果,米歇爾等對在圖像中所顯示的時間性有著深刻的論述:“我們與任何圖像的相遇,某種形式的時間性都嵌入其中”[7]。這種圖像中的時間性包含很多方面,例如圖像的創作時期和產生日期、繪畫中包含的歷史性或者在欣賞圖像時流逝的實際的時間和腦海中留存的記憶片段。圖像是某物的符號或者象征,它與所代表的事物必須具有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與人腦中的記憶密切相關,一幅圖像能否被認為與某物相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欣賞者以往的社會實踐和生活經歷,圖像包含的內容必須喚起他記憶中的某個角落。龍迪勇強調:“記憶是一個心理學范疇,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架在時間與敘事之間的橋梁”[11]。所以圖像存在于人腦記憶中的方式并不是定格的,而是“移動著的圖像”,是在一定時間中流淌的片段,若將記憶當作一種媒介,那么圖像與詩歌、音樂、文學一樣構成記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沃爾特·佩特對喬爾喬內“繪畫詩”有著感人至深的描述:
它部分是戲劇詩的最高品類的理想狀態,它向我們表達了一種意味深長的意義和栩栩如生的片刻,它僅僅是一種姿勢、一種表情、一個微笑,或許是一些短暫但絕對具體的瞬間,但是,一長段歷史的所有動因、所有趣味和所有的結果,全將自己濃縮于其中了,而且它也似乎將過去和未來全都融入了強烈和可感的現在。[12]
從這段話中,我們竟然能在喬爾喬內筆下感受到時間的流逝,體會到歷史的變遷。喬爾喬內的高超之處來源于對主題對象的選擇,其目的不是宗教之需,也不是教化之用,而是畫一群男男女女的實際生活片段,他們或是談話亦或是奏樂,仿佛在畫中感受到了音樂的狀態以及一種寧靜恬美卻激動人心的詩意,這也是為什么喬爾喬內的繪畫能夠成為戲劇詩所追求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繪畫作為定格在瞬間的空間藝術形式,在一些美術家例如喬爾喬內筆下卻能夠體現出其中所包含時間的流逝,也就是繪畫藝術向文學藝術的跨媒介。
(三)文字向圖像的跨媒介
除了在作為空間藝術的圖像中能夠表現出文學詩歌般表征時間性的藝術效果之外,我們也經常能夠感受到作為時間藝術的文字追求某種造型藝術的視覺效果。文學的表達媒介是語言和文字,實質上是在時間的進程中用來表情達意的,可詩人卻能夠突破語詞媒介的局限給予讀者一種獨特的空間效果,跳出語詞媒介的“本位”,轉而去追求圖像的美學效果,這同樣也是另一種跨媒介的表現。語詞媒介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義性和模糊性,以及讀者基于文本所展開的無限自由的想象性,這種模糊和暗示正是文學饋贈給讀者最好的禮物。而在二十世紀現代藝術中,卻能夠將語言視為聽覺媒介甚至視覺媒介,幾乎消除掉單詞語義的暗示性。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達達主義的創始人特里斯坦·查拉擅長將單詞和語句進行隨意地“裁剪”“拼貼”,在他眼里,“拿份報紙,剪下單詞,打亂順序再重新拼貼,那便是超越粗俗的原創。”達達主義打破了語詞固定在書本中的排版形式,主張無意義無規則地拼貼,并賦予單詞物質形態和視覺效果。同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具象詩”運動認為詩歌的視覺元素與文本元素同等重要,“具象詩”又被稱為“視覺詩”或“圖案有形詩”,是指以語言作為對象,可以自由地組織與解讀其中意義,并非一仍舊貫按照語言符號所代指的意義去理解,而是通過空間位置、圖像、字體符號以及單詞之間的感受來解讀作品的意義。所以,通過對文字的排版使其具有既定的視覺效果,將文字變成詩歌本身的一部分,而非僅僅是承載語義內容的媒介形式,這正是“具象詩”的思想所在,也是文字向圖像跨媒介的重要體現。
應當說明的是,以上達達主義和“具象詩”以及類似的藝術現象是通過特定的方式清空語義內容,將傳統文學中透明的語言賦予物質性,文字在其中不再是在時間維度上傳達思想內容的媒介載體,而是將單詞語句經過藝術家的加工處理給觀者一種空間上的視覺形態,這是作為時間藝術的語言文學呈現出視覺圖像效果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文字在不改變物質形態的前提下,既保持語詞媒介的美學特征,又可以突破語詞這種媒介材料的束縛,去追求空間性的視覺效果,這種視覺效果并不是通過作為肉體器官的眼睛,而是腦海中的“眼睛”來呈現。這種美學現象稱為“藝格敷詞”,即“以文述圖”,是指對藝術作品進行形象、生動的描述的寫作手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一種修辭學傳統,它在古希臘語中的含義是“充分講述”或“說出”,是古希臘城邦中法庭起訴和在議會大廳及其集會演講時所使用的一種語言技巧,演講者通過文字或者口語的方式使聽眾通過想象感受到一種逼真、形象的視覺圖像效果。“藝格敷詞”成為西方的一種文學體裁最早出現于《伊利亞特》中對阿喀琉斯的盾牌的描述,文藝復興時期瓦薩里將其發揚光大,十九世紀初期詩人濟慈的《希臘古甕頌》被奉為“藝格敷詞”的經典之作,直到現在依舊是當代文學理論以及藝術學理論關注的重要領域。喬爾喬內的繪畫具有一種浪漫的詩意,而詩歌和文學同樣能夠表現出視覺藝術的特征,詩人以畫家的角度利用文字再現繪畫的藝術特質如構圖、色彩、韻律、動感,使讀者雖處身外,卻宛若置身其中并浮想聯翩。這種奇妙的藝術現象正是來源于詩人和作家對于傳統寫作技巧和規律的突破和革新,使屬于時間性媒介的語詞呈現出屬于空間性媒介的圖像的美學效果,而這正是語詞向圖像的跨媒介。
三、結語
綜上,諸多藝術媒介如語詞與圖像在跨媒介的獨特視角下表現為在保持本質媒介不變的同時,追求異質媒介包含的美學特色或者與之結合,產生一種嶄新的、令人贊嘆不已的藝術意蘊,表現出單一媒介無法表現出的藝術內涵,好比語詞在一些創造性的作家筆下主動地去表現繪畫甚至雕塑的空間效果,而在一些美術家筆下的繪畫形象中也能感受到猶如詩歌般的時間性以及音樂般的狀態。兩種媒介的相互結合并不是對彼此的侵犯,而是對自身的突破與超越,正如麥克盧漢所說:“兩種媒介雜交或交會的時刻,是發現真相和給人啟示的時刻,由此而產生的新的媒介形式”[13]。兩種媒介結合時,能夠孕育和產生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在很多具有“出位之思”的獨創性的作家或藝術家的手中,我們都能通過欣賞他們的藝術作品感受到這種不可思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