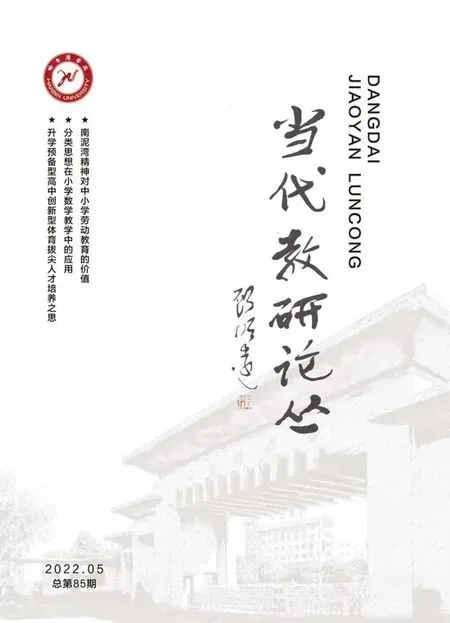符號互動理論視域下課堂師生互動探析
王 琳,李雙龍
(喀什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新疆 喀什 844099)
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教育現代化加快推進的背景下,教育的主要目標不再局限于僅僅促進學生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發展以及情緒情感發展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提高教育發展的質量,培養高素質高質量發展的人才,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對高質量人才的需求。201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要求強化課堂主陣地,切實提高課堂教學質量;要求注重啟發式、互動式、探究式教學,教師課前要指導學生做好預習,課上要講清重點難點、知識體系,引導學生主動思考、積極提問、自主探究。[1]課堂師生互動交往方式改變了教師灌輸式的傳統教育,更加注重師生雙主體的相互作用,共同發展,共同提高。課堂師生互動的加強是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培養學生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打造教師與學生雙主體課堂、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培養高質量人才的重要場域。
一、符號互動理論核心觀點
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治·米德對符號互動理論進行了系統闡述,其學生布魯默正式提出符號互動理論這一概念。米德被一致認為是符號互動理論的鼻祖,關于符號互動理論的主要觀點集中體現在其著作《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中。符號互動理論主要研究微觀層面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往行為及其在互動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生活。符號是人與人交往的中介,符號的意義是通過人們之間的互動形成的,在此交往過程中形成了“主我”與“客我”,使人在與社會交互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社會化的人。課堂師生互動也是人與人,即教師與學生之間借助教材等符號媒介,通過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交流促使學生個體社會化的過程。在教師與學生課堂互動過程中,雙方互動交流的信息等自我言語行為形成“客我”,在“主體我”與“客體我”相互作用過程中,學生“自我”逐漸完善,個體社會化行為顯著增強。
1.表意的符號是人際溝通和思維發展的橋梁
符號互動理論認為符號是認識世界、認識他人的工具,其存在于人們日常生活中,是社會形成和發展的基礎。符號具有多種表征形式,包含言語符號和非言語符號,如語言、姿勢、動作、眼神、表情以及文本材料等都屬于符號的范疇。符號是符號互動理論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符號互動理論認識和闡釋世界的重要工具。符號的功能多樣:第一,符號可以指認事物的特征,描述其外部與內部特征,對事物進行全面整體的簡要介紹,利于我們更好的快速辨認事物;第二,符號為人際溝通提供了橋梁,符號的表達為我們與他人、社會、世界互動提供了橋梁紐帶;第三,符號是自我形成的前提,運用符號與他人交際的過程是認識他人、認識自我的過程,是形成“主體我”與“客體我”的表現。正是在這一人際表達中,自我逐步形成發展起來。“符號是一種被賦予意義的感知,一個符號所具備的可以被其他的符號解釋的潛力稱之為意義。”[2]符號的意義的認識和實現借助于“解釋”這一表征,通過解釋,主客體對符號有共同的意義理解,使對主客體具有共同意義的符號轉化為表意的符號提供了可能。[2]“當有聲的姿態對作出這一姿態的人產生它對其對象亦即明確對它作出反應的人所具有的同樣影響,并因而涉及作出這一姿態的那個個體的自我時,它便成了一種表意的符號。”[3]“只有憑借表意的符號,心靈和智能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只有憑借表意的符號,思維才可以發展,思維是個體借助這些表意的姿態與自己進行的內在化的隱含性的會話。”[3]
2.互動是意義傳遞與自我形成的基礎
互動存在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世界的關系中。互動發生的過程依賴語言和符號進行。互動的發生具有多層意思:第一,互動的主體必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才能構成,單個主體不能實施互動;第二,互動的發生必須依賴一定的互動媒介,語言、動作、姿勢等都是符號產生的媒介形式;第三,互動雙方必須具有依賴關系,相互獨立,毫無關聯不可能進行互動;第四,互動的過程既是互動雙方自我構建的過程,也是互動主體自我內部構建的過程,外部顯性的雙方互動也促進了內部隱性的主體內部自我的會話;第五,互動發生的情景也是影響互動內容及表現形式的重要因素。符號互動理論關于互動的研究是從社會學視角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互動領域由個人場域擴展到社會場域甚至更大的研究場域。米德的互動理論避免了唯心主義的缺陷,強調互動的意義是個人與他人、社會的交流交往過程,是由個人與外部事物共同交流交往,既不取決于個體也不取決于客觀事物。事物的意義是在互動過程中主客觀因素共同相互作用的。
3.社會情境是心靈、自我與互動持續進行的依托
布魯默指出,“社會生活是人們的行動組成的。而這些行動是發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或與一定的情境有關的,他們是因為對情境的解釋產生的,是由確定那些必須加以說明的事物的意義,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所決定的。”[4]米德指出,“心靈是他(某人)根據出現的不同刺激把握住這些不同反應的可能性,正是把握住這些不同反應的可能性構成了他的心靈。”[3]他進一步指出,“只有當社會過程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或者說出現在該過程所涉及的任何一個特點個體的經驗之中時,心靈才能在該過程中產生。”[3]“自我是逐步發展的;它并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經驗與活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即是作為個體與那整個過程的關系及與該過程中其他個體的關系的結果發展起來的。”[3]“自我個人作為可以成為其自身對象的自我,產生于社會經驗之中。”[3]“自我是在它所由產生的社會情境中實現的;當某人使自己順應于某個環境時,他成為另一個個體,但是在成為另一個個體時,他影響了他所生活的共同體。”[3]
二、符號互動理論應用于課堂師生互動的適切性
符號互動理論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獨立存在的理論體系,其既包含庫利、托馬斯等人提出的先前理論的積淀,又有布魯默、戈夫曼、貝克爾等人對符號互動理論的延伸發展。符號互動理論是一個內涵豐富、極具深度與廣度的研究微觀領域人際互動、社會互動的社會學理論。
1.人物符號與師生互動
師生互動行為是指教師與學生以教育為中心所形成的各種依賴性行為的總稱。師生課堂互動行為是指教師與學生在班級課堂環境下進行的以教學為主的活動,是班級層面的社會互動,是師生雙主體通過課堂教學活動所表現出來的一系列相互依賴的行為過程。[5]課堂師生互動是師生雙方運用符號等進行知識、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塑造的過程,教師和學生是這一互動過程的人物符號。
2.內容符號與師生互動
課堂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教師與學生運用一切語言與非語言行為進行互動,教師與學生的語言、姿態、表情、動作、眼神、共同使用的教材文本等都是二者之間互動的內容。師生互動是師生雙方交往了解彼此的過程,互動的發生必須憑借一定的互動內容,沒有互動內容的互動雙方無法交往、無法了解,這樣的互動稱不上互動,互動也就不能發生。
3.意義符號與師生互動
托馬斯的“情境定義”為師生一致認同了解互動內容進行了闡釋,其為符號互動理論作出了貢獻。托馬斯“情境定義”主要思想觀點有:在環境與反應之間不是簡單的刺激—反應行為,在刺激與反應之間有一個情境定義的過程,該情境定義是對環境刺激進行解釋的過程。只有互動雙方對情境定義有一致的認同,對情境意義有一致的理解,此時的互動才是有意義的。課堂師生互動中的“情境定義”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課堂師生互動中,教材文本、外部內部環境、語言姿態都會被教師和學生進行解讀,構成了師生互動的基礎。但是這些內容符號只有被教師和學生賦予同樣的意義,教師和學生才會對其有共同的認知、認可、認同。只有對這些內容符號有共同的理解,才能實現師生之間的良性和諧的互動。
4.環境符號與師生互動
課堂師生互動是教師和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意義理解、價值追尋的過程。課堂中的桌椅擺放、教室裝飾、教師與學生的精神面貌、衛生打掃程度等,都屬于課堂師生互動中的環境符號。其中最值得重視同時又是最有可能忽略的是課堂師生互動中的教師與學生的精神風貌和課堂表現,戈夫曼(布魯默的學生)的戲劇理論為我們對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將戲劇比擬引入社會學分析,運用戲劇舞臺的特有意向來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戈夫曼把社會看作是一直在演出的戲劇舞臺,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生活舞臺上的演員,自我是社會情境的產物。戈夫曼戲劇互動理論的主題是“印象管理”,即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塑造一個自己所希望的印象,或者說當人們觀察他們時,他們應如何表現自己。[6]戈夫曼認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個舞臺,每個人都想要在舞臺上盡力表現自己,盡力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而隱藏自己的另一面。戈夫曼強調的是運用符號進行角色扮演,相比于布魯默,他更強調如何運用符號更好地實現人與人的互動。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上的互動表現也是戲劇理論的重要表征。課堂就好比一個舞臺,教師在課堂外進行備課,在課堂上竭力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竭力給學生留下美好的印象;學生在課堂上同樣展示自己最想被老師了解的一面,努力表現自己的良好形象,盡力給老師留下美好的印象。
5.“自我”與師生互動
“自我”是包含“主我”與“客我”的同一體。課堂師生互動既是教師主體與學生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同時也是教師自我,即教師內部隱性的“主體我”與“客體我”的互動,也是學生自我,即學生內部隱性“主體我”與“客體我”互動的過程。查爾斯·霍頓·庫利是美國較早期的社會學家,他提出了“鏡中我”理論,認為一個人的自我是在與他人交流交往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形成了個人對自我的認識,他人是自己的一面鏡子,個人可以通過他人了解自我。庫利強調主觀的內在心理上的互動,認為個人的心理特征、性格等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與他人互動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在課堂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交往中,會由于對方對自己的態度情感表現形成自身對自我的認識與反思。課堂師生互動最明顯的外部表現是教師和學生以一定的語言、動作、姿勢等為中介進行互動交往。在師生互動交往中,教師(學生)與學生(教師)由于與對方的交往,從對方對自己的態度、行為過程中也不斷反思自己,從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行為特征,從他人身上了解自己并且不斷調適自己與社會的要求相吻合,這就是自我發展的過程,更是個體適應社會、個體社會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