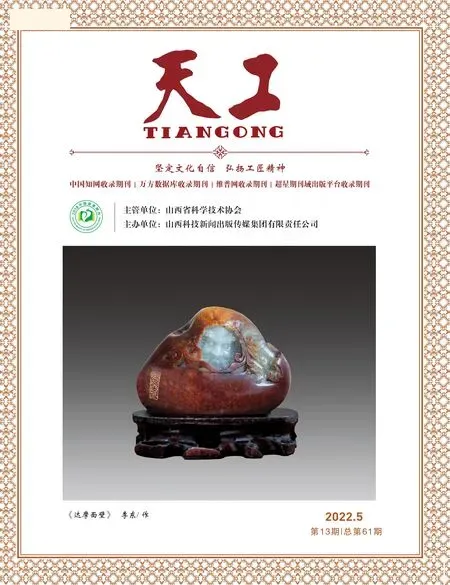徽州工匠文化及其特征探析
費利君 王小榮
1.安徽工程大學藝術學院 2.池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長期以來,在對徽學的研究中,對徽商文化的研究頗豐,徽匠文化則較少被關注。這一方面是因為徽商在明清創造了輝煌業績,其影響遍及海內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工匠職業身份低下,關于他們的資料記載不僅少而且散,甚至根本就沒有專門的文字記錄,研究難度大。但徽州工匠文化成就了藝術的徽州、視覺的徽州,是徽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傳統文化復興和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加強對徽州工匠文化的研究,對發揚和傳播徽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工匠文化概述
在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社會背景下,因政府的大力倡導,“弘揚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已成為社會熱點。但媒體報道更多聚焦于“工匠精神”,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工匠文化”。殊不知,工匠文化是工匠精神形成的沃土,沒有工匠文化的滋養,就不可能有工匠精神的形成。
工匠,亦稱“百工”“匠人”等,“工”對應的是工藝,“匠”是一種職業身份,引申為掌握專門技術的工人。工匠文化是工匠群體在勞動和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形成的一種造物的習慣、傾向和做法,它超越了物質層面而成為文化的一部分。
目前,學界對“工匠文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對中華工匠文化體系的研究。中華工匠文化綿延幾千年,從先秦至今,歷代工匠不僅創造了輝煌的器物文明,而且有眾多的智者將造物之事總結為規律,撰寫成書,流傳于世,像《考工記》《天工開物》《營造法式》等。這方面以近年來鄒其昌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工匠文化體系及其傳承創新研究”和潘天波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華工匠制度體系及其影響研究”為代表。其次是對“工匠文化”的現代解讀。智能時代的工匠文化,自然有別于手工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內涵,它有著新時代的新要求、新特點和新氣息。
二、徽州工匠文化及其研究價值
徽州處于江南一隅,因自然環境的獨特、人文環境的古樸和儒商文化的發達等,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徽學也被譽為中國三大地方顯學之一。它不僅包括以文書契約、典籍文獻和宗族族譜為代表的大量的文字資料,而且遺留的地面文物從民居、祠堂、牌坊、廟宇、書院到文房四寶、徽州雕刻、刻書版畫等也極其豐富。正是這些大量的地面文物營造了徽州的文化氛圍,造就了徽州藝術殿堂的光環。徽州傳統造物領域的成就,是徽州工匠群體直接創造的結果,是徽州工匠文化滋養的結晶。
今天,發掘和梳理徽州工匠文化,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有利于豐富和發揚徽文化。徽州工匠文化孕育于徽文化的肥沃土壤,可以說它是徽文化在造物領域的特色體現,是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文化發展的實踐看,工匠文化是現代文創發展的源頭活水,對現代文創產業發展具有極高的參照價值,特別是徽州工匠文化培育了眾多知名品牌,這對安徽現代文創產業發展具有啟發意義。
三、徽州工匠文化的形成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工匠群體會形成不同的工匠文化。徽州工匠文化的形成有著豐沃的土壤,是徽州區域自然、人文、商業生態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徽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是徽州工匠文化形成的前提。一方面,徽州自然物產資源豐富,有著大量的木、竹、石、漆等物產資源,為徽墨、歙硯、徽紙、木雕、石雕、磚雕、竹雕、刻書、漆器等工藝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原料的保障。另一方面,徽州被萬山環繞,山清水碧,形成了相對閉塞的自然環境,對外人而言雖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但在當地卻存在著農耕條件較差、人地關系緊張的問題,特別是歷史上因為中原大量移民的遷入,這種山多地少人眾的矛盾自明代以來就很突出,為了求生存,徽州先民不得不從農耕之外尋找出路,于是形成了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的生存路徑選擇。“執技藝”培養了徽匠,外出經商成就了徽商,正如鮑義來認為的:“徽州工藝和徽商都是被徽州這一惡劣環境逼出來的。”[1]可以說,徽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為徽州工匠文化的形成準備了物與人的條件。
其次,徽州崇學的人文環境為徽州工匠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智力支持。徽州自漢代以來,經歷了中原士族為逃避戰亂而發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遷入,中原士族的遷徽,既傳播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農耕技術,也帶來了中原崇儒尚文的傳統,使徽州文化環境自宋以來發生了質的變化,形成了徽州“聚族而居”和“崇儒尚文”的典型特征,呈現出私塾發達、社學林立、書院眾多的重教興文盛況,不僅衣冠士族重涵養,而且普通村民也都有讀書識字的機會,形成了“雖十家村落,亦有諷誦之聲”的濃厚氛圍。所以,徽州工匠群體整體上表現出較高的文化素質。特別是明中葉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新儒學提倡“四民異業而同道”,傳統“士農工商”的四民觀發生了動搖,社會對工匠工作的認可度得到提升。在這種環境下,有大量文人直接參與徽州各類工藝特別是文化類工藝的構思或制作,使徽州工藝多了一份文心,少了一點匠氣,無形中也增加了徽州工匠文化的深度和厚度。
再次,徽州發達的商業環境為徽州工匠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財力支持。明清時期徽商把握商機稱雄商界三百余年,他們沿著長江和運河在全國創造了“無徽不成鎮”的輝煌局面。因商致富的徽商將大量財富回饋故土,興學校、建祠堂、造宅所、辦書院,為工匠階層提供了大量的創作機會,為明清徽州的鼎盛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四、徽州工匠文化的特征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徽州豐沃的土壤既成就了徽商在明清時期的輝煌,也養育了徽匠。徽州匠人在這一方水土中,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憑借吃苦耐勞的精神創造出一個藝術的徽州,形成了極具地域特色的工匠文化。
(一)徽駱駝精神
胡適先生稱徽州人為“徽駱駝”,形容徽州人具有勤勞、堅韌、進取的精神品格。徽州人的這種品格源于遷徽的中原士族。他們在新的生存環境中,敢于直面原先優越文化感的喪失和當地農業生態環境惡劣的雙重困境,依靠自己的吃苦耐勞、堅韌不拔和開拓進取創造出了新天地。這種精神在徽商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大凡從商者要流離他鄉,含辛茹苦,經受精神和肉體的種種磨煉”[2],這已廣為人知;徽州匠人面臨著與徽州商人同樣的生存壓力,他們不能在土地中求生存,所以選擇了除商人外出經商之外的另一種匠人生存策略——“執技藝”。他們吃苦耐勞,依靠自己的手工技藝勤儉持家;他們堅韌不拔,對待技藝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正如鄭振鐸形容徽州版畫刻工時所說的“他們絕不出之于輕心”“他們絕不茍簡潦草”“一律的以全力赴之”[3]。他們開拓進取,將形而下的造物與形而上的文化融會貫通,創造出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文化徽州,使徽州成為藝術的殿堂。
(二)崇德
在對待造物的傾向上,徽州工匠文化表現出濃濃的文化味,崇德向善,雅而不俗。由于徽州地區崇文重教,文風昌盛,徽匠大多具備較好的文化修養基礎;同時作為業主的徽商賈而好儒,偏好儒雅,富有書卷氣,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徽州造物的氣質。所以,徽州工匠群體在造物的傾向上,特別是在文化類工藝的創造上,如建筑裝飾上的圖案、刻書上的插圖、民間的年畫、墨模上的圖案等,往往會運用各種技藝去表現儒家崇德向善的理念,這既滿足了徽商好儒或附庸風雅之喜好,也使自己從物質世界中跳脫出來,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從而使徽匠群體整體上表現出“儒匠”的氣質,也使徽州工藝整體呈現出“崇德”的特征,可以說“徽州幾乎所有的工藝形式都是圍繞儒家理念這個主旋律展開”。正因為徽州工匠文化的這種崇德特征,使其所造之物都烙上了濃濃的文化味,今人置身徽州仍有著強烈的情感歸屬,正如單德啟在感受徽派建筑時所說:“當你走到徽州聚落里,可以感受到情的氛圍:鄉土情、家族情、同胞情、民族情,從而激發一種歸屬感,一種真善美的頓悟,一種從這種頓悟中獲得了對自己、對同胞、對社會、對民族生存和發展本質的體驗。”[4]
(三)尚拙
在對待與自然的關系上,徽州工匠在與山水的相處中養成了尊重自然和巧法自然的習慣,徽州工匠文化整體表現出“尚拙”的特征。拙,與“巧”相對,既是不巧,要避人工痕跡;又是大巧,要法天工,不做作,自然而然。這種避人工、法天工的造物傾向,用明代計成的話說就是“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像徽州古村落,大多依山傍水,隨形就勢,負陰抱陽,形成了“枕山、環水、面屏”[5]的特征。古村落中的民居,粉墻黛瓦,淡雅質樸,與自然融為一體。像徽州歙硯,雕工雕刻時往往順應硯石本身的輪廓和紋理,因石構圖,因材施藝。像徽州盆景,在風格上以蒼古奇特見長,獨具自然神韻。徽州工匠文化整體上表現出的這樣一種避人工、法天工的特征,有著文化的淵源和現實的需要。從文化的淵源來看,中原士族的移住徽州,雖然是從原先的中原文化中心來到了深山窮谷間,但徽州這片山靈水秀、風景迤邐、美得如詩似畫的桃源,也讓他們在與自然山水的相處中有了精神的寄托,可以體會魏晉玄學“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味道,從而頤養自己自然的性情。從現實的需要看,明清時期徽州商人發揚徽駱駝精神,把握時機,奮發進取,積攢了巨額財富,在全國創造了“無徽不成鎮”的輝煌。他們回歸故里,光宗耀祖,建設家鄉,看慣了商海沉浮、世事冷暖的他們,崇尚自然、返璞歸真的思想更能契合他們的心境。
(四)精品意識
徽州雖然自然生態環境優越,但山多地少人眾的矛盾也造成了徽民生存環境的惡劣。徽州工匠在這樣一種生存環境中,唯有勤勞刻苦,利用當地豐富的物產資源、人文資源和商業資源,充分發揮聰明才智,憑借自己的手工技藝創造出最優良的物品,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徽州工匠這樣一種化劣勢為優勢、敢于拼搏、敢爭第一、爭做精品的意識,使徽州工藝在眾多領域大放異彩。徽州的文房四寶,徽筆是新安四寶之一,也曾是進貢之物;徽墨有“天下墨業在徽州”的輝煌;徽紙因質量好在唐代就被定為貢紙;歙硯有“天下第一硯”的美稱,它們歷來被人們視為藝術珍品。徽州的雕刻,以木雕、石雕、磚雕和竹雕著稱,既裝飾著建筑,美化了生活,也給世人呈現出一個崇德向善、栩栩如生的精神世界,至今仍令人嘆為觀止。徽州的刻書,因歙人刻工技藝精細,形成了“凡有插圖必請歙工”的品牌口碑。徽州的漆藝,聞名遐邇,漆匠技藝之精良可與皇宮官作媲美,我國最早的一部髹漆領域的專著《髹漆錄》就是徽州人黃成所撰。徽州工匠文化中的這樣一種精品意識,使眾多工匠在當地脫穎而出,涌現出一批知名工匠,形成了品牌效應,像制墨業中的南唐李廷珪、明代程君房和方于魯、清代胡開文等,硯雕高手唐代汪少微,漆匠明代黃成,張小泉剪刀等等。據余同元整理的《中國歷代名工匠統計總表》中的數據,明清時期中國工藝名家及工匠共1530人,徽州府有154人[6],占十分之一強,由此可見徽州知名工匠群體的龐大。正是由于工匠群體的這樣一種精品意識,徽州工藝在滿足當地自給自足之外,還有一部分是為滿足市場需求而發展成一種富有特色的區域經濟和支柱產業,從而形成了這一地區的文化產業。
五、結語
徽州工匠憑借自身的吃苦耐勞和開拓進取精神,在與徽商、文人等的互動中,把握機會,活用資源,敢于競爭,創造出了一個藝術的徽州,形成了極富地方特色的工匠文化。今天在傳統文化復興、文旅融合和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徽州乃至安徽文創產業,我們要繼承和弘揚徽州工匠精神,厚植徽州工匠文化,利用好自然資源、人力資源、文化資源和旅游資源,用過去的“工匠文化”成就今天的“文創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