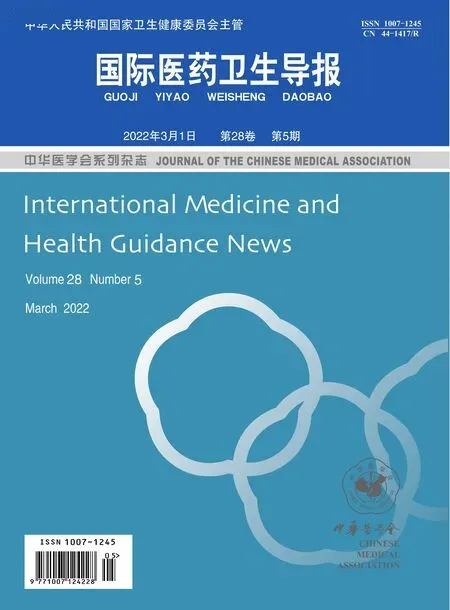漿膜型嗜酸粒細胞性胃腸炎伴胸腹水1例
顏萬勝 葉剛
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消化內科,廣州 510630
嗜酸粒細胞性胃腸炎(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tis,EG)是一類相對少見的炎癥性疾病,其特征為嗜酸性粒細胞(eosinophils,EOS)局限或彌漫性異常浸潤在胃腸壁任何位置,可伴有或不伴有外周血中EOS的增多。EG常以消化道癥狀為主要臨床表現起病,其癥狀多樣,無特異性,容易造成漏診、誤診。根據Klein分型,EG可分為黏膜型、肌型、漿膜型[1]。其中以漿膜型最為少見。本文分析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消化內科收治的1例伴有胸腹水的漿膜型EG患者,并進行相關文獻的回顧復習,報道如下。
病例資料
方某,男性,22歲,因“反復腹痛、腹瀉、嘔吐1個月,加重伴腹脹1周”于2020年1月9日入院。患者入院前2周無明顯誘因出現中上腹痛,夜間或空腹時明顯,疼痛劇烈,疼痛每次持續3~4 h,伴腹瀉,平均解3~4次水樣便/d,間有反酸、嘔吐,嘔吐物為胃內容物,無發熱、胸悶、胸痛等不適。曾至當地醫院就診,查白細胞計數12.28×109/L,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11.1%,當時考慮“急性胃腸炎”,予“蒙脫石散”等對癥治療后,癥狀稍有好轉出院。出院后上述癥狀反復發作。近1周來癥狀較前加重,伴有腹脹。為求進一步診治特來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就診,查血常規提示嗜酸性細胞百分比57.6%,白細胞計數20.64×109/L,門診擬診“腹痛”收入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消化內科。自起病以來精神、胃納差,體質量較前減輕。患者既往有“過敏性鼻炎”病史。患者平素有長期熬夜和宵夜生活史,喜歡在街邊大排檔進食。
入院體格檢查:體溫36.3℃,脈搏128次/min,呼吸18次/min,血壓119/82 mmHg(1 mmHg=0.133 kPa),中上腹輕壓痛,無反跳痛,移動性濁音(+)。余查體未見明顯異常。
入院后完善檢查,血常規示: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47.5%,嗜酸性粒細胞絕對值8.94×109/L,白細胞計數18.83×109/L。腫瘤標志物:糖類抗原(CA-125)334.2 U/ml。超敏C反應蛋白、血液生化、尿常規、糞便常規、甲狀腺功能、凝血功能、病毒全套、心肌酶等未見明顯異常。
患者有不明原因腹痛、腹脹、腹瀉、嘔吐等消化道癥狀,外周血EOS百分比重度升高。患者既往有過敏性鼻炎病史及不潔飲食史。患者近期無服用特殊藥物。綜合患者病史,考慮如下診斷及鑒別診斷:⑴過敏性疾病;⑵感染性疾病(寄生蟲感染等);⑶胃腸道疾病(EG、炎癥性腸病等);⑷風濕系統疾病(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等);⑸腫瘤(消化道腫瘤、淋巴瘤和白血病等)。遂完善糞便蟲卵檢查、風濕免疫指標、胸腹部CT、胃腸鏡、腹腔穿刺、骨髓穿刺活檢等相關檢查。
糞便蟲卵檢查陰性。幽門螺旋桿菌檢測陰性。風濕組套自身免疫抗體及補體正常。胸部CT可見:雙側胸腔少量積液影;腹腔大量積液影。全腹部CT+增強可見:小腸腸壁明顯彌漫性增厚水腫,累及十二指腸、空回腸。腹盆腔內見大量積液(圖1);雙側胸腔積液。

圖1 1例伴有胸腹水的漿膜型嗜酸粒細胞性胃腸炎患者全腹部CT+增強 圖2 1例伴有胸腹水的漿膜型嗜酸粒細胞性胃腸炎患者腹水病理圖(蘇木素-伊紅染色 ×40)
行腹腔穿刺抽取腹水送檢,腹水常規及生化提示腹水為滲出性腹水。腹水培養陰性。腹水病理診斷:鏡下見大量嗜酸性粒細胞(圖2)。綜上考慮為:嗜酸粒細胞性腹水。
胃鏡檢查:胃底及胃體、胃角、胃竇黏膜充血水腫;十二指腸球部黏膜充血水腫,十二指腸降段環形皺襞黏膜充血水腫,散在糜爛。腸鏡檢查見:回腸末端局部黏膜充血水腫,散在紅斑,回盲瓣充血、水腫;回盲部、升結腸、橫結腸/脾曲、乙狀結腸、直腸黏膜彌漫性充血、水腫。病理檢查提示:胃黏膜可見較多嗜酸性粒細胞浸潤,腸黏膜固有層水腫、充血,黏膜下層可見大量嗜酸性粒細胞浸潤(圖3)。

圖3 1例伴有胸腹水的漿膜型嗜酸粒細胞性胃腸炎患者胃腸鏡活檢病理圖(A蘇木素-伊紅染色 ×40;B蘇木素-伊紅染色 ×100)
骨髓穿刺涂片+血涂片見:骨髓增生活躍,見嗜酸性粒細胞極度增多,占37%。外周血白細胞增多,嗜酸性粒細胞占56%。骨髓活檢病理見:骨髓增生明顯活躍,粒、紅、單核/巨核三系細胞均增生,粒紅比例大致正常,粒系以中晚幼/桿狀粒/分葉核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為主,紅系以中幼紅及晚幼紅細胞為主,形態基本正常。結合臨床,考慮為炎癥導致的嗜酸性粒細胞增多(圖4)。

圖4 1例伴有胸腹水的漿膜型嗜酸粒細胞性胃腸炎患者骨髓活檢病理圖(A蘇木素-伊紅染色 ×40;B蘇木素-伊紅染色 ×200)
結合患者病史及檢查結果,考慮患者診斷為EG(漿膜型),并立即給予“地塞米松磷酸鈉注射液5 mg靜脈注射,每日1次”治療。經過激素治療,患者消化道癥狀明顯緩解,腹水消退,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計數迅速下降。2020年1月19日復查血常規示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7.3%,嗜酸性粒細胞絕對值0.52×109/L。患者病情穩定后出院,出院后繼續予強的松30 mg口服,每日1次,每周逐步減量。患者停激素2周后,于2020年2月27日返院復查血常規正常,患者無特殊不適。
討 論
EG是1937年由Kaijser[2]首次提出的,具有消化道癥狀的,在消化道組織中可見嗜酸性粒細胞異常浸潤的一類罕見的炎癥性疾病。目前對于EG的診斷尚無統一標準。國內外研究對EG的診斷多采用Talley等[3]的診斷標準:⑴具有消化道癥狀;⑵病理活檢證實胃腸道有EOS浸潤或外周EOS增多的特征性表現;⑶排除寄生蟲感染和胃腸道外EOS增多等疾病。
在EG臨床表現中,最常見的癥狀為腹痛[4-5],其余還常可表現腹脹、腹瀉、惡心、嘔吐等。EG的臨床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嗜酸性粒細胞在消化道壁浸潤的范圍及程度。漿膜型EG可表現為腹痛、腹水、腹膜炎等[6]。嗜酸性粒細胞性腹水可作為漿膜型EG特征性表現[7]。
常規實驗室檢查對于EG診斷無特異性。相關報道指出:70%~80%EG患者存在EOS增多[8-9]。外周血EOS增多可作為診斷EG的重要導向。但有學者發現部分EG患者的外周血EOS含量正常[10]。因此并不能把外周血EOS含量正常作為EG的排除標準。本文病例是具有典型表現的EG,其外周血EOS高度增多,為我們診斷EG提供了一個重要指引。有學者在對171例嗜酸性粒細胞性腹水患者病因進行回顧性分析發現74%的患者屬于EG[11]。因此,當患者存在嗜酸性粒細胞性腹水時,應高度考慮EG的可能,但還應排除其他繼發性引起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的疾病。
EG內鏡表現無特異性。對于EG的診斷,病理活檢是不可或缺的診斷基石。建議在消化道壁相對正常部位或異常部位多點取活檢,以提高診治,避免漏診。
糖皮質激素是目前臨床上推薦使用的針對EG的一線治療方式。激素對于漿膜型的療效較好[12]。激素使用后,大多數患者的癥狀會逐漸減輕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會迅速下降至正常。目前對于激素的使用尚無統一標準。激素治療應注重個性化調整,待癥狀減輕后逐漸減量。
EG是一個排他性的疾病,在最終診斷EG前需要排除其他可能疾病,以一元論解釋。本例患者主要以腹痛為首發癥狀,伴有腹瀉、腹脹,其消化道癥狀較為常見。但血常規提示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高度增多,引起我們警惕。患者有“過敏性鼻炎”病史,有不潔飲食史,通過糞便培養、蟲卵檢查等排除寄生蟲感染;通過自身免疫抗體及補體檢查等排除風濕性疾病;通過CT等檢查排除實體瘤、克羅恩病等;腹水檢查提示嗜酸性粒細胞性腹水,高度提示EG(漿膜型)可能;行內鏡下胃腸道多部位活組織病理學檢查發現有胃黏膜可見較多嗜酸性粒細胞浸潤,腸黏膜固有層水腫、充血,黏膜下層可見大量嗜酸性粒細胞浸潤。通過骨髓穿刺涂片及活檢,發現骨髓中也有大量嗜酸性粒細胞存在,且以成熟粒細胞為主,排除血液系統疾病。綜上條件,符合Talley診斷標準,最終診斷為EG(漿膜型)。明確診斷后,使用激素治療,患者的癥狀迅速緩解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很快下降至正常,證明治療有效,也再次佐證該診斷。EG的發病率較低,特別是漿膜型EG,在臨床上更為少見。EG的臨床表現及影像學表現較為常見,缺乏特異性。針對本例患者,按照臨床常規思維首先考慮常見病,如急性胃腸炎等。但常規治療效果處理不佳,且伴有外周血EOS升高時,應該想到EG的可能。對于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的高度增多應該引起重視。但需要注意,臨床上可能碰到的EG病例未必有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增多。
本例漿膜型EG的疾病特點就是:具有常見消化道癥狀、外周血EOS計數升高、伴有胸腹水(腹水為嗜酸性粒細胞性腹水)、內鏡下消化道多部位活檢見EOS浸潤、激素治療有效。希望通過本文案例,能夠加深醫護人員對于漿膜型EG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