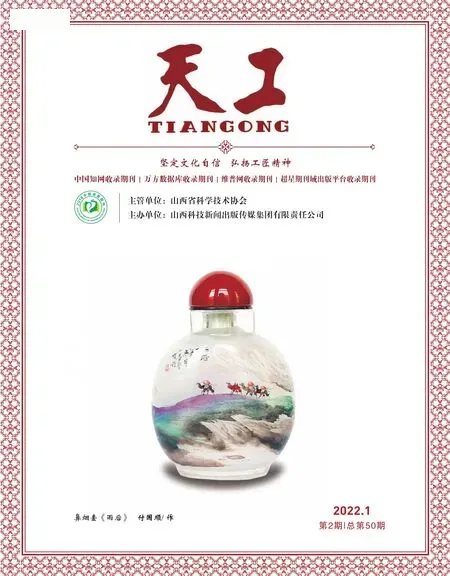清宮里的皮球紋
——乾隆花園古華軒黑漆描金落地罩上的皮球紋探析
吳勝杰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一、古華軒黑漆描金落地罩皮球紋特征
乾隆花園,又稱寧壽宮花園,是乾隆皇帝在位時期主持修建的皇家園林之一。從2001年8月起,故宮博物院與美國世界建筑文物保護基金會合作,對乾隆花園實行了一系列保護與修復措施。
古華軒是乾隆花園第一進院落的核心建筑,軒內金柱間裝飾有一圈黑漆描金落地罩,年久失修,亟待保護。落地罩大邊上殘留的皮球紋由形狀相同、大小相近、內容不同的小團花按照不太規律的組合形式交錯排列而成,小團花周圍飾以單線勾勒的纏枝紋藤蔓。這種裝飾形式與構成方式在中國傳統審美經驗中并不多見。
古華軒黑漆描金落地罩為乾隆年間所建,光緒時期進行過整體的重修,隔扇上殘留的紋飾多為光緒時期所制,乾隆時期紋飾只有少量殘存。經過對殘留描金紋飾的調查與整理發現,仍可辨識的小團花樣式,乾隆時期有20多種,光緒時期有160多種,內容來自傳統紋樣、符號、文字、植物、水果、動物、風景、幾何圖形等生活中的各個方面。
中國傳統圖案美學中似乎非常注重對稱與均衡的特點,特別是在宮廷裝飾中,大到城市布局、宮殿建筑,小到杯盤、首飾,無不時時用秩序、規矩、均衡來體現著皇家的威嚴、端莊、正統。而古華軒黑漆描金落地罩上的皮球紋卻絲毫不見這種威嚴、莊重,給人輕松、靈動、自由灑脫的親近感。小團花一般是以單雙交錯的組合形式分布,但局部時常會出現打破單雙交錯模式而“單單連續”或“雙雙連續”的現象,甚至出現三個一組的形式,布局靈活,可以體會到當時的工匠雖然為至高無上的君王服務,但也不是束手束腳。更能充分展示當時藝人創造力的是小團花的內容多樣性特點,藝人們從生活中提取素材,經過圖案化,置于大小相同的圓形之內,再隨意打亂、隨意組合,形成富有無窮變化的紋飾。
二、皮球紋的定義
皮球紋被人們熟知,主要歸功于明清時期皮球花瓷器的大量出現。馮先銘先生在《中國古陶瓷圖典》中稱:“皮球花紋是瓷器裝飾的典型紋樣之一,指多個大小不一、花色不同的團花,似有規則似無規則地分布在裝飾畫面上,宛如跳動的花皮球,因而稱作皮球花。”馬未都先生在《瓷之紋》中提道:“皮球花為民間俗名,正確稱謂應叫各色團花。”提及皮球花,馮、馬二位先生的解釋是學界的權威,被廣泛引用,但二者均特指瓷器上的皮球花,并不能作為相關紋樣的一般定義。
經筆者考證,清代皮球紋的應用范圍包括瓷器、漆器、金屬器、服飾、家具、內檐裝飾、外檐彩畫等各個領域;構成方式包括散點式、連續式、亂序平鋪、有序排列、與其他紋樣結合等各種形式;顏色組成包括單色和多色。馮先銘先生對皮球紋特點的描述“宛若跳動的花皮球”,貼切、形象、生動,因而這是皮球紋定義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眾多學者對皮球花和團花做過比較分析,如袁月的《皮球花瓷器》、石牧陽的《北方地區出土宋元時期瓷器的團花紋飾研究》等,不一而足,雖然側重點不同,但都不能否認團花是皮球花形成的基礎。綜合多方觀點,筆者認為皮球紋應定義為:多個形狀相近、內容不同的小團花以規則或不規則的方式分布在裝飾畫面上,宛若跳動的花皮球,稱為皮球紋。
三、皮球紋的形成、演變、發展
關于皮球紋的源流,學界有兩種說法,一說源自中國團花,一說源自日本家紋。團花是指在一個圓形范圍內呈中心對稱分布的圖案構成方式;日本的家紋,即家徽,又稱紋章,是家族的標志。
團花和皮球紋固然有傳承關系,但兩者從構成形式上有本質的區別,中國團花受中亞薩珊王朝傳入的連珠紋影響,除了寶相花作為主體紋樣單獨存在外,還有以多個團窠紋有規則排布構成紋樣的。無論何種形式,團花講究對稱性或整體性。而皮球紋是多個形狀相近、內容不同的小團花以規則或不規則的方式分布在裝飾畫面上,側重于多個小團花和組合方式的多樣性,因此,可以說團花是皮球紋形成的基本要素。
而皮球紋源自日本家紋的說法也過于絕對。首先,家紋種類繁多(日本學者丹羽基二收集家紋數量約兩萬個),充分展現了日本民族豐富的想象力和充分的表現力,但家紋的構成方式遵循著一種類似數學排列組合中兩兩組合的內在規律,這種方式在組成畫面內容的邏輯上略帶違和感。而用于清宮裝飾的皮球紋摒棄了家紋中略顯牽強附會的部分,以不同內容的傳統團花為基本單位組成裝飾紋樣,兩者表達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內涵,相比日本家紋,皮球紋在合理性、繪畫性、靈活性、趣味性等各個方面都有了突破。其次,日本家紋產生于平安時代后期,而當時唐代流行的團花等圖案早已傳入日本并在很大程度上引領了日本紋樣發展,從家紋的樣式和產生時間來看,家紋的產生也必然受到團花傳入的影響。
通過前人的研究,加之一些蛛絲馬跡的線索,幾乎可以推導出這樣一個發展歷程:中國團花紋樣受到中亞文化影響,成熟于隋唐時期。公元7世紀至公元8世紀,隨著遣唐使的回國,日本廣泛接受了來自唐朝的團花等紋樣,促進了日本家紋的產生,并在一定程度上為家紋的形式奠定了基礎。平安時代后期,家紋形式產生并被描繪于牛車等物品上,作為家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后來,隨著日本家紋文化和裝飾藝術不斷發展,家紋被廣泛應用到各類工藝美術裝飾中,形成了日本裝飾藝術中典型的散點式自由布局的構圖樣式,并對以后的日本裝飾藝術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后,家紋逐步淡化了家族徽章的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其裝飾作用。明朝后期,大量家紋裝飾隨著日本盛行的蒔繪漆器進入中國。傳入中國后,日本家紋的裝飾風格受到中國文人士大夫的追捧,與發展了千年的中國團花紋樣合二為一,摒棄了不符合國人審美的內容,完全去除了家族徽章的功能,形成了我國傳統紋樣中一個獨特分支——皮球紋。
綜上,皮球紋是團花和家紋在漫長的中日文化交融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歷史的結晶與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