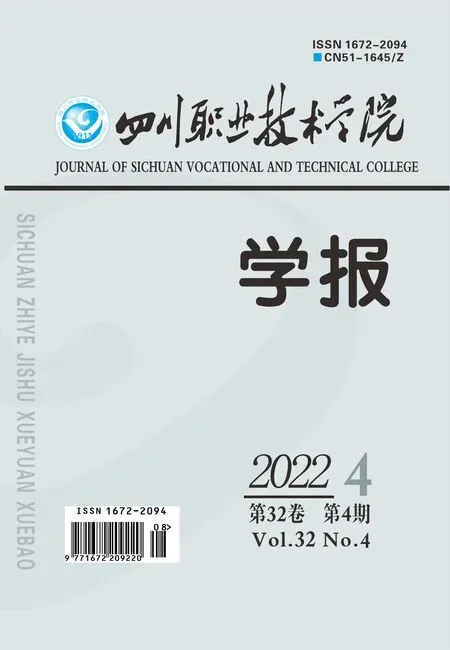西漢大一統視域下儒家士人的政治哲學
魏弋賀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內圣外王”是傳統儒家思想的兩翼,在過往的研究中,學界多強調在哲學視角下對儒家思想的審視,如新儒家代表牟宗三所認為的那樣,傳統儒家在外王方面的理論創造遠不及其在內圣角度思想綿延傳承的盛狀。而余英時則另辟蹊徑,他以政治文化為視角審視了宋明理學的哲學傾向,開辟了一條獨特的思想史研究道路。但同時也要看到,根據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及其同時存在的不同特征,不論是哲學角度亦或是歷史學角度,這種單一的研究路徑是無法真實地還原所要研究對象的全貌的。就具體的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研究來看,更應是如此。思想本身就是現實與創造的交織,因此本文在初步明確儒家士人在其所處時代面臨的現實政治問題時,進一步追問并探究了整個儒家士人階層在其思想體系架構中,對于倫理政治具體表現出一種什么樣的旨趣,呈現出一種怎樣的思維發散,明確中國傳統士人階層在時代感召下的積極態度。
一、大一統政權的初建——政治背景
對與政治相關的道德、倫理問題的討論,必然是以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作為滋養土壤。而從西周到秦漢時期,大一統政權的建立作為統治體系變動的主線,無疑是為儒家“道”與“治”兩種思想的交替展現提供了平臺。西周時期為維系穩定,實行了一種政治與血緣倫理相結合的宗法制度,這已經是學界的共識。許倬云曾這樣描述這種制度
西周的分封諸侯,一方面須與西周王室保持密切的關系,休戚相關,以為藩屏;另一方面,分封的隊伍深入因國的土著居民之中,也必須保持自群之內的密切聯系,庶幾穩定以少數統治者凌駕多數被統治者之上的優勢地位。”[1]
可見以親緣為聯系樞紐的宗法制不論是對西周對外的殖民擴展或是貴族內部的穩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春秋時代,隨著親緣關系的淡化,這種維系紐帶變得異常的脆弱,整個社會的動亂無不預示著一種新秩序即將建立。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是“以宗法姻親、禮樂體系為基本的政治倫理原則,契約關系為實質主導取代了原來的血緣宗親關系。”[2]契約關系并不靠人們之間的情感維系,而是依靠利益的相互妥協,這種秩序僅能作為社會動亂下的權宜之計,極容易隨著利益的變化而受到影響。在長期的爭霸戰爭中,中原諸小國無不是按照形勢發展選擇自己的隊伍,恃強凌弱、趁火打劫的事情時有發生,可見這種契約關系內在的倫理觀念也是現實的、短效的。同時這種契約關系在各國內部的政治觀念中也成為了基本的倫理原則。家國一體的政治生態環境下,臣對君的效忠不僅是處于個人關系上的聯系,同時也是家族倫理秩序的反映,君主同時也代表著整個貴族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而到了春秋時期則出現了變動,一方面是作為同姓同宗的統治者們的親緣感越來越淡薄,如魯之季氏僭用八佾,孔子曾評價其行為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3]季氏全然不將自己視為宗族社稷守衛的一份子,而僅僅是認同自己家族掌權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則是異性對公族的挑戰,晉文公繼位不久就分封異性趙衰、狐溱等人為大夫[4],經過晉國內亂,使得為晉國成為第一個被公卿分割的國家。這些事情無不顯露了宗法等級觀念遭受的巨大沖擊,一種新的統治秩序亟需建立。
春秋戰國較為紛亂的政治形勢在秦的統一下結束,這種統一帶來的最大的變化便是所謂:“國家地域內的公民已經跨越了血緣關系,取而代之的是地緣聯系。”[5]官僚政治下的中央集權展現了強大的威力與現實效益,使得統一成為了每一個政權所必須考慮的政治問題,但同時這種制度也因為秦的滅亡而受到了普遍質疑。盡管此種政治體制展現出了較為僵硬、極端的一面,但西漢初的統治者們仍舊以此作為自己的立國基礎。學者們將漢代對于秦代這種制度上的繼承稱為“漢承秦制”。其主要表現包括有中央層面的皇帝制、三公九卿制的官僚制度,地方層面的郡縣制、基層官吏的任命制度,社會運行層面的軍功爵制、編戶齊民制度等等。可以說在漢初這種動蕩局勢下直接采用這種現行的治理體系可以幫助統治者迅速建立有效的統治秩序。但同時秦亡的反思又不得不使得漢代的統治者在制度上進行一定程度的創新。
有學者認為漢代統治者制度上的最大創新之處便是將郡縣制與宗法制相互結合,用郡縣作為地方治理的繼承單位,大權掌握中央政府手中,同時又分封大批宗室貴族到地方,沿用西周春秋時期的宗法分封,通過這些同姓子弟來控制、監督地方,這一部分土地的維系紐帶則是宗族親緣關系,以避免所謂“孤立”之敗[6]。可以說,在漢代統治者的構想中,地方以官僚的權利控制和宗族的血緣控制兩種力量作為統治基礎,二者既同步作用又相互制約,最大限度的避免動亂的發生。這一時期漢代政治表現出來了明顯的“法周”特征,有學者將其體現出來的特點總結為“尊主卑臣”與“親親尊尊”[7]。另外在律法方面也明顯體現著漢代制度架構中的獨特特色,“約法三章”一事常被視為漢代統治者繼承秦代依靠成文法處理現實問題思想的明例,在紛爭局勢下劉邦依靠明文規定的律法制度應對治理難題是自然而然的選擇。但在宋潔的論述下,“約法三章”的內涵有了更大的擴充,一方面從“抵罪”一詞即可看出,劉邦在制定“約法三章”時是在承認和利用秦律的基礎上實現的,同時“約法三章”的內容也并非只與那句著名的“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等同,且“約法三章”的行使實踐一直綿延至漢代建立,可見這種以律法作為社會秩序維系工具的思想一直在繼承[8]。但同時鑒于秦代僵硬的依靠成文律法作為評判標準,以及法律規定的嚴苛和百姓實際生活的差異釀成農民起義的發生,漢代統治者又對成文法的制定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改,除了有極刑、連坐等律法的廢除,還在律法中加入人倫、道德因素。總體而言,至少從統治階級角度來看,權勢階層迫切地想要一套能夠維系統治的意識形態理論。
二、大一統政權的鞏固——政治需求
盡管漢初統治階層有著諸多的調整,但是隨著社會政治形勢的發展,王朝統治仍舊面臨了巨大的挑戰。在西漢建國初期被視為是保障地方統治基石的分封制遇到了和春秋時期一樣的困境,隨著宗族勢力的擴大,同姓宗室之間的親緣感也在逐漸淡薄,盡管劉姓宗室的繁衍時間遠不能和西周至春秋相比,但是此時社會與民族的凝聚統一使得劉姓宗室并未有如西周初期開拓殖民的共同目標,相反皇帝大權集中的巨大現實效益卻遠遠壓倒了維系宗室統治的信念。這就使得宗室分封成為了威脅統一的最大障礙。正如賈誼所說:“老聃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管仲曰:‘備患于未形’,上也。……智禁于微,次也”[9]58,可見內部的分裂風險已經引起了知識分子的警惕。同時這一時期漢王朝又面臨著北方匈奴的強大壓力,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白登之圍”,僅僅是在軍事上的對抗漢朝便無力與匈奴抗衡,無奈之下劉邦只能采用婁敬的建議,“約為昆弟以和親”,采用和親的方式應對現實危機。
內部力量遲遲不能得到集中,匈奴侵擾的威脅又近在眼前。占據主流地位的黃老思想在國力恢復、穩定社會秩序、磨合內部矛盾層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無法應對這種緊迫的現實問題。大一統的王朝秩序已經成為了整個知識分子們的共識,那么如何最大限度的保障皇帝大權獨攬以維系統治機器的有效運行,又能避免過渡僵硬地依賴律法條文導致的社會矛盾,這是漢初儒生們面臨的現實性問題。
應對于現實性的政治危機,從陸賈到董仲舒分別提出了相應的應對措施。在漢初經濟凋敝的情況下,恢復生產、休養生息是一個王朝的必然選擇。在《新語》中,陸賈指出“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10]2699所謂順守,便是以制度性建設維系長期統治,陸賈的建議符合漢初的實際情況,為高速運轉在戰備狀態下的西漢朝廷按下了暫停鍵。與民生息的需求為黃老無為的思想提供了發展的基礎,陸賈的政治主張亦因現實而與黃老思想產生交集。他在《無為》篇中說:“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11]59即是要效法古代圣王,為此他又進一步勸諫劉邦道:
昔舜治天下也,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禮樂,效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者乃有為也。”[11]59
在這種無為的思想指導下,陸賈先后提出了輕徭薄賦、以民為本、約法省刑等主張,這一系列建議亦被漢初統治者所接受,成為漢初“無為之治”思想中的組成部分。到賈誼之時,漢代已經經過了數十年的休養生息,此時不僅王朝的綜合實力有了恢復,且內外部的矛盾也有了一定的激化,為此相比較于陸賈的政治思想,賈誼完成了由“無為”到“有為”的轉變。賈誼根據當時存在的諸侯王僭越違法,商人地主奢侈逾制,社會上下尊卑等問題,提出了以禮治國的政治對策,“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9]214。其本質是要行仁政,施仁義,用道德教化來移風易俗,依照政府的積極有為來使社會達到一種合理有序的狀態。這之中最著名的莫過于“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即是以鞏固君主集權為目的的主動舉措。可見由于現實政治環境的改變,賈誼的政治主張相較于漢初儒生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依托儒家傳統的禮治思想,勸諫君王對社會秩序進行積極整頓,明確社會等級,以期使各階層明確自我的職責,解決現實性的社會矛盾。到董仲舒時,此時正值漢武帝統治時期,漢朝國力不僅得到了恢復,甚至已經到了可以大有作為的狀態。正是在現實的政治需求以及君主自己宏大的政治目標下,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學提供了思想基礎、理論框架以及建構范式。隨著漢武帝時期整個國家的政治由無為轉向有為,儒學開始了全面的自我調整。為進一步加強君王地位,董仲舒用陰陽、五行、三綱、五常進一步鞏固君王至高無上的地位,相繼提出“大一統”思想、君道觀、統一民族觀等思想。董仲舒認為所謂“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而承載統一的,則是尊天配德的君主,“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12]201由此董仲舒就構建了一個以君王為中心的等級秩序。“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于仁。”[12]329同時君王又是溝通天地秩序與人倫秩序的關鍵,君主作為天道的化身,通過教化來使百姓遵循自己的職責,使天地本有的陰陽規則展現于人間。董仲舒的這種架構不僅適用于華夏族統治區域,甚至在其“大一統”思想指導下拓展至周邊所有所謂“蠻夷”之地。這就為當時漢朝政府的積極有為政策提供了理論保證。
三、大一統政權的深化——政治構想
倘若以現實的政治背景作為視角審視漢初諸儒的政治哲學思想以及相應的政治主張,則很容易得出漢初儒家政治思想是雜糅了道家、法家、陰陽家思想這樣的結論,由此亦能對漢初儒家政治哲學進行合理的解釋。盡管漢初諸儒的政治哲學是繼承于諸子學的政治底色,以從政、為政為主要目標,在政治實踐中不斷演變,但基于此則將其視為對現實政治的被動回應來對待就必然忽略了其中獨立的發展演變脈絡,忽略了哲學思想的創造性。因此我們也必須要認識到儒生們在表達政治主張背后獨立的哲學體系,以期客觀的展示儒家這種倫理政治思想。
陸賈的政治思想可以在其著作《新語》中看出,在向劉邦提出自己的治國理念時,陸賈提到了“行仁義,法先圣”[10]2600,這六個字既是陸賈所提出的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的良方,也是漢儒針對現實性的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凝結的思想創造。《新語》一書開篇即是《道基》,所謂“道”便是宇宙運行最為根本的法則,可見《新語》一書并不是要為西漢政權提供一種具有短期效益的施政計劃,而是要為整個西漢政治政權的存在構建一個能夠上升到天地規律的法理性。陸賈在《新語》中提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圣人稱之。”[11]1“于是先圣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11]9圣人作為可以與天地并立的存在,其最大的貢獻就是觀察天地規律從而制定了人間的秩序,這里一方面說明了這樣一種秩序并非強制性的對人的要求與限制,而是人生存下去的必要基礎,也就是說遵循這樣一種秩序并非是對于強權的服從,而是人創造自己生存條件的義務。那么這就為制定統治秩序的漢朝政府提供了最大的管理正當性,同時也避免了如同秦朝時期依靠高壓、震懾的手段來迫使百姓服從。這里有一個邏輯就是,在陸賈看來專注于刑罰本身就是對于禮儀秩序的拋棄,是政權虛弱的表現,拋棄了禮儀就是置天地之根本法則于不顧而只求一時之效,這樣的話王朝注定無法長久。陸賈提到:“圣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11]168,也就是說儒家所追尋的治道盡管也強調有為,但并非完全的無根據的作為,而是因時因地,根據時勢的變動而治理,這種治理是遵循著天地之道或者說仁義之道的原則來進行的調整,它在一個明確的秩序下又保留了很大的靈活性,事功的實現不滋事端,主要依靠對民眾的德化勸導,這種治理思想是適合漢初的政治形勢的。另一方面也展現出了圣人確立人道的不朽地位,對于圣人如何理解,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認識,但不論何種,都可以將之視為陸賈在歷史經驗總結中感受到的一個維系這種統治秩序存在的核心人物的重要性。將儒家士人作為圣人的代表來看待則賦予了整個儒生階層一種極大的能動性,換句話說儒生們已經儼然以衛道者的身份出現,成為維系整個社會秩序穩定的根本力量。同時這種圣人觀又極大地鼓舞了漢代統治者,乃至形成了一種圣王觀,漢武帝在元光年間所下的賢良征舉詔書中寫道:
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13]161
在后來的詔書中漢武帝也多次提出這樣的盛世理想,顯然是受到了儒生們這種圣人思想的影響,故以成就圣王、實現天下太平安樂作為自己的施政抱負。陸賈《新語》中有大量篇幅描述先圣時期一切行為皆順應百姓自然地需求,人們的言行舉止無不依禮而行的狀態,當然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禮儀道德的制定本身就源自于早期人類的日常行為,但在陸賈這里這種社會顯然被傾注了許多美好的想象,也不能排除漢武帝的這種圣王思想受到了其影響。陸賈的政治思想基本奠定了西漢儒學政治主張的基調,其后的賈誼、董仲舒則就此在不同的方面進行了展開。馮友蘭先生認為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筑要以一個包括宇宙、社會、人生各方面的哲學體系作為中心[14]。那么賈誼與董仲舒就是分別在具體社會規范與宇宙層面進行的思想發揮。對于秦代政治得失的反思工作,賈誼應當是做得非常深入的,繼承于陸賈的思想邏輯,賈誼也認為秦代重刑罰、輕教化、不行仁政本身就是對天道秩序的放棄,這樣的政權必然會被滅亡,“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13]2253那么借鑒這樣的教訓,賈誼提出來的解決方法就是“禮”。針對賈誼“禮治”思想的研究著作有很多,總體來講在賈誼看來:“故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15]214“禮”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定名分尊卑,使人人皆能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禮治”與“仁義”并非矛盾,相反“禮治”正是“仁義”的體現,經過秦末的動亂,社會經濟疲敝,黃老的無為之治確實是順應民情之舉,但是在賈誼看來,這種政治思想是與秦代法治同樣的應急之策。“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13]2242社會必然是在恢復中向前發展中的,仍舊采取放任不管的態度,任由社會矛盾自由激化,這在賈誼看來是同秦朝暴政一樣的行為,是對百姓不“仁義”的做法,一個政權必須要在適度的范圍內有為,百姓既不需要過多的管制,亦不需要過分的放縱,作為天地之道的代理,一個政權的存在就必須要替天行道,教化百姓、移風易俗,創造一個禮儀之邦的“理想國”。“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15]54,同時要“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13]2252,那么這樣才算是逐步建立了一個比較穩固的社會秩序。賈誼所展現的這種有為、無為的融合,同時又極大的賦予其倫理上的特征,足見其儒生本色。在當時充斥著以無為而治為主流的社會形勢下,整個王朝仍舊以休養生息作為主要的政治任務時,賈誼并未固守于當時所面臨的緊要問題,他已經看到了當下的王朝政治思想可能出現的問題,同時在繼承儒家倫理思想的基礎上為政權的架構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政治主張,可以看出他對于創造一個可以維系社會長久穩定的政治秩序的思想嘗試。
相比較于前期儒家政治思想的發展,董仲舒最大的創造之處便在于他將儒家現實的政治思想成功的上升到了哲學境界。這里我們主要討論董仲舒“大一統”思想所解決的現實政治問題及其政治思想上的創造。前面我們已經提到西漢時期儒生們面對的是如何兼顧鞏固君主作為權力核心的秩序的維系作用以及如何最大限度的彌合社會矛盾,保障社會活力的政治問題。對此董仲舒提出了他自己的君道觀,董仲舒的君道觀可以視為一個目的下的多重要求,社會秩序的穩定是一個大而廣的終極目標,它是可以與宇宙之道并存的永恒問題,那么作為維系這種穩定的兩個重要力量——君與民,董仲舒都制定了相應的要求,其實這也是面對官僚政治下的基本矛盾的解決途徑,是在新時期下對孔子時期道德治國思想的繼承。“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庸能當是。”[12]328董仲舒的王者思想既是對“圣王”形象的詮釋,反過來說也是對君王潛力的肯定,王者作為溝通天地之人,很大程度上是承載著將天地秩序重現在人間的責任,這既是君王的義務,同時也是君王獨有的權利。其實在董仲舒看來“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12]201天子天然的就是天德的化身,那么配享這種大德的天子所施加在人間的種種政策,本身就被賦予了天的意志,在這里董仲舒用其較為成體系的形而上的宇宙論為君主權利的合法性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但同時董仲舒又不限于僅僅為現實政治需求服務,君主雖然是天德的化身,但這畢竟還是理想的狀態,實際上凡人之軀的君主仍有種種人欲在身,這在董仲舒看來同樣是對秩序穩定的挑戰。我們剛剛援引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君主樹立了目標,董仲舒的民本思想亦是其維系政權穩定的政治主張,“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12]273孟子的民本思想同樣也是學界的關注熱點,但在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對君王的勸諫并非是以人性之善的仁愛觀出發的,他仍舊是在政權合法穩定的角度上來警戒君主的,可見其民本思想所蘊含的政治意味是很濃厚的。在封建王朝草創之時董仲舒便有如此設計,足見其政治思想并非全然受現實問題的制約,它仍反映著董仲舒在政治領域的思想深度。牟宗三對于董仲舒的思想進行評價時曾用“理性之超越”一詞來作為判斷語,他看到了董仲舒思想駁雜背后的超越,而此種超越正是體現在其政治思想上,同時他批評董仲舒跳過孔子精神而承接五經是其駁雜的重要原因之一[16],但是換種角度來看,董仲舒的這種依歸何嘗不是對于現實政治的超越?何嘗不是以為儒生自我政治思想的超越?對早期儒家過分關注人事而缺少形上層面擴展問題的回應與補充,本身就可見董仲舒倫理政治思想內的哲學痕跡。綜上可以看出,梳理陸賈、賈誼、董仲舒三人政治哲學思想背后的創造,可以發現盡管儒家政治思想的形式因社會現實需求的改變而不斷地變化,但其背后仍有著獨立的發展主線,它反映了儒家傳統政治哲學回應政治而又超越政治的宏富特點,反映了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統包兼容的一貫性。
四、結語
西漢時期,作為秦代確立并鞏固的中央集權式的官僚政治得到了繼承,但是秦朝的短命而亡又迫使西漢儒家士人們不得不對這種政治體質進行改造,因此他們在保證大一統政權成立的前提下,又相繼加入了天命五行、倫理思想等,在最大程度上對官僚政治思想進行了儒家式的改造,以期望保障大一統政權的長治久安,在整個社會由點到面地構建穩定的秩序。漢儒們的思想創造在以后進一步衍生出了倫理與道德、得君與覺民等不同的實踐道路,但不論何種都是對于這種時代問題解決的積極嘗試。不論具體的政治主張對于現實政治問題存在多大的價值意義,儒家知識分子在現實政治背后的積極思考仍舊是值得我們肯定的。政治思想或者說哲學思想或許很大程度上會受到現實問題的制約,但還需要看到儒家知識分子們在思想層面對于現實的超越,陳暢提到:“正是宋明理學內部持續進行的思想革新運動,引導出理學家對三代之治的不同想象”[17]。這即是肯定了儒家士人內部思想上的傳承與創造,亦是其對社會秩序架構的重要價值來源。對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視野展開,要避免外在與內在兩方面的割裂與限制。
總的來講,假如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政治與倫理道德似乎可以歸為兩個完全不同的獨立學科,但是在現實中,政治思想的探索不可能完全脫離倫理道德的影響,在對儒家思想進行探究時,這種現象更為明顯。也正因如此才構成了中國儒家思想中政治思想的獨特性。不論我們是以純哲學的、道德的角度或是純歷史性的、現實性的眼光來看,都無法還原這種獨特的政治思想的全貌,因此在對儒家政治思想進行探究時,既要看到傳統儒家思想的形成所受到的社會現實的巨大影響,另外也不能忽視在不同時代、不同問題背景下儒家士人們的思想創造。當然,這并非要說明這種路徑便是最合適、最全面的,也并非強調只要這樣研究便能整體地還原儒家思想,歷史研究對象總是復雜的、難以把握的,很難以一種確切的結論來闡述其內在的整體特征與規律,但這樣的嘗試依然是有意義的,畢竟當我們愿意邁出腳步,說明我們仍然相信這是一條有終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