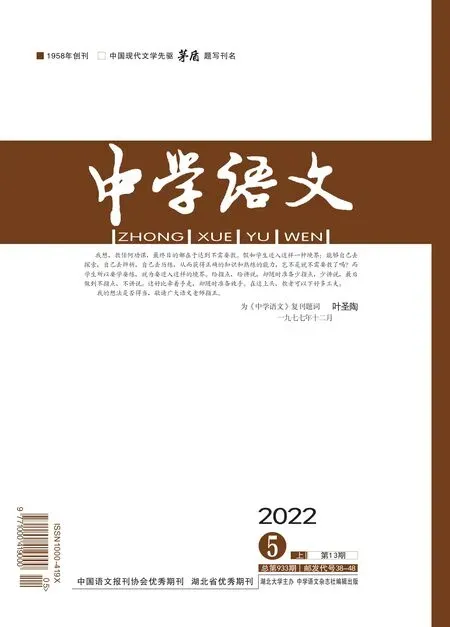生與死的撕裂
——新批評視域下《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解讀
■ 唐芝一
新批評理論最早發源于英國,并逐漸成為英美現代文學批評中最有影響的流派之一,一度攀上四五十年代美國文學批評的巔峰。由于脫離作者,脫離背景,新批評所倡導的立足文本的語義來解讀文學作品的方法逐漸衰落,但其分析手法仍對詩歌批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新批評強調圍繞文學作品本身而展開研究,以文本的內外構成為中心軸,多方面但側重于語言學的角度對文本進行分析與探討,基本概念包括含混、反諷以及張力等。英美新批評派強調,一個優秀的作品要有復雜性或是對矛盾對立的包容性。本文試圖從新批評角度出發,細化為張力、悖論、反諷、含混、隱喻五個方面來解讀《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以期挖掘其新的意義和內在深度。
一、新批評理論解讀
1.張力解讀
在文學理論中,“張力”一詞源于英美新批評派理論家艾倫退特。1937年退特在《論詩的張力》一文中指出:“為描述這種成就,我提出張力(Tension)這個名詞。我不是把它當作一般的比喻來使用這個名詞的,而是作為一個特定名詞,是把邏輯術語外延(Extension)和內涵(Intension)去掉前綴而形成的。我所說的詩的意義就是指它的張力,即我們在詩中所能發現的全部外展和內包的有機整體。”在本文所解讀的這首詩中,細細品味能夠發現詩中充滿了矛盾,字里行間流露著復雜而又深刻的情感,引發讀者深思,勾起作品與現實生活的共鳴。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一共分為3節,在第一節中,詩人連用兩句“從明天起”作為開頭句。詩歌第二節又緊接上一節句式風格,再次強調“從明天起”,“從明天起”詩人要“做一個幸福的人”,“從明天起”詩人要“關心糧食和蔬菜”,“從明天起”詩人要“和每一個親人通信”。這不禁讓人覺得詩人以前或者現在是不幸福的,詩人一直在強調明天,也許是在逃避昨天或者今天,也許是在憧憬明天能夠有所改變,但是詩中確實是沒有看見昨天和今天的影子。這其實就是張力之所在,是對矛盾的包孕。詩中的“我”確確實實不是幸福的,幸福永遠屬于明天,屬于“我”一直企盼的某個時刻,和今天的“我”相去甚遠。細讀本詩能夠感受到詩人對于現實生活的憧憬,同樣,也能感受到這種憧憬所帶來的對于現實的無奈和哀傷。再拋開詩歌回到詩人現實生活中,這種不幸福,這種憂傷遠遠不及詩人對于明天的放棄,寫完本詩兩個月后的詩人,再也沒有“從明天起”了。
除了句式之上所隱含的矛盾之外,本詩意象的選擇其實也暗藏矛盾。通讀全詩,可以感受到這首詩的語言是樸素明朗而又雋永清新的,無論是“喂馬”“劈柴”,還是“大海”“花”“春”,都傳遞著美好與幸福。全詩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讀完能夠讓人感受到希望,感受到對未來的憧憬,但是作者所有的明寫里又有暗示,形成了明暗兩條線索,使全詩形成巨大的張力。所以本詩中所傳達的情感與詩歌語言層面又完全相反,細讀之后悟出的反而是一種沉重之感,或者說是一種強烈和深沉的矛盾。詩中的“我”既渴望把生活過的幸福燦爛,但是現實又把人逼到了絕望。這種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激烈的碰撞,在矛盾的交織中不斷催促詩人走向死亡,“糧食和蔬菜”都不能滿足,何來談“周游世界”,又何來幸福可言?在長期的這種企盼與絕望的邊緣,詩人最終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最終詩人還是放棄了追求塵世的幸福,轉身投入了大海的懷抱去尋求彼岸的幸福。
詩歌第二節中“我”尋求到了幸福,并且還打算將這“幸福”告訴每一個人,但是詩人卻說這是“幸福的閃電”。在常人看來,幸福應當是溫暖的,想要緊緊握在手中的,可是詩人卻把它比作閃電。“閃電”這個意象傳達的應該是明亮和飛速。在本詩中,幸福理解為明亮,則可以照亮每一個人,但是,這明亮的幸福還沒來得及好好感受,卻又飛速般地消失了,“我”想要緊緊握住,卻怎么也握不住,因為這幸福壓根就不屬于“我”。等詩人幻想了一番幸福之后,又光速般地回到了現實,回到了自我之中,這樣的跌宕起伏形成了強烈的張力。我們也就知道了,前面“我”所提到的愿望只不過是幻想,與現實有著巨大的沖突。
2.悖論解讀
文學中的悖論詞語既不是一種詭辯術,也不僅僅是一種修辭,它是文學語言的一種表達方式。本詩中也存在著悖論的現象,細細品味會發現悖論使得詩歌情感變得更加豐富。
《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最后一節寫到:“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詩人除了要祝福陌生人之外,還掛念著山河,結尾處灑滿了浪漫主義色彩,“溫暖”二字更是反映出詩人內心對其渴望,自己無法擁有溫暖,山河不能沒有。“愿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終成眷屬/愿你在塵世獲得幸福”
三句愿你,是因為“愿我”無法奏效,即使是祝福,其實透露出的是悲哀,反襯出詩人沒有燦爛的前程、美滿的愛情也沒有獲得幸福。前程、愛情、幸福這三者是層層遞進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礎,而詩人什么都沒有,詩人有的只能是祝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只愿”和“愿你”將詩人自己與陌生人割裂開來,也把第一節中所幻想的“喂馬”“劈柴”丟掉了。以上所有的祝福是對“陌生人”而言的,而詩人自己并不要這些,所以最后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與第一節中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是不一樣的。詩人通過最后一句又否定了第一節中詩人所想要的塵世的幸福,這里就形成了悖論。
幸福在詩人眼中是可以看見的,因為詩人眼中的幸福是屬于塵世的幸福,而詩人只能默默祝福著陌生人,相對于陌生人,自己是無法獲得塵世的幸福的。無法擁有燦爛的前程,守護不住虛假的愛情,這一切都讓詩人與塵世幸福永遠隔離。
所以第一節中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實際上象征了塵世的幸福,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幸福,而最后一節中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則是與塵世相對“彼岸”,也就是詩人最終選擇的屬于她的幸福——死亡。
3.反諷解讀
“在布魯克斯之前,艾略特、瑞恰慈、燕卜蓀都談到過反諷,但布魯克斯對此作了最詳備的解釋,他把反諷定義為‘語境對一個陳述語的明顯的歪曲。”從“明顯的歪曲”我們可以把反諷理解為:一個詞語在語境下的含義與其表面含義有所不同甚至相反。這個詞語就被賦予了歧義,即這個詞語的語境含義和表面含義存在著邏輯矛盾,是對立沖突的。
就本詩而言,其題目“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就存在著反諷。就其表層含義來說,一望無際大海里有的只能是海鷗、礁石、海浪,詩人面朝大海,是無法看到春暖花開的,反而,能看到的是一望無際的虛無與縹緲。春暖花開理應是五彩繽紛,燦爛奪目的,但詩人卻是朝向大海方向的,看到的全是大海的單調與凄冷,冷藍色所帶來的蒼涼和憂郁全都拍打在詩人渴望幸福的臉上。反觀而行之,也許背對大海,才能真正看到春暖花開。所以在此題目中無論是“面朝大海”還是“春暖花開”都有著反諷的意味,而這反諷意味的背后,其實透露著詩人在矛盾愿景中無盡的糾結。
詩歌的最后一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也存在著反諷。在詩人敘說了“我”明天是如何的幸福,同時也不忘對陌生人給予祝福,對山河給予祝福,三個“愿你”將幸福灑滿整篇詩中,然而最后一句筆鋒一轉,“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一個“只愿”拋棄了前面“我”所幻想的明天的幸福,也能看出“我”最終選擇了和別人不一樣的歸宿。各種美好的愿望和只愿形成的反諷,細細平味,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對詩人的憐惜,給人更深的是一種巨大的落差感、悲痛感。前面一切的美好愿景都被“只愿”一詞擊成泡沫,形成巨大的藝術感染力。
4.含混解讀
含混又稱朦朧、復義,燕卜蓀這樣界定含混:“任何語義上的差別,不論如何細微,只要它能使同一句話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應,就會造成含混。”含混性不同于與混亂性,它隱藏著豐富復雜的詩意,具有美感價值。
詩歌第二節中“我”要將幸福告訴給“每一個人”,第三節中“我”又為“陌生人”祝福。“陌生人”與“我”無太大關系,“每一個人”也與“我”無太大關系,所以從語義的邏輯上來看:“每一個人”應該是包含“陌生人”的。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兩者其實是同樣的人,但是“我”和這兩者的關系卻又有著微妙的不同:“我”與“每一個人”是要傳遞幸福;“我”與“陌生人”是要為他祝福。詩人把“陌生人”至于“每一個人”之后,其實是在暗示自己以后可能無法傳遞幸福了,只能提前祝福了。這個“陌生人”指代的是誰,或者指代的是哪一批人,我們無從得知,我們只知道“我”將生前最后的祝福送給了“陌生人”,這樣含混的表達,讓詩歌充斥著一種復雜的美感。實際上,無論是題目中的“大海”,還是詩歌中的“大海”,都不僅僅是我們平常所見的大海,它有著不同的含義,“大海”一詞,從方法看屬于比喻含混。
5.復義解讀
對“復義”(ambiguity)這個來自西方的文論術語,漢語學界有多種譯法。大多數學者譯為“含混”,趙毅衡先生后來譯為“復義”,周邦憲先生等則譯為“朦朧”。漢語中的“含混”帶較強的貶義色彩,“朦朧”強調因某種視覺原因而導致看不清楚的效果,主觀感覺色彩較強,而“復義”則客觀描述文本語義的復雜性特征,既無貶義色彩也非主觀感受,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譯語。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不僅僅只是作為題目在詩中出現,在全文也是其關鍵語句,前后分別出現三次。第一次出現作為標題,是對幸福的隱喻。第二次出現在詩歌的第二節,詩人渴望有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房子,這樣的房子既能迎面吹著涼爽的海風,又能看到鮮花綻放,試問塵世里誰不想獲得這樣的幸福。第三次出現在結尾,一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表明了詩人的態度,此時的面朝大海,是無法看到春暖花開的,只能與大陸背離,縱身一躍,告別塵世幸福。也許詩人無法擁有塵世的幸福,但是在另一個時空,或者另一個世界,詩人總會擁有“彼岸的幸福”。所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則有三個含義,構成了復義。
二、思考與不足
用新批評理論解讀文學作品往往關注的是作品的語義,而具體到現代詩歌,解讀則會集中于現代詩歌中那些復雜且矛盾的語詞,從中挖掘其深意,并加以細致的解讀,揭示這些語詞中所蘊含的反諷、悖論、隱喻等手法,從而感受詩歌語言的魅力,以及語言背后所蘊含的深意。新批評不失為現代詩歌較為新穎的解讀方式,但是就落實于文本進行分析時,仍有缺憾:新批評強調以本文為基,則會導致過多地關注文本,研討文本,從而忽視文本之外因素的影響,例如作者生平及寫作背景等等,這樣的解讀與分析無法做到全面深刻。放眼于語文教學中,任何一篇文學作品的解讀一定離不開作者生平及時代背景,語文課程標準強調“知人論世”,如果“只知文本,無視其他”,很有可能無法理解詩歌的深層次含義,甚至是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