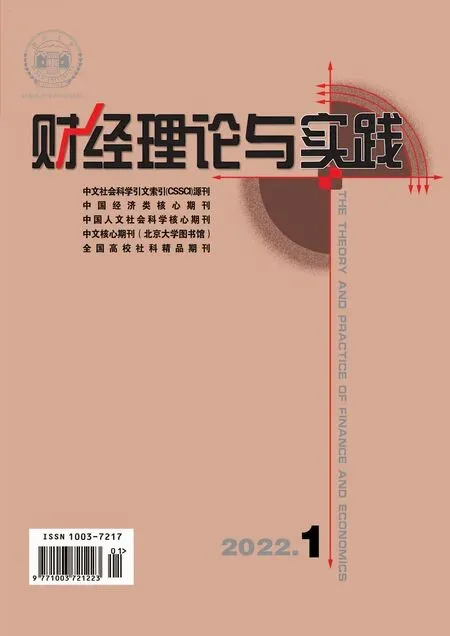“認本家”情結與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
尹律 戚振東 楊婧







作者簡介: 尹 律(1989—),男,江蘇南京人,博士,南京財經大學會計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內部控制評價;戚振東(1975—),男,安徽淮北人,博士,南京審計大學政府審計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審計理論與方法;楊 婧(1983—),女,新疆塔城人,博士,南京審計大學政府審計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治理、內部控制、審計基本理論。
摘 要:姓氏共享干預社會關系是一種文化現象,基于此視角,運用隨機效應的面板Tobit模型,選取2014—2020年我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數據,實證考察管理者姓氏尋宗的“認本家”情結對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影響。研究發現: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宗姓認同會降低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管理者共享小眾姓氏,或企業位于宗族勢力較強、外來文化沖擊較弱的地域,“認本家”文化的影響更加明顯。管理者同姓氏,一個時而隱匿、時而又闖入人們視野的社會關系,能夠產生潛在的經濟后果。
關鍵詞: 宗族文化;“認本家”情結;內部控制;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F239.4;F8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2)01-0081-06
一、引 言
差序格局下的人際關系網絡中,由底蘊深厚的宗族文化形成的社會關系,能夠克服正式制度的缺陷,保障微觀經濟的運行,在市場資源的配置中發揮重要的作用[1]。我國對宗族傳統的研究由來已久,在家族文化中,姓氏是一條重要紐帶,能實現社會關系的外延,它不僅將家族成員聯系在一起,還可能將家族成員外的同姓人群聚集起來,進而成為他們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工具。歷經無數年的歷史延續,逐漸衍生出陌生個體基于共同姓氏“認本家”的現象:同姓個體在社會交往活動中秉承“五百年前是一家”的理念,通過共同的姓氏形成宗姓認同,實現對彼此身份識別,構成遠近親疏的心理定勢。當經濟或政治層面發生利益糾葛時,這種現象顯得尤為明顯。當前市場中活躍著的宗族組織,如店商以姓氏命名,帶有家族色彩的家鄉會、同鄉會等都是很好的例證,部分家族組織甚至建立專門的網站平臺,記錄宗族的發展軌跡以及協同宗族近期的活動[2]。因此,姓氏受到理論界的廣泛關注。學者們普遍認為,姓氏作為研究家譜的工具,能夠揭示個體的DNA信息,甚至會引發族群歧視[3];姓氏可能產生聲譽連帶效應,即以其主人的姓氏命名的公司,對同姓氏員工似乎更具吸引力[4];此外,姓氏還被作為裙帶關系的代名詞運用于財務等其他領域[5]。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產品孕育而生,這為文化與會計融合研究的開展提供了理想的情境,亦為學界更好地理解中國特色的組織治理活動及其人文背景提供了可能。越來越多的經驗證據表明,管理者的年齡[6]、任期[7]、性別[8]等特征影響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姓氏——一個人人皆有卻極易被忽視的社會符號,亦能產生類似的經濟后果:姓氏不僅可以被用來識別宗族本源[9,10],還具有社會認同效應,能夠喚起同姓管理者的“認本家”情結。宗族文化作為一項非正式制度[11],可以為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提供合理的解釋。
二、理論構建與研究假設
社會關系中對人的分類標識通常被劃分為顯性和隱性兩類,前者包括性別、年齡、出生地、種族和民族等,后者包括學歷[12]、觀念和性格特征等。姓氏共享作為一個顯性的社會關系,和其他類型的社會關系存在異同:其一,姓氏共享與隱性社會關系之間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換句話說,個體出生時,血統決定姓氏,因此,就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而言,姓氏共享本身更加具有外生性。每個姓氏背后可能都擁有一段記載特定群體榮辱成敗的歷史經歷,因此,姓氏不僅是某個群體的身份象征,它還可以喚起共享者之間的情緒反應,讓他們感受到強烈的親情和家族內引力。其二,姓氏共享比其他類型的社會關系更加持久,因為其他類型社會關系的維護通常需要近距離的接觸或同其他組內成員的經常互動,而親屬關系在隔絕和靜止狀態下亦持續存在。其三,姓氏同兩個重要的人口信息——出生地和種族,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它們都可以觸發人們懷舊的思緒,同姓的個體很可能來自一個村莊、城鎮或某聚集地,當人們的焦點從“村”或“鎮”轉移到“縣”“市”或“省”這一級,出生地的概念容易弱化,而種族的尋根心結卻易固化起來。經過數百年的流動遷徙,同姓的個體分散在全國各地,甚至遍布許多國家,但其姓氏卻世代相承未曾改變。最初,人們可能通過姓氏來判斷個體的種族歸屬,但姓氏中蘊含的信息遠不止此。誠然,姓氏本身不直接代表企業治理中關注的個體技能或素質信息,但在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同姓本家擁有“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血緣聯系,這種歷代沿襲的身份認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會約束,為宗族文化因素涉足并影響企業治理提供了管道。
管理者的姓氏共享會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一方面,姓氏共享促進相互之間的理解、信任、溝通乃至信息共享[13],從而降低協調和監督成本。姓氏具有高度的可見性,為管理者的“抱團”提供便利。在此群體歸屬感的驅動下,同姓管理者的行為會默契地迎合共同的價值觀和規范,最大限度地規避分歧和潛在沖突[14],而內部控制也是一種降低代理成本、緩解代理沖突的機制。因此,姓氏共享可能提高管理者的溝通效率,進而提升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根據我國企業治理相關的規范性文件,董事長屬企業董事會成員,致力于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與股東的利益取向不悖。總經理屬高級管理人員,其利益函數可能和股東的有別,兩者均屬企業的關鍵管理者[15]。同姓管理者傾向于彼此信任,如果涉及個人或集體的利益,他們甚至會勾聯在一起,對損害利益的行為進行道德批判——如上所述,姓氏因其歷史悠久、呼之欲出的社會和文化底蘊而形成強大的親和力,即便董事長和總經理非親非故,同姓關系也能夠誘發兩者間親密的情感,這種交往是“群體思維”的先驅[16]。然而,成為盟友的同姓董事長和總經理在組織和領導內部控制的日常運行時,容易凌駕于管理層的其他成員之上,他們不太輕易接受另類的觀點。長此以往,企業決策中科學民主的和諧氛圍就會打破,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內部控制建設效率的提升構成阻礙。
可見,管理者的姓氏共享與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值得研究,故提出如下對立的研究假設:
假設1 同姓管理者的“認本家”情結可能提升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
假設2 同姓管理者的“認本家”情結可能降低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
三、數據來源及變量說明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選取2014①至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樣本并做出如下篩選:其一,剔除金融行業(依據2012版證監會行業分類,包括貨幣金融服務、資本市場服務、保險業和其他金融業等)的公司;其二,剔除家族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可能存在夫妻、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兄弟姐妹、堂兄弟、叔侄、爺孫等親緣關系);其三,剔除樣本區間內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公司;其四,剔除觀測值缺失的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測度數據源自DIB迪博數據資訊,管理者個人資料和財務數據源自國泰安數據服務中心,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上進行縮尾處理,篩選后共獲得7425個觀測值。
(二)變量說明
1.自變量:設置姓氏(Surname)虛擬變量,如果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姓氏相同,取值為1;否則,為0。
2.因變量:采用內部控制指數的千分數(Ic)測度內部控制有效性。該指數圍繞上市公司合法合規、報告、資產安全、經營、戰略五大目標的實現程度進行設計,將內部控制缺陷作為修正變量,形成由基礎層級、經營層級、戰略層級和修正指數構成的量化體系。
3.控制變量:選取經營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報酬率(Roa)、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董事會規模(Board)、獨立董事比例(Indep)、股權集中度(Balance)、審計意見(Opinion)、成立年限(Age)等[17]。另設置年度虛擬變量控制時間效應。
4.構建隨機效應面板Tobit模型②,如式(1)所示。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1的描述性統計顯示,內部控制有效性(Ic)的平均值為0.604,中位數為0.656,標準差為0.189,說明各家企業之間的內部控制有效性可能存在較大差異;董事長和總經理為同姓“本家”的樣本占比為4%,說明我國的姓氏數以百計,各個姓氏人口占比相對較小,導致兩個同姓個體共事的概率偏低。
(二)主回歸結果
表2中,列(1)為運用內部控制總指數回歸的結果,虛擬變量Surname的系數為-0.021,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降低了企業的內部控制有效性,假設2成立。列(2)~(6)為運用內部控制分項指數回歸的結果,列(3)中虛擬變量Surname的系數為-0.020,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列(6)中虛擬變量Surname的系數為-0.017,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降低了企業財務報告及其相關信息的真實完整性,阻礙了企業發展戰略的實現進程。列(2)、(4)和(5)中虛擬變量Surname的系數分別為-0.015、-0.022和-0.041,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對“經營管理合法合規”“資產安全”“提高經營效率和效果”等企業內部控制目標的負面影響不大。
(三)穩健性檢驗
1.Placebo檢驗。
上述結果顯示,內部控制有效性會因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而下降。假定在特定年份,其他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這些企業的兩大關鍵管理者實際上為異姓),是否依然能夠發現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與內部控制有效性的顯著相關?若不能,則表明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確實是導致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下降的因素之一;反之,則表明內部控制有效性下降的現象在董事長和總經理非同姓企業也存在,管理者姓氏并非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的解釋變量。
運用Stata計量軟件進行安慰劑檢驗,為每位高管隨機分配姓氏,將虛擬的姓氏一致性變量同對應企業的內部控制有效性利用模型(1)重復回歸100次和500次[18]。結果顯示,系數顯著為正和顯著為負的占比差異較小(100次模擬時分別為9%和2%,500次模擬時分別為6.2%和3.8%),意味著處理效應并不存在,確實是姓氏一致性(而非其他因素或噪聲)降低了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本文主要結論的穩健性得以驗證。
2.PSM檢驗。
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企業與非同姓企業的治理水平向來有別。針對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問題,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依據經營規模、成立年限、股權集中度、獨立董事比例、管理者性別③等特征,為姓氏一致性企業1∶1匹配出相應的非姓氏一致性企業,再用配對后的樣本進行實證檢驗,Surname的系數為-0.031,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即主要結論未發生改變(見表3)。
五、進一步分析
(一)小眾姓氏更加“認本家”
心理學理論認為,姓氏在社交網絡中扮演的角色取決于其稀缺性。小眾姓氏共享使得素昧平生的兩個人在市場中偶遇時產生一種特殊的親和力。因此,相對共享大眾姓氏的管理者,共享小眾姓氏的管理者更加有可能在會計決策中相互妥協,成為盟友。為測試小眾姓氏是否會更加認同“本家”,將Surname變量劃分為三類,分別設置Common(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且為大眾姓氏④取1)和 Rare(董事長和總經理同姓且為小眾姓氏取1)兩個虛擬變量,以董事長和總經理不同姓為參考基準,將Common和Rare同時加入計量模型進行回歸。結果顯示(見表4),Rare的系數為-0.029,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Common的系數為-0.003,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相對于小眾姓氏管理者之間有強烈的認同感,大眾姓氏管理者之間的認同感較弱(0.003<0.029),后者對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影響不明顯。
(二)宗族勢力干預和外來文化沖擊
個體的成長環境對于其價值觀的形成具有深遠影響,如果個體成長于宗族文化較為深厚的地域,耳濡目染,其習慣思維和價值觀念會有意無意地打上宗族文化的烙印,更加容易與“本家”形成身份認同。考慮到我國的企業通常在當地招募管理者,基于區域宗族勢力的頑固程度,將企業總部所在省份分成“強”(廣東、廣西、福建、江西)、“弱”(黑龍江、吉林、遼寧)和“中”(其他)三組[19],這種分類迎合“北方人比南方人獨立”的現實[20]。定義啞變量Clan,如果企業注冊在宗族勢力頑固的省份,賦值1;否則,賦值0。結果顯示(見表5),交互項Surname×Clan的系數為-0.047,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相對家族勢力不頑固的省份,在家族勢力頑固的省份,管理者同姓氏對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抑制作用更加顯著。
換一個角度分析,姓氏一致性對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抑制作用源自幾千年歷史文化積累形成的群體意識,這同西方文化強調的個人自由主義形成悖論。相對而言, 在法律體系建設較早且較為健全的國家,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顯著[21]。外來文化沖擊是否會影響我國傳統的姓氏文化對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抑制效應?依據企業所在地是否為改革開放的試點城市⑤,將企業劃分為兩組,結果顯示(見表6),在非改革開放試點城市組,Surname的系數為-0.034,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在改革開放試點城市組,Surname的系數為-0.018,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外來文化沖擊會削弱同姓個體之間的身份認同,進而阻礙姓氏一致性對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抑制作用的發揮。
六、結論和啟示
姓氏作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符號,在我國的宗族文化土壤中發展出個體基于共同姓氏“認本家”的現象。從同姓管理者“認本家”的微觀視角切入,考察宗族傳統“是否影響”以及“如何影響”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現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宗姓認同對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產生負面影響,即董事長和總經理的宗姓認同會降低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董事長在經營過程中擁有更高的話語權,其和同姓總經理形成的信任關系,降低了兩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他們以共同利益為導向,提高工作目標的一致性,對有損共同利益的行為形成道德批判。研究結論在解決可能的內生性問題后依然成立。進一步考察宗姓認同在不同情境下對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差異化影響,發現:共享小眾姓氏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更加認同“本家”;外來勢力對宗族文化的傳承造成較大的沖擊,當企業位于宗族勢力頑固的地區時,宗姓認同的影響較為明顯。
從以上結論得到以下啟示:一方面,文化是市場參與者構建人際信任、擴展關系邊界的重要依據,看似尋常的文化現象的背后往往蘊藏獨特的信任模式和合作方式,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企業內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實施等治理過程;另一方面,我國數千年的歷史演進孕育出種類繁多、內涵豐富的文化遺產,形成諸如“認本家”等普遍卻常被忽視的傳統文化現象。因此,要注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并在此視域下探索提升企業內部控制效能的路徑,形成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相互制衡的市場保障機制。同時,也要注意抑制本家文化中的負面因素和逆勢影響,防范其在高管群體中的裙帶關系、利益輸送和不健康的非正式組織活動,出現管理的“雙標”,干擾和削弱內部控制機能的正常效力。
注釋:
① 根據財政部和證監會《關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類分批實施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的通知》,自2014年起,主板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和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均納入強制披露范疇。
② 影響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因素較多,如管理成熟度(生命周期)、人員素質、信息技術、董事會和監事會會議次數、事務所類型(是否為“四大”或“十大”)、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超速或常規)、企業違規情況等。鑒于此,考慮個體效應,使用隨機效應的面板Tobit回歸。同時,似然比(LR)檢驗結果強烈拒絕原假設“H0:σu=0”,也認為個體效應是存在的。
③ 考慮到籍貫非必須披露的信息,故選擇管理者的性別(董事長和總經理同性,賦值1;否則,賦值0)作為匹配變量。
④ 根據公安部發布的統計數據表明,“王”(7.1%)、“李”(6.96%)、“張”(6.42%)、“劉”(5.16%)、“陳”(4.26%)、“楊”(2.97%)、“黃”(2.16%)、“趙”(2.03%)、“周”(1.88%)、“吳”(1.78%)屬大眾姓氏,這些姓氏均為超過2000萬的中國人所享有。
⑤ 第一批次試點城市為: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第二批次試點城市為: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
參考文獻:
[1] 戴亦一,肖金利,潘越.“鄉音”能否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基于方言視角的研究[J].經濟研究,2016(12):147-160,186.
[2] 潘越,寧博,戴亦一.宗姓認同與公司治理——基于同姓高管“認本家”情結的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9,19(1):351-370.
[3] Kumar A, Niessen-Ruenzi A, Spalt O G. What’s in a name? Mutual fund flows when managers have foreign-sounding names [J].Review of Finance Studies, 2015(28):2281-2321.
[4] Belenzon S, Chatterji A K, Daley B. Eponymous entrepreneur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107): 1638-1655.
[5] Du X. What’s in a surname? The effect of auditor-CEO surname sharing on financial misstatement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9, 158(3):849-874.
[6] Lin Y C, Wang Y C, Chiou J R, et al.CEO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4, 22(1):24-42.
[7] Campbell S, Li Y, Yu J, et al.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community on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39(2):1-15.
[8] Chen Y, Eshleman J D, Soileau J S. Board gender divers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J]. Advances in Accounting, 2016, 33:11-19.
[9] Giannetti M, Zhao M. Board ancestral diversity and firm-performance volatility [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9, 54(3):1117-1155.
[10]Jung J H, Kumar A, Lim S S, et al. An analyst by any other surname: surname favorability and market reaction to analyst forecasts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9, 67(2-3):306-335.
[11]Piotroski J D, Wong T J. Capitalizing China: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J]. NBER Chapters, 2012, 47:201-242.
[12]Gu Z, Li Z, Yang Y G, et al. Friends in need are friends indeed: an analysis of social ties between financial analysts and mutual fund managers [J].Accounting Review, 2019, 94:153-181.
[13]Gompers P A, Mukharlyamov V, Xuan Y. The cost of friendship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6, 119(3):626-644.
[14]Van Peteghem M, Bruynseels L, Gaeremynck A. Beyond diversity: a tale of faultlines and frictions 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J]. Accounting Review, 2018, 93(2):339-367.
[15]王俊,吳溪.管理層變更伴隨著更嚴格的內部控制缺陷認定標準嗎?[J].會計研究,2017(4):81-87.
[16]Ishii J, Xuan Y. Acquirer-target social ties and merger outcomes [J].Financial Economics, 2014, 112(3):344-363.
[17]池國華,郭芮佳,王會金.政府審計能促進內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嗎?——基于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J].南開管理評論,2019,22(3):31-41.
[18]潘越,翁若宇,劉思義.私心的善意:基于臺風中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新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7(5):133-141.
[19]Tan Y C, Xiao J, Zeng C, et al. What’s in a name? The valuation effect of directors’ sharing of surnames [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21(122): forthcoming.
[20]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et al.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J].Science,2014, 344(6184):603-608.
[21]劉超,阮永平,劉溢華.同姓關系對高管在職消費的影響研究[J].管理學報,2019,16(12):1781-1789.
(責任編輯:寧曉青)
3288501908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