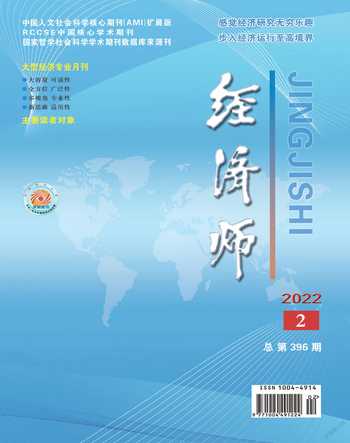基于微信平臺的商科課程全生態管理實證研究
顧靜 姜金德 張婧
摘 要:微信作為國內使用最為廣泛的社交媒體軟件,在移動學習、社交學習上的優勢明顯。微信平臺支持下的商科課程全生態管理實施方案,包括課程公眾號、知識服務公眾號與傳統教輔相結合的課程資源設計,基于雨課堂和微信群的課程互動設計和遵從團隊發展規律、構建自適應性學習共同體的協作式教學策略。通過教學實踐的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微信平臺支持下的討論交流對同學關系、師生距離、學習氛圍、課內學習輔助、課外學習輔助均具有正向影響,其中同學關系與課內輔助對課程教學效果的影響顯著。
關鍵詞:移動學習 社交學習 商科教育 虛擬學習社區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22)02-204-04
一、引言
2015年《地平線報告》指出,未來的在線學習將更加社交化。國內外研究人員發現,學習的社交化有利于學習績效的提升。Rau等人指出,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流行的知識分享、集體學習的在線平臺。Greenhow認為,社交媒體能幫助學習者與他人進行更為有效的溝通,幫助他們分享觀點、構建認知和收獲反饋。由此可見,將社交媒體運用于教育信息化新模式的構建、運用于混合式學習、翻轉課堂具有廣泛的理論基礎。而微信作為一款國內流行的、具有社交、通信和平臺化功能的手機應用,在移動學習領域的優勢不可估量。
目前,關于微信在教育信息化中應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信的應用模式、微信學習平臺的設計、微信學習資源的設計、微信學習的互動模式、基于微信的移動學習等,大多從某一門課或微信的功能特點出發,從技術角度謀求適合教學。而對微信運用于課程管理的普適性研究較少,實證研究就更少。本文基于目前各高校仍以傳統教學為主的現實情況,提出微信平臺支持下的商科課程全生態管理實施方案,包括課程資源的設計、課程互動的設計以及構建自適應性學習共同體的協作式教學策略設計。最后通過三個班級的實證數據,驗證微信社交軟件在課程全生態管理中的作用機制。
二、理論回顧
(一)移動學習
移動學習是隨著無線通信技術的發展而興起的一種新型學習方式。Alexzander Dye認為,移動學習是在移動設備幫助下,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發生的學習,移動學習中使用的設備必須有效呈現學習內容,并且提供教師與學習者之間的雙向交流。移動學習者采用“碎片化”的學習方式,一般很難長時間保持注意力的集中,這就要求學習資源必須“微型化、顆粒化”。鑒于此,基于微信的移動學習資源設計應遵循碎片化原則,將知識點進行拆分。此外,為保證學習者在利用零碎時間學完所有片段后能掌握一個相對完整的知識點,這要求各片段組合背后具有一個完整的知識框架。
(二)基于社交媒體的學習
基于社交媒體的社交學習具有學習性和社交性雙重功能,學習者借助社交媒體建立社交關系,通過交流互動、知識分享、協作學習形成集體智慧,提高學習績效。一些研究表明,社交媒體的應用使非正式學習、碎片化學習成為可能。茆意宏以微信平臺為例,對大學生微知識學習行為的過程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大學生會通過微信獲取知識、交流學習心得,并存在一些深度學習行為。微信可以給人帶來內容滿足感、社會滿足感和快樂滿足感,有助于學習者社會化、增強自我認同和交往能力。高校可以利用微信等平臺開展微知識服務,以更新教學模式,提高知識服務水平。
(三)虛擬學習社區
虛擬學習社區由虛擬社區的定義發展而來,它是以知識傳播為目的的虛擬社區。Hilts和Wellman認為虛擬學習社區具有雙重功能,一是幫助師生完成學習目標,二是為學習者提供信息交流的平臺。Lewis和Allan(2005)認為,虛擬學習社區通常包括如下特征:共同的目標、共享的資源、成員自主、高度的溝通、交互和協作、信息共享、知識建構、知識遷移。過去,虛擬學習社區多指師生利用課程網站進行在線學習時所形成的社會群體。但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尤其智能手機普及后,移動學習、基于社交媒體的學習形成了更有活力的虛擬學習社區,為正式和非正式學習小組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知識傳播環境。
三、微信平臺支持下的課程全生態管理實施方案
基于微信在移動學習、社交學習、構建虛擬學習社區中的運用,本文提出了微信平臺支持下商科課程全生態管理的實施方案,包括課程公眾號、知識服務公眾號與傳統教輔相結合的課程資源設計,基于雨課堂和微信群的課程互動設計和構建自適應性學習共同體的協作式教學策略。如圖1所示。全生態主要指微知識載體的多樣性、微知識服務的全程性和微信群聊溝通的自組織性。
(一)公眾號微知識與傳統教輔相結合的課程資源設計
課程資源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針對課程建立的微信公眾號,將章節按主要知識點進行切分,在課程公眾號中進行編輯,并通過目錄的形式索引,方便學生查閱。每個知識點都可以作為一篇小文章或微視頻進行發布,并通過鏈接形式跳轉到相關知識點,形成知識之間的關聯。第二類為相關知識服務公眾號的媒體資源,這類教學資源時效性高、實踐性好,教師通過篩選發布給學生,可以作為課堂案例、課后閱讀資料或作業題材使用。第三類為課程幻燈片、習題、電子書等教輔資料,通過課程群或基于微信的智能教學工具(例如雨課堂)進行發布,方便學生在課上及課后隨時隨地閱覽。
(二)基于雨課堂和微信群的課程互動設計
課程互動主要通過雨課堂和微信群聊來完成。雨課堂通過上課點名、測驗、投票、彈幕、紅包等手段活躍課堂氣氛,引進競爭機制,加強群體學習效果。微信群則構成了課下的三維虛擬學習環境,方便師生分享學習資料、進行討論和社交。傳統教學模式下,師生互動大部分發生在課堂上,為一對多關系。這容易導致學生與老師之間溝通少,激勵不足。學生之間除了上課時集中,其它時間均為獨自學習,容易產生孤獨感。通過雨課堂、微信群為學生提供一個虛擬學習社區,將增進師生、生生之間的情感紐帶,形成歸屬感。師生在討論、協作過程中,完成知識共享、遷移,最終內化。整個溝通過程中,教師的中心位置逐漸淡化,形成多中心的網絡結構和學習共同體。
(三)構建自適應性學習共同體的協作式教學策略
在教學策略方面,基于目前各高校仍以傳統教學為主的現實情況,本文提出了以微信作為信息載體對課程進行全生態管理的個性化實施過程。首先,教師可以自行決定微信在課程中的介入程度。例如,是否一次性建立針對課程的公眾號,或者分計劃逐步完成。又如,雨課堂在課上的運用程度和微信群的互動程度如何。這都由課程性質和老師的教學風格、教學資料積累決定。
教師在運用微信進行課程管理時,要遵循團隊發展的四階段特征:形成期、風暴期、規范期和績效期。在形成群聊(團隊)初期,多發起話題,相互熟悉認識、導入課程、介紹前沿發展,形成課程學習的目標和愿景,增強團隊凝聚力。在風暴期,團隊成員容易對課程內容、老師的教學方法產生疑惑,學習熱情消退。此時,教師需要與學生充分溝通學習中遇到的問題,共同提出解決方案,抓住一切機會鼓舞士氣,樹立典型。在規范期,學生團隊榮譽感很強,在群聊中無私分享各類知識和觀點,展開協作,表現出很強的主觀能動性。在這一階段,老師要多給學生一些挑戰性任務,加大知識注入,適時加以點評和指導。在績效期,學生已經形成了學習共同體,能夠相互學習、群策群力,知識傳播鏈路將更加多元化。此時,教師需要從更高的層面引導學生,采用基于問題的學習、基于項目的學習、研究導向型學習方法,鍛煉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科學研究能力。
微信作為信息載體可以在此過程中發揮多種作用,首先,公眾號的微知識為學生提供了課前預習、課后復習的素材,為翻轉課堂和移動學習提供了應用基礎。其次,基于雨課堂的智能教學工具,可以在課堂上與學生互動,分享幻燈片和練習題,并展開現場投票,活躍課堂氣氛。最后,微信群形成的虛擬學習社區是一個自適應性的學習共同體,它伴隨團隊的成長不斷成熟完備,最終形成自身的知識分享、傳播、加工、吸收機制,對課程知識資源庫產生貢獻。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討論
(一)問卷調研與統計描述
為了驗證微信在商科課程全生態管理中的效果,實證部分選擇了兩門課程作為樣本展開了調研分析。一門課程為物流信息管理,共有2個教學班級,每班78人;另一門課程為項目管理,共1個教學班級39人。調研問卷就師生距離、互動交流、學習氛圍、知識分享、同學關系、課程管理效果等問題進行提問,采用1—5分的likert量表,分別代表非常不贊同到非常贊同。通過網上問卷發放,共回收有效問卷124份,回收率為63.6%。對于各題項的統計描述信息,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基于微信的商科課程全生態管理在師生距離、討論交流、知識分享、同學關系、課程教學效果上均獲得了較為滿意的評分(>4),其中在知識分享、師生距離、討論交流上的分數最高,分別為4.35、4.26和4.23.
(二)模型構建與仿真結果
為了進一步探究微信在商科課程全生態管理中的作用機制,利用AMOS建立了結構方程模型,如圖2所示。模型適配度指標CMIN/DF=17.938,RMR=0.094,GFI=0.770,RMSEA=0.371,NFI=0.82,RFI=0.58,IFI=0.828,TLI=0.594,CFI=0.826,擬合參數不理想。
根據表2中路徑系數的顯著性水平和表3中的模型修正指數(Modification Index)來進行模型修正,除去回歸系數不顯著的路徑,增加可測變量的殘差變量之間的相關路徑,最終得到修正的模型,如圖3所示。
根據正態性檢驗的結果,各變量的偏度小于3,峰度小于8,可以認為服從正態分布。預設模型的卡方值為20.861,自由度為11,顯著性水平p=0.035,接受虛無假設,理論模型和實際數據可以契合。模型的適配度指標CMIN/DF=1.896<3,PMR=0.042<0.05,RMSEA=0.085<0.1,GFI=0.957,NFI=0.978,RFI=0.959,IFI=0.990,TLI=0.980,CFI=0.990,均大于0.9,PNFI=0.512,PCFI=0.518,均大于0.5,說明整體模型適配良好。
模型估計得到的路徑系數如表4所示,所有路徑在P<0.001的水平下顯著。由圖3中的標準化回歸系數可知,基于微信的討論交流對同學關系、師生距離、學習氛圍、課內學習輔助、課外學習輔助均具有正向影響,其中對學習氛圍(0.93)、師生距離(0.91)和同學關系(0.84)的影響最大。微信討論交流通過加強同學關系、課內輔助對課程教學效果發生影響。
(三)結果討論
實證結果表明:
1.師生借助微信平臺構建了學習共同體,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溝通交流、分享學習資源、共同完成學習任務,從而在成員之間形成了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人際關系。但其中,只有學生之間的關系對課程教學效果影響顯著,這說明去中心化的網絡結構,即改變以老師為核心的單向知識傳播模式,有助于提升學習績效。
2.通過微信形成的虛擬學習社區,減少了學生獨立學習的孤獨感,增進了學習動機和責任感;學生之間相互支持和依賴,交流顯、隱性知識,形成知識傳播的有效環境,加深了對知識的理解,提高了認知水平,使之學會學習。
3基于微信的學習具有社交性,根據情境學習理論和關聯主義理論,借助社交媒體建立社交關系,通過溝通交流、知識分享建立情感,可以形成良好的學習氛圍。
4.根據模型檢驗,微信課內輔助對課程教學效果作用顯著,而課外輔助不顯著。這說明學生基于微信的學習更多地發生在課堂上,但課內輔助與課外輔助具有一定的相關關系,教師可以由課內推及課外,逐步增加課外學習的資源、要求和難度。
[基金項目:2019年南京曉莊學院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課題項目“OBE理念下應用型本科物流管理專業能力架構研究”]
參考文獻:
[1] 唐承鯤,徐明.基于社交媒體合作學習效果的影響要素與實現機制分析[J].遠程教育雜志,2015(6):32-38.
[2] Kabilan M K, Ahmad N, Abidin M J Z. Facebook: An online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of English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J].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010,13(4): 179-187.
[3] 彭學軍.微信公眾號+翻轉課堂的創新型教學模式研究——以數據庫基礎課程為例.職教論壇,2017(15):77-80.
[4] 范文翔等.移動學習環境下微信支持的翻轉課堂實踐探究.開放教育研究,2015,21(3):90-97.
[5] 姚潔.微信雨課堂混合學習模式應用于高校教學的實證研究.高教探索,2017(9):50-54.
[6] 徐梅丹.構建基于微信公眾平臺的混合學習模式.中國遠程教育,2015(4):36-41.
[7] 朱學偉等.微信支持下的移動學習平臺研究與設計.中國遠程教育,2014(4):77-83.
[8] 王萍.微信移動學習平臺建設與應用.現代教育技術,2014,24(5):88-95.
[9] 邱炳發等.微信支持下的移動學習資源設計研究.現代教育技術,2016,26(3):115-120.
[10] 蔣志輝等.基于微信的“多終端互動探究”學習模式構建與實證研究.遠程教育雜志,2016(6):46-54.
[11] 李曉霞.基于微信的移動學習研究.教學與管理,2016(8):75-78.
[12] 羅潔.信息技術帶動學習變革——從課堂學習到虛擬學習、移動學習再到泛在學習.中國電化教育,2014,(1):15-21.
[13] 茆意宏.大學生微知識學習行為研究——以微信平臺為例.情報理論與實踐,2016,39(11):68-77.
[14] Hiltz.R and Wellman. Asynchronous Learning network as a Virtual Classroom[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3 ,40(9):44-49.
[15] Lewis,D.&Allan,B.(2005).Virtual Learning Communities: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M] .Maidenhead:Ope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單位:南京曉莊學院商學院 江蘇南京 200171)
[作者簡介:顧靜,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項目管理與風險控制;姜金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為項目管理與供應鏈管理;張婧,博士,講師,研究方向為物流管理。]
(責編:賈偉)
3389501908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