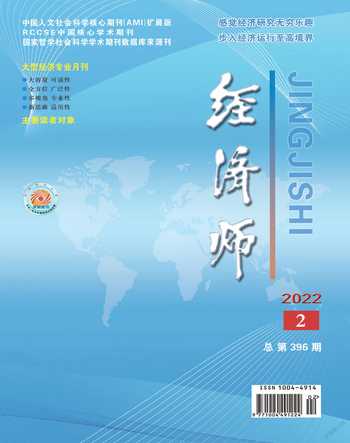就業壓力對大學生職業探索的影響:職業決斷力的中介作用
摘 要:職業探索對個體職業發展至關重要,有關就業壓力和職業探索關系背后的機制研究還比較缺乏。鑒于此,文章以2106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就業壓力對職業探索的影響,以及職業決斷力在二者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發現:(1)就業壓力與職業探索呈顯著負向關系;(2)職業決斷力在就業壓力和職業探索之間起完全中介的作用。
關鍵詞:就業壓力 職業探索 職業決斷力
中圖分類號:F240;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22)02-253-03
一、問題的提出
大學生就業關系著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和復雜,就業壓力逐漸增大,就業難度日益突出,就業問題日益增多[1]。在無法改變外部環境的情況下,對大學生自身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其對自我有更加清晰和明確的認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尋求適合自己的職業,即提升職業探索水平[2]。
職業探索是指個體為實現職業目標而采取的一種心理或身體活動,包括對信息尋求,對自我和環境的認識[3]。實證研究也表明,有過職業生涯探索的個體在工作后,會體驗到更高的滿意度、工作效能感和職業成就感[2]。鑒于職業探索對個體職業發展的重要意義,了解職業探索的影響因素顯得尤為重要。故職業探索的發展必然與內部特質和外部環境相關。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對職業探索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例如:五大人格[4]、父母教養方式[5]等。但是較少探討了就業壓力這一個體職業探索的影響及機制作用。
就業壓力是指個體面對求職、擇業時受內部或外部就業壓力源影響而引起的生理、心理和行為的應激過程[6]。一方面,當個體感知到較大的就業壓力時,很可能選擇逃避就業,表現出退縮行為,因而職業探索動機和行為較少。另一方面,就業壓力可能通過影響個體的認知評價,進而對其職業探索活動產生影響,例如,職業決斷力。
職業決斷力是指個體感知到自己能沖破限制條件做出職業選擇的能力[7]。不同程度的就業壓力會影響個體對于自己能沖破限制條件做出職業選擇能力的判斷。職業決斷力水平高的個體,即使在擇業過程中面對外部眾多職業障礙,也相信自己的能力水平,對自身評價較高,具有積極的自我概念,從而對職業探索這一活動產生動機[8]。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探討以下問題:第一,就業壓力和職業探索是否存在負向關系;第二,職業決斷力是否在就業壓力與職業探索兩者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2106名高校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男生為991 人,占比47.1%,女生為1115人,占比為52.9;平均年齡20.12歲(SD=1.60),大一627人,大二485人,大三473人,大四521人;文史類專業為66人,理工類專業為1864人,其他專業為176人。
(二)研究工具
1.就業壓力量表。采用劉微微[9]編制的就業壓力量表來測量被試的就業壓力狀況。該量表共19個題項,分為4個維度,分別為:“心理預期”“挫折體驗”“家庭因素”“缺少求職幫助”。此量表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方式,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平均分進行分析,被試得分越高表示就業壓力越大。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32。
2.大學生職業決斷力問卷。采用張軍成等[8]編制的大學生職業決斷力問卷。該問卷共包含9個題項,分為3個維度,分別為:“職涯準備決斷力”“社會輿論決斷力”“職業環境決斷力”。該問卷采用李克特6點計分方式,從“強烈不同意”到“強烈同意”。采用平均分進行分析,分數越高,表示職業決斷力越強。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81。
3.職業探索量表。采用許存[10]修訂的職業探索量表來測量被試在過去3個月內的職業探索活動頻率。該量表共包含18個題項,共4個維度,分別為:“環境探索”“自我探索”“目的—系統探索”“信息數量”。該量表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從“很少”到“經常”。采用平均分進行分析,得分越高,表示探索積極性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63。
(三)數據處理
使用SPSS 22.0和Mplus 8.3對數據進行描述分析、相關分析、結構方程模型和中介效應的檢驗等。
三、研究結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與檢驗
本研究通過自我報告的方式收集數據,因此,結果可能會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因此,首先采用匿名施測、加設反向題等方式從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其次,采用Human單因子檢驗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統計檢驗。結果表明未旋轉得到8個因子,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9.45%,小于40%的臨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研究變量之間的相關
研究變量及其維度的描述性統計及相互之間的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就業壓力與職業決斷力(r=-0.27,P< 0.01)、職業探索(r=-0.22,P<0.01)顯著負相關,職業決斷力和職業探索呈顯著正相關關系(r=0.62,P<0.01)。
(三)測量模型檢驗
在建立結構方程模型之前,先對測量模型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測量模型擬合良好,擬合指數如下:χ2=192.498,df=51,χ2/df=
3.774,CFI=0.990,TLI=0.987,RESEA(90%CI)=0.036(0.031,0.042)
,SRMR=0.031。每個項目包在其所屬潛變量上的負荷均在0.70以上,說明打包之后形成的項目包能夠較好地表征其對應的潛變量。
(四)結構方程模型檢驗
以就業壓力為自變量,職業決斷力為中介變量,職業探索為因變量,建立結構方程模型。結果顯示,結構方程模型擬合良好(χ2=274.745,df=51,χ2/df=5.387,CFI=0.990,TLI=0.987,RESEA
(90%CI)=0.046(0.040,0.051),SRMR=0.031)。如圖1所示,就業壓力對職業探索的直接預測作用不顯著(β=-0.025,P>0.05),就業壓力負向預測職業決斷力(β=-0.316,P<0.001),職業決斷力正向預測職業探索(β=651,P<0.001)。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參數Bootstrap法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抽取5000個樣本,結果顯示,職業決斷力在就業壓力與職業探索之間的中介作用顯著(ab= -0.205,SE=.022,95%CI=[-0.249,-0.161])。
四、討論
本研究探討了就業壓力對職業探索的影響,以及職業決斷力在二者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顯示,就業壓力與職業探索呈顯著負相關,就業壓力通過職業決斷力進而影響職業探索,并且職業決斷力發揮完全中介作用。
(一)就業壓力與職業探索的負向關系
本研究發現,就業壓力與職業探索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說明,就業壓力越大,職業探索水平越低。這可能是因為:較大的就業壓力,使個體產生了較高的應激水平,沒有有效的應對方式[11],沒有信心面對和解決當前問題,挫傷其積極性,促使個體通過退縮和逃避行為來進行自我保護,進而導致其職業探索水平降低。這提示我們,幫助個體緩解就業壓力,建立良好的應對方式,有助于其求職行為。
(二)職業決斷力完全中介就業壓力對職業探索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就業壓力通過職業決斷力進而影響職業探索。首先,就業壓力負向預測職業決斷力,即就業壓力越大,個體職業決斷力水平越低。這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一致[12]。職業決斷力強調個體認為自己能克服外界限制條件的主觀信念,是個體在了解外界情況,結合自身條件而做出的主觀判斷[10],因此,當外界條件改變時,自然會影響個體的判斷,尤其在外界限制條件與障礙增加時,可能會大大降低個體解決問題與克服困難的信心。因此,職業決斷力是解釋個體在面對就業壓力時能否獲得一份合適工作的關鍵因素。其次,職業決斷力正向預測職業探索,即個體職業決斷力水平越高,其職業探索積極性越強。職業決斷力高水平個體對解決擇業過程中的問題和克服困難充滿信心,因此,當預期進行職業探索,他們也傾向認為自己有能力突破眾多限制條件,獲取一份合適的職業,在未來工作中會有良好的表現。因此,職業決斷力高水平是促進個體積極進行職業探索的良好品質。這提示我們,培養個體職業決斷力能夠促進其職業探索。
綜上所述,就業壓力會通過影響個體職業決斷力,進而影響其職業探索。當就業壓力增強,個體職業決斷力可能隨之下降,進而導致職業探索水平增加。反之,當就業壓力下降,個體職業決斷力會增強,進而增強職業探索積極性和行為。
五、啟示與建議
本研究的結果為高校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提升大學生職業探索水平的途徑。第一,幫助個體緩解就業壓力,降低其對未來就業問題的恐懼、擔憂等,采取積極應對方式,減少退縮與逃避行為,進而提高其職業探索水平。第二,幫助大學生提升職業決斷力,進而促進其職業探索動機。第三,幫助大學生提早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提高求職、就業意識,明確就業目標,對照查缺補漏,發掘和培養自我才能,提高就業競爭力。第四,社會各界應增強對大學生就業的社會支持。通過以上行為來增強大學生職業決斷力與職業探索,進而推動其積極從事求職行為,逐漸實現職業成功。
參考文獻:
[1] 李春玲.疫情沖擊下的大學生就業:就業壓力、心理壓力與就業選擇變化[J].教育研究,2020,41(07):4-16.
[2] 程婧楠,劉毅,梁三才.大學生生涯適應力與職業探索:職業使命感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7,25(02): 237-240.
[3] ZHANG H, HUANG H.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mediates the peer support-career exploration relationship[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8,46(3): 485-498.
[4] LI Y, GUAN Y, WANG F, et al.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BIS/BAS traits as predictors of career exploration: The mediation role of career adaptability[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5,89: 39-45.
[5] 曲可佳,鄒泓,黃紹舒,等.父母教養行為、自主與大學生職業生涯探索的關系[J].心理發展與教育,2016,32(06):675-682.
[6] 劉芷含.大學生就業壓力與主觀幸福感:雙向中介效應[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9,27(02):378-382.
[7] DUFFY R D, DIEMER M A, JADIDIAN A. The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Work Volition Scale-Student Version[J].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12,40(2): 291-319.
[8] 張軍成,黃穎潔,張淑瑩,等.大學生職業決斷力的測量問卷與個體差異[J].心理技術與應用,2019,7(10):629-640.
[9] 劉微微.研究生就業壓力、就業力和就業質量關系研究——基于2020屆“雙一流”高校碩士畢業生的實證分析[D].華東師范大學,2020.
[10] 許存.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及其與焦慮、職業探索的關系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08.
[11] 孫世月,趙亮,陸曉玲,等.行業特色型高校本科畢業生就業壓力的調查與研究[J].中國林業教育,2018,36(06):22-28.
[12] ZHUANG J, JIANG Y, CHEN H. Stress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during COVID-19: A serial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21,49(8): e10551.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科文學院 江蘇徐州 221132)
[作者簡介:莊建鋒(1977—),男,漢族,江蘇睢寧人,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責編:若佳)
3434501908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