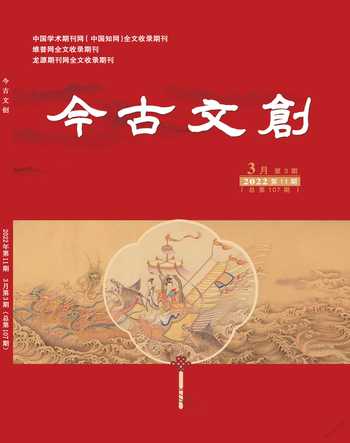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口含物研究
【摘要】 口含是中國一種古老的喪葬習俗,這種習俗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長江下游地區死者口中含物的傳統。最初的口含物以石器、貝類為主;后期逐漸改用玉類。長江下游地區是玉琀的主要發源地。以玉琀陪葬,既顯示著墓主人高貴的身份和地位,也是對死者的一種神化。
【關鍵詞】 口含物;葬俗;玉琀;長江下游地區
【中圖分類號】K87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1-0053-03
口含,即下葬時在亡者口中塞入米、粱、貝、珠、玉等物,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喪葬儀式。
當口含物為玉制成的,稱為“琀”,《說文解字》曰:“琀,送死口中玉也。”
目前關于口含的專門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文化角度對口含物的種類、含義或作用進行分析;二是從歷史角度對口含習俗的起源、發展及在等級制度下的演變進行考察。關于口含的文化內涵研究已比較充分,有大量的古代典籍可作為參考。但對于口含起源研究尚有不足,主要是對缺乏文獻記載的史前時期不夠重視,未充分挖掘和運用考古材料來追溯口含習俗最遙遠的起源。
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在死者口中含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在長江、黃河流域的一些新石器墓葬中都發現死者口中含有石塊、陶球、玉器等物。在整個新石器時代,長江下游地區出土的口含物,數量最多,分布也最廣。研究新石器時代的口含物補充了口含風俗發展歷程最初的一步。本文將運用考古學材料,再結合文獻記載,分析新石器時代的口含物有何特征與內涵。
一、新石器時代長江下游地區的口含物
長江下游地區發現的口含物數量較多,且分布的范圍和時間跨度較大。大致來說,以口含物的材質區分,可歸為兩部分。一是龍虬莊文化和北陰陽營文化,以骨珠、石球為典型器;二是馬家浜文化、三星村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以玉器為典型器。
(一)龍虬莊文化與北陰陽營文化的口含物
高郵龍虬莊遺址距今約6600—5000年。遺址第四層M140墓主人為一名性別不詳的少年,口中含有一枚骨珠[1]41。第四層M169死者為一名青年女性,陪葬物中有一枚卵石壓在下頜骨之下,考古學者推測可能原含于口中[1]66。第五層M103中埋葬的青年女性口中含有一個石球。石球材質為半透明白色石料,直徑1.4厘米,打磨得十分光滑[1]324。龍虬莊遺址第4層和第5層屬于第二期,年代距今約 6300—5500 年[1]379。
南京北陰陽營遺址時間稍晚于龍虬莊,距今約6000—5000年。在遺址出土了76粒瑪瑙石子,原產于南京雨花臺一帶,故又名雨花石[2]77。質地細膩,有不少色彩斑斕、花紋絢爛者。推測是北陰陽營居民特意從他處收集而來,用于觀賞和把玩。其中有一些發現于死者口中。
龍虬莊遺址和北陰陽營遺址出土的口含物,都是骨珠、石球一類的器物。通過人骨測量報告,在龍虬莊遺址和北陰陽營遺址的死者下頜骨上并未發現超過正常咀嚼形成的嚴重牙齒磨損。因此,龍虬莊和北陰陽營的骨珠、石球應當是死后放入嘴中。
(二)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玉質口含物
1.馬家浜文化的口含物
在上海青浦崧澤遺址M163墓主口中發現了一件管形玉器,材質為瑪瑙,青綠色,圓管形,管體不規整,器面有研磨痕跡,兩端截面不平,長1.6—2.1厘米、口徑1.3—0.9厘米[3]217。這件以玉制成的口含物年代距今約6000年,通過對死者口齒的觀察,為死后放入口中。這件玉管是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時代最早由玉制成的口含物。
2.三星村文化的口含物
江蘇金壇三星村遺址距今約6500—5500年,與馬家浜文化中晚期至崧澤文化早期相當。在遺址發現了兩件玉器,都位于死者口中。一件出土于M925,呈圓餅狀,材質為微透明乳白色石英石,器面光滑圓潤。直徑2.9厘米、厚0.7厘米。另一件出土于M860,為扁平三角形玉琀,三角中心穿一孔。材質為灰綠色葉蠟石,器表磨光。殘長2.7厘米、厚0.5厘米[4]。
3.崧澤文化的口含物
在崧澤文化上海青浦崧澤遺址出土了三件玉質口含物[5]37。M60:10出土于崧澤遺址崧澤文化第二期。呈扁平圓餅形,一側穿有一小孔。淡綠色,直徑4.1厘米。墓主為成年女性,隨葬器物13件。M82:4發現于第三期。呈圓璧形,淡綠色,直徑3.7厘米。墓主為中年男性,隨葬器物5件。M92:4發現于第三期。呈扁平雞心形,中間有一大孔,墨綠色,長4.2厘米。墓主似為一中年女性,陪葬器物10件。
崧澤遺址第二期M90的人骨樹輪校正年代為距今5860±245年,第三期的M87的人骨樹輪校正年代為距今5180±140年[6],可為這三件玉器的絕對年代稍做參考。
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遺址出土了一件崧澤文化時期的玉器[7]29。M12:1,發現于墓內人骨口的部位。材質為石髓。形狀呈扁平圓形,圓面邊緣有一小孔,與崧M60:10器型相似。直徑1.9厘米。M12:1的年代與崧澤遺址崧澤文化第二期相似[7]125。
在浙江嘉興南河浜遺址第一等級墓葬M27出土了一件玉璜,出土時位于墓主人的口中。材質為白色透閃石軟玉。呈扁平長條形,兩端略凸起,如凹字狀,兩端鉆小圓孔。長9.5厘米、寬1.4厘米、厚0.4厘米。M27共有隨葬品23件。玉器5件,陶器18件[8]117。M27為南河浜遺址崧澤文化晚期二段[8]109。崧澤遺址第三期M87所出土隨葬品與南河浜遺址崧澤文化遺存晚期二段偏晚的墓葬出土遺物相一致,距今約5100年。南河浜遺址崧澤文化晚期二段的大致年代范圍為距今5300—5100年[8]205。
4.良渚文化的口含物
良渚文化時期在福泉山遺址和廣富林遺址都有死者口中含玉。
福泉山遺址M139,在墓主人頭骨口內出土一件瑪瑙玉石。呈半球形,底面打磨平整,鉆有一對牛鼻形孔。顏色為半透明的淡咖啡色。高1.3厘米、直徑2厘米[7]93。墓主為一成年男性,在四肢上下分兩行放置了12件石鉞,另有彩繪陶器和玉器34件,在東北角墓坑外有一青年女子做人牲[7]60。該墓葬為福泉山遺址良渚文化第一期,為崧澤文化向良渚文化過渡時期,距今約5200—5100年[7]130。
另一件發現于M145。材質為灰白色透閃石,呈扁平舌形,平整一端穿有一孔。長4.85厘米、寬1.8厘米[7]93。全墓共計有石、玉、陶器26件。墓坑北面有一人殉坑,內有兩具人骨,一為兒童,一為青年女子。兩具尸骨都側身屈肢,面頰朝上,呈反縛掙扎狀[7]64。M145屬于福泉山良渚文化第二期,距今約5000—4900年[7]130。
在上海松江廣富林遺址M15出土一件玉錐形器,含于死者口內。材質為青白玉。兩面對鉆穿孔。長3.7厘米。墓主為一中年男性,隨葬器物12件,是該墓地隨葬器物較多的一座。該墓葬年代屬于良渚文化早期[9]。
以上所列出的玉器均是出土時發現于死者口中。通過人骨測量報告,均未發現死者齒面萎縮內收及齒面磨損甚重的現象,說明這些玉器為死后放入口中。由于大量墓葬人骨腐朽嚴重,無法辨別痕跡。所以,應當有不少口含物未被確認,它們的真實數量只會比現在掌握的要多。
二、口含物與“口含”所反映的喪葬觀念
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墓葬中所發現的諸多口含物是在人死后,往死者口里填塞進去的。從現有考古材料來看,這種在死者口中含以物的葬俗與后世的“口含”有諸多共性,當是“口含”的直接起源。
口含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記載,《禮記·雜記》曰:“含者又作唅。”《公羊傳·文公五年》載:“含者何?口實也。”故口含又名“口實”“口唅”。當口含物為玉制成的,稱為“琀”,《說文解字》曰:“琀,送死口中玉也。”6000年前馬家浜文化崧澤遺址出土的管狀玉器,是迄今所知最早用玉做成一定形式的器物含入死者口中的例證,是玉琀的前身。
諸多文獻典籍的記載表明,在死者口中放入口含物,反映著中國人對死亡的獨特觀念。古人講究“事死如生”,也就是對待死者就像他還活著一樣。東漢何休注《春秋公羊傳》云:“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露其口。”親人不忍死者空著嘴和肚子離去,故在死者口中塞滿米貝、珠玉之物。因此,含的作用是使死者口實,不在陰間挨餓。
而由玉做成的玉琀和其他材質的口含相比,更多出了幾重含義。一是玉在人們的思想中更多的是代表著一種財富的象征,陪葬于墓中,顯示了墓主人高貴的身份和地位;二是古人相信玉乃聚日月精華、采天地靈氣而生,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與巫神通靈,保護死者尸體不腐、靈魂永生。《抱樸子》中有“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之說。
漢代玉斂之風尤盛,貴族在墓葬中會以大量的玉器陪葬。以玉片串聯而成的玉衣包裹全身,口中含著玉琀,手中握著玉握,“九竅”(眼、鼻、耳、嘴、生殖器、肛門)堵著玉塞。
馬家浜文化、三星村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玉琀的大量使用,說明生活于五六千年前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先民就已經對玉賦予著某種特殊內涵。
三、新石器時代長江下游地區的口含物與周邊地區
口含物的比較
在新石器時代,除了長江下游地區外,在其周邊地區也發現過各具特色的口含物。
目前中國發現年代最久遠的口含物遺存出土于距今約8000至7200年的內蒙古興隆洼遺址。在編號為M118的墓葬墓主人口內發現一件石管[10]。這件石管是目前最早的口含物。
大汶口文化時期的一些墓葬發現死者口中有含著石球、陶球的現象。如山東兗州王因遺址大汶口文化,一些墓主人口中含有直徑約15—20毫米的石、陶小球,且存在齒面萎縮內收和齒面磨損甚重的現象[11]。這應當是生前就將石、陶小球長期含于口內所致。這種生前含球的現象,有別于死后的“口含”葬俗,目前僅見于海岱地區。
山東兗州王因、鄒縣野店和江蘇邳縣大墩子是“口頰含球”習俗的主要發現地。
在四川省巫山大溪文化的個別墓葬有以魚陪葬的現象。有的魚放置在死者身上,有的在腳邊,有的在雙臂之下,還有個別含在嘴里。大溪遺址第一、二次發掘中,編號為M3的墓中就有魚隨葬。魚放置在人骨架胸腹之上的兩側,魚頭向北,尾端含于死者口中[12]。大溪遺址第三次發掘中,M78的墓主人口中也含著一條完整的魚[13]。這種現象反映了魚在大溪人的生活中有很神圣的地位。人們不僅生前食魚,死后要隨葬。魚很有可能是大溪人崇拜的靈物。
可以看出,上述各地區獨特的喪葬現象,與以玉、石、珠、貝、粱、米來填充亡者口腔的“口含之禮”差異甚大。
在興隆洼遺址發現的石管,僅此一件,其具體意義尚不明確,無法判斷是偶然現象還是某種習俗。海岱地區的口含物為人生前就將石、陶小球含于口內,且含球個體在整個墓地所占比例很小,這種行為應該不屬于普遍的現象,是在少數人中才有的一種行為。大溪文化中死者口中含魚,屬于當地特有的一種靈物信仰崇拜。以上風俗都具有地域特殊性,與長江下游地區延續千年、分布廣大的埋葬風俗不一樣。長江下游地區的這種埋葬習俗與后世的“口含”更有相似性。因而,興隆洼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出土的口含物并不是后世“口含”的直接起源。
四、結語
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口含物的確認將“口含”的歷史推進至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補充了其發展歷程最初的一步。
在對口含物的發展史進行梳理后,可得出幾點總結:
一是在口含物使用初期材質以石器、貝類為主;后期材質逐漸改用玉類。
二是長江下游地區是玉琀的主要發源地。中國使用玉琀的歷史可追溯至距今6000年前的馬家浜文化。這一時期的玉琀并非像后世那樣專門制作而成,往往是死者生前之物放于口中陪葬。如扁平三角形器、雞心形器,穿孔圓餅形器,舌形器等等,都穿鑿有小孔,應當是死者佩戴在身上的掛飾一類。所以玉琀的形狀、大小并不統一。
三是玉琀在長江下游地區出土得并不多,只有極少量的墓葬中有玉琀出土。所以,以玉琀陪葬在這一時期是比較特殊和罕見的葬俗。發現玉琀的墓葬往往有大量精美的陪葬品,規格和數量遠超同遺址的其他墓葬,甚至有人殉。墓主人應當是氏族的首領或祭司,玉琀是只有他們才能享有的葬儀。因此,當時的玉琀已經具有彰顯身份地位的作用。另外,玉石在當時人心目中有神圣的地位,給氏族首領死后口中納一玉器,也是對死者的一種神化。
參考文獻:
[1]龍虬莊遺址考古隊編著.龍虬莊:江淮東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2]南京博物院編著.北陰陽營:新石器時代及商周時期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217.
[4]王根富,張君.江蘇金壇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J].文物,2004,(02).
[5]黃宣佩,張明華主編.崧澤: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6]黃宣佩,張明華.青浦縣崧澤遺址第二次發掘[J].考古學報,1980,(01).
[7]黃宣佩主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福泉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8]劉斌主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南河浜:崧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9]宋建,周麗娟,陳杰.上海松江區廣富林遺址1999—2000年發掘簡報[J].考古,2002,(10).
[10]楊虎,劉國祥.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聚落遺址1992年發掘簡報[J].考古,1997,(01).
[11]胡秉華.山東兗州王因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1979,(01).
[12]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記略[J].文物,1961,(11).
[13]范桂杰,胡昌鈺.巫山大溪遺址第三次發掘[J].考古學報,1981,(04).
作者簡介:
李佳羽,女,漢族,重慶江津人,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指導教師:劉俊男。
276350170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