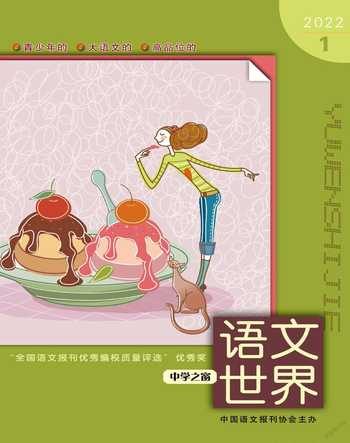一棵樹的遐想
苗新坤
記得5歲的時候,大舅從他們家扛來了一棵棗樹苗,栽在了我們家門口。這一鍬挖下去,便開啟了它30多年的生涯,確定了它的一生。
樹一天天地長大,一如我一樣。
一入夏,棗樹的葉子發華滋,棗花像女孩的耳釘一樣,星星點點,散發著馨香。西面的兩棵槐樹和一棵梧桐與它相映,院子里郁郁蔥蔥,好不美麗。
母親與父親經常去地里干活,留下我一個人在家。院子里經常曬著往年的稻谷、麥子,一地陽光,照得谷麥熱熱的。母親說棗樹不生蟲子,干凈得很,就讓我坐在樹下做作業,同時也要看好糧食,防著雞來啄食。棗樹下,于是就有了大板凳、小板凳、書包還有竹竿,滿滿當當,豐富極了。這是我的世界。我的初中快樂的學習時光,便與這棵棗樹結了緣。涼涼樹蔭,習習清風,自在極了。可是,那些雞的光顧總使自己學得不再孤單、枯燥。有時,一道題太“引人入勝”,自己仿佛落入迷宮,雞們審時度勢,成了游擊戰士,勤奮地啄食著,等我注意到它們,它們也早已注意到了我,有準備隨時逃離之勢,不過在逃與不逃之間,還是不肯停止,能啄則啄。迫于守住“靈感”的需要,我也只能靜靜地遠觀,撩起竹竿,裝腔作勢一番。就這樣,來回往復,與之周旋。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在樹下去做題目來學習是行不通的,你剛要沉下心來,卻又要浮動起來,這仿佛一片羽毛剛要落地,又來了一陣風。讀書、背書倒是不錯的,是對付雞鳥來襲的妙招。沒想到《出師表》《醉翁亭記》《馬說》《曹劌論戰》這些經典篇目還有如此的內力。我若無其事地發著聲,一只雞正趕來,我突然抬高聲音,它頓時立在原地,不敢向前,戒備著我,頭忽東忽西,我忽然做出撓頭姿勢,嚇得它扭頭便跑。一陣風吹來,棗樹搖曳著,一如我發出的得意的笑聲。更有令人捧腹的時刻,我拿著書,偏對著滿地的稻谷,我瞟著它們的一舉一動,似乎,這次是鄰居家的雞,我逐漸放低了背書的聲音,雞也放慢了腳步,我又恢復了背書的樣子,若無其事,雞也試探性地逐漸靠近,我頓時抬高聲音,站起了身子,做出雄鷹展翅的武姿,它仿佛嚇破了膽,頓時撲騰了起來,還“咯咯”地叫著。想想,沒有誰像我把書背得像交響樂一樣,高低緩急起伏,動感十足。
七月小棗八月梨。樹上的棗漸漸熟了。不過自己還是有些失望,這棵棗樹的棗比起舅舅家的,少得可憐,小得委屈。父親總是取笑,說它是“公樹”,“下不了蛋”。可往上看看,一窩一窩的,還是有些。棗身大都變了紅。母親說,這是“靈棗”(方言對甜脆品種的稱呼),好吃得很。班主任周老師布置了周末作文,題目倒很常見——“一件趣事”,但還是苦于“趣事”老生常談而無趣。我坐在樹下,突然一顆棗被鳥啄掉了,靈感頓時出現了。對!打棗!這時,谷麥重新歸倉,我早已不用為“雞”發愁了。父親拿起竹竿,踩在板凳上,一下,一下,輕輕地敲著。頓時,棗子滿地“嘣嘣”地蹦著,它們像長了腿一樣到處亂躥,母親拿著“升筐”(方言稱呼量糧食的容器,容量為一升)到處撿,應接不暇。一顆棗子“嗒”的一聲落在大板凳上的本子上又彈了出去。你看,它多好,主動給我送來“趣事”。我將棗拿來,不待母親去洗,早已放在嘴里,“呼哧呼哧”地嚼著,果然清脆,果肉還散發著晶亮的光。吃著棗子,完成了作文,真是美事一樁。還記得,周老師把我的文章打了“優秀”,表揚了我。我心里就想,有了這棵樹挺幸運,初中的美好學習時光總離不開它。
漸漸地我讀了高中。14歲的我站在講臺前自我介紹,一臉稚嫩,讓同學發笑。其他人,個子比我大好多,一出口就是我所不知的《文化苦旅》或是王國維的“治學三境界”,聽后感覺自己太渺小。同宿舍的一個同學姓武,有點皮,怎么都不會和愛讀書聯系在一起。他告訴我,《文化苦旅》已經讀了三遍了,正準備讀第四遍。我生怕他問我“知不知道有個人叫余秋雨”這一扎心的問題。我就見賢思齊,先問他借來一看。晚自習前的黃昏時刻,開始有一個身影靜靜地坐在教室里,感受著這“苦旅”的深沉雋永和文化散文的筆調。教室的外面,是一片池塘,旁邊還有一株柳樹和一個牌子,牌子上綴著晏殊的詞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忽然感覺,這便是詩詞中的意境。這種獨特享受,正是校園之外不曾給予的。這也是一個人的世界,一個人的天地,仿佛與棗樹下的世界全然不同。有一天,晚自習突然停電,整個教學樓一片漆黑,瞬間是一陣歡呼。老師讓我們到門口的商店買蠟燭,不一會兒教室里就一點一點地亮了起來。整間教室燈火通明,人影憧憧,昏黃的燭光似乎也帶來了另一番寧靜,大家彼此都很近。這個夜晚似一條靜靜的小河,潺潺地流著。外面,可以聽到風在拂動,是柳樹。我翻著魯迅的《阿Q正傳》,屋舍中這種最樸素的燈火陪伴著我讀書是不常有的,古人那種一室一燈一人的幽獨在那一刻似乎在心中浮現出來。曾經的黑夜,一個身影在燈下拿起筆,伴著煙圈為這個人物定下一個“阿Q”的稱呼;現在的黑夜,有一個身影依然在燭火下讀著這個人物的故事。他們之間劃了一道時光的長虹。我才明白,魯迅先生為何鐘情在黑夜燈下漫筆。黑夜,讓眼線縮短,卻讓心界伸展。
忽然,來電了,大家卻不約而同地“唉”了一聲。從此,我便喜歡在一個又一個黑夜捧讀了。
如今,棗樹早已不在,父親也已不在,教室后面的池塘變成了小山、涼亭,柳樹,也不在,但那片棗樹蔭和“溶溶月”“淡淡風”的詞句總也揮之不去。不知,她們是否曾經記得那段時光,如果記得,還認不認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