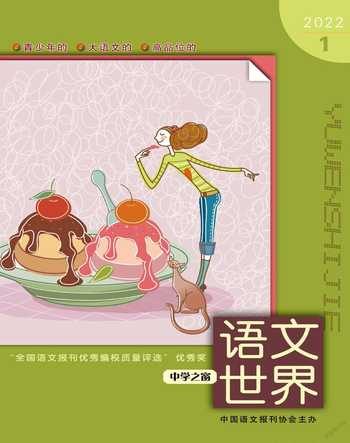一曲《雨霖霖》最是凄涼美
劉洋
宋人俞文豹的《吹劍續(xù)錄》中記載了一個段子: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七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兒,執(zhí)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fēng)殘月。學(xué)士詞,須關(guān)西大漢,執(zhí)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這個段子的真實性值得懷疑,但這個段子卻精準(zhǔn)地指出了宋詞兩大流派的代表作家、代表作——蘇軾和他的《念奴嬌》、柳永和他的《雨霖霖》。《雨霖霖》是婉約詞的巔峰之作,一提及它,我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凄涼二字,但這種凄涼卻富于美感,《雨霖霖》打動我們的正是它的凄涼之美。這種凄涼之美,可以通過以下幾個層面看到。
一、景物的凄涼美
《雨霖霖》里的景物帶著濃郁的凄涼色彩,《禮記·月令》中記,“涼風(fēng)至,白露降,寒蟬鳴”。寒蟬是蟬之一種,以明時令。凄切的寒蟬時時提醒著離人,這是清秋季節(jié)。“長亭”是送別之所,是傷心之地。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是離人的分別之地。李白《菩薩蠻》“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就說盡了游子歸程的綿遠(yuǎn)悠長。“晚”,是一個富于感傷氣息的時間,天色向晚,光線逐漸變暗,人的心情也會暗淡。李白的“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溫飛卿“時節(jié)欲黃昏,無憀獨倚門”都是將愁情放在黃昏時分去寫。清秋的凄涼日,傍晚的凄涼時,加上這驟雨之后寒蟬的凄切哀鳴,一面是戀戀不舍的戀人,一面又是催發(fā)的“蘭舟”,離別之際的傷心之人哪有帳飲的心緒。眼前的景物這般凄涼,別后的景物同樣如此。
一望無際的千里煙波,暮靄里蒼茫遼遠(yuǎn)的楚天,充滿著壓抑之感,好在此時澆愁的酒還沒有散去。行人酒醒的時節(jié),正好到達(dá)長滿楊柳的岸邊,清秋的冷風(fēng)吹過,一鉤殘月升起。離人的眼中只有低垂的楊柳,嗖嗖的曉風(fēng),如鉤的殘月,景色是無邊的凄清蕭條,離人的心情應(yīng)是無限的惆悵傷感。不管是眼前的景,還是別后的景,都是凄涼的。這景是愁緒滿懷的離人的眼中所見,帶上了離人的愁情,這景的凄涼又反過來將離人的愁情加倍放大。這景是優(yōu)美的,尤其在今人讀來,長亭、寒蟬、蘭舟、煙波、楚天、楊柳、殘月的組合,完全是一幅彌漫著凄美的水墨畫卷。
二、離情的凄涼美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別后音訊難通,看起來是生離,實際上為死別,離別就顯得分外傷感,正如《孔雀東南飛》中所講的:“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所以江淹感懷,“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歐陽修《玉樓春》有句:“別后不知君遠(yuǎn)近,觸目凄涼多少悶。”“多情”的詞人柳永注定了逃不脫這無以言說的濃得化不開的離情。《世說新語·傷逝》中王戎說過,“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這是在說圣人已經(jīng)超越了情的限制,麻木的人不懂得情為何物,只有明于情,深于情的人,對于情才有更加刻骨銘心的體味。
大凡文人都應(yīng)該是“情之所鐘”者,生活潦倒,以“白衣卿相”自詡的柳永更是“情之所鐘”者。柳永懂得分別之時的難舍,深味分別之時的苦,與情人的分別定格在了“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中,這也成為了文學(xué)長河中有情人離別時最為經(jīng)典的鏡頭。“執(zhí)手相看淚眼”的千言萬語,最后都在一個“竟”字里化作了“凝噎”。韓愈在《送李翱》中說:“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后思。”柳永心懷別時之苦,他更懂得分別之后的思念會更苦,“此去經(jīng)年,應(yīng)是良辰好景虛設(shè)”,一別之后的相見無期,也就讓詞人從此眼中失去了美景,心中再沒有了良辰,這是何等的深情,何等的思念之苦。詞人或許惱怒自己的“多情”,多情讓人苦,我們卻恰恰在這“多情”里看到了有情之人分離的凄涼,凄涼背后的美麗動人。的確,“多情”讓人苦,但“多情”之苦才讓人感到世間的溫暖,活著的意義。
三、人生失意的凄涼美
《雨霖霖》原名《雨霖鈴》。據(jù)唐《明皇雜錄》《樂府雜錄》等記載,唐玄宗因為安史之亂出逃,在“馬嵬兵變”中處死楊貴妃,后來入蜀,“于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yīng),上既悼念貴妃,采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哀傷幽怨、凄婉動人的《雨霖鈴》原本是一支悼亡的曲子,柳永卻選擇此曲填寫,寫和戀人的分別,詞里分明寄寓著詞人人生失意的凄涼。
出身世宦的柳永,原名三變,三變典出《論語》:“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可見,家人對柳永所寄予的厚望,希望他能夠像謙謙君子一樣,遠(yuǎn)望嚴(yán)肅莊重,近看溫文敦厚,講起話來也一絲不茍。不負(fù)厚望的柳永在18歲就取得了赴京應(yīng)進(jìn)士第的資格,然而進(jìn)京參加科舉,卻屢試不中。初試落地,他還有些豪氣,作《鶴沖天》詞抒發(fā)懷才不遇的牢騷,其中一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因有輕慢朝廷的嫌疑,惹怒宋仁宗,叫他“且去填詞”,柳永尚能以“奉旨填詞柳三變”自嘲。作《雨霖霖》時的柳永剛剛經(jīng)歷第四次科舉落榜,連續(xù)的科舉失敗,他已對仕途無望,憤而離開汴京,雖然此時的他詞名滿京師,才華人盡皆知。故而,“便縱有千種風(fēng)情,更與何人說”里充滿了寂寞,既是戀人不在,更是人生無奈,人世孤獨。戀人亦是知音,一別之后便是得而復(fù)失,知音難覓,詞中的情感已經(jīng)超越了普通的男女相思,直指人生在世的精神需求。
一曲《雨霖霖》傳唱了千年,打動了無數(shù)讀者。這些讀者里,有的感懷于早已消逝的詞中之景,有的感懷于男女之情,也有的感懷于人生在世的孤獨,但撥動讀者心弦的一定是沉淀在這首詞最深處的凄涼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