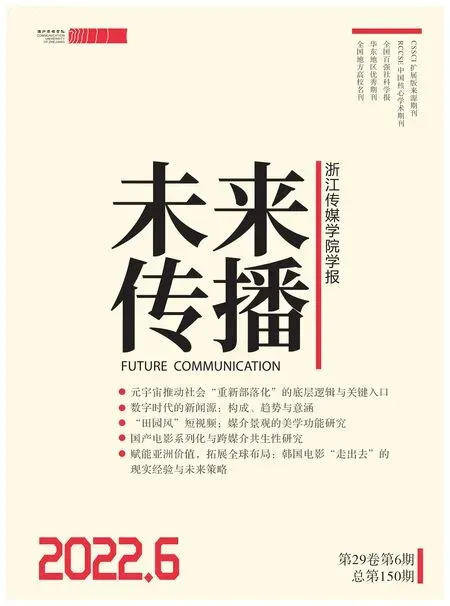“田園風”短視頻:媒介景觀的美學功能研究
丁莉麗
(浙江傳媒學院電視藝術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近年來,“田園風”短視頻風靡網絡世界,尤其是隨著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快速運轉的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這場疫情被認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全社會對高歌猛進的“現代性”(1)關于“現代性”,至今沒有確切的定義和概念,大致包含三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啟蒙現代性”,核心要義是側重于強調物質層面的發展,以追求高消費及高生活質量為導向的社會化進程,推崇理性,崇拜成功。本文所指涉的“現代性”這一概念,接近于“啟蒙現代性”。二是“現代性批判”。催生現代性的工業文明母體自19世紀以降日益呈現出其異化人性的一面,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 成為當下現代性話語中的主流聲音。三是“審美現代性”,在藝術范疇內作為一種重要的審美理念而存在。進程的一次脫軌和斷裂,也是“現代性危機”的一次全面爆發。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被疫情陰影籠罩的時刻,來自中國的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粉絲從700多萬一舉飆升到了1000多萬,至今已經達到2300多萬。2020年底,藏族青年丁真微抿干燥的嘴唇、露出靦腆微笑的7秒鐘視頻,一夜之間也成為社交媒體關注的焦點。文化界一個普遍的觀點是,以李子柒為代表的“田園風”短視頻是對當下人們進行“情感按摩”(2)持這一觀點的文章包括曾一果、時靜:《“從“情感按摩”到“情感結構”:“現代性焦慮下的田園想象——以“李子柒短視頻”為例”》、尹淑婷:《情感按摩和空間互動:田園短視頻特征極其在青年群體重流行的原因》、鄭永濤:《生活體驗類慢綜藝節目的情感“按摩”及思考》等。的重要工具。而《紐約時報》的美食版專欄則將李子柒定位為“隔離時期的田園公主”:“對于世界各地隔離中的觀眾來說,她這種一切自己動手的田園幻像,已經成為逃避和安慰的可靠來源。”[1]而丁真以“沒有經歷過學而思和奧數”的清澈眼神以及“甜野男孩”形象出圈,則源于久處城市樊籠的大眾對藏區原生態風貌的浪漫化想象。這些論點有合理之處,但或多或少也存在著一種立場的偏頗和理解的狹隘。不容否認,李子柒和丁真們的走紅背后都有著精細的流量計算和得當的文化運作策略,但李子柒能成為全球超級網紅,獲得新華社、央視新聞等眾多主流媒體多次點贊,丁真的視頻也曾數次被外交部發言人推薦,背后顯然還存在著更為深刻的文化動因。參照美國文化批判學者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對于媒介景觀(media spectacle)的定義:“能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并將當代社會的沖突和解決方法戲劇化的媒介文化現象。”[2]這類“田園風”短視頻顯然已構建為當下蘊含豐富現實內涵的“媒介景觀”。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對“田園風”短視頻這類媒介景觀所蘊含的美學功能的探究,不應止步于撫慰焦慮的“情感按摩”作用,而應進一步關注它們作為審美意象所具有的審美救贖功能。
一、慢影像:“現代性焦慮”的撫慰與治療
現代社會將理性精神植入每個社會個體的生命機理之中,理性化、制度化、程序化已經成為當下社會的本質特征。個體在工業化的生產流程上成了一顆螺絲釘式的存在,服從于權力系統的網格化管理。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希·弗羅姆(Erich Fromm)曾經在《人心——善惡天性》(TheHeartofMan:ItsGeniusforGoodandEvil)一書中提到:“在這種工業主義中,人變成了一種物,其結果就是人對生活滿懷著焦慮和冷漠,如果還說不上對生活抱仇恨態度的話。”[3]在以理性精神為指向的“現代性”語境中,“現代性焦慮”幾乎已成為社會個體的普遍性病癥。
“現代性焦慮”的重要表征之一是面對時間的匱乏感。“現代性”語境中,時間受困于資本的裹挾,以“時間就是金錢”這一價值指認獲得了合法性,并由此催生“速度”為主宰的“現代性”敘事,“速度美學”則成為當代唯一的美學。“當代的美學只有一種,那就是關于‘速度’的美學。一切與速度密切相關的事物都受到特別的關注與寵愛,速度成為美的事物必備的性能。速度被贊頌、被崇拜、被當作非人的駕馭力量使我們感到敬畏與震撼。速度成為時代的美學、成為超符碼、成為向四周彌散滲透的中心話語,成為壟斷性的‘暴力語言’。”[4]“速度美學”的壟斷不但體現在追求速度感的“現代性”敘事成為主流,而且在各種文本的敘事邏輯上也深度植入了“速度崇拜”的因子,如當前以“強沖突”“強情節”“快節奏”為標桿的影視劇敘事走向。英國社會學學者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曾如此描述當下的普遍性視覺景觀:“觀眾們如此緊緊地跟隨著變換迅速的電視圖像,以至于難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連結成一個有意義的敘述,他(或她)僅僅陶醉于那些由眾多畫面接連閃現的屏幕圖像所造成的緊張與感官刺激。”[5]當觀眾沉浸于快速的影像流中而目不暇接時,非但無法將那些影像碎片聯接成一個有意義的敘述,且更進一步帶來感官功能的日益鈍化和感悟力的喪失。時間的匱乏感和意義的虛無化本質上是一對孿生兄弟,因為無論是關于時間的感覺,還是意義的生成,必須與身體感官相關聯。換句話說,時間,只有被身體擁有時才有意義。當追求速度成為一種慣性的時候,身體對意義感悟能力的喪失也就成了必然的結果。如“倍速”觀影的流行趨勢,即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現象。在筆者看來,“倍速”播放行為并不完全指向對影視劇“注水”問題的抵御,也是當代觀眾迷戀速度感的表征。“倍速”觀影的喜好其實源于觀眾試圖通過對更多空間的占有來拉長心理時間,但只是對匱乏時間的一種想象性補償,并不能因此收獲時間延續中的意義。“‘現代’的時間概念已經被抽空,瞬間不是一個瞬間,而是無數不斷向前滾動的瞬間,它看似那么重要,實則并不存在,而人們為了擺脫這種無力感,只有不斷地填滿它,當然這也促成了它更快地衰竭。瞬間性,無論是強調時間的衰竭還是其流動不居的特點,與其說是扼殺時間,不如說是扼殺對于時間的厭倦。”[6]“倍速”觀影作為快節奏時代的典型癥候,正是大眾心理時空失衡以及焦慮化生存的映照。
大多數“田園風”短視頻以舒緩的節奏表現浪漫的田園生活,在當前以“速度美學”為主流的語境中屬于“他者化”的影像。例如,“何小勇的農村生活”“杏林小院”等展現的是博主們拿著鋤頭、鏟子,或平整土地,或把一條泥濘道路修整成林蔭小道,或把老房子改建成讓人羨慕的鄉村小院,一點點打造出“向往生活”樣板的過程。“巧婦9妹”承包了100多畝果林,她的短視頻主要分享水果從種植、施肥到收獲的的過程。李子柒創作的“一生”系列短視頻,以正常的時空關系為經緯線,鋪展水稻、大蒜、土豆等農作物的“一生”,從平整土地,撒播種子,再到食物從田間到鍋里的過程。雖然漫長的等待和辛苦的勞作過程被略去了,剩下的是精心剪輯過的節點性的流程匯總,但無論是對農民平淡日常生活的記錄,還是不同莊稼得以生長和食物的制作流程,都是周而復始的過程,是早已經“劇透”得毫無懸念的日常記載。相比于“何小勇的農村生活”和“杏林小院”等短視頻的粗糲質感和原生態風格,李子柒的短視頻更為精致,她借助相對精湛的剪輯技術,在日常生活的直播中精心營造充滿詩意的“韻味”空間,引導觀眾在時間的沉浸中喚醒感官的功能,在韻味的品味中驅散內心的焦慮。令丁真爆紅的7秒視頻則以細微的面部表情、微晃的身姿與背后的藍天、草地形成一種動靜結合的畫面感,其內置的慢生活節奏正迎合了網民對于理想生活的向往。這些視頻片段仿佛一縷縷微風,拂過當代人焦慮的內心。
但是,這些“田園風”短視頻的意義并不僅僅止于對焦慮的撫慰,從某種程度也為當下群體性的“現代性焦慮”病癥提供了一種類似于“敘事療法”的治愈途徑。“敘事療法”的定義是:“指咨詢者通過傾聽他人的故事,運用適當的方法,幫助當事人找出遺漏片段,使問題外化,從而引導來訪者重構積極故事,以喚起當事人發生改變的內在力量的過程。”[7]具體的治療原理是“通過解構性的談話或者活動,治療過程可以幫助咨詢師和來訪者看到來訪者生活中的‘主流控制的敘事’。在治療過程中來訪者和咨詢師開拓視野,重新審視并理解這種‘主流控制敘事’,從而形成‘重新選擇的新穎敘事’,使新的生活可以凸現出來”[8]。在心理學家看來,當代人的焦慮本質是源于理性入侵造成的精神壓力持續增大,此時如果缺少必要的身體活動進行調節,就會引發種種精神疾病。因此,“要從精神疾病的困境中走出來,作為個體,一個很重要的途徑是改變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重新審視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個體的生活需要從理性膨脹狀態向生物自然性回歸,從科學理性的邏輯回歸到生命力的邏輯上,回歸到身體與精神互相協作的真實狀態上”[9]。倡導運動則成為防治精神疾病的具體方式之一。“心理治療應該引導病人投入到自然和身體勞動中,形成熱愛自然和陽光,熱愛體力勞動的生活態度,這是緩解現代社會壓力、抵抗精神疾病的重要途徑。身體勞動是自然賦予人的勞動法則,它可以將人的注意力由主觀世界移向外部世界,注意當下在做的事情,這就減少了指向心理內部的精神能量,使人從精神憂郁和躁狂中走出來。這種治療的基點在于,勞動使得生命有機體整體走向協調與健康”[8](68)。
觀看這類“田園風”短視頻可以作為“敘事療法”的依據,在于其完全契合了“敘事療法的實踐是以人文生態的和諧為途徑的,以生命意義的豐富為旨歸”[7](78)這一要義。從視頻內容來看,這些短視頻都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呈現,無論是田間地頭的操勞,還是食物的制作,一切都是視頻博主親力親為。這些視頻內容不但喚起觀眾曾經的勞動記憶,同時引導他們將活動空間轉向田野、自然,從而將身體從被理性和技術禁錮的境遇中解放出來,在身體與自然的碰觸中找回被“主流控制敘事”所遮蔽的生活意義,從而撫平生命中那些焦慮的褶皺,喚醒自我的生命肌體,完成對受傷身心的療愈。丁真的走紅也是因其身上所展現的“淳樸”與“原生態”氣質,喚起了都市人在忙碌生活之中對于原始自然淳樸生活的向往,并由此完成對受眾心中質樸田園生活美學的召喚和回歸。
2019年底,李子柒的視頻已在國外的視頻網站上獲得了極高的關注度,而在疫情期間,李子柒的粉絲數量得到爆發性增長,正是源于疫情暴發為李子柒的田園生活影像的關注和實踐提供了更多的契機。慢速生活的到來讓曾經匱乏的時間變得充裕,時間和空間的關系發生了逆轉,局促的空間進一步拉長了時間的正常感受,使得如何將多余出來的時間鋪展到日常生活空間之中,成為很多人所面對的問題。而因為疫情管控而被迫封閉隔離的現實環境,讓李子柒的視頻中自給自足、自得其樂的生活狀態為現實提供了映照,從而成為大家希望模仿的對象。疫情期間的人們將時間鋪展到日常生活之中,在體驗勞動的過程中,不但實現了身體和精神的平衡,而且喚起了人們在內心里對于生活意義的重新認知。從歐美中產階級到中國北上廣的城市新貴們從城市中心搬往郊區別墅、排屋的風潮(3)疫情之后,房產市場上計劃以排屋為改善目標的購房者明顯增多,導致郊區排屋價格上漲趨勢遠超普通公寓,這一現象在中國房產市場有詳細的數據支持。歐美也有明顯的趨勢,網上有《疫情促使美國人舉家逃離大城市 搬家公司生意火熱》《疫情如何沖擊歐洲房地產市場 逃離大城市,小花園受歡迎》《疫情下美波士頓房價大漲14% 市區公寓卻暴跌二、三成》等文章均講述了這一現象。,再到疫情暴發之后大眾生活態度的微妙變化,隱約可以看到這一審美風尚的變遷。疫情突然暴發帶來的沖擊以及對慢速生活的體驗,為后疫情時代的人們把握時空關系問題及如何尋找精神家園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考路徑。以“田園風”短視頻為代表的慢影像的流行,顯示時代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節點,面臨著如何重構我們美學坐標的時代命題。
二 、鄉村牧歌情調:審美現代性的觀照
當然,“田園風”短視頻也招致了一些批判,如認為李子柒的視頻舍棄了臟亂差的鄉村場景,通過對于田園生活想象的刻意擺拍,過濾了真實農村生活的艱辛,遮蔽了農民生活中的真實苦難,營造的是一個虛假的烏托邦世界等。2021年初,前媒體從業人員馬金瑜與所謂藏族男子之間的情感糾葛,則讓很多人將扎西與丁真進行類比,認為這一事件恰好印證了作為媒介幻像的丁真純真形象的破滅。這些論調本質上沒有逃脫將“鄉村牧歌”景觀認定為“媒介奇觀”的刻板化視角,其背后是習以為常的“精英化”立場以及對多元化價值觀念的抹殺和時代語境的疏離。同時,這一觀點也忽略了短視頻本身具有的意識形態功能以及消費者自身的主觀能動性,落入了將觀眾視為機械而被動的消費機器的固化思維。學者楊義曾經指出:“出現在敘事文本中的意象是一種獨特的審美復合體,所說的‘媒介景觀’(media spectacle),它不是某種意義和表象的簡單相加,而是內涵意識形態的多構體。原來的表象和意義發生實質性的變異和升華,成為可供人反復尋味的生命體。”[10]媒介景觀并非空洞的符號化呈現,而是具有審美功能的“審美復合體”。“田園風”短視頻的風行以及鄉村媒介景觀之所以能夠得以凸顯,還因為這些審美意象與當下時代境遇之間存在著微妙的貼合關系。
“田園風”短視頻的大量出現和走紅,顯現出“鄉村牧歌”式的歷史景觀正在新的時代情境中重新入場的趨勢。“田園風”短視頻中的“鄉愁”意象,雖然承載著鄉土中國的傳統文化基因,但絕不是簡單地以‘剩余文化’的形式回到當下,而是以鄉愁烏托邦的形式,積極地參與了當代中國現代審美情感結構的重建以及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把過去的歷史記憶,文化的傳統以及中國文化對待人生悲劇的獨特理念,在當代社會和文化語境中重新激活,使之成為一種緩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巨大痛苦的文化形式,用一種女性化的方式,一種優美而哀傷的情感結構,一種抒情而纏綿的審美話語,去探索一種不僅僅是個體性的自我拯救,而是整個民族的偉大復興文化形式,這是中國社會現代性的一個突出特征。”[11]與這一觀點形成印證的是,李子柒、何小勇等這些短視頻博主們在從事短視頻創作之前,都曾有過在城市艱難闖蕩的經歷。何小勇曾經在城里開過“五金店”、在鞋廠打過工,“一事無成”的他后來決定帶著妻子回鄉去尋找商機。李子柒也曾在城市里從事過DJ、餐廳服務員等職業,后因需要照顧祖母而回到鄉村。他們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匯入了當前部分年輕人“逃離北上廣”的潮流之中。同時,回鄉經營以鄉村特產為主的淘寶店,通過發布帶著“鄉村牧歌”風情的短視頻“帶貨”,成為他們“回鄉創業”獲得成功的重要途徑。何小勇、李子柒等短視頻博主創業的成功,一方面顯示出“鄉村振興”政策為個體的自我拯救和發展提供了轉型的契機,另一方面也詮釋了中華文明復興過程中傳統審美文化局部回歸的現實語境。而進一步值得關注的是,對于何小勇、李子柒他們而言,“回鄉創業”的過程也提供了自我治愈“現代性焦慮”的契機,他們在觸摸中國傳統文化范式的同時,也重塑了自我的審美價值體系,而這一切最終又投射在他們的短視頻創作中,體現為“情感消費”引導和“審美布道”的統一。因此,“鄉村牧歌”式媒介景觀的入場與風行,讓當下眾多深陷于“現代性焦慮”中的個體看到如何與自我、現實和解的途徑,這正是“鄉村牧歌”作為“審美現代性”本質力量在當下的顯現。因此,以李子柒、何小勇、丁真等為代表的媒介景觀所蘊涵的鄉村牧歌情調和“鄉愁”意蘊,并非為大眾提供了逃避現實的烏托邦幻景,而是為大眾如何在現實中建構精神家園、擺脫精神迷惘提供了思想的啟迪和實踐的途徑。
事實上,“田園風”短視頻的風行并非突如其來,從前些年《百鳥朝鳳》《岡仁波齊》等“鄉村牧歌”式影片的聲名鵲起,到如今《向往生活》等“慢綜藝”的崛起,這一具有轉型意味的審美風潮一直在慢慢匯聚,漸成氣候。值得注意的是,《百鳥朝鳳》唱出的是一曲“文化挽歌”,關注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快速變動的現代化風潮中傳統藝術的不斷邊緣化以及傳統藝人沒有歸處的困境,表達的是對傳統文化中行將逝去之美的無限依戀和喟嘆。而《岡仁波齊》則更多地彰顯當下藏人在“現代性”進程中卓然獨立的文化姿態,在去岡仁波齊的路上,他們的身旁是不斷呼嘯而過的汽車,但他們依然選擇一步三磕頭的方式去抵達“朝圣”之地。近年走紅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中國村落》等,均著力于展現普通老百姓以“人生藝術化”和“藝術人生化”相融的人生態度和追求表達對“現代化”的頑強抵抗。如紀錄片《中國村落》講述了一些曾經在城市里漂泊的流水線女工、流浪歌手等,最終回到家鄉成為一個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故事。這些“鄉村牧歌”式的影像,雖仍是邊緣化的文化圖景,卻已經在當下日漸得到了恢復和重現。這些文化圖景在“鄉村振興”的宏大敘事語境中具有特殊的指向和意義,因為“鄉村振興”的核心內涵不是讓農村機械地照搬“城市化”的傳統路徑,而是以農村作為主場,探究農耕文明的現代更新之路,也是中華文明的復興之路。
李子柒、丁真等短視頻作為審美意象體現出來的救贖意義、實踐價值,不但體現了對中國正在經歷的“鄉村振興”這一宏大時代命題的呼應,也給處于“大城市放不下肉身,小城市安放不了靈魂”這一悖論中的年輕人提供了思想的啟迪。就李子柒而言,她在視頻中被建構為一個傳統與現代交融的審美意象。一方面,李子柒展現了她極簡主義的生活方式,從穿著打扮的原生態服飾,到凡事親力親為、生活自給自足的生存狀態。鏡頭里的她,亂頭粗服,荷鋤、平地、燒火,刻意淡化表演意識,通過呈現她沉浸其中的專注,張揚她面對平凡生活的淡定和從容。但是,她的極簡主義生活方式只是表象,背后是精致的妝容、得體的服飾,是深植于現代女性消費理念之中的審美趨向的顯現,與普通的農家婦女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這個清新脫俗的民間農女形象,本質上是中產階級知識女性的投影,尤其是通過對李子柒的獨立女性人設與勵志女神形象的塑造,更加彰顯這一現代意味。
從性別認知角度,李子柒的形象又是一個回歸家庭的傳統主婦形象,她對于傳統生活方式的沿襲、與自然合拍的生活體驗、對當下日常生活審美化空間的搭建,都凸顯了對中國傳統家庭生活樣式的回溯。李子柒這一媒介形象所具有的豐富審美意蘊,為當前的受眾提供了眾多的人生啟迪和價值指引。而走紅之后的丁真選擇擔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縣的旅游文化大使,在進一步打造清新質樸的媒介形象的同時,出品了《丁真的世界》《丁真的自然筆記》等涉及文化、旅游、環保主題的短片,通過展示藏地風光,弘揚藏族優秀傳統文化,展現與繁華都市截然不同的壯觀自然景象,呼吁更多人回歸自然、保護自然。作為媒介形象的丁真,與其打造的視覺產品的審美意蘊相輔相成,從而保證了其作為媒介人設具有良好的成長性。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鄉村振興”的大背景,讓源于民間立場的“鄉村牧歌”煥發出了新的生機,成為一種充滿實踐意味的“審美風向標”。在新時代的文藝生產場域中,“田園風”短視頻以其富有時代意味的文化價值與精神表達,詮釋了新時代人民文化主體性的張揚和“人民性”藝術價值導向的傳達。“它既關乎人民的美好生活、文化權益的實現,也有助于提高大眾的審美趣味和藝術鑒賞力,進而在提升社會文明程度中展示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兩新’文藝的發育和自治能力及其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相契合,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文藝繁榮興盛以及國家文化治理有效性的體現。”[12]正是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主題高度契合,讓以李子柒、丁真等為代表的媒介景觀在全球化舞臺上為世界貢獻出了特殊的聲響和色彩。
三、 鄉土文化景觀:人文地理學的重構
人文地理學于20世紀70年代興起。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段義孚認為:“人文地理學通過空間與地方概念,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地理行為的關系和人的空間及地方感。”[13]“人文主義地理學主張通過人的意識、感知和體驗來研究‘地方’及人地關系,并把文學中的景觀視為一種主觀體驗的表達。”[14]簡言之,人文地理學的內涵是指情感體驗投射到一定空間內,為其賦予意義和秩序。因此,在人文地理學的視域中,鄉村社會空間形態,并非只是簡單地對物理空間進行標識,而是表征著具有區域特色的人文景觀。鄉村景觀體現出的空間關系和生產關系的變化,則折射著整個社會觀念的調整和審美的變革。“鄉村牧歌”式媒介景觀的走紅,宣告了跨越不同地域與民族、覆蓋不同圈層的當代超級感性共同體的誕生。這不但體現了中國敘事日益崛起、中國地域審美景觀日漸凸顯的趨勢,而且以其蘊涵的“現代性”抵抗以及審美救贖意味,顯示了當下人文地理學重構之路的開啟。
美國學者戴維·哈維(David Harvey)認為:“地域審美的哲學基礎首要的就是對空間與時間關系的反思。”[15]“被追憶的時間始終都不是流動的,而是對體驗過的場所和空間的記憶,倘若這是真的,那么歷史就確實必須讓位于詩歌,時間必須讓位于空間,成為社會表現的根本材料”[15]。這些論斷充分闡釋了地域表現空間所蘊含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如20世紀90年代以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在《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片中著力于營造的“鐵屋子”意象,成為“古舊中國”的象征,以及第六代導演展現的深陷“現代性”泥潭中的落后鄉村和迷亂都市,均屬于落后于“現代性”進程的“文化他者”空間。“這種文化的時間被劃定在過去,空間被定義在邊緣,價值被定義給少數人。其之所以可能被傳播,是因為其相較于普適的文化具有的一種差異性或奇觀價值。”[16]這正是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的電影在國外獲得關注的重要原因。但當前的李子柒和丁真這兩位身處中國西部鄉村的年輕人以“田園公主”和“草原王子”的形象定位介入全球化空間,已不再是為“現代性”作負面注腳的“他者”文化形象,而是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來重新書寫和定義中國西部敘事,尤其是在西部地域文化的呈現上,突破了西部/東部、傳統/現代二元格局中的邊緣化位置,構成對傳統人文地理學的解構和挑戰。
“田園風”短視頻中的鄉村媒介景觀,顯示出以“鄉村振興”、扶貧大業為表征的“啟蒙現代性”話語和“審美現代性”的感性邏輯在時代現場的正面相逢,兩者的并置和勾連,體現出中國文化景觀的生產,不但突破了傳統人文地理學格局的限制,同時正在以一種新的眼光凝視、重塑西部鄉村審美景觀。李子柒和丁真的短視頻與20世紀80年代第五代導演中貧瘠的黃土高坡這類鏡像,以及當下部分迎合城市獵奇目光的土味審美物象完全不同,而以充滿泥土清香鄉村的視覺呈現、舒展的人性與自然山水和諧一體的敘事邏輯,傳達出更具現代感的審美內核。如李子柒的服飾、裝扮、行為、拍攝方式等,刻意規避了被“凝視”的期待感,而是以充滿自我沉浸感的方式把瑣碎的生活場景演繹為審美活動。李子柒不只是與鏡外的觀眾進行對話,體現出的是一個以本真出場的展演者面對自我文化的自豪感,“這樣一種空前強烈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使得民俗生活的內部正在發生一次悄然重構,重新凝固某些強烈的文化情感,生長出新的文化地基與地層。是民族地區人文地理景觀依照審美法則而進行的重塑與再造。圍繞美學價值的生成,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生態空間正在進行系統性重組,景觀的視覺改造大規模創生著新的文化空間”[17]。從這一意義上看,田園風短視頻為“中國短視頻在文化自覺、文化服務維度上的在地化建設”[18]作出了到位的詮釋。
文化地理學大師段義孚《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的重要觀點是:“‘地方’是空間人文意義系統當中的落腳點;相反,人對‘地方’的意義建構是本能地經驗感知。近些年的研究表明,生態邏輯下的一些地理學研究成果和地球家園能量危機讓現代人意識到,‘空間’不再為我們擁擠的土地提供各種延展可能,我們此時所在的‘地方’是自我與自然互構的人文空間。‘地方’不僅是‘空間’的出發點,更是無限擴張夢想的現實基礎。”[19]在李子柒、丁真以及何小勇等人的短視頻中,不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現,“地方”也成為他們安放人文理想的自然空間。李子柒的短視頻中常見的選題包含民風民俗、時令節氣等,都與自然現象相關。視頻中呈現的山、河、花等這些自然景觀充滿了人間氣息和詩學情趣,視頻中的李子柒沉浸在自然意象營造的氛圍中,體會著春耕夏種、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李子柒和奶奶相依為命,其平淡而溫暖的生活氛圍詮釋著中國文化的傳統人倫秩序和情感取向。馬背上的丁真的清澈的眼神、微笑和背后的雪山渾然一體,人性的純凈和山川的大美相得益彰。丁真在走紅之后曾表示:“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我還是最愛自己的家鄉。”“每天最開心的事就是和朋友們一起賽馬。”正是這種“初心”讓他拒絕了無數傳媒經紀公司的簽約邀請,選擇留在當地擔任文化推廣代言人,賦能家鄉“鄉村振興”事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丁真的選擇不僅是他自身作為媒介景觀得以延續的正確路徑,更是當下社會正在經歷鄉村文化崛起、文化地理格局轉型的重要表征。以李子柒和丁真為代表的鄉村媒介景觀,以封閉性的地理格局呈現、中國傳統生存方式的選擇以及閃耀著生命倫理之光的“地方感”,打破了全球化敘事的神話,為人文地理學注入了新的情感內涵,尤其是在經歷“抗疫”的當下,有著更為重要的實踐意義。
無論是李子柒淡定從容的面容、丁真靦腆單純的微笑,還是何小勇、巧婦九妹等眾多樸實的面容,都和背后的景致緊密交融在一起,以整體性的方式向世界展演出了鮮活、真切的地理疆域形象。中華民族正在借由這些深入文化根部的媒介景觀打造豐滿的自我形象,也吸引著全球的目光。這個形象既是傳統的,又是時尚的;既充滿“中國范”,又蘊含著普世價值理念。以李子柒、丁真等為代表的“中國影像”已走向了世界,而更多的中國鄉村媒介景觀將在西部敘事和地理文化格局的變遷這一廣袤的時代語境中,得到延續和彰顯。
四、結 語
短視頻屬于新媒體時代一種新興的文藝創作,作為一種新的藝術生產樣式正在成為資本追逐的風口。“田園風”短視頻致力于對鄉村的“擬像化”和“仿真化”呈現,由此引導“情感消費”,已成為當下常規化的消費產業鏈。但是,我們并不能因為短視頻背后的流量變現模式而否定其審美引領的價值,作為文化消費產品,情感消費的過程也包含著觀眾接受意識形態的詢喚而成為審美主體的過程,從撫慰自我的“現代性焦慮”,進而對“主流控制敘事”進行反思,重構自我的人生坐標等,“田園風”短視頻在當下具有重要的審美救贖意義。
“鄉村牧歌”式媒介景觀的風行和走紅,正是“審美現代性”作為“自反性現代性”在歷史節點上的彰顯。作為審美意象,“田園風”短視頻中蘊涵的“慢速”生活理念、與自然合拍的人生狀態,以及溫柔敦厚的中國美學精神,在經歷“現代性危機”后世界的重啟中,理應有新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