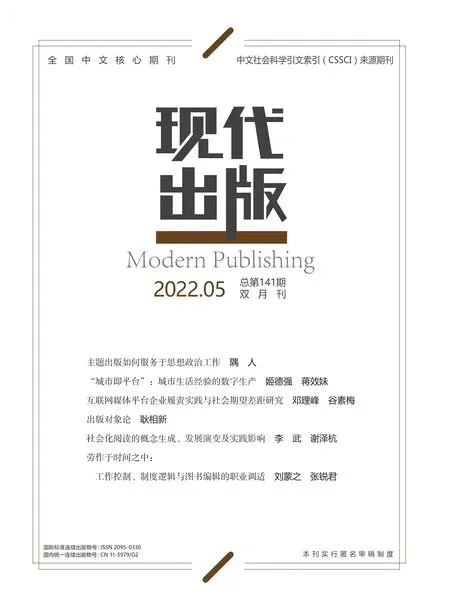出版對(duì)象論
耿相新
在出版學(xué)教科書中,我們找不到有關(guān)“出版對(duì)象”的章節(jié)。但在具體的出版活動(dòng)中,作為出版人,我們卻每天都在和出版對(duì)象打各種各樣的交道。這是一個(gè)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也許還是一個(gè)不值得一問的問題。然而,出版對(duì)象到底是什么?難道它就是我們桌子上或者計(jì)算機(jī)屏幕上的文本稿件?抑或是等待校對(duì)的書稿清樣?或許,我們還可以根據(jù)出版社的不同類型將出版對(duì)象區(qū)分為圖書館分類法中的各類圖書,甚至還可以將其劃分為音像電子出版物和紙質(zhì)出版物等。不過,以上歸類依然沒有解決問題。出版對(duì)象到底是由什么構(gòu)成的?通過對(duì)現(xiàn)實(shí)出版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對(duì)世界出版50強(qiáng)的對(duì)比性觀察,我認(rèn)為,在數(shù)字時(shí)代,出版對(duì)象已經(jīng)發(fā)生重大位移。無疑,重新界定和討論出版對(duì)象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本文擬從出版符號(hào)、出版符號(hào)被傳遞物內(nèi)容類型和出版符號(hào)傳遞物介質(zhì)形式三個(gè)方面,試圖厘清出版對(duì)象的問題,并試圖喚起學(xué)界和業(yè)界對(duì)此問題的重視。
一、出版符號(hào)的界定
出版活動(dòng)實(shí)質(zhì)上就是人類符號(hào)的一個(gè)傳遞過程。德國哲學(xué)家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說:“人是符號(hào)的動(dòng)物。”①為了說明“符號(hào)”,卡西爾區(qū)分了信號(hào)和符號(hào),他認(rèn)為“信號(hào)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號(hào)則是人類的意義世界之一部分”,人之外的動(dòng)物可以感知信號(hào),“動(dòng)物具有實(shí)踐的想象力和智慧,而只有人才發(fā)展了一種新的形式:符號(hào)化的想象力和智慧”,“符號(hào)化的思維和符號(hào)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fā)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②他進(jìn)一步認(rèn)為,人自覺地創(chuàng)造并運(yùn)用符號(hào),由此創(chuàng)造了文化,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符號(hào)的宇宙”,人、符號(hào)、文化三位一體,因此“人是符號(hào)的動(dòng)物”。符號(hào)是中介和媒介,它架起了人與文化之間的橋梁。而出版作為一種人類文化活動(dòng),它使用的工具和作用的對(duì)象就是人所創(chuàng)造的各種各樣的符號(hào)。
既然符號(hào)構(gòu)成了人的意義世界,那么符號(hào)究竟是由什么構(gòu)成的?或者,我們應(yīng)當(dāng)直接提問:什么是符號(hào)?簡(jiǎn)單地說,符號(hào)是攜帶意義的記號(hào)。英文中symbol(符號(hào))這個(gè)詞“來自希臘文里代表token(象征)或token of identity(身份的象征)之義的詞,它結(jié)合了兩個(gè)詞根:sum(一起)和動(dòng)詞ballo(丟擲),對(duì)‘符號(hào)’一詞較寬松的詮釋是‘放在一起’”③。放在一起的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其本源的意指是某人證明某人的關(guān)系。美國《韋氏詞典》對(duì)符號(hào)的定義是“由于關(guān)系、聯(lián)想、習(xí)俗成規(guī)或偶然而非有意的類似,來代表或使之聯(lián)想到其他事物的某種事物”④。這個(gè)定義強(qiáng)調(diào)了“某種事物”能夠代指另一種事物,與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觀點(diǎn)十分一致。雅各布森認(rèn)為符號(hào)具有兩個(gè)方面:“一個(gè)是可以直接感覺到的指符(signals),另一個(gè)是可以推知和理解的被指(signature)。”⑤這個(gè)觀點(diǎn)與費(fèi)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關(guān)于符號(hào)是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guān)系異曲同工。美國哲學(xué)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對(duì)以上的符號(hào)概念進(jìn)行了大大的拓展。皮爾斯認(rèn)為,整個(gè)宇宙充滿了符號(hào)。他給符號(hào)的定義是:“符號(hào),或代表項(xiàng),是對(duì)于某人在某一側(cè)面或能力方面代表了某物的東西。它對(duì)某人說話,也就是說,它在此人的思維中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相對(duì)應(yīng)的符號(hào),或者一個(gè)更加發(fā)展了的符號(hào)。那個(gè)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符號(hào)我稱之為第一個(gè)符號(hào)的解釋項(xiàng)。”⑥這個(gè)定義突破了符號(hào)的能指和所指二元結(jié)構(gòu)而成為“符號(hào)、符號(hào)的對(duì)象與符號(hào)的解釋項(xiàng)”三元結(jié)構(gòu),符號(hào)活動(dòng)就是一個(gè)三元過程,也即“符號(hào)首先是一種解釋項(xiàng),是一種響應(yīng),通過這種響應(yīng)的解釋,另外某種東西才能被看作符號(hào),從而成為被解釋項(xiàng),而且,還能夠生產(chǎn)一個(gè)開放的、由其他符號(hào)組成的符號(hào)鏈”⑦。沿著由符號(hào)的解釋與被解釋并產(chǎn)生新的符號(hào)這一邏輯,任何事物,凡是能夠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就是符號(hào)。皮爾斯在《關(guān)于意義的論文》中列舉了大量的符號(hào)例子,如:畫像、圖片、圖表、手指、眨眼、手帕結(jié)、回憶、幻想、概念、指示、標(biāo)志、數(shù)字、信件、詞、短語、句子、篇章、書籍、圖書館、信號(hào)、命令、顯微鏡、立法代表、音符、音樂會(huì)、表演、自然哭喊,等等。⑧同時(shí),皮爾斯還將數(shù)學(xué)、化學(xué)、心理學(xué)等17門學(xué)科也歸入符號(hào)學(xué)的研究范疇。基于以上認(rèn)識(shí),我們可以將符號(hào)理解為一個(gè)能夠解釋的標(biāo)記或者記號(hào),這個(gè)解釋就是意義,符號(hào)就是表達(dá)意義的載體和表達(dá)意義的條件,而“意義就是一個(gè)符號(hào)可以被另外的符號(hào)解釋的潛力”⑨。換句話說,人的世界就是符號(hào)的世界,也是意義的世界。而出版活動(dòng)的目的正是表達(dá)和傳播意義,自然而然,符號(hào)必然也必須成為出版的表達(dá)和傳播工具。因此,出版的對(duì)象就是人所創(chuàng)造的符號(hào)和對(duì)符號(hào)的解釋。
毫無疑問,人是符號(hào)的制造者,也是符號(hào)的接受者。人的嗅覺、味覺、觸覺、聽覺、視覺五種感官的任何活動(dòng)都具有作為符號(hào)或者成為符號(hào)的潛能。雅各布森尤其重視視覺和聽覺,他說:“人類社會(huì)中最社會(huì)化、最豐富和最貼切的符號(hào)系統(tǒng)顯然以視覺和聽覺為基礎(chǔ)。”⑩作為符號(hào)系統(tǒng)的聽覺,其最明顯的表征是口頭語言和音樂藝術(shù),聲音成為符號(hào)意義的載體。而視覺符號(hào)系統(tǒng)則更傾向于身體姿勢(shì)、書面語言、文本作品、圖像、造型藝術(shù)等。當(dāng)語言被文字符號(hào)記錄而成為文本性的書籍,或者綜合運(yùn)用了空間場(chǎng)景的表演藝術(shù),如演講、課程、戲劇、歌劇、電影、電視等視頻式藝術(shù),則是整合了聽覺符號(hào)和視覺符號(hào)。隨著數(shù)字計(jì)算機(jī)圖形軟件技術(shù)的發(fā)展,虛擬現(xiàn)實(shí)和增強(qiáng)現(xiàn)實(shí)的虛擬影像也一同成為符號(hào)意義的載體。基于以上認(rèn)識(shí),我們將出版符號(hào)歸類為五個(gè)系統(tǒng):文字符號(hào)系統(tǒng)、圖像符號(hào)系統(tǒng)、聲音符號(hào)系統(tǒng)、視頻符號(hào)系統(tǒng)和虛擬符號(hào)系統(tǒng),此五類符號(hào)系統(tǒng)構(gòu)成了總體的出版符號(hào)。
出版是一種符號(hào)生產(chǎn)和消費(fèi)。文字符號(hào)的出版自出版誕生以來即為出版的主流。文字符號(hào)系統(tǒng)是人類的重要發(fā)明之一。在人類古文明時(shí)期,不同的文明發(fā)明了不同的文字符號(hào)系統(tǒng)。人類的語言有7 000種左右,但進(jìn)化到記錄語言的文字系統(tǒng)卻只有幾百種。文字是人類使用聲音、語言的代號(hào)或符號(hào)進(jìn)行視覺交際和傳遞信息的系統(tǒng),這些符號(hào)或代號(hào)與聲音或語言單位的意義約定性地相對(duì)應(yīng)。最早的文字符號(hào)系統(tǒng)起源于圖形符號(hào),也可稱之為象形符號(hào),它是一種象征性代號(hào),這些代號(hào)或符號(hào)可以提煉一個(gè)人或一件事情的特征、特點(diǎn)、特性,并以形象的圖畫形式進(jìn)行表示,這些符號(hào)也對(duì)應(yīng)于口語中的人或事物,約定俗成并形成慣例后便成為文字符號(hào)。迄今,人類所發(fā)明的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主要有三種類型:詞符與音節(jié)符并用的文字、音節(jié)文字和字母文字。如果一個(gè)符號(hào)代表一個(gè)詞,使用大量的符號(hào)即可形成詞符文字系統(tǒng),但此勢(shì)必造成詞符數(shù)量巨大,而且抽象詞也難以表達(dá)。蘇美爾人、古埃及人、中國人把一部分詞符改成不表意、只表音,并將其置于詞符之間,用來表示其他與此讀音相同或相似的詞。蘇美爾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赫梯文字、中國甲骨文字是發(fā)明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詞符和音符并用的文字系統(tǒng),從甲骨文字流變而來的漢字目前依然是中國日常使用的書寫文字和出版符號(hào)。音符也即音節(jié)符號(hào)、語音符號(hào),相對(duì)于詞符數(shù)量較少并相對(duì)穩(wěn)定,如果舍棄數(shù)量巨大的詞符而全部使用音節(jié)符號(hào),那就成為“音節(jié)文字”,音節(jié)文字以楔形音節(jié)文字,西部閃米特音節(jié)文字(腓尼基文字、希伯來文字、阿拉米文字),愛琴海音節(jié)文字,日本音節(jié)文字(假名),埃塞俄比亞文字(阿姆哈拉文字)為代表。其中,日文是詞符和音節(jié)符并用的文字,但其假名是音節(jié)符號(hào)。文字符號(hào)可概分為表形、表意和表音三種類型。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開始使用表音的限定符號(hào),大量和重復(fù)使用的26個(gè)單輔音符號(hào)(每個(gè)符號(hào)代表一個(gè)輔音)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字母表。早期的輔音符號(hào)幾乎全部與詞符、音符和限定符號(hào)一起使用,公元前2000年前時(shí)埃及人開始只用輔音字母書寫,這一符號(hào)書寫原則很快傳入西奈半島和黎凡特地區(qū)的閃米特族人中。?從古埃及的輔音字母表,演化為閃米特語的原始字母表,最后演變?yōu)槲鞣浇裉鞆V泛使用的拉丁字母表。公元前1000年左右,閃語字母演變?yōu)槟祥W語字母系統(tǒng)、迦南語字母系統(tǒng)、亞蘭語字母系統(tǒng)和希臘語字母系統(tǒng)四大支系。迦南語系又再分化為早期希伯來文和腓尼基文。亞蘭語系中的閃語字母系統(tǒng)包括方體希伯來文(現(xiàn)代希伯來文原型)、新西奈阿拉伯文、帕爾米拉字母、古敘利亞景教文、摩尼文等,非閃語分支中從亞蘭字母衍生出的文字主要有印度婆羅米文、佉盧文、波斯文、粟特文、青帳突厥文、維吾爾文、蒙古文等。希臘人在西閃米特輔音字母表中,加入元音而創(chuàng)造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gè)完整的字母文字體系,古希臘文又演化為伊特拉斯坎字母、斯拉夫語系的西瑞爾字母,拉丁字母(羅馬字母)是伊特拉斯坎字母的支系。拉丁字母成為基督教官方文字后,被應(yīng)用到許多不同的語言上,如日耳曼語系的英文、德文、瑞典文、丹麥文、挪威文、荷蘭文;拉丁語系的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斯拉夫語系的波蘭文、捷克文、克羅地亞文、斯洛文尼亞文;芬蘭語系的芬蘭-烏戈?duì)栁摹⑿傺览牡取?從詞符-音符文字、音節(jié)文字和字母文字的溯源可以看到,音節(jié)文字很早就被字母文字替代了,現(xiàn)在流傳下來并仍在使用的文字系統(tǒng)只剩下中國的漢字系統(tǒng)(日文源于漢字)和源于埃及輔音字母的字母文字及其各種變種。人類歷史上的書籍均是由不同的文字系統(tǒng)書寫的。印刷術(shù)發(fā)明之后,漢字書籍(包括日本、朝鮮、越南的漢籍)主要使用雕版印刷和銅活字印刷,字母文字書籍使用古登堡鉛活字印刷機(jī)印刷。19世紀(jì)以來的工業(yè)印刷機(jī)和20世紀(jì)中葉以來的計(jì)算機(jī)數(shù)字技術(shù)逐步淘汰和挑戰(zhàn)紙質(zhì)出版,但這只是出版技術(shù)的演替而已,書籍出版的符號(hào)系統(tǒng)依然是詞符—音符的漢字系統(tǒng)和字母文字系統(tǒng)。通過對(duì)文字符號(hào)的探究,我們不得不說,不同書籍使用不同文字符號(hào)而呈現(xiàn)內(nèi)容,這是出版活動(dòng)的根基,實(shí)際上,某一語言文字的邊界也就是某一出版活動(dòng)的疆界。同理,突破原有出版符號(hào)版圖的翻譯活動(dòng),始終是推動(dòng)文化交流的一種動(dòng)力。在此,文字符號(hào)不僅是出版對(duì)象,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對(duì)出版的一種限制。
出版的本質(zhì)是為了促進(jìn)文化和語言交流。廣義上的文化語言交流,有學(xué)者將其分為三大類型:科技指示符碼—科學(xué)語言(數(shù)學(xué)語言、音樂、化學(xué)、物理、邏輯語、曼瑟爾表色系統(tǒng)、音標(biāo)系統(tǒng))與機(jī)器語言(C語言、Java、二進(jìn)制、二維碼);文化規(guī)約符碼—自然語言(圖像、自然語言、網(wǎng)絡(luò)生成符號(hào)、藝術(shù)創(chuàng)作語言);混合理據(jù)符碼—傳播語言(公共標(biāo)識(shí)系統(tǒng)、手語、旗語、各種指示符號(hào)、圖像混合語言、圖像化音樂記譜語言)。?從這個(gè)相對(duì)系統(tǒng)和完整的語言符碼角度出發(fā),我們可以看到計(jì)算機(jī)時(shí)代傳播和出版符號(hào)的廣度。除文字符號(hào)外,包括計(jì)算機(jī)圖形符號(hào)在內(nèi)的圖像符號(hào)越來越凸顯其重要性。圖像不再單純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圖畫、繪畫、照片、雕塑,現(xiàn)在也應(yīng)包括計(jì)算機(jī)條件下的設(shè)計(jì)、圖形和鏡像等。
圖像進(jìn)入書籍內(nèi)部的時(shí)間十分久遠(yuǎn)。從時(shí)間性上說,圖畫早于文字誕生。書籍誕生之后,插圖也緊隨其后進(jìn)入書籍內(nèi)部結(jié)構(gòu)。早在戰(zhàn)國時(shí)期,中國的竹簡(jiǎn)書籍中就已出現(xiàn)插圖,出土于長(zhǎng)沙的戰(zhàn)國楚帛書也可以被視為一本圖文結(jié)合的書籍。出土于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制作于漢代初年,其中的《天文氣象雜占》等書籍是圖文并茂的。《山海經(jīng)》在漢代是圖文相間的。雕版印刷術(shù)發(fā)明不久,雕版圖像就已成為雕印書籍的一部分,如雕印于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剛經(jīng)》,在書首就置有一幅精美絕倫的題為《祇樹給孤獨(dú)園》的圖畫。明清時(shí)期,雕版繡像插圖更成為書籍美學(xué)呈現(xiàn)方式的普遍現(xiàn)象。世界上最早的書籍插圖可追溯到古埃及的《死者書》(Book of the Dead)中的圖畫。在西方,現(xiàn)今存世最早的附有插圖的手抄本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jì)》,是公元4世紀(jì)或5世紀(jì)時(shí)制作的。?中世紀(jì)的手抄本中大多手繪有極其精美的“裝飾畫”。古登堡發(fā)明鉛活字印刷術(shù)之后,西方的印刷版畫開始興起。出版于1493年的《紐倫堡編年史》一書中附有插圖1 809幅,堪稱插圖書杰作。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阿爾勃萊希特·丟勒(Albrecht Durer)是最著名的書籍插圖家。與木版版畫相比,后起的蝕刻凹版印刷技術(shù)銅版版畫線條更加纖細(xì)優(yōu)美,18世紀(jì)后凹版插圖逐步替代了凸版插圖。1843年,英國人安娜·阿特金斯(Anna Atkins)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使用攝影照片的書籍《英國藻類圖片集:氰版照相法印制》。?從此,攝影照片開始大量涌入書籍內(nèi)部,在工業(yè)印刷最鼎盛的20世紀(jì),專業(yè)的攝影書籍甚至成為一個(gè)重要的出版門類。在數(shù)碼攝影技術(shù)崛起后的21世紀(jì),照片的生產(chǎn)量達(dá)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僅社交網(wǎng)站Facebook上一天上傳的圖片就有數(shù)億張,數(shù)字照片開始成為重要的出版對(duì)象。圖像作為一種出版符號(hào)將有可能超越文字符號(hào)而成為最重要的出版存在。
聲音作為一種人類交流和傳播媒介,其起源與人類語言的誕生同步。聲音的易逝性特點(diǎn)決定了其作為一種出版符號(hào)的困難,但人類努力記錄聲音的探索卻一直未曾停止。依據(jù)記錄聲音的技術(shù),我們將聲音符號(hào)分為間接記錄聲音符號(hào)和直接記錄聲音符號(hào),前者主要指需要用文字或其他符號(hào)記錄的聲音,后者指模擬信號(hào)的錄音、無線電廣播和數(shù)字化數(shù)據(jù)音頻。以書籍形式記錄的聲音符號(hào)在錄音技術(shù)發(fā)明之前,主要類型有音樂樂譜,戲劇劇本和說唱、講唱、彈唱文學(xué)底本。中國最早記錄曲譜的書籍出現(xiàn)于漢代,《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河南周歌聲曲折》7篇、《周謠歌詩聲曲折》75篇就是最早的樂譜,聲曲折是一種古代的歌詩演唱時(shí)對(duì)曲調(diào)的記錄方法,是依據(jù)曲調(diào)高低上下而繪制的一種樂譜,具體形態(tài)已不可知。中國古代最初是用文字記譜,現(xiàn)存的唐代手抄本《碣石調(diào)·幽蘭》是目前僅見的一首用文字記述彈奏手法的琴曲,此文字譜用了4 954個(gè)漢字。?唐代曹柔創(chuàng)新古琴記譜法為減字譜(指法譜),沿用至今。同樣起源于唐代的還有“燕樂半字譜”(工尺譜),在敦煌遺書中發(fā)現(xiàn)有數(shù)種四弦四相琵琶曲子譜,即燕樂半字譜。南宋詞人姜夔的詞曲譜集《白石道人歌曲》(6卷)中有17首詞姜夔自注工尺譜,是“至今傳世的唯一詞調(diào)曲譜”?。明清時(shí)期,民間雕印了大量琴曲小冊(cè)子,而雕版印刷的戲劇劇本和民間唱本,更多達(dá)數(shù)千種,這些都可以被歸類為間接記錄聲音符號(hào)的出版物。錄音技術(shù)被發(fā)明后,尤其是廣播技術(shù)和數(shù)字音頻技術(shù)被廣泛應(yīng)用后,聲音符號(hào)迅速發(fā)展成為人類最重要的大眾媒介之一。錄音技術(shù)和錄音機(jī)(留聲機(jī))是美國發(fā)明家T.A.愛迪生(Thomas Edison)于1877年發(fā)明的,其后,錄音和放音介質(zhì)發(fā)展為力學(xué)介質(zhì)(留聲機(jī)唱片)、磁性介質(zhì)(錄音帶)和光學(xué)介質(zhì)(電影的聲道與數(shù)字式小型光盤),與書籍出版關(guān)聯(lián)度較高的是磁帶,磁帶錄音主要分為開盤式和盒式兩種,以學(xué)習(xí)語言為主的教學(xué)帶主要使用盒式磁帶,在數(shù)字技術(shù)和互聯(lián)網(wǎng)興起之前,盒式磁帶曾是音像出版業(yè)的主要產(chǎn)品。廣播是利用電子技術(shù)向公眾播送無線電或電視信號(hào),它實(shí)現(xiàn)了遠(yuǎn)距離、實(shí)時(shí)、一對(duì)多的單向傳播,無線電廣播只傳播音頻,電視則同時(shí)傳播視頻和音頻,二者向廣大聽眾和觀眾傳播的內(nèi)容主要是教育、新聞和娛樂等節(jié)目。廣播系統(tǒng)、電視系統(tǒng)是與出版系統(tǒng)并行的大眾傳媒,廣播系統(tǒng)興起于20世紀(jì)20年代,電視系統(tǒng)大約興起于20世紀(jì)50年代,它們與圖書出版的關(guān)聯(lián)部分主要在教育方面,遠(yuǎn)程的廣播和電視大學(xué)所使用的教材和教學(xué)輔助材料通常以紙質(zhì)圖書的形式出版。中國自宋代開始流行的口頭講說表演藝術(shù),如說書、講書、評(píng)書、講古、評(píng)話、評(píng)詞等不同稱呼的說話藝術(shù),在廣播、電視興起后,也開始成為廣播和電視的節(jié)目,但表演藝術(shù)家們的底本(話本),通常還會(huì)以紙質(zhì)介質(zhì)的形式出版和傳播。1983年建成的國際互聯(lián)網(wǎng),于90年代崛起為一個(gè)具有覆蓋媒介功能的超級(jí)大眾媒介,以數(shù)字化、電子化的文字、圖像、音頻、視頻形式覆蓋了以往的圖書、雜志、報(bào)紙、攝影、錄音錄像、電影、廣播、電視等媒介,以往的媒體內(nèi)容逐步遷徙到互聯(lián)網(wǎng)和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上,數(shù)字音頻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和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上必不可少的一個(gè)角色。聲音符號(hào)直接轉(zhuǎn)換為數(shù)字形式之后,聽書成為一種開始崛起的出版產(chǎn)品。1997年中國的網(wǎng)絡(luò)廣播誕生,2004年基于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的博客、網(wǎng)絡(luò)聽書網(wǎng)站興起,2012年規(guī)模化的音頻聚合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出現(xiàn),基于聲音符號(hào)的音頻介質(zhì)開始朝垂直化、社群化、產(chǎn)業(yè)化的方向發(fā)展。?數(shù)字音頻越來越成為一種商業(yè)化的出版對(duì)象。
視覺符號(hào)影像或視頻成為出版對(duì)象的時(shí)間相對(duì)較晚。視覺是人類最原初的感知感官之一,也是人類初始信息交流的媒介之一。在口語時(shí)代,面對(duì)面的視覺交流是最有效的信息傳遞方式。即便是在通過網(wǎng)絡(luò)進(jìn)行遠(yuǎn)距離即時(shí)視頻交流十分便捷和發(fā)達(dá)的今天,面對(duì)面的視覺交流依然不可替代。將人體的姿勢(shì)、手勢(shì)和表情記錄下來成為視頻符號(hào),起源于1888年T.A.愛迪生和他的助手發(fā)明的第一個(gè)實(shí)用的活動(dòng)圖片攝像機(jī),之后他們還發(fā)明了活動(dòng)電影放映機(jī)。1903年之后,隨著技術(shù)的不斷進(jìn)步,電影成為一個(gè)大眾媒體并形成了巨大的產(chǎn)業(yè)。緊隨電影之后,以影像為媒介的電視媒體崛起于20世紀(jì)50年代。英文單詞“Television”(電視)1900年被法國人康斯坦丁·伯斯基創(chuàng)造,本意是“遠(yuǎn)距離觀看”“用電來看”。?與電影不同,電視與無線電廣播和有線電話是近親,屬于電子媒體。電視是活動(dòng)圖像和其聲音的電子信號(hào)傳輸。電視攝像機(jī)將圖像和聲音轉(zhuǎn)換為電脈沖信號(hào),這些高頻無線電載波信號(hào)由發(fā)射天線發(fā)出,被接收天線拾取并再轉(zhuǎn)化為光的亮度變化,在接收機(jī)的熒幕上顯示出來。1936年11月2日,英國廣播公司正式播出電視節(jié)目,被視為電視正式誕生日。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有線電視、衛(wèi)星電視分別加入電視網(wǎng),直到21世紀(jì)初以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為技術(shù)基礎(chǔ)的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的崛起,兼顧了視頻和音頻優(yōu)勢(shì)的電視媒體才開始衰落。電視視頻和圖書出版相結(jié)合的部位主要體現(xiàn)在教育出版領(lǐng)域的教學(xué)課堂和課程上,視頻課與紙質(zhì)書互相支持對(duì)方。但在電視視頻和數(shù)字圖書分別遷徙到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上時(shí),它們雙方都重新找到了新營地。圖書出版將原有的紙質(zhì)圖書內(nèi)容轉(zhuǎn)化成了視頻形式的教學(xué)課程、軟件和學(xué)習(xí)材料,文字作者開始直面鏡頭而轉(zhuǎn)化為演講時(shí)的影像,視頻符號(hào)開始大規(guī)模地進(jìn)入出版領(lǐng)域。視頻符號(hào)成長(zhǎng)為出版對(duì)象,并開始朝專業(yè)化、垂直化、知識(shí)化、課程化、產(chǎn)業(yè)化的方向發(fā)展。
虛擬符號(hào)是由計(jì)算機(jī)創(chuàng)建和產(chǎn)生的。隨著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的發(fā)展,虛擬符號(hào)攜帶意義的場(chǎng)景應(yīng)用越來越多并越來越具有商業(yè)性。計(jì)算機(jī)虛擬符號(hào)已經(jīng)開始成為重要的出版符號(hào),其商業(yè)價(jià)值越來越凸顯。從我們熟悉的虛擬現(xiàn)實(shí)(VR)中追尋一下它的技術(shù)基礎(chǔ),可以得知虛擬現(xiàn)實(shí)的技術(shù)支撐是計(jì)算機(jī)圖形和圖像。虛擬現(xiàn)實(shí)(VR)是“計(jì)算機(jī)創(chuàng)造并以計(jì)算機(jī)為媒介的對(duì)真實(shí)或想象的環(huán)境的模擬”,它是一種虛擬環(huán)境,通過三維(寬度、高度和深度)圖像的體驗(yàn)來提供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幻覺。?三維圖像是關(guān)鍵技術(shù),三維圖像的顯示可以通過頭戴式顯示器、立體眼鏡、耳機(jī)、運(yùn)動(dòng)平臺(tái)、數(shù)據(jù)服裝(數(shù)據(jù)手套)和其他互動(dòng)裝置呈現(xiàn)。計(jì)算機(jī)的硬件和軟件構(gòu)成一種交流媒介,通過人機(jī)互動(dòng)裝置像交流文字符號(hào)和聲音符號(hào)一樣交流圖像、聲音和動(dòng)態(tài)模型以形成仿真模擬。三維圖像的底層技術(shù)是計(jì)算機(jī)圖形和圖像,計(jì)算機(jī)圖形是由計(jì)算機(jī)繪制的直線、圓、矩形、曲線、圖表等外部線條構(gòu)成的矢量圖,計(jì)算機(jī)圖像是由像素點(diǎn)陣構(gòu)成的位圖,計(jì)算機(jī)可以將一件現(xiàn)實(shí)存在的或想象的視覺信息以數(shù)字化的圖形和圖像形式表達(dá)為仿真的形象,運(yùn)用透視線條、隱藏表面消除等技術(shù)使二維的計(jì)算機(jī)屏幕能夠有效地模擬三維世界,從而形成虛擬現(xiàn)實(shí)式的計(jì)算機(jī)模擬世界。虛擬現(xiàn)實(shí)(VR)已被廣泛應(yīng)用于藝術(shù)、工程設(shè)計(jì)、娛樂游戲、工業(yè)仿真、培訓(xùn)實(shí)訓(xùn)、課堂教育、醫(yī)學(xué)、軍事、航空航天、能源交通、生物、水文地質(zhì)、事故還原、工業(yè)制造等領(lǐng)域。和傳統(tǒng)出版關(guān)聯(lián)度較高的是教育領(lǐng)域,虛擬現(xiàn)實(shí)技術(shù)能夠?yàn)閷W(xué)生提供一個(gè)生動(dòng)、逼真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可以為學(xué)生提供諸如物理、化學(xué)、生物等虛擬實(shí)驗(yàn),也可以為職業(yè)學(xué)校的學(xué)生提供各種虛擬演練和動(dòng)作操作。數(shù)字技術(shù)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計(jì)算機(jī)所創(chuàng)造的虛擬圖形和圖像,它們也同樣起到了攜帶意義的中介符號(hào)的作用,已經(jīng)演變成一種出版符號(hào)。
二、出版符號(hào)被傳遞物內(nèi)容類型
如果我們將出版符號(hào)理解為出版活動(dòng)中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那么,我們隨之要進(jìn)一步思考的是,作為中介的出版活動(dòng)在時(shí)間和空間上要傳遞的內(nèi)在形式是什么?符號(hào)學(xué)中將符號(hào)的傳遞分為遺傳和傳統(tǒng)兩種類型。遺傳屬于生物學(xué)中基因代碼的范疇,而傳統(tǒng)則被視為“一種文化可被看作是一個(gè)有機(jī)體群體,其行為方式受制于特殊傳統(tǒng),即經(jīng)由學(xué)習(xí)獲得之,并在創(chuàng)造性的修正之后將其傳至下一代”?。關(guān)于遺傳和傳統(tǒng),《符號(hào)學(xué)手冊(cè)》的作者認(rèn)為:“兩種傳遞類型(遺傳和傳統(tǒng))都是記號(hào)過程,而且被傳遞物(知識(shí)、態(tài)度、生產(chǎn)技能和制造物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記號(hào)為基礎(chǔ)的。”?符號(hào)的創(chuàng)造過程也就是記號(hào)的過程,由記號(hào)(符號(hào))的生物性所決定,符號(hào)傳遞既具有一代一代的時(shí)間性,也具有地理概念下的空間性。無論是傳遞的生命力,還是傳遞的廣度,出版活動(dòng)中的核心要素是首先要界定清楚傳遞什么,換句話說,被傳遞物是什么。我們認(rèn)為,出版活動(dòng)中的被傳遞物是數(shù)據(jù)、信息、知識(shí)和智慧。
狹義的數(shù)據(jù)指數(shù)字或數(shù)值,是人類通過觀察、實(shí)驗(yàn)、檢驗(yàn)、統(tǒng)計(jì)或計(jì)算,通過對(duì)客觀事物的邏輯歸納而得出的結(jié)果,也指用于進(jìn)行各種數(shù)學(xué)統(tǒng)計(jì)、計(jì)算、查證、決策、科學(xué)研究、技術(shù)設(shè)計(jì)等的數(shù)值。英文單詞data(數(shù)據(jù))是指“一個(gè)有意義的事實(shí)和數(shù)值總體”,中文的“數(shù)據(jù)”定義是“指對(duì)客觀事物進(jìn)行記錄并可以鑒別的符號(hào),是對(duì)客觀事物的性質(zhì)、狀態(tài)以及相互關(guān)系等進(jìn)行記載的物理符號(hào)或這些物理符號(hào)的組合”?。從數(shù)據(jù)的表現(xiàn)形式上可將其分為離散數(shù)值和連續(xù)數(shù)值,即數(shù)字?jǐn)?shù)據(jù)和模擬數(shù)據(jù),數(shù)字?jǐn)?shù)據(jù)主要為各種統(tǒng)計(jì)或量測(cè)數(shù)據(jù),模擬數(shù)據(jù)指在一定的區(qū)間內(nèi)連續(xù)變化的物理量,包括圖形數(shù)據(jù)、符號(hào)數(shù)據(jù)、文字?jǐn)?shù)據(jù)、圖像數(shù)據(jù)等。如果依數(shù)據(jù)的物理性質(zhì),還可以將其分為定位的坐標(biāo)數(shù)據(jù)、定性事物屬性的定性數(shù)據(jù)、反映事物數(shù)量的定量數(shù)據(jù)和反映事物時(shí)間特征的定時(shí)數(shù)據(jù)。在計(jì)算機(jī)數(shù)據(jù)庫時(shí)代,數(shù)據(jù)被定義為“描述事物的符號(hào)記錄”,“描述事物的符號(hào)可以是數(shù)字、文字、圖形、圖像、聲音、流數(shù)據(jù)、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即數(shù)據(jù)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數(shù)據(jù)可以是結(jié)構(gòu)化的、半結(jié)構(gòu)化的和無結(jié)構(gòu)的”?。結(jié)構(gòu)化數(shù)據(jù)是指可以被計(jì)算機(jī)識(shí)別的數(shù)據(jù),是“具有一定結(jié)構(gòu)性、可以劃分為固定的基本組成要素、能夠通過一個(gè)或多個(gè)二維表來表示的數(shù)據(jù)”?。結(jié)構(gòu)化數(shù)據(jù)主要是應(yīng)用于關(guān)系型數(shù)據(jù)庫和面向?qū)ο髷?shù)據(jù)庫中的數(shù)據(jù)。半結(jié)構(gòu)化數(shù)據(jù)主要應(yīng)用于XML(可擴(kuò)展標(biāo)記語言)和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網(wǎng)頁。非結(jié)構(gòu)化數(shù)據(jù)是指不是以一種預(yù)先定義好的方式進(jìn)行組織的數(shù)據(jù),在表現(xiàn)形態(tài)上主要包括文本、圖片、音頻、視頻等,“世界上大約80%的數(shù)據(jù)是以文本、照片和圖像等非結(jié)構(gòu)化數(shù)據(jù)的形式存在”?。通過對(duì)“數(shù)據(jù)”概念的理解,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認(rèn)識(shí)到,數(shù)據(jù)已經(jīng)不再是單純的數(shù)學(xué)概念下的數(shù)字或數(shù)值,它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演化為記錄和描述一切事物的符號(hào)。自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得到迅猛發(fā)展,數(shù)據(jù)庫出版迅速成為一種新的出版形式,數(shù)據(jù)隨之成為最富有前景的出版對(duì)象。
數(shù)據(jù)本身并不能完全表達(dá)事物的內(nèi)容,需要解釋才能表達(dá)出完整的意義,對(duì)數(shù)據(jù)含義的說明既是一種數(shù)據(jù)解釋,同時(shí)也是對(duì)數(shù)據(jù)的一種加工。在計(jì)算機(jī)系統(tǒng)中,數(shù)據(jù)是所有能以二進(jìn)制信息單元0、1的形式輸入計(jì)算機(jī)并被計(jì)算機(jī)程序處理的符號(hào)的介質(zhì)的總稱。數(shù)據(jù)的價(jià)值在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發(fā)明之后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數(shù)據(jù)經(jīng)過組織和加工產(chǎn)生價(jià)值和意義。對(duì)各種數(shù)據(jù)進(jìn)行收集、存儲(chǔ)、加工、傳播、應(yīng)用是一種數(shù)據(jù)處理活動(dòng),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類、組織、表示、編碼、存儲(chǔ)、存取、控制、維護(hù)是形成數(shù)據(jù)庫的關(guān)鍵。數(shù)據(jù)庫就是用數(shù)據(jù)模型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數(shù)據(jù)特征進(jìn)行抽象、描述、組織和控制,是一種持久存儲(chǔ)在計(jì)算機(jī)內(nèi)的有組織、可共享的數(shù)據(jù)集合。依數(shù)據(jù)庫管理模式,數(shù)據(jù)庫分為層次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網(wǎng)狀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關(guān)系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面向?qū)ο髷?shù)據(jù)庫系統(tǒng)、演繹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分布式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并行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工程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Web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混合型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等形式。按照應(yīng)用領(lǐng)域、市場(chǎng)用戶需求和商業(yè)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已經(jīng)進(jìn)入市場(chǎng)并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效益的特定的、專業(yè)的、特種的數(shù)據(jù)庫大體有:與計(jì)算機(jī)并行和分布式技術(shù)結(jié)合的并行數(shù)據(jù)庫、分布式數(shù)據(jù)庫;與人工智能和計(jì)算智能結(jié)合的主動(dòng)數(shù)據(jù)庫、演繹數(shù)據(jù)庫、模糊數(shù)據(jù)庫、知識(shí)庫等;與多媒體技術(shù)結(jié)合的圖像數(shù)據(jù)庫、圖形數(shù)據(jù)庫、文本數(shù)據(jù)庫、情報(bào)數(shù)據(jù)庫、多媒體數(shù)據(jù)庫等;與計(jì)算機(jī)硬件結(jié)合的內(nèi)存數(shù)據(jù)庫等;滿足特殊需求的實(shí)時(shí)數(shù)據(jù)庫、空間數(shù)據(jù)庫、工程數(shù)據(jù)庫、生物信息數(shù)據(jù)庫等。?作為出版行為的數(shù)據(jù)庫出版,已經(jīng)成為數(shù)字出版的基石,不僅僅是在底層技術(shù)上,在數(shù)字出版產(chǎn)品上它的盈利規(guī)模也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紙質(zhì)出版。
數(shù)據(jù)通常被理解為未經(jīng)過加工和組織的數(shù)字、文字、圖像、圖片、聲音、視頻等原始符號(hào)記錄,而信息則被視為通過人腦或計(jì)算機(jī)對(duì)原始數(shù)據(jù)進(jìn)行篩選、加工和創(chuàng)造后產(chǎn)生的有意義的數(shù)據(jù)。在數(shù)據(jù)和信息的關(guān)系上,可以說,數(shù)據(jù)是信息的表現(xiàn)形式和載體,它們可以是符號(hào)、數(shù)字、文字、圖像、圖形、聲音、視頻等;而信息則是數(shù)據(jù)的內(nèi)涵,是對(duì)數(shù)據(jù)有意義的表示,是對(duì)數(shù)據(jù)做出的具有含義的解釋,“信息是結(jié)構(gòu)化的數(shù)據(jù)”。如此解釋數(shù)據(jù)和信息,是計(jì)算機(jī)時(shí)代的一個(gè)視角解讀,但究竟如何定義信息,或者說如何定義出版活動(dòng)中的信息概念,其實(shí)還存在諸多難度。
在出版活動(dòng)中,我們可以將信息視為用于傳遞、交流、傳播和反饋的關(guān)于客觀事物或意識(shí)、思維、思想的符號(hào)與內(nèi)容。現(xiàn)代意義上的“信息”概念,最經(jīng)典的定義是1948年克勞德·香農(nóng)(Claude E.Shannon)在《通信的數(shù)學(xué)理論》一文中所表述的:“信息是用來消除隨機(jī)不確定的東西。”?香農(nóng)的這篇論文從通信技術(shù)的發(fā)展角度開創(chuàng)了信息論,但他的這個(gè)定義卻是缺乏意義和語境的純粹數(shù)學(xué)概念,他將信息視為發(fā)送者傳遞給接受者的訊息,可以用0和1的符號(hào)串形式來編碼,信息是一個(gè)抽象的科學(xué)概念,可以用數(shù)學(xué)方法加以定量表征,“信息量等于不定性的負(fù)量”。香農(nóng)的信息定義并不和意義產(chǎn)生關(guān)系,他認(rèn)為:“通信的基本問題是在某一點(diǎn)上準(zhǔn)確或大概復(fù)制在另一點(diǎn)上選擇的訊息。訊息常常是有意義的。換言之,它們根據(jù)某一系統(tǒng)指涉某些物理實(shí)體或觀念實(shí)體,或與之有關(guān)聯(lián)。通信的語義方面和工程問題沒有關(guān)聯(lián)。語義的方面是,實(shí)際的訊息選自于一套可能的訊息。”?對(duì)香農(nóng)的信息概念進(jìn)行闡釋和拓展貢獻(xiàn)最大的是沃倫·韋弗(Warren Weaver)和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韋弗從技術(shù)、語義和效用三個(gè)水平方面解讀了香農(nóng)信息和通信研究的方向:“水平A.通信的符號(hào)如何能精確地傳送?(技術(shù)問題)水平B.所傳送的符號(hào)如何準(zhǔn)確地傳達(dá)所希望的意義?(語義問題)水平C.所接收到的意義如何有效地以所希望的方式影響行為?(效用問題)。”?我們可以看到韋弗已經(jīng)將信息理論拓展到了傳播學(xué)領(lǐng)域,他關(guān)注到了符號(hào)的發(fā)送者和接受者,關(guān)注到了信息產(chǎn)生方式、信息載體和信息內(nèi)容,關(guān)注到了符號(hào)意義的傳送與反饋,為出版產(chǎn)業(yè)應(yīng)用信息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維納是控制論的創(chuàng)始人,他一再強(qiáng)調(diào),他是用信息論工具來研究控制系統(tǒng)和建立控制論的,是用統(tǒng)計(jì)學(xué)的方法來研究信息論的,控制系統(tǒng)中的過程是通信,控制系統(tǒng)是由系統(tǒng)、信息、控制、反饋和通信組成的。維納的信息定義是:“信息是人們?cè)谶m應(yīng)客觀世界,并使這種適應(yīng)被客觀世界感受的過程中與客觀世界進(jìn)行交換的內(nèi)容的名稱。”?這個(gè)定義是對(duì)香農(nóng)信息概念的發(fā)展,它強(qiáng)調(diào)了借助反饋維持穩(wěn)態(tài)的作用,也就是說,信息是關(guān)于事物運(yùn)動(dòng)的知識(shí),信息是內(nèi)容,信息是人們?cè)谂c客觀世界之間建立聯(lián)系的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具有意義,通過控制物質(zhì)領(lǐng)域的意義以減少世界的不確定性。通過“交換”(反饋)賦予信息以意義,信息表達(dá)目的是維納對(duì)香農(nóng)信息概念的拓展。加拿大物理學(xué)家、傳播學(xué)家羅伯特·K.洛根(Robert K.Logan)更進(jìn)一步認(rèn)為“沒有意義的符號(hào)并不是真正的信息”,他與路易斯·斯托克司(Louis Stokes)提出的數(shù)據(jù)、信息、知識(shí)和智慧的定義,更成為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理論基礎(chǔ),這個(gè)基于信息的關(guān)于知識(shí)進(jìn)化的理論模型,實(shí)際上也是數(shù)字出版理論探索的一個(gè)工具。洛根認(rèn)為,“數(shù)據(jù)是純粹和簡(jiǎn)單的事實(shí),沒有特殊的結(jié)構(gòu)或組織,是基本的信息原子”;“信息是有結(jié)構(gòu)的數(shù)據(jù),信息賦予數(shù)據(jù)意義,為數(shù)據(jù)提供語境和意義”;“知識(shí)是戰(zhàn)略上使用信息,以達(dá)成個(gè)人目標(biāo)的能力”;“智能是在符合個(gè)人價(jià)值并在大社會(huì)語境里選擇目標(biāo)的能力”。?在洛根的理論框架里,數(shù)據(jù)是信息發(fā)送者和接受者之間傳輸?shù)男盘?hào)、消息、符號(hào),數(shù)據(jù)語境化之后附有了意義而成為信息,信息得到應(yīng)用而轉(zhuǎn)化為知識(shí)和智慧。洛根的這個(gè)信息和知識(shí)模型是對(duì)香農(nóng)、維納信息論和控制論的發(fā)展,有效解釋了數(shù)據(jù)、信息、知識(shí)和智慧(思想)之間的關(guān)系,它既是一個(gè)知識(shí)生成的模式,也是一個(gè)思考如何進(jìn)行知識(shí)生產(chǎn)和傳播的方法論。
洛根在《什么是信息》一書中,還進(jìn)一步將信息區(qū)分為微觀信息和宏觀信息,微觀信息是字符串或符號(hào)串,宏觀信息是生物有機(jī)體、語言和文化,并延伸到技術(shù)和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這個(gè)新視角,對(duì)指導(dǎo)我們的出版活動(dòng)具有更直接的理論意義。在符號(hào)域中,心靈、語言和文化,一直是人類書寫的主體和表達(dá)的主題,它們得以以書籍的物理形式出版和傳承,而到達(dá)信息社會(huì)和信息時(shí)代,計(jì)算機(jī)數(shù)字技術(shù)和通信技術(shù)的結(jié)合為出版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jī)遇,攜帶意義的數(shù)據(jù)和信息與知識(shí)和智慧一樣成為重要的出版對(duì)象,其產(chǎn)品形態(tài)以數(shù)據(jù)和信息數(shù)據(jù)庫為主要出版形式,這是迄今為止出版史上最大的一次出版對(duì)象的轉(zhuǎn)移。自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信息內(nèi)容產(chǎn)業(yè)開始興起,通信網(wǎng)絡(luò)、互聯(lián)網(wǎng)提供商、計(jì)算機(jī)硬件和軟件提供商、信息內(nèi)容提供商共同構(gòu)建了一個(gè)龐大的信息產(chǎn)業(yè),出版商也隨之成為信息業(yè)的一個(gè)組成部分。現(xiàn)在,信息產(chǎn)業(yè)所創(chuàng)造的商業(yè)價(jià)值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過傳統(tǒng)的紙質(zhì)出版業(yè)。
知識(shí)是人類歷史上符號(hào)傳遞中最重要的傳遞內(nèi)容。自文字發(fā)明以來,知識(shí)是最適合文字符號(hào)系統(tǒng)傳遞的傳遞內(nèi)容。回顧一下出版歷史,我們很容易得出知識(shí)是書籍內(nèi)容基本構(gòu)成的結(jié)論。在計(jì)算機(jī)進(jìn)入出版業(yè)之前,我們甚至可以說,一部出版史實(shí)際上就是一部知識(shí)出版史。從洛根的知識(shí)論模型,我們也可以看到電子計(jì)算機(jī)的影響因子,對(duì)數(shù)據(jù)和信息的深度關(guān)注正體現(xiàn)了對(duì)計(jì)算機(jī)語言的高度重視。洛根之后,王維嘉在《暗知識(shí):機(jī)器認(rèn)知如何顛覆商業(yè)和社會(huì)》一書中將知識(shí)區(qū)分為明知識(shí)、默知識(shí)和暗知識(shí)三類,也可以推導(dǎo)為人類知識(shí)和機(jī)器知識(shí)兩大類。所謂“明知識(shí)”,就是人類可以用語言表達(dá)或用數(shù)學(xué)公式描述的知識(shí),也可以稱之為“正式知識(shí)”,“它們被記載在書籍、雜志、文章、音頻等各種媒體上”;“默知識(shí)”是只可意會(huì)、不可言傳的知識(shí),屬于“默會(huì)知識(shí)”,絕大多數(shù)的知識(shí)無法用語言表達(dá)、無法記錄、無法傳播和積累,如大量的傳統(tǒng)工藝和技能;“暗知識(shí)”是人類既無法感受也無法表達(dá)的知識(shí),屬于“機(jī)器知識(shí)”,是機(jī)器從視頻、圖片或其他場(chǎng)景中萃取的參數(shù)集之類的模仿人腦和模仿演化而產(chǎn)生的知識(shí),是機(jī)器發(fā)掘出來的,人類無法理解和陳述,但機(jī)器可以記錄并通過網(wǎng)絡(luò)以光速傳遞給其他機(jī)器。?如果從數(shù)量上來衡量,盡管人類積累了5 000年的明知識(shí),但其數(shù)量卻是有限的;其次是默知識(shí);而由各類計(jì)算機(jī)所產(chǎn)生的暗知識(shí)則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過人類知識(shí)。2 000萬冊(cè)紙質(zhì)書的總信息量相當(dāng)于20TB,現(xiàn)在每年產(chǎn)生的文字大約為160TB,而每年僅上傳到社交平臺(tái)YouTube上視頻的量就大約有157 680TB,各種傳感器和計(jì)算機(jī)監(jiān)測(cè)下所產(chǎn)生的數(shù)據(jù)和信息量則可達(dá)到天文數(shù)字。?以20世紀(jì)40年代末計(jì)算機(jī)誕生為分水嶺,知識(shí)開始被區(qū)分為人類知識(shí)和機(jī)器知識(shí),這是知識(shí)史上的革命性變革,以出版知識(shí)為使命的出版業(yè)也可以隨之被區(qū)分為人工出版和人工智能出版、印刷機(jī)器工業(yè)出版與計(jì)算機(jī)數(shù)字網(wǎng)絡(luò)出版、紙質(zhì)出版和數(shù)字出版,這一重大分野應(yīng)當(dāng)成為我們重新思考出版符號(hào)和出版對(duì)象的邏輯起點(diǎn)。
在計(jì)算機(jī)語境下,知識(shí)總是和信息密不可分,知識(shí)的概念、定義和內(nèi)涵與信息、數(shù)據(jù)也緊密地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在計(jì)算機(jī)數(shù)據(jù)庫和知識(shí)庫的背景下,知識(shí)被定義為:“知識(shí)指人們對(duì)自然現(xiàn)象的認(rèn)識(shí)和從中總結(jié)出的經(jīng)驗(yàn),或指以各種方式把一個(gè)或多個(gè)信息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信息結(jié)構(gòu)。”?可以說,知識(shí)是信息綜合處理的結(jié)果,信息通過相互比較,結(jié)合成有意義的關(guān)聯(lián),信息是知識(shí)的內(nèi)涵與實(shí)體,而數(shù)據(jù)符號(hào)則是信息的外延與形式,數(shù)據(jù)是表示事物、概念的一種符號(hào),信息是數(shù)據(jù)所表達(dá)的事實(shí),知識(shí)是信息經(jīng)過加工、整理、改造而成的一般概念的信息,因此,“知識(shí)是經(jīng)過消減、塑造、解釋和轉(zhuǎn)換的信息”?。其實(shí),這個(gè)計(jì)算機(jī)時(shí)代的知識(shí)定義只是眾多定義中的一種,但這個(gè)重視關(guān)聯(lián)的定義內(nèi)涵,我們卻可以追溯到知識(shí)起源時(shí)期的希臘,數(shù)學(xué)家畢達(dá)哥拉斯說“始基和萬物皆為數(shù)”,柏拉圖認(rèn)為“科學(xué)知識(shí)來源于洞見理念世界,而這理念世界是由數(shù)和形的理念組成的,這就是說,科學(xué)認(rèn)識(shí)就在于用數(shù)學(xué)概念的體系去把握自然”?。理念世界是“可知世界”,物理世界是“可見世界”,人類知識(shí)就區(qū)分為可見世界的意見和可知世界的科學(xué),意見包括信念和猜想,科學(xué)包括推理知識(shí)和理智直覺,因此,柏拉圖認(rèn)為“知識(shí)是一種被證實(shí)為真的信念”,而證實(shí)的途徑靠數(shù)學(xué)、邏輯、演繹推理、經(jīng)驗(yàn)和歸納。?用數(shù)學(xué)去把握世界和用數(shù)據(jù)、數(shù)值去建構(gòu)世界知識(shí),其邏輯思維是統(tǒng)一的,是一脈相承的。
無論如何定義知識(shí),知識(shí)作為人類文明的內(nèi)容傳遞是確定的。我們從人類的知識(shí)傳遞史和知識(shí)的分類史中就可以看到知識(shí)傳承和傳播在人類文明發(fā)展中是何等重要。在西方,亞里士多德將知識(shí)分為純粹理性(理論科學(xué),形而上學(xué)、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實(shí)踐理性(實(shí)用科學(xué),倫理學(xué)、政治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和技藝(創(chuàng)制科學(xué),音樂、詩學(xué)、建筑)三大類別。17世紀(jì),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將人類科學(xué)知識(shí)分為記憶科學(xué)(歷史學(xué)、語言學(xué)),想象科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和理智科學(xué)(哲學(xué)、自然科學(xué))三大類別。20世紀(jì),羅素將人類知識(shí)劃分為科學(xué)、神學(xué)和哲學(xué)。而在中國,孔子時(shí)代的知識(shí)分為六藝,即禮、樂、射(射箭)、御(駕車)、書(文字)、數(shù)(技術(shù)、技巧、數(shù)學(xué))。漢代的知識(shí)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shù)術(shù)和方技。隋唐時(shí)期,中國的書籍知識(shí)分為經(jīng)、史、子、集、道藏和佛藏。20世紀(jì)初,中國的學(xué)科知識(shí)分為七大類,即“七科之學(xué)”(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yī)科、農(nóng)科、工科)。20世紀(jì)70年代,以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為基礎(chǔ)的數(shù)據(jù)庫、知識(shí)庫興起后,人類知識(shí)被分為敘述性知識(shí)、過程性知識(shí)、控制性知識(shí)、元知識(shí),也被分為對(duì)象知識(shí)、元知識(shí)、進(jìn)程知識(shí)、常識(shí),就知識(shí)內(nèi)容而言分為原理性知識(shí)和方法性知識(shí),就知識(shí)形式而言分為顯性知識(shí)和隱性知識(shí),就知識(shí)性質(zhì)而言分為理論性知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性知識(shí),就知識(shí)的確定性程度而言分為確定性知識(shí)和模糊性知識(shí)。2012年,Google推出面向互聯(lián)網(wǎng)搜索的大規(guī)模知識(shí)圖譜,知識(shí)圖譜通常將知識(shí)分為事實(shí)知識(shí)、概念知識(shí)、詞匯知識(shí)和常識(shí)知識(shí)。無論東方、西方,也無論古代、當(dāng)代,知識(shí)一直是書籍最重要的內(nèi)容。而書籍,正是出版的主要呈現(xiàn)方式。
出版是傳遞人類符號(hào)的中介,在數(shù)據(jù)、信息和知識(shí)之外,人類智慧也是出版?zhèn)鬟f的重要內(nèi)容類型。1988年,運(yùn)籌學(xué)家羅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畫出數(shù)據(jù)、信息、知識(shí)、智慧的金字塔知識(shí)模型,在此之前,提出類似觀點(diǎn)的還有工程師邁克爾·庫利(Michael Cooley)和教育家哈蘭·克利夫蘭(Harlan Cleveland)。艾可夫之后,管理學(xué)家維娜·艾莉(Verna Allee)、傳播學(xué)家洛根又強(qiáng)化了此觀點(diǎn)。艾莉在《知識(shí)的進(jìn)化》中又豐富為數(shù)據(jù)、信息、知識(shí)、含義、原理、聯(lián)合智慧體的學(xué)習(xí)和管理模型。這個(gè)模型中的智慧,毫無疑問成為出版?zhèn)鞑ブ械闹匾M成部分。但什么是智慧?出版活動(dòng)中的智慧包括什么類型?這正是需要我們厘清的關(guān)鍵。
概括而言,在出版內(nèi)容的類型中,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數(shù)據(jù)、信息、知識(shí)之外的都應(yīng)屬于智慧的范疇。但這樣的判斷過于寬泛而流于空洞。在進(jìn)一步界定之前,讓我們首先明晰一下智慧的概念。漢語中的“智慧”一詞,指“辨析判斷、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能力”,也指才智、智謀,最早見于《墨子》:“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此之智慧,既指才智,也指能力。南北朝時(shí)期,“智慧”一詞也用于梵語“般若”和梵文“阇那”(Mati)的意譯,“泛指一切有分析和有決斷性的認(rèn)識(shí)能力”,即“具有觀察對(duì)象和思維分析、斷除疑惑的認(rèn)識(shí)能力”?。梵文的智慧,指向破除迷惑證實(shí)真理的識(shí)力和邏輯推理的能力。在古希臘,“Sophia”(漢譯智慧)一詞的原意指擁有“專業(yè)知識(shí)”或“技能”,“哲學(xué)”(Philosophia)一詞由“愛”(philein)和“智慧”(Sophia)構(gòu)成,本意為“愛智慧”。?蘇格拉底說:“我假定,智慧使人們變得聰明”,“說人聰明不就是說他們對(duì)事物擁有知識(shí)嗎?”,“那么,知識(shí)與智慧是一回事嗎?”。?被稱為希臘“最智慧的人”的蘇格拉底并沒有解答清楚這個(gè)令人疑惑的問題。柏拉圖區(qū)分了“智慧”和“哲學(xué)”,他認(rèn)為“哲學(xué)就是擁有真知”。亞里士多德進(jìn)一步指出:“智慧是關(guān)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學(xué)。”?他還認(rèn)為:“智慧既是理智也是科學(xué),在高尚的科學(xué)中它居于首位。”?哲學(xué)不等于智慧,但它卻可以是通向智慧的“真實(shí)的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識(shí),但它卻可以是至高的知識(shí);智慧不等于技能,但它卻可以是理念的能力。20世紀(jì)末,艾莉給智慧的定義是“智慧就是獲得和運(yùn)用知識(shí)的能力”,“智慧是看穿事物核心或?qū)嵸|(zhì)的才能,它是處理知識(shí)以抽象出本質(zhì)的規(guī)則和事實(shí)的一種高創(chuàng)造力的連接方式”。?
基于以上對(duì)智慧的理解,結(jié)合出版的歷史與當(dāng)下數(shù)字出版的現(xiàn)狀,我們首先可以將默會(huì)知識(shí)和技藝性知識(shí)列入智慧內(nèi)容的范疇,其次是哲學(xué)和文學(xué)藝術(shù)類內(nèi)容,最后將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人文科學(xué)中不能用數(shù)據(jù)、信息和知識(shí)表達(dá)的內(nèi)容全部納入智慧內(nèi)容。也許這不是一個(gè)科學(xué)的類分,但它表示了智慧出版內(nèi)容的豐富性和廣泛的適用性。我們應(yīng)當(dāng)看到,紙質(zhì)出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默會(huì)知識(shí)和技藝知識(shí)的表達(dá)方式,但數(shù)字化的聲音、視頻和虛擬技術(shù),卻為今后的智慧出版提供了無限想象空間。
三、出版符號(hào)被傳遞物介質(zhì)形式
出版活動(dòng)具有物質(zhì)性和精神性。作為物質(zhì)活動(dòng),它受時(shí)代技術(shù)的限制,作為精神活動(dòng),它受人的思維能力的限制。如果我們將出版理解為是將一定的符號(hào)及內(nèi)容經(jīng)過編輯加工復(fù)制于一定的載體形成產(chǎn)品并進(jìn)行廣泛傳播的行為的話,那么,由符號(hào)、內(nèi)容和載體構(gòu)成的出版物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出版對(duì)象。出版物的物質(zhì)性、物理狀態(tài)、媒介形式由制作技術(shù)決定,出版物的精神呈現(xiàn)由符號(hào)、內(nèi)容類型、意義價(jià)值決定。綜合起來,我們認(rèn)為,出版對(duì)象的呈現(xiàn)方式會(huì)隨著出版技術(shù)的發(fā)展而出現(xiàn)多形態(tài)的特征。自20世紀(jì)下半葉以來,隨著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的發(fā)明和發(fā)展,出版對(duì)象的介質(zhì)和呈現(xiàn)方式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概括起來,自紙被廣泛應(yīng)用之后,其成為出版對(duì)象的主流介質(zhì),但當(dāng)下電子介質(zhì)卻異軍突起。因此,我們將重點(diǎn)討論出版介質(zhì)中的紙質(zhì)介質(zhì)和電子介質(zhì),紙質(zhì)介質(zhì)之前或與紙質(zhì)介質(zhì)并存的泥質(zhì)介質(zhì)、石頭介質(zhì)、莎草介質(zhì)、貝葉介質(zhì)、簡(jiǎn)帛介質(zhì)、羊皮介質(zhì)等略而不論。
具有一定物理狀態(tài)的紙質(zhì)書籍已經(jīng)誕生1 900年。迄今,封裝型的紙質(zhì)書籍依然是全世界讀者最喜歡的出版物。紙質(zhì)書籍之前,還存在其他物理形狀的書籍。最早的書籍,是蘇美爾人以楔形文字書寫在泥板上的泥板書籍,之后有埃及、希臘、羅馬人書寫在莎草紙、羊皮紙上的莎草紙書、羊皮紙書,以及中國的書寫在竹簡(jiǎn)、縑帛上的竹簡(jiǎn)書籍和帛書,在南亞還出現(xiàn)了書寫在貝多羅樹葉上的貝葉書籍。在中國雕版印刷術(shù)發(fā)明前,書籍的物理形狀主要是卷子狀,莎草紙書、羊皮紙書、竹簡(jiǎn)書籍、帛書和寫本時(shí)期的紙質(zhì)書籍都是卷子狀,泥板書籍是塊狀,貝葉書籍是長(zhǎng)條木夾狀。卷子狀書籍的規(guī)格受制于載體材料,如:“用以書寫一卷希臘文學(xué)作品的紙草,其單張的尺寸很少(甚至從來不曾)超過13×9英寸,而對(duì)于中等檔次的書來說,更為常見的尺寸是10×7.1/2英寸。另一方面,袖珍本詩集的紙高可能要短得多。”?自公元2世紀(jì),羅馬開始出現(xiàn)冊(cè)子裝幀的紙草書籍,主要流行于基督教人群,至公元4世紀(jì),紙草卷子和紙草冊(cè)子一并讓位于皮紙冊(cè)子。中國自東漢至唐代,紙質(zhì)書籍的裝幀形式一直是卷軸狀,唐代末年出現(xiàn)雕版印刷冊(cè)子裝幀書籍,到北宋初中國完成由卷軸裝幀書籍向冊(cè)頁裝幀書籍的過渡,冊(cè)頁線裝是中國書籍的主要形態(tài),一直延續(xù)到晚清。15世紀(jì)中葉,德國谷登堡發(fā)明鉛活字印刷術(shù)后,西方書籍一直是冊(cè)頁精裝。西方在19世紀(jì)開始普及紙皮精裝書籍,20世紀(jì)30年代開始廣泛流行紙皮平裝書籍,直到今天,精裝書籍和平裝書籍依然并行。中國自19世紀(jì)70年代開始引進(jìn)西方印刷技術(shù),尤其是石印技術(shù)的普及,加速了雕版印刷的衰落,書籍形態(tài)也引進(jìn)了西方書籍的紙皮精裝與平裝形式,但由于經(jīng)濟(jì)等原因,中國的書籍形式一直以紙皮平裝為主,進(jìn)入21世紀(jì),紙質(zhì)精裝書籍漸多。20世紀(jì)80年代電子書籍興起之后,尤其是90年代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之后,紙質(zhì)書籍被替代的預(yù)言不絕于耳,但實(shí)際情況是,紙質(zhì)書籍非但沒有被取代,其出版品種還實(shí)現(xiàn)了幾何級(jí)數(shù)的增長(zhǎng)。我們可以用數(shù)據(jù)對(duì)比一下。1996年日本出版的紙質(zhì)新書是63 054種,而2019年是71 903種。?1996年美國出版的紙質(zhì)新書是68 175種,2019年是203 757種。?1996年中國出版的紙質(zhì)新書是63 647種,2020年是213 636種。?盡管紙質(zhì)書籍已經(jīng)退縮為出版符號(hào)所呈現(xiàn)的一種內(nèi)容載體形式,但我們堅(jiān)信,延續(xù)了1 900年的紙質(zhì)書籍傳統(tǒng)依然會(huì)繼續(xù)發(fā)揮它的功能。
與紙質(zhì)書籍對(duì)應(yīng)的出版符號(hào)主要為文字和圖像不同,電子書籍對(duì)應(yīng)的出版符號(hào)還包括計(jì)算機(jī)圖形、音頻和視頻符號(hào),因此,電子書籍作為出版符號(hào)的一種呈現(xiàn)方式,具有跨符號(hào)的綜合特征。所謂電子書籍(Electronic Book),就是指“通過計(jì)算機(jī)或類似設(shè)備,以數(shù)字代碼方式將圖、文、聲、像等信息存儲(chǔ)在磁、光、電介質(zhì)上,并可復(fù)制發(fā)行的大眾傳播載體”?。電子書籍依賴的最底層技術(shù)是電子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但電子書籍的誕生實(shí)際上是一系列新技術(shù)交互作用的結(jié)果,這些技術(shù)包括電子技術(shù)、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軟件技術(shù)、信息處理技術(shù)、通信技術(shù)、激光技術(shù)、自動(dòng)化技術(shù)、材料技術(shù)、精密機(jī)械技術(shù)、印刷技術(shù)、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多媒體技術(shù)等。用數(shù)字來表現(xiàn)模擬,用離散來表示連續(xù),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模擬變量用大量的連續(xù)的二進(jìn)制0、1的數(shù)字化方式表示,用數(shù)字表示一切,從而再現(xiàn)現(xiàn)實(shí)世界,將此原理運(yùn)用于表示文字符號(hào)、圖像符號(hào)、聲音符號(hào)、視頻符號(hào),由此而創(chuàng)制出電子書籍。電子書籍與紙質(zhì)書籍最大的不同是符號(hào)信息載體截然不同,紙質(zhì)書籍的符號(hào)信息載體是紙介質(zhì),電子書籍的符號(hào)信息載體是磁記錄介質(zhì)、光記錄介質(zhì)。磁介質(zhì)包括軟磁盤(FD,F(xiàn)loppy Disk)和硬磁盤,硬盤有移動(dòng)硬盤和固定于計(jì)算機(jī)或服務(wù)器中的固定硬盤兩種;光介質(zhì)為光盤,包括只讀光盤CD-ROM、交互式光盤CD-I、圖文光盤CD-G、照片光盤Photo CD、高密度只讀光盤DVD-ROM等。在實(shí)際的出版活動(dòng)中,依據(jù)內(nèi)容符號(hào)系統(tǒng)的特征,我們將電子書籍分為文本電子書籍、靜態(tài)圖像電子書籍、動(dòng)態(tài)圖像電子書籍、聲音書籍和綜合性的多媒體書籍等。電子書籍與紙質(zhì)書籍的另一個(gè)顯著不同是,電子書籍的內(nèi)容符號(hào)載體與閱讀終端是分離的,從物理形態(tài)上看,電子書籍由內(nèi)容符號(hào)存儲(chǔ)載體、傳輸載體和閱讀終端載體三部分構(gòu)成,存儲(chǔ)載體是磁盤或光盤,傳輸載體是計(jì)算機(jī)或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或移動(dòng)通信網(wǎng)絡(luò),閱讀終端是計(jì)算機(jī)屏幕或類計(jì)算機(jī)屏幕,電子書籍需要三個(gè)載體的結(jié)合才能完成閱讀或觀看行為。因此,從閱讀終端的角度分析,我們還可以將電子書籍分為離線載體閱讀、在線載體閱讀和無線移動(dòng)載體閱讀。離線載體主要是FD磁盤、CD-ROM光盤,在線載體主要是在線計(jì)算機(jī)、在線筆記本電腦,無線移動(dòng)載體主要是手機(jī)、平板電腦、手持閱讀器。無論載體介質(zhì)如何不同,也無論傳輸通道是計(jì)算機(jī)、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或通信網(wǎng)絡(luò),有一點(diǎn)是相同的,那就是閱讀內(nèi)容都要通過終端的屏幕,終端屏幕成為我們可視的物理形態(tài)。
與紙質(zhì)書籍相比,電子書籍對(duì)內(nèi)容符號(hào)的呈現(xiàn)方式更趨多樣化。根據(jù)實(shí)際出版活動(dòng)中的產(chǎn)品形式和市場(chǎng)行為,我們將電子書籍分為五個(gè)產(chǎn)品系統(tǒng)。一是單一符號(hào)系統(tǒng)型電子書籍。單一符號(hào)指純文字符號(hào)或純聲音符號(hào),如1991年5月中國出版的第一部電子書籍《國共兩黨關(guān)系通史》就是純文字符號(hào)的,此書150萬字,由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同時(shí)出版了紙質(zhì)印刷版和電子版,電子版可全文檢索,以軟盤形式呈現(xiàn)。再如1993年1月出版的中國第一張數(shù)據(jù)光盤《中國企業(yè)、公司及產(chǎn)品數(shù)據(jù)庫》也是純文字符號(hào)的。中國20世紀(jì)90年代的電子書籍以純文字符號(hào)呈現(xiàn)的方式為主,并且以軟盤載體為主,后期大規(guī)模的尤其是以PDF格式呈現(xiàn)的電子書籍多轉(zhuǎn)向以光盤為載體。二是多媒體型電子書籍。電子書籍往往綜合性同時(shí)呈現(xiàn)多種符號(hào)系統(tǒng),如在一個(gè)出版物產(chǎn)品中同時(shí)出現(xiàn)文字符號(hào)、圖形設(shè)計(jì)、圖像符號(hào)、音頻、視頻、動(dòng)畫等,構(gòu)成多媒體、跨媒體或融媒體的產(chǎn)品,多媒體是電子書籍的重要特征。從概念上來說,“多媒體是將不同的媒體種類在個(gè)人電腦上融為一體呈現(xiàn)出來”,從產(chǎn)品的角度而言,多媒體“是指基于個(gè)人電腦的集文本、聲音、圖像、動(dòng)畫和圖表于一體的出版產(chǎn)品”。多媒體產(chǎn)品可以是離線的,也可以是網(wǎng)絡(luò)在線的,離線的多以CD-ROM光盤的形式呈現(xiàn),在線的主要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傳播。三是互聯(lián)網(wǎng)型電子書籍。電子書籍的載體可以是軟磁盤和光盤,也可以是計(jì)算機(jī)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書籍內(nèi)容符號(hào)存儲(chǔ)于計(jì)算機(jī)硬盤或服務(wù)器硬盤中。互聯(lián)網(wǎng)分為計(jì)算機(jī)互聯(lián)網(wǎng)和移動(dòng)通信互聯(lián)網(wǎng)兩類,電子書籍的閱讀通過PC端計(jì)算機(jī)屏幕和智能手機(jī)端屏幕實(shí)現(xiàn)。計(jì)算機(jī)互聯(lián)網(wǎng)的商業(yè)應(yīng)用始于1991年,1994年中國接入全球互聯(lián)網(wǎng)。電子書籍內(nèi)容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在2002年被新聞出版總署列為互聯(lián)網(wǎng)出版,并將互聯(lián)網(wǎng)出版定義為:“互聯(lián)網(wǎng)出版,是指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服務(wù)提供者將自己創(chuàng)作或他人創(chuàng)作的作品經(jīng)過選擇和編輯加工,登載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或者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送到用戶端,供公眾瀏覽、閱讀、使用或者下載的在線傳播行為。”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之后,迅速成為電子書籍的主要傳播載體和渠道,由此也導(dǎo)致了軟盤載體和光盤載體的衰落。2007年,蘋果公司推出通過移動(dòng)通信網(wǎng)絡(luò)來實(shí)現(xiàn)無線網(wǎng)絡(luò)接入的智能手機(jī),從此開啟了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新時(shí)代,智能手機(jī)端電子書籍進(jìn)入新的傳播時(shí)代,手機(jī)成為電子書籍閱讀最重要的工具,PC端互聯(lián)網(wǎng)的影響力開始下降。以無線通信技術(shù)為基礎(chǔ)的手機(jī)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還被學(xué)界和業(yè)界視為一種新的出版平臺(tái),即手機(jī)出版平臺(tái),手機(jī)出版也相應(yīng)成為一種新的出版業(yè)態(tài)。四是手持閱讀器型電子書籍。電子書籍的閱讀和使用必須依賴閱讀專用軟件和硬件。電子書籍閱讀軟件的提供商主要是Adobe公司和微軟公司,Adobe電子書籍閱讀軟件以PDF格式為基礎(chǔ),可以下載到各種PC計(jì)算機(jī)、筆記本計(jì)算機(jī)、掌上電腦(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ce,PDA)和專用電子書閱讀器上,比微軟的閱讀軟件略勝一籌。像紙質(zhì)書籍一樣可以便捷地拿在手里隨時(shí)隨地閱讀,是電子書閱讀器開發(fā)的動(dòng)力。1986年美國富蘭克林電子出版公司(Franklin Electronic Publishers)研制成功的一種裝載《富蘭克林拼寫詞典》(Franklin Speller)的手持電子閱讀裝置,是世界上第一種手持電子閱讀器。之后,SoftBook出版公司推出了類似掌上電腦的第一代硬件Softbook閱讀器,NuvoMedia公司1998年推出了Rocket Ebook Reader(火箭電子書閱讀器),EveryBook公司推出了EB Dedicated Reader手持閱讀器,電子書籍手持閱讀器市場(chǎng)逐步成熟。日本的夏普公司、松下電器公司和索尼公司也分別研制并上市了自己的電子書閱讀器,但市場(chǎng)效果不佳。2007年亞馬遜公司發(fā)售的Kindle專用手持電子書閱讀器是“史上首次取得商業(yè)成功的電子書閱覽設(shè)備”,2010年蘋果公司的平板電腦也成為非常成功的電子書閱讀器。目前,與電子書籍一道,電子書閱讀器也成為一個(gè)產(chǎn)業(yè)。五是數(shù)字圖書館型電子書籍。傳統(tǒng)的以紙質(zhì)文獻(xiàn)為主的圖書館是一個(gè)搜集、收藏、整理紙質(zhì)圖書和文獻(xiàn)并提供查閱、咨詢服務(wù)的知識(shí)傳播實(shí)體機(jī)構(gòu),但自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隨著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通信網(wǎng)絡(luò)傳輸技術(shù)、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多媒體技術(shù)和數(shù)字出版技術(shù)的發(fā)展,信息和知識(shí)的采集、處理和傳播方式發(fā)生了革命性的巨變,傳統(tǒng)圖書館開始轉(zhuǎn)向信息資源數(shù)字化、信息檢索計(jì)算機(jī)化、信息傳輸網(wǎng)絡(luò)化、信息資源利用全時(shí)空化、信息服務(wù)個(gè)性化,數(shù)字圖書館開始成型并能提供全球性的平臺(tái)化服務(wù)。所謂數(shù)字圖書館,就是“指搜集、存儲(chǔ)、組織數(shù)字化形式的信息,通過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提供各種咨詢、檢索等服務(wù)以及傳遞信息的系統(tǒng)”。數(shù)字圖書館自1998年起逐步成為一個(gè)技術(shù)系統(tǒng),這個(gè)技術(shù)系統(tǒng)的解決方案IBM公司將其架構(gòu)為資料加工生產(chǎn)與獲取系統(tǒng)、存儲(chǔ)與管理系統(tǒng)、搜索與取用系統(tǒng)、信息傳遞系統(tǒng)、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管理系統(tǒng),數(shù)字圖書館技術(shù)在資源建設(shè)和管理、用戶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務(wù)方面形成了有別于出版技術(shù)系統(tǒng)的新知識(shí)管理技術(shù)系統(tǒng)。而與此同步,數(shù)字圖書館在提供公共信息和知識(shí)服務(wù)的同時(shí),其性質(zhì)也開始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一部分?jǐn)?shù)字圖書館依然保留了公共服務(wù)性,一部分?jǐn)?shù)字圖書館轉(zhuǎn)向了商業(yè)性。電子書籍、多媒體資源、數(shù)據(jù)庫等數(shù)字資源成為數(shù)字圖書館的數(shù)字產(chǎn)品,商業(yè)性數(shù)字圖書館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數(shù)字圖書館扮演了出版中介的角色,成為一種出版行為,如將紙質(zhì)書籍?dāng)?shù)字化并有償提供用戶服務(wù);二是出版商開發(fā)售賣性質(zhì)的數(shù)字圖書館;三是技術(shù)提供商或網(wǎng)絡(luò)運(yùn)營商聚集內(nèi)容資源開發(fā)搜索或閱讀有償服務(wù)。由此,數(shù)字圖書館成了一個(gè)數(shù)字產(chǎn)品,同時(shí)它也成為數(shù)字出版活動(dòng)的一個(gè)組成部分。
聲音符號(hào)既是出版對(duì)象,也是一種出版呈現(xiàn)方式。作為產(chǎn)品的聲音類書籍,其名稱還沒有獲得業(yè)界和學(xué)界的共識(shí),有的名為“有聲讀物”“有聲書”“有聲書籍”,也有人稱之為“音頻書”“音頻書籍”。英文audiobook現(xiàn)在通常被譯為“有聲書”,美國有聲書協(xié)會(huì)對(duì)此詞的定義是:“包含不低于51%的文字內(nèi)容,復(fù)制和包裝成磁帶、高密度光盤或單純數(shù)字文件等形式進(jìn)行銷售的錄音制品。”由此,有聲書從載體上可以分為磁帶型、光盤型和網(wǎng)絡(luò)數(shù)字型三種,前兩種是有形的,后一種是在線的,但它們都是電子技術(shù)的產(chǎn)物,屬于可以用聲音表達(dá)的電子書籍形式。而在此之前,有聲書的源頭是唱片。最早的有聲書可以追溯到1931年美國盲人基金會(huì)和美國國會(huì)圖書館聯(lián)合推出的“有聲書計(jì)劃”,主要是小說,錄制為時(shí)長(zhǎng)20分鐘的唱片供盲人使用。1963年,荷蘭飛利浦公司研制成功全球首盤盒式磁帶,1970年第一盤120分鐘的磁帶誕生,1971年Advent公司發(fā)售201型磁帶機(jī),錄音和播放器成本和高保真質(zhì)量大為提高。20世紀(jì)70年代,有聲書開始流行。20世紀(jì)90年代,CD光盤型有聲書開始流行。1997年,Audible.com推出世界上第一款面向大眾市場(chǎng)的數(shù)字聽書播放器,數(shù)字有聲書開始走向市場(chǎng)。2010年后,有聲書市場(chǎng)突然出現(xiàn)爆發(fā)式增長(zhǎng)。2010年,美國有聲書出版品種數(shù)為0.62萬種,2015年達(dá)到了3.56萬種。2017年,美國有聲書出版數(shù)量達(dá)到4.6萬種。世界出版50強(qiáng)的大眾出版集團(tuán)是美國有聲書出版的主力,如企鵝蘭登書屋、西蒙&舒斯特公司、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的有聲書銷售增幅都超過了20%。中國的有聲書發(fā)展也超過了世界發(fā)展水平,“艾媒咨詢《2018—2019中國有聲書市場(chǎng)專題研究報(bào)告》數(shù)據(jù)顯示,2018年中國有聲書用戶規(guī)模達(dá)到3.83億,預(yù)計(jì)將在2020年達(dá)到5.59億人”。2018年市場(chǎng)規(guī)模達(dá)到46.3億元。目前,出版、生產(chǎn)和傳播有聲書的企業(yè)主要有三類:傳統(tǒng)出版社或集團(tuán),如中國出版集團(tuán)、中信出版集團(tuán)等;數(shù)字閱讀平臺(tái)加入聽書功能或新建聽書平臺(tái),如掌閱聽書、閱文聽書、咪咕閱讀、QQ閱讀、微信閱讀、百度閱讀、網(wǎng)易云閱讀等;新興聽書平臺(tái),如懶人聽書、得到、十點(diǎn)課堂、樊登讀書、喜馬拉雅FM、蜻蜓FM、荔枝FM等。作為數(shù)字時(shí)代電子書籍的一個(gè)品類,有聲書為紙質(zhì)書籍和原創(chuàng)電子書籍內(nèi)容轉(zhuǎn)換為聲音產(chǎn)品提供了可能并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這一可能,有聲書已經(jīng)成為出版產(chǎn)業(yè)新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點(diǎn)。
以視頻方式呈現(xiàn)紙質(zhì)書籍內(nèi)容,在計(jì)算機(jī)數(shù)字化時(shí)代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實(shí)。與有聲書的書籍形態(tài)相對(duì)應(yīng),視頻書的概念呼之欲出。所謂視頻書,我們可以將其定義為:以二進(jìn)制數(shù)字化方式記錄、存儲(chǔ)和編輯加工制作的具有一定長(zhǎng)度和主題集中的、在計(jì)算機(jī)網(wǎng)絡(luò)或通信網(wǎng)絡(luò)傳輸、傳播的動(dòng)態(tài)影像內(nèi)容。簡(jiǎn)言之,視頻書是數(shù)字化的動(dòng)態(tài)影像的書。一定長(zhǎng)度是相對(duì)于短視頻而言的,我們認(rèn)為,無論什么形式的書籍,均需要主題和長(zhǎng)度,如紙質(zhì)書籍要求不低于49個(gè)頁碼,那么,視頻書的時(shí)長(zhǎng)應(yīng)當(dāng)不低于30分鐘,也就是說長(zhǎng)視頻以上才可以稱得上為書。關(guān)于視頻長(zhǎng)短的界定,一般將5分鐘以下列為短視頻,6—30分鐘為中視頻,30分鐘以上為長(zhǎng)視頻。一種視頻書,我們認(rèn)為是長(zhǎng)視頻的形式,它可以由大量短視頻和中視頻構(gòu)成,也可以由一定數(shù)量的長(zhǎng)視頻構(gòu)成,與一部紙質(zhì)書籍由若干章節(jié)構(gòu)成同理。當(dāng)前中國出版的視頻書,均是由數(shù)量不等的長(zhǎng)、中、短視頻組成的,如201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朽的馬克思》,是紙質(zhì)書和視頻書同時(shí)出版的,紙質(zhì)書為平裝16開,視頻以二維碼的方式印于書尾,讀者用手機(jī)掃描二維碼即可觀看視頻,視頻共有37集100分鐘。換言之,我們也可以說短視頻是視頻書的重要組成元素。短視頻的發(fā)達(dá)是視頻書的起點(diǎn)和基礎(chǔ)。短視頻應(yīng)用最早出現(xiàn)在美國,2011年第一款短視頻制作應(yīng)用軟件Viddy問世,“用戶可通過Viddy拍攝短片并添加音效和特效美化功能,最后剪輯成視頻短片在社交平臺(tái)分享”。美國三大社交平臺(tái)迅速跟進(jìn),Twitter推出Vine短視頻應(yīng)用App,F(xiàn)acebook推出Instagram短視頻分享軟件,YouTube推出MixBit視頻分享軟件,短視頻隨即爆火。中國的短視頻用戶和分享數(shù)量在很短的時(shí)間內(nèi)即成為全球第一,2021年短視頻用戶規(guī)模達(dá)9.34億,愛奇藝、優(yōu)酷、騰訊視頻居于行業(yè)頭部位置。短視頻的快速發(fā)展,為視頻書的開發(fā)奠定了內(nèi)容和素材基礎(chǔ),但從出版的實(shí)踐活動(dòng)看,視頻書還不是一個(gè)成熟的出版門類。隨著5G、6G時(shí)代的到來,長(zhǎng)視頻將成為主要的傳播場(chǎng)景,視頻書的時(shí)代才可能真正到來。視頻書將會(huì)朝三個(gè)方向發(fā)展:一是紙質(zhì)書籍的視頻化,這是初級(jí)階段;二是原創(chuàng)視頻書興起,出版者按照書籍的主題和邏輯制作視頻書,同時(shí)也可以還原為紙質(zhì)書籍,進(jìn)入融合出版階段;三是課程化視頻書崛起,將各門類知識(shí)制作為長(zhǎng)視頻的課程,形成以視頻形式存在的課程式的獨(dú)立產(chǎn)品,課程將成為視頻書的主流,這是視頻書最重要的方向,進(jìn)入場(chǎng)景化出版階段。
數(shù)據(jù)庫作為數(shù)據(jù)、信息、知識(shí)和智慧的呈現(xiàn)方式,并且成為一個(gè)出版活動(dòng),完全依賴于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的發(fā)展。20世紀(jì)60年代中期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產(chǎn)生,歷經(jīng)第一代層次和網(wǎng)狀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70年代第二代關(guān)系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80年代面向?qū)ο髷?shù)據(jù)庫系統(tǒng)三個(gè)發(fā)展階段。按照提供數(shù)據(jù)的性質(zhì),數(shù)據(jù)庫分為文獻(xiàn)數(shù)據(jù)庫、數(shù)值數(shù)據(jù)庫、事實(shí)數(shù)據(jù)庫和多媒體數(shù)據(jù)庫;按照數(shù)據(jù)庫內(nèi)容分為綜合性數(shù)據(jù)庫、專業(yè)性數(shù)據(jù)庫和專題性數(shù)據(jù)庫;按照數(shù)據(jù)庫載體類型分為磁帶數(shù)據(jù)庫、磁盤數(shù)據(jù)庫、光盤數(shù)據(jù)庫和聯(lián)機(jī)數(shù)據(jù)庫。與出版最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是文獻(xiàn)數(shù)據(jù)庫,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收錄了論文、稿件等的目錄事項(xiàng)或摘要等,所謂二次信息的文獻(xiàn)參考(reference)數(shù)據(jù)庫;一類是收錄了數(shù)值、圖像、影像、聲音、圖書以及論文、稿件等文獻(xiàn)全文(fulltext)的事實(shí)(信息源)數(shù)據(jù)庫。”1961年1月,美國化學(xué)會(huì)《化學(xué)文摘》服務(wù)社創(chuàng)辦的新雜志《化學(xué)題錄》(雙周刊,一年24期)同時(shí)出版紙質(zhì)印刷版和磁帶版,此磁帶版被視為世界上第一種電子出版物,此題隸屬于二次文獻(xiàn)性質(zhì),具有數(shù)據(jù)庫雛形。1964年,美國醫(yī)學(xué)圖書館利用計(jì)算機(jī)對(duì)《醫(yī)學(xué)索引》(Index medicos)進(jìn)行排版并將數(shù)據(jù)轉(zhuǎn)換到磁帶上形成機(jī)讀數(shù)據(jù),此數(shù)據(jù)庫通常被視為最早的計(jì)算機(jī)數(shù)據(jù)庫。此后,美國的《化學(xué)文摘》《生物學(xué)文摘》《工程文摘》《科學(xué)引文索引》等計(jì)算機(jī)數(shù)據(jù)庫建立。二次文獻(xiàn)型數(shù)據(jù)庫自此進(jìn)入出版領(lǐng)域。全文數(shù)據(jù)庫出現(xiàn)稍晚,1973年“美國米德公司建成世界上第一個(gè)面向公眾查詢的大型全文數(shù)據(jù)庫Lexis”,自此,全文數(shù)據(jù)庫成為全球文獻(xiàn)數(shù)據(jù)庫的發(fā)展方向,并成為數(shù)字出版的重要門類。中國的數(shù)據(jù)庫開發(fā)稍晚于美國,1980年,中國化工信息研究所開始研究和建設(shè)第一批中文數(shù)據(jù)庫,至1991年,“全國共建成800多個(gè)數(shù)據(jù)庫”。1992年,北京大學(xué)發(fā)行英文版《中國對(duì)外經(jīng)濟(jì)貿(mào)易法律全文數(shù)據(jù)庫》光盤,這是我國第一個(gè)CD-ROM全文數(shù)據(jù)庫。1993年,中國第一家數(shù)據(jù)庫專業(yè)公司“萬方數(shù)據(jù)公司”成立。2000年,原萬方數(shù)據(jù)(集團(tuán))公司由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信息研究所聯(lián)合中國科技出版?zhèn)髅接邢薰尽⒖萍嘉墨I(xiàn)出版社等組建成立北京萬方數(shù)據(jù)股份有限公司,推出萬方數(shù)據(jù)知識(shí)服務(wù)平臺(tái)、萬方醫(yī)學(xué)信息服務(wù)平臺(tái)、萬方數(shù)據(jù)中小學(xué)數(shù)字圖書館、萬方視頻知識(shí)服務(wù)系統(tǒng)等數(shù)據(jù)庫產(chǎn)品,萬方公司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數(shù)據(jù)庫出版公司之一。作為一種出版形式,數(shù)據(jù)庫出版已經(jīng)覆蓋到出版物的各個(gè)門類,也已經(jīng)覆蓋到社會(huì)科學(xué)、人文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的各個(gè)學(xué)科,甚至延伸到了人類生活的各個(gè)方面。
在出版符號(hào)和內(nèi)容呈現(xiàn)上,數(shù)據(jù)庫不僅僅是一種呈現(xiàn)方式或出版形式,更重要的是它還是技術(shù)和工具。數(shù)據(jù)庫可以作為獨(dú)立的電子產(chǎn)品被銷售給機(jī)構(gòu)和客戶,同時(shí),它還為計(jì)算機(jī)互聯(lián)網(wǎng)(PC端互聯(lián)網(wǎng))和通信互聯(lián)網(wǎng)(移動(dòng)端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應(yīng)用平臺(tái)(App)提供后臺(tái)技術(shù)支持,如后臺(tái)數(shù)字內(nèi)容管理系統(tǒng)(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CMS)、數(shù)字資產(chǎn)管理系統(tǒng)(Digital Assets Management,DAM)、數(shù)字權(quán)利管理系統(tǒng)(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DRM)等均屬于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的范疇。平臺(tái)是一個(gè)用戶界面,各種應(yīng)用程序(App)是一個(gè)個(gè)不同程度的用戶界面(平臺(tái)),這些平臺(tái)只有通過后臺(tái)的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管理才可以實(shí)現(xiàn)應(yīng)用。應(yīng)用層面的搜索引擎、信息檢索、決策工具、咨詢服務(wù)、一對(duì)一解決方案、個(gè)性化服務(wù)等均依賴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數(shù)據(jù)庫實(shí)際上是數(shù)字出版的核心基礎(chǔ)和底層技術(shù)。在出版活動(dòng)的實(shí)踐層面,三大領(lǐng)域的出版商,其數(shù)字內(nèi)容、平臺(tái)、服務(wù)和應(yīng)用無一不通過后臺(tái)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來實(shí)現(xiàn)。專業(yè)出版領(lǐng)域,出版商一方面直接提供書目、索引數(shù)據(jù)庫和全文數(shù)據(jù)庫,一方面搭建在線數(shù)字平臺(tái)提供檢索工具、研究工具、決策工具和解決方案,如勵(lì)訊集團(tuán)的ScienceDirect數(shù)據(jù)庫在線平臺(tái),“收錄了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醫(yī)學(xué)類別下22個(gè)學(xué)科的2 500多種期刊以及數(shù)千種圖書、1.2萬多個(gè)視頻、超過170萬張圖片等”。此數(shù)據(jù)庫既是全球最大的全文數(shù)據(jù)庫,也是在線的一個(gè)信息查詢和信息服務(wù)平臺(tái)。在教育出版領(lǐng)域,出版商同樣通過直接提供在線海量信息資源庫和推出在線平臺(tái)提供一系列教與學(xué)服務(wù),尤其是在個(gè)性化學(xué)習(xí)和一對(duì)一學(xué)習(xí)解決方案方面,教育出版商更需要通過網(wǎng)站和教學(xué)平臺(tái)來實(shí)現(xiàn)。如培生集團(tuán)的EQUELLA(數(shù)據(jù)庫)是一個(gè)“專業(yè)的教育內(nèi)容數(shù)字在線倉庫”,MyLab是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在線學(xué)習(xí)和輔導(dǎo)工具,Pearson Learning Solutions在線平臺(tái)“是為用戶解決學(xué)習(xí)過程中各種需求和問題的個(gè)性化學(xué)習(xí)解決方案”。在大眾出版領(lǐng)域,出版商更偏重于建立自己的電子書資源庫和有聲書資源庫,直接在自己的平臺(tái)上分銷,而原創(chuàng)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平臺(tái)則選擇了直接搭建終端閱讀平臺(tái),將作者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作品放在平臺(tái)上供用戶在PC端、手機(jī)端、平板電腦端直接閱讀或聽取,二者的后臺(tái)都需要一個(gè)數(shù)據(jù)庫來支撐。大眾出版的這兩種數(shù)字出版模式,前者以企鵝蘭登書屋為典型,后者以閱文集團(tuán)的起點(diǎn)中文網(wǎng)為代表。由上可知,數(shù)據(jù)庫出版這種形式已經(jīng)滲透到數(shù)字出版的各種形態(tài)之中。
總體而言,進(jìn)入印刷時(shí)代,出版介質(zhì)主要是紙介質(zhì);進(jìn)入計(jì)算機(jī)時(shí)代,出版介質(zhì)進(jìn)入磁介質(zhì)、光介質(zhì)和紙介質(zhì)并用時(shí)代,而出版物(書籍)則相應(yīng)以紙質(zhì)書、電子書、有聲書、視頻書、多媒體書、數(shù)據(jù)庫形式呈現(xiàn)。
四、結(jié)語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認(rèn)為出版對(duì)象由出版符號(hào)系統(tǒng)、被傳遞物內(nèi)容類型和內(nèi)容載體介質(zhì)三要素構(gòu)成,反過來說,符號(hào)、內(nèi)容和介質(zhì)共同構(gòu)成了出版對(duì)象。出版對(duì)象就是由一定的符號(hào)系統(tǒng)表達(dá)一定的內(nèi)容并承載在一定的介質(zhì)之上,呈現(xiàn)出不同形態(tài)的出版物。構(gòu)成出版物的三個(gè)要素缺一不可。譬如,漢代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由作者書寫在竹簡(jiǎn)上,他書寫的符號(hào)系統(tǒng)是文字,被文字傳遞給后人的內(nèi)容是歷史知識(shí),符號(hào)、知識(shí)和介質(zhì)共同構(gòu)成了《史記》這本書。紙被發(fā)明之后,其內(nèi)容被重新書寫在紙上。雕版印刷術(shù)被發(fā)明后,其內(nèi)容又被雕版印刷在紙上。石印、鉛印、數(shù)碼印刷機(jī)被發(fā)明后,其內(nèi)容又被機(jī)械印刷機(jī)印刷在不同的紙上。計(jì)算機(jī)被發(fā)明后,其內(nèi)容又以二進(jìn)制的數(shù)字方式被存儲(chǔ)于計(jì)算機(jī)并被轉(zhuǎn)換到不同屏幕上而成為電子書,其內(nèi)容還被數(shù)字化為有聲書、視頻書,以及被制作為數(shù)據(jù)庫以供檢索和研究。無論《史記》這本書的形態(tài)如何變化,但構(gòu)成它的符號(hào)、內(nèi)容和介質(zhì)要素必須是完整的。然而,在實(shí)際的出版活動(dòng)中,我們看到的往往是變化,出版符號(hào)系統(tǒng)在變化,內(nèi)容類型在變化,載體介質(zhì)在變化,這些變化都不同程度地來自技術(shù)的發(fā)明、發(fā)展和應(yīng)用在出版對(duì)象的演進(jìn)中起到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技術(shù)影響到了符號(hào)系統(tǒng)的變化、內(nèi)容類型的變化和載體介質(zhì)的變化,由此也決定了出版對(duì)象的物理形態(tài)和呈現(xiàn)方式的變化,進(jìn)而,所有的變化都影響到出版活動(dòng)的意義和利益獲得。作為業(yè)界中人,我們必須隨著出版對(duì)象的變化而變化,必須找出出版對(duì)象變化的規(guī)律,必須理性地動(dòng)態(tài)定義自己的出版行為,厘清這些變化正是我研究出版對(duì)象的目的所在。也許,也是意義所在。
注釋
① 卡西爾.符號(hào)形式的哲學(xué)[M].趙海萍,譯.長(zhǎng)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股份有限公司,2018:216.
② 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41,42,35.
③ 馬祖爾.人類符號(hào)簡(jiǎn)史[M].洪萬生,洪贊天,英家銘,等譯.南寧:接力出版社,2018:2.
④ 見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ymbol,查詢時(shí)間為2022年8月22日。
⑤⑩ 霍克斯.結(jié)構(gòu)主義和符號(hào)學(xué)[M].瞿鐵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129,139.
⑥⑦⑧ 彼得里利,蓬齊奧.打開邊界的符號(hào)學(xué):穿越符號(hào)開放網(wǎng)絡(luò)的解釋路徑[M].王永祥,彭佳,余紅兵,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28,5,28.
⑨ 馮月季.傳播符號(hào)學(xué)教程[M].重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7:3.
? 費(fèi)希爾.書寫的歷史[M].李華田,李國玉,楊玉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30.
? 光復(fù)書局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大美百科全書[M].臺(tái)北:光復(fù)書局企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0:380.
? 胡易容.圖像符號(hào)學(xué):傳媒景觀世界的圖式把握[M].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14:82.
? 余鳳高.插圖的歷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8.
? 凱夫,阿亞德.極簡(jiǎn)圖書史[M].戚昕,潘肖薔,譯.北京:電子工業(yè)出版社,2016:184.
? 夏野.中國古代音樂史簡(jiǎn)編[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0:75.
? 姜夔.姜白石詞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3:4-5.
? 孟偉.音頻媒體研究[M].北京: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2020:2.
? 熊澄宇.媒介史綱[M].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11:153.
? 瓊斯.新媒體百科全書[M].熊澄宇,范紅,譯.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7:474.
?? 李幼蒸.歷史符號(hào)學(xué)[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3:283,283.
? 百度“數(shù)據(jù)”詞條,由“科普中國”科學(xué)百科詞條編寫與應(yīng)用工作項(xiàng)目審核。
??? 《數(shù)據(jù)庫百科全書》編委會(huì).數(shù)據(jù)庫百科全書[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09:11,662,848.
? 大數(shù)據(jù)戰(zhàn)略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塊數(shù)據(jù)2.0[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39.
? 霍爾姆斯.大數(shù)據(jù)[M].李德俊,洪艷青,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7.
? SHANNON C E.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J].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1848,27(3):379-423.
?? 洛根.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號(hào)域、技術(shù)域和經(jīng)濟(jì)域的組織繁衍[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9:23,41.
?? 周昌忠.西方科學(xué)方法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38,13.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簡(jiǎn)明版)[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10):5441.
?? 王維嘉.暗知識(shí):機(jī)器認(rèn)知如何顛覆商業(yè)和社會(huì)[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0-31,25.
? 何守才.數(shù)據(jù)庫綜合大辭典[M].上海: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文獻(xiàn)出版社,1995:180.
? 肖仰華.知識(shí)圖譜:概念與技術(shù)[M].北京:電子工業(yè)出版社,2020:15.
? 方勇.墨子[M].北京:中華書局,2015:63.
? 任繼愈.佛教大辭典[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182.
? 先剛.柏拉圖與“智慧”[J].學(xué)術(shù)月刊.2014(2):49.
? 柏拉圖.柏拉圖全集[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56.
? 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7)形而上學(xué)[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6(7):29.
? 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8)尼各馬科倫理學(xué)[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6(8):127.
? 艾莉.知識(shí)的進(jìn)化[M].劉民慧,等譯.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83-85.
? 凱尼恩.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M].蘇杰,譯.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2:111.
?? 羅紫初.比較出版學(xué)[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6:60,60;魏玉山.國際出版業(yè)發(fā)展報(bào)告:2020版[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21:370,17.
? 中國出版年鑒1997[J]1997:8;中國出版年鑒2021[J].2021:836.
? 張立.數(shù)字出版學(xué)導(dǎo)論[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