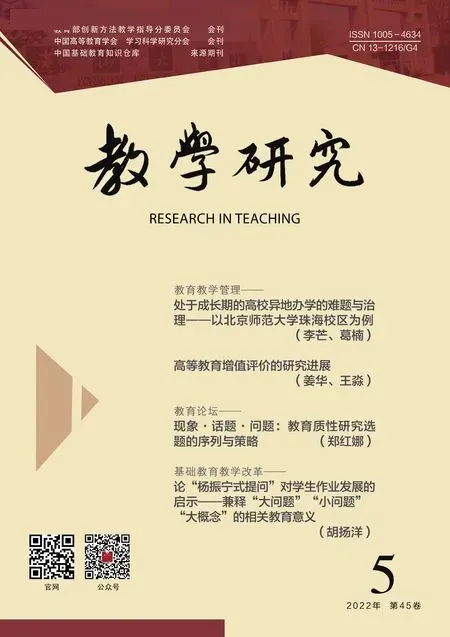我國近現代閱讀實驗系列研究述評
耿紅衛
(河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五四”以來,我國心理學研究開始興起,借助課堂教學這一平臺得以快速發展。艾偉、杜佐周、沈有乾、龔啟昌等學者可以說不只是心理學家,更是教育家,在漢語文教育心理學實驗研究方面都有著突出的建樹。就閱讀綜合性實驗研究而言,如艾偉在閱讀興趣、閱讀速率、閱讀理解能力等方面,龔啟昌在“閱讀之機能”“閱讀之理解與速率”“閱讀之興趣”“閱讀的方法與條件”和“閱讀之教學原則”等方面,對20世紀前期國內外近20年學者的研究成果做了介紹,并對漢語文閱讀心理做了重點實驗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研究結論[1]。就閱讀專題性實驗研究來說,如艾偉等學者都相繼開展了一系列的單項實驗。實踐證明,近現代閱讀心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于當時及日后語文教材的編寫和閱讀活動的開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1 閱讀興趣實驗
20世紀30年代,一些學者開始對兒童心理與兒童閱讀興趣等問題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他們認為,兒童心理的發展特點和狀態影響著閱讀興趣的養成,同時只要閱讀材料內容得當,就能刺激興趣,誘導興趣,育成興趣。
1.1 艾偉的閱讀興趣實驗:反復求證,力求科學
艾偉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心理學家,注重閱讀的實效性,在漢語文閱讀心理方面的實驗研究成果碩豐。1938年9月,艾偉以某小學五六年級上學期9名學生為實驗對象,以16篇文言文為實驗材料,組織實施了第一次閱讀興趣實驗。他按照學習內容將文言文材料分為四大類,即兒童故事、驚人的描寫和敘述、生動的描寫與敘述、靜的敘述。讓每位學生將所學的16篇課文按照自己的興趣大小進行等第的排列,最后將學生排列出來的文章興趣的等第加以平均,進而觀察位于不同等第文章的所屬特性。此次實驗的結果為:由于所閱讀的文章特質不同,學生的閱讀興趣也會有很大不同,學生最感興趣的是兒童故事類材料,比較感興趣的是驚人的描寫與敘述類材料,一般感興趣的是生動的描寫與敘述類材料,而興趣不高的是靜的敘述類材料。但是,就這個實驗研究而言,實驗結果的可信度并不高,結論也比較片面,對當時教材的編寫參考價值也不大。究其原因,該實驗存在被測試人數過少、文言文材料偏難且數量有限、實驗的方法和技術手段也不夠科學等諸多制約因素。
在汲取第一次實驗教訓的基礎上,艾偉于1939年6月再度舉行較大規模的閱讀興趣實驗。該實驗以四、五、六年級下學期26名小學生為測試對象,實驗材料為當時通行的教材,隨機從中抽取數篇文章,體裁既有白話文也有文言文等,主要采用等第的辦法,對文章的興趣的評價結果進行表達。被測試文章按照興趣等第由高到低排列為:《刮骨醫毒》、《好妹妹》(一)(二)(三)、《千里尋父》、《鴿子醫生》(一)(二)(三)、《魯賓孫漂流記》、《世界最大民族》(一)(二)、《喜雨》、《孫中山先生的故居》、《愚公移山》、《黃天蕩之役》(一)(二)、《出塞》、《最早的火車》、《書籍的故事》、《夏日的田園》、《水的旅行》(一)(二)、《交通大道》、《勸種牛痘》、《蒙古人騎馬》、《報告鄉村生活的一封信》、《窯居生活》。實驗結果為:學生對于閱讀讀物興趣相近,閱讀興趣的濃與淡和讀物特質轉變有緊密關聯性,學生對驚異、生動、動物敘述、談話式、幽默、情節、男性、女性、兒童等類讀物最感興趣,但是對于成人、靜的敘述、知識灌輸、道德暗示等類讀物閱讀興趣不高。學生對于韻文并沒有表現出異常的偏愛,對于文言文與家庭生活經驗類的材料興趣不高,甚至淡然,沒有白話文受歡迎。究其原因,與閱讀的難度關聯度不大,與學生的生活經驗接近的閱讀興趣會高一些。在實驗研究中,他認為,作家應當熟悉兒童發展的心理,同時要多創造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唯有這樣的作品才能引起兒童的閱讀興趣[2]。由此可見,第二次閱讀實驗相比首次實驗而言,在實驗對象、材料、方法等方面都有所改進,增加了實驗的信度和效度,無形中也提高了實驗結果的科學性。
到了20世紀40年代,艾偉開始在初中進行“由背誦結果分析學生之興趣”“學生對讀物興趣之評判”等多個閱讀興趣實驗。其中最為典型的實驗就是艾偉通過背誦來觀察學生對閱讀內容的興趣。此次實驗材料均為初中國文教材的文章,共計43篇,被試學生16人。背誦等第為1~27,實驗表明:興趣最高者為《陋室銘》,最不感興趣者為《甌喻》。實驗的結論是:(1)初中的學生最感興趣者為驚人或奇異的敘述,如《口技》等;(2)學生也喜歡描繪生動或者帶有情感敘述的文章,比如《捕蛇者說》等;(3)容易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包括幽默、奇辟、別致的韻文,如《歸去來辭》等;(4)另一個為學生所歡迎的閱讀內容就是偉人故事或者兒童故事,如《岳飛之少年時代》等;(5)簡短的游記與教條有時也能使學生感興趣,如《座右銘》等;(6)學生們不感興趣的內容則是包括《習慣說》等這些刻板的理論以及類似《甌喻》的靜態的描述;(7)就文章形式而言,初中學生喜歡文字簡潔、敘述曲折、淺近易識類的,如《口技》等;而最不喜歡文字艱深、生澀、難于了解類的文章,如《戰國策》各篇等[3]。實驗表明:就各種讀物而言,兒童的閱讀興趣不隨成人的喜好而轉移,成人喜歡的讀物,未必就受到兒童的歡迎。因此在閱讀學習中,兒童閱讀不喜歡的內容,教學質量就會降低。這一實驗結果備受當時學界的關注,成為語文閱讀教材編寫的主要參考依據。
1.2 胡士襄、江文宣等學者的閱讀興趣實驗:擴大規模,力求實效
在艾偉的指導下,胡士襄、江文宣于1943~1944年間,以初小三年級上學期至高小二年級上學期685名學生為測試對象,進行了一次規模比較大的閱讀興趣實驗。實驗結果表明:學生對不分階級性別的兒童故事;兒童現實生活的敘述與描寫類的文字材料;驚人的敘述與描寫,包括冒險故事;擬人敘述的諸多動物故事;贊頌祖國的愛國故事;能夠滿足兒童心理需求的幽默故事以及具有兒童感興趣的人物故事或時事報告等讀物材料最為感興趣。然而,學生對于自然、衛生、公民等常識性知識;枯燥乏味的應用文材料;成人角度寫作的作品,不論是幽默、諷刺類的,還是機智、勇敢類的語言風格;含有道德馴化類的材料以及平鋪直敘、內容單調等的劣質文章,均表現出反感和厭惡的情緒[2]。此次實驗研究方法與前幾次基本相同,其價值非常明顯,在于以存在的大量樣本為基礎,證實了其研究結果的有效性。此研究與艾偉的同類研究結果相近,對于當時國語課程與教材改革、教學方式的變革都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通過對以上學者關于閱讀興趣實驗研究的梳理發現,中國的兒童對于國語、國文的閱讀與美國兒童對于英語的閱讀一樣,盡管材料不同,但閱讀興趣趨勢基本相同。就讀物的特質而言,兒童對驚異、生動、動物敘述、談話式、幽默、情節、男性、女性、兒童類的閱讀材料感興趣,而對于成人、靜的敘述、知識灌輸、道德暗示類的閱讀材料興趣不足。從國外的同期研究看,美國兒童對道德行為敘述類材料也最不感興趣。可見,中外兒童的閱讀興趣點大體是相同的。研究發現,兒童讀物的深淺程度、兒童文學的優美程度及讀物的內容,此三者之間有密切關聯,但是兒童的閱讀興趣與讀物的難度則沒什么關聯。就文言文與白話文學習而言,與閱讀興趣關聯度不大,但是文言文讀物的選擇要重于白話文。
2 閱讀速率實驗
2.1 漢字直排橫排對閱讀速率的影響:實驗中確立漢字橫排的優勢
從商代甲骨文誕生之日起到近代時期,我國文字不管是甲骨文、大篆、小篆還是隸書、行書、楷書、草書,均為縱行書寫與編排,一行十幾字到幾十字不等。閱讀者的習慣是從上向下,從右到左。鴉片戰爭爆發后,西方的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晚清政府的國門,拉開中國近代史的序幕。這也是中華民族屈辱史的開端,中華民族不僅遭受到經濟侵略和軍事侵略,而且來自西方的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沖擊也日益加劇。同時,在這種西學東漸的背景之下,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一些文人志士開始學習西方一些新式教育理念,外語學習一時成為時髦。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到以拉丁文字為主的外國文字的編排方法和閱讀方法與國人的閱讀習慣不同,即從左至右編排,且為橫讀。當時受到西方文字編排的影響,我國開始嘗試漢字的橫排實驗。比如,1904年編寫的《漢語字典》是第一次漢字橫排的印刷品,1915年創刊的《科學》雜志等也陸續采用了橫排版。在民國初年,作為方塊字的漢字橫排與豎排印刷混雜與并存的局面十分嚴重,也沒有統一的編排標準。這一現象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并試圖通過教育心理實驗來對比中西文字編排方式與閱讀速率的關系。尤其是對于漢文而言,哪種編排方式更符合人們的閱讀心理,更符合人們的閱讀規律,依然是爭執不斷。
比如,1918年,張耀翔以中國留美學生為對象做了一次中英文閱讀速率實驗,實驗結果是直排好于橫排。1925年,沈有乾依然選擇中國留學生作為被試對象,做了一次關于中英文閱讀橫排或直排材料的實驗,用照相機記錄被試者眼球注視的時間、字數,以秒為單位作為讀取字數多少的衡量標準。研究發現:被試者在閱讀中文時,眼睛運動的角度要小于英文,閱讀豎版文字,眼睛停頓的次數要多于英文,就每秒閱讀的字數而言,中文數量多于英文數量。最后得出了要想提高漢文閱讀速度,就需要改變人們長期形成的閱讀習慣,在文字編排上就必須采用橫排印刷的結論。同年,陳禮江、哈爾以兩篇漢語散文為實驗材料,做了漢字直排與橫排哪種方式更適合閱讀的研究,最終的結論是兩種編排方式無優劣之分,只不過閱讀速率純粹受到個人閱讀習慣和閱讀訓練的影響而不同罷了。趙欲仁等學者在1925年的實驗證明了橫排比直排更有利于閱讀與寫作。1929年至1930年前后,周先庚的研究結論是:影響誦讀速度最關鍵的是漢字的格式塔和漢字的位置,而漢字的橫讀速度與豎讀速度之間并無顯著的差異。由此可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漢字的橫直排對閱讀和寫作速度的影響問題尚無定論,橫排優于直排者有之,直排優于橫排者有之,直排、橫排無所謂優劣論者也有之。不過,就當時諸多實驗的科學性而言,由于個別學者的研究對象是成人留學生,研究方法上過于注重主觀推理以及經驗和習慣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所研究的結論可靠性不高。
艾偉在1927~1928年采用速視法,通過看無意義的材料進行漢字橫直排的研究,科學性比較強,現作重點闡述。艾偉的橫直閱讀實驗研究,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實驗共有280人,其中小學六年級和初中二年級各100人,高中一年級80人;實驗材料分為白話、文言及無意義漢字三種。第二種實驗共有160人,男女生各半,均為高中一年級學生,實驗材料中所有漢字純屬于無意義的,只是各組的筆畫不盡相同。通過一系列的實驗,艾偉借助表格數據統計方式使研究結果更加彰顯,核心內容為:(1)在白話、文言以及無意義的漢字中,均為直行成績比較優秀;(2)三種漢字形式的成績比較,白話成績最為優秀,文言次之,無意義者最次。這種情況在橫行、直行中也如此;(3)就橫行與直行比較而言,白話、文言、無意義三者之中,橫行速度相對較快,但同時錯誤也較豎行多;(4)在不同筆畫(無意義)的各組字中,其成績速度和筆畫數不一定成反比;(5)就兩性差別而論,橫行與直行表示的差異并不明顯;(6)在不同筆畫(無意義)的試驗中,橫行成績遠優于直行成績;(7)通過對兩組實驗結果的比較,平均成績中橫行的成績較為優秀。在系列研究中,艾偉得出低年級直行閱讀較優而高年級橫行閱讀較優(無意義材料表現更為明顯)的初步論斷。為了進一步印證此觀點,他在參考杜佐周、陳禮江、哈爾、沈有乾等學者研究意見的基礎上,排除閱讀習慣和熟悉材料的干擾,通過速視法,最終得出橫行閱讀速率大于直行閱讀速率的結論。
以上幾位學者對于漢字橫排與直排(豎排)問題的研究,最終使橫排成了漢文的主流,對當時各種教材及印刷物的印制有著積極的社會價值。但如何排版問題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夕依然爭論不斷。隨著漢文橫排在閱讀中的優勢愈加凸顯,最終在新中國成立不久逐步取代漢文直排,并得以廣泛推行。1949年,新中國制定簡化字拼寫方案,決定使用橫排印刷。目前,除了出版個別古籍以外,其他紙質文本和資料均采用了漢字橫排的形式。這些成績的取得與錢玄同、陳獨秀等學者的提倡,以及艾偉、杜佐周等學者的實驗研究是分不開的。
2.2 篇幅長短對誦讀速率的影響:默讀的速率要好于朗讀
傳統語文學習的經驗之一就是多誦讀一些經典篇章,這是學生積累知識、發展語感、學好語文的有效途徑之一。如何提高誦讀效率問題不能僅憑直覺和經驗,還需要一定的科學方法來驗證。20世紀30年代,艾偉對此做過四次分項實驗研究。首先是“篇幅長短與誦讀速率”的關系研究。實驗材料為64字到302字的文言文若干篇,在教者講解清楚后,讓被試者誦讀一篇數遍,直到會背為止,并記下每次誦讀的秒數。這樣的背誦課文實驗,不僅可以看出學生讀的遍數與費時多少的問題,而且也可以看出學生智力上的差異。其次是“文章內容在背誦與默寫上的影響”的研究。實驗材料為初一文章中的7篇,讓學生熟讀成誦,觀察學生誦讀次數與閱讀內容深淺之間的關聯。通過系統的數據分析,艾偉認為:《陋室銘》一文語言比較風趣幽默,《馬說》一文所述多是兒童常見的動物,了解起來比較容易,所以這兩篇文章費時短,易讀易記,且不容易遺忘。而《春夜宴桃李園序》字數并非最短,但費時最多,原因是文章立意玄誕,內容枯燥乏味,非學生興趣之所在。《孔子世家書》《曾文正家書》之類的文章,多是空泛的道德說教,內容也很枯燥,所以兒童也不愿意讀,即便會背也容易遺忘。再次,文章的體式研究。采用高中二年級的散文和韻文各兩篇,分析其對誦讀速率的影響。最后,年齡的影響研究。分別對兒童與成人、兒童與老人的誦習速率作了比較。艾偉通過整理與分析,綜合四項因素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1)在四個因素中,文章的篇幅長短對誦讀的影響最大;(2)文章內容也是影響誦讀速率的因素之一,但往往與學習者的興趣相關;(3)文章的體式,不論是散文還是韻文,都能影響誦讀速率,這是學習方法及習慣造成的;(4)年齡使誦讀速率有差異,但組間差小于組內差[3]。對此實驗,艾偉曾評價道:“在學習心理實驗班里最近八年來所作類似的研究非常之多。其所獲得的材料并由此而擬定的原則,足夠我們編輯一部合乎兒童學習心理的初中國文課本。”[4]
同期,有學者做了整讀、段讀實驗,得出的結論是:篇幅小于300字的文言文,整讀速率高;而篇幅在300字以上的,段讀的成績較優。還有學者通過對800名小學生的朗讀行為和默讀行為進行比較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學生年齡不同,對朗讀與默讀的理解和速率不同,年級越高,理解和速率就會隨之增加;從理解的角度看,朗讀比較適合低年級學生,而默讀更適合高年級學生來理解閱讀內容,從速率的角度看,朗讀低于默讀。通過一系列閱讀速率實驗表明,朗讀的方式固然很好,但是通用于中小學各個年級,以小學低年級尤勝,可以多采用此學習方法。而對于高年級以上的學生,隨著年齡的增加和閱讀理解能力的提高,默讀更有利于提高學生的閱讀速率,應以此類學習方式為主。因此,就教師教學而言,建議要重視兒童的默讀習慣,因為默讀習慣是制約默讀速率的重要因素,小學低年級尤甚。國外同期的研究表明,在閱讀理解方面,默讀好于朗讀,尤其是小學高年級表現最為明顯,而默讀習慣是否養成與閱讀速率和理解力的高低有正關聯。朗讀教學也不容忽視,對于一二年級的兒童閱讀興趣的培養,顯得尤為關鍵,因此,教師要在朗讀材料、朗讀技法上給予指導。近現代艾偉等學者的有關研究盡管還不太符合嚴格的實驗程序,但他們得出的研究結論,今天看來也是比較正確的,對于語文閱讀方式和模式的變革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3 閱讀能力實驗
3.1 默讀能力:多種因素制約默讀能力的高低
我國古人學習重視朗讀、誦讀和吟詠,但也在大量地從事著默讀教學實踐,但從實驗研究的角度看,到了20世紀20年代默讀才被學界重視起來。在眾多學者的實驗中,以艾偉關于默讀能力的實驗最為突出。1936年艾偉為了深入了解學生閱讀的速度與理解程度,對其默讀行為做了一系列實驗,研究的結論是:第一,閱讀理解力與閱讀速率成正比,默讀能力與智力成正比。比如,在一秒鐘內讀7個字或8個字的小學生,其理解力就強于能讀5個字或6個字的小學生。第二,中國孩童的默讀速率與理解都可以借助訓練而逐步提高。認為中國的默讀訓練太遲,強調應從三、四年級就開始有意識地組織訓練。第三,原本默讀能力差的學生經訓練進步較快,而原來默讀能力好的學生經訓練進步較慢。在這些實驗中他總結出國語默讀應具備迅速瀏覽撮取大意、精心評讀記取細節、綜覽全章挈取綱領、玩味原文推究含義等四個方面的能力,據此編寫有“中小學各級默讀能力測驗”(有常模)材料,并得以廣泛推廣和使用。通過對有關默讀能力的實驗研究發現,兒童在迅速瀏覽撮取大意、精心評讀記取細節、綜覽全章挈取綱領、玩味原文推究含義等四個能力方面發展不均衡,尤其是兒童在玩味原文推究含義這一能力方面表現最為薄弱,這與此能力難以養成和不夠重視有關。此外,同一年級兒童之間的能力差別大于年級之間兒童閱讀能力的差異。
3.2 閱讀理解能力:與知識背景、聯想能力等有緊密關系
對于閱讀理解能力,艾偉曾為此做過專門實驗,實驗在南京某女中進行,應試者為初高中六個年級72人,每個年級12人,所有應試者國文成績均為優良。閱讀材料為第二次編制的國文理解力測量量表甲,其中文言文1篇,共926個字;白話文1篇,共1 763個字,設計問題為20個。應試者共參與五次解答,對五次結果做出比較[3]。研究發現,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主要有三種:第一,理解是一種思維習慣,是一種本能的主觀反應。有些人的理解力已經達到一種習慣的高度,遇到熟悉的事物就能夠立刻反應。對于這種閱讀理解習慣已經高度養成的人,他們在閱讀經驗范圍內的書籍的時候,能夠達到迅速聯想、一看就懂的情形。第二,對于內容比較深的書籍或資料,需要慢慢閱讀,長時間聯系性閱讀作為理解能力的有效補充,使原來本能的反應得以鞏固和提高。第三,盡管閱讀者具有良好的閱讀習慣,但對于閱讀中遇到的新的生字詞及難以深入理解的內容,需要多次反復閱讀方可達到理解的效果[5]。概而言之,主要包括純粹理解力、記憶理解力、文字連貫上的理解力,這三種理解能力其實與學生的知識背景、聯想能力及閱讀習慣有密切的關系。很顯然,學生如果具備厚實的先前知識經驗作為基礎,具有快速的聯想和想象能力,具有良好的閱讀習慣,那么就更有利于提高他們的閱讀理解能力。
3.3 文白能力:凸顯文白學習的漸進性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以文言文為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很大,很多學者倡導徹底廢除文言文的學習,主要學習白話文、語體文。然而,傳統文化對中國人的影響很深,很難說立即廢除,更何況有很多優秀的傳統文化需要弘揚和繼承。20世紀20年代的文白之爭,最終在“以學習白話文為主,兼學文言文”上達成了一致意見。到底什么時候開始教授文言文,學生應具備怎樣的文白閱讀能力,學界沒有統一的看法。為此,艾偉做過三次實驗,但每一次結論都有差異。1926年艾偉在上海、南京、杭州三地做第一次實驗。通過實驗,他認為對于兒童而言文言文理解起來比較困難,建議小學語文教材中刪去文言文,在初中語文教材中遵照由易到難、文白比例(隨年級的增高加大文言文學習的分量)的原則編寫一些文言文讓學生學習。1928年以來,艾偉在北京、天津和蘇北等地進行第二次實驗。幾年的實驗表明,學生無論在文言文閱讀理解方面還是在閱讀速率方面,都比白話文進步慢,因此,他建議文言文教學應從初一全面展開,只教授文言文而不教授白話文。1940年以來,艾偉在中山大學實驗學校進行第三次實驗。當時他主持該校的教學工作,以小學高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開展文言文閱讀教學實驗十分便利,實驗的效果也好于往年。實驗的結論是:高小是開始文言文教學的最佳時間。通過對艾偉的系列實驗分析發現,小學生白話文理解程度好于文言文,文言文學習時間不宜過早,最好在高年級進行。而中學階段,就文白程度而言,從初一到高三,學生的理解程度逐年增高,即年級越高,無論文言文或白話文,成績均隨之提高。但是文言文的進步不如白話文迅速,尤其是對于語文程度比較薄弱的學生而言,相對聰明者、語文程度好的學生,文言文的進步也比較迅速,但多不及白話文進步快,或許與學生的生活經驗及語言習慣、語言環境等有密切關聯。艾偉關于學生文白能力的研究、中小學文白能力的分級測量研究,盡管還有很多不足,但對于學界文白觀念的轉變以及教科書文白比例的編寫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4 結語
從近現代閱讀實驗的情況來看,中國的教育理念與心理學有密切的聯系,并逐步走向人性化與科學化。關于閱讀興趣的研究,實驗圍繞學齡兒童展開,根據文章的特質進行興趣等第的劃分,最終發現國語教學應該根據孩童身心發展的規律來制定更適合學生學習的內容。有關閱讀速率的研究,通過“漢字直排橫排隊閱讀速度的影響”以及“篇幅長短對誦讀的影響”進行科學的、系統的實驗,并通過對白話、文言以及無意義的文字進行多方比較,最終得出橫排是最適合中國人閱讀的排版印刷方式的結論。同時,也發現了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應針對篇幅長短來制定不同的誦讀方法,從而實現教學目標的最優化。關于默讀能力的研究,艾偉認為默讀能力和理解力與智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并歸納出了默讀能力的四要素,依據此編制出廣為流行的中小學默讀能力測驗,指出人們的閱讀能力與個人經驗背景習慣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此外,還對文言和白話能力進行了比較分析。隨著閱讀心理實驗的不斷深入,觀念一次又一次地更新,最終得出了文言文教學應從高小開始的結論。由此不難發現,語文教育的科學性正在深入人心。總之,受西方現代教育觀念的影響,近現代一些學者開始反思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此為契機來改造中國的教育。
艾偉等學者在閱讀心理方面的實驗嘗試,使得更多人認識到實驗科學、教育測量等理念和方法,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閱讀教學改革實驗具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在科學主義教育思潮以及西方現代教育理念的影響下,我國語文教育迎來了改革的春天。閱讀教學領域的改革實驗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比如,錢夢龍主持的“語文導讀法”改革實驗,旨在以發展學生的智能為前提,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為主要目標,讓學生通過三至六年有計劃的訓練,達到“不待老師講而學生自能讀書”的目標;蔡澄清的閱讀教學“點撥教學法”,通過點撥,啟發學生開動腦筋,引起共鳴,達到掌握知識并發展自學能力的目的。另外,曾祥芹主持的“新概念閱讀教學”散發訓練體系(精讀、略讀、快讀)改革實驗、顧德希承擔的“高中語文閱讀教學教法”實驗研究、程漢杰主持的“快速閱讀”改革實驗、晏茂新主持的“四級臺階速度訓練研究”[6]、竇桂梅的“主題閱讀”教學改革實驗、韓興娥的“海量閱讀”教學改革實驗等閱讀教學實驗,都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對當今新課程標準的制定與修訂、語文教科書的編寫以及閱讀教學課堂實踐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