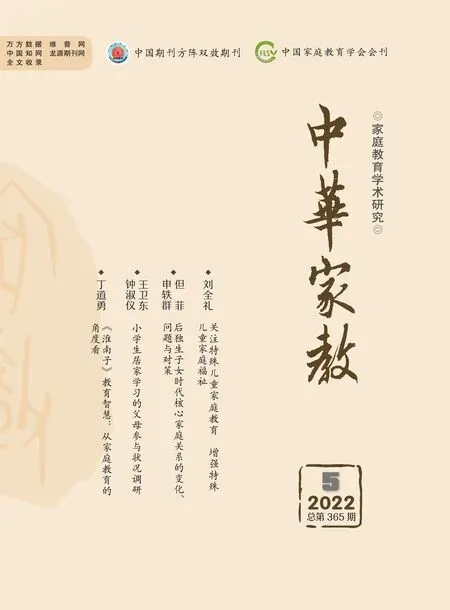聽障兒童語言認知的神經基礎及其對家庭教育的啟示*
雷江華
語言教育是聽障兒童教育教學中的核心問題。家長作為孩子的第一任老師,最為關注聽障孩子的早期語言發展狀況;作為孩子的終身教師,最為注重聽障孩子的語言發展在其生涯發展中的作用;作為孩子的人生導師,需要做好孩子語言發展的全程規劃。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對聽障兒童的語言教育呈現出不同的樣態,需要予以關注與分析,并盡可能引導他們根據聽障兒童語言認知的神經生物基礎,厘清語言發展的思路,進行循證實踐,進而采取有效的對策,最終實現聽障兒童語言的高質量發展,為其人生發展奠基。
一、聽障兒童家庭教育的現實透視
筆者曾在聽障兒童家庭教育的問卷調查與訪談中了解到,大多數聽障兒童家長在孩子被發現或診斷為聽覺障礙的早期階段都經歷了痛苦的心路歷程,特別希望通過醫療手段讓自己的孩子變“聾”為“健”,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治愈聽障孩子的耳朵上,希望他們像健聽兒童一樣利用聽覺自然獲取語言信息,實現聽覺語言的認知加工,最后能用口從咿呀學語到能說會道。家長的這種想法實際上遵循的是健聽兒童“以聽促說”的發展思路,自然會不遺余力地花費大量的財力與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想各種辦法(如藥物治療、針灸治療等)治愈孩子的耳朵。然而,當治療效果沒有達到預先期望時,家長便會想到通過配戴助聽器或植入人工耳蝸來進行補償,讓聽障孩子能感知到日常生活的語音,并能與他人進行交流。《登峰》一書中,杜在新女士就表達了她當年求醫問藥的艱難歷程,但難能可貴的是,在求醫問藥的路上她仍能在醫院堅持對孩子進行語言康復訓練,并制訂了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實現了孩子“聽力在最差之列,但語言康復卻是最好的”[1]。因此,家長在聽障兒童語言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從“醫學的終點是教育的起點”轉到“醫教結合”的軌道上,避免錯失孩子語言康復訓練的關鍵期,注意全程規劃聽障孩子的語言康復訓練,即使戴上助聽器或植入人工耳蝸后,也要堅持語訓賦能增效,因為語訓跟不上或效果不佳,聽障孩子很可能能聽音但不一定能很好地辨音,進而影響語言的有效加工與流暢表達等。
即使家長能做到“醫教結合”,且意識到了語言訓練對于聽障兒童的重要性,在現實的語言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口語與手語的艱難抉擇,大多數家長在早期極其希望孩子能學習口語,達到與健聽兒童一樣聽話說話的目的,如《登峰》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不管他如何焦急迫切需要的食品或物品,只要是打手勢,我就裝著不理解、不知道。他不得不跟著我學說話,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需求”[2]。不得不承認,口語對于聽障兒童和健聽人士的溝通與交往是非常重要的,筆者曾遇到兩個印象深刻的案例,她們都能與我進行比較順利的口語交流,但是在手語的學習上卻大相徑庭。前者是一名聽障兒童,通過隨班就讀順利讀到研究生,最后就業受阻,在母親的陪同下來向我咨詢。我通過與她的交流,發現她的唇讀能力很強,表達能力也不錯,但詢問她是否學習過手語時,她選擇了沉默,母親在旁補充說未曾學過。我便建議她學手語,像她這么優秀的聽障研究生,找到一份工作應該不會有什么障礙。她學了手語后果真如愿找到了工作。后者是一名聽障大學生,她獨自來找我,其看話能力與說話能力都很強,我很好奇她如何有這樣突出的能力,她說是因為現實的生活讓她既要用手語,也要用口語,時而需要進行兩者的互譯,是現實的生活讓她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語言發展之路。她甚至表達了早期用手語促進口語語訓的一些做法,引人深思。由兩個案例可知,前者遵循的是先口語再加手語的發展之路,后者遵循的是口手并進的發展之路。而現實的情況可能更為復雜:有的家長持“存口語廢手語”的單一口語發展路徑,其中存在看話與聽語的“只聽不看”“看聽并進”等不同的主張;有的家長則主張早期進行口語訓練,在一定的時候介入手語,即持“口前手后”的先口語單獨發展,隨后“口手并進”的發展思路;還有的家長主張根據現實生活的需要,不但堅持“口手并用”,而且還期待“口手并進”,等等。
總之,家長在家對孩子進行語言教育過程時,需基于聽障兒童生涯全程發展的規劃,進行理性的深思熟慮與智慧的語言教育,根據聽障孩子語言發展的實際情況走出一條具身發展之路。無論家長選擇走什么樣的語言發展之路,需正視的一個現實是:聽障兒童的語言發展應從單純的語音與語法的訓練走向生活的語用,即要讓聽障兒童將學到的語言在現實生活中予以有效地運用,否則就可能影響聽障兒童未來的溝通與交往。這也是聾校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增加《溝通與交往》課程的原因所在,其中特別指出“在溝通交往能力發展的過程中,聾生的口語、手語、書面語能力都應得到發展。這些能力的發展是相互關聯的。在教學中要重視口語訓練,但不要把口語能力作為唯一的培養目標;要重視聾生的發音練習,但不要把語音清晰度作為唯一的訓練目標;要重視手語學習,但不要把手語運用作為聾生掌握語言的最終目的”[3]。
二、聽障兒童語言認知的神經基礎
家長秉承“醫教結合”的理念,在聽障孩子語言教育過程中呈現的“口”與“手”之艱難抉擇,除需要經驗的總結與個案的列舉外,更需要科學的依據有效指導聽障語言訓練工作。目前,認知神經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從腦科學研究的角度來探討其語言認知機制成為可能,一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使研究者看到了大腦活動的空間結構圖,二是事件相關電位使研究者明晰了大腦活動的時間路線圖,兩者的結合則有利于全面把握聽障兒童語言認知加工的神經基礎。
(一)語言加工神經基礎的相似性
左腦不但是口語的認知加工神經基礎,而且在手語加工中得到了驗證,這不但說明手語和口語一樣是大腦左半球的功能,而且凸顯了其作為語言加工優勢半球的地位。根據手語腦功能成像的研究結果,發現手語與口語的大腦皮層機制并無質的差異,手語不但激活了語言中樞,而且與有聲語言的絕大多數功能區是疊合的,語言的半球單側化現象以及語言大腦功能定位區很少受語言模式特征的影響。[4]據此可確定手語的語言地位,故應重視手語在聽障兒童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又如,聾人進行英語押韻和手語押韻判斷時,激活的腦區與健聽口語者進行英語押韻判斷時激活的腦區相似,包括左側背側前額葉,延伸到額下回,左側頂上小葉。由于不同的語言加工方式均激活了這些腦區,研究者認為,“由這些腦區組成的語音加工網絡可能是多通道或者‘超通道’的”[5]。不同語言加工的相似性說明了不同的語言可能具有共同的神經生物基礎,也就是說,不同的早期語言訓練可能會塑造出相似的神經通路。
(二)語言加工神經基礎的差異性
手語和口語具有相似的左腦機制,但在具體激活位置、范圍和程度上存在差異。腦成像技術提供了更細致的手語腦加工機制及其與口語、書面語的對比。MacSweeney 認為聾人和健聽人語音加工的大腦機制十分相似,左側額下回、頂上小葉、額上回中部均被激活,證明左半球額頂葉組織在英語和手語語音加工中的穩定作用。但他也發現語言形態、聽力狀況和手語早期習得對該區域具體作用的發揮存在影響。早期習得手語的聾人在手語語音加工時以上腦區激活程度相對較弱,后天習得手語的聾人則在左額葉皮層下部出現更大激活,從額中回和中央前回延伸。聽力狀況也對語音加工的腦機制有所影響,盡管左腦以上三個區域均被激活,但聽障者比健聽者更多激活了左側額下回區域,活動位置向額葉中部和中央前回延伸,在額葉上回也有一部分激活,且該現象與聽障人士手語習得年齡無關。[6]Emmorey則直接對手語和口語產出的左腦機制進行探討,發現在左頂葉區內部,聽障者緣上回和上頂葉兩個區域比口語者激活的程度更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手語輸出時需要手形、位置、方向等因素相互配合,因而更多激活左側緣上回區域;另外,聽障者在手語產出過程中可能還需要對手臂、肢體動作等進行本體感覺的監控,因此相比口語者,聽障者的左側上頂葉比健聽人的激活程度顯著增強。[7]手語的加工機制表現出“左腦主導,右腦參與”的特點。而唇讀作為一種視覺語言認知活動,激活了大腦的視覺中樞、運動中樞、聽覺中樞和語言中樞等。唇讀作為一種基于面部加工的技能,需要通過口形和面部運動來加工語言,唇讀的初期需要右腦嘴形提取有用的信息,但是接下來則更多地需要左腦對接收的信息進行語言分析。因此,唇讀對大腦半球的依賴程度取決于不同的唇讀任務的要求。[8]這說明,在聽障兒童語言教育過程中要堅持左腦與右腦同時開發的全腦開發策略。
(三)語言加工神經基礎的可塑性
很多研究發現,大腦皮層具有很強的可塑性。聽障兒童的聽覺皮層也不例外,他們早期的語言經驗對語言加工神經通路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影響。從聽障人士唇讀的大腦機制研究來看,國內外研究人員通過腦功能成像技術的研究發現,唇讀是一種視覺語言認知活動,唇讀作為視覺刺激激活了聽覺皮層(左右側顳中回),說明視覺感知的跨通道特性。[9]盡管有特定區域加工模型與信息傳輸接替模型對唇讀的大腦機制進行理論解釋,但其中更多的證據支持信息傳輸接替模型。[10]前文描述的兩個案例中,兩名唇讀能力優秀的聽障學生通過視覺的唇讀獲取了有效的語音信息且進行了語言加工,進而與人進行有效的溝通,從實踐層面也印證了跨通道的可塑性。大腦皮層的可塑性不僅體現在發育過程中,而且延伸到發育成熟以后,體現了全程可塑的特點——“活到老,塑到老”。[11]
(四)語言加工神經基礎的關聯性
既然口語(聽語與視覺的唇讀)、手語、書面語都是語言,那么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何?特別是聽語與唇讀的關系,口語與手語的關系如何。會不會像某些家長認為的那樣:聽障孩子不用手語就能將口語學好,不用口語就會把手語學好,或者說需要將兩者結合起來?那么兩者之間是否可以進行有效的啟動或聯動,彼此之間是相互促進還是相互抑制?如果彼此抑制,則需要從中二選一;如果是彼此促進,則兩者應該齊頭并進。為進一步明晰上述問題,研究人員通過事件相關電位技術研究了聽障大學生的跨形態啟動,初步發現了書面語、手語與口語分別對唇讀的啟動,共享語義,可能共享語音。[12]正如一位校長在交流聽障兒童上課學習的情景時談到,即使只準聽障兒童用口語,但這些兒童會將手放在背后偷偷地打手語。至于聽障兒童同時進行多種語言加工時是各自存在獨立的加工通道還是共通的加工通道,則取決于多種語言學習的先后順序、語言使用習慣、早期語言經驗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如早期語言經驗除對大腦語言功能存在塑造作用,對語言能力的發展也至關重要。Mayberry 認為,早期語言經驗,不論口語還是手語,對語言能力的發展十分重要,不僅對第一語言,而且對后來學習其他語言同樣重要。[13]
三、聽障兒童語言教育的基本思路
基于家庭教育現實的思考與大腦機制的分析,家長要從動態的視角來認識、研究與開發大腦,需要根據聽障孩子的語言發展規律,依據語言認知神經基礎的相似性、差異性、可塑性與關聯性等特點,在抓住關鍵期的基礎上,注重全程語言康復,采用全面語言康復策略,走出一條具身發展之路。
(一)創設豐富的語言環境,做到全面供給
家長要盡可能為聽障孩子提供全面豐富的語言,給聽障孩子創造語言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如“一主多輔”“多語并進”等,即使家長想特意為聽障孩子設計某一語言的針對性發展之路,也需要根據孩子的實際情況(如語言基礎、認知能力、家庭交流環境等),最好提供豐富的手語、口語、書面語的交流方式,采取“一主多輔”的策略,讓聽障孩子建立適合自己的語言發展之路。否則,家長單一封閉式的語言教育對聽障孩子來說,可能會是一種語言環境剝奪,不但影響其語言發展,而且影響他們的認知與社會性發展,更影響其大腦神經元之間聯結的形成。
(二)改變單一干預思路,進行綜合干預
聽障兒童的語言訓練問題,有的可能不一定是語言本身的問題,很可能是其他能力沒有跟上導致的語言發展滯后,例如學習了很多機械性的語言卻沒有在實際交流環境中應用,導致所學非所用。有的則是認知能力限制了語言能力的發展,例如伴隨智力障礙或自閉癥的聽障兒童的語言發展可能不如單一聽覺障礙的兒童,還有手語失語癥的聽障兒童可能需要走其他的語言發展之路,等等。因此,家長要根據聽障孩子的語言行為表現探討其中可能的影響因素,進而采取有效的綜合干預方法提升語言教育的效果。
(三)權衡利弊得失,引導兒童做好個體選擇
家長在引導兒童進行語言訓練時,無論做出什么樣的選擇,都會存在利弊得失。例如,筆者曾遇到有的家長說很后悔孩子早期沒有學手語,盡管早期口語訓練的效果很好,但最后還是需要手語的介入。這里家長實際上是對自己過去走單一口語發展道路的一種追溯式的反思,進而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手語何時介入比較妥當且效果較好”的實際問題,值得家長們深思。因此,家長在對聽障孩子的語言發展進行分析時,除了要考慮當前的情況外,還要從聽障孩子終身發展的視角引導其做好個體選擇。
(四)遵循語言發展的規律,做好具身設計
上述在全面供給情況下的綜合干預在做出個體選擇后需要家長進行精準設計,讓聽障兒童走出一條具身發展之路。這種設計要做到理性思考,基于生涯規劃的全程設計,而不是短期的考量,真正讓聽障兒童未來能適應社會,有尊嚴地生活。例如,家長要遵循聽障兒童語言發展“非言詞性表達先于言詞性表達”[14]的規律,利用聽障孩子非言詞性的要求、抗議、請求、反應、表情與目光等,在交流過程中激發他們學習語言的動機,并根據其語言優勢做好具身設計,以提高聽障兒童語言發展的質量。
四、聽障兒童家庭教育的幾點啟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作為家庭教育的法理之源,明確了家長在教育中的職責與角色,更希望賦能于家長提升家庭教育水平。聽障兒童的家長更需要擔負起語言教育的重任,在做好家校合作的基礎上,有條不紊地做好家庭教育工作,重點關注聽障兒童的語言康復訓練,促進他們語言的高質量發展。
(一)家長要意識到語言是最難的課題
家長對待聽障兒童的語言教育需要在艱難前行中學習、研究與教育,明確自己作為撫養者、學習者、研究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15],通過學習掌握與應用語言康復訓練的方法,通過研究明晰聽障孩子語言康復訓練中的難點與痛點并自覺解決,并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教育方案以提高聽障孩子語言教育的成效。筆者曾遇到一些語言發展比較好的聽障兒童的家長,有的家長談到自己如何自學語音訓練知識,甚至是語言學的教材等,然后根據教材的內容研究自己孩子的發音,通過千百次的嘗試,終于摸索出一些心得與經驗。這些家長明顯做到了對聽障孩子語言教育問題的行動研究,并注意收集記錄平時的語訓材料,通過日積月累,逐漸引導聽障兒童走出一條自身發展的務實之路。
(二)家長要努力成長為最優的教育者
家長是最熟悉自己孩子的人,需要發揮對孩子了如指掌的優勢,協調好自己的工作與教育孩子的責任,如有可能,可以通過各種途徑,通過教育好自己再教育好孩子。總體來看,家長可以通過實現三步走的路徑讓自己成為孩子最優的教育者。第一步是家長要在與教師的合作中“師教師”,即向孩子的老師學習,通過向教師學習,轉變自身的教育理念,掌握基本的語言教育或訓練方法,配合教師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第二步是家長在學習成長過程中要不斷取師之長,補己之短,逐漸接近“似教師”的狀態,慢慢能逐漸主導孩子的語言康復訓練;第三步則是家長實現質的升華,通過學習交流與教育聽障孩子的實踐達到“是教師”的狀態,承擔起指導聽障孩子語言訓練的任務。《登峰》一書中,姚登峰的母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為了做好孩子的語訓,不但制訂了專門的計劃,而且想到將同伴吸引到家里來玩,并要求他們跟聽障孩子講普通話,以提供訓練語言交往的機會,更引導孩子自己要堅持語言康復訓練。
(三)家長要將生活塑造成最好的教科書
聽障兒童的語言教育要遵循語言發展的規律,抓住關鍵期,同時要注意立足聽障兒童實際生活,學會在生活中進行語言康復訓練,在語言康復訓練中引導聽障兒童進行溝通交往,做到學用結合,特別需要利用生活中鮮活的語言素材,例如“好”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表達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樣,如果只是簡單機械地學習語音,可能難以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杜在新女士曾有如下的經驗之談:“我把家里每件物品都貼上寫有漢字和拼音的名稱。他的目光注視到哪里,我就說到哪里;我看到什么,就教他什么。他想表達什么,我就告訴他什么。”[16]“水,是生活中的高頻詞,在洗澡、喝水、洗菜、洗衣時都要接觸水。我們一起到自來水龍頭下學習‘水’的發音,通過直觀的認識,他一下子就明白這種液體就是水。然后我拿來幾個盆子和杯子,分別裝上冷水、涼水、溫水、熱水和開水,讓他感受它們之間的區別、名稱,他一下子全記住了。”[17]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根據全程可塑的神經機制,聽障兒童的語言訓練錯過了關鍵期“并不意味著機會的完全喪失”[18],只是語言發展相對困難些而已!
(四)家長要將溝通與交往作為最大的要務
語言教育最終目的是讓聽障兒童學以致用,學會有效溝通;讓聽障兒童能結合生活的具體語境,學會運用恰當的語言,促進社會交往。過去,聽障兒童語言康復訓練存在遮擋口形讓他一心一意去聽的做法,盡管這樣的聽覺語言訓練有助于孩子利用聽覺掌握發音等,但也可能誤導孩子未來在與人交往時忽視用眼睛注視對方,讓人感覺缺乏交往的禮儀,這樣可能會影響孩子未來正常的社會交往,因此需要將語言康復訓練放在聽障兒童未來溝通與交往的具體實際中進行綜合考慮,實現語言的全面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