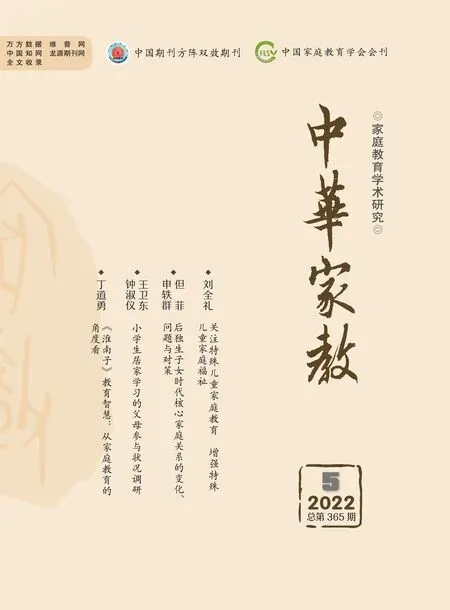《淮南子》教育智慧:從家庭教育的角度看
丁道勇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①本文中的《淮南子》引文,均以劉文典的集解本為底本。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是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集體創作的產物。我們常用的一些成語,直接或間接來源于這本書,比如“一葉知秋”(《淮南子·說山訓》)、“削足適履”(《淮南子·說林訓》)、“塞翁失馬”(《淮南子·人間訓》)、“南橘北枳”(《淮南子·原道訓》)等。這間接表明,該書雖然因為劉安的叛亂而遭厄運,但其文本仍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勞思光寫道:“漢代知識分子于儒則不解孔孟之旨,于道亦不解老莊之精義。”[1]《淮南子》就是一例。該書反復談及治術、征戰之事。因此,盡管在行文中大量引用《老子》《莊子》,其主旨已與《老子》之言“道”和《莊子》之言“我”相去甚遠了②舉例來說,《老子》講究“絕圣棄智”;《莊子·天下》中的灌園叟寧愿費力抱翁,也不愿意使用省時省力的機械。他說:“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對于這些機械的手段,“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可是,《淮南子·主術訓》卻明確鼓勵人使用智術:“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這段話源自《荀子·勸學》:“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此例可窺見《淮南子》“兼儒墨,合名法”的一斑。。《漢書·藝文志》對“雜家”做過如下定義:“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2]該書把《淮南內》《淮南外》歸入雜家,此后遂成為一個定論。雖然在思想史上《淮南子》算不得是開端性的書籍,但書中的很多內容仍然富有教育智慧,對于今天的家長也有一定的啟發。
一、素而不飾,不妨礙孩子表達真情實感
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
——《淮南子·精神訓》
明明很想看,可因為于禮不合而不敢看;明明很想做,可因為于禮不合而不敢做。從待人接物到坐臥飲食,凡事都用禮來約束自己。這樣做固然是一個修身法門,但是在《淮南子》看來,這樣的人“終身為悲人”。孔子見了容貌艷麗而名聲不佳的南子。子路知道此事以后,大為不悅。孔子矢口否認,說自己要是有什么壞心思,“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若從《淮南子》的立場來看,孔子急于否認的正是“目雖欲之,禁之以度”的東西。類似地,顏回過世這件事,對孔子打擊很大(“子慟矣”),以至于孔子有“天喪予!天喪予!”的感嘆。盡管如此,孔子仍舊謹守禮制,說“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論語·先進》)。在《淮南子》看來,這都是在壓迫真性情。可是,情感哪里是可以輕易用人力控制的呢?“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淮南子·精神訓》)人的情感好比江河之水。源頭既然已開,就只好順勢疏導,而不可以使用蠻力去堵塞。《淮南子》進而舉證說,顏回、子路、子夏、冉有都是孔門高徒,可是全都沒有得到善終:顏回十八而卒,子路在衛國被剁成肉泥,子夏雙目失明,冉有則患上了不能見人的惡疾。為什么會這樣?因為這些儒門弟子“迫性拂情”“不得其和”。且不說《淮南子》的舉證能否成立以及對于儒家的判斷是否失當,如何認識和對待自身情感,的確是一個有價值的問題。
在家庭教育環境下,家長常常給孩子立定太多的規矩、榜樣。在小孩子的判斷力還不健全的時候,就已經堆積了大量成見。結果,在很多問題上,他們表現出了不必要的拘束。有的孩子明明愛吃糖,可是在人前就是要表現出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非得在人后偷偷吃。吃不吃糖,總歸不是一件急事和大事。不過,這樣的小事也能反映出這個孩子不敢在人前表現真性情的特點。他心里可能早就有了一桿秤,認為愛吃糖不夠懂事。家長教孩子少吃糖甚至不吃糖,本是為了防止齲齒之類的問題,是為了孩子好。可是,如果一個孩子在大人不知道的時候偷偷吃,吃完又不敢去清理口腔,那大人的教導豈不是恰恰事與愿違?與其這樣,還不如讓孩子大大方方、想吃就吃,吃完記得清理口腔就好。“終身為悲人”的命題告訴我們,總是壓抑孩子的真實情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過分地壓抑,孩子們反而容易對一些東西表現出不恰當的貪欲。進而言之,一個孩子如果自小就違逆自己的情感,不關注自己的真實感受,時時處處修飾自己,那么他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今日教育界關注的情感學習議題,針對的就是那種無法妥善認識、接納自身情感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今日中小學生乃至大學生身上都不罕見。開始關注自己的感受,學會信賴和面對自己的感受,是兒童學習自我保護的重要一課。這是《淮南子》中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個立場。更進一步,僅僅是發出禁令,往往不是什么好的教育方法。舉例說,孩子愛玩手機,僅僅是禁止能有什么用?想玩的孩子還是想玩。想玩的心沒有變,問題就沒有真正解決。“愉而不偽”“素而不飾”(《淮南子·本經訓》),是人之初始就具備的天賦。家長要謹防自家孩子喪失這樣的天賦。
二、禁于未發,不能坐等勢大再設法解決
夫鴻鵠之未孚于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凌乎浮云,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褰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騖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
——《淮南子·人間訓》
就算是鴻鵠這樣的大鳥,在其尚未出生以前,也能輕易傷其性命;待到其羽翼豐滿,就算有高超的射術,并假以兵器之利,也往往對其無可奈何。類似的,就算寬廣如長江,其源頭部位也只不過一條窄窄的溪水。這兩樁事實,共同說明了一個道理:凡事在初始時,都比較容易干預。既然在源頭部分更容易干預,那么一個自然的推論就是,問題要及早發現、及早干預,最好能消滅于無形。“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圣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①從這段引文可以窺見《淮南子》與黃帝思想的聯系:“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兵,不亦晚乎?”(《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姚春鵬譯注:《黃帝內經》,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2 頁。)(《淮南子·說山訓》)可惜的是,在問題剛剛發生時,普通人恰恰容易忽略它;非要等問題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人們才會看到問題的嚴重程度。此時,問題已然開始棘手,解決問題的難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患至而后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淮南子·人間訓》)等到病入膏肓才開始尋醫索藥,就算是扁鵲、俞跗那樣的名醫圣手也無可奈何。我們平常所說的“一葉知秋”“千里之堤,潰于蟻穴”②“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淮南子·說山訓》)“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淮南子·人間訓》)這些《淮南子》里的成語,表達的都是同樣的道理。實際上,《老子》所謂“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強調的就是這種順勢而為,而并非真的無為:從成事的一面來說,要從細處入手;從預防的一面來說,也要從細微處著眼。“人皆務于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淮南子·人間訓》)聰明人不能只是忙于解決問題,而要防患于未然。
在家庭教育中,最常見的一種提問方式是:“我的孩子如此這般,請問我該怎么辦?”這種對“怎么辦”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讓人頭疼的事情就在眼前,哪還有閑情逸致追根求源?可是,這種提問方式恰恰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眼前的問題,源頭并不在眼前。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式的速效方案,在家庭教育中往往不得要領。上引《淮南子》中的這段話告訴我們,問題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并且解決問題的黃金時機就在問題剛剛露出苗頭的時候。也許有人會說,這道理固然沒錯,可是之所以家長難當,不就是因為這樣的“苗頭”難以發現嗎?其實不是這樣的。很多時候,我們明知不對,可又因為為時尚早,覺得一切都還不要緊。舉例來說,有的孩子愛出風頭,凡事都要顯擺自己;有的孩子霸道,自己理虧就用強;有的孩子看著好好的,可是幾乎從不和家長交流。所有這些,都是眼前看著沒什么,長遠來看會出問題的狀況。家長并不是看不到,只是眼下不當回事。如果讀了《淮南子》這段話,家長就不會直接問怎么辦,而要想一想自家孩子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不愛和家長說話的。“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淮南子·說山訓》)解決問題的過程,也遵循同樣的原理。當親子間已經不再和諧,再寄希望于某個教育秘訣,期待有一個法寶可以一劑而愈,這是幻想。在解決家庭教育問題上,適當的預期是那種長期、一貫的努力。
三、大處著眼,不總在細節問題上打擊人
屈寸而伸尺,圣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丑,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圣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于息,不可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
——《淮南子·氾論訓》
大義無虧,小節上不妨有所伸縮。這樣做,人行事時才不會那么僵硬,仿佛隨時隨地都要和人碰得頭破血流的模樣。上面這段話,以周公和齊桓公為例來說明這個道理:二人都做過可為人詬病之事,可是周公最終守住了大義,齊桓公則以功業掩蓋了自己的過往。人們終歸不會因為二人此前的過錯就否定他們。這段引文中的“目中有疵”“喉中有病”之類,都是些無傷大雅的毛病。既然整體上看并沒有妨礙,就大可無視它們。這就是“小惡不足妨大美”(《淮南子·氾論訓》)。最后一句話可以認為是概括和引申:如果領導者只關注屬下的言行,期待屬下周到殷勤,反而忽視他們實際的工作成績,這就是在舍本逐末。《淮南子·道應訓》中引用了《呂氏春秋》中寧戚(即《淮南子》中的寧越)干齊桓公的故事,表達了同一個道理①“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仆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呂氏春秋·離俗覽第七·舉難》)(陸玖譯注:《呂氏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寧越是春秋時衛人,齊桓公任其為上卿。齊桓公在任用寧越以前,身邊的臣子都來勸諫,建議齊桓公派人到寧越故鄉走訪一二,以便更準確地了解寧越的為人。齊桓公回答說:“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既然認準了寧越非比常人,就不要介意寧越可能有的那些小毛病。這種用人上的包容之道,和上面這段話中的“小枉而大直”遵從同一個道理。《淮南子·氾論訓》中記載了兩個相反的案例。正向的例子是曹劌,他曾經三戰不勝,但是“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最終得以戰勝齊軍,一雪前恥。(“一鼓作氣”這個成語就來自曹劌此戰。)反向的例子是季襄和陳仲子。二人“不食亂世之食”,結果生生把自己餓死了,這就被認為是“小節伸而大略屈”。
在家庭教育中,常有一種“別人家孩子”的錯覺。因為距離更親近,我們看自家孩子,更容易看到細節;看別人家的孩子,更容易得到整體判斷。更何況,家庭教育中需要家長督促的部分又實在有點多,結果家長面對自家孩子很容易不淡定。一面勞心勞力,一面又不容易得到孩子的歡心。《淮南子·繆稱訓》上說“水濁者魚噞”,又說“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養魚的人,不能總去攪和水;遠行的人,不能總是鞭打馬兒。對于自家孩子的教養問題,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如果家長總在孩子耳邊念叨,恐怕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讀《淮南子》,可以得出一條一以貫之的建議:凡事從大處著眼,只要孩子整體發展仍處于健康良性的軌道上,細節問題可以不必那么介意。舉例來說,對初學寫作的孩子來說,如果一開始就高標準、嚴要求,跟他說這也不對、那也不好,我想這并不是一個好的教法。只要孩子愛寫,喜歡用文字的方式來表達自己,那就是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上。至于遣詞造句、布局謀篇,大可以等以后再說。類似地,書寫、閱讀也是如此。有一個孩子,到了四年級還要在讀書時查字典,因為家長告訴他遇到攔路虎不能輕易放過去。家長的建議對不對呢?也許不好說不對,不過總歸不是我欣賞的。遇到生字就查字典,這樣讀書還會有趣味嗎?《淮南子》告訴我們,只要愛讀,就盡可以讀下去。愛讀書的孩子,就算不查字典,字詞最終也不會是問題。《淮南子·氾論訓》上說:“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家長如果能以這樣的眼光看待自家孩子,大人孩子都會輕松許多。
四、各得其所,相信不同才具的人各有所長
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于其所適,施之于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于廟牲,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
——《淮南子·齊俗訓》
《論語·季氏》區分了四類人:“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雍也》進而明確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陽貨》有另一段文字可作為補充:“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概括來看,上智(生而知之)、下愚(困而不學)都不是教育的對象,唯有學而知之(孔子本人就是一例)、困而學之者,才是教育的適宜對象。也正因為如此,整部《論語》是以《學而》篇為首的。人有才具差異,這一點《淮南子》是認同的。但是,《淮南子》并不認為這種才具差異等同于高下之分。這是《淮南子》與《論語》在人才分類觀上的重大差異。首先,上面這段引文中的一系列比喻,都在表達同一個觀念:巨木雖大,不適宜剔牙;簪子雖精美,不適宜為棟梁;馬不適宜負重,牛不適宜奔馳;其他如鉛、銅、鐵、木,均各有其適用之處,也都有其不適用之處。這些比喻,意在表明人的才具高低并非關鍵,關鍵在于能否得其所。“天下之物,莫兇于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淮南子·主術訓》)①書中還有其他類似的例子,比如:“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兇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圣人制其剟,材無所不用矣。”(《淮南子·繆稱訓》)這里的“無所不用”和《莊子》里的“無用之用”不是一回事。看起來最沒用的東西,只要放到適合的地方,就能發揮其效用。這是從正面來說的。從反面來說,“以斧劗毛,以刀抵木”(用斧子剃毛發、用小刀伐巨木),就是沒有用對地方,結果才具發揮不出來的情況。《淮南子·泰族訓》把天下人才區分為英、俊、豪、杰四大類:“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杰。”但是,在這種人才分類觀的背后,是更深層次的人才平等觀:無論是英俊還是豪杰,都要各得其所才能發揮作用;否則,才具再高也未必能建功立業。所謂“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就是這個意思。這種人才分類觀與《論語》中那種對才具高下的強調是十分不同的。這也是《淮南子》總體來看更近于道家,而并非儒家的一個原因。
在家庭教育中,家長容易出現兩個“看不見”:第一是看不見孩子的資質差異。遺傳和環境是兒童發展的兩大要素。教育至多是環境因素中的一部分。我們都期待自己的孩子有著非比尋常的天分。可是,這種期待往往是出于善良意愿,大部分家長終歸要接受自己孩子只是一個平凡人的事實,小部分家長最終甚至不得不承認自己孩子的確要笨一點。自己的孩子有更大概率不是天才,這是很多人當了很久家長以后才能有的領悟。《淮南子》告訴我們,這并不意外。人群內部的才具差異,從來都是如此。不過,《淮南子》完全不消極,反而可以繼續給家長提供一點安慰和建議。這就不得不提到家長容易出現的第二個“看不見”了:看不見決定孩子前途的絕不僅僅是個人資質。《淮南子》告訴我們,重點不在于個人才具的高下,而在于找到適合自己發光的地方。生性淳樸的孩子,未必會比那些心生九竅的孩子過得差;反過來也是如此。如此來看,家長也許就會多一分放松、少一分緊張,在教養孩子的問題上少一分執拗。當然,這種從容并不意味著放棄努力。恰恰相反,“各得其所”也是要有所得的。真正要反對的,是不正視其才具基礎的那種不切實際的努力。要相信,世上不存在一種絕對占優的性格,找不到一種絕對成功的人生模板。基于《淮南子》的這種建議,我們就更能看到眼前的孩子,而不是一個我們心里想要的孩子。
五、結論:順勢而為
《老子》使用“有”和“無”這對概念,搭建了一個以“道”來統御一切的完整世界觀。這同樣適用于《淮南子》。首先,“域中有四大”:四大分別指“人(王)”“地”“天”“道”,四大是“有”。其次,“有生于無”。位于四大頂端的“道”是“有”,生于“自然”這個“無”。(《淮南子·天文訓》有“道始于虛廓”的表達。)“自然”已經是“無”,就此終結了追問的鏈條。在這里,“自然”扮演了一個必要的理論空位,它本身無法被定義,但是又必須用到。《老子》被稱作《道德經》,河上公把它劃分為“道經”和“德經”兩個部分。不過,在《老子》的世界觀中,“道”和“德”只是一層規范性聯系。“人”與“地”“天”并列,三者統稱萬物;萬物皆法“道”,“道”法“自然”。其中,“天”“地”與“道”的關系始終一貫,“人”與“道”的關系則尚未確定。不過,正因為“天”“地”始終合乎“道”,人才要去效法。在這個世界觀中,人的作用被極大地壓縮了。人可能合乎“道”,從而有“德”;也可能因大道廢弛,而失“德”。不過,人無論如何也無法左右“道”,反而無時無刻不被“道”所左右。《淮南子》繼承了《老子》這一世界觀,首篇即為《原道訓》。“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這是在告誡人們,凡事不能舍本逐末。如果一味用強,以為自己很有點小聰明,就可以罔顧事實、無視規律,結果必定會遭遇挫折。通篇讀下來,《淮南子》中反復強調的正是“道”這個主題。這樣看來,人在“道”面前,豈不是完全被動的了嗎?
《老子》中有“勢成之”這一表達,這是對“道”這個主題的演繹,給人提供了主動選擇的空間。“勢成之”代表了一種有自知之明的、去人類中心化的立場:人可以通過審時度勢有所作為。這里的“勢”,明面的意思是各種主觀和客觀條件的組合,暗含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總會實事求是,動靜舉止都符合客觀規律。《韓非子·難勢》有一段話:“慎子曰:飛龍乘云,騰蛇游霧,云罷霧霽,而龍蛇與蚓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3]這里的“慎子”指的是《莊子》中的慎到。《莊子·天下》對慎到的評論是:“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評價他呢?《韓非子·難勢》的反駁給出了答案:慎到以為任何人只要得了勢,都可以飛龍在天。反駁者卻認為,得勢固然重要,能夠乘勢而為的人也很重要。能夠順勢而為,是道家的積極有為之處。只不過道家的“人”往往是老子那種“隱君子”[4],所以才不會專門去強調人的因素。但是,講“勢成之”,總歸會講到人。而道家的“人”是智慧的,其智慧會用來認識“道”,而不會妄自尊大地用自己的一點智謀來替代“道”。“湯、武,圣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淮南子·主術訓》)道家在解讀這些古代賢人時,沒有強調他們的個人才能,而是強調他們的順勢而為。敬畏客觀規律,并且打算以全部聰明才智去發現和順從這些規律,這是道家與儒家的一大不同點。從兒童教育的角度讀《淮南子》,得到的相關啟示都與此有關。
從順勢而為這個命題出發,《淮南子》的上述教育智慧是可以連貫起來的:尊重、鼓勵孩子的自然情感,這是一種順勢而為;見微知著,及早干預問題,這是一種順勢而為;從大處著眼,重視整體走向,這是一種順勢而為;正視孩子的天賦,實事求是做出努力,這同樣是一種順勢而為。《淮南子》告訴家長,不要固執于自己的主張和想象,而要實事求是、遵循客觀規律去教育孩子。《淮南子·時則訓》花了大量筆墨,描繪有德天子在各個時節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比如什么時候禁止伐木、什么時候禁止捕殺母獸、什么時候可以筑城、什么時候適宜決獄,等等。這些文字,不僅可以從現代自然科學的角度來閱讀,也完全可以把它們與“勢”這個概念結合起來看。有別于儒家的“禮”,道家的“道”并非一套人們共同遵守的規則,“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各就其勢,不敢更為”(《淮南子·說山訓》),也就是這里所說的順勢而為,才是妥當的立場。“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淮南子·繆稱訓》)今天,不愛自己孩子的家長怕是不多。可是為什么“親子叛父”的事情并不罕見呢?原因仍在于“道”與“勢”。如果不能敬畏“道”從而順從“勢”,就算下定決心要好好愛自家孩子,也未必就真的在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