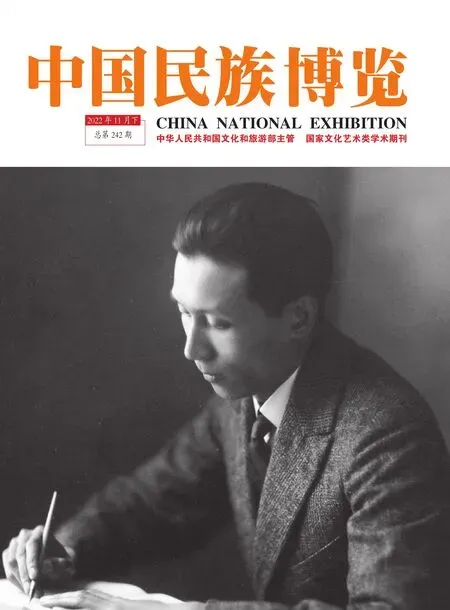北方曲藝三弦伴奏中的“變”與“不變”
——以岔曲伴奏為例
陳 楚
(中國音樂學院,北京 100000)
一、概述
三弦,又稱“弦子”,中國傳統彈撥樂器。音箱木質,扁平近橢圓形,兩面蒙皮(蟒皮),俗稱“鼓頭”。以琴桿為指板,無品,張三條弦,按四、五度關系定弦(見圖1)。[1]
三弦為曲藝音樂伴奏歷史悠久,《評彈通考·書場》中記載:“說書有文武之別,說文書者,一人曰單檔,二人為雙檔,手彈三弦,且說且唱……”[2]由此可見,三弦在明清兩代被眾多的說唱曲種作為伴奏樂器,頻繁地出現于各個書場的表演舞臺上。
我國北方曲藝三弦作為流行于我國北方各大曲種中最主要的伴奏樂器,是我國曲藝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服務于曲藝音樂演唱,遵循著曲藝音樂“依字行腔”的創作核心,很好的保存了我國傳統曲藝音樂的原貌,原汁原味地展現了我國傳統曲藝音樂的文化精髓。
二、曲藝三弦伴奏音樂分析——以岔曲為例
岔曲作為單弦曲種中的一種獨立體裁,以抒情寫景式的小品被大家所熟知,演出中常作為墊場節目出現。岔曲結構短小,伴奏規整,通俗易懂,變化少,容易掌握,學習過程中常將小岔曲作為曲藝音樂學習的開端,便于初學者了解唱奏關系,為下一步的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演唱時,只用一把三弦伴奏,演員自打八角鼓,由此可見,三弦在岔曲音樂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岔曲分為“小岔曲”和“大岔曲”:小岔曲結構較為短小,音樂遵循六八句原則,即詞句為八句,樂句為六句,詞句與樂句交錯,樂句由三弦伴奏的過門分開。
雖然在實際演唱過程中,不同的演唱者會根據自身的演唱習慣和個人喜好有所變化,但三弦伴奏的基本旋律框架和唱詞所對應的節奏是穩定不變的。小岔曲唱詞與三弦伴奏關系如下:

?
大岔曲則是“在‘小岔曲’的格式中,額外插入若干‘數子句’(由若干五字句和七字句組成),而形成一種大型結構的岔曲”。[3]
岔曲中的三弦伴奏音樂包含過門、隨腔伴奏、臥牛、數子句和結尾五個部分。
(一)過門
過門分為大過門和小過門兩種。
(1)大過門:分為曲中的大過門與開頭的大過門兩種,二者旋律基本相同(如圖1):

圖1 岔曲三弦伴奏大過門
(2)小過門:是大過門的片段(見圖2),主要用于樂句與樂句之間的連接,在學生練習或者排練溜活兒時,弦師也常用小過門起。

圖2 岔曲三弦伴奏小過門
(二)隨腔伴奏
可分為伴奏基本旋律和拖腔伴奏兩個部分。
1.伴奏基本旋律
唱腔部分的基本旋律骨架是確定的,雖然“加花”后存在許多變體,但基本旋律框架與唱詞的對應是不變的、音樂的氣口和韻律是不變的,可謂“萬變不離其宗”,旋律具有很強的穩定性(見圖3):

圖3 岔曲三弦伴奏旋律骨架
2.拖腔伴奏
樂句的每一句在結束處都有拖腔伴奏,拖腔伴奏后接大小過門。拖腔伴奏也同樣具有非常強的穩定性,基本上適用于所有的小岔曲的唱段。
(三)臥牛
曲藝音樂術語,常用于岔曲中。“臥牛兒”是“跌”(疊)一下的意思,是在曲調進行上安排的小轉折。使用方法是在岔曲后半段中某一下句唱詞的半句處,在演唱上處理成帶有半結束性質的下行句,唱腔稍作停頓,加上小過門后,再接唱下半句。接唱時多為重唱一個字。[4]在曲藝三弦伴奏中,臥牛分為兩種:硬臥牛和軟臥牛。
(1)軟臥牛:運用了偏音,小二度重復的環繞音型,旋律較婉轉,常用旋律為:

圖4 硬臥牛常用旋律
(2)硬臥牛:運用了純五度的大跳,單音重復,旋律較為平直,常用旋律為:

圖5 軟臥牛常用旋律
(四)數子句
是大岔曲中用于描述情節、事物時常用的一種節奏較為規整,語言性、節奏性較強的擴充段落。“數子句”以兩小節為一個基本單位,最基本伴奏的旋律是的重復,第二小節的第二拍是斷句的位置,伴奏的節奏會發生變化,變為(見圖6)。

圖6 “數子句”基本旋律框架
樂句與數子句的連接旋律(如圖7),首先進入散板、漸慢,之后“1”單音重復,逐漸變得密集打搓,最后進入線條性旋律,以“5”的上滑音為標志,開始進入數子句:

圖7 樂句與數子句的連接旋律
4.結尾:結尾部分的旋律較為固定,彈奏沒有太大的變化(如圖8):

圖8 岔曲三弦伴奏結尾
四、岔曲伴奏中的萬“變”不離其“宗”
上文介紹了岔曲三弦伴奏音樂的基本旋律,然而弦師在演出中的實際伴奏也并非完全如此。岔曲三弦伴奏具有非常強的包容性,能夠適用于不同演奏程度的弦師——它的基本旋律簡單,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對于初學者而言容易上手。但其演奏技法十分豐富,二度創作空間非常大,資深弦師會根據演唱隨機應變,具有非常強的靈活性。這一部分中,筆者將談談岔曲伴奏中的“變”。
(一)大過門中的“變”與“不變”
大過門的旋律結構基本為兩個小過門加入中間旋律。筆者記錄了兩個版本的大過門(見圖9),通過對比不難發現,兩種大過門主要的不同之處就在中間部分,筆者已用黑框畫出,岔曲大過門(二)中的旋律比岔曲大過門(一)中多了一板,旋律得到了擴充,筆者所列舉的只是自己學習階段能夠達到的程度,許多資深、有經驗的弦師在伴奏過程中會將旋律進一步擴充。大過門的旋律中最為穩定的片段就是小過門旋律。

圖9 兩個版本大過門對比
除了旋律的擴充,還有演奏技法的豐富以及節奏的細化,如圖10 中所示,大過門的中間部分的,由單音的彈奏變為了打搓,強調了附點節奏的重音,同時加強了短音與后面旋律的連貫性。之后細分節奏的與基礎旋律中的相比,減少了一個氣口,同樣增加了樂句的連貫性。
(二)基本伴奏旋律中的“變”與“不變”

圖10 小岔曲伴奏第一句對應的唱詞
岔曲的基本伴奏旋律存在許多變體,筆者在此略舉幾個例子(見圖11)。

圖11 岔曲三弦伴奏旋律骨架及其變體
隨著伴奏技術的的不斷進階,伴奏弦師會根據演員的唱“自由發揮”,豐富伴奏旋律,同一唱段也會出現不同的伴奏,常見的手法有改變八度和加花伴奏,如圖12 中所示,小岔曲《春至河開》中“綠柳時來”這一句的“時”字,三弦伴奏高八度彈奏了兩拍的細分旋律,音響效果上增添了幾分明亮和動感。

圖12 小岔曲《春至河開》中基本旋律的加花變奏
以上筆者僅僅分析了岔曲三弦伴奏基本旋律最普遍的階段性變化,在熟練掌握以上變化之后,弦師會根據自身能力進行更為復雜的變化,例如加入滑音、隨腔演奏旋律等,使得旋律在聽覺上更為豐富、生動。
(三)數子句中的“變”與“不變”

圖13 數子句的基本旋律及其變體
五、岔曲伴奏音樂中的“唱奏合一”
上文中我們總結了岔曲伴奏音樂中的“變”與“不變”,作為岔曲伴奏的承載者——弦師,其彈奏的中心目標是演員,一切的變化都是因演員的演唱而產生,所謂萬“變”不離其“宗”,伴奏的“變”來自于唱腔的“宗”,弦師的“變”來自于演員的“宗”。白鳳巖《曲藝音樂研究》一文中第四部分“曲藝音樂伴奏”中特別提到了弦師與演員的關系問題,作者指出伴奏音樂首先要做到的是幫助唱腔表達內容感情,要服從于唱腔。其次伴奏音樂要彌補唱腔中字句間隔的空隙,給演員以換氣休息的時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演員與弦師必須互相照顧,不能各顧自己。[5]因此,弦師所需要具備的基本素養除了扎實的基本功、了解唱腔之外,與演員的配合也是需要學習和鍛煉的重要功課。演員和弦師在長期的配合中,培養默契、取“長”補“短”、彼此磨合,由此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演唱、演奏風格,為觀眾呈現出十全十美的演出,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大而全的審美需求。
“開口唱”是了解唱詞、唱腔和斷句的必經之路。弦師在伴奏時既要專注自身的彈奏,又要熟悉演員的唱腔。既要作為局內人,與演員一同詮釋角色,又要作為局外人,幫助演員更好地演出。既能將旋律送到演員嘴里,又可以從演員那里接過旋律。因此,弦師對于音樂的整體把控尤為重要。好的弦師常常能從音樂的角度為演員提出建設性意見,甚至幫助演員設計唱腔,更好地詮釋故事內容。以駱玉笙為例,17 歲改唱京韻大鼓,1934 年拜韓永祿為師,學習劉派大鼓曲目。其間韓永祿并沒有生硬地照搬全教,而是根據駱玉笙的音色特點,兼采白派、少白派之長,為她設計獨特唱腔,形成了獨特的“駱派”風格。
除此之外,筆者在梳理資料時發現,許多曲藝大家是從三弦伴奏開始學習,潛心研究曲藝音樂的唱詞唱腔、音樂表達,總結經驗,最終成為被大家熟知和喜愛的曲藝大師。就以“鼓王”劉寶全為例,幼年時隨父親撂地演唱,為其父三弦伴奏。之后接受了弦師韓永忠的建議,登臺演唱,陸續拜曲藝大師胡十、宋五、霍明亮為師,并為其伴奏。倒倉期間,劉寶全除了用心為師父伴奏之外,還將大量精力用于認真研究京韻大鼓的唱詞唱腔、身段表演上。嗓音復原后劉寶全重新登臺演唱,開始嶄露頭角。劉寶全一直致力于京韻大鼓唱腔唱法的革新,其行腔、節奏等方面的技巧較之前輩們有了大幅度的改變,個人特色日益鮮明。同時,劉寶全也培養了大量的三弦伴奏人才,如白鳳鳴、韓德榮等。由此可見,三弦琴師在曲藝音樂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面對不同的演唱者,弦師要對自身的伴奏進行合理的調整:當面對初學的演唱者時,弦師往往表現得較為強勢,用伴奏要穩住演唱者,絕不能讓演員帶著伴奏走。對于具有豐富演出經驗的成熟的演唱者,弦師經常與演員互動,根據其內容及情緒的變化對自身的伴奏進行調整。所謂“托腔保調”,即襯托唱腔、保帶調門,在實際演出中,弦師往往要是先“保調”再“拖腔”。并且“保調”是對唱腔的規約與限制,而“拖腔”則是在此基礎之上的激揚與發揮。[6]這時,配合尺寸的拿捏尤為重要——不可喧賓奪主、本末倒置。
六、結語
綜上所述,曲藝三弦伴奏音樂具有很強的穩定性與靈活性:穩定性來源于各曲種穩定的旋律框架;靈活性來自演員的即興表達,演員是弦師關注的焦點。弦師作為曲藝伴奏的重要載體,除了掌握精湛的演奏技藝,更要起到掌控全局的重要作用——既要作為局內人,與演員一同詮釋角色;又要作為局外人,幫助演員呈現更完美的表演。伴奏服務于唱腔是曲藝三弦伴奏的核心,曲藝音樂遵循“唱奏合一”音樂傳統,伴與唱緊密相連、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