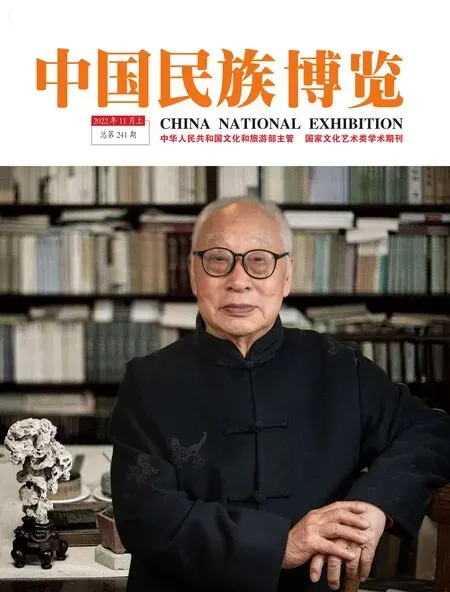北魏商業經濟發展探析
吳潤寰
(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重慶 401331)
鮮卑原為北方一個少數民族,經濟以游牧經濟為主,后統一北方,建立魏政權,開始筑城定居,農業經濟開始發展起來,農業經濟的發展又為商業經濟的發展打下基礎。本文試圖梳理北魏商業經濟發展脈絡,對認識鮮卑民族漢化和北魏王朝發展興衰具有重要作用。
一、北魏商業經濟發展的基礎
鮮卑民族自公元386年定都平城后,一直處于較和平時期,戰爭較少,統治階級重視發展農業上產,息眾課農,把勸課農桑作為基本國策,大力發展農業、畜牧業。同時,北方經過連年征戰,民生凋敝,人民百姓也渴望恢復生產,為北魏經濟發展營造了一個有利的社會環境。
(一)統治階級的重視
拓跋鮮卑作為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后,極力發展經濟以鞏固政權,穩定人心,同時為其開疆拓土提供保障,因而北魏統治階級十分重視經濟恢復與發展。作為傳統游牧民族,首先對畜牧業極為重視,通過一系列兼并戰爭,奪取大量牲畜和牧場,畜牧業發展較快。定都平城后接受漢化思想,重視農業發展。如拓跋珪“各給耕牛,計口授田”,[1]馮太后“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1]太和十年(486年)采納李沖的建議,實行三長制,厘定賦役稅收。
鮮卑民族受中國傳統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較小,因而對商業抑制較小,如拓跋珪“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1]即表明北魏并未抑制商業發展。平城當時專門設市,以供商業交易。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下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太[1]和十九年(495年)統一度量衡,促進了北魏商業發展。
(二)畜牧業和農業的發展
畜牧業是鮮卑民族的傳統支柱產業,自拓跋珪定都平城后,并未忽視畜牧業的發展,通過對高車等其他游牧民族的戰爭,擄掠了大量牲畜。如天興二年(399年)拓跋珪大破高車等部,獲“馬三十余萬匹,牛羊百四十余萬”。[1]至拓跋燾“遣軍襲擊東部高車,其獲馬、牛、羊百萬多匹(頭)”。[1]建立漠南、河西、河陽牧場,規模盛大,并設置專門機構管理,可見北魏畜牧經濟之盛。
自建都平城后,從畜牧經濟向農業經濟轉變,計口授田,并于太和九年(484年)頒行均田制,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口增長迅速,“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焉”,[1]據此則北魏實際人口已達三千萬以上,可見人口之盛,市場廣闊,為商業經濟發展提供了經濟、市場基礎。
(三)水陸交通的發展
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平城通往冀州的恒山直道的開通。道武帝天興元年(398 年)正月,發卒萬人鑿山通道,打通了穿越恒山山脈和聯系中山與平城的道路。拓跋燾時,又于太延二年(436年)修通了莎泉道。文成帝于和平二年(461年)“發并肆、五千人,治河西獵道”。[1]與之相對的水上交通也發展起來,修治了利用黃河從河西至沃野鎮的水道。這些水陸交通要道的開通,把北方重要城鎮連接起來,極大的促進北魏商業貿易發展。
北魏還同西域諸國保持貿易關系,漢代的“絲綢之路”仍然相當繁華,是一條重要的國際商道,許多中外商人通過此路發展貿易交流,是北魏對外商業發展的重要通道。
二、北魏商業經濟發展的表現
(一)從事商業人口的增加
商業經濟發展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從事商業的人口大量增加。河東太守元淑說“俗多商賈,罕事桑農,入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2](可見從事商業人數之多,出現了像劉寶等富商巨賈,分號幾乎遍及全國,頗有現今連鎖經營之方式。據《洛陽伽藍記》記載,這些大工商業者“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金銀錦繡,仆隸畢口”,[3]足見其財力雄厚。在這個時期,除了官商以外,經商的還有上至貴族、官僚,下至平民白姓各個階層的人物。由于當時貿易發展的刺激,一些“高貴”的人們也與民爭利,經起商來,一時間貴族、官僚經商成風。李崇“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1]拓跋浚時“牧守之官,頗為貨利”。[1]
(二)城市的發展及市的出現
因戰爭被破壞的城市,在北魏時期也正在興起,并逐漸恢復繁榮。例如洛陽、長安、平城、鄴等城市都具有相當的規模。“商業依賴于城市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受到了一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4]北魏數次移民充實京師人口,天興元年(398年)“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徙河、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技巧十余萬口,以充京師”;[1]后又繼續移民,到獻文帝時較大規模移民八次,前后移民達百萬口之多,對于平城城市的發展和商業繁榮有重要作用。
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后,洛陽不僅是全國政治中心,又是商貿中心,成為當時全國乃至東亞最大的商業中心。洛陽的市位于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回八里”。[3]而且市規模較大,“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3]“市西有延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3]“市北有慈孝、孝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輀車為事”;[3]“別有阜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3]“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3]將市分門別類,已經可見商業的集中化,足見洛陽商業繁榮。又“別立市于城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3]設于洛水和伊水交匯之處,臨四館等降附者及少數民族,以方便西域胡商交易,又“伊洛之魚,多于此賣”,[3]是洛陽水產交易市場,“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3]城東“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市”,[3]面積較小,城北不設市,但“京師瓦器出焉”也表明是一出磚瓦買賣集中地。洛陽大市、四通市、小市等專業市場齊全,規模龐大,商品繁多,南朝、西域 ,甚至大秦等國外商品也流通較多,洛陽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長安自古即是著名的商業都市,“廄庫未實,則通好于西戎,商胡販客,填委于旗亭”,[5]可見長安胡商云集,商業繁榮。洛陽市設市令管理市場,并征收市稅,“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表明洛陽商業發展已有完整系統。
(三)貨幣的出現
北魏初期貨幣使用很少,沿用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但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貨幣出現了,貨幣的出現表明北魏商業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高度。太和十九年(495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1]“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1]通過兩次鑄錢,解決了一部分錢荒問題,但是新鑄錢幣數量有限,部分地區仍用舊幣和絲織品,不能有效解決貨物交易問題。熙平二年(517年),北魏采取崔亮的建議,廣開銅礦鑄幣,但私鑄錢幣粗制濫造,質量低劣,以致出現“商貨不通,貿遷頗隔”。[1]不論貨幣質量和數量如何,政府發行貨幣是肯定的,雖對商業造成多少混亂,但北魏商業的發展卻未受較大影響,任然是商業發榮的體現。
(四)對外貿易的發展
北魏時期的對外貿易,雖然沒有以后隋唐那樣繁榮,但也取得不小的成績。同日本以及朝鮮半島上的高麗、百濟、新羅等東方諸國常有來往,日本“自魏主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6]高麗在拓跋賺時,也和北魏開始了往來。北魏同西域各國也有貿易關系,當時西域商人往來者甚多,例如,吐谷渾“體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2]北魏河西各郡大量使用西域出產的金銀器物,如河間王元深宴請諸王的瘤器、都是西域所產,極其精美。北魏還同西方中亞等國有來往,“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余家。門巷修整,閻闔填列,青槐陰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季在焉”。[3]充分表明北魏對外貿易的繁榮,西域胡商往來不絕,所居洛陽者不可勝數,甚至有專門為胡商所建的房屋供其居住。
三、北魏商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總之,隨著北魏政權的穩定,畜牧業、農業經濟的發展,鮮卑民族的觀念發生轉變,商業經濟開始迅速發展起來。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北魏的商業發展經營模式靈活,管理較松,這對北魏經濟繁榮及同周邊地區的經濟交流和友好關系的起到積極作用。
自遷都洛陽后,隨著鮮卑民族漢化的不斷深入,思想觀念的普遍轉變,商業經濟又有了很大發展,為隋唐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隋唐商業的繁榮也與北魏商業發展不無關系。但隨著商業迅速發展,當時北魏出現一種極壞的風氣,貴族官僚熱衷于經商,獲利后開始安于享樂,致使朝政腐敗,奢侈攀比成分,極大損害了北魏政權的統治。
四、結語
北魏作為第一個統一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一直積極學習漢文化,在統治階級的努力下,實現了從草原游牧經濟到封建農耕經濟的轉變,為商業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一切促使北方經濟發展超過南方,為隋唐統一中國打下雄厚經濟基礎。統治階級作為鮮卑民族,受重農抑商思想影響較少,積極重視商業發展,大力興修水陸交通,同周邊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聯系加強,極大的豐富了人民生活。從此,鮮卑民族漢化不斷加深,變成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